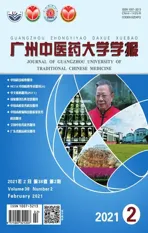基于数据挖掘探析《内外伤辨惑论》的组方用药规律
2021-01-21张伟健李勉力陈新博黄彦子李海文李京伟康建媛郭绍举
张伟健, 李勉力, 陈新博, 黄彦子, 李海文, 李京伟, 康建媛, 郭绍举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广东深圳 518033;2.深圳市中医院消化科,广东深圳 518033)
《内外伤辨惑论》为“脾胃学说”创始人李东垣的奠基之作,也是唯一一部由他本人定稿并作序的著作[1],该书除了详尽阐述外感病与内伤杂病的“辨别十二法”外,还根据内伤脾胃病的发病特点创制了诸如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名方,在遣方用药上颇具特色[2]。目前业内围绕此著作的辨证诊断经验已经做了一定的探讨[3],但对其构方思路的研究仍显不足。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是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开发的以中医数据为核心的分析软件,该软件集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网络科学等学科方法和技术于一身,能够有效避免既往单纯依靠频次统计来分析经验的弊端,对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4-6]。本研究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运用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复杂系统熵聚类以及改进的互信息法等[7-9]数据挖掘方法对《内外伤辨惑论》中的药物基本信息、核心药对组合和组方规律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把握李东垣的学术思想,并为现代中医临床诊治脾胃系疾病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处方来源和预处理所有处方均来自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年出版的《内外伤辨惑论》[10],共收集到处方46 首;参照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1]对筛选出来的46首处方中涉及的中药名称做统一规范化处理,如将“官桂”统一为“肉桂”,将“橘皮”统一为“陈皮”等;将药典中未收录,现已不入药用的中药予以剔除,如“脑子”等。
1.2数据录入将上述筛选出的46首处方的方剂名称和药物组成逐一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系统的“方剂管理”模块,采用2人双录入双审核的方法,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8]。
1.3数据分析
1.3.1 频次统计分析 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统计报表”模块中找到“方剂统计”功能,点击“基本信息统计”,将方剂中所有中药的出现次数、四气五味及归经情况进行统计,并按使用频次从高到低的排序进行数据的导出。
1.3.2 组方规律和新方分析 在“数据分析”模块运用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复杂系统熵聚类和改进的互信息法对目标处方的核心药物组合和组方规律进行分析,逐渐提高“支持度”和“置信度”以剔除周围药物,使核心药物组合明确。本研究将“相关度”设置为8,“惩罚度”设置为2,运用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提取新处方,并对结果进行网络可视化展示[12]。
2 结果
2.1频次统计分析
2.1.1 用药频次分析 共收集到46首方剂,涉及中药79味,使用频次共363次。使用频次≥7次的中药共22 味,其中白术使用次数最多,其次为陈皮、炙甘草、人参、枳实、神曲等;频次和频率(频次/46×100%)分布见表1。

表1 《内外伤辨惑论》方剂中使用频次≥7次的中药分布Table 1 Distribution of herbs with the frequency being and over 7 times in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次(%)]
2.1.2 药物性味及归经分析 系统提取出的79味药物中,药性分布主要为温、寒、平、热、凉,其对应频次依次为204、79、30、20、6 次;药味主要分布为甘、辛、苦、酸、咸、涩,其频次分布为205、169、153、28、2、2 次。79 味药物的归经共涉及12 条经络,排名居前3 位的依次为脾经、胃经、肺经,其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其他经络。《内外伤辨惑论》所载方剂的中药性味归经频次统计见表2。
2.2组方规律分析
2.2.1 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规律分析 应用Apriori关联规则算法,将置信度设定为0.9,支持度个数设置为8时,可得到《内外伤辨惑论》方剂中的核心药物组合14 个(见表3),出现频次最高的前3 个药物组合分别为“陈皮-人参”“白术-枳实”“陈皮-白术”。《内外伤辨惑论》方剂的核心药物组合网络展示见图1。
2.2.2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关联度分析 依据收集到的方剂数量,结合经验对参数设置在不同数值的结果预读[9],将相关度设置为8,惩罚度设置为2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药物组合的关联度。关联系数≥0.036 2的16对药对组合见表4。
2.2.3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潜在药物核心组合分析 根据相关度与惩罚度的相互约束原理,对药物间的关联进行复杂系统熵聚类分析,得到潜在的3味药物核心药物组合结果见表5。

表3 《内外伤辨惑论》方剂中的核心药物组合(支持度个数为8,置信度为0.9)Table 3 Core combinations in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number of support degree being 8,confidence degree being 0.9)(次)

图1 《内外伤辨惑论》方剂中的核心药物关联规则网络展示图Figure 1 Network diagram of accosiation rules of the frequently-used herbs in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

表4 《内外伤辨惑论》方剂中关联系数≥0.036 2的常用药对Table 4 Distribution of frequently-used herbal pair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ing and over 0.036 2 in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

表5 《内外伤辨惑论》方剂演化的核心药物组合Table 5 The derived core herbal combinations in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
2.2.4 基于无监督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分析 同样将相关度设置为8,惩罚度设置为2,根据相关度与惩罚度的相互约束原理,对表5中潜在的核心药物组合进行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分析,可演化出6 首《内外伤辨惑论》方药的新处方(见表6),新方的网络可视化展示见图2。

表6 由《内外伤辨惑论》方药演化的新方Table 6 New prescriptions derived from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

图2 由《内外伤辨惑论》方药演化的新处方网络展示图Figure 2 Network diagram of of the new candidates derived from the formulas of Differenti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iseases
3 讨论
3.1 《内外伤辨惑论》的用药特色及学术思想本研究共收集到《内外伤辨惑论》方药处方46首,涉及中药79 味,以辛甘温类药物及归脾、胃经的药物为主,少用寒凉类药物,归心包经的药物使用次数最少。其中使用频率较高(≥10 次)的14 味中药按照第2 版《中药学》[13]教材记载的功效主要可分为以下8 类:(1)健脾益气的炙甘草、白术、人参、黄芪;(2)行气消积的陈皮、枳实、木香;(3)消食和胃的神曲;(4)升举阳气的柴胡、升麻;(5)温化寒痰的半夏;(6)利水渗湿的茯苓;(7)补血活血的当归;(8)温中散寒的干姜。这些药物为“甘温除热”代表方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体现了李东垣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的学术思想[14-15]。值得注意的是,性味统计项中寒性、苦味类药物虽分别排在第2 位和第3 位,但其使用频率却仅占四气项的23.3%(79/339)、五味项的27.4%(153/559)。由此可见李东垣对于苦寒类用药尤为慎重,对于实火内盛或阴火过亢者才酌加寒凉泻火药,或以寒热配伍之法平调寒热,中病即止,忌大苦大寒亦或耗气散气之品,以防过寒败胃,耗伤正气[16]。如在《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中以黄连清膈丸治心肺间有热及经中之热,在《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四时用药加减法》中以黄连、附子治“心下痞、觉中寒”。此原则在现代临床实际中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随着现代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的改变,疾病的发病机制亦随之改变,如夏日贪凉饮冷、恶晒阳光、滥用苦寒抗生素等日积月累地消耗阳气,导致虚寒体质人群多见,故临证用药尤当注重补中升阳,慎用寒凉。
东垣先生认为“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内伤脾虚证皆不足之病,不足则补之,不可泻之[17-18]。至于其恶寒发热等“阴火”表现,李东垣认为此乃脾胃之气不足,清阳不升导致的一种火热邪气[16],“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生长之令不行,无阳以护其荣卫,不任风寒,乃生寒热[19]”(《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治疗上当以柴胡、升麻等味之薄者,引脾胃之清气行于阳道[20]。由此发展而来的“升阳散火法”“补土伏火法”在现代临床常见的虚寒性口腔溃疡的治疗中仍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中焦清阳不升,浊气下留于肾,使阴火上浮,与湿、痰、瘀等病理因素胶着而产生各种假实之证,因此,如何通过调理脾胃、消散阴火是治疗此类疾病的关键[21]。《内外伤辨惑论》中用药以“调和脾胃、益气升阳”为原则,补其中、升其阳、泻阴火,根据脾虚湿滞、痰结、气滞、食积、寒凝等不同的病变特点加减用药,标本兼治[22],体现了其对《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立法原则的传承。此外,李东垣还提倡通过顺应四时、调适饮食、劳逸适度的生活方式来顾护后天脾胃,以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目的[23]。
3.2 《内外伤辨惑论》的组方配伍规律根据药物间的关联规则,运用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和复杂系统熵聚类从系统中提取得到14 个《内外伤辨惑论》方剂的核心配伍组合(表3),使用频次≥9 次的9 个药物组合依次为①陈皮-人参、②白术-枳实、③陈皮-白术、④炙甘草-陈皮、⑤炙甘草-人参、⑥升麻-柴胡、⑦半夏-陈皮、⑧人参-黄芪、⑨白术-神曲。其中第2对药对(白术-枳实)来源于其师易水学派张元素的枳术丸。东垣先生自母亲去世后拜张元素为师,其学术思想深受张元素的影响[24]。李东垣依据对内伤饮食理论的理解,在枳术丸原方的基础上创制了半夏枳术丸、橘皮枳术丸等一系列类方[25],方中白术补脾益胃、燥湿和中,枳实破结消胀,二药合用,既补脾虚,又不忘消其痞积。可见,李东垣“发明脾胃之病,不可一例而推之,不可一途而取之”的《脾胃论》思想在此已初步形成[25]。第7对药对(半夏-陈皮),半夏配陈皮强化了燥湿化痰、理气和胃之功,现已在二陈汤、温胆汤等经典化痰方中得到广泛应用[26-27]。其余药对组合均为补中益气汤的药物组成。
风药的运用是李东垣的一大特色,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亦体现了这一要点。由改进的互信息法从系统中提取出的16 对关联系数≥0.036 2 的药物组合里,含羌活、防风、独活等风药的药对多达9对,如羌活-生地黄、羌活-郁李仁等,占总药对数的56.25%。李东垣之所以喜用风药,除了升阳之要义,还认为风药具有开郁、行经、胜湿等功效,故常配伍补益药、燥湿药等来治疗各种郁、痹、痛证[28]。现代临床常见的肠易激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具有“风乱”之象的疾病可参照此法治疗。
3.3 《内外伤辨惑论》的新方探讨根据相关度与惩罚度的相互约束原理,运用无监督熵层次聚类分析法可从《内外伤辨惑论》方药中演化出6首新处方[29],其中新处方4(炙甘草,陈皮,人参,甘草,黄芪)和新处方6(甘草,升麻,黄芪,白术,神曲)类似于补中益气汤的加减方,临床可用于脾胃气弱、气虚发热诸证。新处方1(青皮,猪苓,麦芽,白豆蔻)具有破气消食、利水化湿的功效;新处方2(羌活,白芍,枳实,防风)可柔肝祛风、胜湿止痛;新处方3(黄芩,木香,黄芪,黄连)可看作香连丸的加减方,有清热燥湿、行气止痛的作用,可用于治疗大肠湿热之痢疾。新处方5(砂仁,益智仁,姜黄,甘松)还可破血行气,温脾化湿,气血同调,兼护胃本。
总体来看,由《内外伤辨惑论》演化而来的新方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东阳在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的同时,还注重根据伤饮伤食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治法,如消食导滞,分消其湿或祛风胜湿之法等[30],但这些新方在临床上的运用报道仍属少见,其应用价值还需经过广大医家临证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