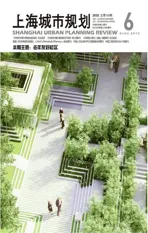上海城市色彩的空间特征初探
2021-01-21SHENLu
沈 璐 SHEN Lu
1 研究背景
色彩虽然是城市的古老命题,但却是现代城市研究中的新领域。色彩是客观存在的,但色彩感知是主观的。城市色彩具有传递城市精神、展现城市品牌、体现城市品质的重要作用,对影响民众的美学感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持续提升城市风貌和城市品质具有长远的意义。
1.1 落实上海新一轮总规的城市色彩要求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明确了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目标[1],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国务院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做好城市设计,彰显自然、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东西方文化相得益彰的城市特色”。
在迈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像绣花一样精细”地规划和管理城市正在成为上海品质化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在实施“上海2035”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这两大落脚点,在规划的细化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加强城市设计,重视城市色彩,让城市少一些钢筋水泥色调,多一些温暖、时尚和富有吸引力的色调。要着眼整体协调性,补齐影响发展质量和整体水平的短板”[2]。那么,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色彩基底到底是什么样?用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一张科学可信的上海城市色彩地图?城市色彩是否具有空间属性,是否与城市结构有关联性?一张具有说服力的城市色彩地图对上海城市色彩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具有基础性和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1.2 超大城市色彩研究的技术困境
1.2.1 城市色彩理论研究演进
现代色彩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德国数学家格拉斯曼(Hermann Günther Grassmann)发表的色彩定律,该定律分辨出了色彩三要素,即色相(hue)、彩度(saturation)和明度(value of lightness)。19世纪末,美国艺术家孟塞尔(Albert H. Munsell)基于色彩三要素,绘制了色立体,奠定了色彩学基石。进入20世纪,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色彩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视觉领域和产品设计中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色彩研究和色彩设计的主体才由艺术和商品进入城市环境领域,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过度工业化和商业化带来的城市色彩问题[3]。
城市色彩的研究萌芽散落在地理学、建筑学、景观学等多个学科门类中。20世纪60年代,色彩地理学首先由法国色彩学家朗克洛(Jean-Philippe Lenclos)①法国色彩学家让·菲利普·朗克洛(Jean-Philippe Lenclos)提出的色彩地理学理论受到广泛的传播,得益于城市规划领域在旧城保护方面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旧城保护的浪潮下,要求对传统建筑色彩环境进行积极保留和修复。提出,将色彩与地理特征进行耦合分析,“一个地区或城市应有自己独特的色彩特征,由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共同决定”,通过“选址、调查、取证、测色、归纳、编谱、总结”获得“城市色彩特质”的方法,形成了当代城市色彩研究的基本方法[4]。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的城市色彩研究延续了法国色彩地理学理论研究和思想,并通过提升测色仪器的科技水平,改善城市色彩研究的实证水平和色彩科学的准确度[5-6]。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景观学界②色彩景观理论是由英国景观学家、格林尼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景观建筑学教授兰开斯特(Michael Lancaster)提出的。兰开斯特教授在《色彩景观(Colorscape)》一书中阐述了色彩与空间、色彩与场所之间的关系,强调色彩彼此之间,以及色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展了色彩景观理论,主张“通过对环境中色彩因子进行控制性的设计来表现地域化、个性化的城市景观”。几乎同时,美国建筑学界专注讨论建筑色彩环境,包括建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的色彩问题③以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布拉德利大学艺术系主任林顿(Harold Linton)教授和建筑师西萨·佩里(Cesar Peli)为代表的建筑色彩研究者,在《建筑色彩:建筑室内和城市空间的设计》(Color in 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 for Building, Interiors and Urban Spaces)、《色彩研究》(Colour Consulting)和《组合设计》(Portfolio Design)等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色彩是除建筑形式和建筑空间以外,与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最重要要素”。。
城市色彩研究的诞生主要是应对旧城改造色彩秩序的重建。由此发展形成的理论和实证[7]基本限定在建筑、建筑群,以及建筑周边的景观环境;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城市微观范围已经非常成熟,但由于受到色彩主观判断的影响,色彩研究需要受到非常严格训练的色彩专家才能胜任。在城市宏观层面,尤其是超大城市的整体城市印象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体量和数量超大,现有的城市色彩认知方法基本无法满足。
1.2.2 上海城市色彩内容范畴
城市色彩因素包容广阔,并且借助各类形式的物理载体,存在于城市的方方面面。因此,城市色彩是实体要素通过人的视觉反映出来的相对综合和整体的色彩面貌,是城市空间内所有可见物体的综合色彩特征。按照城市空间特征,城市色彩可以分为自然环境色、人文环境色和人工环境色等类型。自然环境色主要包括:土地、山体、岩石、植被、江河湖海等;人文环境色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中偏好和禁忌的色彩,以及与此相关的日常服饰和节庆活动的装饰物色彩等;人工环境色主要包括建筑物构成的固定色、构筑物等构成的临时色,以及交通工具等构成的流动色,其中建筑物是城市中最重要的人工环境色。
上海与纽约、东京、伦敦在城市色彩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均位于北纬30°—50°之间,是中等光亮、地形平坦的超大城市。因此,这几座超大城市都具有“全色相、高明度、低彩度”的城市基调色④城市基调色是指城市物质空间呈现出的整体色彩印象。。从自然环境要素来讲,一方面,上海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四季分明、空气氤氲,与高光亮城市相比,中等光亮的照度使得城市呈现的色彩与天空色的反差较小,城市轮廓线不明显;另一方面,河网纵横、蓝绿交织,但缺乏明显的山体作为城市的背景色。从人文环境色而言,城市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城市色彩的复杂程度,包括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历史演进、人文流变等,超大城市难以形成单色相的城市基调色。因此,人工环境色是超大城市色彩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建筑公共立面的色彩所形成的整体印象是超大城市色彩现状中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2 城市色彩评估的感性方法和理性路径
城市色彩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营造令人愉悦的城市色彩环境。自中华复兴之际,蔡元培先生即提出“美育兴国”的理念,力求国家风尚能有兼容并包、融合中西、承继传统、创造当代的美育体系。作为城市研究的组成部分,城市色彩研究需要运用理性的技术方法,构建明确的价值理性和系统的工具理性,将复杂的、感性的城市色彩进行抽象化、数据化、图示化表达,以把握超大城市色彩的全貌。
2.1 大数据勾勒市域城市色彩全貌
本文研究范围为上海市域陆域范围,总面积为6 833 km²;重点研究范围为城市开发边界内已建成的区域。笔者使用了230余万条带有地理信息的城市街景影像数据。街景照片的优势是赋予城市景观以地理坐标,即将城市景观与城市空间进行衔接。
2.1.1 图片分割
计算机深度学习是城市色彩的大数据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工具。在处理230余万张街景图片时,先使用手动模式将图片中的空间要素进行分离,如建筑、植栽、行人、交通工具、街道家具、店招店牌等,将不同的类型图形赋予各自不同的属性标签并进行标记;再引入计算机学习算法,生成图片分割成果。通过场景分割(scene parsing)将街景影像中的建筑公共界面部分单独切割出来(见图1)。建筑公共界面的色彩是人工环境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超大城市的基调色。
通过统计每个位置上建筑在整个视野中的占比,构成“建筑视野率(V)”。上海市域建筑视野率的中位数是0.384,上限值是0.726,下限值是0.098。通过剔除视野中建筑比例过低的数据,筛选出V>0.098的有效数据,作为下一步建筑色彩分析的基础数据库。
2.1.2 色彩还原
图像显示中最常用的色彩显示方式为RGB混色模式,RGB色彩空间体系通过对红(R)、绿(G)、蓝(B)3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但是RGB模式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对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色彩呈独立不相关状态,无色彩还原能力。同样的原理还适用于CMYK混色模式。
HSV色彩模式是基于色相(H)、彩度(S)和明度(V)的色彩空间模式。HSV模式中色彩的连续性强,具有较好的色彩还原可能性(见图2)。运用自动白平衡(AWB)算法,对50%中性灰在各个色温下的色彩表现进行预处理,对HSV色彩通道进行矫正,获得红色增益(rgain)和蓝色增益(bgain)参数,拟合色彩偏移矩阵(见图2),对图像进行处理,使所有街景图片还原到不受光线影响下的情况,并使照射于不同光线下的海量图片具有可比性。
2.1.3 图像基调色的获取
经过图片数据切割和色彩还原后,按照像素进行色彩解析,统计每一张图片的色相、彩度和明度在色立体中的坐标向量。运用中位切分算法(median-cut algorithm),获取每张图片的基调色,将图像色彩看作是色彩空间中的长方体(VBox)来进行图像切分(见图3)。选出“体积×包含像素数”最大的长方体,将其代表的HSV色彩值作为该图像的基调色。
2.1.4 区域基调色的总结
在上海全域建成区范围内,以20×20 m网格为单位,按照图像的地理信息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归纳,计算每个网格代表的区域内的基调色。通过k均值聚类算法(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将网格区域内的基调色进行离散点聚类,将色相、彩度和明度3个变量分别进行聚类,形成3个聚类中心点,最终形成一个HSV值,即网格区域内的基调色。在上海市域空间上进行可视化处理,形成上海第一张“市域城市色彩地图”(见图4)。
2.2 追本溯源, 还原城市色彩形成过程

图1 街景照片的图像切割Fig.1 Image slicing of streetscape

图2 HSV数值矫正(以上海外滩5号日清大楼为例)Fig.2 Correction of HSV values(case of Bund 5)

图3 中位切分法获取图片基调色Fig.3 Color tone matching by median-cut algorithm
上海城市色彩面貌的形成与空间演变历程密不可分[9]。正是在中西文化参与、空间分片式拓展、建造技术与审美不断更替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形成今天上海复杂的城市色彩面貌,我们称之为“海派色彩”,可以分为“起”“承”“转”“结”等阶段。在上海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城市色彩在城市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复杂程度,同时通过规范城市空间秩序,形成有一定秩序感的色彩总体意象。

图4 上海城市色彩地图Fig.4 Shanghai city color map
2.2.1 开埠前水墨淡彩,富有整体感的色彩印象
“起”,即海派文化的酝酿期。海派文化遥远的承袭源于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一方面,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亲水性的特点,本质是一种动态文化,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为前提,故变异性就成为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吴越文化具有开放气质,上海西联内陆、东濒大海,自建城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
直至晚晴时期,上海城市色彩由封建等级秩序和建造技术所决定,色彩类型相对统一。本土民居扎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建筑材料技术,以四合院为雏形演绎出粉墙黛瓦的绞圈房子,材质以粉墙、黛瓦、青砖为主,基本以5YR—5Y的暖色相为基调色,明度不小于8.0,彩度小于0.5,是适合水边建筑的配色方式;点缀色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灵感,建筑构件部分运用G与BG类的“水色”。与朴素的传统民居色彩不同,晚清时期重要的园林建筑和公共建筑使用了大面积的红色木漆和红色清水砖等材料,基调色色相基本为5R正红,辅以金色纹饰点缀,形成了作为江南重镇的上海色彩繁华端庄的一面(见图5)。
2.2.2 租界时期海派杂糅,多元色彩的开端
“承”,即海派文化的生成期。海派文化正式形成是在19世纪后期,繁荣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商品经济、移民人口、西学东渐和租界影响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以上海最为突出,大多先传到上海,然后由上海扩散到中国其他城市,成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主要基地,奠定了上海城市色彩多元融合的海派特征(见图6)。
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设带有中西合璧的海派色彩。外滩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多为灰色和米色的天然石材建造。居住建筑方面,公共租界单元以石库门建筑为代表。石库门建筑以较高彩度的红砖为主要材料,改变了上海水墨淡彩的基调色。
法租界集聚了当时品质较高的住宅区,建设了大量的花园洋房和独栋公寓,比其他居住建筑类型都更为自由的选址以及跨越时空、文化糅杂的建筑形象,产生了具有近代特点的浪漫主义和消费主义特征,多采用奶白色、咖啡色、灰绿色等具有欧洲风格的中低彩度色系。
2.2.3 解放后简洁朴素,计划经济影响下的城市色彩
“转”,即海派文化的转折期。海派文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发生了变异。该时期,上海的城市风格发生改变,从外向、商业型城市转变为工业、内向型城市。建国初期,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上海,为配合生产城市建设,解决亟待改善的居住问题,在当时的城市边缘和规划区外围规划和建造了一批工人新村。最初的工人新村为低层或多层的行列式建筑,多采用灰白色涂刷墙面,一部分坡屋顶建筑采用了青瓦或红瓦。同时,在市中心和各卫星城镇中心也建造了一批公共建筑,建筑形式受国际主义风格影响,造型简洁,色彩朴素。城市整体基调色并没有较大改变。
2.2.4 改革开放后多元拼贴,再度复合化的色彩格局
“合”,即海派文化的更新期。改革开放后,海派文化迎来了自我更新的新时期,上海进入城市发展的快车道,高层建筑的比重大幅度增加。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陆家嘴中心区、古北新区等一批重点新区先后建设,商品房小区出现,采用水泥、瓷砖、玻璃幕墙等大量非天然材质,开始出现一些较高彩度的建筑色彩,如红色瓷砖、蓝绿色镀膜玻璃等,色彩更加丰富,城市色彩基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基调色秩序缺失,形成建筑形式纷乱、土洋混杂的局面。由于规划和建设“一次成型”,出现了“色彩斑块”现象。
进入21世纪,上海城市的建成范围趋于稳定。一系列重点项目的落地及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因。城市格局呈现出近域蔓延与轴向延伸的空间特征,初步形成大都市区的空间框架。城市建设进入品质提升时期,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水平大幅提高,世博会、临港、前滩、虹桥等为代表的重点地区具有较好的色彩品质。新建建筑以冷色调和灰度色为主,建筑改造、建筑刷新同步进行。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彩度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色彩老化、暗淡的情况,反而使城市色彩得到了明度和彩度上的调和。

图5 开埠前基调色、辅助色和点缀色示意Fig.5 Basic, auxiliary and embellishment color before 1842

图6 租界时期上海城市基调色、辅助色和点缀色示意Fig.6 Basic, auxiliary and embellishment color in concession era
2.3 情景调研捕捉地区性色彩特点
大数据支撑的“上海全域色彩地图”和城市发展史推演下的城市色彩演进,都是借用理性工具进行上海全域色彩总结和空间分析。但是站在人的尺度和人的视角,城市色彩更多表现的是视觉感性。
人工测色是传统的色彩调研方法,非常成熟,被大量使用,但其缺陷和不足也是不可回避的。首先,该方法对测色人员的色彩专业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在现场色卡比对的过程中,会遇到天气、照度、温度的多重影响。其次,团队成员的色彩认知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色彩心理学显示,人的情绪也会对色彩判断产生影响。再次,当遇到反光材料和渐变色的建筑立面时,人眼辨识的主观性大大提升,影响客观判断。最后,在以一个色彩总结建筑群色彩,并作为街坊的基调色时,最终结果受到测色人测量建筑表面的位置、顺序和直观印象的叠加影响。
但是,一定范围内的人工测色调研,在收集地区色彩问题、形成地区色彩印象方面,有着大数据不可替代的作用。2018年6月—8月,5个调研小组共15人,以街坊为基本单位开展调研,采用NCS1950 Index色卡,完成外环线以内地区的测色和拍摄工作,生成“外环线内(中心城)城市色彩地图”(见图7)。人工调研一方面对大数据生成的“上海全域色彩地图”的准确性进行校核;另一方面通过人的视角的观察,发现和梳理城市色彩问题,包括色彩和配色与建筑高度、面宽、材质、界面,以及建筑色彩与店招店牌、街道家具等辅助设施的关系等。
2.4 线上互动了解公众色彩喜好
为了详细获取公众对上海市建筑的感知情况,采集上海16个市辖区中106个街道、107个镇的街景图,以微信“H5页面”为载体,通过两两随机配对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对比图,让用户选择更喜欢的一个,再通过算法,将用户的选择拟合成每一张图片的得分,与图片本身的色彩构成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关联性。共收到11 115次用户返回数据。
将互动游戏中的每张图片计算得到的感知得分以圆形半径表示,半径越大,感知评分越高。将图片中的建筑主题色色相与感知评分形成直方图,可得感知评分较高的颜色是赭石、米黄等;色相区域位于5YR—5Y;明度大于6.0;彩度小于1.5(见图8),即受到公众喜爱的色彩分布范围。公众喜爱的建筑色彩与借助大数据和调研法取得的城市基调色是基本吻合的。从色彩角度证实,城市影响人的审美,而人的选择也塑造了城市的风貌和气质。
3 上海城市色彩的空间特征
“上海市域城市色彩地图”呈现了一幅千姿百态的“拼贴画”。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建构色相、明度和彩度与空间布局的耦合关系,进一步分析上海城市色彩空间特征。
3.1 色相空间结构
从中心城范围内来看,暖色与中性色调构成的城市色彩布局比较集中,主要位于浦西的内环内,尤其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和历史风貌保护街坊;冷色调构成的城市色彩布局比较分散、均质,其中7.5B—10B相对集中在陆家嘴商务区和南京西路—静安寺商务区内(见图9)。
3.2 明度空间结构
明度是色彩所表现的明暗程度。黑色的明度最低,级别为0;白色的明度最高,级别为10;在0—10之间均匀分为10个明度阶级。0—3为低明度;4—6为中明度;7—10为高明度。根据色彩地图可知,上海市域城市基调色的明度在中明度6.0以上,明度变化区间较小,形成高明度的城市色彩基调。主城区和新城的明度较外围组团相对较低,处于6.0—7.4之间;开发边界外的平均明度在8.0以上,属于高明度区间;城市开发边界内的明度较城市开发边界外低,前者比后者平均低2.5左右,色彩的城乡二元结构较明显(见图10)。一般来说,城市色彩中保持较高的明度比较容易达到高品质色彩的特征。

图7 基于色彩调研的外环线内“城市色彩地图”Fig.7 Color map based on atlas survey

图8 市民喜欢的色彩范围Fig.8 Citizens' favorite color based on H5 survey

图9 上海中心城色相概率分布图Fig.9 Distribution of hue within the outer ring road
3.3 全市呈现低彩度, 与城市格局耦合度高
彩度表示色彩的鲜艳程度。上海市域建筑色彩彩度总体较低,一般处于0.3—1.5的低彩度区域。彩度空间布局呈现明显的组团式,与城市功能结构耦合程度高(见图11),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新城核心区的彩度为市域范围内最低,其次为主城区内的黄浦江滨江地区和城市副中心;二是主城区内的黄浦江南段地区,浦东部分的彩度明显大于浦西,北段相反;三是苏州河沿岸彩度显著低于黄浦江沿线;四是发展较成熟的城市副中心,如虹桥、花木、中山公园等,彩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集聚效应明显;五是地区中心的彩度与周边地区相比,显示度并不明显。

图10 上海城市色彩明度分布图Fig.10 Distribution of lightness value

图11 上海城市色彩彩度分布图Fig.11 Distribution of saturation
4 结语
随着城市空间的发展,产业经济带来色彩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引发色彩审美的变迁,生态环境影响城市色彩的背景,最终综合反映在色彩空间形态上,使城市空间格局呈现不同的特征,成为城市空间转型的视觉落脚点。从包豪斯时代开始,色彩即成为艺术和工匠的共同纽带,从而产生新的职业门类“设计师”。格罗皮乌斯强调“设计师不是单纯的产品创作者,而是这个社会中重构城市的重要一员”。如果延展包豪斯的概念,那么色彩规划的目的不仅仅是美化城市可见的物质表面,而是建立一种思维方式“在研究当下的基础上,利用过往已知的知识和能力,为城市生活提供面向未来的答案”。事实上,色彩折射了当代城市中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和艺术的综合性问题,如果我们寻求答案,必须再次出发,找到当代艺术、工艺、科技、政策的结合点。
本文通过理性和感性的方法,对上海城市色彩进行全域全覆盖的研究,绘制了上海第一张“市域城市色彩地图”,为上海城市色彩的收集、空间分布的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上海市城市色彩规划,呈现以下4方面的特点:一是从主观感受转变为科学表达,使用统一的数字化色彩表达语汇;二是赋予城市色彩以地理空间属性;三是从单体色彩方案转变为规划管控,将城市色彩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体系,融入各层级的法定规划,具有更好的落地性;四是从模糊概念转变为准确的控制要素,通过城市设计、控详规划、附加图则转化为规划管理语言。城市色彩规划正向着数据化、科学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为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