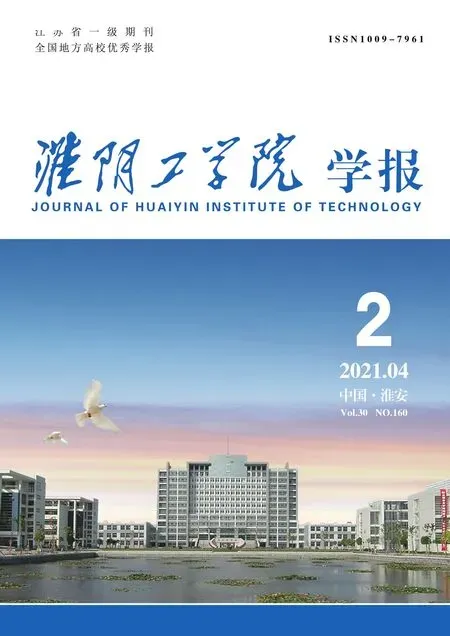“布衣”抑或“王孙”
——以“新黔首挟兵令”为重心的韩信身世再探
2021-01-16罗有,王海
罗 有,王 海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韩信是西汉王朝建立的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时人对其的评价。关于韩信的出身,从古书上看,主要见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三大文献之中,学界亦以此作为主要依托并划分为两种观点。多数学者认为韩信出身平(贫)民①、地位卑(低)微②,极少数学者则提出韩信的出身是高于小民的没落低级贵族[1]、本是王孙论[2]等。长期以来,上述方家的看法始终存在分歧,学界现有的研究视角亦较为褊狭,对韩信出身的判断大多没有全面可靠的论据支撑。然韩信身世的解读与其生平、性格与谋反被诛命运以及司马迁笔下韩信人物的真实形象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此,在《史记》中对韩信身世关键信息进行互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地下出土的简牍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法”解读,或能拓宽视角,对韩信身世进行更为接近历史本真的探索。
1 《史记》“始为布衣”说献疑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身份描述共有两处,史载: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3]2609。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3]2629。
前者“始为布衣”是太史公行文所写,后者“布衣”是司马迁听取淮阴本地人的口述后,于“赞”中记录。通过对《史记》各篇章人物身份的记述进行互见,发现在司马迁笔下,周勃、主父偃、张耳,陈余亦“始为布衣”,其中记载“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余时,太史公更罕见地在同一篇列传中使用了同样的笔法。史载:
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3]2080。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3]2962。
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3]2624。
关于周勃早年生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3]2065。周勃的先祖生活在“卷”地,而后“徙沛”,然古代官府对民众的迁移有着严格的控制。战国时期的《商君书·垦令》篇就有“使民无得擅徙”的规定[4]38,秦汉时期的户籍管理则呈现出更为严密的趋势。《后汉书·张奂传》说:“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5]2140。”东汉名将张奂的这一户籍变动也仅仅是因战功才特许的,那么周勃的先祖以何种身份徙沛,其出身究竟如何是有待商榷的。
西汉名臣主父偃的出身从其姓氏上便可见一斑,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自号为主父[3]1812。”相传姓主父者就是他的后人。观主父偃早年经历,其从小熟读诸子百家并“游齐诸生间”[3]2853,身份自然应与一般平民阶层有所区别。
回溯《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亦未有对张耳陈馀出身“布衣”的只言片语,反而提到张耳“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后来亦是娶“外黄富人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3]2571。陈馀更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3]2571,公乘是秦汉时期二十等爵制的第八等,袭爵者以公号为氏,称为公乘氏。此二人的出身实际上都与“布衣”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因此,“始为布衣”的周勃、主父偃、张耳及陈余出身的存疑,也就使得司马迁笔下同为“始为布衣”的韩信出身越发扑朔迷离。
李长之曾提到:“司马迁本人对文字有着极高的驾驭能力,他常常对一个整个传记,因为抓到最确切的几个字,而用以显示主题。因为司马迁是这样的善于控驭文字,所以他有时把文字当作游戏[6]。”司马迁笔下“始为布衣”之诸多疑点互见似乎更像是他留给我们的文字游戏,而后世史学家班固与司马光亦可能已从太史公对韩信“始为布衣”的记述中看出了端倪,故而在《汉书》《资治通鉴》中对韩信“始为布衣”一说进行了一致的删减,以此来警喻后人。秉承着“实录”精神的太史公是否为韩信身世的真相埋下了更为要害的伏笔,我们当从《淮阴侯列传》中继续寻找端倪。
2 “母冢”“王孙”“执戟”——《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身世追论
太史公在《史记·淮阴侯列传》“赞”中曰:“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3]2630。”关于韩信葬母之地,是太史公亲访淮阴所见,也为我们传递了两则信息,其一,韩信将其母葬于“行营高敞地”。当代已有学者指出:“统治一方的达官显贵死后按照古代墓葬风水观念,墓地必然要选择高敞处,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淮阴区码头镇以东即现在清浦区城南乡西境与武墩镇北境,为战国至秦汉的重要墓葬区,《清河县志·图说》所描绘的众多高墩,均为贵族陵墓[7]。”因此,韩信的墓地选择或也与其过往显赫的望族门楣有关。其二,淮阴只有韩信母冢,除此之外一无父冢,二无祖坟。因此,韩信及其父母应该都不是淮阴本地人,而是后来才迁徙到淮阴的,并且在来淮阴之前,其父便已去世。司马迁并未提及韩信的家世渊源,其先祖与生父的悬疑,使得民间与野史众说纷纭,清人唐梦赉就在《淮阴漂母传》中说韩信是“韩王孙也”③,有人说得更细致,提出韩信是“韩非遗孤”[8],虽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马迁不会在不知晓韩信家世渊源的情况下论定韩信出身“布衣”。
韩信落魄时,幸得“漂母饭信”,漂母却称韩信为“王孙”。史载:“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史记索隐》于其下记,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3]2609。”据此,有学者提出韩信出身“本是王孙”论:“漂母称韩信为‘王孙’,或许从另一头牵引出了韩信隐秘的身世。公元前230年,秦国攻灭韩国,为躲避战乱,不少韩国人向东迁徙,韩信一家,抑或是其中之一[2]?”秦灭六国后,亡国的贵族后裔大都流落到了民间,如,“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3]300。破败的金枝玉叶往往容易受到下层人民的垂怜,漂母尊称韩信为“王孙”,或许是对韩信的身世有所耳闻。这一观点从出土文献中亦有迹可寻,云梦秦简中的《编年记》载:
廿年,韩王居□山。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处其处,有死〔士〕属[9]。
对照《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3]233,”高敏先生分析:“‘昌平君徙于郢’同韩王居于‘□山’两件事情指的是同一性质和同一地区……韩王曾经被囚禁过的‘□山’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楚国的郢都[9]。”可见,韩王安在韩国被灭后被迁居到楚国故都郢某山,一年后新郑爆发叛乱被秦镇压。在这场叛乱中参与的韩国人除大批被杀之外,幸存者也应和韩王安一样被流放到了楚国境内,秦为了避免聚族而居再生叛乱,抑或对韩国故民进行了分散迁移,年幼的韩信可能便随其母流落至楚国淮阴一带,其父亦可能作为领导者之一在叛乱中身亡,淮阴本地人漂母有所耳闻尊称韩信为“王孙”便不足为奇。“本是王孙”论的猜测虽然只是依据现有史料进行的间接推理,不能作为考察韩信出身直接可信的依据。但却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从而为探究韩信身世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指向——没落贵族。
韩信曾在项梁死后“与项王有故”[3]1622,《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3]2622。”可见,韩信曾担任项羽的“执戟”“郎中”。“秦及汉初的三郎确实是指的郎中、中郎和外郎。按秦汉的宫省制度,帝王所居可分为宫中、禁中”[11]。韩信则负责项羽的宫门宿卫,有“近卫”职责。从“戏下分封”以贵族为先,功臣次之,鸿门宴“妇人之仁”[3]2612到末路时“何面目见之”[3]336江东父老来看,项羽此人拥有强烈的贵族情结且极好面子,对于关乎其宫中形象的贴身职位,应是会挑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通晓一定贵族礼仪的人。在担任该职务期间,韩信曾“数以策于项羽,羽不用”[3]2610,加之其日后所表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来看,其自幼应是熟读兵法,家中必有《孙子兵法》等藏书,可见韩信早年家境或并不贫寒,不仅可以接受教育,亦能习剑并钻研兵法。项羽则自幼也接受了类似的培养与训练,但其属大贵族出身,拥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应当能够拥有这样的条件。
从史书上看韩信几乎拥有与项羽等同的成长背景,这不得不让人对其身世产生联想。反观韩信成名之前,如若没有良好地贵族教育基础及素养,又何来受“胯下之辱”时与太史公一样的忍辱负重,何来与萧何交谈后的“国士无双”,何来众多军事指挥的天才战法。
3 “新黔首挟兵令”视阈中的韩信“好带刀剑”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身世诸多疑点以及后人的猜测与推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指向和判断,随着出土文献的整理及公布,结合《史记》运用“二重证据法”,我们在韩信“好带刀剑”一事中找到了关于其身世的关键性突破。史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3]2610。”可见,公元前209年项梁起兵之前,韩信都处于秦王朝严密的统治之下。故而韩信早年于楚地淮阴“好带刀剑”一事则涉及了当时《秦律》对兵器的管控。检《史记》司马迁关于先秦、秦代携带兵器的史料记载,其带剑法令经历了三次转变。具体记载如下: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据此《正义》注:春秋官吏各得带剑[3]200。
简公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3]288。
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锯,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3]281。
上述史料表明春秋时期的各国官吏是可以佩剑的,《老子》中就称贵族“服文彩,带利剑”。有学者指出:“简公六年秦国首次颁布的带剑法令‘令吏初带剑’抑或是秦国向其他诸国学习的成果,亦是其尚武精神的具体体现[12]。”在此之后秦人“带剑”范围由官吏到百姓的扩大,可能与其鼓励全民尚武参军,不断适应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有关。然秦统一之后,“收天下之兵”起码表明了被征服的关东各国民间武器的管控趋向严格。在此背景下,布衣韩信“好带刀剑”于楚地淮阴市集招摇,不得不让人疑窦丛生。
最新整理公布的秦简资料或为我们深入思考韩信“好带刀剑”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2009年曹旅宁在《岳麓秦简挟兵令考》一文中提到,“秦出台《挟书令》史有明文,《挟兵令》却为岳麓秦简所证实。两令皆出李斯之议。秦制,兵器皆属公有,战时借给从军者使用,事毕归公,已为睡虎地秦简所证实”[13]。
2016年陈松长先生在《岳麓秦简中所见秦令令名订补》一文中首次披露了与秦《挟兵令》相关联的两则简文:
0347:新黔首公乘以上挟剑毋过各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剑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
0676:得带剑者毋过各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以新黔首挟兵令议之④(十一)。
上述两简中有关“新黔首”“挟剑”“带剑”内容的记载,对于学术界相关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振波指出:“无论如何,‘新黔首’毕竟不同于‘故黔首’,他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并非朝夕可就,尤其重要的是,新、故之间,是亡国者与战胜者的关系[14]。”朱锦程亦提出:“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不清楚秦从简公到始皇帝间是否有对‘带剑’的规定进行过修订,但从亭长刘邦来看,吏带剑的规定应仍在沿用。而这则‘新黔首挟兵令’可能是针对六国故民中拥有爵位但却没有官职者的规定[15]。”因此司马迁笔下“好带刀剑”的韩信应该并非曹旅宁先生所言之“从军者”,而是于振波先生笔下之“亡国者”,属于上述两则简文中的“新黔首”,亦即“六国故民中拥有爵位但却没有官职者”。
在新黔首的爵位获取问题上,于振波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新黔首可以通过军功斩首、捕盗、常规赐爵等途径获得秦爵,但这几种获爵途径都有明显的阶层痕迹,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新黔首挟兵令”中的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等高爵,推测秦在统一过程中应对新黔首有特殊的赐爵情况[16]。从“新黔首”韩信于前209年加入项梁反秦军之前在淮阴的个人情况来看,此时韩信应当19岁左右⑤,属青年时期。关于秦的“傅籍”年龄,学术界主流意见为“十七岁傅籍说”[17],因此韩信可能曾在秦朝军中服役,但年龄尚浅的青年韩信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以“军功斩首”获得五等以上高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韩非子·定法》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8]。”可见,商鞅变法后以军功斩首可以为官,“不得推择为吏”的韩信显然应无军功。没有通过军功加官进爵以及推举为地方官吏,就很难拥有“捕盗”获爵的身份。秦及汉初法律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能捕以城邑反及知而舍者一人,拜爵二级,赐钱五万[19]。”捕盗者会有大量金钱赏赐,而“常从人寄食饮”的韩信却连温饱都难以满足。加之从常理而言无论是“军功斩首”还是“捕盗”获爵,都是令人敬畏的事情,而司马迁笔下的韩信,不但“人多厌之”,且又被“屠中少年”羞辱,可见其并未通过“军功斩首”及“捕盗”获取爵位而受到淮阴当地百姓的尊重。关于“常规赐爵”,“史书对秦赐爵的记载极少,秦始皇统治期间仅有两次,分别只赐爵一级,其中后一次还是针对特定小区域的赐爵”。可见,这样的“常规赐爵”力度极小且获取条件特殊,即便楚地淮阴有赐爵情况,韩信一次性获得五等以上高爵也并不合理。
综上,韩信并不具备在短时间通过“军功斩首”“捕盗”“常规赐爵”获得“新黔首挟兵令”中高爵的条件,应是于振波上述之“特殊的赐爵情况”。而“特殊的赐爵情况”从传世文献及出土秦简上看,这些特殊赐爵的对象大都来自原六国将相贵族之后以及蛮夷君长等⑥,那么韩信若要符合“新黔首挟兵令”中的带剑身份,其极有可能是通过这种“特殊的赐爵情况”获得高爵,故而司马迁笔下一个六国贵族出身的韩信身世真相,或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4 “志与众异”——韩信与司马迁之心理共鸣
司马迁并未明示“布衣”韩信的家世背景,因此其笔下韩信“好带刀剑”应有“实录”及“虚构”两种可能:其一,淮阴人知晓韩信贵族出身,而熟知《秦律》的司马迁从淮阴人口中听闻韩信“好带刀剑”并记录下来,这一点前文已然推定,如若韩信“好带刀剑”为太史公“实录”则其六国贵族出身或已坐实。若非如此,便有其二,熟知《秦律》的司马迁本已知晓韩信显贵的出身,鉴于政治原因不能言明,由此虚构了韩信“杖剑”,也就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杖剑虚构论”。
韩信处于由秦末汉初这样一个由分裂走向政治统一的时代,而在这一历史趋势中的他“裂土封王”的思想却根深蒂固,这样的思想使得他“志与众异”。从《淮阴侯列传》中于淮阴时至“行营高敞地”葬母,到“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3]2609。再到“胯下之辱”的隐忍,可见其带有强烈贵族情节的孤傲与志向。反秦之后,韩信战功赫赫,“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3]2624。他亦迫不及待地要挟刘邦:“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3]2621。”请立齐王,反不自立,意图“天下共主”。被贬淮阴侯之后又“羞与绛、灌等列”[3]2628。可见,在这样强烈的贵族身份意识下,他抑或渴望回到先秦那个诸侯国林立的时代,一定要恢复其“王孙”的身份与家族往日的荣耀,他并没有像刘邦那样一统天下的决心。但是韩信所作出的努力是与当时天下趋于一统的历史潮流相背离的,所以这种思想意识也使得他周围的人对他的性格持一个相对否定的态度,于淮阴时遭人厌恶与排挤,反秦之后虽战功赫赫,然“敌国灭,谋臣亡”最终被定上了谋反叛国的罪名,落得个“夷灭三族”下场。回溯韩信跌宕起伏的一生,太史公谓“志与众异”来概括韩信其人可谓一针见血。
太史公于《淮阴侯列传》“赞”中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3]2630。”抒发了司马迁对于韩信深深的惋惜。司马迁在其私人书信《报任安书》中写道:“淮阴,王也,受械于陈;……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8]2733!”韩信本为王,受辱于陈为淮阴侯,这都是司马迁最为真实的心声流露,饱含了他对韩信的同情与怜悯,因为他们都曾在自己的时代下由于“志与众异”而招致了相似的迫害与羞辱。
据李长之研究,“司马迁的主要思想路线依然是道家,道家的自然主义是其思想根底”[7]187。然而这样思想实际上又与汉朝建立之后儒学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黄老之学的衰微,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这一大的时代潮流是不相契合的。他与时代的背离注定了他与韩信都将以相对悲壮的姿态呈现在历史上。不谄媚于上,力排众议为李陵辩护最终受到了政治上的残酷迫害,这何尝不是司马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异志”体现。因此他不惜笔墨塑造“志与众异”的韩信,就在于韩信年少时隐忍苟活,成名后受辱被害的悲剧人生与司马迁本人最终下狱受刑的遭遇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正因如此,太史公才于《淮阴侯列传》中反复抒发对韩信的同情与遗憾,才要想方设法为其鸣一个不平,甚至可能虚构“杖剑”以还原其真实的贵族形象。
综上所述,作为秦末汉初重要历史人物的韩信,学界多依据《淮阴侯列传》“始为布衣”的文字判定其为平民出身。司马迁笔下与韩信约略同时期或稍晚的历史人物,如张耳、陈余、周勃及主父偃等人,对其出身亦有“始为布衣”之类的表述。根据上述人物的早年经历分析,四人出身均存疑,这或许是太史公互见笔法的反映。《淮阴侯列传》中的一些关键文字,或许也对韩信的真实出身有所暗指,如“漂母饭信”时“吾哀王孙而进食”的话语,又如年仅二十岁左右的韩信追随项氏便获得“执戟”“郎中”的近卫官职,再如司马迁“如淮阴”实地考察所见“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的淮阴侯母冢。结合《淮阴侯列传》韩信“好带刀剑”记载与《岳麓秦简》中“新黔首挟兵令”相关简文,运用“二重证据法”对韩信的出身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似乎能够说明韩信此举似乎与秦王朝建立以后对原六国贵族之后的特殊赐爵有关,原有的韩信平民出身看法或可商榷。“志与众异”与“则庶几哉”体现出司马迁对韩信的崇敬与惋惜,或许也含有在西汉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太史公与其笔下人物的某种心理共鸣。韩信的真实出身应该从整个《史记》的篇目安排与相关文字中去寻找答案。此外。秦汉之际社会阶层研究中,“布衣”所指内涵与其演变,抑或也能够通过韩信出身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得到学界的重新认识。
注释:
① 刘杏梅,李修松在《从心态史的视角看韩信的成败》(《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韩信出身下层平民。陈兰村,张金菊在《论<史记>汉初“三杰”形象的典型意义》(《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韩信出身贫民。
② 薛志清在《刘邦布衣集团社会流动途径论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冯京游学杭州,遭到官吏侮辱,做诗以韩信、项羽自比。两首诗道出韩信出身的卑微,荀德麟在《韩信谋反辩》(《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亦认同此说法。李慧在《司马迁史记解析刘邦的真实形象》(《语文建设》2013年第30期)一文中认为,韩信出身低微。
③ 清人唐梦赉曾路过淮阴,拜谒漂母词,作《淮阴漂母传》写道:“韩母有子曰信,身长大,好击刀剑,嗜读孙武、穰苴之书,淮阴人不甚惮礼之,又落落不治生产、商贾,常从人寄饮食,漂母独识之曰:‘此韩王孙也’。”(参见唐梦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3 册《志壑堂文后集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490 页)
④ 陈松长先生在2009年3期《文物》杂志上发表《岳麓书院藏秦简概述》中指出其中有《挟兵令》一种。在2016年11华东政法大学出土文献与法律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岳麓秦简中所见秦令令名订补》一文中公布了0347与0676号两条与秦《挟兵令》相关的简文(参见陈松长:《岳麓书院中的秦令令名订补》,《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宄》(第六辑)2017第1期)。
⑤ 关于韩信的生年,张大可、徐日辉结合史实和民间传说推断韩信当生于公元前228年,今从之。(参见张大可,徐日辉:《韩信萧何张良评传》,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李开元据此撰写的《韩信年表》亦指出:“公元前210年,19岁的韩信受胯下之辱。”(参见李开元:《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12页)
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秦灭赵,(李)牧子兴徙咸阳,秦封武安侯。”《岳麓秦简(叁)》案例十四提及,冯毋择在秦始皇二十二年时,就已为秦将军,有卿级的爵位。冯亭为先后为韩赵两国的大将、贵族,与秦可谓有“大仇”,而其后人却能在秦为将相。《广韵》又有“秦灭赵,徙(赵) 奢孙兴于咸阳,为右内史。”睡虎地秦简有:“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参见于振波、朱锦程:《出土文献所见秦“新黔首”爵位问题》,《湖南社会科学》2017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