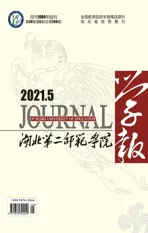黑人男性的身份探寻与自我建构
——论《所罗门之歌》的空间叙事
2021-01-15宋歌
宋 歌
(南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1931-)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所罗门之歌》(1977)是其代表作之一,出版后广受好评,并于次年斩获美国图书评论奖,莫里森也随之步入美国当代重要作家的行列。自该书中译本于1987年出版至今,评论界相继从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等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但鲜有学者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探讨小说中蕴含的空间形式对其主题的阐释和深化意义。
空间叙事学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传统的叙事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侧重从时间层面研究叙事作品。然而叙事既包含时间维度,又包含空间维度。因此,叙事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开始经历“空间转向”。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空间理论和空间叙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建构了“迄今为止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1]58。《所罗门之歌》传达的一个核心主题是黑人主人公奶娃的身份探寻与自我建构,本文拟用佐伦等学者的空间理论,借助三组二元对立关系来解析作品中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历史空间,进而揭示空间形式对小说主题的深化意义。
一、物质与精神:物理空间的并置
物理空间,即佐伦笔下的“地志层面的空间”[2]315,指静态的实体空间。对叙事作品而言,物理空间既是人物生存的环境与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叙事展开的客观条件。依据佐伦的观点,在这个层面的空间中,作者如同绘制了一张叙事“地图”,清晰地展现出该空间的原貌。绘制这张“地图”可以直接采用描述的手法,也可以借助对话或散文体等方式。作者通常会在这张“地图”上并置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如里与外、近与远、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等[2]316。物理空间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学概念,但它兼备社会属性,用福柯的说法便是“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3]204。因此,文学作品通常借助物理空间的对立来呈现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龙迪勇曾指出,“主题”(topic) 这一概念是从拉丁文的“场所”(topos) 演变而来的,因此主题-并置叙事隶属于空间叙事的范畴[4]38。反而言之,小说中空间的并置同样是为主题服务的。在《所罗门之歌》的第一部分中,物理空间的差异及其隐喻非常明显。莫里森运用直接描述的方式,并置了两个对立的黑人社区,以展现相应族群的价值观和权力地位。
小说开篇的场景设置在美国北方密歇根州的某城市,城里除了白人居住区以外,还包含两个集中的黑人社区——“非医生街”区域(亦称北区)和南区。这两个社区分别居住着富裕黑人和普通黑人。主人公奶娃出身于北区某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父亲麦肯利用二战的“间歇”积累起财富。麦肯一家不仅从物理空间上远离南区,并且从心理上拒绝和贫苦的黑人同胞交往。“非医生街”在地理层面更接近白人聚集区,麦肯的生活方式也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如出一辙,与其祖辈在美国南方形成的传统产生了严重的断裂感。然而,麦肯的家长地位和丰厚的物质财富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幸福,反而限制了家中三位女性和儿子的自由。从岳父那里继承的拥有“十二个房间的大房子”没有被描述成“宫殿”,反而被赋予“监狱”的象征。豪华的“柏加”轿车更是被熟悉的人戏谑为“灵柩”[5]32。妻子露丝在家中没有话语权,终日为家务所累。两位女儿在父亲的威慑下,青春早已耗尽,虽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最终沦为家里的老姑娘。儿子奶娃更是过着饱食终日、浑浑噩噩的生活,缺乏学习动力和冒险精神。
相比之下,奶娃的姑妈派拉特居住的南区则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派拉特和女儿丽巴以及外孙女哈格尔共同住在“人行道之外八十英尺远”的一间“狭窄的平房里”[5]27。地理空间的相互隔绝造就了一种与北区黑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家中三代女性生活在一起,过着天然淳朴的生活。没有电和煤气等现代化设施,夜间照明只有自制的蜡烛和煤油灯。然而派拉特家里却充满生机,飘散着令人陶醉的“松树与醇酒的香味”[5]40,也时常回荡着和谐的歌声和笑声。她有一种源于自然的天性,声音如同“圆圆的鹅卵石,互相冲撞着”[5]40,并被赋予“树”的形象。与麦肯家阴郁的豪宅不同,这间平房的三面墙上都有窗户,可供阳光毫无阻挡地射进室内。派拉特漠视物质财富,却注重精神世界,比如爱、尊重、正义、慷慨和同情。
由此可见,北区实为美国北方工业社会的缩影,充满了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但也充斥着“工业废渣”与精神危机。作品中麦肯崇尚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暗示了莫里森对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的强烈质疑。而南区代表着南方,即美国黑人繁衍生息的土地。两个空间的隔离使得居住在南区的贫苦黑人并没有被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病所侵蚀。作品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初秋的夜晚,凉风把一阵阵如同“姜糖”一样“甜丝丝”的气味从湖面吹向岸边。住在北区空调房间里的黑人已经无法闻到这气味,而南区住宅的窗户时刻敞开,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种味道,那“气味赋予他们一切思想和行为一种既亲切又疏远的双重品性”[5]188。姜糖的气味是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隐喻,奶娃在日后的南方之行中数次闻到这种味道,象征着在北方工业社会逐渐失落的非裔文化传统。
除了上述两个并置的物理空间以外,麦肯对父亲的追忆打破了时间上的线性叙事顺序,而记忆通常与某个具体的场所联系在一起,因此记忆同样具备空间特质。麦肯的回忆塑造了一个已经失落的物理空间——林肯天堂。“林肯天堂”是老麦肯在废奴运动成功后亲手开辟的一座拥有一百五十英亩土地的农场,种植着农作物和经济木材。农场的繁荣引起当地白人的觊觎之心,随即将老麦肯杀害,一双儿女也在日后流落他乡。老麦肯视农场为家园,饱含着自由黑人用双手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从先辈那里延续的精神信仰。可见,“林肯天堂”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既拥有财富的光芒,又延续着黑人与土地的联系。麦肯和派拉特都在潜意识中试图恢复父辈的荣耀,然而两人均片面误读了父辈的理想。麦肯只看到前者,他固执地坚信自己对物质的野心源于父亲的遗传。他在生意场上气势汹汹,竭力模仿白人主流社会商业大亨的派头。但金钱束缚了他的精神自我,独处的时候,又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既无财产又无土地的流浪汉”[5]27。麦肯的孤独感体现着富裕的中产阶级黑人对自己的双重身份缺乏认同感,个人定位的困难造就心理空间的缺失。而派拉特在精神层面的单一追求,使得她和家人长期过着物质贫乏、与世隔绝的生活。视角的蒙蔽致使她只能演唱“所罗门之歌”的些许歌词,且并不完全理解这首歌的真实含义,不知道歌词里的“售糖人”(sugarman) 和自己家族的历史有何关联。可见,想要完成父辈的历史使命,只有依靠奶娃的南方之旅。
二、疏离与融合:心理空间的建构
心理空间通常指外部环境和个人经历投射到人物内心之后产生的感悟,既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又包括对他者的认识。王玉括指出,早期非裔美国文学均呈现对“北方的向往”以及“对北方文化的认同”[6]160。从哈莱姆文艺复兴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非裔美国文学主要采用“从南方向北方迁移”、从而寻找自由和自我的传统叙事模式[6]161。然而《所罗门之歌》中主人公却历经了相反的过程。南北战争结束后,从“大迁徙”(Great Migration) 的表象看,南方象征着奴役,而北方意味着自由。事实上,从南方迁移到北方生活的黑人与原来的农业生活方式彻底决裂之后,普遍存在情感层面的缺失。创伤性的社会变迁势必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身份危机。这种“文化错位”现象,是远离民族文化的黑人群体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7]152。因此,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只有疏离了生长和居住的北方环境,重新融入南方生活,才能摒弃自身与民族文化的割裂感,建构起健康的心理空间。《所罗门之歌》中,奶娃在南方之旅中逐步形成的心理空间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础之上。
(一)心理空间建构在与他人产生联系的基础上
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家中三位女性的无条件付出让奶娃习惯了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生活。麻痹的生活状态标志着现代社会带来的异化危机,体现了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对人类价值观的颠覆。奶娃的自我意识萌芽于和父亲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为了捍卫母亲的尊严,他把父亲打倒在地,开始隐约感受到人生存在着“无垠的可能性和巨大的责任感”[5]69。为了让儿子疏远对方,成为自己的依靠,麦肯夫妇相继在儿子面前上演“罗生门”的好戏:他们竭力掩饰自己情感层面的缺失而指责对方的过错。当奶娃意识到他只是“存放别人行动和痛恨的一只垃圾箱”的时候,也曾试图“摆脱他所了解的一切,摆脱他被告知的一切的含义”,但责任感的缺乏导致他并未作出任何改变[5]124。姐姐莉娜的一通斥责让他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的自私和无情,父亲安排他到南方的寻宝之旅不经意间激发了他对自我空间的诉求。
为了顺利找到遗留在山洞里的金子,奶娃首先来到宾州的丹维尔。他入时的穿着与周围淳朴的民风格格不入,在当地黑人眼里,他是一个“白人化”的自命不凡的北方人。尽管如此,丹维尔的环境给予他自由气息。在与库伦牧师的交谈中,他第一次为祖父的冤死感到愤怒,族人对祖父的钦慕让他真切感受到“林肯天堂”的荣耀。随后在维吉尼亚州的沙理玛,奶娃的寻宝之旅逐步演变成建构真实身份的寻根之旅。在北方密歇根的家中,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然而在沙理玛和当地同胞一起打猎的经历,使他顿悟责任感应该建立在和他人产生联系的基础上。南方朴实的民风让奶娃获得新生,他为自己先前的颓废人生观感到羞愧,也对周围的人也有了全新的认识。父亲在他眼中也不再是一个专横自私的人,而是一个对逝者尽忠尽孝的人,只因曲解了父辈的理想,对财富的贪恋致使灵魂走向扭曲。他对姑妈派拉特满怀愧疚,意识到她才是自己人生的领航者(Pilate谐音pilot),试图引导自己和先辈建立起情感层面的联系。奶娃开始从思想上摆脱与他人的疏离感,建构起全新的心理空间,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
(二)心理空间建构在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基础上
迈克·克朗认为,“空间体验”与“自我身份”密切相关[8]61。因此,奶娃在地理空间上从北方到南方的迁移实为其心理空间的投射。此外,依据佐伦的观点,“文本的视点会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超越文本虚构空间的‘彼在’与囿于文本虚构空间的‘此在’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点,两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但不同的聚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1]59。小说第二部分的寻宝之旅一定程度上舍弃了第一部分的全知视角,大多以奶娃的视角呈现,既展示了人物所处的物理空间,又暗示了其心理空间的建构。
老麦肯亲手打造的“林肯天堂”象征着人与自然最紧密的联系。他在土地上耕种并收获,循环往复,保持着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具有朴素的人文意识和生态精神。对于奶娃而言,北方的都市生活割断了他与土地的联系。初到南方,乡间的自然景色令他体会到“千篇一律的厌倦感”[5]230。然而在沙理玛和当地黑人一起狩猎的经历成为他在自然界返璞归真、获得顿悟的重要时刻。打猎前,奶娃彻底脱下象征北方中产阶级身份的名牌着装,换上当地人破旧的军用工装。途中他因体力不支掉队,惊觉从北方出发时所带的行装几乎丢失殆尽,突然领悟物质财富才是他探寻自我空间的“绊脚石”[5]284。当他逐步卸下物质包袱,精神世界才得以回归。狩猎故事展现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景象,奶娃麻痹已久的感官得以恢复,开始倾听丛林中动物的声音和流水声,并感觉躯体“直扎进石头和土壤之中”[5]288,与自然融为一体。重要的是,有着先天缺陷的左腿也不跛了。可见,原有的情感缺失和精神缺陷在自然界中得到痊愈,沙理玛的寻根之旅帮助奶娃构建起健全的心理空间。
(三)心理空间建构在与黑人历史产生联系的基础上
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作品中典型的旅行故事往往和“家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作品通常始于失落的家园,“主人公离开了家,被剥夺了一切”,历尽一切磨难后,回归家园[8]60。从这个层面出发,作为家园的“林肯天堂”已经湮没在历史洪流中,即使重建,也不可能复原。因此,奶娃的寻根之旅带来的是“精神家园”的回归,与其心理空间的建构密不可分。
当从南方孩童口中听到完整的“所罗门之歌”,奶娃终于还原了家族失落已久的姓氏,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可见,精神家园的回归源于对家族历史的明了。莫里森在接受罗伯特·斯特普托的采访时曾指出,“命名”是其作品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真实姓名的缺失以及奴隶制时期白人给予黑奴的怪异名字造就了黑人存在层面的隐匿感和文化上的孤儿身份[9]486。黑人从沦为奴隶的那天起,就被主人剥夺了原有的姓名,从而丧失身份与自我。回北方的路上,奶娃终于明白派拉特为什么要把写有自己的名字的纸条装在耳坠里。因为名字代表记忆,代表和祖先相关的一切历史。美国黑人的祖辈扎根南方,只有与先人建立起联系,才能延续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构建起属于自己族群特有的心理空间。派拉特临终前,奶娃饱含深情地为她演唱“所罗门之歌”,并刻意将歌词中的“售糖人”(sugarman) 改为“售糖女”(sugargirl)。可见,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黑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最终成为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人。
三、终点与起点:历史空间的回溯与展望
龙迪勇曾指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变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10]67。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变迁,空间以动态的形式承载着人类的记忆,形成一系列历史空间。有别于莫里森的其它小说作品,《所罗门之歌》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叙事模式,但故事结局对美国黑人历史空间的回归则显得颇具匠心。奶娃寻宝之旅的终点是美国南方,而这一物理空间又代表着黑人种族在美国大陆繁衍生息的起点。起点与终点在同一场所的对立统一,有助于读者在追溯逝去的历史空间的同时,对未来的历史空间进行展望。
传统文化是历史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裔美国文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非洲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流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然而,双重文化意识容易带来身份的消解与自我的迷失。如何让美国黑人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如何在文化趋同性的潮流中保持独立的民族身份一直成为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重心。《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始终坚守民族性,从未妥协。父亲的不幸遇难致使她从少年时代便过上流亡的生活,然而每到一处,都要取一块石头收藏起来,以纪念被迫离开的南方家园,保持内心与故土难以割舍的联系。废奴运动虽然带给美国黑人自由,但也造就了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甚至“陷于被连根拔掉的境遇”[11]207。南方的诸多地名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并无显示,但这些地域的存在既是美国黑人历史的见证,也是将其与非洲大陆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派拉特一生“只读过一本地理书”[5]142,并把这本书随身携带,体现了她对于民族历史的捍卫精神。刚到沙理玛的时候,奶娃的优越感和虚荣心激怒了当地同胞,他甚至差点被一个族人误杀。当地黑人的嘲弄如同一股想把他从这一空间排挤出去的力量,奶娃非但没有恼怒,反而竭力融入南部人的生活。他虽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人,也“不觉得他们怎么亲近,只是感到和他们有着联系,死后有某种和他们共有的密码、脉搏或信息”[5]301。由此可见,南方既是黑人祖先受奴役的牢笼,又是黑人后裔找回归属感的故乡。
当奶娃完成寻根之旅,在回北方的路上,他摒弃了初到南方的厌恶感与陌生感,“饶有兴趣地读起路牌”[5]339,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南方“平淡无奇的乡村景色”[5]230,并开始沉思祖辈的历史:“在这个国家众多的地名后,埋葬着多少死去的生命和逝去的忆念啊。在那些法定的名称下面,还存在着别的名称,“麦肯·戴德”就是其中一例,多年来的法定名称却用一层灰尘掩盖了人所不见的真正的名称:人名、地名和物名。那才是些有真正含义的名称呢。…… 你得知自己的名字之后,你就应该系之于心,除非这名字载于青史并为人们永世传颂,它将随着你的死去而消逝。”[5]339
依照托马斯·索威尔的观点,美国黑人既属于“最古老”的美国人,又属于“最年轻”的美国人。前者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几乎完全形成于美国的土壤之上;后者是因为直到1865年废奴运动成功后,他们才作为自由人存在[11]192。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的话语权受到剥夺,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命名权。奶娃家族的姓氏戴德(Dead) 源于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个醉酒的白人官员把其曾祖父已故(dead) 的信息错误地填写在祖父的姓氏栏,家族才被赋予如此怪异的姓氏。而这一命名不仅象征着白人对黑人命名权的否认,更意味着对其存在层面的抹杀。因此,还原家族真实姓氏等同于融入先辈的历史,以获得新的文化身份。此外,莫里森选择了“黑人的飞行”这一古老传说作为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力图呈现年轻一代黑人对于建构新的历史空间的渴望以及所做出的努力。小说结尾,奶娃在所罗门跳台上的纵身一跃,体现了重拾信心的豪迈和男子气概,与其祖先为逃离奴隶制而试图“飞回”非洲大陆的无奈之举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正如奶娃在南方家乡沙理玛悟出的道理,“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空气,你就能驾驭它”[5]347。因此,王守仁指出,《所罗门之歌》超越了传统的欧洲寻宝故事,因为作品“通过对会飞翔的祖先的寻觅……不仅关注了美国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还特别重视非洲黑人文化意蕴,展现了一种文化的自信”[12]92,并“在对西方传统文学模式的沿袭和解构中,重建了黑人传统文化”[12]74。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同样成为历史空间的组成部分,决定了人在空间实践中的行为准则。直到今天,奴隶制在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在创作过程中,莫里森曾走遍了国内的博物馆,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奴隶叙事的史料。她曾指出,“没有任何地方、任何东西使人能回忆或忘却奴隶的存在或消失、能回忆或忘却谁在途中死去或幸存”[13]212。还原奴隶制时期的血泪史对于白人而言,会带来道德上的难堪;但对于当今美国黑人后裔而言,同样会带来情感上的创伤。但莫里森并不主张逃避历史,反而竭力将年轻的黑人后裔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唤醒。她坚信只有了解并接纳先辈遭受奴役的历史,才能摆脱精神枷锁;只有自觉摆脱文化上的“他者”身份,才能正确定位现在并展望未来,自由立足于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因此,莫里森没有延用前辈作家理查德·赖特倡导的“抗议文学”的形式来引发社会对于黑人族群的关注与同情,相反力图在作品中树立自信、独立、自爱的“新黑人”形象。
四、结语
非裔美国人的身份探寻与自我建构是莫里森作品恒久不变的主题,为同胞争取平等的话语权以及为黑人作家及其作品正名也是她不懈努力的目标。在空间叙事理论视阈下重读《所罗门之歌》,读者可以从全新的空间角度阐释“探寻”主题。作品中物理空间的并置、心理空间的形成以及对历史空间的回溯与展望体现了莫里森对于当代美国黑人后裔回归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吁。作品开放式的“飞翔”结局象征精神层面的超越和自由,如同为当代年轻黑人指引出前行的方向,也再次应验了莫里森的创作理念:我的作品源于希望的喜悦,而非失望的凄怆[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