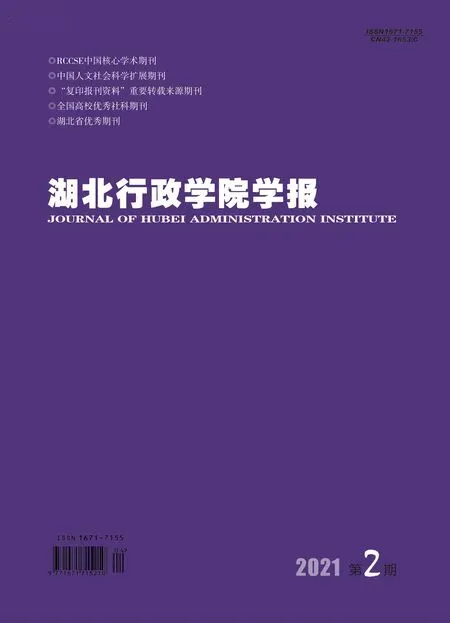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其表现
2021-01-12黄耀萱
黄耀萱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北京100872)
民粹主义是当前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其概念内核复杂,较难定义。1967年,政治学者伊内斯库(Ionescu)和盖尔纳(Gellner)等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了名为“定义民粹主义”[1](P1)的专题研讨会,但会议也没有就民粹主义的概念达成共识。当前,民粹主义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思想潮流,“湖北石首事件”“山东平度事件”“瓮安事件”等是这种思想潮流涌现的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未成为政治势力,是尚未成型的社会思潮。本文主要阐释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概念、特点与表现。
一、“民粹主义思潮”的概念
政治学的诸多概念存在争议,并随着时代发展,概念的争论点以及概念内核都在发生不同的变化。“民粹主义思潮”与“自由”“民主”等概念一样,在学术界争论较多,有学者称其为“空心化”,属于“薄概念”,可以用以形容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形容政治现象时,无论从意识形态、社会运动或政治策略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形成独立的论述[2]。此外,“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可以用在政治、文学、新闻、国际政治等领域,如政治领域里用在选举民主制国家政党,是政党竞选时针对政敌所推行的批判性政策。这些争论都显现出“民粹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因此,研究“民粹主义”首先应理清“思潮”“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等概念的具体内涵。
(一)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概念
传统上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始于美国民粹主义和俄罗斯民粹主义研究,俄罗斯民粹主义研究集中在对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上,其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美国民粹主义研究多集中在对1892年兴起的美国“人民党”的研究上,代表人物有保罗·塔格特、罗伯特·希尔斯、加文·基钦、迪·拉特、玛格丽特·卡农范。对西方民粹主义概念界定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他的著述《民粹主义》一书提出了“中心地带”[3](Heartland)的概念,认为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一个“中心地带”,将非民粹主义者视为中心地带以外的人,将“民众”视为中心地带的核心。即便如此,保罗·塔格特也没有给“民粹”下一个精准的定义。他认为:“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定义了。”[3](P2)
(二)中国民粹主义思潮
与其他较“厚”的政治学概念不同,“民粹”是“薄”概念,是由“民”和“粹”组成的复合型概念。“民”指民众,是政治行为的客体,“粹”是“精华”,可指“人民中的精华”,也可指人民中“蕴含的精华”,是平民主义的概念,同时也是精英主义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民粹’的术语中包含着大众与精英的特定关系。”[4]目前学界公认的“民粹”有两种解释路径[4],一是“民之精粹”,二是“以民为粹”,前者根据美国人民党运动的政治实践得出,后者根据俄国民粹派的政治实践经验总结而出。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具有自身特点,“民粹”在中国受到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在君王统治时期,“民粹”是服务于君王使君王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的统治方式;在现代社会,“民粹”更偏重于“以民为粹”[4]的解释路径,是大众动员的手段,是一种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策略性行为。
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中的“民众”应该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人民”区分开来。民众在这里是指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的集合体,是政治动员的起始单位,而“人民”是政治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下“人民民主”的权利主体,是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国语境下的“人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最大多数群体。因此,选取“民众”作为分析框架与分析单位,着重强调的是民粹主义思潮产生主体的“大众性”。2012年,《人民论坛》进行的由吴江和兰颖主持的《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指出,在1122份有效问卷中“近三成受访者属于民粹化特征显著者”[5],可以据此认定,民粹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散见于民众思想观念中的社会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场域中广泛存在。
二、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特点
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思想源于俄国民粹主义。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受到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影响脱离了原本的“君臣关系”,形成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潮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当前第四波民粹主义思潮①当前民粹主义浪潮具体是第三波还是第四波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第三波民粹主义还未结束,有的认为第四波正在进行中,考察民粹主义流变史,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主要受第四波民粹主义浪潮影响,与全球化的扩张相关联。参见: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01).随之传入并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思想。当前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具有三大特点。
(一)大众性
从词源上考察,“大众”具有“广泛”的含义,是指民粹主义思潮的民众主体身份大多数是社会中下层民众,是社会中身份地位不高的人群。民粹主义思潮的“大众性”是指民粹主义思潮主要产生于民间,是广泛分布于民众中的社会思潮。这里的“大众”应该与“民众”进行区分,“大众”用以形容社会现象的性质,而“民众”用以表达社会现象的主体,即作为集合体的人民。民粹主义思潮形成的“中心地带”代表社会的底层群体,这类群体目前占中国的大多数。“大众性”是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特点之一,这种大众性不仅表现为主体的大众性,也表现为动员的大众性,意指能够动员的民众数量广泛。
(二)反精英
精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民粹主义思潮的反精英特点体现在民粹主义思潮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上。科举考试是中国官僚制的选拨方式,随后逐渐演化为官僚体系。知识的推崇是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但是民粹主义思潮却演变出对官僚制产生的精英的怀疑,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反对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官僚体系和科举取士的代表,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表现在对知识分子道德的怀疑和由此而生的对知识体系的怀疑。反精英的另一个表征是“反智”,即对教育选拔体系和知识精英的怀疑,这是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独特表现。
(三)非理性
人是理性和非理性交织的生物,康德认为理性是一种“德性”,理性是人成为人最重要的品质。而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是缺乏理性的,其一方面是指民众缺少理性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指民众缺乏理性判断能力。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对人的理性有一个著名论断:“理性是激情的奴隶”[6],理性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帮助人进行逻辑判断,但在激烈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的驱使下人会丧失理智,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此时理性便再不是“纯粹理性”而成为情绪的工具,其逻辑思考也变成情绪的利器。民众是“人的集合体”,当极端情绪被唤起,在负面情绪驱使下的民众使用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这种情绪化的意见便是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的体现。
三、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
20世纪学者关于民粹主义思潮存在诸多争论,21世纪以后,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概念模糊不清,既可代指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思想潮流,也可代指民众对政府怀疑批判的思想潮流。究其根本,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精英”和“民众”的对立。无论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手段,其主体始终是民众,客体是精英。研究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表现需要从“民众”和“精英”两个维度切入。
(一)对精英的想象
“精英”是与“民粹”相对的概念,“精英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与“民粹主义”相对概念的,但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手段时,“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精英推行的政治手段,是精英动员民众的政治工具。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主要表现是对精英阶层的“想象”。改革开放加剧了社会分层,部分精英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民粹主义思潮的“反精英”表现在对精英阶层的敌视。
1.对政治精英的想象
从词意上理解,“精英”是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群体的总称。精英主义者认为“精英”是国家稳定的支柱,是统治中影响力最大的群体。社会秩序良好时,民众对精英的认可度较高,稳健的精英群体是社会稳定与和发展的政治保障。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层次因历史原因分为“精英”与“民众”两种群体。金观涛与刘青峰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描述为“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结构主要是由“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或称意识形态结构)相互耦合而成的形态稳定的组织系统。”[7](P11)“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主要是由儒生构成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7](P31)这种结构分层和社会分化成为观察中国封建社会的视角和认识中国政治的结构性方法论。贝淡宁认为中国实行“贤能政治”[8],政治精英处于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上层,同时拥有知识和权力,而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城市边缘地带,因为社会变迁,精英向城市流动,原本的乡绅等精英组织协调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处于政治精英相对缺乏的状态。这种对精英的疏离最终构成民众对精英的想象。
其一,对政治精英体系的质疑。精英是掌握资源的群体,政治精英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官僚制,具有权威性。在今天,政府权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民粹主义思潮的最主要特征是对官方话语体系的解构,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怀疑最终会造成对政府机关的冲击。易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处于社会底层,即按照社会分层结构来说是较少接触到中国政治体制上层的普通民众,民粹主义思潮引发反精英情绪,人在激烈情绪的作用下失去理智,愿意去相信“小道消息”,倾向于去怀疑主流话语体系。这种对主流话语体系的怀疑本质上源于对精英的想象,在具有民粹倾向的群众看来,精英是肮脏的、堕落的、腐败的,基于此,有关“精英”的正面形象都会被怀疑情绪影响,对精英话语体系的“怀疑”便是这种对政治精英群体负面“想象”和反精英情绪的体现。
其二,对政治精英道德的质疑。在社会中具有民粹倾向的民众面对官员以及和政府相关的政府行为时,表现出明显的敌视与怀疑情绪。保罗·塔格特在《民粹主义》中对民粹主义构建了一个“中心地带”(Heartland)。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中心地带”的核心便是民众,与中心地带相对应的“边缘地带”是需要批判的,而边缘地带一般由精英组成。民粹主义者对政治精英的道德观进行质疑,“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否定一切”的反叛性心态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社会中的重要体现。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有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官员是“坏的”,民众是“好的”。这种好坏对立的思维模式和道德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官员道德观念的怀疑是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最显著的表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民粹主义思潮表现为“对政治精英道德的质疑”,具体表现为对政治精英政治立场的质疑。民粹主义思潮对“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的道德动机进行批判,认为官员的政治措施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种反精英和怀疑的情绪演化为对部分政治精英的错误认知。“仇官”是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最主要的表现,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在实际生活中会对政府行为产生质疑,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这种怀疑起初是一种对立的负面情绪,后来被民粹主义思潮的非理性激发成社会思潮,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影响到部分对社会不满的民众,由此产生对政府行为的质疑,这种怀疑心理造成对政府公信力的冲击。
其三,对政治精英动机的想象。在受到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观念中,政治精英是“坏”的,民众自身是“好”的,简单化与“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是民粹主义思潮对政治精英态度中影响最大的思维方式。民众的思想意识一旦失去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便会产生对政治精英的怀疑。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是政治精英施政的动机,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但是在民粹化的民众看来,政治精英的动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种怀疑情绪会产生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陀所形容的“塔西陀陷阱”。塔西陀陷阱是指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情况下“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这种不信任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涉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的评判时,民粹主义思潮容易引起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判,甚至会成为某些群体发泄自身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出发点,错不在自身而在政治精英,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重要表现。
2.对经济精英的想象
在中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对内进行改革,在经济上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引进市场经济的所有制模式,对外实行开放,逐步进入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改变了资源分配与经济分配方式,导致财富积累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而造成社会的自然分层,而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会引起对经济精英的怀疑,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对经济精英批判的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方式受到质疑,引起带有反精英情绪的民众对经济精英的不满。
民众将对经济精英财富获取方式的恶意想象和反精英情绪相联系,此时民众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形成对经济精英财富来源的猜测,这种猜测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预判”,其情感色彩大多数时候是负面的,是一种恶意猜测,是长期以来由社会分层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所催生的负面情绪。涉及经济精英的社会事件发生时,信息的传播往往具有时限性,民众在短期内很难获得关于事件详细且“真实”的信息,这种预判就会影响民众对事件的判断,对经济精英的怀疑会形成对经济精英的批判,甚至产生互联网上的“声讨”,“仇富”心理就是对经济精英敌视心理的具体体现。
3.对文化精英的想象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政治权力而进入官僚阶层的,这种政治权力与知识紧密相连。“知识分子”是官方话语的代表,有其政治指向和民众对知识分子行为的期盼意蕴。在民众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怀有士大夫的“救世意识”,应该具有孟子所说的“言官”“御史”的特征。面对权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秉承“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9],应独立于权力之外,对权力应该起到教化作用,应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
21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已经不再依赖古代科举取士制度了,因此,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印象依旧停留在科举时代“士大夫”的形象。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知识分子却更多带有“价值中立”的意味,不再是权力坚定的“规训者”。受历史环境影响对文化精英的想象崩塌,文化精英不是知识上拥有话语权的“规训者”,这种错误想象与现实不符,在民粹化民众有色眼镜的作用下最终形成对知识分子的怀疑。
其一,对知识分子道德的怀疑。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是国家知识精英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而民粹主义思潮会让民众对产生知识分子的官僚精英体系产生质疑,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良心的体现,而变成政治精英的代言人。与此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受到质疑,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变成“砖家”,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认为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迎合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主流话语体系。
对知识分子道德品行的怀疑会对“知识”本身产生怀疑,一旦民众对专家的道德品行产生怀疑,便会产生反智倾向,对知识分子的道德素养产生怀疑,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引起的“反智性”的具体体现。这种怀疑往往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反对知识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同时也会造成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冲击。
其二,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受尊敬的群体,但在民粹化民众眼中,知识分子形象被异化了,原本的“士大夫”形象被异化为政府的代言人,知识分子成为政府代言的工具,互联网上针对知识分子的网络话语如“五毛”“自干五”是网民对知识分子的贬称,“五毛”在互联网上的解释“是一种特定的称呼,原指发表有利于中国政府或相关部门评论的人员”,通常指政府花五毛钱就能获取其支持的知识分子;“自干五”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的简称,指自身没有能力成为“五毛”但是却想要通过迎合政府而获取政府支持的具有知识分子特质的人。这些对知识分子的贬称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被污名化的现实。
对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批判源于对知识分子和政府机关权力关系的想象,因此,知识分子言论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基于这种想象,知识分子的话语不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权贵”,教授不再是“教授”而是“叫兽”,专家不再是专家而是“砖家”,这些侮辱性质的戏称是对知识分子的贬损。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预设,使得民粹化的民众失去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损害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破坏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二)对民众的过度推崇
民粹主义思潮的“反精英”倾向从其反面来看是对民众的过分推崇。中国政治自古以来不乏对民众在历史中作用的思考。1912年,列宁根据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后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或多或少带有民粹主义的影子,自此,国内开始了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1927年,该文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公开发表。因此中国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关注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自此以后,民粹主义也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11]俄国民粹主义的特点是对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崇拜,民众的意见是“道德审判”的准绳,民众是高尚和值得尊敬的。而民众对立面的精英是腐败、堕落、腐朽的,应该推崇民众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巴枯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向农民学习,农民与自然接触产生的民间智慧是无穷的。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主张“精英”向民众学习。如晏阳初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试图通过提高农民的识字水平来提高整体国民的教育程度,以此希望“化农民”,在河北定县进行教育尝试,期望通过对农民的改造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进而实现救亡图存。
1.对民众道德的过度推崇
其一,民众道德是高尚的。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受俄国影响较深,从五四运动前民粹主义思潮的传入到之后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民粹主义思潮接近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思想体系。“统治者、统治精英上台下台,政治时而清明时而衰朽,时势时而太平时而动荡,而民众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却一直在台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历史主角。”[12](P370)民众是政治运动的核心,承担着政治上的重要角色,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君王史”,更应该是“民众史”,民众是君王统治的对象,同时是君王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随着“1919年五四思想启蒙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等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关键事件的发生,民粹主义思潮如幽灵一般贯穿于中国的“民众史”,农民道德是高尚的,需要向民众去学习。进入21世纪后,对“民众的崇拜”变成推崇民众进行道德审判工具的思想渊源,“民众的判断”是道德审判的准绳。
其二,民众具有道德审判的力量。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民众是有道德的,也是道德审判的最终裁决者。追溯思想史,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拉甫洛夫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希望通过走进“米尔”(村社)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从而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对民众道德的崇拜是淳朴的改革派的政治主张,但是这种思想意识最终因为民粹主义者的个人私欲改变了原来政治理想的淳朴性质,转而进行谋求“暴力革命”。这种暴力是恐怖活动,比较典型的是“自由与土地”社后期被恐怖分子控制,使“民粹式的理想”流变为“恐怖主义”的运动。俄国民粹主义经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传入中国,成为对民众过度崇拜的社会思想潮流,这种思想是当时期待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抓住的“稻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不仅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值得学习,中国普通民众中的生活智慧也值得学习,相对于腐朽的清政府,民众拥有丰富的智识系统,因此,更具有道德审判的力量。
2.对民众理性的过度推崇
其一,民众是政治活动的动力。“天”是中国古代君王合法性的代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君王是“代天言之”,是天意的代言人。君王应该具有德行,只有“以德配天”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历史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崇尚“三代之治”,在“三代之治”时,君王上有一个“天”,天的旨意是高于君王的,而“民意”恰恰是天意赋予民众的思想意识,是天的旨意,因此,君王需要推行“民本”思想,以“民”作为其统治的根本。
在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看来,民众才是历史舞台的核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自古以来民众创造历史愿望的呼声。中国历史中有一部是帝王史,由史官来撰写,另一部是民众史,由民众来书写。在历代王朝的更迭中,王朝的衰败模式大多是“揭竿而起”的方式,而在王朝更迭的关头,民众起到巨大作用。有民众的支持,平民领袖才有进行政治活动推翻旧王朝的动力,因此,民众是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动力。
其二,民众的判断更具合理性。以往的国家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其理论原点是“个人主义”,需要民众看待社会事件时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卢梭的“公意”[13]是这种集体意志的体现,公众的意愿比个人的意愿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是民众的代表,他们的言论更能称为“公意”。这种公意是抽象的契约思维,以人的私有财产为基础。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话语体系下的民粹主义思潮视民众利益为一个整体。契约论不能解释当代的中国问题,但能解释民众的集体意志。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众的理性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色彩,民众的判断更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