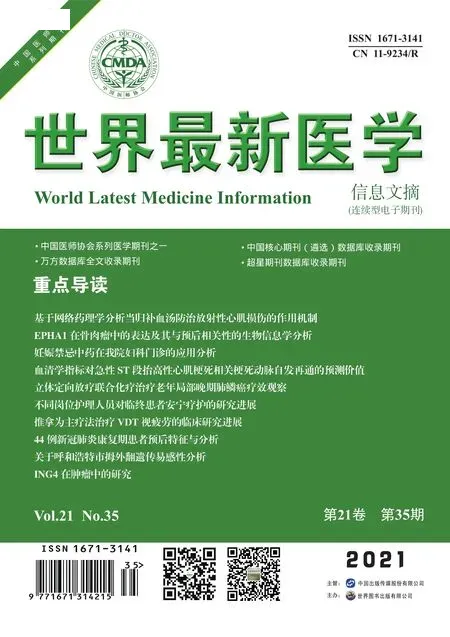从西汉政治制度谈《黄帝内经》脏腑理论
2021-01-10王月
王月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072)
0 引言
对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各种学者众说纷纭[1]。但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它约成熟于公元前1世纪,上限为《史记》,下限为《七略》,也即大致位于西汉武帝时期。因此,了解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黄帝内经》的脏腑理论。
1 西汉政治制度
1.1 西汉中央制度——三公九卿制
在汉代,中央官制依然是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三公即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但严格来说,三公都是丞相[2]。三公里的丞相,属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且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三公中的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3],从秦朝开始,军事长官就靠虎符分一半军权给皇帝,汉承秦制以后,军事长官的军权进一步削弱,作战也要听皇帝的命令,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自由。御史大夫便是监察官,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4]。
九卿并不是只有九个,而是三公之下中央官员的泛指[5]。九卿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重要纽带,作为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西汉时期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做中朝官制度[6]。中朝官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牵制皇权、监督皇权。
1.2 西汉地方制度——郡国并行制
虽然汉承秦制,但汉高祖刘邦认为,秦朝之所以快速灭亡,是没有像周朝一样实行分封制,导致皇帝遭遇外敌时没有兄弟诸候帮助的结果。于是汉朝学习秦朝,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2],地方郡国拥有中央的权力,对地方放权意味着中央集权被削弱,部分地方郡国有了和中央对抗的实力。为了加强皇权统治,也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统治时期,采用主父偃的建议,采取“推恩令”[7]——地方郡国的继承不再局限于嫡长子,所有的儿子都可以分封到郡国的一部分。因此,地方郡国越分越小,地方郡国的实力也被削弱。
《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1年,此时推恩令早已实行,郡国的地位已经和普通的郡县相差无几。因此,《黄帝内经》中提到的州郡与推恩令实行后的郡国,应当处于同一行政地位。
2 《内经》中的官职
《内经》中多次以官职来比喻人体脏腑功能,在《灵兰秘典》篇中曾写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这段话把官职和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结合起来,以求合理阐述五脏六腑的生理特点,看起来一目了然,但汉朝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其中提到的官职,与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有较大出入。因此,根据史实来对比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官职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黄帝内经》中的脏腑理论,提高我们对中医理论认识的准确度。
3 从西汉官职再论《内经》中脏腑功能
3.1 心
心者,君主之官。心在人体中的地位相当于皇帝,掌管人体所有的生命活动,即“神明”。古代皇帝自称“天子”,来说明自己是君权神授,表明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侵犯,未尝不是把自己当做“神明”的一部分[8]。中医理论中,神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明包括人体所有生命活动,狭义的神明则专指人体精神活动。西汉政治制度中,皇帝是国家的中心,作为君主,与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相关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还有对人民方方面面的约束。西汉时期的皇帝,通过分封制削弱了地方实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整个国家的管控更加有力,体现的是统治力量的增强和统治范围的全面。因此,广义的神明的解释显然更合本意。
3.2 肺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在汉代三公九卿制中,三公都是丞相[9]。可是而肺并无三个,故肺对应的是三公中的丞相,而不应该是三公合起来的丞相职能。“治节出焉”——治节,即治理调节。刘力红在《思考中医》[10]一书中解释肺主治节,认为“节”为节气,是古代历法的记载方式,三天为一节,体现的是气候短期的变化,肺主治节就是肺来帮助人体适应短期气候的变化,若肺气不足,人体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则易外感。而且肺合皮毛,其治节体现在对皮毛的控制上,临床有肺气虚患者,皮毛疏松,不耐外邪,一旦气候变化邪气便从皮毛趁虚而入,而为反复外感,正是由于肺气虚而不能“治节”。其联系到西汉时丞相的职能,汇报给皇帝的事务也是各种人世的变化,与气候的变化相类似。显然,肺的功能,是“君”的使者,代替“君”来亲自管理“臣”。故此,肺对除心之外的每一个脏腑都有多少的控制作用,这与中医基础理论中“肺朝百脉”的功能相一致。
3.3 肝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将军即军事长官,将军并非莽夫,内经中对于将军的描述却是“谋虑”,更像是描述一个军师而非莽汉。在汉代的三公九卿制中,太尉是军事长官[11],但因为不掌握实权,这位军政长官的专长并不是上阵杀敌,而是筹谋策略、下达指令。
3.4 胆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中正之官,即司法官员。还是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三公九卿制地位最高的是三公,对应五脏六腑中的肺、肝、胆。一般认为五脏最重要,六腑次之。但是根据《黄帝内经》,六腑中的胆和五脏一样重要,又有“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的结论。与西汉当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西汉的监察制度不断优化,是政治体系的一次大完善,国家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接受监察官的监察[12],以免滋生腐败,与“十一脏腑取决于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3.5 膻中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臣使之官即作为臣子的官员,其地位应该相当于“九卿”。至于喜乐出焉,从九卿的具体职责可以看出,“喜乐”应当是情绪的代称,臣使之官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上传下达,他们的言语直接影响了“君主”的喜怒。故此,喜乐出于“臣使之官”。
3.6 脾胃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13]。“仓廪之官”我们可以理解为管理国家粮库的官员。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变的真理,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说国家的繁荣是一棵树,那么农业就是它的土壤。因此,“仓廪之官”是为所有的“官”提供物质来源的重要脏腑。然而在中国古代,仓廪之官也最容易滋生腐败的职位,因为他的掌握着国家最重要的粮食,粮食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资源,而在脏腑中,脾胃疾病总与其他脏腑的疾病相兼出现。
3.7 大肠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传道之官,即负责运输的官员,受盛之官,即负责容纳的器具。笔者认为两者可以合起来理解为转运使,大肠是运粮食的人,小肠是放粮食的器具,两者组合,把粮食转到该用的地方去。比如发生了饥荒,要把粮食运到灾区,粮食已经送到地方,地方收下粮食,把粮食分给地方人民,至此,粮食已经变成了食物,故而“化物出焉”。至于大肠之“变化”,则是将粮食变为食物送至民众手中,这与《黄帝内经》中对于大肠的描述有所不同,目前中医基础理论对于“变化”的认识是由食物变化为糟粕。
3.8 肾
到了这里,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不少医家认为“作强之官”指的是手工业者,但是“伎巧”这个词语的描述,则显得肾这个脏腑有一种游刃有余的灵活感。结合肾的生理功能,即主蛰,封藏之本,显得十分含蓄而有内涵,似乎没有“伎巧”所描述的灵活感。因此对于肾来说,笔者认为他应该是皇帝的老师,相当于中朝官[14],而我们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一身之气都来源于肾气,充养于脾气,即便是身为君主之官的“心”,亦离不开先天之本的充养,连君主都要受它约束,自然“作强”,这与西汉皇帝受中朝官制约监督的状况不谋而合。
3.9 三焦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农业,而提高农业粮食产量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水利灌溉,故而历代帝王均有兴修水利的习惯,哪怕是昏庸的隋炀帝,都知道要开通大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既保证了农业的发展,又能够应对旱涝灾害[15]。《黄帝内经》对于三焦的描述,和水液代谢密切相关,而脾作为土脏,喜燥恶湿,脾不运化最易生湿,湿即水液代谢异常产物,因此脾与三焦对水液代谢的重要性,如同决渎之官与仓廪之官对农业的重要性。
3.10 膀胱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州都之官是标准的地方官员,是国家意志和中央权力在地方的分散[16]。“津液”应当是各种液态精微物质,对于州都的实力,分散在州都里的每一个人身上,就像是一个个水滴,水滴聚成小溪,小溪汇成江河大海,大海就是整个国家。
综上所述,五脏六腑,是人的体生理机能进行的场所,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各个机构不同的运转。《黄帝内经》的成书,亦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时代特点,其成书的西汉时期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特点,而熟悉当时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黄帝内经》的医学内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相比《黄帝内经》中对于脏腑生理寥寥几句的概括,了解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将这样的政治背景与《黄帝内经》的理论相互印证,更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医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