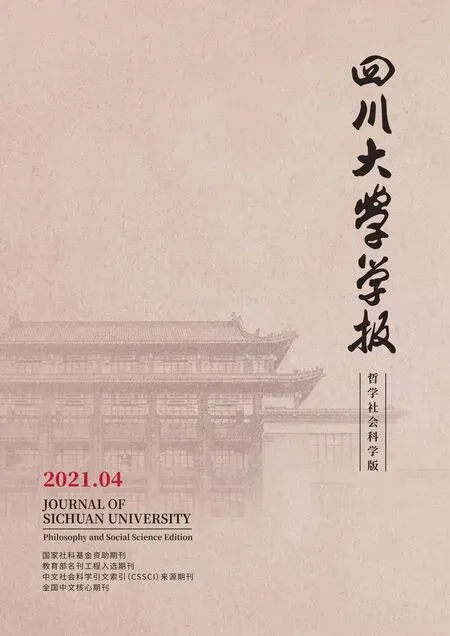普遍主义与例外主义的变奏:战后初期美国围绕国际人权的争论
2021-01-08刘祥
刘 祥
国际人权(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是人权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国际层面围绕人权,尤其是“作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主题的人权”的关注及活动。(1)Louis Henk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s Rights,” Nomos, Vol.23, 1981, Human Rights, p.259.“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机制”等议题受到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者的长期关注。而史学界对国际人权的研究始于美国学者保罗·劳伦(Paul Gordon Lauren)于1998年出版的《国际人权的演进》,他以不同时期世界范围内重要个人、社会组织对国际人权的构想及其面临的挑战为主线,描述了国际人权由理念逐渐发展为现实的曲折历程。(2)Paul Gordon Laur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Visions Se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劳伦的著作为此后众多个案研究奠定了基础,史学家尤其对国际人权的起源、大国国际人权政策、跨国人权运动等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
对美国与国际人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一是1940年代美国在奠基联合国人权议题中扮演的角色,二是19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的兴起及其全球影响。(3)关于1940年代美国参与联合国人权议题的研究,参见Mary Ann Glendon, A World Made New:Eleanor Roosevelt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Elizabeth Borgwardt,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lenn Mitoma, Human Right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American Pow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Rowland Brucken, A Most Uncertain Crusade: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1941-1953,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4.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美国人权外交是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代表性著作主要有Barbara J.Keys, Reclaiming American Virtue: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of the 197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Joseph Renouard, Human Righ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rom the 1960s to the Soviet Collaps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对美国参与国际人权立法和人权外交的探讨,参见刘杰:《美国与国际人权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世安:《评美国的跨国市民社会运动与人权外交》,《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第13-21页。这些研究在揭示美国国际人权政策发展的同时,存在多重缺陷:一是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活动,忽视了国际人权在其国内政治中的复杂影响;二是没有深入挖掘原始材料并据此分析国际人权议题对于美国的深刻内涵;三是未能从概念化的角度总结战后美国围绕人权争论的两大理念特征。国际人权虽然关注的是人权在国际层面的发展,但它与国家内部同样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将聚焦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对国际人权的讨论,特别是围绕以《联合国宪章》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国际人权文件在美国的适用性问题,试图从普遍主义与例外主义两大理念竞争的角度出发,分析美国参与国际人权议程的国内回响及其对美国人权政策的深远影响。
一、国际人权话语与战后初期美国国内政治
二战是人权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及其带来的惨痛伤亡推动着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思与深入研究。纳粹德国对人权的侵犯被视作战争根源之一受到世人关注,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被视作构建长久和平的重要前提。正是在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中出现了国际人权的理念,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普遍接受的人权文件,二是组建国际组织推广人权理念,二者都体现出人权的全球特征。就人权文件而言,二战时期美国社会组织发布了大量以宣言或法案为名的人权文件,试图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法学家威廉·刘易斯(William Draper Lewis)领导制定的《基本人权声明》,其中囊括了人身自由、公民政治权利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权利。(4)Statement of Essential Human Rights, February 7, 1944, The Statement of Essential Human Rights Records,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rchives, Box 4, Folder 41, Biddle Law Libra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Philadelphia, PA.
国际人权理念还体现为通过国际组织来推动人权,这在战时美国国内的国际主义组织中得到普遍支持。美国国联协会(League of Nations Association)在1944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美国应倡导建立由专家组成的永久性人权委员会,其功能是关注国际权利法案的制定及实施,并在各国设立分支办公室,协助国家和地方机构推动人权保护,当对人权的侵犯威胁到和平时,委员会有权调查并制定报告。(5)Berley Levy, “International Safeguard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403, Sep.1944, pp.552-575.正是在美国社会组织和不少拉美国家的推动下,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多处涉及人权,人权自此正式迈入国际政治领域。(6)关于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宪章》中人权条款的关系,参见刘祥:《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第123-133页。
战时美国对国际人权构想的底色是国际主义思想,这与美国政府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划相辅相成,因而取得较大的成功。战后初期,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国内得到延续,联合国被视作维护和平的重要平台,美国社会组织继续关注联合国人权活动,特别是新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及其制定的国际人权文件。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出现对国际人权的争论。宪章在美国国会通过后,众多美国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宪章中的人权条款为依据,呼吁国际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美国在国内政治中践行对宪章的人权承诺。这一承认国际人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观点往往遭遇反对意见,后者提出宪章人权条款并不完全适用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法律和权利理念塑造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这开启了美国国内围绕国际人权的争论。
战后美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战时生产向和平时期的过渡,这与就业密切联系,“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问题受到关注。充分就业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提出的“第二权利法案”,其内容涉及包括工作权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7)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11, 1944, In Samuel I.Rosenman,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4-45,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0, pp.41-42.这是罗斯福延续新政的努力,受到美国产联、全国农民联盟以及自由派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支持。(8)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5, p.260.1945年初,充分就业法案被提交到美国国会,要求联邦政府通过投资和财政拨款等形式确保具有劳动能力及意愿的美国人享有充足的就业机会。(9)S.380, Introduced by James E.Murray(D-Montana), Robert F.Wagner(D-New York), Elbert D.Thomas(D-Utah), Joseph C.O' Mahoney(D-Wyoming), Congressional Record, 7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Senate, January 22, 1945, pp.377-378.这些要求“本质上都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显然与美国传统权利理念相冲突。(10)Henry Hazlitt, Full Employment:An Analysis, New York: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 1945, p.5.美国国会在战后为此召开听证会,就业权的普遍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国际主义组织代表认为宪章中的人权条款包括充分就业,在国内实现这一原则对于提升对联合国的信心大有帮助。(11)Statement of Ulric Bell,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mericans United for World Organization,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5,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United States Senate, 7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on S.380, July-September, 1945, Washington, D.C.: U.S.Govt.Print.Off., 1945, p.186.还有经济学教授将推动充分就业视作美国加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时做出的承诺,认为美国理应承担这一责任。(12)Statement of Ernest M.Patterso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5, Hearings, p.622.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通过的一份报告,将刘易斯的《基本人权声明》中的就业权条款视作对普遍就业权的支持。(13)Assuring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Competitive Economy,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to Accompany S.380, Washington, D.C.: U.S.Govt.Print.Off., 1945, pp.69-80.
法案反对者则对充分就业权利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一位企业代表反对就业权与工作权的提法,他认为将教育、住房、健康、休憩等权利都列为人权的做法将会削弱人权的实质内涵,这些权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权不同。(14)Statement of Beardsley Ruml, Treasurer of R.H.Macy &CO.,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5, Hearings, pp.397-398.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Taft)则警告称,工作权利的获取只能存在于自由企业制度中,任何来自政府对就业的直接承诺都将“最终导致指令性工作,而这正是苏联的体制”。(15)Clarence E.Wunderlin Jr., ed., The Papers of Robert A. Taft, Vol.3, 1945-1948,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这些声音实际上都是对普遍人权的质疑,尤其是指出了美国的国家角色、权利理念与充分就业权之间的巨大差异,反对将宪章运用于美国,例外主义由此得以凸显。正是由于这些反对意见,最终国会通过的法案抹去了最初的新政特征,这份由杜鲁门签署的《1946年就业法》(Employment Act of 1946)甚至完全放弃了“充分就业”的提法,只是模糊地提及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手段为就业创造条件。(16)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p.263.充分就业法案在国会遇阻体现出以工作权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权利此时在美国的不利处境,普遍人权的话语未能以符合美国理念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新政实践。
国际人权话语为战后美国的权利运动提供了更大的价值,这首先体现在平权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问题上。1920年代,美国妇女活动家提出以平权修正案的形式消除政治和法律层面基于性别的歧视,并要求国会为此采取相关措施。1923年,平权修正案被提交到国会。此后新政及二战时期,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尤其增进了对该提案的支持,1944年大选时两党党纲都对这一提案表示欢迎。但劳工妇女组织对此提案却表达了鲜明的反对,这些组织认为平权修正案只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口号,它将使基于性别的劳工保护性立法无效,为家庭主妇和丧偶者设立的福利将被削减,修正案的结果将使女性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17)关于二战之前美国围绕平权修正案的争论,参见Nancy F.Cott,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1920s: The National Woman's Part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1, No.1, Jun.1984, pp.43-68; Rebecca Dewolf,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nd the Rise of Emancipationism, 1932-46,” 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38, No.2, Jan.2017, pp.47-80.
平权修正案在战后再次被提交到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45年9月为此召开听证会。二战时期出现的普遍人权话语为平权修正案提供了新的动力,宪章中明确提出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的代表援引《基本人权声明》以及宪章中的人权条款对修正案表示支持。(18)Statement of Mrs.Harvey W.Wiley from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Equal Rights Amendment, Hearing before a Subcommittee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79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S.J.Res.61, September 28, 1945, Washington, D.C.: U.S.Govt.Print.Off., 1945, pp.7-8.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an's Party)的代表列举了宪章中禁止性别歧视的条款,并称“性别平等理念及实现这一理念的决心受到全世界代表的支持”。(19)Statement of Alice Morgan Wright from National Women's Party, Equal Rights Amendment, Hearing, p.12.类似的观点在听证会上多次出现,国际人权的普遍性成为其重要话语。反对派则高举美国例外主义的旗帜,美国劳联和产联称修正案将“摧毁现存的法律制度”,所有涉及妇女和家庭的保护性法律都将受影响。(20)Quote from Statement of Mrs.J.A.Stone from 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of America, Equal Rights Amendment, Hearing, pp.52-53.有妇女组织指出涉及妇女地位的法律主要是各州法律,平权修正案将侵犯州权。针对这些质疑,全国妇女党曾制作小册子声明修正案不会干涉各州权力且不会削减妇女活动此前取得的成果。(21)National Woman's Party, Equal Rights Amendment:Questions and Answers, Washington, D.C.: U.S.Govt.Print.Off., 1946, pp.9-12.不过这并未平息争论,在1946年参议院的讨论中,反对者仍以州权进行反击,来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认为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该州“超过一百部法案”将需要修订。(22)Speech by Charles O.Andrews(D-Florida), Congressional Record, 7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July 17, 1946, p.9224.罗斯福夫人和前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同样反对平权修正案,她们批评其为“欺骗性口号”,不能实现它所宣传的目标,反而会使妇女丧失已有的权利,尽管罗斯福夫人同一时期在联合国支持设立妇女地位小组委员会以提升全世界妇女的地位。(23)Quote from Speech by John R.Murdock(D-Arizona), Congressional Record, 7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July 19, 1946, p.9401.平权修正案的反对者以例外主义为核心,构筑了关于美国特殊的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的话语,以拒绝宪章人权条款的普遍性,最终阻碍了平权修正案在战后的实现。
国际人权话语在非裔美国人权利问题上引起了更大争议,不少黑人组织将目光转向联合国,采取直接的请愿行动。(24)关于战后美国黑人组织向联合国的数次请愿,学界已有非常充分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黑人组织如何运用国际人权话语及其行动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影响。已有研究参见Carol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1944-195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8-112; 于展:《冷战初期美国黑人的联合国请愿活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1-22页。1946年6月6日,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要求关注美国黑人人权问题。请愿书用统计数据展示了美国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并指明宪章的序言、宗旨以及联大及其经济社会理事会职能部分都包括推动人权的表述,新成立的人权委员会也有权为保护少数群体和禁止歧视提供建议,因此联合国应通过人权委员会研究美国黑人的处境,为“抑制和消除”种族歧视及实现“更高标准”的美国人权提供建议。(25)A Peti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on Behalf of 13 Million Oppressed Negro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1-14, Papers of the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Part II, Records and Correspondences, 1943-1947, Reel 28(Hereafter cited as NNC Papers, Part II),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这份请愿书在黑人群体中得到不少支持,《芝加哥卫报》的一位读者建议“其他黑人组织也应向联合国请愿,使美国在对外呼吁民主的同时,世界舆论能够注意到美国的虚伪”。(26)“Interest in NNC Appeal to United Nations,” Chicago Defender,Aug.17, 1946, p.14.这很快成为现实,1947年10月,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领导人杜波依斯(W.E.B.Dubois)主持撰写了另一份递交给联合国的请愿书。该请愿书中称美国黑人向国会的请愿屡遭失败,表明“国内的纠正手段已经穷尽”,应将黑人问题置于国际组织考虑,并详细论证了联合国有权关注这一问题。(27)W.E.B.Du Bois, ed., An Appeal to the World:A Statement on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the Minorities in the Cases of Citizens of Negro Des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n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Redress, 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lored People, 1947, pp.1-10.
向联合国请愿的做法也引起质疑甚至是反对,全国黑人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主席玛丽·贝休恩(Marry Bethune)称她“对于请求联合国调查美国黑人的做法不是很确定”,因为联合国处理的是国际问题而非国家内部问题。(28)Marry Bethune to Max Yergan, November 20, 1946, NNC Papers, Part II, Reel 28.逐渐升温的冷战斗争则为请愿活动带来了更深的质疑,联邦调查局认为全国黑人大会受苏联的控制。(29)Edward Scheidt to the Bureau, Oct.22, 1946, FBI File, Quote from Brenda Gayle Plummer, Rising Wind:Black Americans and U.S. Foreign Affairs, 1935-19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172.有色人种协进会也受到了更多批评,西弗吉尼亚的一家报纸认为协进会的请愿只是为了舆论造势,它在羞辱美国的同时将“为苏联提供新的武器”。(30)Quote from Anderson, Eyes off the Prize, p.108.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南部保守派议员的长期抵制,黑人组织的“美国性”受到质疑并因此受到影响,全国黑人大会陷入财政危机,坚持扩大国际影响的杜波依斯也与有色人种协进会管理层进一步分裂。以人权普遍性为工具向联合国请愿扩大了黑人诉求的影响力,却威胁了美国例外主义话语的塑造,极大地限制了民权运动在此时的进展。
简言之,二战时期美国社会组织和政府共同参与塑造的国际人权话语对战后美国有着持续影响,工人、妇女、黑人权利活动家利用普遍人权的话语,特别是宪章中的人权条款来为自身议题服务,这些活动大多没有取得成功。反对者利用美国例外主义对改革措施提出反对意见,强调以美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双方的争论体现出美国国内出现的微妙变化,战时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在此时开始与更为实际的政治和社会需求产生冲突,国际人权的争议性质开始凸显。
二、例外主义与国际人权反对之声的发展
1947年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运行,杜鲁门任命罗斯福夫人为美国在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委员会很快开始商议制定国际人权文件,直到1948年底《世界人权宣言》最终在联大获得通过,这一历程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不少社会组织仍然对此表示极大热情,但围绕联合国人权文件的可能性、有效性及其对美国的潜在影响,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国际人权的声音,反对意见在运用例外主义话语的同时进一步扩充了其内容,并逐渐将其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使得国际人权反对之声在1940年代末的美国得到迅速扩展。
1947年6月,针对联合国启动制定国际人权文件,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发表声明质疑道:“人权宣言如何能适用于所有人,而不只是基于西欧和美国价值观念之上的权利声明呢?”(31)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49, No.4, Part 1, Oct-Dec.1947, p.539; Christopher N.J.Roberts, The Contentious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2.该组织指出,18世纪美法革命时期的权利文件对于20世纪的“印度尼西亚人、非洲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并不具有说服力”。(32)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pp.541-543.美国人类学会显然对于联合国能够制定一份反映世界不同文化的人权文件表示怀疑,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也认为联合国人权文件有“倡导美国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危险”,他进而质疑人权文件与改善人权状况之间的相关性。(33)Julian Steward, “Comments on the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50, No.2, Apr.-Jun.1948, p.352.
除了对其可能性表示质疑外,美国也存在质疑国际人权文件有效性的声音。1948年7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对于行政部门在联合国人权问题上的态度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人权文件上的“理念和原则现在无法在我们国内得以实现,也不确定将来能够完全实现”,这可能激起“对美国虚伪的指控”,最终损害对联合国的尊重和信心。(34)George Kennan to Humelsine, the Under Secretary Office, July 8, 1948, Subject Files of Duward V.Sandifer, Box 7, Folder: Human Rights, General 1948,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凯南对美国国际人权政策的批评得到了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认同。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认为“某个特定群体自称的道德普遍性往往并不适用于另一个群体”。(35)Hans J.Morgenthau, Politic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48, pp.191-196.1950年春,摩根索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美国的正义观念在国际上可能并不适用,因为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对这些观念的共识,“在国际范围内求助于道德原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可能只反映某个特定国家的理念而不能获得普遍承认。(36)Hans J.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1, pp.34-35.凯南和摩根索都被视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国际人权并非推动美国外交的有效工具。
美国国内针对国际人权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体现出例外主义的理念,即美国存在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人权理念,将其国际化可能不会提升美国在世界舆论中的地位,反而会加剧局势紧张。其中,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以下简称律师协会)是1940年代末持续反对国际人权的重要组织,它聚焦于从法律角度批评国际人权对美国的危害,对国际人权在美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1945年,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律师协会主席大卫·西蒙斯(David A.Simmons)认识到美国权利理念与宪章人权条款的差异,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以权利法案为基本法的国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世界其他地方权利的受限”,宪章中的人权条款只针对“其他国家”。(37)David A.Simmons, “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31, No.7, Jul.1945, p.378.同样参加会议的律师协会成员威廉·兰瑟姆法官进一步认为宪章设立的人权委员会将开启“潘多拉魔盒”,需要国际法院来裁定哪些属于宪章规定的国内事务。(38)William L.Ransom, “Let's Look at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Vol.31, No.7, Jul.1945, p.342.
194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制订人权文件,并于1948年初起草了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权宣言两份草案,律师协会对此密切关注,2月当选协会主席的弗兰克·霍尔曼(Frank E.Holman)在此后成为反对国际人权的重要发言人。4月22日,霍尔曼在演讲中批评人权宣言中的社会经济权利是“对苏联阵营的绥靖”。5月,在一次研讨会上,霍尔曼认为国际人权文件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基本经济和社会传统”。6月,霍尔曼在犹他州声称国际人权法案中的“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条款将“取消美国移民法律,并使得大量的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进入到美国”。9月,霍尔曼正式就任协会主席,他很快确认主席的使命就是要“揭露联合国众多机构,特别是人权委员会支持的条约法律带来的危险和谬误”。(39)Frank E.Holman, The Life and Career of a Western Lawyer, 1886-1961, Baltimore: Port City Press, 1963, pp.361-365, 373.
10月,霍尔曼在加州律师协会年会上对国际人权发起了直接攻击,其批评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他担心国际人权文件将使其他地方的权利内容强加于美国人之上,特别是苏联主张的与美国“个人权利基本理念有很大差异”的社会经济权利。其次,人权公约草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在权利保障中的职责,这与美国的国家角色不符,而且公约可能需要通过新的国际法院来实施。最后,如果美国支持国际人权,那么通过条约或只需要总统批准的宣言就定义了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对美国宪政的“革命性变革”,侵犯了国会及州的立法权力。(40)Frank E.Holman, “An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Proposals Have Dangerous Implications for U.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34, No.11, Nov.1948, pp.984-986, 1078-1081.霍尔曼反对意见的核心正是美国例外主义,他认为美国人权状况远高于国际水平,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反而会降低其人权标准,且需要防止其他国家借国际人权干涉美国内政。霍尔曼的这次演讲奠定了他对国际人权的总体态度,在从1948年底开始长达六周的全国巡回演讲中,霍尔曼大谈“美国遗产”“美国精神”“法下的自由”“家长制与国家主义”,将他和律师协会塑造成为美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捍卫者。(41)Holman, The Life and Career of a Western Lawyer, p.375.除公众宣传外,霍尔曼还致信国务院要求“美国律师能够在宣言通过前有机会仔细研究宣言内容”,特别是考虑到该文件“可能损害美国权利法案”。(42)Frank Holman to G.Bernard Nobl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9, 1948, Records Relating to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Affairs, 1940-1956, Box 2, Folder: Frank Holman,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RG5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大获得美国支持并通过后,霍尔曼仍提醒美国人该文件的潜在危害。(43)Frank E.Holman, “International Proposals Affecting So-Called Human Right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14, No.3, Summer, 1949, p.485.
霍尔曼的预言在1950年初几乎变为现实。4月24日,在“藤井整诉加利福尼亚州”(Sei Fujii v.State of California)一案的判决中,加州上诉法院援引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条款,宣布自1930年以来在该州实施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无效,未入籍的日本人同样有权在该州购买土地。判决书声称:宪章中的人权条款经参议院批准后就具有了条约的效力,依据美国宪法成为境内的最高法律,《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明确规定财产权为人人皆可享有之人权。(44)“Extracts from Briefs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in Fujii v.California,” Law Guild Review, Vol.10, No.3, Summer, 1950, p.54.《外国人土地法》与这些国际文件相冲突,因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判决一经公布立刻受到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宪章缺乏自我实施条款,不能自动成为在美国境内实施的法律。(45)“U.N.Pact Assailed as ‘Supreme Law’,”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50, p.19.霍尔曼指出判决如若生效,共产主义国家将可以在西海岸任意购买土地,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的推论将使美国的自治权不复存在。(46)Frank Holman, “Treaty Law-Making: A Blank Check for Writing a New Constituti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36, No.9, Sep.1950, p.787.案件也引起了国会的关注,有参议员称该判决将使“任何一州对性别做出区分的法律都将失效”。(47)Speech by Holmer S.Ferguson(R-Michigan), Congressional Record,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April 28, 1950, p.5996.受此影响,1952年4月,加州最高法院在该案最终判决中依然裁定《外国人土地法》无效,但援引的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而非联合国人权文件,该判决书还指明“宪章条款并不能凌驾于国内法之上”。(48)“Court Upsets Alien Land Law of California: Finds It Violates 14th Amendment,”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il 18, 1950, p.14.
1950年代初国际人权在美国引起更大争议的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罪公约》)的制定。该公约是对大屠杀的反应,它于1948年12月9日在联大正式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一个人权公约。(49)关于美国在《灭种罪公约》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参见Brucken, A Most Uncertain Crusade, pp.171-209.《灭种罪公约》引起律师协会的警觉,这一“国际法下的新罪名”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的种族问题,公约对灭种罪的定义及其惩治也与美国法律制度多有龃龉。1949年2月,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认为参议院不应仓促批准公约,它可能导致“将指控和审判美国人的司法权交给国际机构”。(50)“International Covenant: House Urges Study of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35, No.3, Mar.1949, p.197.霍尔曼举例称,底特律的种族暴乱、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遭遇都可能受公约管辖,责任人可能在国际法庭受到俄国法官的审判。(51)“U.N.Covenants Hit as Peril to U.S.Way of Life,” Chicago Daily Tribune, April 17, 1949, p.8.
1950年初,美国国会召开对《灭种罪公约》的听证会。国务院代表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司法部代表菲利普·帕尔曼(Philip Perlman)代表行政部门表达了对公约的支持。腊斯克认为公约符合美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冷战对抗中,美国需要批准公约来巩固自己的“道德领袖地位”。(52)Statement of Dean Rusk,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enocide Convention: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on Jan.23-25, Feb.9, 1950, Washington, D.C.: U.S.G.P.O., 1950, p.21.帕尔曼则申明公约不会让渡国家主权,公约也没有剥夺州的立法权,种族灭绝不会在美国出现,批准公约只是表达美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态度,履行国际义务。(53)Statement of Philip B.Perlman, Solicito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Genocide Convention: Hearings, 1950, p.53众多社会组织代表也在听证会上支持批准公约。除了宗教组织和国际主义组织继续从权利普遍性来论证外,也出现了其他更为现实的因素。美国产联强调种族灭绝对劳工经济的负面影响,大量难民的出现将造成经济动荡。(54)Statement of Stanley Ruttenberg, CIO, Genocide Convention: Hearings, 1950, p.125.东欧裔美国人组织强烈要求美国挑战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政策,希望借公约给苏联施压,美国劳联同样认为批准公约有益于冷战斗争。(55)Statement of George P.Delaney, AFL, Genocide Convention: Hearings, 1950, p.413.这表明在例外主义的攻击之下,普遍人权的话语已不足以支持美国批准公约,需要加入更多的现实考量。反对批准公约的力量也不甘示弱,律师协会代表批评公约“并非美国观念的产物”,并以联合国文献记录为证据,批评美国代表在公约制定过程中未能坚持立场,公约未能体现美国法律理念。(56)Statement of Alfred J.Schwepp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Genocide Convention: Hearings, 1950, p.198.
双方的分歧未能化解,主持听证会的小组委员会在1950年4月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即建议美国批准公约,但带有四点谅解,以表明美国对公约中“有疑问的语句含义”的看法,尤其强调公约将不会改变美国国内的罪名定义。(57)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Report,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Vol.2, 1949-1950, Washington, D.C.: U.S.Govt.Print.Off., 1976, p.788.尽管如此,报告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仍然遭到冷遇。当国务院法律顾问强调公约对美国道德地位的影响时,参议员亚历山大·怀利(Alexander Wiley)声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没有资格在道德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对美国指手画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Tom Connelly)则认为“一旦我们签署了公约,当其他地方出现骚乱时,每个国家都会抓住我们,希望我们去干涉和制止”。(58)Genocide Convention, May 23, 1950, September 6, 1950,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Vol.2, 1949-1950, pp.384, 653.由于未能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内部获得一致支持,《灭种罪公约》就此在参议院搁浅,直至里根时期才最终获得通过,这是反国际人权运动的重要成果。
围绕《灭种罪公约》的争论表明,美国国内基于例外主义的反国际人权话语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例外主义首先体现为美国的独特性,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以人身自由和公民政治权利为主的传统权利理念,以《权利法案》为核心的权利文件,独特的联邦-州二元法律体系等等。这些在战后美国围绕充分就业、平权修正案的争论以及美国人类学会的声明中都有体现。随着联合国人权活动的开展,例外主义的重心转向避免联合国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干涉。这首先体现在对黑人请愿的批评,随后又体现在美国律师协会对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的持续攻击之中。例外主义日益壮大的同时冷战斗争持续升温,美国一方面需要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借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来攻击冷战对手;另一方又要在国内塑造舆论共识,避免国际人权对国内事务的干涉。这两大目标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使得美国急需做出政策调整。
三、国际人权的异化与美国的转向
1950年代初,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反国际人权的例外主义话语的内涵不断扩大并逐渐与国家安全产生联系,这为美国国内诸多议程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会,使国际人权在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异化,即对其批评附着了其他复杂的因素,最终对国际人权在美国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对联合国批评的增多。罗斯福在战时构想的在联合国基础上的大国合作随着冷战的开始而破灭,联合国成为双方争取世界舆论的竞技场,美国国内质疑联合国为苏联所操纵的声音高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及对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反对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质疑。
国际人权异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它成为国会争夺外交权力的工具。1951年9月14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瑞克(John W.Bricker)在参议院引入决议案,要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总统签署的条约不能削减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不得制定任何与美国公民权利自由、政府制度形式以及其他国内管辖权相关的条约或行政命令。按照美国宪法,总统享有缔约权,同时宪法第六条又规定:“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受其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相抵触的内容。”(59)转引自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8页。布瑞克的决议案正是要求废除这一条款,而这是他长期反对国际人权态度的延续。他曾在国会上批评联合国人权公约将会损害美国权利法案赋予公民的权利,他还特别指责美国国务院企图利用人权公约来摧毁美国的新闻自由。(60)S.Res.177, Submitted by John W.Bricker(R-Ohio), Congressional Record, 8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July 17, 1951, p.8254.
不过,布瑞克9月决议案的内涵显然要大于人权问题,它实际涉及的是美国国会与总统对外交权力的争夺。布瑞克在介绍这份决议案时指出,美国外交混乱的根源在于“行政部门未经国会授权或批准,订立了众多不符合宪法的行政协定”。(61)Speech by John W.Bricker(R-Ohio), Congressional Record, 8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September 14, 1951, p.11361.美国宪法虽然对总统和参议院的外交权力进行了划分,但正如宪法史学者爱德华·科温(Edward S.Corwin)所说:宪法“赋予总统某些能够影响我国对外关系的权力,赋予参议院某些同样笼统的权力”,但最终权力的演变“取决于具体的事态”。(62)转引自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66—1865)》,周贵银、杨光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2页。自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在实践中发展出了总统外交权力,特别是多次对外战争极大地扩张了总统外交权力。但这一扩张总是受到国会的限制,参议院对威尔逊国联计划的否定便是突出的体现。冷战的出现使双方权力争夺进一步激化,据政治学者杰里尔·罗赛蒂(Jerel A.Rosati)的研究,在1951—1955年,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外交权力出现了明显的对抗,其“高峰”正是布瑞克提出的宪法修正案。(63)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受到部分议员的支持,布瑞克在1952年2月再次提交一份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条约不能干涉美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职能,同时只有在国内相关立法存在的情况下,条约才能以国内法的形式在美国实行。布瑞克的这份决议在参议院获得不少呼应,塔夫脱进一步认为应该“修订订立条约的方式”,特别需要厘清条约与行政协定的关系,避免以行政协定的方式避开国会对条约的监督。(64)Speech by Robert A.Taft(R-Ohio), Congressional Record, 8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ruary 7, 1952, p.910.决议也得到部分民主党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对杜鲁门政府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不满和对联合国表示怀疑”的南部和西部民主党人。(65)Duane Tananbaum, The Bricker Amendment Controversy:A Test of Eisenhow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3.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5月为此召开听证会。布瑞克声称决议案的首要目标是“禁止使用条约作为国内立法手段,以此来放弃国家主权”。布瑞克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51年春通过的人权公约草案为例,批评公约条款可能“废除麦卡伦国内安全法的大部分内容”,美国劳工、种族、移民、教育政策都将由完全的国内事务变为国际事务。这显然是借用了霍尔曼的论点,但布瑞克的更大目标在于限制总统外交权力,他抨击美国对外政策的“显著缺陷”在于总统通过越权、隐瞒信息等方式,未经国会批准就承担了国际义务。(66)Statement of John W.Bricker, Treaties and Executive Agreements: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Eighty-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May 21, 22, 27, 28, June 9, 1952, Washington, D.C.: U.S.G.P.O., 1952, pp.1-21, 30.行政部门在听证会上做出反击,美国国务院代表列举了众多令美国受惠的国际商务条约,同时美国参与国际管控毒品条约的例子也表明社会问题领域的条约也有利于美国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67)Statement of David K.Bruc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reaties and Executive Agreements: Hearings, 1952, p.187.司法部副部长认为决议案将“严重削弱美国有效开展对外关系的能力”。(68)Memorandum Submitted by Philip B.Perlman, Solici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Justice, Treaties and Executive Agreements: Hearings, 1952, p.397.尽管听证会上仍有为国际人权辩护的声音出现,但反对布瑞克的有效武器是更为现实的外交考虑,国际人权的异化消解了其原本的重要性。
1953年1月,新一届美国国会开会第一天,布瑞克提交了一份新的决议案,要求约束新任总统的外交权力。3月26日,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公开谈及这一问题,他认为修正案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总统的外交权威,尽管他不直接挑明这正是修正案支持者的动机,但它确实将产生这样的效果。(69)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March 26, 1953, In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Dwight D.Eisenhower, 1953, Washington, D.C.: Govt.Print.Off., 1958, p.132.私底下,艾森豪威尔认为修正案将使任何涉外事务都陷入瘫痪,通过外交协定来“为美国在北非的空军基地招收工人、在法国设立北约司令部、盟友间交换重要信息”都将难以完成,因为它们将需要国会的批准。(70)Tananbaum, The Bricker Amendment Controversy, p.72.
布瑞克的议案得到了超党派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商议对策,一方面他们需要分裂布瑞克的支持者,特别是拉拢其中的部分共和党议员以及南部民主党人;另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的政策也需要调整,以避免布瑞克以此为攻击目标。后一任务主要由杜勒斯完成,他授意国务院重新研究公约问题。国务院提交的备忘录提供了多种政策以供选择,包括停止参与联合国公约制定,采用其他手段来实现人权宣言标准,或者只参与制定公民政治权利公约,杜勒斯选择了前者。(71)Brucken, A Most Uncertain Crusade, p.235.杜勒斯在2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政策转向,并在3月底再次向总统确认了这一政策,他在备忘录中认为“苏联及其盟友并没有受到人权公约的限制,现在签署公约对美国益处不大”,美国应寻求更好的促进人权方式。(72)Nancy Beck Young,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cy, Vol.4:President Eisenhow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ricker Amendment, Bethesda, MD: LexisNexis, 2007, p.65.杜勒斯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认可。
1953年4月6日,在国会第二次就布瑞克修正案召开的听证会上,杜勒斯宣布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新政策:“本届政府将致力于以说服、教育和树立典范的方式鼓励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和个人自由,而不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部分国家的社会和道德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因此,国际条约不再是推动人权的有效手段,“本届政府不会寻求批准任何公约,或将其作为条约列入参议院考虑范围”。(73)Statement of John F.Dulles, Secretary of State, Treaties and Executive Agreements: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Eighty-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Feb.18, 19, 25, Mar.4, 10, 16, 27, 31, Apr.6-11, 1953, Washington, D.C.: U.S.G.P.O., 1953, p.825杜勒斯的声明是美国国际人权政策转向的标志,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公约起草阶段便宣布了否定政策,这是194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国内反国际人权力量的重大胜利,它的出现又与国际人权在美国的异化有密切联系。在行政部门已经否定国际人权的情况下,布瑞克修正案在1954年初的国会投票中仍然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再次表明修正案的核心问题并非人权问题,而是国会与总统的外交权力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参与的国际人权议题成为布瑞克修正案的“第一个受害者”。(74)John Allphin Moore, Jr.and Jerry Pubantz, To Create a New World?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eter Long, 1999, pp.87-88.
美国的新政策推动后,国际人权的普遍性受到抵制,例外主义更为鲜明,国际人权开始向美国式人权转化。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拒绝国际组织对美国人权议题的干涉,这在前述美国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国际人权话语的运用及其遭遇的阻碍中得到充分体现。国际人权被认为将减损美国人应享有的权利,同时以国际手段推进人权议题也被视作是对美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
其次,美国式人权还体现在拒绝承认作为人权的社会经济权利,将人权定义为仅包含人身自由及公民政治权利,并将美国塑造成为西方传统权利理念的继承者。早在1949年,美国国务院便应联合国秘书处的邀请制定了一份名为《人权:美国传统的发展》的小册子,它以《圣经》为起点,到《世界人权宣言》结束,其中绝大多数权利文件以及个人声明多指向消极权利,且来自美国,展示了美国对西方文明的继承。(75)Division of Historical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e, Human Rights:Unfolding of the American Tradition, 1949,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and Its Predecessors, Position Papers Maintained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1945-1974, RG 59, Box 44,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这在联合国编纂的《人权年鉴》中也得到体现。该年鉴由各国提供其国内的人权资料,经秘书处汇总后出版成册。1949年的美国部分归纳了美国人享有的人权,包括就业、住房立法以及教育等权利。(76)U.N.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for 1949, pp.237-239.到了1952年时,美国国务院已不再单独列出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而是划分到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并称之为“平等机会的获取”。(77)U.N.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for 1952, p.311.到了1955年,国务院提交的报告直接分为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这样的划分在此后一直得到延续,体现出作为国际人权的社会经济权利并没有被美国政府视为美国人权,这是例外主义者的重要成果。美国式人权的这两大特征为19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二战后初期美国围绕国际人权的争论体现出人权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诸多特征。首先是人权的争议性质。人因其人的身份享有的权利便是人权,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与“权”的范围都在不断地演变,战后初期美国国内政治中对普遍人权的使用便是试图扩大人权的主体及其权利边界,这引起例外主义者的反对,双方的争论推动了美国由二战向冷战过渡中诸多国内议题的激化。人权的争议性体现出历史中的人权并没有获得它在当代美国政治中无可指责的道德地位。其次,人权的争议性伴随的是其模糊性,这在反国际人权话语中有鲜明的体现,以霍尔曼为代表的律师群体利用联合国人权文件的模糊性来夸大宣传。在其描述之下,美国制度及法律均遭受严重威胁,其国家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国务院及司法部的法律声明在此危机想象之下效力大减。布瑞克也利用人权的模糊性将人权公约与其他一般性条约和协定相联系,在异化国际人权的同时迫使行政部门放弃参与国际人权。最后,美国围绕国际人权的争论还体现出人权的工具性。战后美国妇女及黑人利用人权话语来推动其国内议程,反国际人权力量则使用例外主义的美国人权观来反对联合国对美国国内的干涉,行政部门则利用放弃参与国际人权来获得宪法规定的外交权力的巩固。这些都反映出国际人权在当时美国政治中的复杂内涵。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普遍主义与例外主义的人权理念在美国不同历史阶段扮演了不同角色。普遍主义代表着二战时期国际主义的深远影响,它在1950年代初逐渐被强调美国特征的例外主义代替,后者在此后得到延续,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使用更多的是例外主义的公民权利而非人权理念。但是,当美国在1970年代需要从越南战争中恢复道德形象,需要从失败的冷战缓和中再次找回对苏联政权攻击的时候,人权便再次进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之中。(78)Barbara J.Keys, Reclaiming American Virtue: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of the 197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此后美国向外推广的人权理念已经实现了例外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统一,一方面,它是例外主义美国人权观的延续,侧重于公民政治权利而忽视作为人的生存发展基础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强调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潜在威胁而非保障,忽视此时联合国人权立法中集体人权等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披上了普遍主义的外衣,正如奠定美国人权外交基础的1974年《对外援助法》所声称,“美国总统应缩减或终止援助系统侵犯国际承认的人权的政府”。(79)Public Law 93-559, An Act to Amend 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 Dec.30, 1974, p.1815.借助其霸权实力,美国在人权外交中将其例外主义的美国式人权塑造成为“国际承认”的普遍主义人权,并借用战后初期美国国内支持国际人权的话语,使人权成为美国价值理念对外输出的有力武器,这是战后初期美国围绕国际人权争论的深厚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