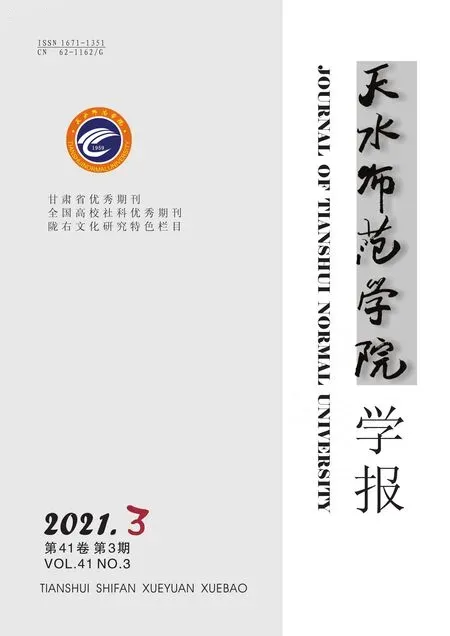“非虚构”背景下当代诗歌“事实的诗意”
2021-01-08薛世昌
薛世昌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我们有幸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许多曾经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正在渐次破溃,包括文学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人们在“虚构”的、“非真实”的语境中浸洇已久,追求“真实”的、向往“非虚构”的时代终于悄然来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非虚构小说”为肇始,而以2010年我国《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设置为标志。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大量对于“元虚构”“前虚构”“零虚构”“后真相”等诸多概念的思考。从表象上看,在“非虚构”浪潮中首当其冲者,是以纪实性文学传统为根基的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历史传记以及散文等,诗歌世界似乎在一片“非”声中暂时风平浪静,若无其“非”。其实不然,逢此“非非”之世,诗歌不可能独“是”其身。“以陈述事实为基本创作手法”“以写实手法力图反映当下现实生活”“以新闻事件与散文写作手法相结合”,[1]以及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去魅、刷新,甚至更为抽象的写作如“在场”和“及物”,这一切不可能与诗歌写作漠然无关。事实上,从当年阿吾等人倡导的“不变形”、于坚的“拒绝隐喻”,到近年来伊沙“事实的诗意”,中国当代诗歌的“非虚构运动”早已是风景这边独好,值得“非虚构”的研究者移目关注。
一、中国当代诗歌“非虚构”的急先锋:“不变形诗”
1986年前后,在颠覆了“朦胧诗”的那场中国现代诗浪潮中,涌现出许多标新立异的诗歌流派,如“他们”“非非”“莽汉主义”等,其中就有阿吾和斯人等力主且影响深刻的“不变形诗”,其实就是中国当代诗歌“非虚构”的先声。
诗歌向来被认为是“变形”的艺术,清人吴乔以“文饭诗酒”为喻对此进行过经典的阐释:诗就像是生活从米到酒的变形。变者,改变也,当代诗评家陈仲义解释说:“‘改变’是变形的最大特征,不论是整体、局部、外在、内里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形的内涵都十分稳定,都是艺术家的审美智慧对外部世界的强势变造。”[2]语中的“外部世界”,指的是天下事物及其关系,而“对外部世界的强势变造”就是对天下事物及其关系进行变造、改造、改变、变形,就是将自然性的“表象”及其关系变为人文性的“意象”及其关系。如“麦南手段高明/名声远播/清早的门口/就排满了坏牙”(林军雄《牙医麦南》),在散文的描述中,排队的一般是“人”,而在诗歌的描述中,排队的往往是“坏牙”。把一个整体的“人”局部化、特征化为“坏牙”,这就是诗歌艺术最为基本的变形。诗注定是现实生活的变形。这一变形也注定要通过想象而得以实现。
然而,阿吾他们却要通过“元语言”向诗歌变形这一诗歌艺术的基本原则大胆地说“不”。当时,他们提出的概念是“反诗”。他们曾解释说:“‘反诗’有另一个词‘不变形诗’,其意涵于我们是相当清晰的:反的不是诗歌的精神,而是当时为朦胧诗所笼罩的唯意象、超意象、意识流的倾向。”[3]后来,阿吾的朋友西渡对阿吾的诗歌理念进行了如下全面精当的总结:
阿吾的“反诗”主要从两个方向上对世俗的诗歌样式发起攻击:其一是反修辞。阿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仔细地分离强加在缪斯女神身上的种种脂粉,除下她身上已经成为累赘的华丽而花哨的重重衣饰,以便我们重新发现她的祼身之美。其二是反象征。阿吾从他在北大所受的科学训练中为诗歌借来了一副近乎物理学的(可惜不是化学的)、客观的、冷静的眼光,他用这副眼光观察周围的事物和各种事件,甚至包括心理的、文化的事件,并借此重新发现了表象的价值。阿吾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合而言之就是,以一种客观的、说明的语言达到对事物的“不变形”处理,从而让事物自身在诗中现身,并最终更新我们的眼光。[4]3-5
显然,阿吾认为世界在想象式变形的言说中已严重扭曲,他要把这严重变形的事物进行还原与纠正——其言说效果当然也就是将“熟悉”变得“陌生”。如其《今天没有落日》句:“今天没有落日/没有一块红红黄黄的东西/在这远天,要掉不掉的样子”。相对于之前“落日”这一事物的大量变形,阿吾“还”给了我们一个“元”的落日:一块红红黄黄的东西、要掉不掉的样子。我们和这样的落日还真是“分别得太久太久”。瑞典诗人特朗斯托罗姆曾这样写落日:“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我们与这样的落日更是恍若隔世。类似者还有《对一个物体的描述》《出去》《三个一样的杯子》《苦难十四行》《地铁》《苍凉期》等。当然,阿吾最著名的“不变形”实践还是他1987年的《相声专场》。《相声专场》充分地实践了阿吾“不变形”的艺术意图——在诗歌的写作中去除文化装饰、回归事物本身,通过“元语言”对事物进行“还原式命名”。“报幕员被还原为‘一个女人’,双口相声的表演被还原为‘高瘦子’和‘矮胖子’之间的一场听得见声音却不知其义的对话,单口相声的表演被还原为一粗一细两个声音的问答,群口相声的表演则被还原为用数字编号的‘五个人’之间的奇怪的争执,观众的反应被还原为‘哄堂大笑’和‘右手打左手’的过程。”[4]5他们这般不肯“与时俱进”,他们这般急速地向着客观真实奔去,向着一个“去化妆”的甚至“去戏剧”“非过滤”的时代裸奔而去,是极具先锋性的艺术行为,是一个诗歌新时代的预言。
二、“不变形”的大背景:“写作的零度”与“散文化”
1953年,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发表了《写作的零度》一文,概括并推出了他从加缪小说中发现的“写作的零度”这一概念。针对浪漫主义的滥情与夸张,特别是意识形态写作中的国家主义立场,罗兰·巴特通过“写作的零度”概念,主张采取中性、客观、民间的写作立场,突出地描述个人视野中不带价值判断的话语所过滤的原生现实。所以,“写作的零度”又称单色调写作、白色写作、纯洁写作、中性写作、非感情化写作、不介入式写作、零度写作等。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它影响了小说写作的“零度叙事”,也影响到诗歌写作的“零度抒情”,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罗家生》,伊沙的《车过黄河》、韩东的《有关大雁塔》、阿吾的《相声专场》等,皆受其影响。
“零度写作”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整个文化“源始命名”的追索。
源始命名,指的是命名者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事物并且第一次言说这个事物。由于身处“后命名”时代的人们在接受命名的时候事实上已不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事物”,也不再是“第一次言说这个事物”,所以,这一命名也就渐渐地形成了对这一事物的遮蔽——人们也就在事实上远离了关于事物的“源始命名”(于坚把这一现象称呼为“隐喻”并力主“拒绝”)。在这一文化进程中,优秀的诗人纷纷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使命——逆着文化的方向而运动,重归“源始命名”并为事物去蔽、去魅、去伪。在中国当代诗坛,阿吾、于坚、伊沙、韩东等人,无不对这一天降大任的文化使命心领神会,并从各自的理解出发进行了种种旨在回到事物本身的“归零”式写作。他们几乎一致地发现了超越性与还原性之间那种奇妙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联系:越是原点的,越是超越的!越是回到事物本身的,越是形而上的——这恐怕也是亚里士多德对文学艺术最早也最深刻的认识。他的“摹仿说”,其实就是对物的最大贴近,自然也是对物的最大超越。
正是在这样追求“本真”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诗人也开始了对于“虚构”的警惕。2001年,于坚就说:“世界在上面,诗歌在下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诗歌开始呈现一种向下的倾向。这个‘下’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汉语诗歌,大多数时间是在意识形态的天空中高蹈,站在虚构一边。浪漫、理想、升华、高尚,对世俗生活的蔑视,完全脱离常识的虚构。”[5]305于坚同时认为:“虚构的方向是朝上的。‘上’在汉语里意味着什么?‘天天向上’‘奋发向上’‘上面来的’……,‘上’,与文化肯定的方向、权力话语有关。”[5]305-306于坚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描述了中国先锋诗歌“向下的倾向”中潜在的“非虚构”倾向。事实上,“第三代诗歌”诸如“回到事物本身”“不变形”“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呈现就是一切”“回到常识”等诗歌主张的关键词也都指向着“非虚构”,它们事实上已然包括了去除装饰、回归事物、元语言、拒绝修辞、客观、中性、纯洁、零度等先锋诗歌的概念,“零度情感的介入,诗被‘第三代’诗人赋予了明确的具象性,将自我的痕迹降低到了最低处”。[6]所以,阿吾当时的“不变形”既是他个人的主张,又深深契合着当时整个文化界“零度写作”的、回到真实的、反对隐喻的普遍愿景,所以,阿吾肯定不是孤军奋战,肯定有他的战友与同道——他们也许互不认识,但他们却是声气相投。除了前面提到的于坚、伊沙、韩东等,赵丽华也是其中梨花春雨一般声名灿烂的一位。
赵丽华,中国当代著名的方向性诗人,中国当代诗歌“还原式命名”的骁勇女将。她真切而紧贴生活的写作中一个突出的艺术追求就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归真返璞。这一追求也就是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这一文学认知在中国当代诗坛一个重量级的诗歌践履。怀揣着玉宇澄清之诗歌志向的赵丽华所有那些去魅的、去神性的、去伪饰的文字,让她的诗歌一步一步地前往着“曾经”的背面、“历史”的源头、“原点”的感觉,而体现出强烈的“原生态”命名特点。她试图在那些意义归零的地方开始意义的重建。赵丽华的还原式命名,首先表现在她对“大词”的警惕,其次也表现在她对“拒绝隐喻”的警惕。她的许多诗都被胡塞尔的哲学名言不幸命中:“面向事实本身”。如她的《天空很早以前就是蓝色的,而大地刚刚呈现绿色》:“从滩里/到下官地/有两只鸟/在迎面飞/它们刚刚交叉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全是描述,全是事实,全没有“立象以尽意”,甚至全是大实话。静心揣摩,其平实的叙述拒绝着想象与变形,甚至也拒绝着意义——她一定认为自己所描述的带有极强的“经验直接性”之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强大。可惜当后来“事实的诗意”在中国诗坛普而遍之的时候,赵丽华却改行画画了。
“非虚构”的另一言说背景就是“散文化”的人类言说之大趋势。
小说家马原曾有一本小说讲义,径名《虚构之刀》。马原所理解并力挺的“虚构之刀”当然是小说家看家护院的“小李飞刀”,但自“非虚构”概念风起于青萍之末以来,“虚构之刀”即遭遇到了“非虚构之刀”的挑战。“非虚构之刀”似乎更为厉害,堪称横扫江湖的“无影刀”——人们看到了一只叫作“非虚构”的偌大箩筐,它几乎包罗广义的散文文体的一切类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回忆录、传记文学、长篇散文、长篇历史散文……。可以说,不论是小说的虚构,还是诗歌的想象,它们都遭遇到了“散文化”这一言说大趋势的裹携。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后现代以来,从小说到诗歌,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散文化”的大趋势。小说界“散文化小说”与“淡化情节小说”的出现,诗歌界“自由诗”“散文化诗歌”与“散文诗”的出现,新闻界“华尔街日报体”即“DEE结构”的出现,散文界内部“文化散文”和“历史文化散文”的出现,都是这一大趋势的不同体现。即在散文内部,也特别强调散文言说对于事实性的夯实,比如文化散文对“史料”的强调(同时对“诗意”渐生警惕),比如叙事散文对“亲身经历和现场体验”的强调。人们认为:“真实性不仅是散文创作的原则,也是有效传播的基础。可信,是信息传播的生命,也是有效传播的关键。作家对待写作对象如同科学考古一般严谨,既做细致的田野踏勘与调查,又做深入的文献梳理与考证。”[7]195所以,“非虚构”,也可以理解为“散文化”。或者说“散文化”的实质,也就是“非虚构”。
不能否认的是,有一些散文作者不甘心于散文的“平淡”,他们往往会在散文里讲述一些惊险的举动、意外的行为、巧合的事件,给散文涂抹一层戏剧性的色彩和噱头以博人眼球。“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不够诚实的现象不只发生于诗词歌赋,也常常发生于散文——“为文造情”“因文生事”。当然,散文也大度包容地默许了这类散文的存在。散文本来就是天下最为宽容的一种文体,它或近于新闻,或近于历史,或近于诗,当然也有或近于小说甚至近于戏剧者(如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某些篇章)——它们多多少少都有些虚构。在其巨大的兼容性这一点上,说散文是“水性杨花”应该话出有因,不无根据。这样“时而虚构”的散文作品时有所见的存在,自然也影响到人们的散文观——认为散文有时候也可以虚构。然而,我们却不能据此就认定并且主张散文的虚构。散文的第一品质就是“非虚构”,散文的第一美感就是由主要描述已然世界而带来的现实真实感。而真实,又向来是文学的第一品质,只不过文学的真实这一总体品质摊派到文学的下一个层级之后,却有了不同的分工:诗歌承担的是文学的情感真实(承担的资质是诗人的想象力),小说承担的是文学的理想真实(承担的资质是作家的虚构力),而散文则承担了文学的现实真实(承担的资质是作者的经验力)。相比于小说与诗歌,散文更倾向于追求“事之真”(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之真),所以人们一直认为散文是不可以虚构的——散文的“莫虚构”这一态度自然也就保持着散文的“非虚构”这一品质。
三、2016年作家网冰峰的《非虚构诗歌宣言》与“非虚构”的基本理念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此诗歌写作非虚构的风声动向,一定会有嗅觉灵敏者做出捕捉与响应。果然,2016年,作家网总编冰峰(赵智)就推出了《非虚构诗歌宣言》。
冰峰这样描述其“非虚构诗歌”的“宣言”动机:“我们想让诗歌从诗人狭小的牢房里走出来,与生活发生关系,与博大的土地、街道、人群发生关系,与一切真实的事物发生关系。”语中的关键词,是“真实的事物”。他又说:“要让诗歌走进生活,与更多的人生活在一起,让更多的人感知诗歌的体温、人性和力量。”《宣言》也描述了“非虚构诗歌”的基本品相:“去掉所有的装饰,放下语言的架子”“好好说话,说人话,说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用诗歌记录时代,呈现生活的真实”“诗歌呼吸的节奏是自然的”。可惜他所描述的这种品相,毫无个性与独特之处,是诗歌的“标准相”。他也特别地强调了“真相”:“在揭示真相的时候,我们不发表偏激观点,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对发生的事件,不批评,不赞美,要客观呈现,交给读者去评价、评判。”作为对客观强调的重要辅助,他也重点讨论了想象。他认为之前的诗歌是“孤独”的,“诗歌躺在诗人的想象中花开花落,了却一生。”由于他把“想象”确立为“非虚构”的敌方,所以他同时也在“宣言”中把“想象”视同于“巫术”:“我们不需要用巫术来治疗疾病,巫术是想象,我们需要用真实的药品或手术,从根本上治疗病灶。”“想象”既已如此,那么与想象沾边的“虚构”显然同属客观的对立面——主观,所以他一再重申:“我们不需要想象和虚构,想象和虚构是假的,是虚拟的空间,有可能出现无数的可能。”他甚至把“意象”和“华丽的词汇”混为一谈:“意象和华丽的词汇是诗歌的化妆品”。《宣言》的最后一句是“脱光伪装,和虚假宣战吧。”显然,《宣言》所理解的“非虚构”,就是“非伪装”和“非虚假”,就是“真相”与“真实”。[8]
这份《非虚构诗歌宣言》所主张的诗歌理念并没有得到冰峰个人诗歌实践的有力支持,所影响的范围也比较有限,但是《宣言》有其明确的之于“粉饰”与“伪装”的现实针对性,也有其明确的关于“真相”与“真实”的坦荡追求,故其宣言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肯定,但是,他的“非虚构之刀”霍霍所向,伤及了诗歌的意象和想象,却是同样明显的殃及无辜。所以他这份宣言最大的理论贡献,他这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主张,倒也涉及“非虚构诗歌”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非虚构诗歌”,“非”的到底是什么?意象与想象也是它“非”的对象么?“非虚构诗歌”之于意象与想象,必欲“非”之而后快么?它们真的是不共戴天非“非”不可么?“非”掉了意象与想象之后的诗歌,可能确实不再虚构了,但它还是“诗”么?
或者说,“非虚构”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非虚构”,目前人们的理解并不统一,有人理解为“对写作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文化现象全面透彻的把握,以及强调‘在场’感的写作风格。”[7]194-195也有人概括其精神为“新实证精神”、描述其动作为“向外转”……,本文认为,万流归一,关于“非虚构”最为简洁的精神概括应该是:“非主观”。
《庄子·应帝王》中的这则寓言故事从来就发人深省:“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根据这个寓言故事来理解“非虚构”,则所谓的“虚构”就是“日凿一窍”之“凿窍”,而“非虚构”也就是“前虚构”也就是“日凿一窍”之前的天然“浑沌”,就是浑朴、质朴。即以具体诗歌为例,四川诗人靳丹樱有诗《白鹤嘴的初夏》:“男人扶犁赶牛,妇人们埋头插秧/偶尔直起腰/像几只高贵的鹤∥妹崽把鹅撵下塘,顶着荷叶,踮脚跑过湿漉漉的田埂/捉蝴蝶去了/风开始翻书,满枝桑叶哗啦啦响∥时间在白鹤嘴收拢翅膀/竹蜻蜓般易于掌控。躺在草丛,我是朵懒散的蘑菇∥小蚂蚁不管不顾/顺着一架燕麦梯子奋力爬向天空”。全诗质朴自然,却有一个地方被“凿”了一“窍”,那就是:“妇人们埋头插秧/偶尔直起腰/像几只高贵的鹤”,如果不说“高贵的鹤”而只说“鹤”,那就是真正的浑沌了。因为这里的“高贵”二字涉嫌了“主观”。
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固然是客观的,但是“我们认为的美”则是主观的。“高贵”就是靳丹樱认为的鹤之美,要是换一个人,可能会说是“孤独的鹤”。“高贵”也好,“孤独”也罢,它们都是主观的,都不是客观的。客观的表述就是“……像几只鹤”——只有不给它定语的鹤才能保持鹤的所有能指,而给了定语的鹤则只有定语给它的所指。所以,诗是对定语的反抗之地,而学术语言又是定语的泛滥之所。所以,最大的真实就是最少的定语,最大的非虚构就是事物本身。尤其当人们对主观想象感到了普遍的审美疲倦、心理疏离,那么,一真遮百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以真实与客观而为基本立场的非虚构也就显示了它的价值——价值永远都是基于需要的产物。
四、伊沙:他的诗也曾多有虚构
诗人伊沙近年来力主的诗歌理念“事实的诗意”,虽然没有形成那么正式的“宣言”,但却是“非虚构”在中国当代诗歌界认真且有力的响应,他力推的“新世纪诗典”也是“非虚构”写作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和所有不断成长的艺术家一样,伊沙也是不断成长的伊沙。如果以他《车过黄河》中的“黄河”为界,则伊沙从“黄河这边”时期,到“黄河那边”时期,就是一个精进蜕变的过程——他的《车过黄河》,堪称伊沙对自己这一进步“自占的预言”。[9]这预言也是伊沙对一个时代的预言——过了“黄河”的,不只是伊沙,而是一支浩大的队伍,是整整一个时期;同时,“车过黄河”也是一个隐喻。如果说“黄河”意象意味着传统,则“过黄河”就意味着对这一传统的越过。而伊沙从“黄河这边”到“黄河那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虚构”到“非虚构”。也就是说,意识到“事实的诗意”这一诗歌的“非虚构”然后为之大声疾呼、努力彰明,这在伊沙是有一个过程的。
开始的时候,伊沙的诗歌创作中不无“虚构”的影子。
伊沙有首《和日本妞亲热》(1991)的诗:“在不愿透露的地点/和一个日本妞亲热/如坠温柔乡/这是一生少有的机缘”,其中的“我”,有人可能会按“署名性”的“我”来理解。[10]其实,这里的“我”应该是一种“假名性”的即虚构的“我”。这倒不是要“为尊者讳”,这实在是伊沙要用“我”来增加诗歌叙事的“在场性”和“现场感”。伊沙《血液净化中心》云:
“一座单独的小楼/像一张嘴的形状∥我知道命在这里/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我的母亲拒绝了/这项交易∥作为尿毒症患者/她拒绝透析∥拒绝自己的血/在此得到净化∥她的信念/朴素而又简单∥她说早晚都是一死/她不希望在她死后∥父亲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穷老头∥而我身为儿子的痛苦在于/就算我拼命挣钱∥也喂不饱这张/能吐出命来的嘴”(2000)。
有谁会愿意伊沙诗中之所写竟是事实呢?我们都希望那个“我”其实是伊沙的假名。
但是伊沙曾经很喜欢这样的假名,比如他在《学院中的商业》(1992)中就说:“我是倒卖避孕套的人/在午夜两点/敲开男生宿舍之门”。伊沙自己肯定不会去倒卖避孕套,那个“我”无疑是种假名,是一种情感一定要真而行为并不一定也要真的虚构,是伊沙的诗歌叙事中由于“情节”的需要而设置的一个“角色”。有一种诗歌近于散文,有一种诗歌近于小说,伊沙的诗歌,在假名性这一点上,近于小说。他在《结结巴巴》中的那个“结结巴巴”的“我”,同样也是一个假名:一个想象中可能的我,而不是一个现实中已然的我。生活中的伊沙并不结结巴巴,倒是伶牙俐齿。甚至,伊沙的《乌鸡》都涉嫌虚构:“一生中/我有一次/仔细地观察过它/也就一次/某年冬/当我从菜市场穿过/因它而驻足/我想它是/鸡里的黑人吧/肯定是/我因这个想法/而放弃了它/决定不以此/传统补品/来为产后卧床的老婆/催奶”(2000)。但是谁又会在乎它是否虚构呢?
彼时,伊沙在诗歌里不只虚构“我”,有时还虚构“他”,如其著名的《鸽子》:“在我平视的远景里/一只白色的鸽子/穿过冲天大火/继续在飞/飞成一只黑鸟/也许只是它的影子/它的灵魂/在飞/也许灰烬/也会保持鸽子的形状/依旧高飞”(2000)。难道他诗中的这场“冲天大火”不是虚构的吗?再如他的《死者》:“在某人的追悼会上/我看见死者坐起来/朝我们伸着手/说着什么/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是烦那没完没了的悼词/他是在拒绝追认——‘让我死吧,让我带走你们的错误。’”这不是“轻度的虚构”又是什么?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因此而对伊沙有所非议。如果我们的文学史上存在过一个堂堂正正的“虚构时代”,那么,在那个并不遥远的“虚构时代”,大家都免不了会与虚构沾亲带故而不够诚实。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虚构”,重要的是你有多长的时间深陷于这样的“虚构”。伊沙的可贵与聪明就在于,他很快就从“虚构”中“迷途知返”而开始了对“事实的诗意”之努力追求、悉心体认,并终于得到了陈仲义的肯定:“‘事实的诗意’是伊沙一个基本的诗歌立场、态度、诗歌的审美尺度和诗语方式。”[11]
五、“新世纪诗典”中的伊沙:“事实的诗意”
“事实的诗意”这一说法,为伊沙最早概括和命名。他声称:“由我发明的‘事实的诗意’,指的就是身体在场的写作——它意味着:你是生命与生活的在场者,你的身体感觉、写作意识和你手中的笔是相通的,你不应该抽离人的身体去强调文本的艺术性,不要将你接收的事物关在抽空的意识中。”[12]伊沙又说:“我早就在强调‘事实的诗意’:语言的似是而非和感觉的移位(或错位)会造成一种发飘的诗意,我要求(要求自己的每首诗)的是完全事实的诗意。在这一点上,我一点都不像个诗人,而像一名工程师。”[13]陈仲义先生可能觉得伊沙这话说得太“发飘”,所以郑重地解说如下:“这与陈超说的‘用具体超越具体’有一定相通之处。所谓事实的诗意,是面对人、物、事、理的准确、具体、充盈的处理;‘事实性’不是用意象化手段抽绎经验,抵达喻指象征,而是在近乎客观、通明的语境中打开‘事实’自身。”[11]24而沈浩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对伊沙“事实的诗意”阐释得最为清楚明白:
伊沙对于“事实的诗意”的概括和命名,令“后口语诗歌”对于“具体”和“及物”的强调变得更加清晰。如果说“口语”是一种语言选择的话,那么“事实的诗意”这一理论的提出,则为当代口语诗歌提供了一具重要的“身体”。自古以来,诗人的努力,就是用“象”来实现“抽象”,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意象派”,就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美学。“事实的诗意”的提出,在诗人们所不断强调的“意象”“形象”“物象”之外,又多了一个“事象”。现代诗歌的诗意凝着物将不仅仅在于“意象”,“事象”比“意象”有更充分的“具象”特点,并能包含“物象”与“形象”。[14]
沈浩波自己对“事实的诗意”也是身体力行。比如他的《绝望》:“深夜,他在朋友圈里/发表了一首绝望的诗/我们纷纷在下面点赞/赞美他把绝望写得深刻/他整夜守在手机屏幕前/看我们赞美他的绝望”。这首诗,沈浩波叙述的全是事实。事实是分层的。朋友圈发布、朋友点赞、守候点赞,这是较浅层面上的事实;深夜、发诗、纷纷点赞,是较深一层的事实;而绝望的诗、点赞其深刻的绝望、整夜守候,则是更深一层的事实。也许这首诗的意义就产生于这更深的一层事实。目击而道存,这俨然就是“事实的诗意”,也俨然是王国维“无我之境”在所谓“现象学视域”下的发展与丰富。
综合各家所见和伊沙自己的说法、实践以及伊沙在“新世纪诗典”诗歌平台基于“事实的诗意”之诗选,关于伊沙“事实的诗意”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八点:文化的与生命的,生命更重要;写出来的与活出来的,活出来的更重要;心灵的与身体的,身体也重要;类我的与个我的,个我更重要;事实的与想象的,二者要对接,事实更重要;现实的与超现实的,二者相伴随,现实的更重要;比兴的和赋的,赋的更重要;语言的与事实的,事实的更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伊沙一再强调:“口语诗人写起诗来‘事儿事儿的’——在我看来这不是讽刺和调侃,而是说出其‘事实的诗意’的最大特征。”[15]但是我们对“事实的诗意”仍然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理解。“事实的诗意”之提法虽然具体而微,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不止于上述八端)。如果把“事实的诗意”轻描淡写地理解为“触动你的‘事’儿”,就有些狭隘,即使把它扩大到“现场感”“历史事实”“心理事实”“潜意识”,仍然不够开阔。所以,有必要对以上“事实的诗意”之八点内涵再做两点特别的解释。
(一)在“事实的诗意”这一旗帜下,“事实的诗意”主要以“诗歌事象”为主。
在“非虚构”的写作背景下,“人物”被区分为:作家创造的人物、现实生活创造的人物。作家创造的人物,是作家“想象”出来的,而现实生活创造的人物(在“非虚构”作品中)是作家在生活中“遇到、寻找到、认识到”的人物。在“非虚构”的写作背景下,诗歌的“意象”也被区分为:诗人创造的意象、现实生活创造的意象。诗人创造的意象,是诗人“想象”出来的,而现实生活创造的意象(在“事实的诗意”作品中)是诗人在生活中“遇到、寻找到、认识到”的意象。在伊沙的“新世纪诗典”中,这种诗人“遇到、寻找到、认识到”的意象,往往是一种“事象”:通过叙述而呈现的事实性、事件性意象(而不仅仅是事物性意象)。
所以,“事实的诗意”之“事实”,应该包括所有的客观之物。而“事实的诗意”,就是要让此一事实从现象走向“深度”。没有现成的“深度事实”,只有诗意能让事实获得深度从而成为“深度事实”。比如下面的这一个“事实”及其“事实的诗意”——“十八岁时他也苦练过虚晃/为了避免正面碰撞,优雅地/绕过一个个障碍物,仿佛/听到从场边传来此起彼伏的喝彩声/运球到前场后,轻松挑篮得分/那一瞬间,未来从云中向他飞来”(马小贵《为一场错失绝杀的比赛而作》)六行诗全是赋——描述,也全是事实,但如果没有最后一行的“跳篮”,其事实的深度又何在呢?其事实的美感又何来呢?所以应当这样认识伊沙“事实的诗意”:它是传统赋法的现代一变,它在“事”与“物”二者中侧重于“事”而漠然于“物”,所以相对于传统的“体物”诗观,它更强调“体事”。如果说于坚对“赋”的发展,在于他的罗列性探索,则伊沙对“赋”的发展,就是直陈性即叙述性探索。他们二人在这方面的努力都是可贵的、重要的,有价值的。置身在“言志”“缘情”“体物”“田园”“山水”等的旧声喧哗之中,于坚的“拒绝隐喻”和伊沙“事实的诗意”都是真正的诗人秀外慧中的诗歌发现。
(二)“事实的诗意”既是号召性的,也是批判性的,它主要批判的是“虚构”而不是“想象”。
“事实的诗意”主要拒绝与批判那种“非事实”的甚至是“虚构”的诗意,但是它并没有一味地拒绝“想象”,没有简单地认为“想象”与“事实”是矛盾的。“想象”与“事实”并不矛盾。比如伊沙的《无题之10》:“冰是水长出的牙/咬住了几条游船/船的表情/像咬住了钩的鱼/湖面上有人溜冰/拖船而过/像拖着自己忽然长出的/鱼的尾巴”,你能说其中的“想象”不是一种“事实”吗?而且“诗意”和“事实”也不矛盾。“事实的诗意”这一提法本身包含着一种表意的张力,即“事实”与“诗意”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却又是统一的。事实,尤其是深度的事实,恰恰可以走向写意,进而走向诗意。
六、伊沙诗歌理念“事实的诗意”之影响
伊沙不只是“事实的诗意”之竭力主张者,也是“事实的诗意”之奋力实践者,伊沙诗歌“事实的诗意”比比皆是,如《张常氏,你的保姆》《教子有方》《告慰田间先生》《9.11心理报告》《每天的菜市场》《最黑暗的睡眠》等,可谓“层出不穷”。在他的诗中,口述的、实录的、田野调查的、回忆的、现身说法的、纪实的……,非常“杂”,也非常“及物”,非常具有“非虚构”的特点。如他的口述实录诗《没见过的榜样》:“近几年来/我减肥的榜样/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小三/我家的钟点工王姐/(也是她家的钟点工)/老是念叨她:/“人家真敬业啊/为了瘦/为了美/为了一周一次/与那老男人见面/真是蛮拼的/真能管住嘴/不馋,不吃/从没让我做过一顿饭”,等等,这里不再列举。
伊沙是个极具现实关怀的诗人。伊沙的同事王敏撰文评价道:“伊沙诗歌无论是对现实还是历史,也无论是对普通人群还是边缘人,都保持了现实的眼光,直面真实,表现鲜活的人生体验。”[16]但伊沙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影响有限,伊沙的聪明或者说伊沙的担当在于“君子善假于物”——他通过主持“新世纪诗典”这一诗歌平台,有效地破解了个人力量的有限性,影响所及,奔向现实、直面现实、介入现实问题的“非虚构”写作硕果迭出。比如蛮蛮的《赫本是个好姑娘》:
“我把手机里的图片放给姥姥看/奥黛丽·赫本在非洲/背上一个瘦如骷髅的男孩/把赫本的话念给姥姥听/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姥姥想了一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赫本是个好姑娘/但是你/给我好好吃饭”。
这首优秀的“新诗典诗”,为叙事的事、为用口语叙事的诗挣得了光荣,而且也为“事实的诗意”这一诗学主张挣得了光荣。这首诗,全是事实:非洲是事实、奥黛丽·赫本在非洲是事实、她被拍了一张照片是事实、她背上一个瘦如骷髅的男孩是事实、赫本的话是事实、我让姥姥看照片是事实,我把赫本的话念给姥姥听是事实。“姥姥想了一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赫本是个好姑娘/但是你/给我好好吃饭”。这也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的组织却极其诡异、巧妙,短短的一首诗,三个人物栩栩如生,各具性情。这样的诗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蛮蛮还有一首《没什么大不了》也是“事实”满满:“站在图书馆门口发了一条说说/阳光像金子般撒在大地上/幸福/嘀嘀/好友秒评/矫情/又不是金子像阳光般撒在大地上/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首诗,尤其像是从哪儿“捡”来的。再比如“新诗典”诗人张侗的《在超市》:“一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踩着许多/被五花大绑的螃蟹/挣扎着/正从26.8元区/向36.8元区/艰难爬去”,也让人过目不忘。这些“新诗典诗人”,“口述”“窥私”“务实”“接地气”甚至“非主流”,“拟真”“仿像”甚至“超现实”,他们纷纷朝向着“非虚构”这一时代的天空而振翕试翼。他们无疑是21世纪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与守卫者。
七、结 语
“非虚构”在终极的意义上是“唯物主义”艺术观之于“唯心主义”艺术观的胜利。但凡事皆有分寸,“事实的诗意”在“非虚构”的同时,需要时刻注意的是:不能让“事实的”走向“故事会”,尤其不能走向“荒诞的故事会”,更尤其不能走向“关于他人的荒诞故事会”,需要时刻注意诗意开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要特别警惕于陈仲义所提醒的“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14]27在中国古人关于诗歌写作赋比兴的概括中,之所以没有唯赋是求、唯赋是作,就是要通过比兴而走向诗意的不断敞开、不断伸展、不断广阔,而诗的过程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诗意不断澄明的过程。诗歌在“及物”的同时也要“及我”。“作者”已死,但是“诗人”却要永远活着!如果大家还记得伊沙著名的《饿死诗人》一诗,就会明白下面的这句话:饿死那些在书房里“虚构”麦子的诗人吧,让真正的诗人在“非虚构”的麦田里挺然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