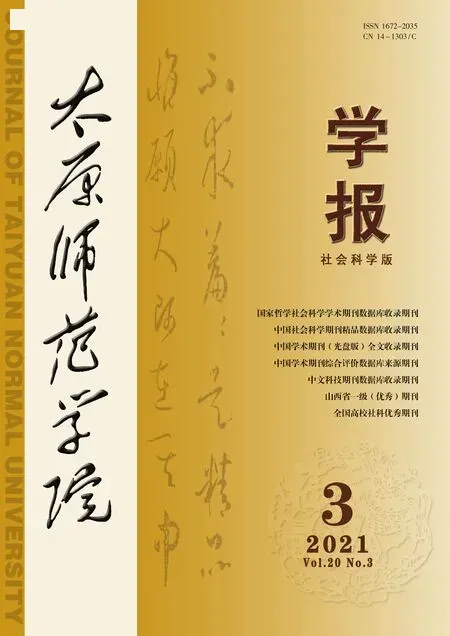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及其财政意义
2021-01-07贾洁蕊
贾洁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税收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1]“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2]所以一方面税收对国家的经济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税收制度的构建也要受国家经济贸易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海外贸易征税从唐宋元时期的市舶抽解,到明末的丈抽和饷税征收,再到清初设置海关税,每一次嬗变都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财政意义。
一、市舶征税及海关税研究概述
中国海外贸易活动源远流长,但直到唐代,官府才开始派遣市舶使(1)唐代“市舶使”的明确记载出现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有多个史料可以印证。如《新唐书》的《柳泽传》记述,“开元中……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柳泽认为周庆立进奉奇器会激发帝王的贪欲,所以上书进谏。《册府元龟》中记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唐会要》《古今事文类聚》《记纂渊海》《玉海》《历代名臣奏议》中。到广州进行近似的征税行为(2)唐代皇帝派遣到沿海地区参与海外贸易事务的官员有“市舶使”“押番舶使”“监舶使”等,多是由宦官担任,目的是为皇室采办珍奇宝货。唐代并没有形成规范而稳定的海外贸易征税制度,这种舶货的采办也没有为官府提供较为稳定和直接的财政收入,所以称为“近似的征税行为”。。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体系朝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外贸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所仰仗的重要产业,所以市舶征税制度也极为规范和严密。桑原骘藏(1929)以对南宋末年泉州提举市舶蒲寿庚的身世考察为线索,对唐宋元三代的市舶制度进行了论述。[3]藤田丰八从市舶机构、市舶官制、市舶条例三个部分论述了宋代的市舶制度。[4]陈高华和吴泰[5]、高荣盛[6]、黄纯艳[7]都重点研究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及市舶制度。明代至清前期,中国财政体系开始向近代化转型。传统的市舶制度在明代末期逐渐没落,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设四海关之后,中国开始征收较为规范的海关税。陈尚胜[8]、李金明[9]、郭宗保[10]、关镜石[11]、李庆新[12]在研究明代海外贸易背景的基础上,探讨明代市舶制度的变化及市舶向海关转型的问题。也有学者研究了清代财政体系向近代转型的表现与原因,倪玉平基于详尽的数据从财政收入、支出和管理各方面论证了清末“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近代转型。[13]王文素、龚浩认为财政现代化的标志是实现财政的控制权由专制君权向民权的转移。[14]赵云旗[15]、马金华[16]认为现代财政制度的起点和核心内容是预算制度,并探究了传统预算制度现代化转型的过程。目前学者的研究或是从历史的视角分别梳理市舶和海关税的发展历程,或是遵循财政理论框架而研究近代财政转型问题,缺乏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本文基于对比和分析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近代海关税的过渡过程,重点研究这个制度变迁的原因及财政意义。
二、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表现
中国的海外贸易征税肇始于唐代,唐代海外贸易发达,对社会各经济领域和百姓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趋复杂的海外贸易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出台合适的市舶制度,所以唐代产生了市舶制度的雏形。宋元时期市舶制度较为完善,其征税制度中包含了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减免税和税收处罚等绝大多数现代税制的基本构成要素。此外,征税制度中的税收管理内容也较为丰富。明中后期,海外贸易状况和市舶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迁,隆庆开海和饷税征收是市舶征税制度变迁的重要表现。清初实行海关税制度,市舶征税制度就此终结。具体来说,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表现在税制体系的变革、税收征收形式的变化、税收管理制度的演进等方面。
(一)税制体系的变革
1.由单一的进口税变为进出口税相互配合的税制体系
宋太宗雍熙年间对海外贸易征税的措施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17]4559元世祖定江南之后(3)《元朝典故编年考》、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续文献通考》上明确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定江南”,而后制定了市舶抽解之法,但《元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文献通考》、《粤海关志》都没有记载“元世祖定江南”的时间,而是明确说“至元十四年(1277)立市舶司一于泉州”,所以市舶抽解制度应该是早于至元十四年(1277)就制定了。,“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返互易舶货者”,对其货征税,“以市舶官主之”。[18]总的来说,宋元时期市舶司都是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税。但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征税开始出现进口税和出口税配合的税制设计。如明末的饷税体系里,有“陆饷”,对外来商船征进口税;也有“引税”,对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征收出口税。到了清末,海关征税中更是明确有“出口税”这一税种。
2.由简单的抽分变为多税种配合的复杂税种结构
宋代市舶征税的基本标准就是粗色和细色。《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契勘舶务旧法,应商舶贩到物货,内细色五分抽一分,粗色物货七分半抽一分。”[19]细色是名贵香料、宝石等奢侈品,粗色是纺织品、木材、药材、食品等价格较为低廉的日用品,这样的分类较为粗放,不能实现税收公平。元代,市舶征税开始实行土货和番货区别对待的“单抽”“双抽”制度。客船从泉州、福州等地贩运的货物多是本国所产的土货,只是商人从一个沿海港口走海路贩运到另一个港口销售而已, “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20]。“双抽”之制是指番商的舶货要接受“抽分”和“舶税钱”双重征税,“单抽”是指土货只需要缴纳“舶税钱”。明代的饷税由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构成,这种税种结构已经较为复杂,政府开始依据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合理地选择税种,并使其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布局。清初设立了四海关,海关向商船征收的关税大致包括船税、货税和杂税。清代的海关税和明末饷税在征税形式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海关税的税种结构较之前的市舶征税更为清晰和缜密,体现了税收近代化演进的特点。
(二)税收征收形式的变化
1.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
宋元时期是对舶货进行实物抽分,如日用品(如白番布、花番布、胡椒、槟榔)、选购品(如沉香、丁香、檀香)、特殊品(如金子、银子、水银、硫黄)和奢侈品(如龙涎香、象牙、珊瑚)。实物征税有诸多弊端,有的舶商不如实上报货物数量,有的商船在入港前就被中国商人私下用小船将货物买去。明中期逐步确立货币体系的银本位制后,“隆庆五年以夷人报货奸欺,难以查验,改定丈抽之例”,[21]开始进行货币征税。在明末饷税征收上,多处税则有“征银”的规定。如征收水饷时,“西洋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饷五两,每多一尺加银五钱……”再如,万历十七年(1589)每百斤胡椒征银两钱五分,万历四十三年(1615)每百斤胡椒征银两钱一分六厘。[22]96
2.由从量征收变为从量和从价相结合的征收方式
宋元时期市舶征税都是按照货物的数量按比例抽分,如宋太宗雍熙年间市舶征税的标准是“十先征其一”,“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17]4563从这里的计税依据“斤条株颗”可看出当时是从量征税。明中后期,海外贸易征税的计税依据开始变化,出现从量和从价相结合的税收征收方式。如隆庆五年(1571)广东海外贸易征税实行“丈抽之例”,按照商船的长宽、容积、载重、载货种类来确定税额。再如饷税中的陆饷以货物的价值征税,“以货多寡,计值征输”,“胡椒、苏木等货,计值一两者,征饷二分”。[22]90康熙二十八年(1689)海关税的征税则例规定,货税包含进口税与出口税,进口税税率为从价4%,出口税税率为从价1.6%。[23]
(三)税收管理制度的演进
1.公凭、商引和青单
宋元时期政府对舶商颁发“公凭”,明代政府对私人海商颁发“商引”,清代厦门海关给商船发放“青单”,在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过程中,这种颁发许可证并督缴税款的税收管理方式在各个朝代有所延续。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诏令:福建沿海港口如有商舶到达,市舶司要对其进行查验,如果拥有抽买之后的“回引”,即完税凭证,就可通行。国内商人若想交易政府抽解的舶货,也要向市舶司申请公凭引目。宋代市舶条例中也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24]明代海澄月港征税规定,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都要进行货物种类、数量、船只大小等基本情况的登记,由督饷馆发给商引,每引按章纳税,此时税收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意义开始凸显。清代厦门海关有正口和小口,小口有商船通行,“则遣人丈量浅深,计算多寡,分别征饷,自本地出者挑赴正口大关报税,给青单放行,谓之出水”。[25]此处青单便是一种完税凭证和许可证。
2.牙侩、舶牙人和三十六行
从宋元时期出现的“牙侩”“舶牙人”,到明代的“三十六行”,再到清代的“洋行”,这种由第三方专业经纪人疏通官府和舶商的关系,或者代为销售货物,或者征税的做法基本沿承下来。在宋代文献中依稀可见牙人的身影,如明州往来的商船在交易时“官吏之虐取,牙侩之控扼,卒使之干没焉”,[26]此中可见“牙侩”在贸易港口的行为十分活跃。《元典章》《通制条格》《粤海关志》等文献都记载元代时“舶商请给公据,照旧例召保舶牙人,保明某人招集人伴几名,下舶船收买物货,往某处经纪”。[27]“舶牙人”就是元代活跃在海外贸易领域的经纪商,其对海外贸易舶船进行担保,帮助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明初市舶司在管理贡舶贸易时设有官牙,牙人拥有官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负责在官方簿册上填写舶船的负责人姓名、货物数量等信息,并“每月赴官查照”。[28]明万历年间,在澳门出现了规模很大的 “三十六行”,类似的组织还有“客纲”“客纪”“揽头”“铺行”“夷商(舶)纲纪”等。这些都是由官方许可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机构,他们领银定货,并协助官府从中征税。到了清代,受到官府授权、代表官府主持外贸业务的机构是“洋行”,主要职责是代理外商缴纳关税、帮助外商购销货物、协助清政府监督外商活动,所以洋行具有半官半商双重身份,担负商业和政治双重任务。从宋元时期的牙侩、舶牙人,到明代的三十六行、客纲、客纪,再到清代的洋行,虽然这些海外贸易中介组织的职能范围在不同朝代都有些许差异,但是这些中介组织在海外贸易中起到媒介的作用,并协助政府在日益繁荣的商业活动中进行税收管理,这是各个朝代共同的特点。
三、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原因
市舶征税和海关税都是财政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体现了财政制度与时俱进的特征,当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发生变化,财政制度就会相应调整,以保持自身的适用性和先进性。
(一)国家政治形势影响税制设计
国家征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形式,所以税收受一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影响。明代和清初都是由于东南边境国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使海外贸易征税制度发生变迁。如明初统治者对待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是贡舶贸易和禁海相结合。贡舶贸易是统治者以“赏赉”的方式向朝贡国家购买商品,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禁海是为了打击倭寇势力,维护王朝统治。但贡舶贸易和海禁却引发海寇商人与倭寇的勾结,严重摧残了东南沿海的生产力发展。痛定思痛,朝廷不得不在海澄月港开海禁,允许私人贸易,也相应进行税制体系的调整,设置督饷馆,开征饷税。再如清初,由于沿海一带盘踞着反清复明势力和海盗团伙,为了巩固政权,清政府于顺治十二年(1655)开始禁海。但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反清势力和“三藩之乱”都已平息,沿海安全已无忧患,所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禁,“今海内一统,海宇宁谧,无论满汉人民一体,令出海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允行”。[29]随之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并制定以船税和货税为主体的海关税体系。由此可见,国家政治形势和基本国策的变化会影响和推进税制改革。
(二)商品经济发展潮流迫使税制变革
税收体现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迫使海外贸易征税制度发生了变革。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明代中后期是西方国家工业化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范围新航路广泛开辟,西方国家海外贸易大发展,西方传教士将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介绍给中国,这些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冲击。从国内环境看,东南地区社会的经济形态出现了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海外贸易通过市场机制和东南地区各行业密切联合,并有力地拉动了国内产能扩张和经济增长,商品经济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此时,世界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已席卷了中国东南沿海,国内市场通过广州、澳门、月港的海洋网络伸展到了亚太地区、美洲新大陆和欧洲。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也给明王朝带来大量的白银,导致银本位制度在明代中后期确立。明代官府也不得不顺应经济形势的大潮,将海外贸易管理的政治意义转变为经济意义,开始进行饷税的改革,饷税的开征使中国海外贸易征税从实物税向货币税、单一税制向复杂税制、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体现了经济格局变化对税制体系的重大影响。
(三)税收使私人经济行为拥有合法依据
税法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或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家机关制定公布的法律。所以纳税凭证就是商品自由流通的许可证,私人主体纳税后就拥有了可以广泛流通的合法依据,私人经济行为就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明中期和清初都出现过势头强劲的私人海上贸易现象,虽然遭到官府一再禁止,但这种私人海上贸易行为却愈演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这些海寇商人与沿海百姓关系很密切,百姓可以通过帮助这些海寇商人运送货物维系生活,于是“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30]可见私人经济活动如果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有助于百姓生活的,就应该被允许,一味对其遏制便适得其反。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问题的本质,“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明统治者只好在海澄月港开放海禁,“因其势而利导去,弛其禁而重其税”,[31]允许私人海商请引并缴纳饷税便可以自由贸易。在这里,私人海商缴纳税收就得到了官府的承认,其经济行为就可以合法化,海商可以维持自己的外贸利润,同时官府也可以保证社会稳定和获取财政收入,所以税收成为官府和私人海商之间的纽带和润滑剂,使二者达到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四、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财政意义
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反映了价值规律在财政活动中的凸显,反映了税制体系的近代转型,也反映了政府间的博弈。海关税取代市舶征税,有助于理顺商品货币关系,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
(一)反映了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
1.价值规律在财政活动中愈来愈凸显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式一直是朝贡贸易,贡品由使节代表其君主奉献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则给予丰厚的回赐。朝贡贸易是不等价不公平的交易,更多的反映了中国对周边国家控制的政治秩序,以及不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状况。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被迫改变。如明初实行朝贡贸易,政府付出巨额代价来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气象,但海禁反而导致私人海上贸易行为活跃,而这种民间贸易活动更体现了经济社会的正常需求。当明代官府不得不开海禁征饷税、认可民间的公平贸易和平等交易后,沿海经济恢复发展,市舶收入也大幅增加。清代海关税设立后,更是完全确立了税收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和调控地位。所以财政活动应该重视和合理运用价值规律。
2.税制体系的近代转型
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过程中,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从量征收向从价征收转变体现了税制体系的近代转型。在一个国家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的阶段,纳税人会以实物的形式缴纳税收。但是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以货币的形式征税,便于纳税人缴税和国家的税收管理,避免实物衡量所产生的弊端,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有助于发挥税收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市舶征税从宋元时期的实物抽分,到明末饷税征收银两,再到清代海关税全面征银,体现了税制演变的基本规律,体现了古代税制向近代税制的转型。再者,宋元时期市舶征税是简单的从量征收,这种征税方式的主观因素较多,容易产生“官吏虐取”的问题。明中后期海外贸易征税开始实行从价计征,即依据货物的价值而按比例征税。从价计征的方式能够大大扩展征税对象的范围,能够体现价格信号的灵活性,有利于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量计征转变为从价计征反映了税收征收手段的进步。
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走向分权
纵观市舶征税向海关税过渡的整个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海外贸易税收的管理权方面有一个博弈较量的过程。宋初,受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影响,市舶管理实行“州郡兼领”,东南沿海市舶之利都是被地方政府控制。元丰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当时的《广州市舶条》规定市舶事务由漕臣兼领、由转运使主持,(4)本文认为北宋时期转运司更多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宋史·职官志七》中记载:转运司官员的职责是“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蠧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所以转运司的职责有三:一是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二是对所辖州军间的财赋及州军与中央政府间的财赋进行调拨调剂,保证各州军的财政支出,类似于今天的纵向转移支付与横向转移支付。三是履行对州军财政监督的职责。所以从转运司的职责来看,其更多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崇宁初(1102)到南宋末年官府对市舶事务设置“专置提举”,市舶收入被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元初市舶管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摇摆不定,元代中期市舶事务均由各行省管理,从此市舶事务由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来管理成为基本的制度。明初,永乐皇帝派遣宦官掌管沿海朝贡贸易,架空市舶司权力,市舶管理体现了“国家主导”的特点。明朝中后期逐渐开海贸易,不管是隆庆时期定“丈抽之制”,还是海澄实行“月港税制”,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并积极参与其中(如饷税就是各府轮流督饷),(5)万历三十四年(1606),考虑到各府佐轮流到漳州督饷十分不便,所以改由漳州本府的五名府佐轮流督饷,每年由一名府佐负责饷税征收事务。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这体现了“地方主导”的特点。清前期的财政收入格局中,中央财政占绝对主导的地位,海关税是属于中央的税收,地方可支配的部分极少。但是到了清后期,在财政格局的巨大变化中,海关税中一些项目也开始由地方掌握,如洋药税及洋药厘金、土药税和土药厘金这些涉及厘金的项目就由地方政府主导征收,其收入也由地方政府支配。在1900年清廷户部所提出的非正式预算表中,“海关税”列入“各省入款”,可见地方财权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中逐渐扩大。[32]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市舶征税和海关税的财权争夺的博弈过程中,可窥见中国古代财政体制演变的规律,总的来说,古代中国的地方政府不可能有科学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也不可能有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权,但是在经济社会的演进中、在一些具体财政事务上,地方政府还是在不断地与中央较量和抗衡,以争取适当的权力。
(二)财政逐步加强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作用
财政的机制设计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在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过程中体现了财政对经济社会宏观调控的作用:其一,古代中国各个朝代在海外贸易征税的整个过程中都注重对财税法的建设,如宋代有《元丰市舶条》,元代有《至元市舶则法》和《延祐市舶则法》,清初创设四海关时颁布了粤海关《海税则例》作为试行,后来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式颁布四海关征税则例,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增订浙、闽二海关税则。规范的财税法则的建立使经济主体依法纳税,遏制沿海贸易肆意苛征的乱象,限制投机、走私和非法流通,有利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实现。其二,市舶征税和海关税都属于工商税收,是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肯定了商品贸易行为,为商品流通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营造商业竞争的公平环境,有利于推进商品经济发展和海外贸易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三,在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过程中,货币税和从价计征的方式都有利于彰显价格信号的作用,体现价值规律在财政和经济活动中的意义,并且使税收从生产环节转向销售环节征税,有利于顺畅商品货币关系。总之,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财政体系的转型,由此财政体系表现出更为现代化、开放性和国际化的特点。
五、结论
任何制度都不会突然消亡,而彻底转换成另外一个全新的制度。从时间点上看,中国古代的市舶制度在康熙初年设立四海关时便终止,中国开始了海关税的时代,但是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中存在诸多的继承、蜕变和演进的特征,二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税制体系的变革上看,市舶征税是单一的进口税和简单的税种划分,而饷税和海关税都是出口税和进口税相配合、多税种相配合的税制体系。从税收征收形式的变化上看,市舶征税是从量征收实物税,而饷税和海关税开始实行从量和从价相结合的货币税。从税收管理制度的演进上看,颁发许可证并督缴税款和借助中介经纪人参与税收管理的方式在各朝代有所延续。财政政策具有内在的调整机制,当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就会相应调整,既要保持自身的连续性,又要保持适用性和先进性。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形态出现巨大变化,国际化浪潮加剧,朝贡贸易衰落,私人经济活跃,沿海地区动荡不安,所以财政制度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也进行了大的变革,市舶征税制度开始向海关税变迁。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反映了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反映了财政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作用,反映了财政对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