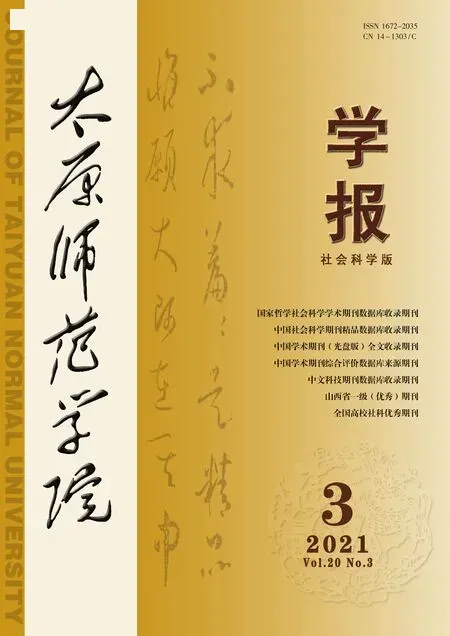宋人选宋文类目与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
——以《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为中心
2021-01-07李法然
李法然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类编总集与类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书的编录体裁中,便有“类文”一种。[1]而方行铎在论述文学与类书的关系时,更将《文章源流》《文选》等类编总集,直接视作这种“专取其文”的类书。[2]张涤华对类书的定义为“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析,利寻检,资采缀,以待应时取给者。”[3]据此定义,类书应具备对一定范围内的一切知识进行分类管理的功能。同理,类编总集也应有相似功能。因此,通过类编总集的分类方式,可以窥见该书所收范围内,编者与作者对于知识的认知。
此后编纂的总括一代文章的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因“以《文选》为蓝本”,后世称之为“《文选》类总集”。[4]《宋文鉴》同样被视作“《文选》类总集”,却放弃了《文选》体下分类的结构,转而采取体下直接依作者时序编排的方式。不过,体下分类的组织方式却被宋代的另一部当代文章选本《二百家名贤文粹》所继承。对于这样一部三百卷规模的大型选本,迄今为止专题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拟先梳理此书之文献、判明此书之性质。在此基础上,结合此书的分类方式,通过与《文苑英华》《唐文粹》对比,揭示此书所呈现的宋人所特有的知识世界。
一、《二百家名贤文粹》文献研究与此书的性质
宋人所编《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三百卷,《郡斋读书附志》卷下著录,称“《论著》二十二门,《策》四门,《书》十门,《碑记》十二门,《序》六门,《杂文》八门,总目六,分门六十二”[5]1216,并详载二百家姓名。此书今存,题《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书前有王偁庆元二年(1196)序,书后有“书隐斋”庆元三年(1197)跋,学者据此定为“庆元三年眉山书隐斋刻本”[6]。
此书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保存宋代古文文献,厥功至伟。但由于其中文献问题尚未厘清,以至利用此书研究与辑录宋代古文时,会出现重收、误收情况。此书的文献问题本不复杂,传世版本均为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但均为残本,所残存的位置互有不同。对此,傅增湘表示:“此书近年内阁大库流散出残本,频年阅肆见四十七卷,余收得七卷,李木斋师有六卷,余卷分藏各家。海源阁亦藏残本一百九十七卷,卷次均经剜改。”[7]其中海源阁藏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是现今存世的体量最大、最完整的残本,本文将大量使用此本,简称“海源阁本”。但正因其卷次均经剜改,为此本的使用增加了难度。
此外,傅增湘还著录过一种残本:“存卷十五、十八至二十、九十至九十三、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六十八、一百七十至一百七十六、一百八十四至一百九十、二百五至二百八、二百七十二至二百七十七、二百八十五至二百八十六,计存四十一卷。……各卷钤有甓社书院文籍楷书朱记。内卷一百七十至七十六计七卷余藏。”[8]其中卷二〇五至二〇八、二七二至二七七、二八五至二八六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卷一七〇至一七六,即傅氏本人所藏七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与潘氏宝礼堂捐赠的卷六十八至七十二、一六五至一六八,[9]以及周叔弢捐赠的卷一八八至一九〇[10]合为一部,凡十九卷,以下简称“国图本”(1)国图所藏《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残本凡三种,本文所称“国图本”特指此种,特此说明。另两种一为前举海源阁本,一为零页一册,未见。。至此,傅氏所录唯卷十五、十八至二十、九十至九十三、一六四、一八四至一八七未见。其中卷九十一、九十二,可知即海源阁本卷十八、十九,[11]卷一六四即海源阁本卷七十四,卷一八四至一八七即海源阁本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唯卷十五、十八至二十、九十、九十三面目不得而知。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六卷,存卷一三五至一四〇,亦有“甓社书院文籍”楷书朱文藏书印。
依据海源阁本与上图本、北大本、国图本的对应关系,可以恢复大部分被剜改的卷次,部分阙卷的内容也可推知。如卷一七七至一八〇,当为上执政书二至五,卷一八一至一八三则为上侍从书一至三,卷二二〇至二二三为祠庙记二至五。再参照《读书附志》给出的各体类目数量,策以下五体中所有类目与卷次的对应关系均可推知。
《读书附志》所提供的此书所收作者名单,起自宋初两朝为相的赵普,终于宋孝宗淳熙年间的宰相赵雄,可见此书为南宋人回视本朝自立国迄于中兴的文学发展而进行的总结。有关此书的去取原则,备载卷末“书隐斋”跋中。今录于此,并略作疏证,以判明此书之性质:
文章莫盛于国朝,而得见其全者或寡。自近岁传于世者,诗有《选》,经济有《录》,《播芳》《琬琰》皆有集。凡前辈大老巨工名儒,风骚翰墨,与夫抗奏发潜之文,亦略备矣。独其著述论议,所以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今古者,或罕其传。脱或有传,则散而未一。此书旁搜类聚,总括精华,会众作如汇百川,气象浑大,诚足以补前人缺典。观者不特可以识斯文正宗,抑见巍巍皇宋文物之盛如此云。[12]
其中“诗有《选》”指曾慥《皇宋百家诗选》。《郡斋读书志》著录五十七卷,称:“选本朝自寇莱公以次至僧琏二百余家。诗序云:‘博采旁搜,拔尤取颖,悉表而出焉。’”[5]1072知此书为南宋人所选宋初迄于南渡之诗。“经济有《录》”指赵汝愚所编《经济录》。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引朱熹语:“读者着眼便见,盖非《经济录》之比也。”小字:“《经济录》,赵公丞相编次。赵丞相谓《文鉴》所取之略,故复编次此书。”[13]所谓《经济录》即《皇朝名臣奏议》之别名。《文选补遗》卷五《条国家便宜奏》题下注:“赵汝愚进《经济录》奏札曰:‘切惟古以来,凡有国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规模制度,其事切于时而易行,不必远寻异世之法。故魏相为丞相,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故事,及贤臣所言,请施行之,此最明于治体之要也。’”[14]此言正见赵汝愚《乞进皇朝名臣奏议札子》中。《播芳》疑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所收以四六为主,多应酬之文。《琬琰》当指《名臣碑传琬琰集》,即碑志史传文字。跋称“补前人缺典”,说明此书的编选范围排除了上述“风骚翰墨与夫抗奏发潜之文”,即陶冶性情的诗、用世的奏议与应酬的四六、志传。而所谓“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今古”,则是正面提出此书所“补”的内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向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著书立言的终极目标。“天人之际”被余英时拈出,作为讨论中国的“轴心突破”的关键词。[1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在“轴心突破”完成之后,被搁置了近千年,其间的儒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人伦层面的“礼”,如清人赵翼所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16]。直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这一问题才被重新提出。在宋儒的论述中,先秦儒学中“天”的最后一点神秘主义色彩被彻底扫除。所谓“天之所以为天,本何为哉?苍苍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盖自然之理也。”[17]“天”的含义已经无限接近于“理”,学者的关注点也由人伦层面的“礼”,贯通至天道层面的“理”。由此引出此书所补的第二项内容“发明道学”。其中“道学”当取广义,即“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18]14之“道学”。而《中庸》所载圣圣相传的,正是夫子所罕言的“性与天道”[18]79。也就是说,“发明道学”,便是有关“经纬天人”的学问。这种学问由“天人之际”进一步落实到人事,便是“该贯今古”。宋代史学的发达已经屡为前人所道,而正是受到“经纬天人”与“发明道学”的影响,“宋代史学的优长在于史识、史论、史评的方面”[19]230。也就是说,此书剥落了文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20]的外在功能,而直指知识阶层“立言”以安身立命的核心。而“立言”的具体内容,体现出宋代思想的新动向。
此书卷首有《二百家名贤世次》一卷,备载所收诸家科第,宛然一篇“二百家名贤登科录”。在“门阀贵族被消灭,‘士’的产生途径只剩科举一条的北宋以降”[21],进士及第便成为跻身“知识精英”阶层的重要标志。而此书的编纂体例,如跋中所谓“旁搜类聚”,即搜集力求全备,而以分类的方式加以组织。由此,此书所收对象为宋代的知识精英,所选内容是他们“立言”的核心部分。而此书分类录文的方式同于类书,事实上是一种对知识的分类管理。这样,我们大可从中一窥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
二、经史与天道:议论文字与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管理
论著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手中承载知识、表达思想最为直接的著述形式,是上述“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古今”各项最为理想的载体,是“立言”的最为直接的手段。《二百家名贤文粹》凡三百卷,其中“论著”一类多达一百三十四卷,超过总卷数的三分之一,可见编者对于这一类文章的重视,也反映出宋代知识阶层对于文章等级关系的认识,如吕祖谦所说:“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22]。不过殊为可惜的是,所占比重最大的“论著”一类,其残缺也最为严重。一百三十四卷中,八十八卷已不可见,所存仅为三分之一。所幸宋代类编的大型总集尚多,如百卷本《重广类编三苏先生文粹》,以及七十八卷的《新刻诸儒评点古文集成前集》等。我们不妨以此为参照,以略补《二百家名贤文粹》“论著”类的残缺造成的缺憾。
今存《二百家名贤文粹》,以海源阁本卷一所收苏轼《巢父论》为开篇,所标类目为“古圣贤一”,以下“古圣贤”论四卷,备论巢父、许由、夔、鲧、重黎、伊尹、太公、周公、孔子、伯夷叔齐、柳下惠、季札、孔门弟子、孟子等。之后所存,国图本卷六十八至七十二,与海源阁本卷八至十三衔接,为“历代人臣”论,起自西汉之晁错、贾谊,迄于晋之王衍、祖逖。“古圣贤”论、“历代人臣”论,在宋人的论体文分类体系中,均属于“历代人物论”。而“历代人物论”之中,至少还应包括“帝王论”,论述尧、舜、禹,及夏、商、周的上古帝王,位列“圣贤论”以上,以及“历代人君论”,论述列国以下历代君主,位列“历代人臣论”以上。或有将列国君臣与历代君臣又加细分者,可以参看百卷本《三苏文粹》卷十一至二十八。更进一步,“历代人物论”尚不应是宋人论体文分类的开端。“历代人物论”属“史论”的范畴,在此之上,应当还有“经论”。同样参照百卷本《三苏文粹》,以三苏五经或六经总论开篇,以下为各经以及四书分论。笔者不敢保证《二百家名贤文粹》一定也采取了这样的分类方式,但在“古圣贤”论以上缺失的六十三卷中,足以容下“经论”与“帝王论”“人君论”的部分。
海源阁本卷十四至二十一为“圣道”论,脱离了围绕经史的讨论,开启了另一个话题。论者指出,“受到新儒学,特别是理学观念的影响,南宋类书中越来越体现出不同于汉唐天命观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痕迹”[23],并以《古今源流至论》各集以《太极图》《西铭》《通书》《四书》以及“道学”“格物之学”等开篇为证。这一现象,也表现在《二百家名贤文粹》的“圣道”论中。此类备论宋代新儒学中“神”“诚”“明”“德”“权”“仁”“义”“礼”“四端”等概念,海源阁本卷十六以一卷篇幅论“学”,卷十七则杂论儒行、不朽、功夫、言行、祸福等。卷十八以下收入周敦颐《通书》、张载《正蒙》、邵雍《观物篇》等理学先驱的经典著作。
“圣道”以下,为“治道”“臣道”。若参照《古文集成前集》戊集卷一,于《大臣论》之上又收《为君难论》《君心论》《君体论》,则“臣道”之上,应当还有“君道”一类。“治道”“君道”“臣道”,稍稍涉及具体人事,但以“道”命名,仍然是有关教化、礼乐、刑政的总则。以下“官职”“用人”“朋党”“风俗”“财用”“兵”“边防”等类,备论制度、食货、兵戎,可以总称为“时务论”。自“圣道”类以下,若参照《近思录》纲目,则“圣道”包含了“道体”以至“改过迁善,克己复礼”等类,即理学家的本体论与功夫论,“治道”“君道”“臣道”,相当于“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下则相当于“制度”与“君子处事之方”[24]。可见,“圣道”论以下各类,是按照理学家所划定的路径展开知识结构的。
若参照宋初所编,总结先唐及唐代文学的类编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中论体文的类目,则《二百家名贤文粹》“论著类”所体现的宋人独特的知识管理方式便可以一目了然。《文苑英华》论体分天、道(笔者按:指道教、神仙等)、阴阳、封建、文、武、贤臣、臣道、政理、释、食货、兄弟、宾友、刑赏、医、卜相、时令、兴亡、史论、杂论等类,《唐文粹》则分天、帝王、封禅、封建、兴亡、正统、辨析、文质、经旨、让国、兵刑、临御、谏争、嬖惑、前贤、失策、降将、佞臣、郊寝、明堂、雅乐、车服、刑辟、谥议、历代是非、丧制等类。可以明显看出,二书对论体文的分类,与唐代至宋初的类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巩本栋指出,《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的一致性,在于“按照天地君亲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秩序分类和安排所选文章的顺序”[25]。观二书对论体文的分类,均以“天”为首,而以下有关人事诸类,则以帝王为人间的核心进行呈现。尤以《唐文粹》最为鲜明,“天”类以下,便是“帝王”类,之后“封禅”等类,直接与帝王相关,而“辨析”至“让国”有关经典的学问、“前贤”以下有关历史的学问,与“郊寝”以下有关礼仪的学问,均围绕着帝王展开。
《二百家名贤文粹》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变化。“经史论”取代了“天”类,被置于“论著”之首。前贤论述“宋型文化”,每以讨论义理的朱子学为代表。(2)关于“宋型文化”,可参见傅乐成先生《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氏著《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376-378页),及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8-227页)等。但如周裕锴所说:“就是被清人目为空疏的宋代理学,实际上也是‘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26]更何况,在理学最终定型之前,在唐宋之间价值体系重构的过程中,经典的内在一致性与历史的前后一贯性,被视作重要的路径,二者分别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为代表。[27]286-313可见人文的经史取代了自然的“天”,成为了宋人一切学问的基础。接下来,“圣道”类集中体现了宋儒对于宇宙与人的新思考。此类思考自中唐已经发生,《唐文粹》注意到这一点,但并未将这些论述整合进论体文所承载的知识体系,而是专设“古文”一体,处置此类文章。[28]197而在《二百家名贤文粹》中,如前所述,“圣道”论以下各类,依照《近思录》的纲目展开,“圣道”成为了一切立足于人事的学问的起点。而在全部《二百家名贤文粹》“论著”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中,“圣道”上承经史,下启治术,在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中处于枢纽位置。
若再参照明人所编《性理大全》,可以发现,上述知识体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性理大全》以《太极图》等著作开端,继之以有关理气、性理与为学功夫的论述,佐以经史,再展开为君道、治道。仅就分类来看,与《二百家名贤文粹》相仿,但展开的方式,则完全以宋儒义理之学为基础,而有关经史与治道的学问,则是围绕义理之学组织起来的。包弼德认为,唐代的文化观“立足于历史”,宋代则“立足于观念”,[27]539《唐文粹》论体文与《性理大全》的组织方式,正好体现出唐宋之际思想转型的两端。而《二百家名贤文粹》“论著”类,以“圣道”为枢纽,连接起经史与治术,正好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体现出宋代精英阶层独具特色的知识管理方式。
三、投谒与问答:书简尺牍与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表达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进行知识表达最为直接的方式是论著。除此之外,书信往还也是表达知识的重要手段。且这一手段的重要性,在宋代有增加的趋势。《二百家名贤文粹》继“论著”与“策”之后,收“书”五十五卷,便反映出这一点。
首先,仍以《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为参照。《文苑英华》所收“书”一体,先依受书人,后依所言内容分类,《唐文粹》悉依所言内容分类。《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书”类,则完全按照受书人分类,与上述二书皆不同。而更为不同之处在于,《二百家名贤文粹》所列受书人以皇帝为首。而《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二书,皆专设“疏”“书奏”文体,用以处置“上皇帝书”一类文章。(3)《二百家名贤文粹》因已有赵汝愚《皇朝名臣奏议》一书,而未专设奏议类,却在“书”类当中为“上皇帝书”留下了位置。事实上,宋人对“上皇帝书”一类文章的文体定位不甚清晰,同样是分集编排的别集,《东坡七集》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编入《奏议集》,而《欧阳文忠公集》则将《准诏言事上书》编入《居士集》。准此,宋人对于“上皇帝书”究竟属于书简还是奏议颇为犹豫。如此便可以理解《二百家名贤文粹》不收奏议,而在“书”中收入“上皇帝书”。因此《文苑英华》所列受书人是以太子为首的。
《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上皇帝书”,又与《文苑英华》《唐文粹》所收奏疏颇有不同。如海源阁本卷六十九所收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作于嘉祐四年(1059)入京为度支判官时,[29]而书中所言变法构想,影响了北宋之后数十年的政局。又卷七十所收苏洵《上皇帝论十事书》,以布衣之身,备论大政,与《权书》《衡论》《几策》相发明。与王安石上书针锋相对的是卷七十一所收苏轼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上皇帝论人心风俗纪纲书》,苏轼时任开封府推官,[30]而所言之事,则是关乎“国是”的大问题。同卷所收苏辙《上皇帝论三冗书》同样作于是年,则直指北宋承平百年的积弊,苏辙时方服除入京,尚未有具体任职。[31]可见,不同于针对具体事务的奏疏,《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上皇帝书”,可以与上书人的政治地位、具体职掌无关,而是面对皇帝全面阐述上书人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类“上皇帝书”所体现的是上书人的“政论”而非“政见”,是士人依据自己的学养形成的“一套对于政治的总体论述”[19]319。而由此产生的“上皇帝书”,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投谒,投谒对象是皇帝本人。事实上,苏辙便因前举上书而入职制置三司条例司。
至于以下上宰相、执政、侍从、台谏、监司帅守书,则更为直接地承担着投谒的功能。这种完全依照受书人官职分类的方式,周剑之在研究宋代启文的分类时尝予以关注,并采取“门阀士大夫”向“科举士大夫”转型的理论框架加以解释:“在门阀士大夫居于领导阶层的时期,士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建立,更多依赖血缘、婚姻等方面的联系。而在科举士大夫占领导地位的时期,士人之间的联系,则更多建立在科举制度与职官选任制度的基础上,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32]。以此回视依受书人官职分类的书简,便不难看出其投谒功能。但是书毕竟不同于启,启可以是高度程式化的、纯粹以应酬为能事的文体,但书必须有具体内容。因此,投谒书简也可视为表达知识的手段。
投谒书信常伴随着投献文字。如唐人举进士之行卷,便“往往另外准备一封书信,连同行卷一并投献。这封信除了表达自己希望被赏识、提拔的愿望之外,往往还将所献文字,加以扼要的介绍,以唤起对方的注意”[33]。宋代进士科虽因糊名誊录制度,以致行卷之风不行,但在宋初科举制度尚不甚完善之时,仍有行卷行为发生。高津孝曾论及柳开与王禹偁的行卷活动。[34]而海源阁本卷七十八(国图本卷一六八)所收田锡《上中枢相公书》,首称“乡贡进士田锡谨以长书一通,献于相公黄閤之下”,又云“相公若以片文知于小人,则锡有二十编之文,愿受知于门下”,又言“年龄在躬,三十有九。昔在于蜀,同与科场者,今皆列丹陛,升清贯,出奉帝皇之命,入居台省之职。而小人犹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困为旅人,辱在徒步”。而田锡适于是年秋登进士第,[35]则此书为进士行卷无疑。
当然,进士行卷毕竟不是宋代科举的主流,而制举行卷则更具宋代特色。钱健壮等注意到宋代制举行卷,并指出:“受行卷目的的驱使,宋代的宰相、参知政事等执政官,两制、学士等侍从官,以及地方转运使或知州,是应制举者的最主要投献对象”[36]107。而如前所述,宰相、执政、侍从、监司帅守,正是《二百家名贤文粹》“书”类的分类体系。事实上,海源阁本卷八十二(国图本卷一七二)收冯澥《上文太师干求举贤良书》(4)此篇《宋代蜀文辑存》卷三一据海源阁本卷八二收入,作冯澥,续补又据国图本卷一七二收入,作冯山,误。《全宋文》卷一七〇八、二八二一因之重收。、卷九十八收蒋之奇《制举投献第一书》《第二书》,便是制举行卷。前引程先生文中指出唐代进士行卷投谒书信,需要对行卷文字进行简要介绍。同样,钱先生文中也指出此类书简“重点放在解释、说明行卷内容,阐明其主旨与精神指向”[36]118。这样,原本由制举进卷中策论承担的知识表达功能,[37]258也经由投谒行为,为书简所分担。
有别于依照受书人官职的分类方式,《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书”中,还有“师友问答”一类,以“师友”二字泛称受书人身份,而未再作细分。不同于此前数类面向政坛公开的书简,师友之间的往还书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私密性。如海源阁本卷一百所收吕大临《上横渠先生》三书,几全为通问寒温之语。私密性达到一定程度,在文体学上便应当划归“尺牍”。对此浅见洋二指出,“文集中收录的文本是文人有意面向社会,并想要载入史册、流传于世的文本,自然带有强烈的公开性。与之相对,尺牍具有较强的私密性,或许不宜收入文集中。至南宋,尺牍才在文集的分类中占有稳固的位置”[38],并举《东坡集》《后集》有“书”而无“尺牍”为证。从北宋“书”“尺牍”判然两分,到南宋尺牍进入文集分类的过程诚如所言。窃以为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书”与“尺牍”合流的现象。如同为朱熹与吕祖谦的往还书信,在朱熹《晦庵集》中称作“书”,而在吕祖谦《东莱集》中便称作“尺牍”。南宋作者及其亲属、后学,热衷于将“尺牍”混同于“书”编入文集,则是取消了师友往还的私密性,而一概公之于众。这一行为,或许是在践行北宋理学先驱“从个人内在生活到外在国家政策,全部用公道来贯通”[39]的处事态度。而这一过程,在《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师友问答”之书中,便已透露出端倪。
《二百家名贤文粹》对“书”的分类,与朱熹《晦庵集》颇有相似之处。元人黄溍《跋晦庵先生帖》称:“先生文集所载尺牍,分时事出处、问答两门。”[40]《二百家名贤文粹》面向公共政坛之书与师友问答之书对举的结构与此相同。所不同的是,《二百家名贤文粹》将面向公共政坛的部分依受书人身份细分,而师友问答则笼统归为一类;《晦庵集》则相反,面向公共政坛之书以“时事出处”一类涵括,而师友问答部分则依受书人细分“汪张吕刘”“陆陈”“知旧门人”等类。如果说《晦庵集》的分类方式表现出南宋士人“转向内在”之后对于原属于“私”领域的知识表达更为重视的话,那么《二百家名贤文粹》总结北宋立国至南渡中兴之文章,表现出的便是宋代精英阶层知识表达方式转变的过程。
四、游赏与著述:文人意趣与写作技能
在中国文言散文之中,记与序一向被认为是“文学性”最强的两种文体。《二百家名贤文粹》虽号称“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古今”,但其中除上述承担知识管理与表达功能的策论与书简外,也收有记、序二体凡六十五卷,在全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记、序二体在宋代以前便已相当成熟,吴承学指出:“自从唐宋古文兴盛以后,出现文、史合流的倾向。文章学内部越来越重视叙事性,叙事性文章也大为增多。具体反映到文体之上,便是记体与传体的高度繁荣”[28]192。至于序则更可以远绍《毛诗序》与《太史公自序》。《文苑英华》与《唐文粹》之中均设有记、序二体。但比较二书与《二百家名贤文粹》对记、序二体分类的异同,仍然可以看出此二体在宋人笔下的新变。
前引吴先生文中已经注意到,“《文苑英华》中‘厅壁记’共10卷,在记体之中所占分量最重”[28]192。《文苑英华》对于“厅壁记”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体量之大,也体现在分类之细。在“厅壁”之下,《文苑英华》又依所记官署细分为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藩镇、州郡、监军、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簿尉、宴飨各类。正如朱刚所说:“一般地说,如果某一类别的子目被分得过细,很可能是此类题材的诗作十分发达的证明。”[41]“厅壁记”在宋代以前的发达可想而知。据唐人描述,“厅壁记”的内容为“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作用是“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42]可见,“厅壁记”完全着眼于为官职守,总结前辈经验,以备后人借鉴。此外,《文苑英华》又有“宴游记”七卷,体量上仅次于“厅壁记”。如果说“厅壁记”着眼于作为官僚的公事,那么宴游则是士大夫的私人空间。于是可以看到,宋初总结前代文学时,“公”与“私”的领域是被判然分开的。
《二百家名贤文粹》中所收记体,以“学记”“祠庙记”与“楼观”“堂宇记”为多。学记、庙记关系密切,均反映出宋代右文重学的风气,[43]可与前文有关“经史论”的论述相参,在此不必赘述。而诸多“楼观”“堂宇记”,却是值得注意之处。此类所记楼观堂宇,多有宴游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与唐人“宴游记”相同。但此类宴游,并非全然私事,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政治信息。如赵惠俊指出:“京城的宴饮活动可示太平,地方也同样需要类似的礼仪性活动的展示。……如果一地已然太平,但郡守无法通过宴饮、游冶等活动向民众展现太平,便是其过失。”[44]《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楼观”“堂宇记”便显示出宋人宴游的这一功能。如海源阁本卷一三一所收苏轼《超然台记》称:“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治下百姓与地方官相安无事,于是治园圃,而为宴游之计。卷一三四所收孙觌《滁州重修醉翁亭记》也表示:“山舒水缓,年丰事少,公日从僚吏宾客徜徉泉山,把酒临听,乐而忘归。”将欧阳修乐游醉翁亭的背景描述为“年丰事少”。而刘尚荣则指出,“作者未忘自己的太守身份与职责,所谓‘太守之乐其乐’实即作者刻意营造的‘与民同乐’”[45],以为太守之乐,事实上是其职责所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楼观堂宇记”中,宋代知识精英们营造宴游场所,主持宴游活动,事实上都是在履行其地方官的职守。而履行的方式,如前举孙觌记文中所说:“望清流关,吊古战场,而川湮谷变,不可复识矣。登卫公怀嵩楼,酌庶子泉,观李阳冰小篆,而笔画雄怪,号天下之奇迹。记菱溪石,徙置幽谷中,以遗好奇者洞心骇目之观”。采访古迹、探幽寻奇,无不充满着人文意趣。宋人每有“文章太守”之称,(5)如欧阳修《朝中措》词称刘敞“文章太守”,苏轼《西江月》词称欧阳修“文章太守”,秦观《与邵彦瞻》称鲜于侁“文章太守”,《(隆庆)高邮州志》卷七亦载杨蟠有“文章太守”之称。而“文章”与“太守”的结合,也将“公”领域的官事职掌,与“私”领域的宴饮游赏结合起来,与前文所述“师友问答”之书中显示的“公”与“私”的贯通一脉相承。
不过,在《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楼观堂宇记”中,还有一类文章同样值得注意。如海源阁本卷一三二所收诸“轩记”,卷一四一、一四二所收诸“斋记”,卷一四三所收诸“庵记”。这里的轩、斋、庵,不再是宴饮游赏与履行地方官职责之处,而是士大夫悠游退居与从事个人文化活动之所。同样的文人意趣,在上述诸记中,不再表现为宴饮游赏,而是表现为书斋生活。书斋作为一个封闭空间,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为士人提供了反躬内省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公”与“私”不再贯通,而是呈现出士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外在职守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点,在位列诸“轩记”之首的苏辙《东轩记》中便有充分的显现。[37]222-225由此,宋儒开启了“转向内在”的进程,与前述“公”与“私”的贯通形成充满张力的悖反。
与此同时,书斋是宋代精英阶层从事读书与著述活动的场所。有关书斋生活的记述,事实上也就是对于读书著述生涯的呈现。这便又回到了宋人右文重学的传统。这一点,在《二百家名贤文粹》对于序体的分类中也有所体现。此书序体以“经史序”为首,与前文所述“论著”类以“经史论”为首同一机杼。以下依著述形式,依次是“文集序”“诗集序”与“图籍序”,秩序井然。“送别序”与“名字序”单列于各类著述序之后,绝不相混。反观《文苑英华》文集、诗集、诗序与游宴、饯送、赠别序交错而出,而除诗文以外的著述形式,如经、子、家谱、日历、图籍等,总以“杂记”涵括。由此可以看出,与宋初总结前代的情形相比,在《二百家名贤文粹》所体现的宋人知识体系中,读书著述成为了一个单独的知识门类,而各种著述形式已经形成清晰的组织结构。读书著述在宋代的风行,也便从中得以体现。
关于读书著述之风,戴建国在研究汉宋之间类书之因革时指出:“唐前重学术竞争,学风高炽,有高尚的人文底蕴;唐及五代十国重智力较量,文风盛行,有真率的人文底蕴”[46]。如前文所述,成熟的“宋型文化”虽以义理之学为代表,但在宋代右文重学的风气下,首先兴起的是经史之学。“十三经”的格局最终形成,注疏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强调。这一学风的转变,力矫晚唐进士之浮薄。前文有关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的论述,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展开的。但与此同时,晚唐的“文风盛行”在宋代并未消弭,写作技能也仍然被强调。在上述《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序体文所构建的著述形式的组织结构中,“文集”与“诗集”依然占居着重要的位置。而在《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构建的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中,于“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古今”之外,仍然为“文学性”极强的记、序二体保留着位置,其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看来,戴先生所谓唐前之“学风”与唐五代之“文风”,同时为宋所继承,在宋代并驾齐驱。由此,张力与悖反再一次呈现在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中。
五、结语
包弼德在论述宋初对文治的恢复时指出:“唐代的文对于学者们应该做什么有两个答案。初唐的朝廷学术告诉他们应该通过对文化传统与形式的编纂、综合,赞美海内的重新统一,改变五代以来的文化衰落。但是晚唐古文学者告诉他们应该建立独立的学术界,以反对流俗,为道德和共同的利益说话。”[27]186本文用以参照的《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同样编于宋初,恰好应对了这两种不同的取向。《文苑英华》编订的初衷是在太平盛世“以文化成天下”[47],而姚铉编订《唐文粹》,则与中唐以下的“古文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8]二者共同开启了宋代精英阶层建构其知识世界的历程。至南宋庆元间编刊的《二百家名贤文粹》,这一知识世界已颇具规模。
从《二百家名贤文粹》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宋人以“圣道”绾合经史与治术,在知识门类上处于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过渡之中;可以看出宋人在投谒与师友问答的过程中进行的知识表达,在表达方式上处于由面向公共空间向师友之间私密往还的过渡之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在人文意趣的笼罩下,公与私之间、内与外之间,以及尊经学、重义理与重视写作技能之间存在的张力。如此,《二百家名贤文粹》中展现出的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显示出不稳定的、紧张的状态。思想领域的“唐宋转型”正在发生,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思想因素,尚处在胶着的较量当中。近年来,受到“唐宋转型”说的影响,以“宋型文化”进行宋代文史研究颇为流行,成果也颇为丰硕。然而,“宋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一定出于后人回视下的总结。而宋人当代文章选本中所反映出的知识世界,远较类型化的“宋型文化”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