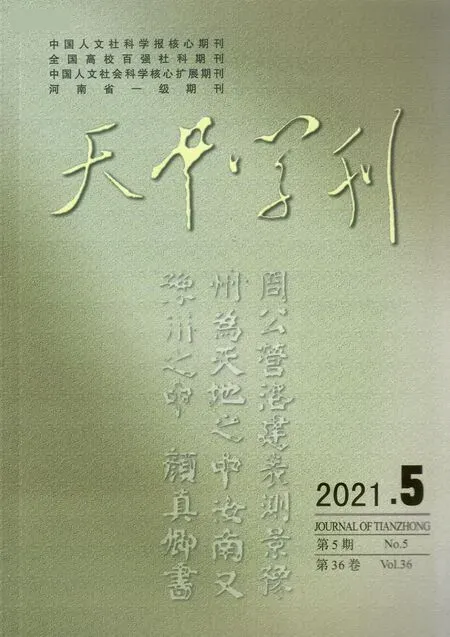转益多师 推陈出新
——试论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
2021-01-07宋笑
宋 笑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在中国古代灿若繁星的作家群体中,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无可替代,他们伟大的人格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他们的作品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经典,研究屈原、李白、杜甫无疑极其重要。新时期以来,杜甫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山东大学张忠纲教授是贡献最大者之一。张忠纲先生早年的研究兴趣较广,从六朝诗歌到宋元戏曲小说,后来逐渐集中于杜甫研究,其杜甫研究成果丰硕,除了单篇论文之外,专书有《杜诗纵横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杜甫诗话校注五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杜甫诗》(中华书局2013年)、《诗圣杜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杜甫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等,以及他参与或组织编写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等,杜甫研究著作多达20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杜甫全集校注》与《诗圣杜甫研究》两部“大书”。《杜甫全集校注》是由萧涤非先生牵头组织启动、由张忠纲先生担任终审统稿才得以完成,这是倾三代学人的心血共同著就的一部集大成式的杜集校注本。该书体例严谨,注释详明,当代著名唐代文学专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盛赞其为“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1]。在萧涤非先生去世后,张忠纲先生继承先师遗志,将大量精力投入全集校注稿的审定、修改中,《杜甫全集校注》方得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集校注稿集中了他个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只是因为著作体例的原因,无法系统呈现他的研究。可以说张先生组织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这部书对当代杜甫研究的贡献非常之大。张忠纲先生研究杜甫其人其诗已经发表的单篇论文大都收入《诗圣杜甫研究》,此著收录了90余篇论文,上编主要探讨杜甫家世、交游、思想、诗歌艺术等问题,中编是由唐至清对杜甫其人其诗研究的整理与述评,下编则对近现代杜甫研究进行了整体的考察。
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成果被学界所重视,出现了多篇研究张忠纲先生论杜的专论文章,如中央财经大学左汉林的《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张忠纲先生〈诗圣杜甫研究〉读后记》[2]、詹杭伦教授的《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评张忠纲研杜专著二种》、[3]西北师范大学郝润华与武国权合写的《杜甫诗话的集成性整理——评〈杜甫诗话六种校注〉》[4]、福州大学梁桂芳的《“杜诗学”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张忠纲、赵睿才、綦维、孙微〈杜集叙录〉》[5]。这些文章多是对其某部著作研究方法与特色的总结与评述,但对张先生论杜的系统研究学界未见有专论发表。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互有交叉):一是杜甫其人研究,此部分是对杜甫家世、生平、思想、交游的考证;二是杜甫诗文研究,此部分是对杜诗及杜文进行的整理、校注、辨伪、辑佚等工作;三是杜诗学文献研究,此部分是对杜诗学一般规律与杜诗学史的研究。本文首先回顾张先生学术研究历程,然后重点从上述三方面入手,系统阐述张忠纲先生杜甫研究的重要贡献,最后讨论张先生杜甫研究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下分别述之。
一、张忠纲先生研究杜甫学术经历
张忠纲先生1940年5月4日出生于山东潍坊,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张先生在学期间博览群书,常常手不释卷,自身的勤奋刻苦与名师的教导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根基。1964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冯沅君研究宋元文学,后留校任教。冯先生在教学工作中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仅亲自为他制定培养计划,而且每周定期为他辅导课程,对张先生读书笔记的批改极为细致,其讲解也往往具有真知灼见,冯先生严谨细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使张先生受益无穷。“功夫要死,心眼要活”,这是冯先生教导张先生的“治学三昧”,张先生在此后的学术道路上一直坚守着这八字箴言,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
张先生的杜甫研究从一次“勉为其难”的上任开始。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在山东大学成立了《杜甫全集》校注组,萧先生点名让他参加校注工作,张先生与杜甫研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萧先生的率领下,校注组首先远赴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广罗传世杜诗文本,校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幸的是,萧先生于1991年因病溘然长逝,校注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但张先生没有放弃杜甫研究,一直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带领学生出版了多部杜甫研究著作。2009年,山东大学重启《杜甫全集校注》的项目,任命已经退休的张先生担任终审统稿人。张先生不仅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杜甫全集校注》的第一、二、十七、十八共四卷及附录五种《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的撰写工作,而且带领校注组通审书稿、统一体例,修正讹误,对杜诗的编年与编次重新做了调整。因为全书有14卷成书于1994年以前,张先生均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补正。最终三代学人接力完成的12册共680万言的巨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张先生对两位老师的躬亲指导感念至今,而他也不负师恩承继了两位老师的衣钵,一生致力于古文学研究。冯先生的博通古今、萧先生的博观约取在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融合,其学术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在张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学人坚韧不拔、求实创新的学术传承精神。
值得一述的是,1994年10月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张忠纲先生被选为副会长。2000年10月,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张忠纲先生被选为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直到2017年卸下杜甫研究会会长的担子。多年来,张忠纲先生不仅坚持开展杜甫研究,而且还积极组织杜甫研究会,大力推动当代的杜甫研究,为当代杜甫研究的深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张忠纲先生论杜甫其人
张忠纲先生多年研究杜甫生平的成果大多被收入《诗圣杜甫研究》,这些文章大多公开发表过,论及杜甫的思想、家世、交游等方面。
关于杜甫与原始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张先生的着眼点是将杜甫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谈到杜甫与儒家的关联就必然涉及其忠君思想问题,对于“杜甫之忠君为愚忠”的说法,张先生在《忧国忧民无已时——杜甫爱国思想琐谈》一文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辩驳。张先生主张追溯杜甫生活的社会环境,还原杜甫忠君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萧涤非先生曾提到,“杜甫的忠君思想,固然受了儒家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他所处的封建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不但有他的阶级烙印,而且也有他的时代烙印,不仅是他的阶级局限,而且是他的时代局限,即历史局限”[6]。张先生基本认同萧先生的观点,但他认为杜甫的忠君是和爱国、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杜甫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在国富兵强的开元盛世度过,当“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深切感受到了“国破山河在”(《春望》)的民族危机感,无比痛恨安史叛军带来的杀戮与痛苦,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剿定叛军,恢复唐王朝的繁荣稳定。杜甫力量微薄,只能寄希望于当朝皇帝,坚信有朝一日君主能够平定叛乱,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杜甫的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被叛军俘虏后坚守气节,冒死逃出贼窝去往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在等级制度森明的封建社会,君主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代表了封建国家的势力,杜甫之忠君其实质就是爱国,杜甫批判当朝统治者穷奢极欲,也是因为爱国。张先生认为,与其说杜甫是忠臣,不如说他是直臣,“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7]。
张先生在文中还涉及对杜甫性格的探讨,该话题极具前瞻性与广延性,足见其目光之敏锐。自20世纪50年代杜甫研究兴起后,人们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构建新杜学体系,杜甫被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但杜甫的形象出现了单一化、片面化的问题。张先生眼光独到地发现这一鲜少有人触及的话题,提出杜甫也有桀骜的性格侧面。文章先举杜甫疏言救房琯之例以证其言。房琯与杜甫为布衣之交,二人友情深厚。房琯得肃宗重用后,正直为人的他屡次直言进谏,可惜小人谗言在侧,肃宗渐恶房琯。至德元载,房琯率军与安史叛军交战,义军大败,杜甫诗“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即描绘了当时惨烈的战后场面,此事触怒肃宗,琯终被罢相。而杜甫却上疏为房琯争辩,言“罪细,不宜免大臣”(《新唐书·杜甫传》),肃宗大怒,后经大臣力保才免于诏三司推问,然而肃宗此后便疏远了杜甫。杜甫并未因此三缄其口,仍然上书为房琯求情,还常常在诗中表达对房琯的思念,其傲骨可见一斑。另一例,就是杜甫对李白的态度。杜甫与李白二人感情相当深厚,杜甫常写诗夸赞李白。当李白出于爱国热忱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却被无辜牵连进肃宗与永王权力斗争的漩涡,以致流放夜郎之时,杜甫未落井下石,反而盛赞李白,为李白辩白冤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杜甫性格的桀骜不驯与李白的狂傲有很大的不同,杜甫之傲是骨子里正义和坚韧的外显形式。张先生并无专论探讨杜甫的性格,但却拓宽了杜甫研究的视野,给后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张先生是山东人,因此他尤为关注杜甫在山东的行迹与交游。“放荡齐赵间”(《壮游》)是杜甫早期漫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杜甫的性格复杂性、思想多元化与诗风丰富性的形成意义重大。《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一文以杜甫游历的泰山、兖州、单州、济南四个地点为考察对象,详细考察了杜甫游历之处的名胜古迹,澄清了杜诗中许多存疑的地点。如张忠纲先生对杜诗“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清河”二字提出质疑,认为《宋本杜工部集》所注“清荷”(一作“青荷”)才为此诗原貌。学者大多将“清河”释为济水,然济水有“清河”之名始自杜佑《通典》,此书成于杜甫逝世30年后,在时间上无法对应。张先生还从地理位置方面考虑,“盖北渚高踞水中,四周荷叶田田,故曰‘凌青荷’”[8]211。因此,尽管杜诗注本多从“清河”,张先生校注的《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为《校注》)卷一中仍据《宋本杜工部集》所注改为了“青荷”,由此可见张先生的胆识与见地。《杜甫与山东籍诗人的交往》一文考察了杜甫与13位山东籍诗人的交往,这些诗人或与杜甫有唱和之诗,或曾出现在杜诗当中,对杜甫的日常生活研究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彰显了张先生杜甫研究的另一个特点:诗史互证。张先生不仅考察了杜甫与交游对象的相关诗歌,而且从遗世之史书、笔记、墓志铭中寻找蛛丝马迹,最大限度地挖掘了杜甫可能有所交往的山东籍诗人与杜甫的关系。除此之外,张先生还写作了《北宋时期的山东杜诗学》《南宋时期的山东杜诗学》与《山东学者注杜评杜概论》等有关山东地区的杜诗学研究文章,表现出了一位学者对故土的热爱。
三、张忠纲先生论杜甫诗文
(一)论杜诗文之思想内容
张忠纲先生论杜诗文涉及多方面、多层次,包括对杜甫诗文创作年代的辨析、对杜诗文的注解、对各版本杜集异文的考订、对杜甫佚诗的整理和对杜诗结构的阐释等内容,研究范围极广。
张先生考释杜诗创作时间的首要原则是本于作品,从杜诗文中提炼关键线索。北宋蔡兴宗首倡杜甫于天宝九载预献《三大礼赋》之说,赵次公、葛立方、黄鹤等都主九载献赋,而自钱谦益力主“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的天宝十载说后,其后的注杜学者多从钱说,学术界受此影响对于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时间基本认定为天宝十载。而张先生却在《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一文中大胆质疑,认为此说“实为千年误读”[9]228。“臣生长陛下淳朴实之俗,行四十载矣”(《进〈三大礼赋〉表》)。张先生根据杜甫文章中关键的“行”字为立论的切入点,无论是在陶渊明的诗歌还是前代学者注解中,“行”理解为“行将”应无异议,杜甫献此文时年纪将近而未到40岁,即为39岁,也就是天宝九载。杜文中还提到,“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朝献太清宫赋》)。“孟陬”即正月,第二年正月的“大礼”即为天宝十载举行的祀太清宫、祀太庙、祀南郊三大典礼,因此若将三赋归于天宝十载,则与杜文中“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之言相悖。张先生不仅细致考证了天宝九载说的可靠性,而且对天宝十载献赋之说也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预献三赋之说并非臆测,杜甫《封西岳赋》就是未封预献之作,此即实例,且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泰山之时,提前一年就广为宣扬,因此杜甫能准确说出典礼的具体日程安排也就并不奇怪了,此文足见张先生心细如发。
张忠纲先生极注重对杜诗的训诂,这与他多年的《校注》编纂经历密不可分。训释杜诗全面详赡而内容精细,这是张先生校注杜诗最突出的特点。凡杜集版本解释有出入之处,张先生皆举其要,分析其观点是否合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予以论证。张先生考释名物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人物、地点、食物、器物等多方面。《题张氏隐居二首》中考证了“张氏”为何人,“石门”为何地,“杜酒”有何典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七有句“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对其中“生菜”一词,清代洪仲认为是韭黄的别名,而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杨伦《杜诗镜铨》都未细究其类属。张先生查阅药学著作《本草纲目》与谱录类书籍《广群芳谱》等专业资料后才下定结论:生菜是白苣的别名。仅此二字,注释长达百余字,读者能从详尽的注释中更加了解杜甫所处时代的生活面貌,从而更能接近真实的杜甫。张先生注诗所引书目也很广泛,不仅有各版本杜集,还有诗话、史书、韵书等资料,一条注释中常引多种不同书籍,可见张先生积累之丰厚。张先生常运用“以诗解诗”的方法释杜诗。如《游龙门奉先寺》“云卧衣裳冷”中“云卧”二字有作动词、名词两种争议,作者认为当以前解为佳,并举鲍照“云卧恣天行”(《代升天行》)句和孟浩然“云卧昼不起”(《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句为证,二句与杜诗结构相似,用法亦相似,“云卧”与上句“天阙”为借对法,这是以前人之诗释杜诗。以诗解诗还包括杜诗互释法,也就是不同杜诗之间的相互论证。《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诗,有“碣石小秋毫”句,“碣石”为山名,是杜甫青年时期漫游齐赵所到之地。张先生释该词时提到杜甫《昔游》诗“寒芜际碣石”句也提及此地,因而判断杜甫“盖追忆齐赵之游也”[8]55。将杜诗联系起来分析,往往能发现问题的不同侧面。
张先生的杜甫研究中还涉及杜诗的辑佚和辨伪工作。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千年来杜甫之诗被后世广为传颂,杜诗注本也层出不穷,《校注》共收录杜诗1450余首,杜甫自述40余岁时即写诗千首①,而今存杜甫43岁之前的诗歌不过百余篇,可见遗失之多。张先生力求搜集杜诗佚句,为后进学者提供研究素材。“黑暗通蛮货”一句,诸家杜集未曾著录,而《墨客挥犀》《冷斋夜话》《诸家老杜诗评》等13本诗话、笔记著作皆收评此句,张先生逐一列出书目供读者参考。为尽量恢复杜诗全貌,张先生对杜诗疑伪之作也进行了整理。《哭长孙侍御》诗有人认为是杜甫所作,一说为杜诵所作,作者对两种说法都进行了探源。《中兴间气集》《文苑英华》皆作杜诵诗,《宋本杜工部集》《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均认为此为杜甫之诗。而作者则从艺术风格上做出判断,引《读杜心解》之言,认为此诗“浅俗而平,不类少陵”[10],非杜甫之佚作。惜其无更多资料,无法更深入地展开观点的论证。张先生对杜诗的辑佚与辨伪成果相对比较零散,非其研究的重点。
(二)论杜诗文之特点
校注杜诗踵武前贤,辨伪存真。校注杜诗时张先生充分吸取了前人的治杜成果,对旧注积极地加以利用,不足之处予以补充。前注中若有与注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一般引用前人重要注本。为使其观点更有说服力,张先生很少使用孤证,一条注解之下常常列有五六种重要的前代杜注。《望岳》诗就对“岱宗夫如何”的“夫”字进行了详细的注解,“翁方纲曰:此一‘夫’字,实指岱宗言之。即下七句全在此一‘夫’字内。”[8]4仅一“夫”字,即引用李长祥、赵秉文、汪灏、翁方纲、徐仁甫五人注解,可见校注其详。若注者有不同于前贤之观点,也会在注解中详细说明。同篇诗作关于“望”字,历代注家的理解多有出入,有学者认为此诗所作之时杜甫已然凌岳而望,注者则赞同乔亿的说法,认为此诗“句句是望,不是登”[8]3。对于较为确定的讹误,《校注》通过考证直接指出旧注的错误之处。比如《登兖州城楼》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旧注多认为兖州就是汉代的东郡,校注者不以为然。“唐兖州,治所在瑕丘(今山东兖州)。瑕丘,汉属山阳郡。故唐之兖州,非汉之东郡明矣”[8]9,这就纠正了前人不加考辨产生的错讹。
善于从杜诗中挖掘深藏的情感意识。从情感内涵上来说,杜诗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杜诗中的情感具有普遍性,读者为忧国家兴亡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杜甫感动不已,又觉这位可敬的大诗人还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可爱之处,读到诗人倍感痛苦孤独时写下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又为之叹惋。杜诗中体现出的情感复杂而多变,张先生抓住了杜诗的这一特点加以探析,对于诗中名句的细致分析自不必言。张先生还以敏锐的感受力捕捉某些关键字眼里深藏着的杜甫的复杂情感。《月夜忆舍弟》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忆弟诗,首联“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并非此诗最为人称道的名句,张先生却以灵巧之笔分析了“雁”对杜甫传达浓烈思念的重要作用。“可能是因为漂泊流离的缘故,杜甫对雁声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战乱不止,雁鸣不止,客愁不止,杜甫简直把他的漂泊生活和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9]325。离群之雁,思念之哀声,不就是远离故土、思念家人的杜甫自身之象征吗?《旅夜书怀》一诗是一首感伤老年多病、漂泊无依的律诗,张先生在赏析此诗时重点分析了一组形容词和一组动词,认为“连用‘细’、‘微’、‘危’、‘独’四字,不仅准确地写出了旅夜独宿的情景,而且深细入微地传达出诗人孤寂悲凉的心情”,“‘垂’、‘阔’、‘涌’、‘流’四字力透纸背,表现了诗人处于逆境中的博大胸怀和兀傲不平的感情”[9]327-328。
四、张忠纲先生论杜诗学史
张忠纲先生对于杜诗学史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杜甫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诗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其人、其诗的研究千百年来浩如烟海,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足以证明自古至今学者对杜甫研究的重视。“对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研究者们开始希望进行一定规律性的讨论和归纳,是学术发展的必然。”[11]总的来说,张先生的杜诗学史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宏大广阔、高瞻远瞩的研究视野
张先生连续多年发表年度杜甫研究综述的相关论文,其研究站在杜诗学史的前沿对学界杜甫研究进行了回顾,体现了张先生对杜甫研究现状的关注。在年度杜甫研究述略中,张先生从杜甫思想性格、生平交游、诗歌艺术及杜诗学方面总结了新近出版的研杜著作与文章中的热门观点,分析了每年度的杜甫研究特色,并对未来的杜甫研究提出展望。《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略》一文对20世纪杜甫研究的著作进行了总体的关照,张先生将20世纪杜甫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以前。受到“民主”“科学”等西方文化思想的启发,学者努力将杜甫还原成为普通的诗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诗人来研究”[9]1131。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7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并力图以其观点重建新杜学,杜甫被冠以“人民诗人”的称号,萧涤非、傅庚生等学者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引起学界剧烈反响,杜甫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杜甫研究陷入了低谷,杜学备受冷落。第三阶段为1977年至今,“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杜学的中兴”[9]1140,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尤多,杜学综合研究兴起。学界围绕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涉及杜甫思想、生平、交游、杜诗艺术、杜诗学等多个方面。杜甫研究名家辈出,杜甫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最终得到确认。
对前贤学术研究客观公允的总结与评价也是杜诗学研究的重点。张先生写作了多篇论述前代学者杜甫研究的文章,总结了前辈学者杜甫研究的成果。这些文章的研究特点有二:一为概括准确且评价公允;二为注重弘扬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一文,介绍了萧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与研杜成果,总结了萧先生杜甫研究的重要观点并加以评述。对于时代给予萧先生的局限性,张先生毫不掩饰,但他同时提出,“如果完全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这种‘局限性’,甚至寻瑕索斑,求全责备,断章取义,任其发挥,那恐怕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9]1406。正是对前辈学人研究有清醒认识与客观评价,张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扬长避短,形成自身独有的研究特色。
(二)考据翔实、新见迭出的杜诗学史文献研究
张先生杜甫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引领杜诗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代表了这一时期杜诗学文献研究的最高成就。
张先生编写的《杜甫年谱简编》考证精细,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杜甫研究成果,而且逻辑缜密、语言简洁、颇多创见,对杜甫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宋代杜集“集注姓氏”考辨》一文长达8万多字,曾在《文史》连载,后先生又加以增补,收入《诗圣杜甫研究》书中。该文以《分类杜诗》所载的“集注姓氏”为底本,并以《分门集注》和《黄氏补注》所载为参考,共考证宋代杜集集注姓氏156家,是首次对“集注姓氏”的详确考辨。
2008年,张先生与他的学生赵睿才、綦维、孙微合著的《杜集叙录》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该书梳理了学术界杜诗学文献研究的发展状况,肯定了前贤诸作奠定的宝贵基础,亦指出旧著在新的视角下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更加完备的杜诗学文献目录。该书共收录杜集文献1260多种,分唐五代编、宋代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现当代编、国外编(亦按国家或地区及时代先后为序)共7编,邀请海内外最负盛名的专家进行撰写,保证了此书的学术质量。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张老师对现存杜诗学文献坚持亲见原书的原则,带领弟子苦心钩稽,辗转多地搜集资料,“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仅从前人的书目和著述出发,致使谬误流传,错讹辗转因袭之弊”[12]15。如《草堂》刊载的《关于〈重雕老杜诗史押韵〉》一文,该文作者自称“我因在湖南工作,曾有机会获观半日,愿举所知,以告同好”[13]。又云:“本书有题跋三处,为一人笔迹。书前题记署‘嘉靖岁在巳己(按:应为“己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复翁识’,下钤阴文‘黄丕烈印’,阳文‘荛圃’二方印”[13]。该文作者断定黄丕烈题跋为书贾伪造。因湖南图书馆所藏元刻本《重雕老杜诗史押韵》为海内孤本,亲睹者极少,而该文作者又曾亲见其书,据之成文,他人获观不易,故《杜集书目提要》照抄此文。而张先生在长沙开会时特意到湘图翻阅此书,三访湘图,始得如愿,才知书前题记署的是“嘉庆岁在己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复翁识”。之后张先生还进行了查核,明代嘉靖(1522-1566)共45年,无“己巳”年,而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正是“己巳”年。黄丕烈(1763-1825)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喜藏书,尤嗜宋本,精校勘之学。所以黄丕烈题跋与钤印是真的,而非书贾伪造。“一字之差,相差二百多年,又关乎真伪之别。”[12]15-16因此先生专门写了《是“嘉庆”,不是“嘉靖”》一文,纠正了“嘉靖”之误。《杜集叙录》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还补充修订了前作的重收、误收、书名、卷数、作者生平等讹误,在收录书目数量与收录书目时间跨度上都远超前作,成为新一代杜诗学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杜甫研究领域的纵深层次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杜甫诗话六种校注》亦是杜诗学文献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杜诗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自杜甫的诗歌价值被世人所识,后世诗话无不论及杜诗,然而专论老杜之诗话甚少,多零散而不成体系。现存最早专门论杜的诗话当属宋代方深道所编《诸家老杜诗评》,一般杜诗研究者所见,多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残三卷明抄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五卷清初抄本,鲜为人知,此前研究者无一提及。其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刘凤诰的《杜工部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与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都以杜诗为专论对象。张忠纲先生独具慧眼,将五种杜甫诗话整理成集,精心校注,后加入张先生编注的《新编渔洋杜诗话》,六种杜甫诗话集结为一册,定名为《杜甫诗话六种校注》(以下称为《诗话》)。“全书共辑录诸家诗话二百余条,其中六十余条,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或与他书引文有较大出入,这部分资料,弥足珍贵。《杜工部草堂诗话》,传世版本较多,但多系残本,《四库全书》所收《草堂诗话》,较通行各本多出三十余条,很少为人注意,一些研究杜诗的论著和文章,亦未提及,而所引有为他书所未载者。”[14]2杜诗注本如汗牛充栋,由于时代久远,古籍字句错讹尤多,张先生不辞辛劳,遍稽群籍,考其真伪,溯其源流,力求“无一字无来处”。如《诸家老杜诗评》卷三第145条所辑诗话,《诗话》考证“此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潘子真诗话》第37条引刘凤诰《杜工部诗话》云云,刘实照抄仇注”[14]64,这就厘清了不同诗话之间的渊源关系。再如《诸家老杜诗评》卷三《蔡约之〈西清诗话〉十六事》第122条所辑诗话云,“余常质之叔父文正”,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云,“当绦之时,蔡氏无谥文正者”[15]22,“宋代蔡氏谥文正者唯沈”[15]143,而蔡沈在时代及辈分上皆与蔡绦不相合,且蔡沈的谥号为明代才追谥,因此认定“文正”是叔父的字而非谥号。张先生查找史书等资料后认为,文正是蔡绦叔父蔡卞,而非蔡绦之谥号。《宋史·蔡卞传》:“卞,字元度……政和末,谒归上冢,道死,年六十。赠太傅,谥曰文正”[14]55,《宋会要辑稿》中也提到“蔡卞谥文正”,因此文正应是蔡卞而非蔡沈,这就纠正了前代学者的失考之处。《诗话》取材详赡,体例严密,校注精审,是张先生为杜甫研究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五、张忠纲先生杜甫研究的学术特点
(一)博观约取、言必有征的治学原则
张先生继承了冯沅君、萧涤非两位先生博观约取、精严审慎的学术传统,不轻易沿袭前人的观点,同时也谨慎地下结论。为寻找第一手文献,张先生常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览群书,探幽析微。其《读杜辨疑举例》一文,一些小标题之下虽只有短短数行,但张先生却需查阅数十种文献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在《渔洋论杜》一文中,张先生驳斥了王士禛不喜杜诗的偏见,在遍检王士禛和他人所引有关王士禛的言论后,发现王渔洋总体上对杜诗的评价很高,而批评杜甫的言论仅占十分之一,且有一些评价确为客观公允的。最后张先生才初步得出结论,“上述看法是片面的,是不符合渔洋论杜实际情况的;渔洋对杜甫是推崇的,肯定的”[14]554。
张先生还非常注重通过实地考察辨清杜诗有关的地名和典故。《校注》编纂期间,张先生与校注组其他同仁于1979年和1980年两次由山东开始沿杜甫漂泊之路去往各地进行考察,校注组共同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就是此次考察的成果之一,这些新见后来在《校注》的编写中体现出来。在注解《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时,关于“历下亭”的位置张先生提出了与旧注不同的见解,认为杜甫诗中的历下亭,并非今之历下亭。张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水经注》所载的“池上客亭”就是杜诗所说的历下亭,建于北魏时期,其位置在趵突泉北的五龙潭附近,而今天大明湖中的历下亭是清初所修建,与杜诗“海右此亭古”从时间和位置上都无法匹配。实地考证与文献梳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贯穿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生涯,为后进学者所效仿。
(二)知人论世、熟读精思的研究方法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张先生的杜甫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校注》采用的编年体例,这也是“知人论世”之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杜甫一生命途多舛,“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以诗人细腻之笔记录下国家的满目疮痍与百姓的苦难,史书所载的重要战争在其诗中都有反映,因此杜甫作品的艺术内涵是很复杂的。从杜甫的编年集中,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杜甫的真实生活与思想情感,从而反馈到杜诗的研究中。鲁迅曾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助于明白形式,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在此书的“凡例”中也谈到编年的原因:“以之编年,则可见诗人生平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盛衰,此本书所以取编年之体也。”[8]
张先生的文章当中也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诗圣杜甫研究》收录了多篇杜诗赏析文章,每一篇文章都仔细考证了诗歌写作时间、历史背景与杜甫的生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把握杜诗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孤舟一系故园心”——读〈秋兴八首〉其一》一文,张先生明确指出,“要知诗人‘所兴之何在’,须联系作者的经历和当时的形势才能探知其‘苦心’”[9]329。文章先介绍了杜甫客居夔州且病痛缠身、知交零落的经历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然后分句探析其诗歌艺术的高妙之处,进一步谈到诗歌中体现出的杜甫身世之叹的情感意味,由此更易使读者兴发感动,体会诗中所蕴藏的生命意识。
(三)实事求是、吐故纳新的治学路径
旧注因时代所限缺乏资料或思想的局限性而暴露出诸多问题,张先生充分吸取了近30年的最新资料以弥补前注的不足。比如杜甫曾作《赠韦左丞丈济》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献与韦济,旧注多谓二诗应作于天宝七载。然而据新出土的《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记载,韦济“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8]216。从出土资料来看,韦济在天宝九载至十一载之间任尚书左丞,而杜诗云“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可知是韦济任左丞的第一年,因此二诗作于天宝九载以后,应无异议。韦济之墓志铭1992年才出土,而实际上《校注》的第一、二卷已在此之前完成,张先生在统稿时注意将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已经完成的校注稿当中,重新修订了之前校注的讹误。在《校注》中诸如此类的修订不胜枚举,可见张先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
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是其研究领域成果最丰硕、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其研究涉及杜甫其人、杜甫诗文及杜诗学文献研究等多个方面,研究中心侧重于杜诗文的校注和杜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关于杜甫其人研究,张先生提倡摒弃人们赋予杜甫的称号,还原真实的杜甫形象。关于杜甫诗文研究,张先生在校注杜诗文时踵武前贤、辨伪存真,展现了一代学人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在杜诗学文献领域,张先生的研究具有宏高的研究视野及敏锐的洞察力。张忠纲先生的杜甫研究成果是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与杜甫研究的重要收获,贡献颇大,将为杜甫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很好的基础,影响深远。
注释:
① 杜甫《进雕赋表》:“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余篇”(《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