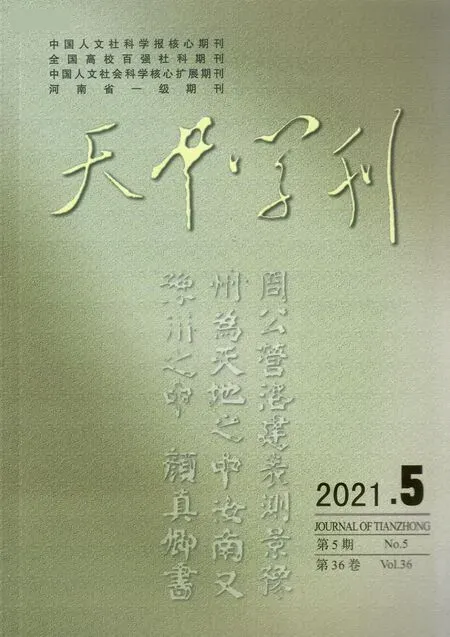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研究
2021-01-07吴振华
吴振华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晚唐大诗人、大骈文家李商隐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截至目前,从生平事迹考订,到作品整理校注和思想艺术成就探讨,学界已取得许多重大的甚至是带有总结性的成果,还在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以致陶文鹏先生在评估20世纪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时认为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超过了唐代所有的其他大诗人。而在众多的研究李商隐的学者中,我认为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成就最为突出。
刘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有近30年的时间一直花在李商隐诗文集的全面整理和研究上。他先后与余恕诚先生合著了《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1986年增订再版)、《李商隐》(中华书局1980年版)、《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台湾洪叶文化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中华书局2004年增订重排本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卷》(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增订注释全唐诗·李商隐诗注》、《新编全唐五代文·李商隐文校勘编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还独著出版了《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商隐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汇评本李商隐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全唐五代诗·李商隐诗集编校》、《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李商隐诗文集及校注评点本提要》,此外,还和王蒙先生共同主编了《李商隐研究论集(1949-1997)》(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总共15种之多,极为丰富浩博,可以说这系列著作,既是20世纪后20年由于拨乱反正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持续形成的“李商隐研究热”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李商隐研究形成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为李商隐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些著作本身又以里程碑的性质成为将来李商隐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刘先生曾谦逊地说:“李商隐诗文整理研究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肯定会有别的学人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刘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一、文献整理方面
刘学锴先生和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研究主要用力于李商隐诗文整理、资料汇编及理论研究两大领域。前者以《李商隐诗歌集解》和《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成就最为突出。五卷本《李商隐诗歌集解》(下文简称《集解》)包括会校、会注、会笺、会评,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此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第一,广搜旧本,进行全面比勘会校。著者共搜集了10种李商隐诗集的旧刻、旧抄,并在详细比勘的基础上将它们归纳为四个系统。在比勘基础上以毛氏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其他三个系统各本参校,并以唐宋元有关主要总集进行他校。择善而从,不主一本。明清以来诸家校改意见凡可参者也悉入校注,从而使《集解》的校勘真正具有会校性质。第二,对李商隐生平及诗歌系年的考证。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虽被称为清代集大成的善本,然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而严重。他发扬光大的肇始于吴乔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方式,以及用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参悟”之法进行李商隐生平游踪的考证,致使年谱中有关“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的考证及与两游有关的诗歌系年与笺解缺乏可靠证据,难以成立,并因此造成义山生平系诗考证方面的长期混乱。《集解》对有关两游的诗歌作了有力的辩证,对冯、张有关“两游”的系诗作了重新编年;此外,对商隐生平经历中“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王氏逝世的时间等,也都做出了新的考证结论。第三,《集解》在笺解每一首诗时,能较准确地把握住义山诗的艺术特征,区分义山诗中咏物、咏史及内涵虚括具有象征色彩的托物比兴诗歌的不同类型,避免考据家以史证诗的穿凿附会之弊。面对纷繁复杂的歧解,《集解》提出“融通众解,不废单解”的诗学观点,对这类诗歌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更加开阔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还诗中所抒之情以本来面目,极富启迪性和灵活性。第四,《集解》的汇评模式,按时代先后汇集了自宋迄今(少数篇章酌收当代)学者对李商隐每首诗的疏解笺证与评论品鉴。把这些材料连贯起来,几乎就是对商隐每一首诗的诠释史、研究史,不仅给理解、赏鉴、研究商隐诗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的材料和多角度思考的参照,而且对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接受史及诗学亦有重要启示意义。
《集解》(增订重排本)[1],中华书局2004年11月出版,是该书1988年第1版基础上的增订本,增加了246个页码,比原版新增14.2万字,字数达到134.1万字。原版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就被誉为古代作家专集整理的“扛鼎之作”,对近20年来李商隐研究热潮的形成及将李商隐诗歌研究推向深入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新版又汇集了近10多年来的许多新成果,在资料收集、生平考证、汇释笺解等方面更加精纯,堪称一部集会校、会注、会评、笺解大成的著作。新版与原版相比,主要变化有如下两点:一是诗歌篇目的编年做了一些调整;二是补充了许多新获得的资料。新版虽然不能说已将所有李商隐诗歌研究材料及最新成果网罗殆尽,但可以说比原版更成熟、更精纯,可读性更强。
五卷本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是迄今第一部李商隐文的编年本和全注本(以下简称《校注》),对存世李商隐文做了总结性的清理,在编排、校勘、辑补、考证、注释等方面展开全面系统的立体研究,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细加寻绎、甄别真伪、择善而从;又融汇了著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独到见解,堪称荟萃诸家之说、后出转精的集大成之作。
《校注》体例上颇具匠心。首先,合本集、补集与新辑佚文为一编,改传统的分体编次为按年编次。将352篇商隐文中可编年的作品逐一按年编次,少数难以编年之文(共17篇),则置于编年文之后。《校注》成为迄今最完善的存世李商隐文整理笺注本,编年的体例有利于学界展开对商隐文的分期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时代内涵、个性特征以及诗文创作之间的互动、渗透关系。其次,辑录诸家笺校注释、系年考证,并对其精心考索、细加按断。《校注》采取会校、会注、会笺的形式,先按时代前后顺序引录前人的考证、校笺成果,在鉴别其正误当否的基础上加以按断,或拓旧补阙,或辩证疵误,或提出新见。最后,书末设置附录,包括李商隐文佚篇篇名、分体目录、各本序跋凡例、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及存目文。
《校注》对校勘倾注了很大力量,著者广搜旧本,进行全面比勘会校,取得了超越前人的丰硕成果。既纠正了各旧本的讹误,如解决了李商隐文中存在的文与题脱节的矛盾问题,又改正了李商隐自己用错的讹误,如断定《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中的“壮室”为“强仕”之误。《校注》在李商隐文的编年与生平考证上用力颇勤,尤见功力。《校注》在对李商隐所有诗文进行深入探讨和透彻把握的基础上,对旧说详加考订,或肯定,或补苴,或纠正前人之说。另外,《校注》对李商隐移家关中的具体时间、王茂元出镇陈许及商隐入陈许幕的时间、商隐在居丧期间迁葬、安葬亲属的时间与过程、王茂元灵柩运抵洛阳安葬的年份及商隐两次祭文的写作时间、丧服满后入京的时间、大中元年随郑亚抵达桂林的时间等众多疑难问题都有精切的考证,对旧说有重要补正。
总之,《校注》对樊南文的系统整理,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新时期李商隐文研究的一大空白,为新世纪李商隐研究提供第一手信实可靠的资料,而且就文体学研究而论,对文学史上某些骈体文大家的文集进行校勘注释,可以改善骈体文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具有促进骈体文与其他文体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
李商隐的作品,历代不少学者文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断进行搜集、整理、注释、评论,使之得到流传,而且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历代的这些注释、评论、鉴赏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如果把它们汇集起来,可以看到自唐末以来直至近代人们对李商隐作品的整理研究与理解接受情况,以及透过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各个时期的文化背景、文艺思潮、审美情趣,同时又能提供除诗文全注本以外的较为丰富的李商隐研究史料。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先生合编的《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资料第一个重要价值是所收的内容全面而广泛,包括李商隐生平事迹的记述、李商隐佚诗及佚文、李商隐诗歌及骈文的评论、作品时代背景及本事的考证、文字典故的诠释。其中对李商隐诗的总评以及对作品的评释、鉴赏,为收集的重点。其次,这部资料收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如:纪昀的《玉溪生诗说》。更有在大陆仅存的孤本、抄本,甚至在大陆已经找不到的仅存于日本的一些著作。又如王鸣盛手批冯浩注本,仅北京图书馆有存。朱彝尊评点《李义山诗集》为黄永年先生收藏的过录本,也极为罕见。钱龙惕的《玉溪生诗集》在朱鹤龄之前,就把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前后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这些重要作品的内容发掘清楚了,证实了李商隐是当时诗人中唯一敢于义正词严地斥责宦官暴行的诗人,对正确评价李商隐非常重要,但这部书只朱鹤龄引用过一部分,全书在国内找不到了,是著者通过袁行霈先生,据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影印过来的。再有一本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雍正二年刊刻的杭州人徐德泓、陆鸣皋的《李义山诗疏》,简称徐陆合解。该书在大陆已经失传,但日本怀德堂文库(今归大阪大学图书馆管理)却藏有徐陆合解的《李义山诗疏》,此书亦被收入《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可见这部书汇集了不少有用且难得的资料。有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研究在文献方面就有了一套完整扎实的资料。这些都将大大推动李商隐研究的发展。
二、理论研究方面
刘学锴先生、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集解》《校注》所代表的是基础研究;在《集解》等著作基础上,进一步撰写论文、论著、评传等,可算作理论研究。他们在《集解》中给作品所加的笺释性的按语,虽然非常注意有关背景和本事方面的材料以及它与作品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又总是力避拘执穿凿,避免把本事、素材或某些人事因素与经过集中概括、提炼升华后的艺术作品混为一谈,因而主张辩证地、通达地看待其间的关系,以求从更高层次或更广阔角度给作品做出阐释。这是在遵循知人论世途径解读作品时,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追求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问题做出更为周全合理的认识,使注疏笺解这类可以称为实学的学术研究能够通之于辩证法。
刘学锴对李商隐诗歌的研究侧重论述其各种题材及体裁的主要特征、成就与贡献,同时亦侧重对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渊源与影响、阐释史与接受史等方面的论述。他在《李商隐诗选》修订本《前言》中,根据对李商隐最具有代表性的《锦瑟》、无题、咏物诸诗的分析,揭示了李商隐独创性的“以心象融铸物象”的抒情方式:“他的内心体验往往比他对外物的感受更为深入细腻。当心灵受到外界触动时,在心境中会出现一串串心象序列,发而为诗,则可能以心象融合眼前或来源于记忆与想象而得的物象,构成一种印象色彩很浓的艺术形象……他的诗集中固然有许多按传统方式写出来的佳作,但最具艺术创造性的,则应为着意追寻和表现自己心象的一类。这在古典诗歌形象序列中是一种新类型,对传统抒情手法有所突破。”[2]在对李商隐总体成就评价方面,刘学锴在《李商隐诗歌研究》引言中,承接清代吴乔提出的“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的论点,认为“李商隐所辟,则是人的心灵世界这一还未被前人深入表现过的领域。他的诗所特具的感伤情调、朦胧意境、象征暗示色彩,都和表现内心深隐幽微情绪相关”[3]1。他在《李商隐诗歌研究·本体篇·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与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一文中侧重于从诗歌所表现的内容着眼,认为抒写人生感慨是李诗的基本特征。它既纵贯其整个创作历程,又弥漫渗透于各种题材、体裁的诗歌中,并指出其诗歌所抒写的人生感慨,多为内涵虚括、广泛的情绪体验,如间阻、迟暮、孤寂、迷惘幻灭之慨等,故在表现手段上亦多借境(或物)象征,境界亦因此呈现朦胧模糊而多义的特征。这是从总体上探讨义山诗歌风格特征的有创见的重要观点,尤其从创作理论方面入手对象征手法及其诗多义性的解释具有启发性[3]50-65。
诗文交融影响研究方面,刘先生的《玉溪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论樊南文的诗情诗境》从诗对文的影响角度论证了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樊南四流与玉溪诗消息相通”观点,他通过考察“樊南文中的诗语”“樊南文中的诗情”“樊南文中的诗境”,认为从根本上说,皆源于商隐特有的“诗心”,这与义山对人生悲剧特有的关注和深刻体验相关,也是他独具的感伤气质与个性使然。刘先生最后指出:“中国古代骈文的发展与诗歌有密切关系。二者相互为用,是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现象。诗之骈化与骈之诗化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统观唐代,诗歌号称极盛,骈文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朝着越来越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很少出现具有诗情诗境的名文。直到李商隐,才以其特有的诗心诗才,在一部分骈文中恢复并发展了抒情化和诗化传统。由于李商隐骈文的诗化,是在经历了唐诗的高度繁荣,包括作为传统五七言诗诗艺的总结,在李商隐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诗化的程度较前更有所提高,艺术上也更加纯熟。这是李商隐对骈文发展的一种贡献。”[3]78
在溯源沿流研究方面,刘先生的《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通过细致比较李商隐与宋玉身世境遇、思想性格的相似点,分析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主题和悲秋伤春的意蕴,考察以“微辞托讽”的比兴手法“抒写艳情绮思”,既指出了李、宋二人的相似点,也辨明了两人的重要区别:“宋玉的哀愁感伤,主要是感慨个人境遇的困顿和由此引起的对昏暗政局的怨愤,内容比较单纯具体;而在李商隐的作品中,其哀愁感伤已在具体的经历遭际的基础上,扩展深化为一种包蕴着对整个现实人生的带有哲理性的思索与感喟,内涵更为虚泛抽象。”最后,在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之后,他总结说:“如果把宋玉、李商隐、曹雪芹作为三个阶段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感伤主义从主要是伤感个人境遇到整个人生,最后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感伤的大体轨迹。与此同时,则是其表现形式越来越虚泛抽象,带有人生哲理的意味和空泛悲凉的色彩,这大体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失意知识分子对现实感受的深化和由此引起的心态变化。”而对于这类作品,刘先生认为它们“大都以伤感、哀婉的形式肯定生活中的美,从而引起人们对它的珍惜流连,很少表现出对生活的阴暗绝望和厌弃逃避,相反地倒往往在缠绵悱恻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执着,因此能在感伤中给人以诗意的滋润”[3]80-93。
《李商隐诗歌研究·余论篇》的《分歧与融通》从创作起始阶段的触绪多端、百感交集,创作过程中在特定题材的歌咏中融入多方面的生活感受,创作完成后接受主体对同一作品的多侧面感受与认识这几个方面,论述了义山的意蕴虚泛之作何以有许多歧解和为什么能够将它们融通。认为“作者酿米成酒,由丰富的生活原料提纯升华为艺术真实、典型境界,解诗者自不宜再将蕴含丰富的典型境界指实为某一局部的生活依据。但每一种提供了局部生活依据的解说对把握典型境界的丰富蕴涵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214。这种“融通众解,不废单解”的诗学主张,是《集解》编排意图的最完美的体现,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余论篇》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李商隐现象》则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来审视李商隐研究中出现的“钟摆现象”“分歧现象”和“索隐现象”,认为:“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虽然是带有研究对象独特性的一种现象,但它又多少具有一定的共性。‘钟摆现象’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标准,或者说用政治、道德的评价代替艺术评价,就不仅存在于李商隐研究中,而是在一定时期中带有共同性的一种倾向;它所具有的两极摇摆的极端性,则应更值得注意,而加以避免。作品诠释中的分歧现象、索隐现象,也经常发生在其他一些著名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同样需要正确对待、科学分析。而引起这些现象的共同原因——对文学象征探讨之不足,则尤其值得治文学史者注意。”[3]226这种宏阔的文学史眼光正是刘先生能在李商隐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保证,也对我们后学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研究方法方面
(一)从文本细读走向理论概括
刘学锴先生的大学研究生阶段,是跟随北大的林庚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受林先生的熏陶,特别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感悟和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理论把握。例如刘先生在把握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时,先将义山诗中的感慨分为“命运感慨”“世情感慨”“情绪感慨”三种类型,其中“情绪感慨”又细分为“间阻之慨”“迟暮之慨”“孤寂之慨”“迷惘幻灭之慨”,而这四种感慨又分别落实到“隔”、衰飒迟暮色彩的意象、“梦”、“无端”等具体词语、诗句和意象的分析上。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从先秦到晚唐,诗歌中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大体上有两条并行的发展轨迹:一条是由主要感慨人生之短促到感慨人生之坎坷,再到感慨人生的悲剧命运以及人生的孤寂、间阻、迷惘、幻灭,呈现出由自然到社会再到内心的发展趋势,亦即由外向内、由表层到深层的过程;另一条则是人生感慨的内涵由具体逐渐走向虚括,表现手法由直抒转为象征。李商隐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正同时反映出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内涵虚括充满伤感情调,具有象征色彩和朦胧意境的抒写人生感慨之作,在古代史诗上是独特的存在,它相当全面地体现了李商隐诗歌的基本特征。”[3]65再如论述李商隐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时,刘先生也是在对义山诗所具有的五大词化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得出“在婉约词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五七言诗词化趋势的终结者,李商隐诗歌有着特殊重要的影响”这一论断的,并指出:“后代词家向前代诗人学习时,一般都是把他的整个创作作为对象,在涵咏体味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大可能像对待类书那样专门撷取其词藻字面。”而这种汲取或借鉴并不局限于那些词化特征,这样就自然引出更深一层的内在影响,即“在绮艳之中融入身世之感与时世之感”“融情的比兴寄托”“表现感伤情调和感伤美”“时空交错与跳跃的章法结构”等方面[3]103-111。其论述视野宏阔,论证细密,结论坚实,并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从刘先生的整个李商隐研究乃至其他研究来看,他都娴熟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从《李商隐诗歌集解》到《李商隐诗歌研究》,再到《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都是这一研究方法不断结出的硕果。这种方法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新一代学人总体上有一种浮泛空疏好标新立异的作风,因而提倡标举刘先生等这一代学者的这种脚踏实地稳健的治学方法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在文献整理爬梳中有精到发现
刘先生早年读研究生时就练就了很深的文献学功底,这也是他能深入研究李商隐的重要保证。他善于从文献的整理爬梳中有精到的发现,如对李商隐诗歌系年的考证。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虽被称为集大成的善本,然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而且严重。他发扬光大的肇于吴乔的索隐猜谜式的解诗之法,以及用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参悟”之法进行李商隐生平游踪的考证,致使年谱中有关“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的考证及与两游有关的诗歌系年与笺解缺乏可靠证据,难以成立,并因此造成义山生平系诗考证方面长期的混乱。为解决疑案,《集解》对与两游有关的诗篇均做了潜心的研究和有力的辨正。随后由于整理李商隐文集,又有了新的发现。李商隐在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这四五个月时间中,究竟存不存在冯浩、张采田所考证的“江乡之游”,刘先生先后发表过两篇考辨文章《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补正》(《文史》第40辑),主要是从李商隐与刘湘阴黄陵晤别的时间不在冯、张所说的会昌元年春,而是在大中二年春加以辨正。但对冯、张之说的辨正还有另一重要的方面,即考证李商隐在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这段时间的具体行踪,以证明商隐在此期间绝不可能作江乡之游。岑仲勉曾指出冯、张之说中商隐会昌元年正月与刘春雪黄陵晤别与代华州、陕虢草拟贺表在时间上的矛盾,但由于未结合商隐诗文详考这段时间商隐的具体行踪,故留下疑问。近年来,刘先生在撰著《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的过程中,结合每篇文章的系年考证与注释,接触、发现了一些有关的新材料。通过对商隐在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这段时间所撰文章的系年考证及与此相关的商隐行踪考证,证实了这四五个月中,李商隐先是于九月中旬东去济源移家,十月十日移家长安完毕,又应王茂元之召赴陈许幕,为其撰拟表状启牒多篇;约在十二月下旬,又离陈许幕之华州,并于会昌元年正月上中旬为华州、陕虢草贺表。因此,这四个月中,他绝不可能分身作“江乡之游”,自然也不可能在会昌元年正月与刘苜贲在湘阴黄陵晤别。接着刘先生还在详考与刘贲苜关系非常密切的裴夷直的仕官履历,对刘贲苜自柳州量移澧州的时间及刘苜贲前往江洲的目的、可能死于江洲等做了合理推断,使结论更加坚实。
刘先生这种数十年如一日苦苦钻求、寻根究底解决学术疑案的精神确实能给人深深的鼓舞和启迪,这本身也是李商隐研究的重要收获。他在《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4]一文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李商隐从大中五年(851年)冬到九年冬在东川节度使(治梓州)柳仲郢幕府长达5年的期间有没有回过长安?在细审李商隐诗文及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在这5年中,商隐曾回过长安,而且在诗文中留下了回京的足迹。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李商隐由于思乡念子情切,曾于大中七年仲冬由梓起程返京,约八年春抵京。在京期间,曾分别为张潜、薛杰逊代撰谢辟启、谢聘钱启共3首,又有《赠庾十二朱版》诗。约在大中八年仲春末或暮春初启程返梓,行前往访韩瞻,遇韩回朝,作《留赠畏之》。暮春末过金牛道,约是年夏抵梓。九月一日作《剑州重阳亭铭》。考出的这次归京之行,涉及对3篇文章和3首诗的正确系年,对旧说做了纠正。并进而认为:由于这次回京,释放了郁结已久的思念家乡和子女的情怀,回梓后,大中八、九两年所作的诗中,没有再出现先前那种强烈而频繁的思乡情绪,甚至连罢幕时和归京途中的诗里也没有出现思乡的诗句。这又从反面证明商隐在“三年已制思乡泪”之后确回过一次长安。文章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再如,他的《李商隐诗文集中一种典型的脱误现象——从〈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题与文的脱节谈起》[5]一文通过细审《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的内容,发现状题与状文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与矛盾,并发现状中叙及以举自代的周墀、崔龟从二人的历官与高元裕任京兆尹的时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挖掘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断定此状文当作于会昌六年三月至八月这段时间内。从这篇举人自代的状文看,状的原题可拟为《为京兆公举人自代状》,而讹为《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的原因,比较近理的解释是:李商隐自编的《樊南甲集》中,既有为京尹高元裕代撰的举人自代状,又有为京尹韦正贯代撰的举人自代状,由于编入文集时“以类相等色”,二状因体裁相同,性质相近,遂紧相连接。《文苑英华》在编书时,“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取入”(周必大《文苑英华》序),誊抄时因前后紧接相连的二首举人自代状,遂脱抄《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之正文与《为京兆公举人自代状》之文题,将前题与后文合而为一,成为前题不对后文的剪接品。因为冯浩等注家未能考证清楚,所以这篇拼接品的秘密1000多年来一直被掩盖起来。文章由此出发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有典型性,如果进一步据以考察李商隐诗集中的脱误,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在李商隐诗集中也多有存在,从而有助于我们解开不少题与诗相脱节的疑团。另外,还有他的《白描胜境话玉溪》[6]以接受史的新视角,通过对历代研究李商隐诗的主导看法的梳理,揭示出李诗具有藻丽之外的另一重要的白描特征,发前人所未发。这说明李商隐的白描型作品与特定的生活与感情内容、某些体裁的体性、特定时期的心境及诗艺的由绚返素的一般规律密切相关。最后文章探讨了以白描为主要特征的诗歌在义山创作中的意义及不被重视的原因,认为义山许多绮艳之作流传广远的关键在于其绮艳的外表下蕴含着绵邈的深情,这就是义山的“真色”,而其白描型诗内在本质同样也是这种真色,两类诗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如果说前者是以“借色”显“真色”,那么后者就是以朴素的白描直露本色,从更直接地显露义山诗本质的角度看,后者更有认识意义。两类不同特征的诗各有艺术表现的难度,也各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而义山这类诗不被重视的原因与历代被接受的情况密切相关:从晚唐的全盘否定到宋初西昆派的大力标榜,再到清代钱谦益等人的重新挖掘,都只关注或接受了李诗“沉博绝丽”的一面,而很少有人注意白描胜境的特征,虽然吴仰贤等人已发现了这一点,但没有得到主流接受的认同,因此白描胜境的诗歌没有作为一种重要类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说明某种长期积累加深的传统看法影响到对一个诗人的创作做出全面客观的认识与评价。因此,该文的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揭示出义山诗确实存在但从未被人认同的重要艺术特征,更在于为从新的视角全面审视古代诗人的创作以期得出全面完整的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宏观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案研究
当今学界,刘学锴与余恕诚两位先生的合作研究堪称典范,30多年的合作中,他们亲如兄弟,两个几乎始终并列在一起的名字具有范式意义。然而两人的研究方法却互有补充,各具特色。他们相同之处就是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都重视对文献的整理爬梳,然后走向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不同的是:余先生的唐诗研究总是以微观的个案为起点作宏观的文学史概括,而刘先生则相反,总是在宏观的文学背景下,在通观的基础上对个案作精细研究,细到“题无剩义”。像前举的几例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考察义山诗中的人生感慨,要联系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感伤主义传统,刘先生的贡献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揭示出李商隐为文学史提供的“新东西”。如《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7]就是先梳理李商隐以前咏物诗的发展,概括出“略貌取神、因物喻志的比体咏物诗(魏晋之前)”“图貌写物的赋体咏物诗(齐梁到初唐)”,指出到盛、中唐虽然咏物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只有到晚唐李商隐“借咏物寄慨个人身世境遇,寄寓人生感慨”“寄寓深微的精神意绪,表现某种感情境界”才做出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义山咏物诗的重大艺术贡献:从物与人的关系看,义山的托物寓怀是从先前二者比较简单的比附发展为注重整体神合的较高层次的象征;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义山托物寓怀诗的显著特征是离形取神,传神空际;从物与情或理的关系看,义山托物寓怀诗的显著特征是不涉理路,极富情韵。总之,无论是从感情的产生(触物起情)或感情的表达(多用有神无迹的象征)来看,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都更接近于“兴”体,而与传统的因物喻志的比体咏物诗、齐梁到初唐的赋体咏物诗有明显区别。从简单的比附到注重整体神合的高层次象征,从有形无神或略貌取神到离形入神,从有景(物)无情或理胜于情到深刻抒情,正是这种“兴”体咏物诗对古代咏物诗在艺术上的重大发展。再如对义山咏史诗的研究也运用的是同样的方法,还有像对义山七律、七绝的研究都是如此,此不赘述。
从总体上看,刘先生的整个李商隐研究从文献整理到《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也表现出“题无剩义”的特点,可以说他的李商隐研究是宏观背景观照下个案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义理考据辞章的完美结合
刘先生在《我与李商隐研究》一文末尾曾这样说:“义理、辞章、考据之学,虽各分途,但又相互为用,相互促进。我的主要力量,虽在义山诗文集的校注笺解与系年考证方面,但于理论研究、作品赏鉴方面,亦并未偏废。”[8]他在长期做诗文整理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写出了角度新颖有深度的论文,还写了近百篇鉴赏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融化到《李商隐诗歌集解》《汇评本李商隐诗》的总按和增订本《李商隐诗选》的注释与说明中。凡是读过《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诗歌研究》《李商隐传论》的人,都会深感先生文笔之美。例如,他在分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时说:“‘身无’与‘心有’相互映照,不仅写出心虽相通而身不能接的苦闷,而且写出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慰藉,将对立情感的相互渗透与交融表现得深刻细致而又主次分明。”[2]94用工整流丽的语言将义山对爱情的体验表达出来了。又如他对《夜雨寄北》的分析:“三四紧扣夜雨,从深重绵长的愁思中生出异想、转出新境,遥想他日重逢,在重逢的欢愉中回首凄清的往事,不但使重逢显得珍贵而富于诗意,而且那遥想中的重逢本身也多少给眼前凄冷的雨夜带来一丝温暖,给寂寞的心灵带来一点慰藉。”[2]214简直就是一段恰到好处诠释诗情诗境的美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酷爱先生之文,每每总感到像在品味山泉烹煮的绿茶,心头是情思荡漾,隽词妙语,珠圆玉润,没有一点艰涩,只有无限的畅快。将学术论文写成美文,这也是刘先生的李商隐研究能取得重大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