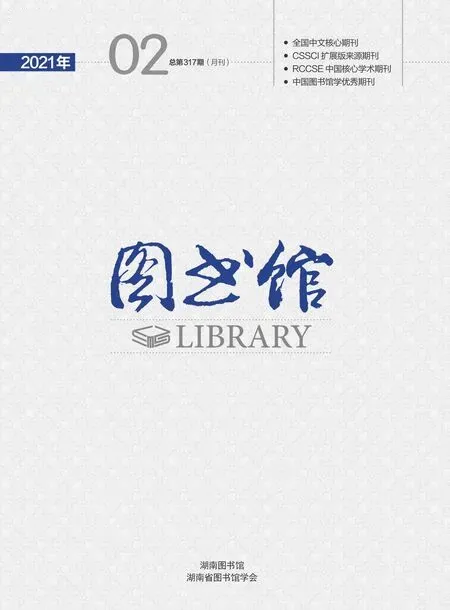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的优质IP培育研究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2021-01-06张立朝
张立朝
(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自2016年《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6号,以下简称《意见》)实施以来,包括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在内的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纷纷采取措施,依托所藏文化资源,着力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拉开了国内文化文物单位以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激活藏品、活化经典的序幕。
经过几年的发展,文化创意产品已经成为诸多文化文物单位的一张靓丽名片,尤以故宫为甚,已经从围绕藏品开发产品为主的文创1.0时代迈入同市场力量一起挖掘、生产和运营传统文化的文创2.0时代,从单纯围绕藏品讲故事,到以藏品、建筑承载的传统文化为核心,构建起以创意产品、教育培训、数字展览、研学旅游、艺术授权互为表里的大文创体系,孕育出故宫文化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超级IP。目前,我国图书馆界的文创开发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在此,笔者结合国家图书馆在相关领域的探索,从优质IP培育的角度谈谈对公共图书馆文创开发的一些启示。
1 IP的定义及特点
1.1 IP的定义
IP的英文全称为“Intellectual Property”,其原意为“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也称为智力成果权[1]。根据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2]。该表述于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以后被广泛使用。目前关于IP的热议普遍存在于影视剧、游戏、漫画等泛娱乐领域。国内文化文物单位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及各级政府建立的公共文化设施,其基于政府背景的社会公信力、海量的文献信息资源、珍贵的古籍藏品、品牌化的社会教育资源等,都可以纳入IP范畴。
1.2 公共图书馆IP的特点
一般来说,IP作为一种专属标签明显的无形财产,具有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特点[3]。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文创IP还具有以下特点:
1.2.1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文化创意产品亦可称为文化创意衍生品,在文化IP消费的链条中处于末端及周边,一款成功的文化创意产品一定是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即内容是其衍生推广并产生市场价值的核心。同影视、艺术、游戏周边消费一样,文化创意产品是公众因对经典影视、知名艺术作品、优秀游戏项目的钟爱而“爱屋及乌”,引发的对承载了影视、艺术作品、游戏等内容的周边产品的喜爱与消费。在美国,“超级碗”的每次举办,都能带来大洋彼岸的狂欢。作为美国第一运动,美式橄榄球崇尚力量、速度与精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与“团队协作”精神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当代美国人的价值观[4]。故宫成为热门旅游地,故宫文创产品广受好评,同样是故宫古代宫廷文化在新时期所焕发出的魅力的体现。
可以说,IP的核心要素并不仅仅体现在美丽的形象、好听的故事,也不是单纯的功能性的满足,更多的是让消费者从内心认同或欣赏的文化与价值观,是精神和价值层面的认同。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是最大的典籍文献收藏与利用的场所,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5]。承载民族记忆和民族思想,讲述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仁爱和谐、家国天下的典籍文献就是公共图书馆潜在的优质IP 。基于此衍生出的文化创意产品是图书馆藏品与文化在文化服务载体、传播渠道上的衍生与延伸,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所表达的核心价值也一定是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
1.2.2 高质量的受众群体及强大的流量优势
优质IP的一大特点就是自带流量。海量级的粉丝及潜在受众群体,构成了IP文创衍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以故宫为例,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广告文”,几乎每篇都能获得“10万+”以上的阅读量,《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纪录片在豆瓣的评分更达到8.8分以上,可见其优质IP的强大用户流量,以及其用户的活跃度。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以其海量的文化资源及免费开放的服务形式每年要接待数以亿计的读者。以国家图书馆为例,每年接待读者数量达到550万人次以上。国家图书馆牵头组建的“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目前已吸纳了包括省级、副省级、地市级在内的116家公共图书馆加盟,年接待读者数量更达1.5亿人次,这个数量级的流量使得培育图书馆优质IP成为可能,也为此激活了图书馆文创的大量潜在消费群体。公共图书馆的受众群体主要集中于学生、学者等知识诉求群体,相较于博物馆等受众,其年龄阶层更宽泛,忠诚度及综合素质较高,文化消费或知识消费欲望更强烈,消费质量也相对较高。如果能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充分挖掘此类用户的消费潜力,则有助于满足其个性化精神消费需求,进而丰富图书馆的服务内涵,培育新时期图书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多种服务业态。
1.2.3 巨大且可持续的挖掘空间
优质IP的开发与培育并非一蹴而就,其收割期同样也非“仅此一次”。真正的优质IP会紧随时代步伐,围绕其核心价值观,持续进行内容再生产,叠加式获取用户与经济及社会效益。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曾中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字,且有“易代修史”和盛世修典的优良传统[6]。图书馆作为典籍文献的重要收藏单位,可以说其承载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以国家图书馆为例,作为国家总书库,继承了自南宋以来历代皇家藏书以及明清以来众多名家私藏,最早的馆藏可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珍品特藏包含敦煌遗书、西域文献、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古代舆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稿等330余万册(件)。截至2019年底,国家图书馆文献总量达4000多万册(件),数字资源总量超过2000TB。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曾说过:“典籍之美,表现在典籍内容的思想深邃、文辞优美、叙事生动和批判犀利上,也表现在典籍形式的手泽如新、写刻精美、墨乌纸玉、装帧典雅上,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7]由此可见,图书馆藏品包罗万象,撷精取粹,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图书馆如果能据此结合新时期公众的文化需求特点、社会热点等,提炼开发出针对不同服务对象的内容产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与科技、旅游等行业开展不同形式的跨界合作,推动“文化+科技、非遗、影视、游戏、旅游”的深度融合,必能衍生出众多受众面广、深受年轻世代追捧、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新型文化创意产品,培育图书馆用户黏性,不断强化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作用。
2 图书馆优质IP的培育
优质IP既要保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很高的品味调性,又要保持自身的新鲜感,不断拓展新形象,讲述新故事,时刻洞察和把握粉丝社群的需求,吊足消费者的胃口。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提到:“IP存在的理由是内容的持续经营,每一个差异化具象的动作都是真实的内容建设。反差越大,越能成就IP的独一无二。”[4]笔者认为,IP运营的1.0版本是产品内容的不断延伸、迭代;2.0版本是品牌的跨界出击,进而生成新的IP内容;3.0版本是“润物细无声”,成为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是IP融入生产、生活的至高境界。
2.1 核心价值观的准确提炼与不断衍生
优质IP具有独特的、内涵丰富的、可人格化的价值观,能够形成很高的辨识度和身份认同,并且具有针对特定人群的独特吸引力。《西游记》从经典文本到反复解构、恶搞和创作,衍生出大量类似《大话西游》《大圣归来》的全新IP,历久弥新,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是孙悟空机智勇敢、忠诚执着,敢于战天斗地的可贵人格;国产电影《流浪地球》的广受欢迎,同样是因为其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
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要立足职能、藏品、业务特点,呼应新时期公众文化需求,创新服务方式,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培育独特IP。
2.1.1 立足职能,引领阅读
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到“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求知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图书馆作为城市文明的象征,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立馆之本,以“推广阅读”为己任。“阅读”既为文明社会的共识,自带势能,又能引导正能量及塑造核心价值观。可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潜在超级IP。近年来相继出现的知乎、得到、喜马拉雅、樊登读书会等阅读类平台都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打造出了“阅读”IP。例如,中国知名的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以“用声音分享人类智慧”为使命,首创PUGC内容生态,不仅引领着音频行业的创新,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文化和自媒体人投身音频内容创业,其中包括高晓松、马东、吴晓波、蔡康永、李开复等8000多位有声自媒体大咖和500万有声主播,吸引了超过4.7亿手机用户,以及超过3000万的汽车、智能硬件和智能家居用户,占据了国内音频行业73%的市场份额,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大IP[8]。
现代社会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工作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公众在信息化、网络化、碎片化阅读的大环境下很难获取更高质量的信息。图书馆作为政府主导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有职责、有资源、更有高度,更应以建设知识型社会、培育文化自信为使命,以服务读者为核心,分群体、分主题提供高质量的阅读产品,打造阅读高地,引领阅读风尚。以国家图书馆为例,作为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以推广“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为题,整合其辐射的专家、读者、文献信息等资源,推送高质量的、极具权威性与指导性的“阅读书单”,增强图书馆导读公信力与领导力,持续打造多样化、个性化的周边产品,服务图书馆知识消费群体,引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与此同时,可结合公众休闲性、体验性文化消费的特点,开发集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品。2018年国家图书馆开发的“翰墨书香书法套装”,便是集非遗技艺、知名馆藏碑帖、专家讲解、人工智能体验方式等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品,一经推出,广受好评,总销量超过2万余套。
2.1.2 围绕馆藏,生生不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文献收藏利用单位,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所藏典籍文献记载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方方面面,历久弥新。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要围绕这些经典文献,提炼其核心价值,与当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以文化创意产品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公众对美、对经典的再认知,进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9]。以国家图书馆近两年开发的两个IP为例,围绕馆藏《庆赏昇平》这一清代京剧脸谱典籍,国家图书馆的文创设计师对其中家喻户晓的公主、状元、孙悟空、哪吒、门神等人物形象进行卡通化设计,并将其形象应用于交通卡、T恤、书签、年礼等产品上,借助公众对被赋予美好寓意、自带流量的几位戏曲人物的喜爱,延伸至对京剧知识的推广,以交互式的“文化营销”方式拓展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被誉为“中古时期的大百科全书”。国家图书馆于2018年策划举办了“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并依托展览开发了“贵人不忘事”等20余种主题文创产品,涵盖丝巾、领带、装饰画等家居生活用品。例如,通过对《永乐大典》内收录的珊瑚枝万字纹、子母龟万字纹等多款万字纹进行重构设计,配以《永乐大典》的柠黄、砖红两种主题色,设计出一款形式别致而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丝巾,并通过“卖出去”的方式让公众“把图书馆带回家”,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
2.2 流量级客户的精确培育
超级IP的诞生,除了丰富、可人格化的内涵与价值观,还需要细化应用场景、个性化的流量培育,尤其是以人为中心的渠道或口碑,亦即培育人的参与感、仪式感、卷入感和温度感。在万物互联的新应用场景下,消费者买单的不仅是一个饮水的杯子,更多的是饮水功能之外所承载的文化或信息所带来的快乐情感溢价,说到底其实就是人的精神与价值方面的消费需求,这也是目前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消费的原因所在。
当今时代,“人”不缺乏物质,缺的是温度,亦即情感的交流。基于文化土壤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也不应是冷冰冰的,而应是有血有肉、具有人格魅力的。2007年,由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创作的大黄鸭火遍全世界。2013年进驻北京园博园、颐和园后,通过销售衍生产品等在两个月时间内创造了超过两亿元的收入。究其原因,就是霍夫曼设计出的大黄鸭在保持简单外形的基础上,通过游历全球的方式,以其质朴、简单的举动触动了观众内心最脆弱的一环,让所有观众都能够从中找到童年的美好记忆,而这种“记忆”是没有任何国界之分,不带任何政治、种族色彩的。
反观图书馆,新时期公众对图书馆的诉求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阅读场所,求知之余,更是连接读者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其可以是老年人回忆青春求知时光的场所,还可以是年轻人诗意恋爱、职场人士静思的场所,更可以是家庭情感互动交流的场所。在此,我们可以从罗振宇创立“罗辑思维”的初衷得到一些启发,“罗辑思维”以“卖书”为目的,但其在具体运营思路上不再局限于“营销手段”的丰富性上,而是在于用户的精准推送与培育上。挖掘每本书的闪光点、独特的解读角度,以及连接用户、与用户互动的社群能力,成为其成功的关键所在[10]。确切地说,“罗辑思维”一方面找到了“对的用户”,另一方面契合了用户“对的需求”,从而实现了用户“注意力”的成功变现。
基于此,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消费群体的培育就要在清晰的图书馆“目标族群”的基础上,高质量满足其个性化、不断叠加的情感诉求。一方面要强化交流与认同,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不同的交互内容与方式,通过策划典籍类展览、建设数字图书馆体验中心、引入咖啡厅等多业态服务方式,为“阅读”打造舒适的软、硬情境。国家图书馆2017年与中信出版集团合作举办“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展出了25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的近300幅作品,并衍生出近百种文化创意产品。观众置身其中,通过浏览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大师名作、与童年最爱合影、往来展品间寻找印章手迹、现场临摹一幅电子名作等方式,各自找寻童心与乐趣。与此同时,开发出的近百种文化创意产品成为观展者情感延续的最后落脚点,造就了一场文化消费盛宴,90天内文创收入达近千万;另一方面,新时期图书馆要根据公众的不同需求,强化馆藏资源尤其是稀缺性资源的开发着力点,持续提供针对不同人群的有价值的内容,促进图书馆忠实用户数量不断裂变,培育用户黏性,形成流量级用户,并最终依托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文化创意产品实现流量变现。如2018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将诗书礼乐完美结合,为公众系统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恒久魅力,勾起人们对学生时期读过的经典名篇的无限回味。结合其“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国家图书馆在随后的两年内与中国邮政集团等开展跨界合作,陆续推出“从诗经到红楼梦”多媒体邮册、汲古通今主题套装、《传习录》主题学习用品、诗书礼乐音乐会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服务),涵养了一大批经常光顾国家图书馆文创空间的忠实用户,并持续生成市场红利。
2.3 优秀IP的无限跨界
优质IP具有良好的延展性,能够快速连接、快速造势、有效承接与转化,理论上其价值可无限延伸。跨界是IP延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跨界”,意指不同领域、行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范畴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事物,使得原有的几个范畴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态势。IP跨界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成功引发了社群共振,同时突破了不同社群间的壁垒,最终依托裂变传播的强大扩散力,使跨界形成巨大效应[11]。笔者认为,图书馆IP的跨界可以分为文化产业内的跨界和非文化产业内的跨界两种。
2.3.1 文化产业内的跨界融合
优秀IP在文化产业内的跨界融合指IP与文化及相关技术如非遗技艺、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与融合。传统的图书馆IP以内容见长,一方面因其内容无所不包,很难提炼出身份特征明显、易受公众追捧的话题,加上解读功力上的缺乏、现代人获取信息途径的多样化,在IP的培育及传播上有很大难度;另一方面,又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可挖掘性,使其在跨界合作上有着很好的延展力。如果能够精准把握图书馆的藏品特点,并与非遗技艺、旅游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等很好地进行融合,就能够博采众长,打造出颜值与气质兼具的文化创意产品,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开设以来,与众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在2017年举办的“器用为尚——中国古代文房文化展”上,国家图书馆结合传统文房概念,打造出面向中小学生的、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参与研制、阿里巴巴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翰墨书香人工智能书法文具盒”,产品套装内既有基于国家级非遗技艺打造的笔、墨、纸、砚、水滴等文房用品,也有从馆藏《千字文》等碑帖中集出的108个书法字体所组成的习字帖。帖中四字为一组,由知名书法家对其进行书写要领的解读、书写示范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公众只要下载“天猫精灵”App,用“扫一扫”功能扫描每个书法字体,就会有相关的视频解读。该产品因为集结了国家图书馆重要书法藏品、国家级非遗技艺、知名书法家讲解等众多文化资源,极具趣味性、知识性与互动性,一经问世便迅速成为国家图书馆文创的代表性产品。首批产品推出后,国家图书馆更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联手对产品内容进行了深度加工,并与中小学生的校本课程进行了深度结合,精准实现进入市场。
2.3.2 非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
IP在非文化产业中的跨界融合,表现为以其创意性、知识性、艺术性等,从文化供给侧角度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文化艺术性,提高其附加值。
与非文化产业的融合,一方面,可以图书馆的宏富馆藏为基础,培育能为相关产业赋能的经典IP,丰富产品内涵。国家图书馆自2017年以来,以国家图书馆藏金石拓片、善本古籍、名家手稿等珍贵典籍为基础,开发出手机壳、充电宝、丝巾、T恤、笔记本等涵盖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等多个主题的文化创意产品近300种。这些产品相较于同等功能的普通商品,在保证其功能满足的基础上,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故事与文化情感,在与消费者形成购买关系的同时,附带了文化与情感的交流碰撞,使其成为一件有文化、有温度、有体感的商品。例如国家图书馆开发的“贵人”充电宝,产品外观出自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永乐大典》中的“贵人”页,在提升产品美观度的同时,也形象诠释了“手机遇充电宝即遇贵人”,无形中提升了产品的趣味性。
另一方面,借助“阅读”“信息中心”职能,图书馆既可通过建立智慧图书馆,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构筑面向市民的泛在知识服务,使信息、技术、创意可以在部门间和市民间进行跨时空和跨界的传递、互换和互动,打造更智慧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12];也可以充分借鉴现有部分特色书店、酒店等的做法。如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书香陪伴、比邻而居的图书室或阅读空间成为诸如地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风景名胜等竞相引入的功能。日本茑屋书店不仅是一个特色书店,更是一个致力于为公众提供生活解决方案、提升生活品质的服务商,让公众能够在场景化、多样性、复合型的阅读空间获取那种触手可及的精神快感[13];汉庭酒店推出“书香汉庭”项目,就是借助一种全新的酒店生活方式,改善入住客人的人文环境,满足客人追求高雅生活的现实需求;亚朵酒店的“竹居”是一座全国连锁的共享图书馆,其与上海三联书店合作,打造“流动的图书馆”,让人们在旅途中可随时借阅,随处归还,形成一种“阅读之旅”的独特体验,由此培育出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14];位于诸多商圈核心位置的诚品、言几又、钟书阁、西西弗等特色书店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商场的文化、文艺气息,成为吸引年轻人驻足的重要方式。
3 结语
公共图书馆优质文创IP的培育,需要紧紧围绕其职能、宗旨、藏品,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以精准化满足公众所需为出发点,大胆创新服务方式,精耕细作,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深入融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