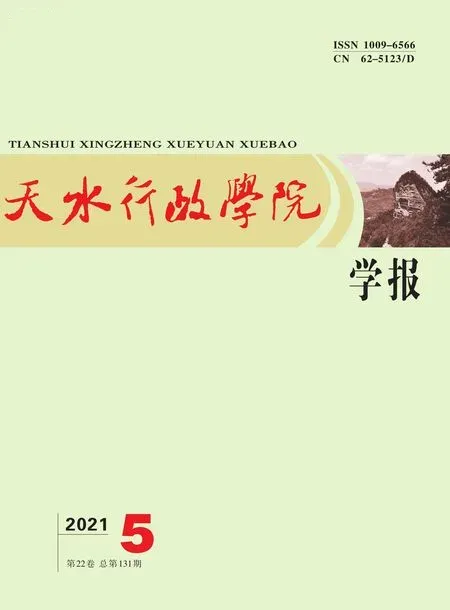从乡贤到新乡贤:身份与特质的转变
2021-01-06粟霞
粟 霞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广东 佛山528300)
华夏文明发源并依赖于农耕,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春秋时期,管仲按照为社会贡献大小,排列出“士农工商”的顺序,到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首倡“重农抑商”,而后其成为整个帝制中国时期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农业成为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卓越成绩;另一方面,“三农”问题依然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面临的最大难题。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党的十九大上,更是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乡村振兴,无疑需要建基于对乡村本有特质与资源的真切把握。为此,本文将聚焦于传统乡贤及新乡贤,借助对二者身份、特质及其转型的剖析,以期管窥传统与现代乡村社会的大致生态,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提供历史与现实的参照。
一、张力与博弈:从绅士到乡绅的利益转向
无论农业、农村和农民,还是乡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中都由来已久。学界部分学者对于乡贤的界定,往往将之与乡绅打包一并,并默认其与官僚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这种大而化之的解读,却不一定符合事实。概括来讲,帝制时代的乡贤只是作为乡绅的正面代表,乡绅则是与城镇等地的绅士共同构成一般化的绅士集团。因此,想要澄清乡贤之定位与特性,必然借由从绅士到乡绅再到乡贤的诠释路径。其中绅士集团无疑与官僚集团密切相关,而乡绅集团则可能更多代表地方利益,甚至与官僚统治产生对立。
传统绅士集团作为亦官亦绅的存在,生成根源乃在于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帝制中国,虽然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但因幅员辽阔,帝王又分身乏术,使其在不分享政权的同时,也不得不从社会上寻觅可能的助手,即通过官僚集团的构建,尽可能推行自身意志。
与之相应,民间社会的家族为了维护或扩大自身既得利益,一方面,不得不去接近皇权,成为体制内的官僚;另一方面,又因为担忧皇权的过度集中,而不能不想法对之进行软禁,并期待着能够早日衣锦还乡。正是由此,帝制时代的官僚与绅士往往是作为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对此,费孝通先生在《论绅士》一文曾描述如下:
传统社会里的大家族就是这种团体。全族人合力供给一个人去上学,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都靠福了。在朝廷里没有人,在乡间想保持财产是困难的。……
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归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满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便有了安全,面团团,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他们在农业经济中是不必体力劳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可以说是不劳而获的人——这种人就是所谓的绅士。绅士就是退任的官僚或官僚的亲亲戚戚[1]。
相较于绅士,乡绅的身份与特质无疑重在一个“乡”字,即利益共同体及行为规范上的地域性色彩。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三农”一方面关涉社稷之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动乱之源,因此国家在面对和解决“三农”问题时,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一面:既需要在生产和劳动力上尽力维系广大农村持续而稳定的输出,又需要在智识和思想上努力调控广大农民安贫且守礼的取向。
但是,幅员辽阔、交通与信息传递的相对落后、帝制行政效率的相对低下等原因,使得乡村的有效输出与管控,难免存在一定的真空地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帝制统治和乡村秩序被迫分成两节。如何使这二者之间能够有效的沟通与联接,自然也就成为整个帝制中国时期核心议题。乡绅的存在和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凸显出来的:既成为官方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的有效延伸,也作为民间利益共同体的代表,对抗着帝国触角的长驱直入与过度盘剥,并最终在此维系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间之间的微妙平衡。
乡绅作为绅士的一种,在绝大多数状况下符合费氏所述之绅士特征:既需要借助官僚途径来亲近皇权,以维系自身的利益,又必须钳制和逃避皇权,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因此,往往自身兼具官僚的身份,或者至少拥有官僚的庇护。但是在少部分时候,乡绅也可能成为官僚体系自身的对立面,即为了维护自身或家族在地方的利益,而与代表皇权意志的官僚进行博弈。兼具官僚身份的绅士,往往因为任官回避制度,不得在原籍任职,以致官僚的身份与职责显得更为突出。与之相对,乡绅之为乡绅,则主要是指居住于本地的权势控制者,又或者“衣锦还乡”的官僚,以致绅士的诉求,而非官僚身份成为首要特征。
二、德性与经验:传统乡贤的核心特质
如果说帝制之下的乡绅,更多代表的是民间实际的利益统治集团,那么乡贤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正面形象,即不仅需要实际掌控着乡村的权力网络、教化资格或经济资源等,更重要特质还在于“一定是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2]。对此,可以从传统文化对于“贤人”的诠释中看出。
孟子认为,殷商之所以在纣王之时没有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有微子、比干等一众贤人的辅佐[3]。在历史记载中,这些贤人的特质则又集中体现在德性纯美、天下为公两大维度。荀子则在《哀公篇》中记录了孔子对于社会人的五重划分——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其中,“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4]可见,在荀子眼中的贤人,需要具备三大具体要素:一者,行为符合规范;二者,言论能令百姓听从和效法;三者,不聚不义之财,且能主动布施百姓。
将儒家贤人的标准放置到乡贤身上,后者在能力和影响力上可能不及前者,但精神特质却是相近的,即实现“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不仅需要洁身自好、品行高洁,做乡邻的道德标杆,而且必须要造福一方、惠及民众,主动分享自我财富以提供公共物品,获得乡邻的认可。如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讲,乡贤便是乡党中的“达者”,应以“兼济乡党”为志。反之,若只是实际控制地方资源,但却只将权势用于谋私,而罔顾公共利益和百姓安宁,则只能成为乡党之中的“劣绅”,而不可能被定义为“乡贤”。
除了德性与为公的特性,乡贤之所以成为乡贤,往往还有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被官方予以确认的要求。一方面,无论是德性还是行为的规范,都不可能是一家之言,虽具有地方特色,但终究不免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另一方面,乡贤作为乡绅的一员,虽然主要代表地方,却也必须实现与官府的协调,否则必然被当作反对力量遭到压制。汉高祖刘邦最初在设置“乡三老”(即“乡贤”称呼的前身)时,便已然提出能“帅众为善”,并“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的要求,同时也明确赋予相应的取消兵役、赏赐酒肉等优惠待遇:“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5]这无疑揭示了乡贤身份与官方教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汉高祖对于乡贤的选拔标准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也即其年龄必在“五十以上”。要知道在孔子的自我陈述中,三十便达成“而立”,五十岁则实现了“知天命”;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中,五十岁则是应该开始受到别样的待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也即可以穿上丝绵袄了[6]。换句话说,在传统社会,五十岁相当于是暮年之际,何以反倒可以被高祖视作能引导一方的贤人呢?对此一问题的解答,也就涉及到传统对于“齿”的尊奉及其背后生存模式的话题。
《礼记·祭义》曾分析过上古之世对于年齿的尊重,并将之与孝悌联系在一起,认为尊老的规范,若是能推行到社会的各大领域,便能有助于社会风尚及道义的塑造: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弟达乎州巷矣[7]。
孟子也认为年龄可与德性、爵位相比配,共同作为天下三大需要尊重和遵循的对象。不同的是,孟子将对年龄的尊重主要放置在乡党范围来对待:“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8]
毫无疑问,“尚齿”是传统社会极为重要的规范。然而,只是简单从孝悌、敬爱等层面来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似乎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毕竟,从今日之社会来看,尊老爱幼作为社会规范,虽然可以扩大生命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但终究也只是与其他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相并列的道德条目,而不足以将之提升成超越其他条目的最高准则。更何况,在儒家爱有差等、亲属有别的大原则下,对“陌生人”的友善本来就遭到一定程度的遮蔽。对此,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的“礼制秩序”及“长老统治”的相关解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解读视角。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9]。
从费先生的解读可知,传统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因为农耕文明的限制,人们必须依赖于固着于特定地域的土地,同时也面对相近的生产与生活经历。由此,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阅历、知识和地位,“好古”和“尊老”自然也就不只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是能够产生实际好处的经验。俗语所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正可作为“尚齿”之实际需要的最佳注脚来审视。有鉴于此,刘邦要求“乡三老”之人选,必须满足五十岁的年龄标准,也就变得易于理解了。这本身也预示着,乡贤身份的又一种特质——经验。
综上,传统社会的乡贤作为乡绅之中的正面形象,一方面,是根源于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博弈,以致呈现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但归根结底,乡绅与乡贤,首先是作为乡村社会及其资源的代表而出现,并在此基础上与官方发生着各种关联或平衡;另一方面,乡贤核心的道德品质在于不仅能“独善其身”,即贯彻儒家修养工夫,更需要“兼济乡党”,即能持守公心、服务乡邻,尤其体现于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再一方面,鉴于乡土社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特点,成为乡贤往往还需要年龄和阅历的资格,这不仅是道德上“尊老爱幼”的需要,更反映出乡间的知识和能力,主要是经验的,而非创新的。
三、解体与重构: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的定位
近代中国迫于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开始了救亡和启蒙相纠葛的现代化路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及其内生性的乡贤群体,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外来商品的侵入、持续不断战争及赔款,使得农村手工业难以为继,农产品及劳动力等资源被强制征用,乡绅集团也因此逐步往城镇迁移。
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外局势影响,不得已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农村资源向工业和城镇的被动输出局面,依旧无法得到扭转;革命塑造的平等人格,则使传统乡贤既有的“官方色彩”遭到解构,乡村资源及其权力逐步回收到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则更是导致乡村资源的外流、乡村传统价值的解体。
综上,在传统乡土社会及乡贤群体解体的同时,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地位”及“困难性局面”却并未产生根本性改变。正是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因此提出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落实,关键在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此,就必须摆脱既往依靠政府单向推动的建设思路,借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合作,以便高效且合宜地整合各色资源,并避免建设过程的断层现象。其中,培育乡村发展的自治性、内生性力量,也即新乡贤群体的再造,又尤为关键。毕竟唯有内生和自治,才能熟悉乡村所需、并为此持续施力。
结合乡贤历史与乡村振兴目标来看,新时代的新乡贤,至少应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既称之为“乡贤”,则必然需要具备传统乡贤的核心素质,唯有品德高尚,挺立一己的道德人格,才能为村民所认可,并有机会借助“上行下效”,改变既有乡风中不合宜的地方;唯有立志于服务乡邻,有以一己之能去改善村容、村貌的胆气与担当,才能
在困难中坚韧不拔,才会真正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另一方面,既称之为“新”,意味着新乡贤必然超出传统权力框架来定位:新乡贤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语境下的产物,而是乡村的民主、自治与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粘合剂;新乡贤的任务不只是保证乡村的既有秩序与基本温饱,也不是单纯以发展乡村经济为任务,而应助力“五位一体”在乡村的落实;新乡贤既不是单纯的乡土代言人,也不是城市化的宣传者,而是要在保存乡村既有特色的基础上,有效吸纳现代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思维理念,实现乡村在“乡土气”与“现代化”上的完美对接。再一方面,新乡贤之所以“新”,还预示着要正确审视代际之间的关系和信息的转化,处理好德治、礼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新乡贤的存在与作用,不仅需要协调好乡村新老代际之间的沟通工作,自身也需要尽力适应新旧思维之间的转化;不仅要践行以德服人、以礼治村的态度,更应秉持以法治村、依法办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