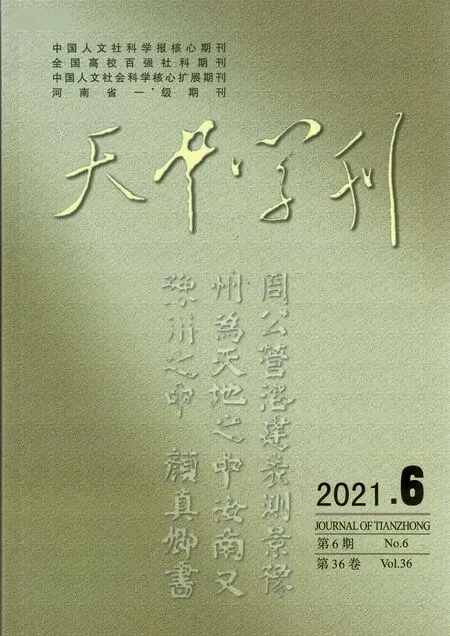以史为鉴:学衡派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和展望
2021-01-06王哲
王哲
以史为鉴:学衡派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和展望
王哲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援引西方“民主”“科学”等文化概念,以中国近世衰落历史为据,发起了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种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声音。学衡派通过对比古代文明古国发展史、研究中国文化史、分析中西近代发展史,重构了研究中国历史的路径。他们一方面还原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另一方面则从史学的功能性出发,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探寻了中国文化本原及其价值,分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缺陷,探索了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学衡派;中国文化;历史;新文化派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洋枪大炮打开国门,西学东进成为趋势。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推导和耳濡目染之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秩序逐渐崩解,中国传统的学术也开始转型,尤其在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之后,中国文化观念和学术传统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处于黯淡没落的状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掀起了一场新史学的革命。在他看来,中国只具备西方所盛行各种学科中的一门——史学,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梁启超这种以史学等学术内容观照近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态度一直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以中国近世衰落史为依据,以新文化改革救亡图存为指归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号召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于是在整理国故的浪潮下,传统的学术被西方学术全面批判和解构。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史学,“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在具体内容或研究题目方面已逐渐向史学转移”[3]。胡适以存疑的科学态度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壮大了“疑古”史学,但新文化派的历史研究主要引入西方流行研究方法否定了传统学术价值,在这种态势下,包括学衡派在内的新文化派反对者也纷纷研究历史,著书立说。学衡派主要成员是东南大学的张其昀、柳诒征、缪凤林等史地学派成员以及旅美游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大都中西贯通,对中西学问都有深刻理解,主张反对全盘西化,发扬传统文化价值。学衡派所追求的即《学衡》简章提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4],因而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一方面不像传统学术对象局限于中国或单纯采用西优中劣的结论,而是通过分析世界各国历史,结合中西历史得失,用相对科学的方法得出学术上相对严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结果展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又表现出其研究的鲜明实用导向。目前学界对学衡派历史研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学衡派对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性和通过历史研究彰显中国制度文化价值的实用性两方面,而对学衡派通过研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大历史来树立历史研究的学术典范和发扬传统文化价值甚少注意①。笔者以为,通过分析学衡派对中外历史的研究,可以管窥学衡派史学研究的学术理路以及对中西历史的认识,进而把握其建构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脉络。
一、通过对比古代文明古国发展史验证中国文化生命力
在五四时期,不管是新文化派还是学衡派,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中国历史,而是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发展史中衡量评判。新文化派对中国历史持全面否定的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历史是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他大声疾呼:“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20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5]陈独秀视中国的制度文物等国粹为民族灭亡的毒瘤,希望通过铲除中国的旧国粹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5]。而且,他还举出同是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灭亡的例子作为“天然淘汰”的前车之鉴:“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5]从陈独秀的论述中可以窥见,当时学界对中国制度文物等历史的研究已经不纯粹是学术讨论,而是要服从于救国的需要。对此,鲁迅有个著名的论断:“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6]在救国的旗帜下,中国的国粹是否具有延续中国国运的生命力成了重要问题。
学衡派正是基于寻找中国制度文物的现代生命力,对当时同样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国进行了研究。张其昀以其他古国的灭亡和中国的延续相对比,探寻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认为巴比伦等古国的灭亡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夫同为文明古国,彼皆一荣久瘁,黯然终古。我则拓地独广,传世独久,俨然为东方大宗。后果如此,前因安在?”[7]他认为“我中国所以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其道在中”,这是先民为了避免偏激的经验,也是中国国名的由来;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的“持中、调和、容让、平衡”等观念影响深远,最终成了民族精神[7]。他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两方面详细分析了各文明古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只有中国的地理环境可称“中和”,“惟我中华据完全之大陆,江淮河济,朝宗于海,平原弥望,规模宏远”,“土壤本沃,日暄雨润,五谷丰登”。大禹治水、秦修驰道、隋开运河等克服了地理环境的障碍,调剂了物资,物质变得丰富,礼仪开始兴盛。张其昀指出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有伟大的气度——“外拓国家之藩篱,内兴僻壤之宝藏”,“新旧杂居,诸族混融,一视同仁”,“温度雨量,俱不过分”,“民情风俗,安雅优美,不激不偏”[7]。因而,张其昀强调中国民族的发展一面拥有相对优渥的自然环境,一面突破了客观环境对发展的限制。从国家的文化传统来看,张其昀认为中国具有其他文明古国所未有的“中庸”“心理势力”优势。在政治方面,中国历来“文武交相用”,武备方面只注重足兵而不言穷兵,并“以文化孕育四邻,初无利其土地之心”,自然地成了各国的宗主,并使它们“同化于中国之文教”[7];中国不仅因文化得以保存,而且号召全世界遵守正义人道,与近代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者相较,简直天壤之别。在宗教方面,只有中国是将人格神灵演进为抽象观念,揭示大自然公理为人世标准,有宗教之意,但与宗教有别,关注现实生活,“以天为勉励道德,非以天为惑世愚民之用”[7]。在经济方面,中国“以实用为主,不以浮侈为利”[7],并号召薄于为己、勇于为人,为民族鞠躬尽瘁。在社会阶级方面,中国秩序靠“五伦之教”维持,但是伦理是道德本原,其目的在使上下两方面调剂,“并非专苦一方”[7],也很公平。在人伦方面,中国除了刑罚外还有礼乐,提倡中庸的道德,使人“守中而不趋极,有节而不过度”,成己成人。因而,“君子依乎中庸而行,虽朝代屡更,而社会之潜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7]。综上所述,张其昀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于“政治方面折衷于文武之间”“宗教方面折衷于天人之间”“经济方面折衷于汰灭之间”“社会阶级方面折衷于严荡之间”“人伦行为方面折衷于过与不及之间”[7]。
基于中和的地理环境和中庸的心理势力两方面的分析,张其昀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根就在于实行“中道”,“中道”赋予了中国“广土、众民、博物、永年”的特殊国情和绵长的生命力[7],这种富有生机的“中道”是有益于世界文明的。因此,他对未来也做出展望,号召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文明的影响。
二、通过研究中国文化史探究中国文化本原及价值
学衡派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在近代被新文化派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的问题进行了澄清,认为中国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其发展路径不可以照搬西方。柳诒征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不同,“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这种特异性是“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借觇文化之因果也”[8]2。他还撰写了《中国文化史》,从1925年起在《学衡》杂志上连载,于1932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柳诒征把中国文化史分为上古文化史、中古文化史和近世文化史三部分,分别对应中国的独立文化时期、中印文化融合时期、中印欧文化融合时期。他自称作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等问题[8]2。其实,柳诒征所要探寻的就是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中国得以存在所发挥的价值、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现代价值。
柳诒征认为中国文化成型于中国国名确定之时,要探究中国文化的内涵,必须理清中国国名的意义。他引用孙星衍的《禹贡》当从《史记》以“邦”作“国”的观点,提出中国国名最早出自《禹贡》“中邦锡土姓”的记载[8]37。《禹贡》之后,“中国”的国名则不断出现于《左传》《礼记》等典籍中。对于当时章太炎提出的“中国”表示地理中心位置的观点,柳诒征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中国“别于四裔”不在于地理位置,而在于礼义文化。他引《公羊传》和韩愈的观点,提出“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8]2。《论语》中尧要求舜“允执其中”和《礼记》中舜“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的施政方式都表明中国的国名“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8]38–39。由于唐、虞时期教育就崇尚“中道”,养成了中国尚中的普遍民性,因此,“中道”就是中国文化的本原,中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8]39。在论及孔子时,柳诒征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孔子所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尽己”[8]275,孔子把中庸看作最完美的道德,并且认为民众很难达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柳诒征反驳了章太炎关于“恕”是认知的说法,认为“恕”是孔子提供的行为规范。所以,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本原就是“中道”或“中庸”,并且需要依循孔子主张的思想和行为去实践。
对于近人颇为诟病的封建制度和阶级现象,学衡派也做出了合理解释,认为这些制度在古代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形成有具体的原因。柳诒征引用柳宗元《封建论》的观点,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即为了解决群体之间的争斗,“有德又有大”的众群之长必须做出裁定,由于从上到下有各种各级的群体,最终“天下会于一”,形成封建制度,并盛赞“封建之制,实为吾国雄长东亚,成为大一统之国家之基”[8]24。张其昀认为封建制度形成是为了使中央号令施行畅通,这样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诸夏主要人物,分散四国,而变为多元平均之发展”“民族范围实行扩大”[7],中国得以成为屹立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对于阶级现象,张其昀只承认中国有伦常之分而不承认有阶级之别,柳诒征则承认中国的阶级现象,但认为阶级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当时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阶级之制虽非尽善之道,当人类未尽开明之时,少数贤哲,主持一国之政俗,非有术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则天下脊脊大乱矣。”[8]49对于近人对于代表阶级的古代车服的批评,柳诒征对车服的功能进行了考证,纠正了近人对车服的误解,指出古代车服“为人民行谊之饰”[8]50,有赏罚的功能,蕴含劝人向善的期望,不是专门作为阶级的区别。但是柳诒征并不是盲目认同封建制度、阶级现象以及赞美古代贤王,强调“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8]17,认为古代社会进化不是个人的功绩,而是民族的进化,因此呼吁研究历史不能认为社会进步是一人一家的功绩,要着眼于人民的进化。
新文化派对中国制度文化批判的基点是认定中国制度文化不具备现代价值,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反而会使中国走上灭亡之路。面对这种诘难,学衡派潜心研究,并积极寻找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柳诒征最为称赞周代的制度:“吾国文明,在周实已达最高之度,嗣又渐降而渐进,至今,则古制澌灭殆尽,而后群诧域外之文明。”[8]150在官制方面,周代置官总体上“于组织之中寓互助之意,既以泯其畛域,且使互相监视,不使一机关独断一事,而遂其营私舞弊之谋”[8]155,官府特别注重会计,每旬每月每年都有考成,财政收支都有定例,吏治廉明高效,不像近代军阀、官吏肆意贪渎,中央无可奈何,只能借债弥补亏空。柳诒征认为《周官》精义在于“乡遂之制”,即在天子管理下进行乡遂自治,“其官多由民举,而受天子之命,其职等于王官,而为地方自治之领袖”[8]154。乡遂之官的职能涵盖调查、法治、教育、扶助联合、师田行役、征敛赋贡等各个方面,定期考成,执行权力并昭示于众。他反驳了今人“浮慕西法”者“谓西人能自治,而中国则否”的错误观念,并指出近代提倡自治的人民团体不如“周之会政致事”,弊病丛生,“但知组织人民,监督官吏”,“其侵污欺隐,亦无以异于官吏”[8]161。既然周代制度已有相当高度,那么后来何以日渐衰弱呢?柳诒征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周代制度并不是完美的,“其不尽行者,遂开后世之衰”[8]150。其次,制度并没有起决定作用,关键还是人治。他以《礼记·中庸》中孔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说法为论据,并举出共和制度在美国行治、在墨西哥则行乱的例子,提出“良法美意,待人而行,不得以世乱之因全归于法制也”[8]220。这与学衡派导师白璧德“人事之律”的主张不谋而合:“今欲使之返本为人,则当复昌明‘人事之律’,此二十世纪应尽之天职也。”[9]
学衡派非常注意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话语系统下发掘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此反驳新文化派的批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学”“民主”等西方文化概念的深入人心。学衡派并不盲目吹捧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而是相对科学、客观地分析其优劣成因,尤其注重突出人民主体作用,赞美中国早期的人民自治实践,试图用现代性的研究探索中国制度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三、通过研究中西近代历史勾画中国文化蓝图
在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后,学衡派还对陈独秀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你死我活”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学衡派讽刺了《新青年》诸君移植日本人将中国近世腐败病源归咎于孔子而批孔改革的做法:“某杂志中归狱孔子反复论辩者,殆不下数万言……误以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图,一若焚经籍,毁孔庙,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与列强并驱争先者。”[10]然后,学衡派逐条反驳了新文化派的反孔主张。首先,柳诒征认为如果近人将中国近世病源归咎于孔子必须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孔教已经完全在中国实行,数千年没有更替。他指出孔子之道自诞生起,“未尝完全实行于中国国家社会之中”,而近代社会,实行孔子之道者寥寥可数,“充满于社会国家之人物,所作所为,无往而非大悖于孔教者”[10]。其次,柳诒征强调孔子、孔教就是“一金制之招牌”,店内“货之良窳,当由肆中售卖者负责”,强调归咎于金制招牌是不对的。再次,柳诒征批判孔子尊君演成专制之弊的说法,认为这种议论“实发生于简单之脑筋”[10]。在孔子之前,桀、纣、幽、厉都是专制君主,没有孔子的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前都是君主专制,所以孔教不是君主专制的主因。最后,柳诒征对孔子的思想导致“科举之毒”的说法也做出了回应:“以利禄诱人,而假途于孔子之书,与假途于他人之书,其性质相等。”[10]唐宋曾流行熟读《文选》、苏文考科举,萧统、苏轼当然不能负责,同样孔子也不能对考试的出题负责。
基于孔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认知,学衡派在验证孔子之道与现代化可并行不悖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做出了规划,但这种结论是从分析中国和西方近代发展史基础上得出的。柳诒征指出中国近世衰败有四个关键节点——道光壬寅、光绪甲午、光绪庚子、宣统辛亥,认为道光时鸦片战争之失在于穆彰阿、琦善等污秽官吏及吸食鸦片的病夫,光绪甲午之失在于“淮军多无赖”,庚子之失在于慈禧、刚毅等人以及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在于托名革命之强盗、欺世盗名的政客、地痞流氓等。因而,他疾呼“盖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孔子教人以仁,而中国大多数之人皆不仁”[10],并举出近代中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家庭的分解、情感的沦丧、学术的浮躁等具体案例作为论据。柳诒征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国家问题,不在于信不信孔子,而在于成不成人,要建设新社会新国家,则必须使人人知道怎么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10]。柳诒征还指出,反孔教之说最多的论据就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提倡的勤俭、廉洁、诚信都没有超越孔子之道的内涵,所以孔子是一块招牌,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依然也是一块招牌,“以新招牌易旧招牌,依然不成人也,言之而行之,虽不用孔子之教,吾必曰是固用孔子之教也”[10]。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西力东渐,西方文化在打开中国国门后迅速占据了强势的话语地位,新文化派所提倡的就是以西方近代文化方向为中国文化前进方向。因此,通过研究西方近代历史,把握西方文化特点和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发生巨变的时候,探讨西方文化就变得更为迫切。学衡派意图通过分析西方文化的局限、西方文化的走势以解构新文化派文化蓝图,但其研究主要是通过采纳反思西方近世文化的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见解完成的。白璧德提出“自十六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极端之扩张”,即首先“扩张人类之知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注重功利,崇尚机械的功用,以培根为代表;然后“注重感情之扩张,对人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11],以18世纪的卢梭为代表。培根和卢梭的学说是近代西方思想的两大主要流派,白璧德将之分别称为“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感情的自然主义”,认为两者有一个共通的缺点——“皆未能以内心之规矩供给吾人”[9]。19世纪之后,人们“每以为科学发明,且同情心扩张”,社会就是向文明繁荣进步,“实则向大战场前行”,最终爆发了欧战。白璧德受爱玛生的观点影响,认为世间有“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两种法则,只讲物质之律,“乃灭人性”。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在于“欧洲文明只知尊从物质之律,不及其他,积之既久,乃成此果故也”。吴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质之学昌盛,人生道理晦暗,导致“众惟趋于功利一途,而又流于感情作用,中于诡辩之说。群情激扰,人各自是,社会之中,是非善恶之观念将绝。而各国各族,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这就是“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的贻害,所以他认为“今当研究人世之律,以治人事”[12]。吴宓受白璧德的影响,将人立身行事分为天、人、物三界,指出西方近代流行的就是物界思想,天界则笃信宗教,两者都显示出弊端,只有人界“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吾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说,皆属此类。近人或称之为人本主义,又曰人文主义Humanism云”[13]。因此,他提出“故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坚持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并又以白璧德在欧战后发扬的新人文主义为例,指出“西洋既如此,吾国自当同辙”[13]。
学衡派认为,“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在于坚持“人生正义之价值”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8]275,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前进方向就是实行真正的儒家文化,成己成人,造就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走因循的老路就能实现文明进步。学衡派早已明示孔子之后的时代并没有真正实现儒家人文精神。他们对新人文主义的信奉和对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文文化的肯定也表明,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传统有共通之处。与其说学衡派翼护孔子,不如说其所追寻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西传统中的人文主义文化。
三、结语
五四时期,新文化派援引西方“民主”“科学”等文化概念以中国近世衰落历史为据,发起了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种质疑中国历史文化的社会声音。学衡派则以世界性的视野重构了研究历史的路径:通过对比古代文明古国发展史验证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探寻中国文化之根;通过研究中国文化史,分析中国制度文化的成因,探索中国文化本原及其历史价值、现代价值;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发展史,反驳了近人对孔子的误解,找出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通过分析西方近代发展史,指出西方文化的缺陷以及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相对于新文化派对中国史和传统文化的多“断”,学衡派显然更多的是“论”。虽然学衡派对历史的研究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但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4]。这样就将历史研究从新文化派“救国”的实用功能中解脱出来,还原了历史研究本应具备的学术性。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争是“绅士”与“猛士”之间的和而不同,双方都道义在肩:“一边是世界胸怀”;“一边是家国情怀”[15]。不管是从世界历史验证中国文化价值,还是发掘西方人本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共同之处,都表明学衡派对中国文化足够自信,试图将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方案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发展蓝图,这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五四时代、重视物质的科学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张文建《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郑师渠《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周云《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等。这些研究偏重于学衡派史学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对学衡派援引世界历史树立史学研究范式和论证中国文化价值涉及不多。
[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M]//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1.
[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1):5–12.
[3] 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J].近代史研究,2000(3):59–94.
[4] 学衡杂志简章[J].学衡,1922(3).
[5] 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6.
[6] 鲁迅.热风[M]//鲁迅全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2.
[7] 张其昀.中国与中道[J].学衡,1925(41):1–24.
[8]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 马西尔.白璧德之人文主义[J].吴宓,译.学衡,1923(19):1–23.
[10] 柳诒征.论中国近世之病源[J].学衡,1922(3):1–11.
[11] 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J].胡先骕,译.学衡,1922(3):1–11.
[12] 吴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按语[J].学衡,1922(3):1.
[13]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2(4):1–23.
[14] 周云.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J].甘肃社会科学,2003(2):47–52.
[15] 张宝明.“绅士”对抗“猛士”:一代人的文化自信与人文救赎——从《新青年》到《学衡》[J].探索与争鸣,2018(7):114–120.
Learning from History: Xueheng School's Explor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Zh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 China)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New Culture School cited Western cultural concepts such a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launched a new cultural movement doubting and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Xueheng School reconstructed the path of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one hand, they restored the academic natur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starting from the fun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y verified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plored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analyzed the defects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ven the world culture.
Xueheng School;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new culture School
K203
A
1006–5261(2021)06–0141–07
2021-05-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201);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与质量提升计划项目(SYL19060144)
王哲(1994―),男,河南平舆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