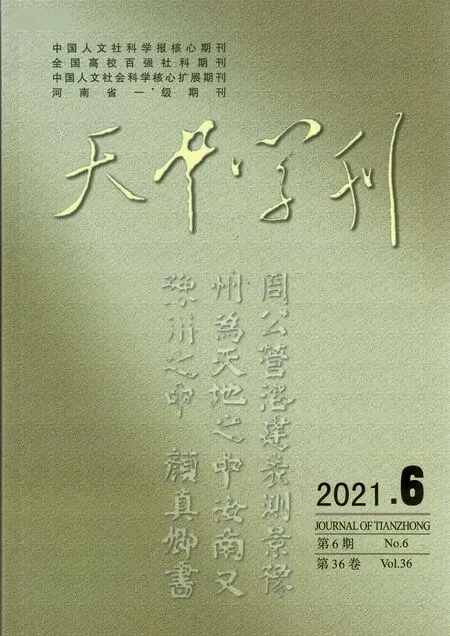“应物象形”与“随物赋形”——论南朝至宋代画论的心性论转向
2021-12-21王玉林
王玉林
“应物象形”与“随物赋形”——论南朝至宋代画论的心性论转向
王玉林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自南齐谢赫提出“应物象形”论到北宋苏轼提出“随物赋形”论,说明南朝至宋代绘画艺术起源论由物本转向心本,艺术创作原则由写实转向写意,揭示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逐步重视主体创作者心性的内在发展理路。在此基础上,审美理想由“气韵生动”追求物象传神转向“萧散简远”追求自由书写,体现了“物感说”到“师心说”文艺美学思想的流变,表现出自然美转向艺术美的美学追求。探究其哲学根基可知,由于佛学思想的介入,天人合一、物我相感、重视自然客体的绘画艺术发生学逐步转向重视创作主体内心所思的心性起源论。
写实;写意;物象;心性;禅宗思想
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所作《古画品录》云:“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1]301绘画六法论,是谢赫对先秦以来绘画理论的总结。从创作过程看,其中“应物象形”涉及画面文本的生成过程,是一切绘画活动的逻辑起点和创作基础。绘画理论发展到宋代,谢赫所谓“应物象形”的审美认识逐渐发生变化。苏轼在《书蒲永升画后》一文中云:“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2]628认为“随物赋形,尽水之变”的画作达到了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可称神品、逸品。“应物象形”“随物赋形”均涉及绘画创作对象的“形体”生成过程,表现创作者的深层审美心态。但二者所论艺术“形体”的生成方式却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象形”到“赋形”一字之差可知,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在艺术造形过程中一跃成为山水画作的核心。随之而来,山水画的创作技法、创作原则亦发生变化。本文立足山水画论由“应物象形”到“随物赋形”的转变,突破学界单一性的独立研究,而将二者联系起来探析此一理论转变背后审美认识、创作方法、文艺美学思想的变化,探究文艺美学的变化规律。
一、“象形”到“赋形”体现由“物本”到“心本”的认识论转向
谢赫所论“应物象形”从理论上高度总结了艺术创作发生、发展的一系列创造活动。宗炳《画山水序》云:“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1]288由目之所及到“应目”,山水、木石等自然外在的客体,中间经过“应”这一审美体验环节,走进审美主体的视野。此时“应”字有两层含义:其一,《说文解字》云“‘应’,当也”[3]502,从创作论的角度看,强调画家的艺术创作要符合自然客体原貌,侧重客观性;其二,“应”者,和也,《周易·乾卦》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4]51,从审美论的角度说,强调画家与审美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从“物感”说的艺术发生学角度看,将“应物”理解成创作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审美感受,进而将“象”解释为从审美感受到绘画创作的艺术加工过程。曹爱华称:“‘象’则是‘物’经过画家主观改造,带有浓浓的画家情感意识在内的‘客体’,是画家眼中心里艺术化的、人化的‘物象’。”并且认为:“源自于古代易学和道学的‘物’‘象’等绘画范畴在山水画创作中已不是纯粹的自然山水及其在自然环境中所表现的生物状态和物质属性,而是符合画家审美感知,且被画家通过美的精神进行熔铸凝练到画面上事物所展现出的美的属性。”[5]54从创作的角度揭示了南朝山水画创作突显出主观性现象的事实,但从理论形态看,此期谢赫所总结的“应物象形”理论,以审美客体的“自然属性”作为艺术创作的前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按古书多假象为像。人部曰:像者,似也。似者,像也。”[3]459从字源学意义上说,“象”最初的含义是“似”,指图形描摹与真实万象相似关系。所以,无论是注重画家主观意识加工的象,还是强调自然属性上的相似性,先秦至南朝,中国绘画艺术始终以遵从自然客体的真实性、客观性为创作标准,以“自然美”为最终审美理想。虽然象形以传神为旨归,但是以客观性为原则的艺术创作,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始终处于客体地位。宗炳《画山水序》所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绘画理论,便是最好的说明。
直至苏轼提出“随物赋形”的绘画理论,绘画艺术才从理论层面真正将画家的主体精神提到艺术创作的主导地位。《说文解字注》云:“随,从也,行可委曲从迹,谓之委随。”[3]70《老子》云:“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所以,“随”有跟从、顺从之意思,“随物”即画家遵从审美客体的自然形迹进行艺术创作。“应物象形”“应目会心”均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直觉、瞬时感受,应之其目即形之于手。与之相比,“随物赋形”中“随”字是延时性动词,由应目到随物的时间差,给予创作者充分的理性思考时间,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充满主体创造性的“赋形”艺术行为。苏轼《自评文》云:“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7]2069苏轼用“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形容其文思勃发、灵感泉涌不能自已的创作状态。其中,“随物赋形”中物、形是“心物”“心形”,即指画家随心物宛转、纵情任性、以主体情性为主导的文艺创作。“赋”字此时用其“授、给予”的引申义,将艺术创作者的地位提到显处,明确指出其对绘画艺术创作的主导性。
从理论层面重视绘画艺术中创作者主体精神的现象,追其根源,姚最“立万象于胸怀”肇其端,张璪所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命题扬其波。而其内在的哲学思想,则是在南朝至唐代佛学大盛的语境下,重视主体心性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此期文艺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应物象形”与“随物赋形”亦体现了艺术原理由“物本论”到“心本论”的理论转向。
二、“气韵生动”到“萧散简远”体现由“写实”到“写意”的方法论转化
谢赫“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绘画最高审美理想,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均为达到此审美境界的路径。钱钟书《管锥编》云:“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8]后二字均为前二字的解释。“气韵,生动是也”是说绘画作品不仅要有气韵,同时还要呈现生动传神的审美效果。“生动”即充满生命活力、富有动感。学界关于“气韵生动”的研究,多关注“气韵”二字,认为“‘六法’中的‘气韵’指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形体中流露出的一种风度仪姿,能表现出人的情调、个性、尊卑以及气质中美好的,但不可具体指陈的一种感受”[9]40。但从绘画的层面看,画中形象不仅要呈现一种格高的审美价值尺度,同时要有所谓“颊上添毫,‘如有神明’,眼中点睛,‘便欲言语’”的审美体验。“气韵”与“生动”相辅相成,只有气韵可达形似,但有生动,就能使画中形象活起来,与审美主体产生情感互动,建构一个闭合完整的审美体验。“气韵生动”作为六法之纲领,以追求充满神韵、生气的形象为目的,自然而然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绘画原则,即“写实”。温肇桐认为“气韵生动”,“以现代文艺理论用语来说,就应该是绘画创作上的主题明确,形象生动与表现真实的整体艺术效果”[10]22。即以尽可能呈现人或自然界的艺术真实为目标,并使之形之于画,达到如在目前的艺术效果,进而对观者产生审美影响,影响其行为实践。中国早期绘画以教化为功用,以对人的伦理道德产生有益影响进而维持社会稳定为目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11]1所以曹植《画赞序》有:“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乎鉴戒者,图画也。”[1]257通过图画教育进行政治教化,使人引以为戒。只有尽可能做到艺术真实、得其气韵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审美效果,产生积极的审美体验。顾恺之《论画》云:“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1]267。秉承客观性的艺术认知,以呈现艺术真实为创作原则,最终只有落实到技法的层面才能实现由认识到实践的完整艺术活动。即张彦远所谓“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11]23。纵观中国绘画史,以写实性为原则的南朝绘画技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经营位置。“经营位置”即画面的结构布局、细节描画、艺术空间的构造等,不仅涉及绘画创作的构思层面,亦关涉运笔操作。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云:
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陵庆云西而吐于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蟮如龙,因抱峰直顿而上。[1]281
整体而论,前后、东西、上下、远近,这些方位名词的运用,立刻营造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营造了强烈的空间感。顾恺之以平视的角度构图,远处在上、近处在下,符合审美主体的日常感觉经验。“天师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荫。”[1]281“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色彩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耳。”[1]281“下为涧,物景皆倒。”[1]282顾恺之深入局部细节,对物影这一细节的刻画,充分体现这一画法体现的写实原则。此外,宗炳《画山水序》所谓“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可将“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一图”[1]288,给人如临其境的真实之感。所以宗炳才能在山水画中卧游以畅神。
其二,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温肇桐《古画品录解析》引刘海粟对谢赫六法的分析称“写实——‘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并认为“刘海粟对‘六法’的认识,继承谢肇浙的说法并作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说法是比较科学的”[10]17。温肇桐认同刘海粟所论“应物象形”与“随物赋彩”所体现的写实原则。东汉张衡《平子论画》云:“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2]9画鬼神易,画犬马难,只因犬马有真实的参照物,而鬼神无具体形象可述,所以可以凭空描画。此一难易之别,侧面说明了绘画所遵循的写实标准。顾恺之《论画》又云:“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1]266–267如果不遵从现实事物的外在真实,则会失去其内在的神韵。同样,图画色彩的运用也是一样。“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浓也。凡胶清及彩色,不可进素之上下也。”[1]267描写对象之色一定要符合客观物色,否则便不能传神。
其三,骨法用笔。除却外在形体塑造的真实,山水画、人物画要真正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还要能通过形象的描摹,由外而内引导审美主体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写内在精神之实,在具体的用笔技法方面还要有骨力,能体现生命的力度。人物画要突出人物身形的消瘦。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称“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1]281,即人物要身形瘦硬而有精神。山水画,要画出山行重叠、相互依托之“势”,“当使赫𪩘隆崇,画险绝之势”。在山水画中,山崖绝悬之处,或线条稠密而紧实,或线条如裂电穿石直贯而下,正是用此具有力度感的线条与笔法突显山石内在的刚毅、劲健。
郭若虚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12]468气韵高古,来源于人品的高格,人品即画品,画如其人。由此可知,宋人对绘画的关注由外在的应物象形进入内在的神韵风度,进而走入画家的精神世界与内在品格。这种由外而内的演进脉络,使人越来越关注创作者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格调,体现在绘画理论上便是画家的主体性色彩日益突出。绘画理论由关注客体到体现主体,中间经历了缓慢的变化过程。姚最《续画品》云“立万象于胸怀”[1]322,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躯,胸有丘壑,主客结合。唐代裴孝源撰《贞观公私画史序》:“大唐汉王元昌,天植其材,心专物表。含运覃思,六法俱全。随物成形,万类无失。”[12]17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11]35。直到朱景玄提出“万类由心”的理论命题,心的作用、意气的显现已经越过客观形象的塑造,创作者主体的思想便在理论层面逐步确立了其在绘画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在此理论视域的基础上,苏轼提出“随物赋形”的画论命题。在绘画艺术的创作原则上,写实向写意的转化亦经历“写真”的过渡阶段。“写实”即侧重客观对象之形、色,“写真”是以道家思想为基底,用一管之笔描画万象之本原、本性,除去伪相,直击实相。即《庄子·渔父》所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13]荆浩《笔法记》云:“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原,夫木之为生,为受其性。”“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花为实。……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12]6“真”即万物自然而然之本性,写真,即遵从万物自然生长的规律,不仅要得其形似还要写其气韵。由此而来,绘画艺术的职责即由进行教化的社会功能,逐渐转化为“明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12]6的审美功能。
在“求真”的创作心态与思维方式基础上,根据艺术发展的内部规律,画家在创作时自然而然追求“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12]498。即画山水之自然之道,使人“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写意”即画家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把握审美对象,通过审美意象表现其对世界、人生的思考,这类审美意象始终带有主体的强烈情感、想象和意欲特征。
苏轼画论回到图画本体,将欣赏者的审美体验由方外之地拉回图画本身。图画本体这一审美意象以其丰富内涵令人品味无穷。苏东坡《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14]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已与创作对象融为一体,画即是作者之思、之意。“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7]356“寓意于物”即寓意于所画之物,见画不见人,达到真正的心手合一之境。“留意于物”即画家的主体精神与所画之物仍未真正融合。但如何表现这画中意?这就需要通过画法作为媒介。以山水画为例,徐国喜云:“山水画外在审美意象的表达要求与画家内在情感思想的外化,就需要画家用一个契合的途径和载体——‘皴法’去立体的塑造山石的肌理和力度、山水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使画家‘因心造境’的山水精神得以彰显。”[15]42而“皴法的演进到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皴法的出现,既是画家求‘真’悟‘道’的结果,也是他们求‘真’体‘道’表达的手段”[15]41。而苏轼的《枯木怪石图》,陈传席先生称:“古木有枝无叶,怪石与古木皆用清淡、空灵、松散之笔似勾似擦,草草而成。土坡一笔带过,怪石似卷云皴,实则无皴法,信手写出,不求形似,不具皴法。倒也‘萧散简远’‘古雅淡泊’。”[9]107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云:“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7]390无法之法,实为大法。只有超越法度,心手相忘,才能任情恣性,这正是苏轼所谓“随物赋形”。“皴法”的点染、勾勒确实可以呈现烟石的若有若无之态,表现山水的结构层次,并结合远近透视法,呈现山水内在的空灵与浑厚,营造天地万象唯一“画”的艺术境界。但刻意的画面构图与技法运用,容易限制作者情思的自由表达,不能达到随心中之物象尽诸纸上的心手合一之境。
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图1)是其“随物赋形”画论思想的完美呈现,其运笔螺旋而上,浓墨与轻墨交织,由怪石涂抹自然过渡到枯枝线条的勾勒,一笔写成。怪石锋利的棱角与枯木遒劲的形姿,表现出其内心的坚韧与刚毅。苏轼所画的枯木与怪石,不是对自然景观的临摹,而是其内心物象的真实写照。此时的枯木、怪石已脱离真实的自然物象,已是经过艺术家精神洗练的意象。

图1 苏轼《枯木怪石图》

图2 《苏轼潇湘竹石图》
与《枯木怪石图》相比,其《潇湘竹石图》(图2)更显平淡淳朴、含蕴丰富。该图用似有似无的笔墨与时而稠密时而零星的点点竹叶,呈现出一种超出尘世的时间感与距离感,简单、朴拙的画面,表现其内心的平淡与从容和执着过后的洒脱与自由。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7]2124与唐代主流书风相比,魏晋书法体现出的自由、淡然之精神,正是苏轼心之所向。《书唐氏六家书后》:“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7]2206书画同源,其对书境的追求,亦体现其对理想画境的探求。
“写实”与“写真”仍以外物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写意”虽有外物作为参照,但创作者主体精神的完全呈现才是其最终目的。以“写意”作为创作原则的绘画,其塑造的艺术形象带有更高的抽象性、典型化甚至符号化的艺术特征,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胡经之说:“美妙的艺术,不仅是形美、声美,更重要的是要意美。”[16]所以,真正具有“意美”的绘画作品才可称为逸品。从“应物象形”到“随物赋形”,绘画理论中主体性的呈现日益显著,究其背后原理即是创作原则与审美理想由写实性到写意性、由“气韵生动”到“萧散简远”的转变,美学追求亦由自然美转为艺术美。
三、“物感说”到“师心说”文艺美学思想的转变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所谓“应物象形”的绘画理论,以“物感说”文艺美学思想为基础。《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17]音乐来源于人心感物而动,故形于声,画的形成亦是画家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象。在“感”的作用下,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客观外物进行情感双向互动,故而形象生矣。《周易·系辞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虞翻曰:“感,动也。以阳变阴,通天下之故,谓‘发挥刚柔而生爻’者也。”[4]592在天人合一、物我相感作用下生成的“象”具有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灵性特征。“物感说”的文艺美学思想,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是“传神写照”“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仅指鉴赏者的审美体验,从本体论的层面看,“气韵生动”更是指出了“象”的主体性与自身性。《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8]一旦画作完成,达到“气韵生动”的传神效果,画家所塑造的“象”便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受创作者的制约。此种思维方式以佛教“形神论”为其内在哲学根基。宋人邓椿在《画继杂说》中云“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2]75,指出“气韵生动”是物之神。“应物象形”只能产生具有自然灵性的“象”,由“自然灵性”到“气韵生动”,需要为其注入“神性”特征。在形神二分的思想下,才能产生顾恺之所谓以形写神的画论思想。慧远《万佛影铭》云:“理玄于万化之表,数绝乎无形无名者也。若乃语其筌寄,则道无不在。”[19]宗炳《画山水序》称:“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1]288在万物皆有佛性、形神一体的思想观照下,才能产生宗炳所谓卧游以畅神。“应物象形”的画论思想以“物感说”为基础,由于佛学思想的介入,走向以形神关系为主导的道路。
苏轼“随物赋形”之论,以“心本论”思想为主导。陈传席云:“绘画之始,一般说来乃是模仿对象。姚最之前的画论,‘传神论’是传对象之神,‘气韵论’和‘以形写形’也都是以对象为准的。只有王微提出的‘拟太虚之体’和‘神明降之’谈到画家作画时的主观作用。而姚最更明确地提出‘立万象于胸怀’,这代表中国画论的大进步。也和他的‘心师造化’论相统一。将万象立于胸中,也就是胸有丘壑。心胸得到充实,作画时所写的不是客观之物象,而是胸怀。但胸怀中必须立有万象,这就是主客观结合。开后世绘画写心之法门。”[9]45此种写心的绘画理论,以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周易大传》提出天、地、人同归于“性命之理”,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20],强调心性合一,《大学》讲“修身在正其心”。可知,心性之学是先秦儒家天人学说的重要内容,以心为本原的心性思维影响着后世文人的一切创造活动。此外,《坛经》云:“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21]断绝一切杂念,不执着于一切相,恢复人自由活泼、无偏私狭隘之心,方能不为外物所役使,达到真正的自由逍遥之境。苏轼《卓锡泉铭》云:“祖师无心,心外无学。有来扣者,云涌泉落。问何从来,初无所从。若有从处,来则有穷。”[7]566心外无学,心外无物,了却杂念,心境坦然方能进入妙境。苏轼亦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艺术创作只有在审美心境上做到澄怀坐忘,凝神入定进入自由之境,身与物化,才能超越一切法度万相,拟写心象。此时之“心象”,不仅拟天地之形容,且写万古之同心,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美学价值。
绘画艺术的文艺美学思想基础由“物感说”转向“师心说”,艺术创作的视野由外物回到内心,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心性哲学形而上之思,逐步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创作预示着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向纵深发展、中国古代文艺精神走向更高层次的独立与自由。以人的心性为艺术创作的根源,以反映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为旨归,此一心性转向为理解艺术的同一性奠定基础,有利于打破不同艺术门类的边界,为诗画融合等跨媒介艺术形式的产生提供便利条件。
[1] 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2]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3]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曹爱华.论传统山水画中“应物象形”的审美观照[J].美与时代(下),2017(10):54–56.
[6]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王弼,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6.
[7]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1.
[9] 陈传席.中国绘画理论史[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10] 温肇桐.古画品录解析[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
[1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12]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13]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1032.
[14] 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2.
[15] 徐国喜.析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皴法演进的内涵关联[J].艺术评鉴,2019(22):41–43.
[16]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0.
[17] 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郑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74.
[18] 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刘孝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721.
[19] 慧远.庐山慧远大师文集[M].张景岗,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7.
[20] 孟子注疏[M].孙奭,疏.赵岐,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1.
[21] 慧能.金刚经;心经;坛经[M].陈秋平,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88.
J201
A
1006–5261(2021)06–0102–07
2021-01-12
王玉林(1992―),女,河南汝南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