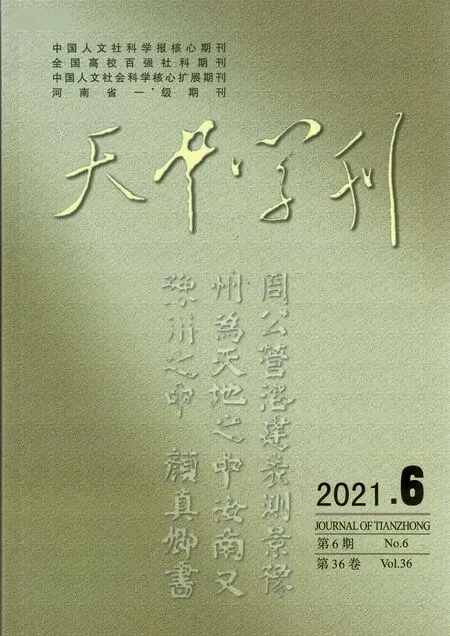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干宝《搜神记》考论
2021-12-21张保见
张保见
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干宝《搜神记》考论
张保见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乐史《太平寰宇记》有集志型特点。《搜神记》是干宝的代表性著作。《太平寰宇记》引用《搜神记》题名的有15条,其中一条为误书。《太平寰宇记》引用《续搜神记》3条,“筝笛浦”一条当出自《搜神记》,今本《搜神后记》误收。从《太平寰宇记》引用《搜神记》个案,可以窥知宋以前古人著述,对于资料来源并不重视,改变自乐史始,或受到类书著述模式的影响。《太平寰宇记》引领了后世地方志的走向。
《搜神记》;《太平寰宇记》;引用;史源
《搜神记》是中国古代志怪类文献的代表性著作,成书后即引起时人兴趣,后世纂述引用较多。至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开创了“集志型”地理总志[1],今所存篇目,多处引用《搜神记》,有值得关注讨论之处。
一、乐史、干宝事迹概述
宋王朝在传统中国社会序列中是一个十分重文的时代,官方以文立国的政策导向,以性理名教、王霸义利之辨为特征的理学的勃兴,以印刷术为代表的文化技术的进步等这些因素,催生了宋代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此同时,文献的编撰和整理受到重视,出现了大批撰著等身的学者。在这批学者中,乐史在宋朝开国文化初兴时期具有重要地位。乐史(930―1007年),字子正,抚州(今江西)宜黄人。中南唐进士,仕秘书郎。归宋,历官平原主簿、武成军节度掌书记。以上书言事,擢为著作郎。太平兴国五年(980)至雍熙三年(986)间,曾经知陵州(今四川仁寿)。后历直史馆,知舒、黄、许、商四州,分司西京,出掌西京磨勘司,改判留司御史台,卒。乐史从政成就不大,但一生嗜学,手披不倦,勤于著述,成就颇丰,所撰简篇总数达32种近1200卷,尤以《太平寰宇记》最为知名,致有人认为“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2]。具有开后世地方志广征博引风气的《太平寰宇记》,对于内容传奇丰富的《搜神记》自然有所引用。
《搜神记》,干宝撰。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生活在两晋之间,后移居浙江海盐终老。少勤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通经学,注解《易》,今佚;有史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3],惜亦不传。《搜神记》无疑是干宝最为人所称道的著作。《晋书》本传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少,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作20卷,《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若以上2志连出,下文则简称《两唐志》)均为30卷。《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以下简称《御览纲目》)、《遂初堂书目》收录,不著卷次。《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作“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崇文总目》亦收《搜神总记》10卷,题曰“不著撰人名氏”。《玉海》卷57:“或题干宝撰,非也。”疑唐代传本较原本已有所更改,宋代传本较唐代或又有所改定。
《搜神记》今存20卷,或为明人重辑本。四库馆臣云:“此本为胡震亨《秘册函》所刻,后以其板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者。考《太平广记》所引,一一与此本相同”,“似此本即宝原书”,随后有详细推考,认为“殊为可疑。然其书叙事多古雅,而书中诸论,亦非六朝人不能作,与他伪书不同。疑其即诸书所引,缀合残文,附以他说,亦与《博物志》、《述异记》等。但辑二书者,耳目隘陋,故罅漏百出。辑此书者,则多见古籍,颇明体例,故其文斐然可观。非细核之,不能辨耳。”[4]明确存世本已非干宝原作,系后人辑录,所辑较为专业,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面貌。学津讨源本亦较常见。今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整理本,以及贵州人民出版社全译本、中华书局《新辑搜神记》30卷本等整理本。
干宝及其《搜神记》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早已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论著代不乏书。近世以来,成果尤丰,仅中国知网就收录有500余篇以《搜神记》为篇名的著述,其中包括2篇博士学位论文,80篇硕士学位论文,涉及语言学、文学、史学、宗教学等众多领域。然检讨已有研究,包括整理成果在内,对于历代史籍引用《搜神记》或有涉足,进一步探讨《搜神记》资料来源以及误辑、漏辑诸事者,或有不足。以《搜神记》为典型的志怪小说的引用,对于《寰宇记》的意义,亦缺乏讨论。故联缀数文于此,就教方家。
二《太平寰宇记》引用《搜神记》条文考
《太平寰宇记》引用《搜神记》共计15条,今逐一考索于下。
(一)鼠怪
鼠怪。《搜神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厅事上,语周南曰:‘尔以某月日死。’周南不应。鼠还穴。至期日,更冠帻绛衣语周南曰:日中死。复不应。鼠入穴。斯须,复出语如初。出入数转,日过中,鼠曰:‘尔不应,我复何求道?’言讫,颠厥而死,即失衣冠。视之,乃常鼠也。”(《太平寰宇记》卷2襄邑县)
按:此条又见于《宋书》卷34、《晋书》卷29。《法苑珠林》卷42引作“出《搜神记》”。《艺文类聚》卷95及《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卷885、卷911引作“出《列异传》”,《太平广记》卷440作“出《幽明录》”。
《隋志》有《列异传》2卷,魏文帝曹丕撰,又云“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旧唐志》作3卷,张华撰。《新唐志》作一卷,张华撰。从今本内容来看,有多条为曹丕后事,疑唐代所传或已非原本,故著者改题西晋张华。《御览纲目》外宋代志目不收,《御览》征引甚众,疑唐代异本宋中期后亦亡佚。今存一卷,疑为宋后人辑录。
《幽明录》或作《幽冥录》,亦属神仙志怪类著述,刘义庆撰。刘义庆是南朝宋人,著有《世说新语》,《宋书》有传。《隋志》20卷,《两唐志》30卷,后不见志目收录,然《御览》引用甚众,疑北宋初尚存,北宋中期后或已不传。有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及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各1卷,另有《琳琅秘室丛书》胡珽辑本1卷及《校讹》1卷、董金鉴《续校》1卷。
疑《寰宇记》此条出自《搜神记》,或源自《列异传》,《幽明录》亦采录。
(二)韩凭冢
韩凭冢。《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取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怨王自杀。妻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又云:“凭与妻各葬相望,冢树自然交柯,有鸳鸯鸟栖其上,交颈悲鸣。”(《太平寰宇记》卷14郓城县)
按:此条,《艺文类聚》卷92也加以引用,称出自《列异传》,韩凭作“韩朋”。《御览》卷925引用时,作出自干宝《搜神记》。
《太平广记》卷463引作出《岭表录异》,韩凭作“韩朋”。《岭表录异》,诸书所引又名《岭表志录异》《录异记》等,3卷,刘恂撰,《新唐志》及宋代诸目均有著录。明初修《永乐大典》尚广征此书,明中期后已不闻流传,清代四库馆臣以《永乐大典》为主辑出的3卷本较通行。另有《百川学海》本、光绪十七年排印本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有鲁迅校勘本可供参阅。从今存条文看,本书所记广泛涉及以广东为主的唐代岭南道之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民族物产等。
疑《寰宇记》所引此条《搜神记》,或源自《列异传》,《岭表录异》亦采录。
(三)马邑城
马邑城,即今州城是也。《搜神记》云:“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忽有马驰走,周旋反覆,父老异之,因依走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太平寰宇记》卷51鄯阳县)
按:此条《御览》卷193引作出《太康地记》,又云“《搜神记》亦载也”。《太康地记》,又名《太康地志》《太康三年地记》《晋太康地记》,不著撰者,《御览纲目》收录,南宋已不见流传。“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90年)。至清有毕沅、王谟、黄奭、王仁俊辑本各1卷。主记地理,间及古史传说,较秦汉地理书有很大进步。《旧唐志》:“《地记》五卷,太康三年撰。”疑即本书。
疑《寰宇记》此条所引《搜神记》,或源自《太康地记》。
(四)高亭
高亭。《搜神记》云:“相州高阳县南有亭,宿者辄死。后有书生宿,夜半有人着皂衣,来呼亭主:‘此有宿客耶?’曰‘然。’喑嗟而去。又有一人衣赤衣,来问如前。移时无复来。生乃呼亭主,问之:‘向黑衣者谁?’曰:‘北舍猪母。’‘赤帻者谁?’曰:‘西舍老雄鸡。’‘汝谁?’曰:‘我老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毒长四尺,并及猪、鸡,亭遂安静。”(《太平寰宇记》卷55安阳县)
按:此条《法苑珠林》卷42、《御览》卷918及947、《太平广记》卷439均有引用,作出自《搜神记》。
(五)无终山
无终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阴山,在县西北四里。《神仙传》云:“仙人白仲理者,辽东人也。隐居无终山中,和神丹,又于山中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又《搜神记》云:“无终山有阳翁玉田,昔雍伯,雒阳人,父母终,葬于无终山。山上无水,雍伯汲水,作义浆,行者皆饮。三年,有一人就饮,以石子一升遗之,使于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有徐氏者,为右北平著姓,有女,人多求之,不许。雍伯试求,徐笑以为狂,乃云:‘以白璧一双,当可为婚。’雍伯至种石处,得五双白璧,徐氏大惊,即以女妻之。”(《太平寰宇记》卷70渔阳县)
按:此条《水经注》卷14、《艺文类聚》卷83、《初学记》卷8、《蒙求集注》卷下、《事类赋》卷9,及《御览》卷45、卷479、卷519、卷805、卷828,都有引用,作出自《搜神记》。
《太平广记》卷4引作出《仙传拾遗》。《仙传拾遗》40卷,唐末五代蜀人杜光庭撰。《崇文总目》《宋志》收录。《中兴馆阁书目》卷4云“凡四百二十九事”。宋后唯见明正统《道藏阙经目录》收录,至迟明中期已不传,疑散佚于元明换代之际。今先有严一萍辑99条,后有李剑国辑128条行世。
即《寰宇记》此条所引当出自《搜神记》,疑《仙传拾遗》亦采录自《搜神记》。
(六)高骊山
高骊山,在县西南七十里。梁武帝《舆驾东行记》云:“自覆船山、酒罂山南次高骊山。传云:昔高骊国女来此,东海神乘船致酒醴聘之,女不肯,海神拨船覆酒,流入曲阿湖,故曲阿酒美也。”又《搜神记》云:“诸葛恪为丹阳尹,出猎于两山之间,忽见小儿,众莫之识。参佐问之,曰:‘此事在《白泽图》,云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名曰系囊。’众伏其博识。”(《太平寰宇记》卷89丹徒县)
按:此条《法苑珠林》卷80、《御览》卷886、《太平广记》卷359均引作出《搜神记》。
(七)石侯祠
石侯祠,在县西一十五里。石高峻,仰之眩目,云庐君之弟所理也。《搜神记》曰:“武宁县有女戴氏,久疾,出觅药,见一石立似人形,礼之曰:‘汝能令我疾差,吾当事汝。’因感梦曰:‘吾当佑汝。’寤而遂差,因立祠。”今犹存焉。(《太平寰宇记》卷106分宁县)
按:此条《太平广记》卷294引作出《搜神记》。《御览》卷51引作出《列异传》。《北堂书钞》卷160引作出《列仙传》。
《列仙传》2卷,题刘向撰。记古来仙人,体例同《列女传》。刘向,字子政,汉宗室,《汉书》有传。葛洪《抱朴子·论仙》称刘向撰。《隋志》及《旧唐志》作《列仙传赞》2卷,《新唐志》作《列仙传》2卷。《直斋书录解题》:“《列仙传》二卷,汉刘向撰,凡七十二人,每传有赞,似非向本书,西汉人文章不尔也。《馆阁书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总目》作二卷,七十二人,与此合。”疑南宋时已非原本。今存2卷本,载71人。有《道藏》《百子全书》《四库全书》等本。
疑《寰宇记》所引此条《搜神记》,或系源自《列仙传》《列异传》。
(八)陵山
陵山。《搜神记》云:“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千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谓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祭。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或有光,见一绣衣妇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当验。’宪乃具告亭中,众人大惊异。至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神谓宪曰:‘诸乡老在此,吾居近水,当少致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亡,惟宪里不被兵。”又隋将麦铁杖为陈擒于此亭侧。(《太平寰宇记》卷126庐江县)
按:此条《太平广记》卷292引作出《搜神记》。
(九)丁姑祠
丁姑祠。《搜神记》云:“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人,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每使役皆有程限,或违顷刻,必加鞭笞,不可堪处,以九月七日自尽而死,遂有灵响,闻于人间。乃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工作不已,使避九月七日焉。’今江南皆呼为丁姑假,九月七日,咸以为息日也。吴平后,其女幽魂思乡欲归,永平中九月七日见形,着缥衣,戴青盖,婢从其后,至牛渚津求渡。有二男子,共捕鱼,乃谓姑云:‘与我为妇,即当相渡’。姑骂之。须臾,有老翁乘船又至,从求渡,翁渡之,至南岸,姑曰:‘吾是鬼神,思报厚德。翁速还,必有所获。’翁至西岸,见两男覆水中,有鱼数千头,风飘上岸,翁取鱼归。俗以姑有灵,故立祠焉。”(《太平寰宇记》卷128全椒县)
按:此条《太平广记》卷292引作出《搜神记》。
(十)岳庙
岳庙。《搜神记》云:“霍岳庙中有大铁锅,受三十石。至祭祀时,水辄自满,事毕即空。”(《太平寰宇记》卷129六安县)
按:此条《御览》卷757引作出《搜神记》。
(十一)断蛇邱
断蛇邱,在县西北一十五里。按《搜神记》:“随侯出猎,见白蛇被伤,乃筑坻于县东北骸山侧收养,既愈,放之,后衔径寸珠以报德。”(《太平寰宇记》卷144随县)
按:此条《史记》卷87“随和之宝”条《正义》引作出《说苑》。《说苑》,西汉刘向撰。原20篇,北宋初已残,曾巩整理为20卷,清人又有所增补。本书按类记叙春秋战国至汉代遗闻逸事,对后世小说和民间故事有一定影响。《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本较通行。
疑《寰宇记》所引此条《搜神记》,或源自《说苑》。
(十二)鹄奔亭

按:此条《太平广记》卷127“苏娥”条引作“出《还冤录》”。《还冤录》,史籍不载。又,此条见于颜之推《还冤志》,疑《太平广记》所引“还冤录”即《还冤志》,又名《还冤记》《还魂记》《冤魂志》《冤报记》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2:“《还冤志》,三卷,内府藏本,隋颜之推撰。之推有《家训》,已著录。此书《隋志》不载。《唐书·艺文志》作《还魂志》,三卷。《文献通考》作《北齐还冤志》,二卷。考《宋史·艺文志》作颜之推《还冤志》,《太平广记》所引亦皆称《还冤志》,与今本合,则《唐志》为传写之讹。至书中所记,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齐,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后终隋代。观陆法言《切韵序》,则开皇之初,尚与刘臻等八人同时定韵,更不得目以北齐,殆因旧本之首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遂误以冠于书名上欤!观《宋史》又载释庭藻《续北齐还冤志》一卷,则误称北齐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后,佛教弥昌,士大夫率皈礼能仁,盛谈因果,之推《家训》有《归心篇》,于罪福尤为笃信,故此书所述,皆释家报应之说。然齐有彭生、晋有申生、郑有伯、有卫、有浑良夫,其事并载《春秋传》。赵氏之大厉,赵王如意之苍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亦未尝不载于正史。强魂毅魄,凭厉气而为变,理固有之,尚非天堂地狱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辞亦颇古雅,殊异小说之冗滥,存为鉴戒,固亦无害于义矣。陈继儒尝刻入《秘籍》中,刊削不完,仅存一卷。此本乃何镗《汉魏丛书》所刻,犹为原帙,今据以著录焉。”因此,《寰宇记》此条出自《搜神记》,疑《还冤志》采录此条或源自《搜神记》。
(十三)鳄鱼
《搜神记》云:“《扶南传》云扶南王范寻,常养虎五六头,养鳄鱼十头,若有犯罪者,与虎不噬,投以鳄鱼不噬,乃赦之。无罪者,皆不噬。”(《太平寰宇记》卷164戎城县)
按:《扶南传》,又名《扶南土俗传》《扶南土俗》,康泰撰。《梁书·海南诸国传》:“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御览纲目》外历代志目不收,卷次不详。《御览》引用有不见于前书者,疑宋初尚存,中期后或已不传。有《麓山精舍丛书》陈运溶辑本1卷。扶南,东南亚古国,在中南半岛,《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新唐书》及《太平寰宇记》《通志》均有传。
《御览》卷938引作出《吴时外国传》。《吴时外国传》,《御览》卷359又引作“康泰《吴时外国传》”,疑亦如《扶南传》,系康泰远通海南诸国后之著述。
《事类赋》卷20、《御览》卷892引作出《异苑》。《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异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参军,元嘉三年,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卒。又称尝为刘毅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今案书中称毅镇江州,褊躁愈剧,又载毅妻为桓玄所得,擅宠有身,多蓄憾诋毁之词,则震亨之言,当为可信。惟书中自称‘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以《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考之,时方以骠骑将军领荆州刺史,与敬叔所记相合,而震亨传中未之及,则偶疏也。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刘知几《史通》谓《晋书》载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去,乃据此书载入,亦复相合。惟中间《太平御览》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此本失载。又称宋高祖为宋武帝裕,直举其国号名讳,亦不似当时臣子之词,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诗中陶侃胡奴事,据《世说新语》但知为侃子小名,勘验是书,乃知别有一事,甫之援引为精切,则有裨于考证,亦不少矣。”
则《寰宇记》所引《搜神记》此条源自《扶南传》,《异苑》亦采录。
(十四)螺江
螺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搜神记》云:“闽人谢端少孤,于此钓得一螺,大如斗,置之瓮中,每日见盘馔甚丰。后归,忽见一少女美丽,燃灶之次,女曰:‘我是白水素女,天帝哀君少孤,遣妾与君具膳。今既已知,妾当化去,留壳与君。’其米常满。端得其米,资及子孙,因曰钓螺江。”(《太平寰宇记》卷100侯官县)
按:此条今本《搜神记》不收,见于《搜神后记》卷5。《艺文类聚》卷97、《太平广记》卷62及《御览》卷8、卷941引作出《搜神记》。谢端,《晋书》卷70《卞壸传》“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门”,西晋人。
《初学记》卷8引作出《发蒙记》。《发蒙记》,晋束晰撰。束晰,字广微,西晋人,《晋书》有传。《隋志》一卷,云“载物产之异”。此后志目不收,而《御览》诸书多有征引,疑至迟宋中期后亡佚。
又见于《述异记》卷上。《四库全书总目》卷142:“《述异记》二卷,内府藏本,旧本题梁任昉撰。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具《梁书》本传。此书《宋志》始著录,卷数与今本相符。晁公武《读书志》曰:‘昉家藏书三万卷,天监中,采辑先世之事,纂新述异,皆时所未闻,将以资后来属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为祖冲之所作,误也。’案《隋志》先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唐志》盖沿其旧文,以为别自一书则可,以为误题祖冲之,则史不误而公武反误矣。其书文颇冗杂,大抵剽剟诸小说而成”,“其为后人依托,盖无疑义”。
据上,疑《寰宇记》所引此条,当出自《搜神记》,或源自《发蒙记》,《搜神后记》似误收,今本《述异记》采录。
(十五)焦湖庙
焦湖庙。《搜神记》《幽明录》:“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大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太平寰宇记》卷126合肥县)
按:此条不见于今本《搜神记》。《北堂书钞》卷134、《太平广记》卷283引用时,作出自《幽明录》,疑《寰宇记》此处“搜神记”3字似为衍文,当出自《幽明录》。
三、《太平寰宇记》引《续搜神记》条目辨析
除上节引用《搜神记》外,今本《太平寰宇记》存文中,又有引用《续搜神记》的3条,今逐一辨析于下。
(一)鲁肃墓
鲁肃墓。《续搜神记》云:“王伯阳者,家在京口,东有大冢,传是鲁肃墓。伯阳妻卒,乃平其坟,以葬焉。经数年,忽一日,伯阳方在厅事中,见一人乘肩舆,从者数十辈,径前,怒谓伯阳曰:‘我鲁子敬也,冢在此二百许年矣,君何敢辄相毁坏!’因目左右与之毒手,从者遂牵伯阳下,以刀环筑之数百而去,登时即死,良久乃苏,其环筑处,遂皆发疽,寻卒焉。”(《太平寰宇记》卷89丹徒县)
按:此条又见《御览》卷559、卷884,皆作出《续搜神记》,惟《太平广记》卷389引作出《搜神记》,今本《搜神记》不录,疑《太平广记》引用之“搜神记”3字处或有脱文。又,《御览》卷375:“《幽明录》曰:‘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岗。夜梦鲁肃诣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公鲁肃与弟争墓。后于生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杀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此条,《太平广记》卷389引作“一说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若不如不复得还。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亦云“出《搜神记》”,与今本《搜神后记》卷六补录异说条同。
疑《寰宇记》所引此条或出自《搜神后记》,《太平广记》注释出处有脱文,或流传中误抄所致,刘义庆《幽明录》亦采录。
(二)秦精
《续搜神记》:“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尝入武昌山中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曲,示以丛茗而后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遗精,精怖,负茗而归焉”。(《太平寰宇记》卷112武昌县,《搜神后记》卷7)
按:此条《茶经》卷下、《艺文类聚》卷82、《御览》卷48及卷867都有引用,作出自《续搜神记》。惟《艺文类聚》卷86引作出《搜神记》,疑脱“续”字。
(三)筝笛浦
筝笛浦。《续搜神记》云:“浦中昔有大舶覆水内,渔人宿旁,闻竽笛之声及香气氤氲,是曹操载妓船覆于此。”(《太平寰宇记》126合肥县)
按:此条又见于今本《搜神记》卷16“濡须口”条,《御览》卷981引作出《搜神记》。《艺文类聚》卷44、《法苑珠林》卷49及《御览》卷75、卷769引用时,均作出自《续搜神记》。
《御览》卷399又引作出《灵魂志》。《灵魂志》,著者不详,历代志目不收,仅见《御览》此条,疑为他书或即《还冤记》别名,见前,或《御览》传抄误录。
《太平广记》卷322“曹公船”条引作“出《广古今五行记》”。《广古今五行记》,亦作《古今五行记》《古今五行志》,《新唐志》《宋志》作窦维鋈撰,30卷。《御览纲目》收录。《崇文总目》卷8注云“阙”。赵希弁《读书后志》卷2:“《广古今五行志》,三十卷。右窦鋈撰,《唐志》有其目,未详何人。纂五行变异,叙其征应,盖为《洪范》之学者。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类足以推一时之吉凶,星禽、五星、禄命、相术之类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书之类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类足以推一国之吉凶,其所知若有远近之异,而或中或否,不可尽信,则一也,且其说皆本于五行,故同次之为一类。”《御览》所引有隋大业间事迹,疑窦维鋈为唐人,事迹不详。宋后志目不收,且文献征引条目,未出《御览》《太平广记》所引,疑至迟宋中期后不传。
因此条所载为曹操轶事,当流传甚广,疑源自《搜神记》,今本《搜神后记》采录或不当。
《续搜神记》,撰者及卷次不详,疑为干宝《搜神记》之续作,《御览纲目》外不见收录,《御览》征引甚众。从现存诸书引文看,所记人物,可考者大抵为东晋宋初人。又《隋书·经籍志》有《搜神后记》10卷,陶潜撰,今存。陶潜,字渊明,《晋书》《宋书》有传。《搜神后记》中有关王伯阳等传说记载均同于诸书所引《续搜神记》,因此,疑此书即《搜神后记》。《四库全书总目》:“《搜神后记》,十卷,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以干支代之,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隋书·经籍志》著录已称陶潜,则赝撰嫁名,其来已久’”,“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雷车诸事,唐宋词人并递相援引,承用至今。题陶潜撰者固妄,要不可谓非六代遗书也。”有中华书局新辑校本。
四、结语
即《寰宇记》所引诸条,出自《搜神记》者,有卷2襄邑县“鼠怪”、卷14郓城县“韩凭冢”、卷51鄯阳县“马邑城”、卷55安阳县“高亭”、卷70渔阳县“无终山”、卷89丹徒县“高骊山”、卷106分宁县“石侯祠”、卷126庐江县“陵山”、卷128全椒县“丁姑祠”、卷129六安县“岳庙”、卷144随县“断蛇邱”、卷159高要县“鹄奔亭”等12条,以及卷164戎城县采录自《扶南传》一条。又,卷100侯官县“螺江”条,当出自《搜神记》,今本《搜神后记》系误收。卷126合肥县“筝笛浦”一条,《寰宇记》引用时,作出自《续搜神记》,实为《搜神记》,今本《搜神后记》采录此条似不当。卷126合肥县“焦湖庙”出自《幽明录》,《寰宇记》编撰时删削不净,“搜神记”3字衍。共计15条。
上文考辨也揭示《搜神记》资料来源较为广泛,除干宝收集独创者外,就《太平寰宇记》所引用条目来看,疑就有来自《列异传》《列仙传》《太康地记》《说苑》《扶南传》等,可窥一斑。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著述,同类著作,重复内容较多,资料重复使用现象显著,越是晚出之书,这种情况越突出,如“鼠怪”“鹄奔亭”“螺江”等条,可谓典型。这造成后世引书,同一资料,在不同著述中引用出处亦自不同。
古人引书,至少从今天传世本来看,在乐史之前,除经典注释及类书外,大多规范性较差,并没有过多留意资料的出处,明确书名或作者,以随手引用手头所能见到的书为主。自乐史著《寰宇记》后,我们发现,除经典注释与类书外的今传世诸书,虽仍有较多引用不注明出处者,然注明出处之作亦多。从这个角度分析,《寰宇记》也可视作一部划时代的著述。当然,乐史著《寰宇记》目的即在补“贾耽之漏落,吉辅之阙遗”[5]1,为此采用了明确资料来源的办法,我们认为,乐史这种著述模式,应当是受到了经典注释与类书编纂的影响。
《寰宇记》“采摭繁富,惟取赅博”[4]925,所收罗之经籍史志极其丰富,这从引用《搜神记》约略可窥,一方面为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不及;另一方面也补充了正史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的不足,真正做到了作者本人所说“沿波讨源,穷本知末”,使“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5]1。
今考《寰宇记》采录之书,有迹可循者,即不下九百种[1]449–450。这种著述方式,资料来源清晰,一方面增强了《寰宇记》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寰宇记》的内容。其中对于逸闻趣事、古迹传说的收录,增强了可读性,保存了文献,成为后世辑佚的渊薮之一。《搜神记》的引用即其代表,致“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4]925。这种“大变”,对于纯粹地理学的发展,的确有所妨碍,却是符合地方志作为“一方古今总览”[6]的特点的发展方向的。四库馆臣说“《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4]923,确为灼见。
[1] 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449–450.
[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3:315.
[3]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50.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75–1876.
[5]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92.
On the Quotation of GAN Bao'sin YUE Shi's
ZHANG Baojia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is a collec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written by YUE Shi.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GAN Bao. There are 15 titles ofquoted from, one of which is wrong. There are 3 stories ofquoted from(continued). That shows the ancient writers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source. Leshi changed this situation and influenced the writing mode of local chronicles.
;; quotation; source
I206
A
1006–5261(2021)06–0082–10
2021-01-20
张保见(1973―),男,河南信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