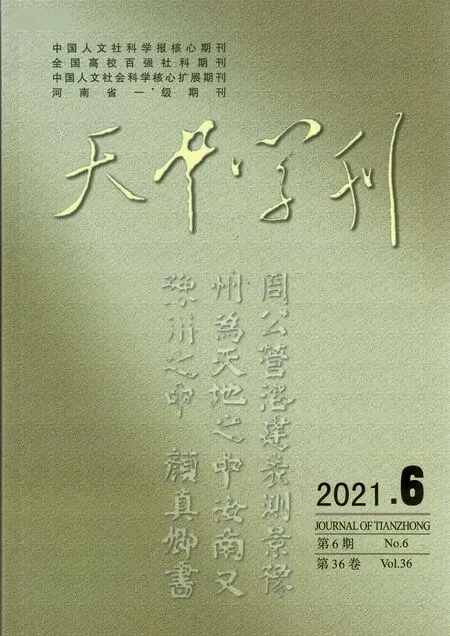生命之歌,生存之歌——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原始歌谣
2021-12-21邓康丽吴广平
邓康丽,吴广平
生命之歌,生存之歌——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原始歌谣
邓康丽a,吴广平b
(湖南科技大学 a. 人文学院;b.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原始歌谣是文学的原初形态,它歌唱着人类最本真的存在与生存,是文学史上最本真的生命之歌和生存之歌。原始歌谣不仅反映了初民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了初民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从自然生态来看,原始歌谣在“咒”与“祝”的交织与统一中展现了初民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对自然的虔诚之心;从社会生态来看,原始歌谣在“自我”与“家园”的和谐与共生中展现了初民率性本真的生命形态和对土地的情感意识。
原始歌谣;生态美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
生态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生发出的存在论美学,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即以一种审美的态度观照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的关系。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曾繁仁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是一种文化态度与立场的问题”[1]102。究其问题的根源,乃是人类对人与自然本源关系的“遗忘与脱离”,最终导致极端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在工具理性和欲望的“促逼”下,逐渐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故此,要找回这种本源关系,保护我们的家园,人类急需建构一种新的适应时代需求的审美取向、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以此来支持相应的一系列观念变革、文化转型和时代风向的改变,这已成为国内外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国际著名生态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自然保护的最终历史基础是美学。”[2]无独有偶,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者也是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将关注聚焦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上,主张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繁仁在《生态美学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原初的审美关系。”[1]4重新发掘这种最基本、最原初的审美关系有助于人类再次把握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同源性,进而找回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对中国原始歌谣进行生态美学解读就是基于此。
中国的原始歌谣是“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3]。因为这种原始性,原始歌谣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本真、最具原生态的作品,其质朴的语言、明快的节奏和直抒胸臆的情感都体现着一种童谣般的真实质地。鲁迅曾对此描述道:“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义而已。声音繁变,浸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4]1这些“自达情义”“任情欢呼”“祗畏颂祝”的原始歌谣,直接体现了初民的心志、情感和生活情状,因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生命之歌、生存之歌。
一、自然生态下“诅咒”与“祝愿”的交织和统一
纵观人类发展史,自然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利用其所生存的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具体条件,形成自己的生产类型和内容”[5]。自然环境的变化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初民的生存和生活,这在初民的歌谣中得到印证。生存环境带来的变化赋予了原始歌谣不同的人文内涵,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欲望下的生命意志,在原始歌谣中体现为诅咒;另一种是诗性思维下的人神对话,在原始歌谣中体现为祝愿。在原始社会时期,“祝”与“咒”同源同体[6]。王力说:“祝愿和诅咒是一件事的两面。《释名·释言语》:‘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善恶之词即兼祝愿和诅咒两面。”[7]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内涵,实则却有着统一的目的,即生存。在原始歌谣中,这两种内涵的交织和统一,生动地展现了自然生态下初民对自然的情感态度。
(一)诅咒——生存欲望下的生命意志
在原始歌谣中,咒语是一种很重要的话语表达方式,同时也是原始巫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原始社会中,咒语往往伴随灾难出现。原始初民在面对不可控的灾害时,认为念咒可以帮助他们支配自然,从而起到消灾解难的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以咒语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巫术要比以敬畏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出现得早,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最早期的咒语未流传下来,所以只能从后期出现的同时包含祝、咒内容的原始歌谣中去探看咒语的面貌和内涵。
在《礼记·郊特牲》中,记载了伊耆氏的《蜡辞》,歌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8]1073《蜡辞》是伊耆氏为了祭神而作的“祝辞”,其除了包含感谢神灵和向神灵祈福的敬畏之意,还包含更为原始更为本真的咒语内容——“祈祷消除地质灾害”“祈祷消除洪水灾害”“祈祷消除动物灾害”“祈祷消除植物灾害”[6]24–29,命令自然环境服从人的意志,进而使人获得生存的机会。从咒语的角度看,歌谣中出现的“土”“水”“昆虫”“草木”四物都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四害”,它们的安和乱直接影响农业的收成。因此,初民使用咒语,是为了影响自然——支配自然现象、调节自然因素,让它们各得其所,恢复正常。
咒语巫术的产生与初民早期的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联。原始初民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尤其在原始社会狩猎时期,不仅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而且要应对毒蛇猛兽的威胁以及不可预测的疾病灾难。初民面临的生存危机,可从一些原始神话传说中窥得一二。《淮南子·览冥篇》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𬊶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9]这些惊天动地的神话传说,折射出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生存世界,置身其中的初民随时可能失去生命。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初民对自然产生强烈的畏惧心理,而同恶劣环境的斗争也让初民感到十分的压抑。正是这种畏惧和压抑促逼着初民穷则思变,于是才有了适宜巫术观念生存的意识土壤。“巫术是原始初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实现自己愿望而形成的信仰。”[10]182可见,咒语巫术的出现与初民生存环境的恶劣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是人面对自然的无力感和自身的生存欲望矛盾交织形成的产物。
求生是生命的本能,生存欲望是生命最基本的欲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要的层次越低,需要的欲望就越大,保证生存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处于原始社会的初民,始终面临自然灾害、饥饿等威胁,徘徊在生死线边缘,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比生存需要还高级的需要。生存欲望成为初民最基本也是最强烈的欲望。在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强烈的生存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初民的斗志,使初民有了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勇气。咒语就是初民与自然灾害斗争时采用的求生手段。载录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逐魃辞》是一首很典型的歌谣体咒语,歌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11]这首歌谣为初民与旱灾做斗争时所作。这里的“神”指天女魃,在神话传说中黄帝与魃一起打败蚩尤,但“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导致大地出现旱灾,因此又被初民称为旱神魃。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初民难以应对旱灾,但又觉得必须解决旱灾问题,这种复杂的情感体现在《逐魃辞》中。《逐魃辞》不仅是祈求,而且是命令,祈求老天普降甘霖,命令旱神魃滚回北方,给旱神魃下驱逐令。初民对“旱神魃”这种命令式的强硬态度,体现了他们直面灾难的勇气,同时也折射出初民心中强烈的生存欲望。
强烈的生存欲望使咒语表现出一种狂热性,狂热之中常呈现与现实不符的情景。《逐魃辞》中的语气不卑不亢,甚至还带着某种颐指气使的傲气。在这种命令之下,自然灾害仿佛变成低人一等的听命于人的事物。《蜡辞》的语句间也透出一种不寻常的安排性口吻,“土”“水”“昆虫”“草木”变成一群需要被人规劝和安置的事物,而人俨然就是它们的管理者。这种“自然渺小”与“人类伟大”的错位和倒置显然不是真正的现实,它是巫术的幻象。然而这种幻象源于人的精神意识,其构成有许多心理因素。李泽厚将巫术概括为“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12]。巫术的幻象就是这些“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对外投射形成的结果,它使初民相信事情会有转机,一切都会变好。从这些心理因素以及其产生的心理效能来看,咒语巫术的内核是充满生命性的。
咒语巫术的生命性主要体现在人的意志力量上,人的意志力量是巫术力量的内核。费尔巴哈在分析巫术的本质时写道:“在这巫术中,人的单纯意志显然就是支配自然的上帝。”[13]初民使用咒语巫术支配农业“四害”、逐旱神魃,本质上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巫术只是一种“替代的行为”[14]72,其本质是人的意志力量的外化和升华。从咒语巫术所起的作用来看,它是“对人的主体性及其力量的巫术式肯定,尽管这种肯定有其盲目、空洞的一面,但仍具有增强人的自信的心理效力”[15]。因此,初民使用咒语去解决问题,虽是一种“近乎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假满足’”[14]74,却并非毫无意义,其意义属于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微观而言,它们“构成了人的主体与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对人类自身力量加以肯定的一个重要环节”[15]51–56;宏观而言,其不屈服于困境、努力生存的顽强生命意志,从人类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说是人类反抗不公命运的初心。因此,作为原始初民的生存之歌,歌谣体咒语绝非虚无滑稽的幻想,它所迸发的勇气和活力,展现了人类如何抵抗巨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努力生存,是人类超强生命意志的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最后咒语可能对现实没有多大作用,但至少它“教会了人相信自己的力量”[16]。
(二)祝愿——诗性思维下的人神对话
从狩猎时期进入原始农耕时期后,出现了为祭祀自然神灵而作的祷辞歌谣。这些歌谣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的媒介,保存了许多上古文化的内容。原始农业生产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初民的生存条件,使初民不再像狩猎采集时期那样为求食而四处奔波,但是农业生产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因而反映在歌谣中,则常常是原始生产者对支配自然的无力,或者作为超自然力加以祈求”[10]30。
在《荀子·大略》中,记载了一首商汤王遭遇旱灾时所做的《祷雨辞》,它虽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但祷辞中仍保留着原始社会时期人对自然灾害的无力感,辞曰: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17]

神灵观念的产生与初民的认识思维有关。在前科学阶段,人类和动物一样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但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率先萌生起来的精神世界又使他们把自然同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19]291,这便是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所言的“原始诗性思维”。原始诗性思维是一种依靠感觉力和想象力来进行的审美思维。维柯在书中如此描述:原始人类“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20]。原始诗性思维的结果就是使初民形成“万物有灵”的认知格局和原始世界观。
进入原始农业时期的初民虽已有隐约的个体意识,但“与自然在感性上依然处于一种相对、相关、相依、相存的期待之中,往昔的那种‘混沌’此时已经化作虚幻中的圆满”[19]293。上文所举伊耆氏《蜡辞》,歌词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要求“土”“水”“昆虫”“草木”回归本位,不要危害农业。在这里,初民显然是把四物当作有灵性的事物,认为它们具有和人一样的感知能力,因此能听懂人的语言。只有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人神对话才得以自然展开和进行。此时,混沌的想象通过泛灵认识得到了“虚幻圆满”的形体。
当面对这些有灵性的自然事物时,初民只有“敬畏、尊奉和对话”[1]144。从《弹歌》到《蜡辞》,再到“葛天氏之乐”,歌谣的内涵由仅限于人的活动范围逐渐发展到更为宏观的天人之际。这种内涵丰富化的具体表现是,歌谣由简单的生活场景描绘发展到富有神学性质的“人神对话”。“人神对话”的实质是单向度的,但其目的却是为了与自然达成一种联结。万物有灵的认知基础使初民相信万事万物背后都潜藏着神灵的力量,初民认为只有与这些神灵达成联结,才能消灾解难、逢凶化吉。
初民通过祭祀仪式来实现与自然的联结,祭祀中出现的歌谣就是人对神灵说的话。“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是伊耆氏对农业神灵说的话。《礼记·郊特牲》有云:“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8]1071《文心雕龙·祝盟》也说:“伊耆始蜡,以祭八神。”[18]109八神就是指与农业有关的神灵。伊耆氏举办“蜡祭”仪式,显然不是单纯的个人活动,而是一个族群对农业之神的虔诚祷告。在另一个更为大型的原始宗教祭祀歌舞“葛天氏之乐”中,初民对自然的这种宗教感情表现得更为全面和强烈。其表演形式与内容为:“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21]288从这段描述可见,葛天氏的祭祀规模、形式显然比伊耆氏的“蜡祭”更大型、更丰富。其八篇原始歌谣虽已失传,但从“载民”到“总禽兽之极”这些歌谣名称来看,都是以祈祷的方式向神灵祈福,歌名的指向也大都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有关。《礼记·乐记》有言:“大乐与天人同和。”这类祭祀歌谣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人对话神,表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奉。
从现代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神对话”包含强烈的原始迷信色彩,是伪科学。但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中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却值得引起深思。
初民对自然的敬畏心理与自然的神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前科学时代,初民缺乏科学知识,对自然现象不了解,自然的变化和力量让他们感到惊奇、震撼。这种感觉投射到原始歌谣中,就成了歌谣里最生动的成分。在初民的认知里,“环绕着人们的生存时空不是无机的、物质的自然,而是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的有机的自然”[22]。初民将这一切解释为“万物有灵”,这种认识观使他们相信自然是伟大的。初民渴望与伟大的自然达成联结,因此以隆重的祭祀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敬畏和虔诚。敬畏自然,本质上是初民向自然显示他们渴望与自然达成联结的虔诚之心。这种虔诚的敬畏在当今这个“祛魅”盛行的世界已变得十分罕见。在过去几百年间,科学理性几乎横扫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原本丰富多样的自然被缩减为单纯的客体,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人们在将这些科学成果变现为人类生活的资源储备后,却被更大的欲望和野心裹挟,日渐遗忘了对自然的敬畏,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无限度的榨取和掠夺。现代人虽不必回到远古那种蒙昧的认识阶段,但是应该对自然保留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海德格尔曾言:“惟当我们把神秘当做神秘来守护,我们才能知道神秘。”[23]25刘小枫也说:“神秘引起的敬畏才是世界意义的保障。”[24]这些富含哲理的话都在表明,自然的神秘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不应为了满足对科技“进步论”的渴望就肆意地人化自然,将自然原本具有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1]39破坏殆尽。自然的神秘包含使世界生生不息运转起来的力量之源,它是世界的根基,人类应对其怀有敬畏之心。
二、社会生态下“自我”与“家园”的和谐与共生
在原始社会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因此这里的社会生态取的是广义的说法,它涵盖了自然生态的范畴,是“社会性的人与其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生态系统”[19]104,即指一种世界性的生态格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其最核心的论题是论述“此在与世界”[25]的“在世关系”,这是对传统“主客关系”的一次超越。从“此在”(人)的生存建构来看,“人之为人”和“世界之为世界”都是和谐共生的。这样的存在论观念在原始歌谣中有相应的对照。然而对照原始歌谣,这种人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却不是意识形态形成的结果,而是生命逻辑与生存逻辑形成的结果。对应“此在与世界”关系的“自我”与“家园”关系是在最本真的生命与生存中体现出来的。
(一)率性本真的自我歌唱
原始歌谣时期是“诗的本真时期”[26]16。本真的诗是“先民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在用直觉感悟、取象类比的方式,融合物我,沟通人神,探寻宇宙奥秘,揭示人生真谛”[26]40。也就是原始诗性智慧的结晶。本真的诗是原始初民自发性创造行为的结果,也是海德格尔所言的“自在行为”的产物,因为“诗的本真”源于“人的本真”。唯有本真的心性才可能创造出具有本真意义的作品。从生命存在论的角度看,本真指一种生命形态或生存状态,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即人在“本己”要素中存在时才能现出的人之“本真能在”[25]307状态。人类生态本性的原初状态便是本真。在一些原始歌谣中,“人的本真”被充分展现出来。
当原始社会迈入原始农业时期,农耕经济自给自足的稳定环境使初民减少了很多生存方面的压力,因而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增添其他方面的生活内容。这一时期一些具有生活气息的原始歌谣已经出现,比如《候人歌》《归妹辞》,这类歌谣呈现出初民细腻而具体的生活情状,极富感染力。
载录于《吕氏春秋·音初篇》的《候人歌》曰:“候人兮猗。”[21]338这首歌谣被誉为“南音之始”,传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21]338从故事背景来看,这是我国最早的思妇歌,歌谣表达了涂山之女对禹的思恋之情。整首歌谣只有4个字,其中前面的“候”“人”是实词,是这首歌谣的思想内容——等候那个人,即等候大禹,后面的“兮”“猗”是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语气助词“啊”。歌者通过前面两个实词非常直接地表明自己的心意,语言的率直体现出情感的纯粹,是“我口唱我心”的典型。后面的虚词,是歌唱者情感激荡而漫延出来的语气助词。《尚书·尧典》载:“歌永言。”永,即延长声音为歌,以声音的长短起伏来表达心意。这些语气助词虽没有实在的内容,却包含着比前者还要充沛的情感和更为复杂的含义,闻一多将其称为“孕而未化的语言”,它们体现着口头文学最原始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原始歌谣属于广义的诗歌,也是最原始的诗歌。诗歌的主要职能是抒情,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7]原始歌谣的抒情,只忠实歌者内心的感受和感情,只在乎歌者情感的宣泄和直抒,这种快意式的表达方式决定了原始歌谣形式上的简单和纯粹。顾颉刚在《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一文中认为原始歌谣和《诗经》之诗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形式。他说:“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28]由此可见,原始歌谣的抒情是重情不重形的,是歌者率性本真的表达,正如鲁迅所言:“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义而已。”[4]1
除了上述所言的“情歌”,这一时期的歌谣还呈现出一些生活细节的场景,比如《周易》“归妹”卦的爻辞,即《归妹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29]193。这是一首反映初民剪羊毛的原始歌谣,歌意是少女用筐接羊毛,蓬松的羊毛显得虚松不实;小伙子用刀割取羊毛,刀刀下去无血。歌词非常朴实简练,有一种一呵而就的浑融感。原始歌谣的特点之一是即兴而发、率性而唱,因此这种浑融感不是由诗意上的雕琢来获取的,并非一种精致美,而是歌者即情即景的吟唱,如摄影师直觉式的抓拍,直觉即是瞬间极致的美。直觉是最直接的感官经验,用克罗齐的美学观点来说,它是人的感官与事物的“第一度”[30]联结,因此避开了思考的雕琢、感受的流转,就是直接地表现或映射对象。这种呈现本身不能作为任何事物的解释或托词,但却不倦地邀请他者去猜测、遐想和思考。《归妹辞》的真就在于它是以直接呈现生活的方式歌颂生活本身,无论是“女承筐,无实”,还是“士刲羊,无血”,都是现实的场景,都是印象的复现,没有其他成分的干预和渗入,因而呈现出一种现实的“无蔽状态”[31],显出生活的本真之境。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本真是生命的根基,亦是生活的根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本真状态的渴望和追求,都是在本真的对立面——“人的沉沦”“人的遮蔽”等非本真的状态中通过反省和思考引发出来的。当人处于非本真状态时,会导致自我疏离和自我异化,本真的自我受到压抑或驱逐,甚至逐渐消失。这对人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是一场巨大的危机。道家美学将本真视为一种至真至纯的生存境界,并希望通过“返璞归真”的方式回到生命自由本真的状态,给生命一个行走的基础。本真状态为何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人最基本的存在形态,犹如大厦的底层建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按照道家美学的阐释,人的本真具有两种内涵:一指“原初的纯真心性”;二指“自然本真的生存态”[32]。这两种内涵在初民的歌谣中都有印证。初民真情、真性的自然流露,呈现的是生命的尽情、尽心和尽性;初民对现实本身的直接歌颂,呈现的是生存的自然、自在和自由。从这些歌谣散发出来的原真美感,便是“原初的纯真心性”和“自然本真的生存态”的真实对照。可见,初民的歌唱自始至终就没有和本真自我剥离。“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大都是壮健的、真挚的、现实的……对于世相,对于自然,对于人生的活动和遭遇,他们有着他们真实的见解和感触。在歌谣里,他们率直地歌咏了它。”[10]178
(二)地利人和的家园意识
海德格尔在论述“存在”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因缘性”,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种独立的存在,任何一种存在都有其他事物的促成和帮衬。可见,存在是关系性的。从“因缘性”的角度看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便会看见人的生命状态会如实反映其置身的生存处境。初民能率性本真地自我歌唱,其背后的环境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人必须活在“本己”要素时才能活得本真,并且这些“本己”要素是由所生存的“家园”提供的,他对此阐释道:“‘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23]15可见,本真自我的存在是一种“在家”的存在,而自我与家园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表面看来的空间关系,它是比之更为深层也更为原始的情感关系。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家园”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存在的所指。对此,海德格尔继续补充道:“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23]15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第一个‘家园’天使”只能存在于人类文明起源的世界,那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在大地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大地”对人类的“赠予”不仅是空间,还有“朗照”。从实际的生存角度来理解“朗照”,它是一切生命需求的供给。但“朗照”不止于生存意义。
“朗照”还预示着另一种大地与人类的联结。在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歌舞——“葛天氏之乐”中,第一首歌谣就是《载民》,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载民》是一首用来“祀地”的歌谣,杨荫浏将其解释为“歌颂负载人民的地面”[33]。将“载”解释为“负载”,其实是一种很表面的解释,《载民》所蕴含的意义绝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负载”。这可以从一些敬奉土地的祭祀仪式中得到印证。“社祭”是从仰韶时代流传下来的土地祭祀形式,是古代很重要的一种祭祀。《公羊传》卷八记何休注说:“社者,土地之主;祭者,报德也。生万物,居万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以祭之。”[34]在这里,对“社”(即土地神)的“报德”有“生万物”和“居万民”两个明确的指向,其中“居”是以“生”为前提的。“居”是“载”的表层义,即“负载”,但“生”却是“载”的深层义和本根义。“生”在《周易·坤卦》中被概括为一种“含万物而化光”的地母品德。《周易·坤卦》有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29]13这种地母品德昭示着土地于初民而言是万物生命的母体,是孕育万物的“生生”之源。而这种母体的“含”和“化”展现的正是一种无私的“朗照”。由此可见,“载”不只是一种初民与土地的空间联结,更是一种“原始的此在与世界浑然一体的关系”[1]67联结。“葛天氏之乐”选择将《载民》放在第一阕,是源于一种生命本能,因为把土地放在第一位,即是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在初民眼中,土地与生命之间是一种亲缘共生的关系。
从本质上而言,初民的地母崇拜“在于确认人与周围环境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35],这可以说是原始初民“土生土长”出来的“土地伦理”。从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民族先天就有一份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这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群体特性,也是农耕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传统。与西方那种通过形而上思索得出来的“家园意识”不同,农耕民族的“家园意识”更像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自觉,是从我们先民开始选择在这片土地安居落户时就已经有的。这片土地的广袤和丰饶给了初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扎根土地的生活才真正使初民得到一种家园般的归属感。
在反映上古时期社会风貌的歌谣《击壤歌》中,初民将这份归属感表现得十分直接和强烈。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①歌谣极简的语言、明快的节奏和高度凝练的画面立刻把读者带入一种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中。在这里,人们过着安居乐业、清贫自守和与世无争的生活。初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息顺应自然规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饮食取之自然(土地);最后一句“帝力何有于我哉?”将歌谣的核心义以反问的句式和语气道出,强烈地表达了初民对这片土地家园和这种生活的热爱。从这首歌谣可以看到,简单的田园生活不仅没有让初民感到枯燥乏味,相反还使之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怎么形成的呢?一是土地之“赠予”让初民对土地产生深深的依赖和感激之情,这是从土地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二是初民积极主动的生存建构,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中可以看出初民的生存、生活都与土地息息相关,从生存资源到生活安排,土地占据了初民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说初民依赖土地而生。但是,这种依赖不是不劳而获的寄生,它需要人付出努力才能获取。这个过程就是歌谣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实际内容。然而,正是因为这个过程,初民才从中获得一种自食其力的充实感,找到一种切实的存在感。这些充实感和存在感其实就是促成归属感的重要渊薮。
由此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家园意识是一种地利人和的结果。土地的“赠予”和初民的生存建构这两股力量的交织和相互回馈,构成了“自我”与“家园”的和谐与共生。“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在这种情感维度和生存维度中得到维护和巩固。
对原始歌谣的生态美学解读属于生态文学研究中“回溯性的挖掘”[36]。它是站在“回归”的角度去展开的,并希望能通过这种参照“原点”的方式对现代的生态文明建构提供一些思考。原始歌谣不仅反映了初民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了初民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这才是生命之歌和生存之歌的真正含义。“本真的诗、艺术之所以重要,即是在其揭蔽中保藏了存在涌现的机缘、天命及原初经验。”[1]75从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角度来透视这些生命之歌和生存之歌,有助于了解最为本真、自然的存在与生存,有助于发掘生命本真的美学。
① 此歌谣首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感虚篇》(陈蒲清点校,岳麓书社1991年版),本作“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见魏征《群书治要》卷十一引《帝王世纪》,沈锡麟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将此歌谣最后一句“尧何等力”改为“帝力何有于我哉”,并删掉了首句的“吾”字,成为此歌谣通行的版本,流传至今。
[1]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柏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M].刘悦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51.
[3]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先秦诗鉴赏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925.
[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 李学智.唯物史观与“地理环境决定论”[J].世界历史,1995(3):116–120.
[6] 吴广平.一首远古先民消灾祈福的巫咒歌谣:《蜡辞》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文化学刊,2008(4):24–29.
[7] 王力.同源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9.
[8] 礼记正义:中册[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仕,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刘安.淮南子[M].马庆洲,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93.
[10] 蔚家麟,鄢维新,朱蓓.歌谣研究资料选[G].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182–183.
[11] 袁珂.山海经校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86.
[12]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2.
[13]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王太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5.
[14]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5] 苏荟敏.咒语的文化心理功能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1–56.
[16]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19.
[17] 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6.
[18] 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0] 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61–162.
[21]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 张树国.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
[23]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4]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6.
[2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1–260.
[26] 陈一平.先秦古诗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7] 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第1册[M].龚抗云,李传书,等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91.
[29]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0] 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3.
[31]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82.
[32] 李天道,唐君红.中国美学之本真生存意识及其自由精神[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72–77.
[3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6.
[34] 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M].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00.
[35] 张树国.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祀歌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36] 高旭国.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四种模式[J].中州学刊,2009(6):231–236.
A Song of life, A Song of Survival——Primitive Ballads in the Ligh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DENG Kangli, WU Guang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Primitive ballads are the original form of literature singing for the most authentic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tent and state of ancient life, but also the wisdom of survival. In the light of nature ecology, they show the primitive people tenacious will of life and their devotion to nature in the interweaving of “curse” and “wish”. In the light of social ecology, they show the ancestors natural living forms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to the land in the harmony and symbiosis of “self” and “home”.
primitive ballads; ecological wisdom; nature ecology; social ecology
I206.2
A
1006–5261(2021)06–0092–10
2021-05-12
2020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1011)
邓康丽(1995―),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吴广平(1962―),男,湖南汨罗人,教授。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