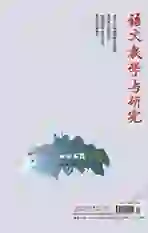鲁迅文章中的“民俗大观”
2021-01-03韩清芳
我国历史悠久,民俗事项丰富,很多作家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时,都喜欢汲取民俗文化的营养,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作为我国文化界的旗手,鲁迅先生对于传统文化虽然带有批判性,但并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继承与发扬。在鲁迅的众多文章中,对于民俗现象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与渲染,当然这种文学创作习惯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鲁迅将个人对民俗的兴趣融入到自己的文章之中,并通过写作技巧和语言不断的丰富其内涵,生成了自我独特的民俗观念,成为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民俗兴趣的内外切入
首先,作为内在驱动力,鲁迅童年生活经历为民俗积淀提供了极大帮助,这散见于其文章中的民俗现象诸如婚礼、丧葬、服饰、饮食以及鬼神巫术等。绍兴作为鲁迅的故乡,本就是浓郁民俗的代名词,例如鲁迅幼年时便形成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式的由酸及甜的未来规划,即家人给其尝的醋、盐、黄莲、钓藤、糖,为鲁迅的民俗观形成了初步的感性经验。及至成年,这种感性知识逐步外延、扩展,从对古籍、民间故事和野史的搜集到自觉阅览以汲取更为丰富的民俗知识,从参与民俗活动具体事项到因具体作品的民俗元素摄入,鲁迅的民俗兴趣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体的理性思考。正如他在理顺民俗文化与国民精神形成的关系中所言,“倘不深入研究民众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并立存废标准,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被习惯的岩石压碎”。这就是鲁迅从感性经验到理性思想启蒙,从兴趣激发到主体自觉民俗观形成之缘起。
其次,作为外在驱动力,正如刘玉凯先生所言,“夸张一点说,五四时差不多所有文化人都曾注意过民俗学问题”;也如钟敬文先生所讲,“古代学人对民俗的重视自古而然”中,这便是“五四”时代的文艺与民俗之风。与时代其他学者相同,鲁迅零散、破碎的历史经验也将国民精神的缺失归咎于传统陋习和封建愚昧,这是基于“五四”时期民族内忧外患的背景以及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即为实现民族自强和国民的精神觉醒,必须要对粗陋的传统文化加以革新。这与钟敬文先生所言的“具有爱国思想和受过近现代西洋文化洗礼的那些从事新文化活动的学者们,大都比较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要振兴中国必须改造人民的素质和传统文化”不谋而合。因此,作为以国民精神自省为写作规范的鲁迅,揭示民族和民众的通病必然通过“批判”作为其写作的重要趋向。
再次,通过对民俗事项的“罗列”,将旧社会病根得以暴露并医治是鲁迅进行思想启蒙和改良人生的重要目的,这也是作为文人的艺术自觉。因此,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分析触角在正统文化与民俗文化杂糅中得以体现。在国民精神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方面,鲁迅既揭示了两者的依存关系,更对精神自省和文化重建置于列宁意义上的“泛文化论”,即“真正的革命者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列宁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倘不将这些改革,则革命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因此,在顺应时代文化改革潮流的同时,鲁迅既能顺乎时代的呼唤,也能通过主体自觉明确自己的写作规范,将民俗文化感性经验的积淀升华更为理性的审视、批判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鲁迅民俗语言的魅力
鲁迅的民俗文化感性经验既有对“我”儿时故乡的怀旧,也有对传统文化因袭的厌恶,这也就导致了在其作品中既有田园般宁静的对《社戏》和《故乡》故土环境的描述,也有如《药》和《孔乙己》中对传统陋习的批判。
鲁迅幼年时期的孩童记忆诸如看社戏、烤罗汉豆、捉鱼虾等,故乡的街坊小巷、桥梁舟楫等诗情画意的水乡风俗,都是其“思乡的蛊惑”。因此,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回忆是鲁迅作品的重要素材。例如,在《社戏》中的情感,“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归省了”。再如,“只要有出嫁的女儿,如果尚未当家,夏日来临时便可以回到娘家避暑”,“我便可以跟随母亲一起到外祖母家住上几日,在那里我可以受到很好的待遇,而且不用去念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外祖母还允许我和其他的玩伴们一起去看至今都很是留恋的社戏”,“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再看《祝福》开篇中鲁迅对环境描写的处理,“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另外,《故乡》开篇同样怀旧,“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幾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鲁迅通过对细节处理的白描式晕染,增强了作品美感的同时,也将“在场感”处理得恰当好处。
当然,鲁迅的“时时反顾”,更多、更深的层面还是通过对故乡民俗事项的回忆,以更为活跃的、理性的态度分析当时国民性精神的形成,即封建陋习和粗鄙民俗文化对国民精神的荼毒,这也是鲁迅对民俗文化与国民精神形成关系的重要见解。例如在《药》中,夏四奶奶给夏瑜扫墓,鲁迅的描述是,“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刻画上,鲁迅将民俗事项和民俗文化作为利器,国民精神中的愚昧无知和夏瑜的英勇不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鲁迅民俗观的内涵
首先,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对民俗文化的概念产生是受制于西方学术潮流,尤其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对民俗文化是“过去的遗存”和“旧的经验和习惯”等的民俗学考古定论,例如《汤祷篇》和《发须爪》。与之相对应的是,鲁迅将民俗文化与社会批评相关联,将民俗文化与国民精神相互投射,以得出民俗文化内化、引导国民性行为的结论。换句话说,民俗文化是内化了的民众生活的本来。因此,以民俗为切入点,鲁迅用笔锋犀利揭示、反思国民精神愚钝、国民生活困苦以及民族落后的缘由。这是在民俗学概念方面鲁迅之于民俗所作出的前沿性、历史性和价值性判断。
其次,从更深层角度来讲,民俗文化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民众精神。这就牵涉到民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杂糅问题。鲁迅认为,民俗即人俗,是国民作为精神娱乐的重要形式,而不是一味对民俗文化施行一刀切。这在鲁迅看来是纠枉过正,是错误的,尤其是他将笔定格于民俗文化和国民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后。同时,随着鲁迅对民俗文化概念和国民精神的进一步认识,他意识到官方文化长期的干预导致了民俗文化与官方文化的杂糅性或一致性,即民俗文化的集体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认识到民俗文化之于民众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靠强制手段就能解决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一座“无形的图圈”,而且“人人如此”。以至于个体对传统文化的“叛离”是对社会整体观念和意识的挑战书。也就是说,“变异”了的民俗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在时空上影响了国民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正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一致性导致的直接结果。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故乡》中闰土的银项圈及对后代产生影响的指向性意义,也能够理解《祝福》中的样林嫂因为嫁了两次而都死了丈夫被认为是不洁的意义,更能够清楚《社戏中》“归省”的含义了。因此,在传统文化与国民精神疾病之间的紧密关系中,鲁迅发出了“历史是多么的相似”以及“现在的年轻人,竟如久远的古人一样苍老”的感叹。这也是鲁迅的文章之所以能够让人振聋发馈的原因——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评论,其面对具体民俗文化事项时的心理分析,是其挖掘到本质的根本原因。
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旗手,鲁迅与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这种决裂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和唾弃,而是一种扬弃,对于好的优秀的文化进行吸收,批判糟粕。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观念是鲜明的,在《社戏》《药》等文章中对于民俗文化进行了精彩的择取与描绘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为当前民俗文化的警惕传承提供了借鉴。以民俗為切入点,鲁迅用笔锋犀利揭示、反思国民精神愚钝、国民生活困苦以及民族落后的缘由,这是在民俗学概念方面鲁迅之于民俗所作出的前沿性、历史性和价值性判断。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鲁迅民俗观论析[J].张春茂.民俗研究.2017(06).
[3]试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J].王靖宇.今古文创.2021(03).
韩清芳,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昌化初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