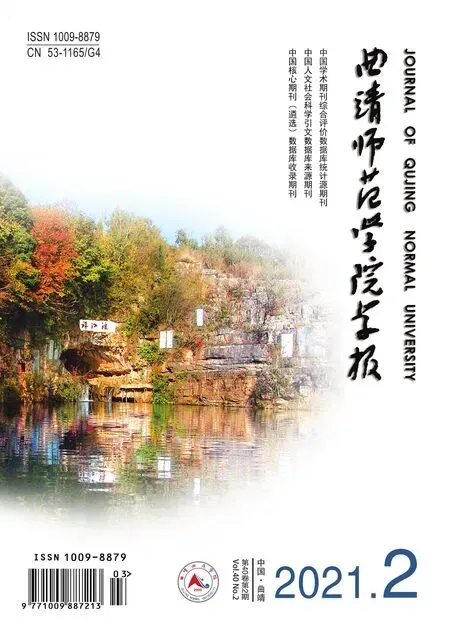曲靖布依族生态意识的缘起及哲学意蕴
2021-01-02代春燕
代春燕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原始生态意识”是指少数民族先民在探求人与天地万物的起源过程中产生的对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和心理活动,正是这些思考和心理活动以神话、古歌及风俗禁忌等形式流传下来,久而久之就演化成了少数民族的生态意识。
在云南省曲靖市生活着大约3万布依族居民,占曲靖市总人口比重的0.51%左右,主要集中在罗平县多依河畔及八大河畔的长底布依族乡、鲁布革乡,是云南省布依族最为集中的一个县。在曲靖市富源县也生活着部分布依族居民,主要分布在富源县的中安镇和富村镇。追寻曲靖市布依族发展演变的历史画卷,我们会发现始终有原始生态意识贯穿其中。这是因为布依族先民普遍相信,天地万物与人的生产生活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总是会在某种力量或者物质的推动下而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所以曲靖布依族常常沿着天地万物及人类生产生活演化发展的路径去解答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关系,去解答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秘密,这便是布依族生态意识的雏形。
一、曲靖布依族生态意识之体现
在少数民族先民探寻人类世界奥秘的过程中,神话与古歌、自然崇拜以及传统生活习俗是少数民族先民生态意识的重要载体。它们是自然生态观产生的温床,是少数民族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也是少数民族先民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布依族的神话与古歌、自然崇拜以及传统生活习俗可以探寻曲靖布依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一)曲靖布依族创世神话与古歌中体现出的生态意识
布依族的创世神话与古歌是布依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思考,生动的反映了天地、万物及人类的起源。透过这些神话与古歌,可以反映出布依族先民的生态价值观。在布依族先民看来,人与自然万物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它们同根同源、共融共生,所以应该被同等对待。
在布依族神话《力戛撑天》里面就把世间万物的产生归功于具有神力的巨人力戛用身体的各个器官来化生万物。“大肠变成红水河(南盘江),小肠变花江河(北盘江),心变成了鱼塘,口变成水井,膝头和手腕变成了山坡,骨骼变石头,头发变成树林,眉毛变成茅草,耳朵变成花,肉变成田坝,筋脉变成大路,脚趾变成各种野兽,手指变成各种飞鸟,身上的虱子变成牛,跳蚤变成马。”[1]
《造万物歌》是曲靖布依族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韵律体古歌,依据《造万物歌》的颂唱,世间万物的产生都是布依族的英雄祖先“布灵”所创造的。而歌词中同样唱到的是布灵用自己的身体创造了万物,而且还用自己的汗毛创造了最初的人类。
在布依族民间,老人们还经常会给下一辈讲树枝变人的故事。据说最早的时候,地上是没有人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雾气,后来天上的神仙到地上来玩,看到地上太冷清,便用树枝砍成人的样子,然后朝小木人吹一口仙气,小木人便活了,这样地上才有了人烟。
不管是力戛还是布灵,又或是老人们讲的树枝变人的故事,其实都反映出在布依族先民心目中,神、人、自然以及万物间是具有同一性的,它们相互联系、紧密共存,共荣共生并且还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布依族人民更加珍爱自然。
(二)曲靖布依族自然崇拜中体现出的生态意识
自然崇拜是少数民族群体中共有的一种文化符号,曲靖市布依族人民的传统生活中同样充斥着丰富的自然崇拜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对山神、树神、水神与火神的崇拜。
在布依族先民看来,万物皆是由专门的神来掌管的。山是由山神掌管,水是由水神掌管,树也是由树神来掌管,火也有火神掌管……人类要想从自然万物中获取生活所需,就得遵循各路神的规矩,就得敬重和保护各神,这样人才不会受到神的惩罚,才能幸福安康,由此产生了布依族对山神、树神、水神与火神等的崇拜。这种对山神、树神、水神与火神等自然的崇拜实则说明布依族对自然万物是存有敬畏之心的,这正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必须具备的一种态度。
对山神、树神、水神的重视和保护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神山、神树及水井的敬重与保护上。曲靖罗平地区,布依族生活的村寨多是山清水秀之地,他们喜欢依山傍水而居,村寨附近总是会有一片被赋予神秘色彩的树林或一座茂密的山头被称作神山,每当祭祀的日子,布依族的男女老少都会盛装打扮、带上供品前往神山跪拜山神。而每一个布依族村寨子周围都会有一棵茂盛的古树被称为神树,树枝上面总是会悬挂着一些红布条,那是布依族村民祈求树神保佑而做的标记。
对待神山和神树一定是要格外敬重的,于是产生了很多关于神山神树的禁忌。如孩子们不得随意去神山树林间打闹,不得随意砍伐神山的树木及神树的枝条,不得在神山周围或神树底下说污秽的话语,不得在神山或神树周围大小便等等,否则便会招来神灵的惩罚,甚至全村的人都会跟着遭殃。
曲靖布依族对火神也是格外尊敬的。例如布依族的长者总是会告诫年轻人或小孩闲暇时不得随意玩火,日常生活中火塘上的三角架等物也要格外注意不能用脚踩踏,行走时不得从火塘上跨过去,否则便是对火神的冒犯。
曲靖布依族对水神的的敬重则主要体现在对水井的保护上。“不可以往水井中吐口水,在水井附近不允许大小便,任何人都必须保护水井的干净卫生,大年初一不能到井边挑水,初二清早举行‘祭井’后方能取水,否则就会得罪井神”。[2]
布依族先民这种对自然的崇拜之情,慢慢演变为布依族生活中一些风俗习惯,甚至是不成文的村规、寨规和禁忌,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得曲靖布依族聚居的地区植被良好、和谐宜居。
(三)曲靖布依族传统生活习俗中体现出的生态意识
竹子在曲靖布依族人民的传统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簇簇、一丛丛,总是给外来者一些特殊的印象和美感。竹林边上悠悠远去的清澈小溪,两三个身着蓝布衫的布依族村民在田间劳作,创造出一副自然和谐的田园诗画景致。
曲靖布依族生活的村寨周围之所以竹林茂盛,一是因为这里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宜竹子的生长,二是因为布依族居民对竹子是格外钟爱的。在布依族看来,竹子之所以生命力极强,总是能旺盛生长且生生不息,这是因为竹子里面住着竹魂,竹魂有着繁衍生息的超能力。如果人类敬重竹魂、亲近竹魂,那么这种超能力便会传递给人类,能确保人类也能永不停息的繁衍生息,使人口兴旺的同时还能去病驱邪。所以当有孩子刚出生时,布依族人家就会在房前屋后载种一丛竹子来保佑孩子健康长大,长命百岁。如果是人丁单少、婚后不孕的家庭也会种一蓬竹子让竹魂来保佑家中人丁兴旺、早生贵子。
布依族对自然的热爱与崇尚还体现在布依族的传统服饰、传统饮食等生活方面。布依族的传统服饰以蓝黑青白为主色调,男子多穿对襟短衣和长裤。妇女的服饰则由大襟短衣和长裤构成,或者大襟短衣和颜色鲜艳的百褶裙构成。不管是对襟衣还是百褶裙,都是用布依族妇女自纺、自织、自染、自绣的布料缝制而成,制作采用的棉布是布依族妇女用植物的纤维制作成线以后纺成,各色的蜡染布所用的蜡染颜料则是从各种植物中提取而成,如各种蓝色是用"蓼蓝草"浸泡过滤制成染料染制而成。青布则是用"蓼蓝草"制成的染料先将布上色,然后再放入野糖梨树皮和红籽刺皮熬成的水汁中继续浸染三次而成。
糯食是布依族最为喜欢的一种食物,他们用糯米做成五颜六色的花糯米,做成拌着锅烟灰的糯米粽子,还有把糯米磨成粉后做成粽叶包裹的粽粑、糯米汤圆等食物。之所以喜爱,是因为布依族先民认为谷魂藏于糯谷之中,多吃糯食便可得到谷魂的庇佑。
由此可以看出,布依族先民的生活所需均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所以他们更加热爱自然,更懂得善待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道理,他们总是能在索取与保护中寻找到平衡点,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曲靖布依族先民生态意识的缘起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从意识的起源看,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意识的本质来看,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曲靖布依族先民生态意识的产生也是与他们生活的物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依族先民的生态意识是布依族的族群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布依族先民认识、征服、祈求自然的需求而不断产生的,它来源于少数民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直接经验。
(一)生态意识是伴随着曲靖布依族先民认识、征服、祈求自然的需求而产生的
曲靖布依族的传统生态意识是布依族先民在思考感悟人与自然关系时逐步形成并演化出现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由于布依族先民对自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通常是将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当看到一些自然现象出现时,他们往往会以为人类自己也有唤起和创造这些现象的可能;同时又时常把仅为人所具有的能力广泛地赋予到自然界的物体上,这就引发了对人类及万物起源的思考,就出现了神人祖先用身体化万物之说。
随着布依族先民群居生活的发展以及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布依族先民们开始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当看到一些自然现象出现时,布依族先民发现有些自然现象是对人类有帮助的,而有些则会给人类造成困苦甚至灾难。于是他们开始总结和思考,辨别哪些自然现象对人类有益?哪些对人类有害?人类的哪些行为能诱发对人类有益的自然现象?哪些人类行为又会招致对人类有害的自然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总结和思考中,曲靖布依族先民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而无助的,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
根据自己对自然的认识、改造甚至征服和祈求的经验,布依族先民们便利用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和智慧,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古歌及风俗禁忌的版本并通过各种形式流传下来,久而久之就演化出布依族生产生活的各种禁忌及对神山、神树等自然物的崇拜,这就是布依族生态意识的雏形。因此,少数民族先民企图认识自然并顺应自然、祈求自然的需求是原始生态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
(二)曲靖布依族生态意识来源于布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
少数民族先民对天地万物、人类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民俗起源思考,通常都来源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受到的启发,而他们试图探索天地万物、人类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民俗起源时,也都是采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经常接触到的具体物质来描述。
例如当他们在利用火来取暖、烧烤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思考最初的火是怎么来的?或者火种是怎么起源的问题。而当一个偶然的机会天上打雷闪电引发野火时,思维发展程度还不高的原始先民们就从此事受到了启发,以为火种是火神赐予或创造的,认为火神有种无以伦比的超能力,只有敬重了火神、顺从了火神的意愿才能得到火神给人类赐予的火种,否则便会惹怒火神招致火神惩罚。这便产生了对火神的崇拜。
关于谷种起源的思考也是一样,当少数民族先民以稻谷作为充饥的食物时,也许他们就会想谷种是怎样来的?而当看到飞鸟啄食谷子,老鼠等动物偷吃谷子时,他们便想象谷种的由来大概与这些飞鸟、动物有关,所以在布依族古歌中还有黄狗带来谷种之说,因此每年的七八月份曲靖布依族居民都会过一个传统节日“新米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煮上刚收割的新米庆祝。为了感激和纪念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狗,要先把香喷喷的米饭喂给狗吃,以感激狗的祖先给人类带来谷种并祈求来年丰收。这便催生了布依族人民对动物的保护意识。
还比如布依族古歌《造万物·造棉》中就记录了布依族先民们布匹织物的来源。“山上有种花,叶子真大张,叶片圆又大,真像大巴掌……拿花慢慢捻,细细丝又长,结实不易断,好比蜘蛛网。”“大家快去拣,拣来野花花,姑娘就捻线,线子挽成团,就把布来编。”[3]这些唱词反映了布依族人民认为美好生活是靠自然馈赠而来,体现了布依人民对自然的依赖,也说明布依族先民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是来源于布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
三、曲靖布依族原始生态意识的哲学意蕴
哲学是什么?简单的说,哲学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和智慧,是人类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从其来源上看,它是萌芽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原始意识。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在当下需要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该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的大背景下,中国哲学正以深邃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引领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走向。中国哲学以《易经》为经典,以孔孟之说为代表,其基本观点中最为核心的是“天人合一”的基本宇宙观和“阴阳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布依族先民的生态意识中同样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基本宇宙观和“阴阳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这又为曲靖布依族原始生态意识增添了一些哲学魅力。
(一)曲靖布依族原始生态意识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神话与古歌可以说是哲学的“史前史”,它体现出的是一种“诗性”的创造性智慧。通过曲靖布依族先民在神话与古歌中体现出的诗性智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为精华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子。
在布依族先民那里,对万物本原的思考是有各种版本的,但不管是什么版本都有个共同点,即都认为世界万物的产生是由某种共同的本原作用的结果,这种本原要么是一种具体的无生命的物质状态,比如树枝、树叶、花、泥土等,要么是有神力的英雄巨人的躯体。
其实在布依族的史诗中还有一种把万物本原归结于一个共同的本原“气”的说法,如“很古很古那时候,世界只有青青气,凡尘只有浊浊气……”[4]正是英雄巨人用这些青青气和浊浊气创造出了人类及万物。
布依族神话中关于天地、人类及万物的起源,最为典型的还是创造出了力戛、盘果、布灵等有神力的巨人,他们凭一己之力劈开了天地、撑起了天地,然后用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幻化成世间万物。这样的诗性智慧正好反映出布依族先民把神、人、自然以及万物相互联系、紧密共存,合二为一的思想。
曲靖布依族中的一些风俗禁忌也反映了布依族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布依族人民喜欢栽种竹子是因为竹魂繁衍生息的超能力能够赋予给人类,使人类能够人丁兴旺。布依族偏爱糯谷食物是因为谷魂可以保佑人类身体康健。而且在布依族神话中还记录了当远古的人类没有谷种的时候,是狗帮助人类找回了谷种,还唤回了谷魂或者谷神,从而使人类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这些都说明在布依族看来,人与自然万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的。
(二)曲靖布依族原始生态意识中“阴阳对立转化”的辩证思维
“阴”与“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这对概念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和阳是推动事物产生、变化、繁盛、衰退的最根本动力,是一对矛盾体。“阴阳观”包含了三个基本方面,即:阴和阳是相互对立的,阴和阳又是统一在一起的,阴和阳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阴阳观”认为万物的发展都是矛盾的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万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就需要寻求对立双方的平衡统一。《易传》中说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一体两面,彼此互藏,相感替换,“不可执一而定象”。这便是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
在曲靖布依族先民的原始生态意识中,“阴阳对立转化”的辩证思维已经开始萌芽,布依族先民也朦胧地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阴与阳对立统一作用的结果。如布依族的古歌《赛胡细妹造人烟》中就说到人类得罪了雷神,所以洪水泛滥,世上的凡人都被淹死了,最后只剩下赛胡和细妹两兄妹,为了人类繁衍,赛胡和细妹只好兄妹成婚,才使人间再次有了人类。在这则古歌中实际上是把兄长赛胡视为阳,细妹视为阴,正是阴与阳的结合才再次产生了人类,这正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写照。
还比如曲靖布依族民间流传着太阳和月亮来历的故事,故事的大致情节是:从前天上是没有太阳和月亮的,大地是一片漆黑的,后来一对布依族夫妻将自己的眼珠挖下来,丈夫的眼珠飞上了天空变成了太阳,妻子的眼珠飞上天空变成了月亮,这样大地才有了光明。这则故事中,丈夫为“阳”、妻子为“阴”,太阳为“阳”,月亮为“阴”,正是阴与阳的结合产生了新的阴和阳。
在曲靖布依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禁忌中也处处体现着阴阳转化、对立统一的思想。阴阳转化与对立统一其实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布依族先民之所以对山神、树神、水神及火神等敬畏与崇拜,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是个矛盾统一体,它们的超能力既可以护佑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护佑与惩罚是一对矛盾,但在某些情况下护佑与惩罚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转换的条件便是你对待神是用“阴”的态度还是“阳”的态度,就看人类是否尊敬、顺从神的旨意。这种趋利避害的智慧在曲靖布依族生活禁忌中是处处体现的。由此可见,“阴阳对立转化”的辩证思维在布依族生态意识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曲靖布依族先民的生态意识中体现出了丰富的哲学意蕴,它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也是做出了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