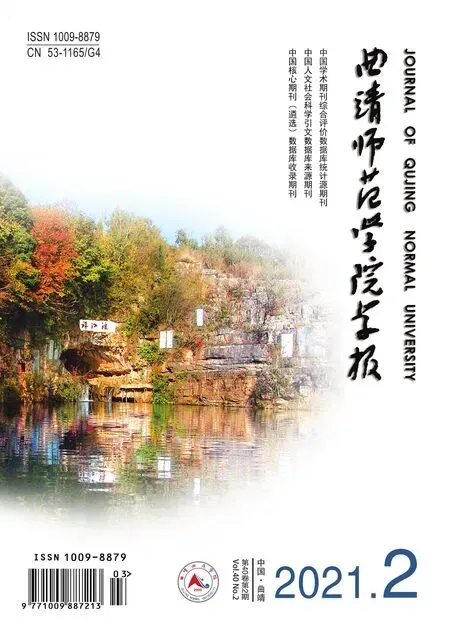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建构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探究
2021-06-21李剑
李 剑
(曲靖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为谋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共赢而提出的极具“中国智慧”的新发展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智慧大国的鲜明形象。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枢纽,地缘空间区位特殊,农业在该区域国民经济成分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分布着众多跨境而居的族群,民族文化渊源十分紧密,这对于推进该区域的农业合作发展具有先天性优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面对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形势,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提出的充分彰显文化自信的价值理念,是为全球解决共同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治国理政时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价值理念目标内涵就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内含的“天下”情怀、“以和为贵”的邦邻之道以及“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是“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新时代深层次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寻求国家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把握人类利益公约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奋斗精神”[1]。“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是要消除文化差异,而是要存异求同,更加尊重文化多元化,以促进相互交流学习来不断继承和弘扬各自文化特点,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最佳状态。其内涵逻辑合理性符合共生性原理,根源于全球化尤其是信息化形势下问题发生、传播与危害的共同性和联系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在认识论层面具有逻辑契合。民族本身也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地理地域、经济生活、语言习俗、心理等因素而结合起来的稳定共同体,其逻辑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契合。因此,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国家层面的合作概念,也可以通过民族关系纽带有效消除合作中的障碍和隔阂,大力推进国家间全方位合作,最终实现人类共赢。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则是这种以民族关系纽带推进中缅合作的良好示范区域。中缅经济走廊则是中缅两国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无疑是影响两国全面推进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关系的示范区域。
“跨境民族”特指居住在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境线两侧的这一特殊群体[2]。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特指在分布在中缅两国国境线两侧的特殊族群的聚居区。从行政区域看,中缅跨境民族地区覆盖中国云南的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6个州市,西藏的林芝市以及缅甸的克钦邦和掸邦两市,两国接壤边境线长达2185公里,藏缅段长188公里,滇缅段长1997公里。从民族构成看,根据相关统计,该地区居住着汉、彝、景颇、傣、布朗、傈僳、拉祜、独龙、哈尼、门巴、回等约16个跨境民族。中缅两国跨境民族成分多、人口数量大、分布地域广。跨境民族对于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中缅两国正常交往,对我国在新时代打造沿边开放新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地理区位特点,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是云南辐射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之地。加强我国与缅甸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与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所内含的跨境民族成员的认同意识、感情纽带、文化同源、文化相近、习俗相似等理念具有高度吻合性,中缅跨境民族在增进民心相通和睦邻友好、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促进中缅边境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价值。各国休戚相关的命运关系充分表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民族、生态、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因此,需要分领域、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等详细规划、因地制宜。
二、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概况与问题归纳
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涉及缅甸2个地市以及我国云南和西藏的7个地市,该地区均属于两国众多民族聚居区、农业经济成分占比较重的欠发达边境地区。农业经济在该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对该区域社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在缅甸的国民经济构成中,农林牧渔业是基础和支柱产业。缅甸具有发展热带农业的先天性自然地理优势。根据缅甸计划财务部统计,2016-2017财年,农业生产总值占比为25.5%,2019-2020财年,缅甸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农业占比21.5%。掸邦位于缅甸东部内陆高原区域,是缅甸重要农业重镇,农业是其主要经济资源。根据掸邦农业部统计,掸邦有230万公顷可耕地,尚有80万公顷耕地未被使用,净播种面积达165.46万公顷,农田开发程度仅为105.1‰。掸邦大多数人口以农业为主,水稻是最主要农作物,蔬菜出产率占全国的60%。缅甸目前正在努力在掸邦北部建立中缅经济区和其他经济走廊,其农产品出口至亚洲、北美洲以及欧洲地区。克钦邦是缅甸北部自治邦,农业也是主要经济来源,农业资源丰富。可种植农田面积达100万英亩,种植面积达57万英亩,可开垦荒地达485万英亩,林业区面积达29万英亩。净播种面积为22.16万公顷,农田开发率只有25.2‰。农作物种类多样,以水稻、玉米、豆类、油作物、甘蔗、水果、咖啡、茶叶等为主。此外,克钦邦橡胶出口量在缅甸国内占据第二位。
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国内段中,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良好。根据各州市相关统计公报整理,林芝、西双版纳、临沧、普洱、怒江、保山、德宏7州市在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在农林牧渔服务业方面,林芝市产值为0.49亿元,增率5.2%;西双版纳为10.68亿元,增率6.3%;临沧为5.98亿元,增率8.1%;普洱为7.62亿元,增率4.1%;保山为4.3亿元,增率6.7%;怒江为2.03亿元,增率3.8%;德宏为4.11亿元,增率6.6%。
此外,在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两项指标上,国内7州市数据为:林芝为2.29万公顷和8.4万吨;西双版纳为;临沧为28.8万公顷和102.67万吨;普洱为34.2万公顷和118.32万吨;保山为145.61万吨;怒江为8.13万公顷和15.89万吨;德宏为387.4万亩和67.75万吨。在主要农产品构成上,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国内段主要以玉米、豆类、青稞、薯类、茶叶、烤烟、中药材、甘蔗、油料、咖啡、蔬果等为主。
综合以上统计数据,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良好,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性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也尚可。但是,根据统计分析,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国内段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第一产业增加值较低,比重较高,农业产业水平整体处于低端化状态;二是农业发展区域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林芝市和怒江州,跟其它5市相比,农业经济发展十分滞后;三是农业中部分行业如林业、渔业和畜牧业等发展增速出现后退现象。

表1 中缅跨境民族地区中国各地州农业经济发展统计表(单位:亿元,%)
受限于各种因素,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缅甸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率低下[4]。例如,其水稻、棉花、黄麻等农作物的但产量仅有我国的0.6、0.4和0.3,其它作物但产量也普遍较低。掸邦工商联合会在报告中提出,掸邦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是效率低下、数据和研究不足、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不足、配套设施和服务不足等困境。“由于长期受制于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缅甸政府虽然坚持改革开放……但农业科技水平仍较为落后,农业研究力量薄弱,劳动力素质不高”[5]。根据国内段各地农业管理部门统计分析,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滇缅、藏缅段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耕地利用率不高,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不足,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民增收抗市场风险能力低下,农业抗灾抗疫能力还不高。从横向对比来看,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总之,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到该区域的农民生活质量和边境民族的和谐稳定,必须加强两国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开放合作。
三、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依据
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因其多民族分布和边境等属性,是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枢纽区域。基于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应该在该区域通过建构农业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来共同解决该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遵循的理念,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共同体,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
地缘关系的紧密性。地缘关系紧密是构建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的自然地理前提。缅甸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中缅边界自西藏察隅县的库阳山口起,至云南勐腊县南腊河口止,接壤边境线长达2185公里,是我国西南各族进入印度地区的重要通道,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因此而形成。边境线两侧有70余条通道彼此相连,中缅两国村寨相望,空间地缘关系十分紧密。缅甸是新中国建立后承认我国国际合法地位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个与我国签署睦邻友好条约的亚洲国家。总体上中缅两国地缘环境相对平稳,地缘政治关系非常紧密。这些跨境而居的民族群体,因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在历史中广泛接触,相互交流学习,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形成了较为相近的农业经济特征和农业成分结构。
族群成员的认同性。族群成员的认同性是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的身份认知基础。缅甸目前共有135个民族,包括克钦族、克耶族、克伦族、缅族、掸族等。“一般认为汉族、阿昌族、瑶族、回族、苗族……德昂族、独龙族以及克木人都属于中缅跨境民族。”[6]“缅甸的果敢族与中国汉族同种同源,果敢人是从云南人变成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7]类似同源族群还包括回族、哈尼族、瑶族、傣族等。这些民族除了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以及宗教信仰,并基于民族文化的同源性而保持诸多联系,“此等联系即使在近现代国界确立之后也从未中断过”[8]。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人类共同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合作理念,而民族或族群是人类群体性和社会性属性的一种表现,是人类活动和互动交流的一种载体形式。族群成员的认同性,可以有效消除人类之间的隔阂,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天然的凝合剂,消除合作中的障碍和冲突。中缅跨境民族或族群的成员认同性,是构建该区域农业发展共同体的天然优势。
族群文化的同源性。民族文化的同源性是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民族成员的认同性,是基于民族文化的同源。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就是各民族在历史迁徙和互动中而形成的特殊区域。同源同种的民族,“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通婚、边民互市、宗教互动、走亲访友等现象非常普遍”[9]。民族文化的同源有利于消除文化隔阂,有利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达成共识。 我国与缅甸都是多民族国家,两国边境地区的跨境而居的民族,由于在文化上的接近,使得该区域在交流中具有先天语言、生活方式、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优势,在加强两国合作方面具有纽带和向导效应。充分利用同源族群的历史文化渊源来增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以民族关系拉进国家关系,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新途径。文化的同源,使得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通婚、通市和人口流动现象十分普遍。民族文化的同源也造成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文化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相近性,这对于共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具有重大价值。
农业资源的同构性。农业资源的同构为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提供好了合作前提。农业经济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经济成分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的同构性孕育着农业经济发展的极大公约性,使得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拓展农业领域开放具有先天性优势。农业资源的同构性,使得该区域在农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相近性,也蕴含着两国在农业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性。一是农业资源的同构性为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提供了前提基础;二是农业资源的同构性为两国在该区域开展深入的技术合作交流提供了广泛空间;三是农业资源同构为两国共同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规划提供了良好前提。此外,农业经济发展所以来的资源结构的共同性特征,也大大降低了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有利于双方集中整合资源来攻克共同存在的瓶颈问题,有利于联合进行资源开发规划制定和技术创新协同。
协调发展的互补性。协调发展的互补性为构建中缅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奠定了良好合作可能性。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具有协调发展的互补性。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属缅区域的掸邦和克钦邦具有区位、土地、农作物种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其盛产的农产品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进口商品;而我国所属地区则在人才、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协调发展的互补性为双方开展农业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良好前景。协调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缅甸部分属于该国中北部地势较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于南部沿海地区明显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较南部地区差距较大。而该区域的中国所属的西南边境地区,也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重要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收入较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以协调发展缩小该区域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是重要途径。而该区域实现协调发展,在合作上具有良好的互补效应,可以深度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降低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农业经济共同发展。
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目标的共同性是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共同体的目标前提。目标的一致是行为一致的前提,是将不同国家和族群经济发展行为揉和到一起,拧成一股绳的必要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我国基于全球问题而提出的发展理念,就是寻求全人类利益的利益交集和最大公约数。中缅两国自建交以来,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共同性,在秉持睦邻友好的原则下,双方一直共同致力于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共赢。共同的目标,是构建该区域农业发展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都是关系着两国整体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极为重视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在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下,中缅边境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对同一问题的一致认知,使得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就具有了初心和使命上的一致性。
综上所论,在中缅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导下,中缅跨境民族地区构建农业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具有充分理论依据,不但意义深远且现实可行。地缘关系的紧密性、协调发展的互补性、农业资源的同构性、族群成员的认同性、民族文化的同源性、发展目标的一致性等因素充分体现出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共同体,要充分发挥以上种种优势因素,系统化规划农业领域的合作发展框架,全方位加强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共赢。
四、共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的举措
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是与我国接壤边境线最长的国家,是联结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对于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具有战略意义。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则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枢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指导下,加强农业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命运共同体,应在以下方面推进。
拓宽农业领域对外开放格局。依托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将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合作纳入总体战略高度,加强顶层间的设计,强化协调机制,充分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秉承“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享原则,中缅应切实推进该区域农业领域的对方外开放格局,大力推进海外农业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合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农业领域投融资合作、农业产业项目合作,充分挖掘两国农业领域比较优势,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鼓励两国农业企业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开展投资,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丰富招商引资优惠措施,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加强农业技术领域合作创新。加强两国在农产品培育与种植、先进加工技术、农业设备研发制造技术、土壤改良技术、耕地质量管理等领域的合作创新,提升农业产业水平迈向高端,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农产品竞争力。以共享理念为指引,加速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传播共享,形成“产-学-教-研”良性循环一体化机制。根据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具体合作领域重点放在良种培育和种植技术、战略农产品的深层加工技术、农业机械化推广技术、畜牧兽医以及渔业开发技术等方面。
深化农业人才领域交流合作。技术领域的合作,离不开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制约当前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一直。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一步降低人才要素在该区域的自由流动和共享壁垒,依托地缘毗邻优势和民族文化同源优势,着力推进该区域农业领域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应将农业高等教育作为合作重点之一,通过高效扶持的方式开展农业教学与科研合作,以破除缅甸农业科技人才瓶颈问题。[10]面向农民、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等农业从业人员等,针对不同需求大力开展广泛性的针对性的培训工作。进一步发挥云南省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地位,鼓励和支持滇缅在重大农业项目和人才培训教育领域的合作,依托双方高校建立人才教育基地,深入推进人才联合培养作。
增强跨境民族文化联系纽带。跨境分布的族群,自古至今民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要积极发挥他们对于增进中缅两国关系的纽带效应,发挥中缅跨境民族在历史同源、文化相近、习俗相近等层面的优势,以跨境而居的族群的文化交流为切入点,加强中缅文化交流合作。丰富民间文化交流形式和平台,通过联合举办旅游节庆、农产品会展、劳务与技术交流会议等形式,以文化交流带动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技术交流。通过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进传统农业改造提升,促进农业与第三产业尤其是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兴产业形态,塑造农产品区域文化品牌和民族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提高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产业附加值,切实提高跨境族群的居民收入水平,改善该区域民生福利。
总之,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区位性、民族性等特征,其社会发展对我国与缅甸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农业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占据重要地位,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共同问题,需要双方共同着力解决。从地缘关系的紧密性、民族关系的认同性、民族文化的同源性、农业资源的同构性、协调发展的互补性、发展目标的共同性等多方面可知,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共同体具有较高可行性。构建中缅跨境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共同体需要多措并举,才能为中缅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