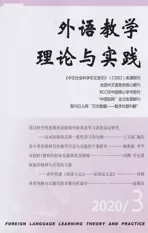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困惑*
——译者行为研究关键概念刍议
2020-12-29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军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军平
提 要: 译者行为研究中的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一直模糊不清,从理论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区分与联系,既是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诉求,也是翻译文化研究与社会翻译学研究理清各自视野与焦点的重要问题。通过概念界定和辨析,可以认为,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关注翻译的社会性,聚焦译作生成过程中译者的社会化行为及其动因,文化性因素则融入了译者的认知语境,是译者行为背后可能的动因之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范式转变,因此“毫无疑问,(它)是翻译研究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肇始以来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Wolf, 2011: 2)。此后,翻译研究一改语言学阶段仅仅关注语言结构层面的研究分析,将视角延伸到了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探究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以及翻译过程中超文本的制约因素。翻译不再寻求传统的语言意义对等,而是作为文化历史事实,追踪其文化交流功能及潜藏在翻译背后的各种力量角逐,凸显了“所有的译文都反映了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条件”(Wolf, 2011: 2)这一特性。据此,翻译研究对象被重新界定为“嵌入原语和目的语文化符号网络中的文本”(Bassnet&Lefevere, 1990: 12),这一界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译文生成的外在社会文化因素便开始介入翻译过程,研究的视域被大大扩展,翻译研究开始了从语言学规定性、原语朝向的语言分析走向了描写性的、目的语朝向的功能描写研究,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促成了描写翻译学的蓬勃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原语朝向”的语言学研究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强调语言层面的意义“对等”;而“目的语朝向”的文化研究则关注翻译的外部语境,侧重对翻译过程中所有外在制约因素的描写和分析。虽然后者所涉因素五花八门,但基本都被统辖在“社会文化”范围之内,因此到处可以看到被“sociocultural-”这一复合前缀修饰的有关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所进行的研究,“社会文化”因素成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的一个特定标签。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世纪大约七十年代“文化转向”兴起,一直到新世纪之初的近三十多年期间,学界对“文化性”与“社会性”二者之间的区分都没有给予重视,彻斯特曼(Chesterman)就曾指出:“翻译研究已经极大地拓展了它的关注点,从偏狭的语言学视野拓展到了各种语境之下,但对于如何精确地厘定这些语境,我们还缺乏统一的理解”(2006: 9)。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翻译口笔译研究经历了一个“社会(学)转向”(Wolf, 2012; Angelelli, 2014),也就是在社会翻译学研究,特别是译者行为研究逐渐兴起之际,有个别学者开始了对此问题的考量。
彻斯特曼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像是“社会文化转向”,因为“实际上,文化转向旗帜下的大部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更加接近于社会学研究”(2006: 10)。就目前学者们在此领域的研究课题来看,“至少可以说,这些题目既是社会学的,又是文化研究的”(Chesterman, 2006: 10)。沃夫(Wolf)则特别关注翻译“社会转向”中的译者行为研究,甚至直接将此转向称为“行动者转向”(2012)。他在对翻译研究发展过程进行回顾,特别是对文化转向进行分析以后认为,“翻译过程的一个重要特性虽然没有被完全弃之不理,但也是被广泛地忽视掉了: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需要考察译者的角色以及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其他参与者的角色”(Wolf, 2011: 3)。这一提议将翻译研究的社会性凸显了出来。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翻译的“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学界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区分研究,特别是近二十年,社会翻译学发展过程中所催生的译者行为研究,正在因面临着“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的模糊不清而引起困惑。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首先,在翻译研究中, “文化性”与“社会性”两类要素之间区分的诉求和必要性在哪里?其次,两种因素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分和联系?最后,基于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的区分,在社会翻译学研究视野之下的译者行为研究中,这两种因素呈现怎样的相互关系?
一、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诉求
描写性方法是译者行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对译者行为的解释,需要我们对其背后的动因进行充分的描写与挖掘。译者作为社会个体所考量的因素,是译者行为研究关注的焦点所在。亨佩尔(Hempal)曾认为就一门经验性学科而言,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对我们经验世界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描写,二是制定通用的原则,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1952: 1)据此,霍姆斯当年就明确认为翻译无可否认地是一门经验学科,因此其研究目标也就相应地有两个:“一、对我们经验世界中出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进行描写;二、建立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通用原则”(Holmes, 2000: 176)。因此,翻译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先对翻译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尝试对其做出解释,通过解释分析,逐步建立通用的规则,来对翻译现象进行预测。基于此研究目标,翻译研究的描写过程就首先需要对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进行详尽的分析,而对于某些翻译现象的解释都必须回到原来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去,寻找其背后的原因,找到彼此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当然,这样的描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上述思路的同时,要注意不能产生简单“机械决定论”的思想,也就是说,基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多样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某个因素与翻译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简单的因果联系和推理,也不宜对某一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过度放大或者太过忽视。
描写翻译学的代表人物图里(Toury)就始终避免寻求可能给予漂亮解释的单个诱因变量,在他看来:“每一个单个的因素,都可能被夸大、削弱,甚至可能被其他的因素抵消”(Toury, 2004: 15)。这也就意味着决定论的推理不能对翻译做出解释。可是,如果抛弃了因果推理,那就意味着另外一种情况:“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就会变成一张张各种不同条件因素的清单,每种都有可能,却没有起作用的主导因素”(Pym, 2006: 5),翻译解释就呈现出了多元化格局(目前的研究状况就是如此),除了让解释变得更加复杂之外,不会得出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承认每个因素都可能发挥了作用,但没有理由认为,所有能想到的因素都能潜在地、平等地对翻译进行足够好的解释。面对此种窘境,图里提出了“盖然率”(Probability)的概念,尝试摆脱此种尴尬的处境。
盖然率意味着我们在提出翻译解释的假设时,主要关注的是“趋势”(Tendency),而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盖然率采用‘越X,越Y’的形式,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一些解释因素出现变化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Pym, 2006: 5)。比如,当我们做出原语文化声誉越高,翻译就越可能采用异化策略的判断时,就意味着我们基于此前的研究,认为文化声誉可能与翻译中的策略选择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与其他潜在因素相比,该因素更有可能是其起因”(Pym, 2006: 5)。这种盖然率的思考模式是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就具体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译者行为研究而言,对翻译解释因素的盖然率评价,我们所要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各种已知的因素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在具体语境下寻找翻译背后的最可能合理的解释和最具有因果关系趋向的分析,而建立数据库的前提就首先需要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辨别与分析。因此可以说,在译者行为研究之中,我们进行“文化性”与“社会性” 因素的区分,既是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的根本诉求之一,也是我们对译者行为进行描写和解释的前提条件。
二、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区分的可能性
从历时角度来看,“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中,都无法避免地涉及到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以勒弗菲尔(2004)为代表的“操纵改写”理论,将翻译置于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看成是一个受制于各种文化要素而进行的“改写和操纵”的过程。其研究的重点是翻译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比如意识形态、诗学等对于译文生成的制约关系。但如果将所谓的“译文生成”重置于具体的社会生产语境,就可以看到,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这些因素施加影响的过程和渠道则主要是社会中的各种参与者,比如赞助人、专业人士、评论家等。通过他们,这些文化因素才能对译者的行为产生制约,并最终“操纵”整个翻译过程,而对于这些社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各种参与者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属于社会性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在勒弗菲尔所勾勒的这样一个文化因素制约的翻译操纵改写过程模式中,也到处都镶嵌着各种社会性的因子。沃夫(Wolf)就认为:
将翻译视为社会实践也是勒弗菲尔研究的核心。特别是改写的概念,不但意味着在文本层面的操纵干涉,也意味着在社会力量互动中引导和控制生成过程的文化机制,而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赞助人系统包括了个人、集体以及各种机构。……勒弗菲尔不但将社会视角融于了这一概念,而且还通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对其进行了拓展。而文化资本,在他看来,是一个特定文化中翻译流通的驱动力(Wolf, 2007: 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翻译过程中社会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翻译首先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这就肯定牵涉到了各种社会因素,而每个具体的社会因素都具有其深层的文化背景,所以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一起,就构成了翻译的“社会文化”语境。但对于翻译现象的观察和解释而言,直接从这么宽泛的视角进行研究,恐怕难以获得更有成效的成果。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对翻译研究分成“社会的”和“文化的”两类因素,进行逐一分析,然后形成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综合解释和预测。因此,对于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的辨析和厘定,也就构成了社会翻译学的基本出发点。那么,鉴于“文化社会性”的紧密关系,对于二者的区分,是否可行并真的有必要吗?
正如我们此前所言,描写性是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翻译现象与行为进行描写解释,就如图里所言,要考虑“盖然率”的问题(Toury, 2004)。而对各种可能因素之间进行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区分,则意在建立起盖然率选择的数据库。因此,对于“社会性”与“文化性”要素有必要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界定和厘清。虽然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谁也无法真正在二者之间划分出一个明确的界限,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要求、视角、方法的差异,进行这样一个基本的区分和辨别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从某些程度而言,也是可能的。彻斯特曼就认为,“对‘社会文化’这一概念从中间进行粗略的区分应该是可能的,其中一个层面主要是社会问题,另一个层面主要是文化问题”(2006: 10)。这样的划分,能让我们更加有效地把握翻译问题的不同层面,因而更加有助于深入研究的开展。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其意义首先可以让我们对翻译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和把握,能够增进我们对翻译复杂性的了解;其次,这样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对翻译过程、特别是译者行为研究,构筑起一个比较明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各种因素的辨别分析,明确文化性与社会性的异同,更利于探索译者行为背后的各种制约要素和互动机制;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划分还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因为社会翻译学研究整体框架的建立,最终需要在充分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描写和分析,因此,对翻译社会性与文化性因素之间关系的把握,有助于为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扫清障碍。
三、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辨析
文化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概念,学界历来对其界定林林总总,光定义就不下四百多种,而且还处在不断的增加之中(吴克礼,2002)。很长时间以来,对如何比较精确地界定“文化”,总是存在不同的意见。当然,作为一个术语,“文化”一词在漫长的语义发展变迁中其内涵与外延都处在不断变化当中。最近几十年,学界好像慢慢取得了一些一致认识(Katan, 1999)。其中克劳伯(Kroeber)和克鲁克霍姆(Kluckholm)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在对以前160多种典型的“文化”定义进行分析和比较的前提下,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文化包括通过符号传递的、已获得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人类群体的区分因素,包含了他们在器物上呈现的方式;文化的根本内核是(比如,从历史上衍生的、经过历史选择的)传统的思想,特别是他们所秉持的各种价值。文化系统可以一方面视为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未来行为的制约因素。”(Katan, 1999: 16) 这一界定将文化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现在外在的行为方式,而另一部分则是其核心部分,包括了传统的思想和价值。文化的核心部分,即价值思想层面是决定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所有被一个文化所认可的行为的最终根源,因此,行为与价值之间构成了一种“向心性”(centrality)的关系。霍夫斯泰德(Hofstede)所提出的具有多层面的“洋葱模型”(Onion Model)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文化的构成:
文化的中心是价值,环绕价值的是实践(行为),实践包含了惯例、英雄人物以及符号。因此,我们越远离文化核心,我们就越深入到社会学领域,深入到了社会行为和包含各种机构、物品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关系领域(转自Chesterman, 2006: 11)。
而文化系统的外在层面,则指明了文化系统同时可以是行为的结果,那就说明行为可以对文化产生影响,是外在的影响因素。而作为未来行为的制约因素,文化却又对行为产生制约作用,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了一种“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双重属性。简而言之,在文化核心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互动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对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而言,“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是行为,而文化研究学者则更关注思想”(Chesterman, 2006: 11)。基于思想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彻斯特曼将翻译过程的主要语境划分成下面三类:
一是文化语境: 关注价值、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传统等;二是社会语境: 关注人(特别是译者),他们可见的群体行为,他们的制度等;三是认知语境,关注心理过程和决策过程等(2006: 11)。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就具体实际的翻译过程而言,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又可以大致归结为两类,因为关注人及其行为,实际上就包含了认知语境,因为这里的“人”主要是指以译者为代表的所有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正是因为“人”或者说“行为者”的存在,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才在认知语境中获得了联结。换言之,认知语境,涉及到的就是“行为者”行为背后的心理认知与决策过程,正是认知语境实现了文化语境与社会语境在行为者身上的统一。相对而言,沃夫对翻译过程的分析更加简洁而具有概括力,他认为:
翻译过程,从不同程度来看,受到了文化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制约。第一个层面是结构性的,包括了权力、统治、国家利益、宗教或者经济等影响因素。第二个层面关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者,他们不断内化上面提及的结构,并遵从他们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来采取行动 (Wolf, 2007: 4)。
但同时,沃夫也反对将文化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对立,因为“没有文化,社会就无法得到充分的描述,同样,没有社会,文化也得不到充分描述”(Wolf, 2007: 4)。由此可见,翻译过程从头至尾都涉及到了文化与社会因素,又加上二者的紧密关系,要想对翻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把握,就不能也无法将文化和社会进行完全剥离。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翻译研究学派,特别是“操纵改写”论者主要关注于翻译过程的文化层面,而对实际翻译过程中社会层面的要素则很少或者可以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言:“诚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一直以来,在社会环境中探讨译作的生产与接受却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忽视”(胡牧,2011: 7)。因此,从社会生产视角来对翻译过程进行考察也就成为翻译研究中“社会学转向”的动因。
在实际的翻译过程描写中让人感到迷惑的是,有时我们很难明确对某个具体的因素进行简单的“文化性”或者“社会性”的辨别,因为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文化与行为(社会)的关系就如一个连续统的两端,从文化到行为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分界线,两者彼此影响与制约的关系更加让我们无法具体地、清楚地分辨实践中的你我。但在我们看来,文化与社会的基本分野却并不模糊,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研究关注的就是译者的行为,涉及到了由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的所有“行动者”的行为,这是翻译的社会实践层面的问题。因此,在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视域中,所有行为者的行为都受到了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也就是说,影响他们行为的首先是社会因素,比如个体的行为或者群体的行为,还有“译者培训机构、职业组织以及他们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工作环境、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翻译政策等许多因素”(Wolf, 2012: 133)。相对而言,所有社会影响因素对行为者而言是一种“在场”因素,而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是参与者作为社会人,其行为背后的动因之一,是社会人属性的一个方面而已。简而言之,以前的文化研究将翻译过程纳入文化力量角逐之下,将翻译看成是文化“操纵”的过程;而社会学视角之下,翻译是各种社会影响因素之下译者行为的结果,文化只是影响行为者行为的因素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概念里面社会性与文化性因素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值得说明的是,不同路径的翻译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概念,虽然本身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却往往都融入了彼此的“模因”,社会翻译学研究也不例外,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就是图里所倡导的“翻译规范”研究。
可以说,图里(2001)的“规范论”是社会翻译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一。在他看来,翻译是规范制约下的社会活动,这里的规范是对于外在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个总括,其虽然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行为准则和关系契约,但同时也融入了对翻译的价值认知,包含了某个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何为翻译”等问题的基本判断。正是现实中翻译过程的参与者,将本来我们所要区分的“文化”和“社会”因素融合了起来。而社会学视域下的行为者研究,是对包括以译者为代表的所有翻译参与者行为的研究,其重视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与行为。在译者行为研究中,翻译过程就成了译者通过对外在翻译规范的习得,通过参考具体的、现实中的社会因素,在选择遵从或者违背翻译规范的互动过程中做出翻译决策的社会生产过程。也就是说,译者行为的背后,是译者针对面临的实际条件进行权衡抉择的结果。在现实中,鉴于译者的“社会性”和能动性,顺从规范并不是译者的唯一选项,有时对规范的“违抗”可能更能体现特定语境下译者的社会性(王军平,2017)。简而言之,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过程,就是译者面对各种翻译规范进行抉择的过程。译者选择遵从或者违背翻译规范,是译者对现实中的社会因素(当然包括社会关系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影响)进行深入考虑,并与各种社会关系互动之后所做的决策在行为层面上的反映。
四、译者行为研究中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以勒弗菲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注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将译作看作是文化因素影响甚至是“操纵”下的产物,其研究过程注重翻译背后因文化地位差异而形成的文化权力、文化干涉对译作生成的影响,似乎文化成为了译作生成的真空,任何具体的、社会的因素都对其无从干涉,真正付诸翻译行为的行为者都成为了文化的玩偶,整个翻译过程中都没有“人”或者“行为者”的主动参与。而社会翻译学研究就是要让翻译回归现实世界,让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参与者都在译作生成的过程中“现身”,将翻译的社会性从文化研究学派笼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凸显出来,关注译作生成过程的社会性。基于这样的理念,“文化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在社会翻译学研究中便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上的变化和调整。
有学者曾将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的“行动者”研究划归为“翻译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研究(汪宝荣,2019),选择将包括译者在内的社会行为者及其社会行为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将译者的行为纳入社会生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摒弃了对文化因素的考察。区别只在于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是从社会因素入手,关注翻译过程中行动者,特别是译者的各种社会化、角色化的行为(周领顺,2013),以及各种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从而对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翻译现象进行描写解释。文化因素则被视为译者社会属性中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了翻译生产的背后场景,成为翻译过程中译者考量的一个视点而已。沃夫在谈到权力关系时就提及:“文化路径的研究已经将翻译过程中各个阶段潜在的权力关系凸显了出来,而现在则需要与社会中译作以及译者的在场性(situatedness)联系起来”(Wolf, 2012: 133),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所揭示的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会作为当前社会翻译研究的一个视点,用来和其他相关因素一起参与解释,研究译者及其他参与者在翻译这项社会生产活动中的行为。
从广义上来看,翻译始终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因此,任何语境下的翻译研究都脱离不了文化因素,也就是说,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交流场所,它为翻译这种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居于每个翻译行为者潜在的思想认识层面,所有的翻译过程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译者个体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具体到实践层面便是:“文化是成套的价值和传统,而社会作为人际间的关系系统,是将这些价值传递给每个个体的一种机制。”(Tyulenev, 2014: 23) 社会学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根本不可能脱离文化因素的干涉,只是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在译作生成的各个阶段,如作为社会个体的译者、他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因素,以及他与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活动包括译者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生产、译本传播以及接受的社会因素。译者对文化层面因素的考虑,是其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进行社会生产实践时,对融入其基本认知语境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此时便作为社会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认知要素发挥着作用。因为能将社会与社会区分开的标志是文化,而每个在特定社会领域中生产实践的个体,必然带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受到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与文化研究不同的是,在将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译者的社会行为之后,译者对于文化因素的考虑,是译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进行主动选择的行为,不再是对外在文化因素“操控”的被动接受。
五、结语
从社会翻译学视域下译者行为研究来看,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行为。正是作为社会参与者之一的译者将语言操作与外部语境进行了联系,让翻译得以在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在语言层面得以实现,翻译结果无论怎样,都是译者在社会语境中抉择的结果。语言层面的研究和外在文化层面的研究,只有通过译者的介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因此,对译者行为的深入研究,就成为“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应该重视的一个领域。目前出现的翻译学“社会转向”则是借鉴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译者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考察。翻译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行为,译者作为社会参与者中的一员,其行为虽然首先受到外在的社会条件(关系)制约,但最终的行为则是其本身作为“社会个体”在充分考虑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做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对“文化性”与“社会性”因素的区分,能够为译者行为分析和解释提供更好的“备选菜单”,有利于凸显翻译的社会性,厘清理论上的混淆,促进译者行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