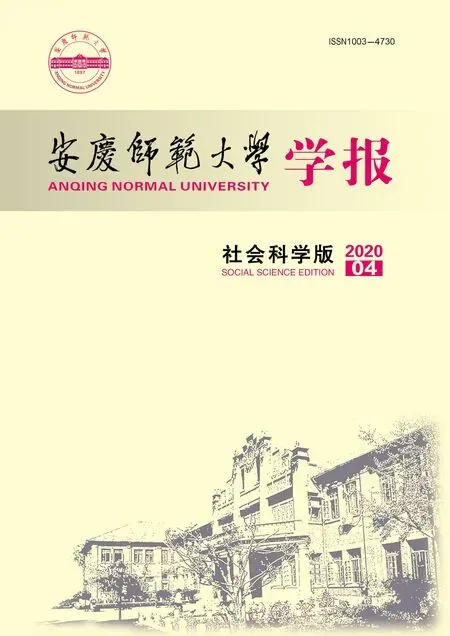桐城派“创意造言”论诠解
2020-12-27俞炜涛
俞炜涛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创意造言”是唐代李翱提出的关于文章写作的重要命题,后世对此多有推阐,其中以桐城派的阐释尤具代表性。桐城派文人在接受和阐释“创意造言”的过程中,既对这一命题的原初意义予以继承发扬,又根据其理论需要赋予新的意涵,并与“理”“气”等文论范畴相勾连,使之成为桐城派文章理论中的重要观点。系统梳理和论析桐城派对于“创意造言”的阐释流变,不仅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此命题的理解,亦可借此管窥桐城派文论重心由“理”向“气”的转进,对于深入推进桐城派文章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意造言”论的提出及内涵
“创意造言”一语出自李翱《答朱载言书》,其文有言: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1]6411。
李翱所谓“创意造言”之“意”是指文章自身所含之意旨,而“言”则指文章的语辞形式。根据李翱对“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论述,可知文章的意旨和语辞都需要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李翱将“意”与“言”并重,在他看来文章的特殊性不仅来自于其本身所含意旨的不同,亦来自于其自身所运用的语辞之差异,也就是说文章的特殊性是由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之独特性所决定,这就意味着李翱弥合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正因为不同的文章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意旨和语辞,那么所谓“文以明道”之“文”就不仅仅是明道的工具,而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
但是,在李翱的文学思想中,文章的本质依旧被归结到了“道”上,这又使得其“创意造言”论的独特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明道”所遮蔽。李翱认同韩愈“文以明道”的观点,如他在《答朱载言书》中所言:“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1]6412在李翱看来,文章的本质在于“道”,而文章本身最重要的作用即为“明道”。他又指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1]6411其中“义”指独立在文章之外的“道”,“意”指文章本身的意旨,“理”则指某一具体的事理,“气”指文章所体现作者的精神气质及文章风格,“辞”指整体的文章,“文”指文章中的具体语句。细绎其意,所崇奉信仰的“道”深刻,则所欲表达的意旨便能较远大而不短视狭隘,进而能明辨事理,其文章的独特风格就能凸显,其语辞形式也能工整盛大。因此,无论“创意”还是“造言”,其最终的旨归就在于使“道”显明,从而促进教化。对于“明道”的执着,使得李翱在提出“创意造言”时十分注重“意”的作用,文章的独特性仅仅来自于“意”体现“道”的深浅程度不同,这就使得文章处于“文”“道”二分的处境。
由此来看,在李翱最初提出“创意造言”之时就隐含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承认文章自身(意旨和言辞)的独特价值,将文章从“明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种是以“明道”为最终旨归,“创意造言”的目的仍在于“明道”。而这两种倾向也为后世对“创意造言”的理论阐释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二、桐城派“创意造言”论阐释
“创意造言”论自李翱提出后,成为后世文家探讨文章创作的重要命题。自宋至清,“创意造言”作为文章的写作要求,其落脚点始终在“明道”上,对文章本身的独特价值鲜有强调。其中,由于桐城派自身文论重心的转移,其对“创意造言”这一理论命题的接受过程独具特色。
桐城派在创派之初,就标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韩愈及其弟子的古文观点被他们奉为古文理论的正宗加以推戴。如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有言: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2]581。
方苞对“创意造言”的含义并未做出直接的解释,但是他提出了“创意造言”的标准问题。方氏认为“创意造言”必须要使文章达到“清真古雅”的审美效果,即在文章的意旨方面需要“清真”,在文章的语辞方面需要“古雅”。而要使“创意造言”能够形成这种效果,就必须符合“是”。所谓“是”,指的是必须合宜,也就是必须达到某一标准。方苞在后文中又讲到:“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意,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2]581这里所谓理、辞、气之“当”,或者说所达到的“是”,指的就是这三者都必须符合于“道”,或更具体指宋儒所言之“义理”。在方苞看来,“创意造言”的运用必须符合“义理”,其中“辞”的运用必须贴合题意,而这里的题意亦更多地指向于“义理”。由此而言,方苞实际上承继了李翱在“文以明道”层面对于“创意造言”的阐释,同样认为所谓“创意造言”必须要在符合“义理”(李翱所谓“道”)的前提之下运用,若是超出了这个前提,那么“理”与“辞”便皆不得当。而此种阐释同样认为对于文章的语辞而言,其真正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体现“道”,其自身并没有本体价值,文章与“道”被放置在了一个割裂的处境之中,“内容”与“形式”被再次分裂。
方苞之后,桐城派对“创意造言”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是刘大櫆的《论文偶记》。其文言:
所谓创意者,如《春秋》之意不同于《诗》,《诗》之意不同于《易》,《易》之意不同于《书》是也。所谓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状,《论语》曰“莞尔”,《易》曰“哑哑”,《谷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然”,左思曰“冁然”[3]10。
刘大櫆对“创意造言”没有解释其内涵,而是列举了不同的例子,但从其所举之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创意造言”的阐释所注重的是文章自身的整体独特价值。刘大櫆的这一段论述是在“文贵去陈言”条之下,也就是说他认为文章的成功需要“去陈言”,而“去陈言”则在于文章的“意”与“言”皆有其特殊性,在临文之际,文章的“意”与“言”皆要重铸,不可与他人同。可见刘大櫆与方苞不同的是,他不仅注重“言”对于文章价值产生的作用,而且将“创意造言”逐渐归结到凸显文章自身的整体独特性中去。
在刘大櫆的阐释中,“创意造言”开始从“道”的附庸转变为凸显文章价值的途径。但刘大櫆没有对“创意造言”作出直接阐释,而桐城后学方东树在其诗论著作《昭昧詹言》中,则运用李翱的“创意造言”理论解释诗法,强调了这一命题中有关文章整体独特性的意涵。如言:
凡学诗之法: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语言,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陋,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4]10。
方东树强调“创意造言”对于诗歌的创新性以及特殊性的作用。他将“创意造言”作为诗法中必要的两个要求提出,同时强调“创意造言”的目的在于“务去陈言”,在于避免文章“凡俗浅近,习熟迂腐”。方东树将李翱所谓“创意造言”中所蕴含的强调文章自身价值亦即文章自身特殊性的意味放在了第一位,并且将其作为文章(包括诗歌)能够独有千古的重要因素。他在阐释“创意造言”时,认为李翱所说“读其《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云云,就“如曹、阮、陶、谢、鲍、杜、韩、苏、黄诸家,一一用功,实见各开门户,独有千古者,方有得力处”[4]9。这实际上就是将文章从“道”的附庸之中独立出来,承认文章的本体价值。他在承认文章本体价值的同时,也将文章从内容与形式二分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所谓“故知诗文虽贵本领义理,而其工妙,又别有能事在”,“文字精深在法与意,华妙在兴象与词”[4]10-11。方东树认为诗文成功的关键除了“本领义理”之外,要注重语辞本身,在这里方氏对于语辞的强调并不是为了使义理能够更加显明,而在于其能够造就诗文的“工妙”,也就是说语辞成为了文章(包括诗歌)意义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
方东树虽然运用文法来解诗,但《昭昧詹言》毕竟是一部诗论著作,其论述始终是从诗的角度出发。而张裕钊则站在文章的角度,从文章本身的价值意义出发来直接阐发“创意造言”,同时他结合自身的审美理想进一步深化“创意造言”之内涵。其论有言:
创意:言人所未尝言。造言:雕琢复璞,陈言务去[5]505。张裕钊和方东树对于“创意造言”的阐释大致相同,他同样强调了“创意造言”对于形成文章独特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张裕钊在“造言”中特别提出要“雕琢复璞”,亦即要求文章语言在“务去陈言”的同时,须有一定的雕琢,但表现出来时又要显得朴质有力,绝去人工。此一主张与其自身的文学审美理想关系密切。张裕钊在与吴汝纶的书信往来中,曾希冀吴汝纶为文能够在“雄奇”风格中掺入“平淡”,他认为“大抵雄奇、平淡,二者本自相合”[5]484。在张裕钊看来,古文的最高境界即在于雄奇与平淡的调和,只有达到平淡雄奇并兼的境界,文章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功。当张裕钊在“创意造言”中加入“雕琢复璞”时,“创意造言”这一理论命题被进一步深化,在原先注重文章自身特殊价值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对文章审美性的要求,彻底表明文章的独特价值即为文章的审美价值,从而使得“创意造言”成为桐城派文论中的重要主张。
从方苞到刘大櫆到方东树再到张裕钊,“创意造言”的内涵被桐城派不断诠释并且深化,进而逐渐成为桐城派文论中的重要内容。方苞突出“创意造言”对于“明道”的作用,在高悬“义理”的同时湮没了文章自身的本体价值;刘大櫆、方东树则将“创意造言”当做文章写作中的重要要求,特别突出文章自身的独特价值,从而使“创意造言”从凸显道的工具转变为体现文章特殊意义的文法要求;而张裕钊则在方东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自身的审美理想,在“创意造言”中加入文章的审美性要求,凸显出文章自身的独特价值即为审美价值,从而使“创意造言”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重要主张。桐城派“创意造言”论的这种流变深化,其本质在于桐城派文人对于文章本质认识的转变——由“理”转向“气”,并且最终深化为“调和之气”。正是由于桐城派对于文章本质的认识从原本非审美性质的“理”转向了审美性质的“气”,其“创意造言”论才会从对“道”的注重,转向对文章本身独特审美价值的重视。
三、“创意造言”论与桐城文论的“理”“气”转变
如前所言,“创意造言”论在桐城派内部的阐释流变源于桐城派文论对于文章本质看法的转变。总的来说,桐城派文论中对于文章本质的认识存在着由“理”向“气”转进的趋势,即“理”的地位逐渐下移,“气”的地位逐渐提升,最终发展为“气中之理”,文章自身的独特价值被彰显。而随着桐城派对于文章本质认识的发展演进,尤其在桐城派文论调和风格的阐释路径影响之下,桐城派文人对“气”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气”不再是单一的混沌之气,而是诸多范畴融合的调和之气,从而将文章的的独特价值固定到审美特质上,彻底突出了“气”作为文章本质的属性。
在桐城派初期文论中,“理”是文章的本质,文章的创作目的即为“明理”。如方苞《檄济宁诸生会课》云:“文章者,道义之余也,而即末以窥本,十可三四。”[2]527方氏认为作为语辞形式呈现的文章不过是“道义”的附属,文章的作用在于真实地传达出“道义”,可见其论述文章的重心并不在于作为语辞形式出现的文章本身,而在于文章所传达出的“道义”或者说“理”。在其论述中文章只是可以被用来窥探“道”的途径,它本身不过是“余”和“末”而已,其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通过它而得到的“道”(亦即“理”)。正因如此,方苞在阐释“创意造言”时特意为其设置了“是”即“当于道”的标准,“创意造言”必须以此标准为前提,并且以达到这一标准是为其最终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方苞《进四书文选表》论及“理”与“辞”时亦提到了“气”,但是他所论之“气”是指存在于文章中用来“依于理以达乎其辞”的一部分,其实质相当于“气脉”。并且“气”是否能够昌盛取决于作者能否“以义理洒濯其心,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因此,方苞文论中的“气”只是组成文本的一个要素,是使古文能够“辞当理”的重要一环,其地位在“理”之下,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彰显“理”。
而到了刘大櫆与姚鼐,“气”则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的意味,其意涵从原先仅仅作为文章要素开始转变为文章本质。刘、姚二人论文,对于“神”与“气”范畴的重视和强调超过了“理”,虽然表面上“理”作为桐城派古文的最高标准依旧高悬,但实际上其地位在不断下移。从刘大櫆开始,原本作为文章最终目的以及最高标准的“理”被搁置,他认为“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3]4。刘大櫆表面上依旧在强调文章应当要明理适用,实际上他为原本作为文章最高标准的“理”设置了一项前提,即“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在“明义理”之前加上了“文人之能事”,这就意味着刘大櫆开始注重文章自身的独特价值。而其所谓“能事”就是指文章的“行文一事”,即作为语辞形式的文章写作。当“行文一事”被刘大櫆着重强调之后,他进而提出了“行文一事”的评判标准不是义理,而是“神为主,气辅之”。所谓“神”与“气”,二者差别并不大,只不过“神”为“气”之主,而事实上“神”也属于“气”。由此,刘大櫆将“神气”提升为古文的最高标准,虽然他还提及“义理”,但“义理”实际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地位,“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3]3,刘氏开始将文章从“道”的附庸中逐渐独立出来,文章自身的独有价值开始显现。而这一观点的转变,使得他在阐述“创意造言”时,重点突出“创”与“造”的作用,强调文章的特殊性,而此特殊性也成为文章自身的价值来源。
后姚鼐承袭乃师观点,明确将“神”“气”与“理”并列,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古文的八大要素。姚鼐将“气”与“理”并列,将“气”彻底提高至了与“理”相同的地位,改变了刘大櫆将“理”虚悬的权宜之计。而这种做法使得桐城派开始对文章的本体价值越发重视,文章本身的自足性被逐步体现出来。在这样的趋势下,文章内部一直存在的“内容”与“形式”的分裂处境被逐步改变。姚鼐《答翁学士书》指出:“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进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6]84姚氏虽然依旧认为“文”属于“技”,但是他也提出“技之精”“诗文美”必然能够“进道”“命意善”。其言下之意就是对于文章而言其本身形式的精美,同样对其内容意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姚鼐提出了“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自此桐城派文论开始将文章作为具有价值自主的实在本体而独立看待。
从方苞到刘大櫆再到姚鼐,原先作为文学本质的“理”的地位在不断下移,而“气”之地位则在不断上升,最终二者几乎成为同等地位的范畴。在桐城派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发展到最后,在桐城派后期的古文理论中,“理”的地位已然在“气”之下,甚至成为了“气”的一部分。
方东树于“创意造言”论中十分强调文章(诗歌)之“意”与“言”的“避同求远”。这种创作要求的提出,是为了能够使文章(诗歌)凸显出每一位作者自身独一无二的气质怀抱。正如他在《昭昧詹言》中将诗归结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4]1其认为诗本身必须表现出作者的个人怀抱性情,唯有如此方为好诗。“古人所以必言之有物,自己有真怀抱”[4]13,在他看来,诗只有凸显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性情怀抱,使诗能够“自成面目”,此诗方能言之有物,才能“立诚”。而这种性情怀抱在诗中的体现,方氏则将其归结为“气骨”。“气骨”是“气”范畴的一个下位范畴,他说:“诗文者,生气也”[4]25,可知方东树实际上也是将“气”设为了评判诗歌的最高标准。但方东树与桐城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理”从作为文学的本质地位下移到了文本的构成因素中。在他看来,要写好诗必须要注重三个因素——文、理、义,“文”指向语辞,“理”指向事理、物理、义理,“义”则指向文法。只有当文、理、义三者俱佳且和谐共存之时,诗之“气”才能凸显出来,其诗才能精深华妙。总之,“理”是能够使诗有“气骨”的一个要素,“理”是组成“气”的一个部分。另外,在方东树的论述之中,“气”的形成除了诗的这三要素的共同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在于诗人自身的“本领工夫”。他说:“古人皆于本领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气骨。”“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以此为学道格物中之一功,则求通其词,求同其意,自不容己”[4]2。方东树认为诗中之“气”的形成需要诗人浸润在义理之中,通过修养成气,也就是说通过“义理”使“气”充盈,然后在创作时通过文、理、义三者的共同作用达到“气骨”凸显的效果。对于方东树而言,文章所要追求的是“气”,“理”是“气”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追求“气”的途径。正是“理”与“气”的关系转变促使方东树将独一无二的个人情性作为文章(诗歌)成功的关键,并且在创作上要求“创意造言”必须“避同求远”。由此,文章自身的本体价值则得到进一步强调。
曾国藩作为桐城派中兴之主,其论文亦以气为主。曾氏日记中有云:“大抵凡事皆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7]1310曾国藩一方面将“气”作为文章的本质,“气”的盛衰成为评判文章的第一标准;另一方面他认为“理”对于文章的作用须得在“气”之下方能得到发挥,也就是说只有当“理”为“气”中之“理”时,其“理”才能“不可厌”。曾国藩将文章中“气”与“理”的位置彻底颠倒,使“气”成为文章本质的同时,也成为“理”发挥作用的前提。
后曾国藩弟子吴汝纶论及古文之时,发挥了其师“气能挟理以行”的主张,将“理”融入“气”中,使“理”成为“气中之理”。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指出:“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8]359直接将“气”作为文章的中心,亦即视“气”为文章的本质所在。吴氏所谓文章之“气”指的是“精神志趣”,而“精神志趣”则是指作者之“行状”,即作者在文章中所表现的行为模样。这种“精神志趣”其实更多指向的是作者的一种真实生命体验,而不仅是虚无缥缈的志向怀抱。同时,吴汝纶提出“古人著书,未有无所为而漫言道理者”[8]1141。他认为古人所著之书,内含“道理”,但是此“道理”惟有通过“行状”即“精神志趣”方能领悟到。由此可知,吴氏亦将“理”融进“气”中,并且此“理”并非是一种纯粹的非审美性质的道理,而是蕴含于“精神志趣”之中,是读者必须与文章中所体现的作者真实生命交会后方能体悟到的“理”。如此一来,吴汝纶一方面将“气”作为古文的本质,另一方面将“理”包含进“气”之中,使“理”带上了审美性质,成为独特的“气”中之“理”。至此,“气”成为桐城文论的核心范畴,“气”所代表的个体特殊性成为了文章价值的来源,文章的独特本体价值得到彰显。
桐城文人对于文章本质的认识由“理”向“气”转进,突出了文章自身的独特价值。同时,受桐城派推崇调和风格的传统影响,作为文章本质的“气”逐渐被认为是不同范畴间相互调和而形成的“气”,这使得“气”赋予文章的独特价值被固定到了审美价值之上。也正是这种对于文章本质认识的深化,造就了张裕钊对“创意造言”论的创造性阐释。
桐城派对“气”深化认识的路径来自于其文论中对调和风格的推崇。姚鼐在《海愚诗钞序》中提出文章风格分为“阳刚”“阴柔”两派。在姚鼐看来,阴阳刚柔是产生文章不同风格的原因,文章的不同风格就来自于阴阳刚柔之间不同比例的搭配。姚鼐此时并没有将阴阳刚柔与作为文章本质的“气”相联系,但这种阐释方法的引入却为桐城后学阐释古文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弟子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开始将“气”与调和的风格联系起来。方氏并没有直接提出“气”与调和风格之间的关系,但他认为好诗必然是有着充盈之气,亦必然能凸显出诗人的自身面目,做到诚而不伪。曾国藩则将原先抽象的阴阳刚柔学说发展为“雄奇”与“自然”两种风格的互相调和,同时在这两种风格之下还细化出八种具体风格。
从姚鼐到曾国藩对于古文风格的论述都十分注重调和之道的运用,这使得张裕钊对于“调和”也很看重。张裕钊曾致信吴汝纶:“鄙意推测,阁下之文,往者抗意务为雄奇。顷果纳鄙说,乃抑而为平淡,而掺之未熟,故气不足以御其词而副其意。此亦自然之势。大抵雄奇、平淡,二者本自相合。”[5]484显然张裕钊所推崇的古文风格是一种“平淡雄奇”的调和风格,并且认为古文只有具备了此种风格,才能传播久远。由此,张氏在论述“创意造言”之时特别加入“雕琢复璞”的审美性要求,以期文章能达到他所推崇的境界。张裕钊在推崇这种古文风格的同时,将其与“气”直接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吴汝纶在原本雄奇的古文中掺入平淡的风格还未纯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气不足”,换句话说当文章之气充足之时,其文章的风格也就是“平淡且雄奇”的调和之风。
张裕钊的这封信确实对吴汝纶产生了影响,吴汝纶后来所推崇的文章风格也由雄奇转变为了“醇而能肆”。同时,吴汝纶也对张裕钊所提及的“气之充”展开了论述,他将气能否充盈归结到作者本身及其在文章中的反映。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言:“夫文章以气为主,才由气见者也。而要必由其学之浅深,以觇其才之厚薄。学邃者,其气之深静,使人餍饫之久,如与中正有德者处,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学掩才。学之未至,则其气亦稍自矜纵,骤而见之,即如珍羞好色,罗列目前,故其文常闳以肆,而才掩学。”[8]359吴氏认为气之形成在于“才”与“学”的互相作用,才比学高,则其文绚烂雄奇;学比才厚,则其文醇厚深静。吴汝纶将文章不同风格产生的原因由原先姚鼐所说的天地之道转移至作者自身的才学之上,并且使其与“气”产生了切实的联系,“才”与“学”的不同比例造就了不同的“气”,而这种不同的“气”反映到文章中则成为了不同的风格,而这种不同的风格所造就的独特审美性使得文章自身拥有了特殊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不同的“气”会产生不同的风格,但在吴汝纶看来最好的风格是一种调和的“醇而能肆”的风格,与之相应,最充足的“气”也就是一种比例和谐的调和之气。
吴、张二人的文论思想互相影响,沿着桐城派原先调和风格论的路径深化了对“气”的认识。这一方面将“气”的充盈深厚与否归结到“才”与“学”二者的调和中去,另一方面则在进一步加强了“气”作为文章本质的最高地位的同时,彻底突出了“气”作为文章本质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正因如此,张裕钊在其“创意造言”论中特别掺入“雕琢复璞”这种调和风格的审美要求,来凸显文章自身的独特本体价值是一种审美价值。可以说,这不仅是张裕钊个人审美理想在创作论上的体现,更是桐城派文论对文章本质理解深化的反映。
四、结 语
桐城派对“创意造言”这一理论命题的阐释,从最初将之作为凸显“道”的工具,到后来成为体现文章自身独特性的文法要求,再到对文章的审美性追求。这一方面是对李翱观点中原本存在的阐释可能性的阐发,但更重要的是桐城派对文章本质的认识转变带来了对于这一命题新的阐释维度。非审美性质的“理”从原先文学本质的位置不断下移,而审美性质的“气”从文本组成因素的位置不断上升,最后使“理”融入“气”中,成为审美性质的“理”,而“气”也成为需要不同范畴相互调和而形成的“气”。总的来说,桐城派对“创意造言”论的阐释流变是其文章理论发展变化的一个反映。
从“创意造言”这一理论命题入手,考察桐城派对该命题的阐释流变过程,并借此窥探桐城派文论发展演进的主要趋向,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桐城派作为上继唐宋,下启新学的文派,其文章理论中蕴含着许多对于前贤理论的再阐释以及启发后学理论的渊薮。因此,将桐城派文章理论放置到整个文论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观照,从整个历史脉络中解读桐城派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有助于将桐城派文章学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