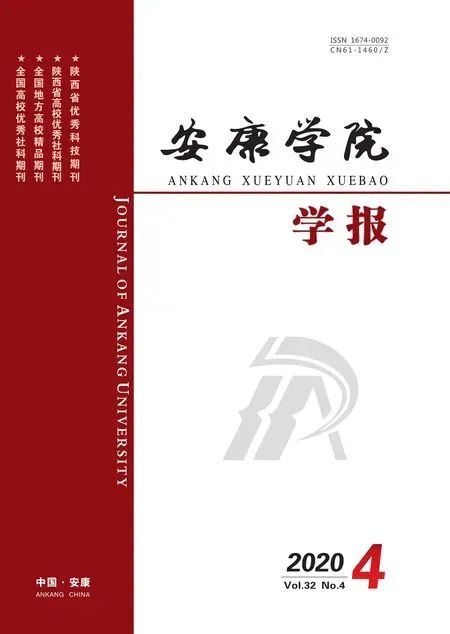语言的水晶之旅
——沈奇诗歌论
2020-12-27李洁
李 洁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诗乃心侣,需以诚待之,或功利化或游戏之,都是一种亵渎。”[1]正是如此虔诚的态度使得沈奇在诗坛耕耘四十余载,依然能够跋涉在诗歌写作的前沿,并以一种创新求变的姿态为诗坛不断制造惊喜。从1970年代发表诗作开始,沈奇就以其丰富的创作热情与敏锐的理论嗅觉开启了语言的水晶之旅,成就了诸多诗坛精品佳作。
一、理想主义或先锋诗者的追寻
从《看山》到《和声》 《生命之旅》,再到《寻找那只奇异的鸟》和《淡季》,以及21世纪以来的《印若集》 《天生丽质》 《无核之云》,连缀起来便是对诗人写作状貌的全景式勾勒。从早期诗作中对远方的探寻与执着开始,就显示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特质,这里的远方既是诗人诗歌理想的寄托,它所蕴含的神秘色彩也是对于诗性、人性追究的一次灵魂涉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处内陆地区的人们对于山外世界的总有一种迷恋与希冀,无数次的想象与期待可能会“很快回来/说一声没意思/从此不再抬头望山”(《上游的孩子》),但是这种蛰伏却不会熄灭内心深处的躁动,山外的世界早已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这种躁动除了对于陌生感的向往之外,也是对人生困境的一种揭示,“在这里长大的/总想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的/总想回忆”(《过渡地带》),内心的矛盾与纠葛是与选择相关的,也和1980年代的精神困境有着相通之处,而这种探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精神淘洗。不断地追求精神上的高地,内心深处却也一直保持着高处不胜寒的警示。所幸,这样一个看似沉重的主题在沈奇先生的笔下,经过他妙笔生花般的幽默与智慧轻轻化解,流露出一种大智若愚般的轻巧。这种洒脱自如的境界往往是由诗人这种随遇而安、达练安然的态度所决定的,诗行当中所特有的清逸气质也就在这种心境的熏陶之下愈发坚定,让这个原本不可破解的含混命题似乎得到了一种暂时的告慰。
除了对于哲思问题的追问之外,沈奇写作早期还表现出了一个先锋诗者的敏感,在《碑林与现代舞蹈》等诗作中呈现出了一定的现代元素,“他们只知道这是公园碑林是它的名字/这城市到处是古迹古迹就是公园/他们只有到这里来/可他们也实在发了昏/在如此古老如此神圣如此辉煌/如此庄严的——碑林/跳起了现代舞……”,将古都西安著名的文化艺术宝库——碑林与奔放、嘈杂的现代舞放置在一个空间当中,以往被称为书法爱好者朝圣之地的碑林无形之中就失去了它原本被赋予的各种意义。符号化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往往会造就简化与偏执的产生,尤其是对已经被先验性的固化了的物象来说,某种约定俗成的紧密联系往往会束缚人们的想象力与行动力,而诗歌在这里的功用就是揭开这些在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负累,还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已经被遗忘或者遮蔽了的真相。
《巫山神女峰》中这样写道:“其实你只是一块石头/一块像女神似的石头/光辉而不实用/你不因人们的想象而变大也不因人们的失望而变小”,“巫山神女峰”在历代文人墨客笔下是被历史文化所建构起来的象征符号,诗人在这里抛却了先在的观念负累,揭示出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寂静而威严的悬崖之上/完成一个/不承认空间有局限的/意向”。虽然在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于历史解构式的书写并不算稀奇,并且在对历史事件、文化现象进行消解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让人眼前一亮的经典之作,但是在对于现代技巧的运用方面也逐渐地走进了“过犹不及”的泥潭,一路先锋的观念以及接连的刺激与堆砌,让人感觉到眩晕的同时,自身也难以走出这种非理性的窠臼。在沈奇笔下这种解构并没有后现代的荒诞和玩世不恭的调侃,呈现给读者的是消解之后的冷静思考。作为诗评家的沈奇对第三代诗人的作品是非常熟悉的,也曾经对其中很多先锋诗作表示过支持,但是面对诗坛的疲软状态,他敏锐地觉察到:“反神性、反崇高、反深沉、反智性、反优美、反抒情、社会性、世俗性、功能性、荒诞性、片段性——一种准备不足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冲动,在很短时间内,将他者的现代感全面引进并接种于现代汉诗之年轻肌体,既促进了对旧诗质的代谢,也同时种下了新的非诗化隐患”[2]。因此,在诗歌创作当中他及时纠偏,在揭开历史真相的同时,除了还原事物本来的面目,更多的是建构它在历史长河中本来所应该具有的位置,并在此背景之上搭建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体系。
二、诗艺审美的显露
早在1980年代,沈奇诗歌当中的“山”“大海”“远方”等意象就已经引起了诗评界的注意。“山”与“大海”是他对于远方的想象和追念,也是他在理想建构过程中所勾画出来的寄托,“山”的高大险峻,在于不断攀登、翻越的行动中一次次得到印证,它带给人强烈的征服欲望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形成的障碍感,这些都足以使得一个渴望远方与理想的心灵产生悸动,诗意也在这一过程当中显露出来。“大海”作为理想的栖息地,给予追寻的灵魂无数次美好的想象,海的辽阔与悠远使得它一直以来都是诗人笔下的宠儿,在沈奇的笔下,这“海”似乎有着更加非同寻常的意义,“许多个世纪以前/我就出发了——”这里渴望的时间之久,代表着它不仅是某一个体的期望,更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心灵朝圣之旅,“——所有的山里人/矮个子的山里人/眼睛都陷下去了/古潭般地向往着/一个大个子的/海”,海的高远在“矮个子的山里人”眼里犹如神灵般高贵,亦如童话般圣洁,似乎飘忽不定,遥不可及,但是所有的“矮个子的山里人”依然一如既往的“走下去”,在这首《致海——北方之河》当中,海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理想的栖息地那么简单,转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执念,一种追求不得却又不得放弃的信念。西方的新批评派的理论中,“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就渐渐积累出其象征意义的分量,成为积淀着人类记忆的一个象征性的原型”[3]。“山”与“海”在沈奇的诗歌话语体系当中便成为这种具有能指概念的象征符号,成为解读他早期诗歌的一扇窗口。
除此之外,在《悬崖旁,有棵要飞的树》中,那棵“挣扎着”“扭曲着”“旋转着”的树,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曾卓的《悬崖边的树》,虽然创作的时代语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其中所迸发出来的生命的意志与力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首诗作也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怀抱着“飞鸟的梦想”,“仅仅为着/那个隐秘的/固执的/永不得安宁的/命题”,看似不可思议的联想从侧面展露了想要突破束缚和偏见的决心,看似悲壮的命运抗争在这里并没有带来西西弗斯般的绝望,因为它原本就应该是“枕着波涛”,拥有“自由的灵魂”,并且熟悉海鸥、海风的“大海之子”(《飞鱼》),即使不幸被无常的潮水抛弃在泥淖当中,即使因为短暂的“生的意志屈服于活的惰性”,但是也终要“被呼啸的春潮唤醒”。这些意象的介入使得诗歌在观念先行的时代显现出了鲜活的生命力,完成了对“树”与“鱼”的诗性想象,同时兼具了对自我理想的寄托。这样的书写突破了以往简单的哲理诗作的局限,不再是将情感与哲思直接倾泻而出,形成一种空洞无力、生硬简单的说辞与叫嚣,而是涵括在间接的意象当中在不经意之间所流露出来的理性思绪。
意象的流动不仅是沟通情感与理性思维的桥梁,同样也能够为诗作增添全新的律动感,使得整首诗作的意境呈现出和谐的美,增强了诗作的音乐性效果。如在《写作或水晶之旅》当中,“听到的只是/语言的/马蹄声声”,为冰冷的文字赋予了声音之后,将诗歌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快感书写得贴切而形象,这种心灵的震颤是只有为缪斯所折服所倾倒的人才能获得的情感慰藉。《你那颗千禧年的头颅》中,“唯你那颗/千禧年的头颅哟/仍壮硕红亮如石榴/随便取出一粒意象/便可令诗的中国/灿然而悦”,这首是和诗友洛夫之间的应和之作,自然也带有长久以来文人之间以诗词交流的古朴和风雅,但是在典雅的底色当中却也能看到一个成熟的现代诗者的调皮与灵动,这首诗单单从题目来看就已经韵味十足,细细品读之后,其中所富有的内涵可谓是绝妙无比,在一切的虚无与永恒的对决当中,经历过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轮回,所有的魔性与禅意也可能在某个特殊的阶段互为因果,但是在这个斗转星移、物我混淆的世界当中,一颗饱含诗意的头颅便能够让整个“诗的中国”为之悦动。
成熟的诗者往往具有语言的洁癖,对于字词的推敲斟酌会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坚持。扩大到句式以及诗行的设置与排列,就更有非常严格的讲究,这也难怪,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在形式层面,除了语言上鲜明的个人特色之外,句式的选择以及排列均是体现个人风格的一扇窗口。
沈奇在2003年时就提出:“形式非本体,但系本体之要素。形式翻转为内容,成为审美本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艺术的一大进步。”[4]体现在他的诗歌写作当中,对形式的重视就一目了然。他早期的诗作很少用较为驳杂和冗长的句式,大多以精练而又意蕴悠长的短句为主,以简练的语言来营造诗歌的意境,呈现诗歌所要表露的情态哲思。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当中,诗意的涌现却要远远大于语言本身的意思,因为在他看来,诗的表达不能过于圆满,在诗行之间要留有余味,整体诗歌的意境表现上要能够发散出余韵,“是怎样的月光/喂饱了你的想象/准备去做一个/可以抚摸的梦//……早晨的忧伤/来路不明/与破碎的风无关/与想象的月亮/和月亮的想象无关//唯几滴雨声在问——/谁是清醒过的人?”(《月义》),“月光”和“雨声”两个简单的物象倾吐了一个关于“雨夜”的心事图景,看似轻巧,但实则道出了人生当中所能够遇见的各种猝不及防的意外安排与想象、期待之间的落差。“以梦喂养/心中兰草/等/秋风拥抱”(《慵夏》),简单的十三个字分为四行,但是每一个汉字背后所包蕴的情思与韵味都发挥到了极致,夏日对清凉的企盼以及自我内心的修行渗透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个“等”字为一句,极为传神。
三、从个人经验到古典理想的重构
“与‘先锋’为伍,为之鼓与呼,在我来说,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基于人文精神及历史成因的担当与责任。”[5]进入1990年代之后,对先锋的反思使得沈奇这一时期的诗作当中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征,既没有完全摆脱一直以来先锋诗歌观念的影响,毕竟他一直都深谙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纹理,并且长久的致力于现代诗歌的关照和研究当中。但与此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了现实空间当中。这一空间既包括个人生存的日常,也含蕴了滋养其成长的文化氛围,逐渐将个人日常经验与诗学观念糅合在一起,并达到了个人历史经验与诗学形式的完美统一。尤其是在写给友人的诗作当中,既不乏诗歌观念的表露,包括诗学技巧以及语言思维的设想,亦投射出了情感的特殊魅力,以往诗歌当中的高蹈抒情在这些诗作中逐渐地渗透出了个人经验的信息。这一时期已然显露出对于古典的亲近感,亦或许长期以来一直并未彻底地走出。
从《寻找那只奇异鸟》中的部分诗作开始,到《淡季》,再到《印若集》,从写作时间来推算,诗人这一时期开始着重力于两岸现代诗理论与批评,或许是在诗学肌理的切割剖析当中逐渐挖掘到了传统的魅力,或许是长久以来驻足于诗歌现场,敏锐的理论嗅觉使诗人为诗坛的积弊找到了良方,在1990年代后期,对于诗歌语言的重视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诗歌实验就融合了日常经验与古典韵味。“想象一座小小的古典庄园/在美丽而幽静的汉江河边/白墙黑瓦前厅后院”(《沈园》),古典意味十足的庄园是诗人对理想的生活居所的精心勾勒,看似不合时宜的“后退”与停留,正是诗人对这个被钢筋水泥所裹挟的冰冷尘世的拒绝与反省,现代人在无限制的欲望驱使之下心灵失去了依托,灵魂也开始失重,对神性的呼唤不仅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真谛,同时,诗人也指出了在经历过1990年代的迷惘之后诗坛的重要转向,“路多起来的时候/选择便成为陷阱更成为负担/你只能站住,或者叫‘退出’/在疯长的水泥森林和并未完全/失去神性之光的蓝天白云之间/在沉沦或飞升、死于非死之间/拉上:那道诗性想象的窗帘”(《沈园》),诗歌承载了太多它本不应该有的负累,它所展现出来的神性与灵性、抽象与本真,关涉到生命最根本的终极关怀才是诗歌的本质,而不应该在文化的废墟与现实的泥潭当中亦步亦趋。
“虚根素心/目垂而渺/枕清露时小眠/饮流云而微醺/澄怀观照/观一世界的喧嚷/与沉默中理解/草木性情”,这首《睡莲》以典雅、清新的文字铺设了一个境界高远、精神矍铄的物象,空灵的语言背后是诗歌语境的雕琢与营造,文字在这里成为意境堆砌的基石,对汉字思维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已见端倪。尤其是诗歌当中出现的一系列颇具古典意蕴的意象,与古典诗歌当中寄情山水自然与神性生命的审美特性相契合,禅意在其中已经有所显露。其实“现代禅诗”在沈奇的诗论当中早就所提及,在1999年的《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一文当中,他就将“口语诗”与“禅诗”作为新世纪诗歌发展的主要流向。在1990年代末期,他的诗歌创作也即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迹象,《天生丽质》面世之后,这一心象或者理想可以说是得到了全面的绽放,《天生丽质》在诗坛获得了极高的礼遇,无论从诗歌观念的冲击还是诗歌本体层面来讲,这部诗集对当下诗坛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都不可不谓之壮观。
单从题目来看,《云心》 《茶渡》 《青衫》《秋白》 《松月》,诗人所选取的两个单独汉字所蕴含着的诗意空间就已经足够耐人寻味,每一个单独的汉字在这里都能够承担起一个想象的诗意空间,再加上通过汉字之间的叠加之后所形成的画面感,以及同音字之间的巧妙搭配,使得整个诗句更显得余味悠长。除此之外,这种意境的营造当中所形成禅意,更是整首诗作当中不可缺少的画龙点睛之笔,“孤云如佛/独立晴空//孤云不语/也无雨//雨在心里/语在山溪//其实孤云不孤/孤独的只是那片//再无其他云彩的……天空”(《孤云》),孤云与天空互为依存,互为因果,“不语”与“无雨”之间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音韵上的相似之处,更有语义方面的相通,“孤云不语”即是万里晴空,当然也会“无雨”,“雨”在云的心中,而“山溪”中的私语却最有情趣,“孤云不孤”,孤独的却是少了云彩的“天空”,一个“孤”字在这里充满禅趣,“孤”与“不孤”也只是在于心。
在诗人看来,《天生丽质》的写作是他在四十余年的诗歌写作之余所进行的文本实验,但是这种实验一定是建立在深谙汉语传统的基础之上,并与古典诗质的脉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在《写作或水晶之旅》一诗当中,沈奇将写作称为“水晶之旅”,将每一个字词的光芒缀连起来,倾听语言背后的声音,并触摸到它的温度与质地,从而在这个自由的王国之中搭建起属于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微妙关系,任凭那晶亮的珠子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呱呱坠地。相信这一旅程之中应该会出现更加曼妙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