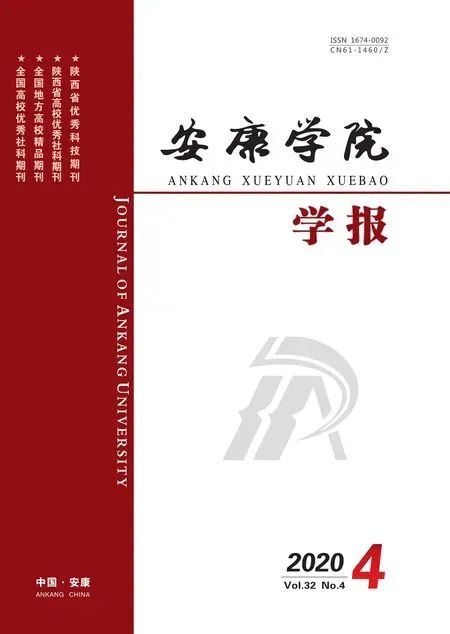杜甫涉病诗的情感解读
2020-12-27李胜男
李胜男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涉病诗是指以自我或他人的疾病作为主要或次要描写对象,借此来抒发诗人情志的诗歌。以诗歌中是否涉及疾病描写(肉体上或精神上)为标准,可以发现杜甫现存的涉病诗共有207首①杜甫现存的涉病诗共207首,其中长安求仕时期(746—755)3首;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19首;入蜀与草堂时期(759—765)49首;夔州时期(765—767)100首;漂泊荆湘时期(768—770)36首。此统计根据仇兆鳌《杜诗详注》得出,中华书局,2015年版,以下引用杜甫诗句及篇名均出自此书。。这些诗内容丰富、主题不一,背后蕴含的情感也多有不同,或在壮年时已有早衰之感,或在空间的无垠中深觉孤独,或始终坚持着“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一、壮年早衰感
杜甫一生患病多种,从天宝十载作出第一首涉病诗《敬赠郑谏议十韵》,到大历五年的绝笔诗《风疾舟中扶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时间跨度长达十九年,期间杜甫一直在进行涉病诗的创作,足以看出其长年受疾病侵扰。在杜甫的疾病世界里可以看到,杜甫的时间要比他人流逝得更快,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生理上和托物言志的物上。
天宝十载,杜甫不过四十岁,就已在第一首涉病诗《敬赠郑谏议十韵》中发出“多病休儒服”的不得已之叹。此时他仅仅吐露己身患有疾病这一事实,却未具体阐明其所患疾病的种类,亦未说明自己的生理状况。天宝十三载的《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杜甫第一次在诗歌中把己身病态做了细节上的展示,“疟疠三秋”说明他已患有疟疾多时。此外,同年所作的《进封西岳赋表》里曾言“况臣常有肺气之疾”[1],可知他此时已得肺病。疟疾与肺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使杜甫“颜色恶”、不能眠、寒热交战、头白眼暗、有褥疮和“皮黄肉皱”。此时杜甫四十三岁,由于肺病和疟疾属于对身体危害大、发病期长且极易产生各种并发症的慢性病,老杜的生理和心理皆承受着巨大的打击,使得他不可避免地产生“命如线”的哀叹,也是在此时,他开始产生壮年早衰之感。大历五年,杜甫抱病躺在潭州开往岳阳的船上写下《风疾舟中扶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一绝笔诗,这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首涉病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次描写自己的病态。此诗开篇便从风疾叙起,这一病症早在广德二年的“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就曾提到,可见其病经年未愈。此时他也不过五十九岁,却在这种患病多年且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察觉自己已经气失调、汗涔涔、行需杖了,宛如耄耋之年的形骸,甚至认为自己“尸定解”,即将迎来肉体的消亡,他的壮年早衰感在此达到顶峰。
除了在生理上有明显展示外,在托物言志的物上也暗含隐曲,别有深意。杜甫擅于咏物诗的创作,早年喜爱咏雄壮之物,如写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写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但在入蜀之后,咏物诗描写对象的特征从雄壮转为病枯。上元二年秋,杜甫在成都作《敬简王明府》,一联“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道尽不能道之苦楚。以病骥自拟,以秋鹰自比,叹己穷途流落,望有高义一援,也就是陈贻焮认为的“所幸有过几天主客之谊和一段文字因缘,迫于眉急,只得硬着头皮写诗去诉苦求助”[2]。同一时期,杜甫又作《病柏》 《病橘》二诗,这两个枯萎憔悴的物象使得杜甫产生了同情、悲悯之感,面对无人问津的衰病之柏、失贡之罪的酸涩病橘,杜甫仿佛看见了自己。从民胞物与、物我情同的角度来看,这是杜甫对自我认知的投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骁腾到病骥,从雄鹰到病柏、病橘,恰如自己从健壮到老病。由此可见,生理上的早衰之感不知不觉被杜甫写进咏物诗里,造成托物言志的物发生变化。
杜甫在涉病诗里频频写到“老”字,足以看出他对自身衰老速度快于常人的在意程度,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象呢?
其一,疾病的多样性和长久性不仅对肉体造成损伤,更是对精神的无限消磨。消渴、肺病、疟疾、齿疾、耳聋、痹症、无力等都是杜甫所患的病症。翻阅杜甫的涉病诗可以发现,老杜提及次数最多的疾病是消渴。从天宝十三载初春第一次以“长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频”的隐喻出现,到老杜逝去的大历五年再一次以“不达长卿病”的形式出现,时间跨度长达十六年,足以见此病绵延之久、磋磨之深。此病会使患者少眠、畏热、口干,且无法根治,对肉体和精神的损害都很大。除了消渴,疟疾也一直困扰着杜甫。“寒热百日相交战”说明杜甫患的是“间日疟”——寒热往来,隔日而发,迁延不愈[3],这种慢性疾病长时间地损耗病人的身体机能,“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就是杜甫对此病发作时生理状况的细致描写。此外,齿疾、耳聋、无力等症状虽不能辨定是自然衰老的症状还是消渴、肺病、疟疾这三种慢性病的并发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发力,加速了病人躯体的老化。纵使杜甫竭力想要控制住生命的快速流逝,如他努力学习医学知识,创作了大量的涉医诗、涉药诗,熟谙中医养生之法,甚至为治疗疟疾而“徒然潜隙地,有腼屡鲜妆”,但都只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无法完全根治疾病,以至于他在病逝的前一年还发出“余病常年悲”的萧瑟之感。
其二,“羁旅病年侵”是造成杜甫有盛年早衰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作为“老儒”的毕生追求,恰如庄子所说的“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4],即指在主体修养方面,以达到仁、圣境界为极限,在社会政治教化方面,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然而,安史之乱一爆发,明皇仓逃、肃宗登基、借兵回纥,战争不停、纷乱不止,老杜的理想也变成了空想。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地将杜甫个人拖入郁郁不得志的人生状态,他只能四处漂泊,远离朝堂。自天宝十五载起,因战乱,短短几年杜甫就奔赴过奉先、白水、三峡、鄜州、延州、长安、凤翔等地。旅途之艰辛,从《彭衙行》中可窥见一二。被安史叛军抓回长安时,老杜自叙“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表露出的早衰感尤为强烈。杜甫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却在离开夔州之后,又经过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州、耒阳等地。旅于一叶扁舟,远离政治中心,原本就使杜甫心绪不佳,加之气候不适,贫病交迫,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的早衰之感。
二、个体孤独感
在杜甫创造的涉病诗空间里,弥漫着一种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这一份疏离的格调原是与杜甫积极入世的儒学观点相悖的,但恰恰因为这两者在杜甫身上达到了和谐,才塑造出一位浩瀚无垠空间里的孤者形象。当患病的杜甫面对亲友的分离、早年好友的生疏、密友的逝世及远离“故园”时,个体孤独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在写给亲人的涉病诗里,大多是亲人不在身边的情况,杜甫既因担忧对方生死却无计可施而感到无助,又因相见之日的遥遥无期而倍感孤独,《忆弟二首》就把这种复杂的情感展现得一览无余。第一首首联开门见山,杜甫直言在战乱中与弟失散,虽然听说弟弟已去济州,但因不能确定消息的真实性,仍然心有不安。三四句又将情绪绷得更紧一些,杜甫收不到弟弟的信件,只能希望战乱早日平息,然而这愿望却是极渺茫。五六句把紧张感又上升一层,自失散之后,老杜辗转相忆,忧思成病。末联的情感却陡转平淡,原先的忧愁变为悔恨,强烈的恨意却因无处安放,只能随东流之水缓缓消逝,最终化为平淡,这一举措的无奈与哀伤溢于言表。第二首前两联的情感始终在上扬,河南定、盼弟归,杜甫的孤独仿佛即将要被兄弟相见的喜悦冲淡,然而后两联的音书不到、花开无人赏,再一次使杜甫的希望破灭,诗人的孤独感卷土重来,淹没了一切。
写给友人的诗,内容更为丰富些,表达方式也更为多样化。其一,当友人在政治舞台上更进一步时,杜甫虽为好友同喜,却也不可避免地会自伤自怜。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首大段,总以怀人意,摄起高、岑之文章官职,起法便妙,似以‘故人’侧到‘今我’”[5],“我”之境遇在诗歌一开篇就已明了:“今我独凄凉”,余下部分虽有宾主并提,但诗人的孤独感是贯穿全诗的。其二,早年结交的好友却不曾在杜甫处于糟糕境地时送来一丝安慰,借诗讽刺世态炎凉的背后,是深深的孤独与无奈。“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虽是旅中寂寞,思想故人的意思,但仇兆鳌注“盖裴在蜀州,但寄诗而未尝一过,故公讽之如此”,颇有几分道理。随后所作的“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道出旧日同僚无人问津之哀伤。《棕拂子》一诗又借物来表达诗人认为君子不应遗旧交的观点,杜甫对于品节的坚守反衬出他人对于品节的践踏,更突显了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个性。其三,生平好友逐一离世,难免使老杜产生兔死狐悲之心。“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是苏源明、郑虔同在广德二年卒后杜甫所作,好友接连去世,世上再无知心人,无人同行之孤独感充溢在字里行间。此后又有《八哀诗》 《遣怀》《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等悼亡诗,无一不是情感真挚、痛哭流涕之作。好友先己离世,老杜独自行走于天地之间,其悲怆与孤独之沉重非常人所能解。
杜甫的异乡孤独感蔓延在每一天且浓度极高,有两种表现。其一,因其常年漂泊,这份孤独体现在对“故园”的依恋上,莫砺锋先生认为“‘故园’即‘故国平居’,也即‘京华’、长安,诗人自己的追求和失败都发生在那里,唐帝国的兴盛和衰败也集中体现在那里,所以长安是诗人魂梦所系之地”[6]191。其二,离开“故园”后,杜甫无法把任何一处居住地当作故乡来寄托情感,因而“客堂”和“客居”就承载着老杜的他乡孤独感。《杜臆》谓“客堂与客居不同”[7]232,“客居”是诗人在他乡长久居住的场所,“客堂”是诗人在他乡短暂借住的地方,老杜对“客居”的感情明显要比对“客堂”的感情更浓烈些。由此可知,对于杜甫来说,处所不仅仅是提供居住的地方,还是寄托情感的空间。故,在此以《客堂》为例,详细剖析老杜异乡孤独感的生发和走向。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首段是前十四句,杜甫开门见山,直叙自己远离故乡,住在有深山、林麓的客堂,但因常年漂泊身患疾病,行走十分困难。纵使如此,老杜做客已久、思乡之心切却是直白不隐晦的。第二段是从“客堂序节改”至“营葺但草屋”,客堂之景的秀丽令老杜开始回忆成都往事,他把谢官这一举动归结为自己性喜独幽。末尾十句是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杜甫打破了在前文所述谢官之理由,转以坦白诉说自己的愿望,即归朝报主。事实上,这份归朝报主之心直到杜甫生命终结都没有实现,当了解杜甫的整个政治生涯后再来看这首诗,无异是孤独的、悲凉的。杜甫的异客之情,因漂泊而增添疲病,因思归而复生微小的希望,因渴望归朝报主而加上伤感,最终因一切理想的破灭而回归孤独。
不管是写给亲友的涉病诗,还是自叙漂泊的涉病诗,其中的孤独意味可用杜甫自己的诗句来做一个总结:“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此时诗人心目中的白鸥已不再如早年的诗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那样具有豪情英气和飘逸色彩,而变成孤独、飘零的象征了。”[6]168
三、“再使风俗淳”之坚定感
杜甫在创作涉病诗时,常常把疾病与仕、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疾病引发的结果不止仕和隐。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老杜对“再使风俗淳”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与坚守。以《夔府书怀四十韵》为例,从中寻找疾病与其引发结果的蛛丝马迹,把这些细枝末节串联起来可以发现:疾病,促使杜甫更急迫地求仕,但当他的求仕之路遇到挫折时,疾病就成了他自我安慰的借口,即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对仕途的追求。杜甫仕途之路的终极目标是“再使风俗淳”,为实现这一理想,老杜甚至可以牺牲自我的仕途。
《夔府书怀四十韵》是在大历元年秋时作,全诗可分为四节。
第一节自首句至“拔剑拨年衰”。首联“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为全诗划定范围:不仕河西尉是杜甫个人的事,官军收复蓟北一带(安史叛军的根据地)是国事,诗人意在阐释国家与个人之间命运与共的关系。萍流六句,自叙不才,因帝王慈恩而得以从仕。拙被六句,辞官居蜀,因疾病而自惭不能为帝王分忧,“病隔君臣议”这一句,是疾病作为分隔君臣的缘由第一次出现。事实上,杜甫一生未进入政治中心,他离帝王最近的一次是在至德二载,从长安逃往肃宗行在——凤翔,因此被授左拾遗,但很快就因房绾之事被贬华州,从此远离君主。因此可以认为,疾病是老杜用来自慰不得帝王重用的托辞。参考其他的涉病诗可以发现,这个借口被老杜频繁使用,如“多病休儒服”“入朝病见妨”等,还包括本节最后一句“拔剑拨年衰”。老杜不愿意在诗作中承认君王对自己的疏远,他更愿意把仕途不顺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年衰多病,这一粉饰行为,实际上是他一直以来从未放弃过求仕的证明。
第二节自“社稷经纶地”至“答效莫支持”。上八句写肃宗之乱,中十二句写代宗之乱,后八句为帝王谋策。肃宗之时战乱四起,遍地皆兵,连都城都难逃血腥。肃宗死后,代宗执政,藩镇之患尤为严重,再加上蛮夷来袭,边尘四起。杜甫以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纷争不断的两个根本原因: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老杜明白帝王绝不会因国家大事来询问位卑者的建议,但他依然饱含热情与希望,假设自己与帝王因时事而长谈问答,他甚至已经为解决纷争而提前想好了对策:息兵端、开言路。察其同一时期所作涉病诗可以发现,杜甫此时深受疾病侵扰。此篇诗作的前一年,杜甫就在《春日江村五首》中说过自己的牙齿已经开始剥落、腿脚不便需要扶着拐杖才可以行走。同年,在《返照》中自叙因肺病加重只能躺在床上,还在《遣怀》中谈到自己饮食不佳、频繁呕吐。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杜甫还能观察时局、分析国势、究国乱之病根,不得不说老杜为此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疾病不能阻挡他从仕的念头,反而变相地使其从仕之心更为迫切,他迫不及待地去了解国家大事,以期为君分忧。
第三节自“使者分王命”至“蜀使下何之”。这一节里,杜甫把目光从整个国家缩小到蜀地,他的关注点在夔州民困。蜀有崔旰之乱,有荆楚将乱的预兆,有民穷盗起的恐慌。亲眼看到的蜀地纷争,使老杜求仕之心更强烈,因为在杜甫看来,唯有辅佐帝王这一条路是解救蜀困的最有效手段,而老杜坚定不移持此观点的原因是他从年幼时起就受到的儒学教育。“儒”字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杜甫也曾以“老儒”“腐儒”自居,而儒家一直以来都倡导积极入仕,只有走上仕途才能辅佐君王、匡扶天下,这与老杜想要从仕的渴望相吻合。老杜的涉病诗中干谒诗的数量众多,也说明其从仕的终极目的是“再使风俗淳”。
第四节自“钓濑疏坟籍”至末。钓濑八句写杜甫之境况潦倒,后八句诗人深期有济世之人出现。此诗之末尾,“深期济世之人,应上‘答效莫支持’”,在这里,老杜的求仕之心淡化了,而渴望天下安定的愿望被浓墨重彩地凸显。正如王嗣奭所说:“因致嘱当事有志云台之业者,盖功不必自己出也”[7]270,这一句点明杜甫从仕之目的是为了辅佐帝王,“再使风俗淳”。当国家危亡之时,诗人的终极目标“再使风俗淳”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彰显出来,因此杜甫不再纠结于自己的仕和隐,而是期冀天下有才之人奋起,协力拯救国家出水火。在这场转变中,杜甫个人仕隐的重要性被淡化,他的眼光是整个民生、整个天下。这类似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8]中的天地境界,是超越功利的。这与杜甫的另一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叙相同,这首诗同样有一个明晰的超脱线索:先是困于衰病,再是自叙无人援救之孤独,但杜甫并没有仅限于改变自身一介儒生的境遇,而是渴望天下寒士的生存境遇皆有所改善。最后一句“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又达成一层超越,即“至人无己”,杜甫原是渴望自己从衰病、孤独的境遇里挣脱而出,在这里则转为把天下寒士从衰病、孤独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使个人再一次陷入衰病与孤独也无所畏惧。
通读全诗,可以看见疾病与“再使风俗淳”这一政治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除去上文所提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在大历三月所作的《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也同样阐述了这一复杂关系。前五首均阐述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被除后各节度使相继入朝这一事实;在第六首诗中,老杜不自觉地担当起言官角色,规讽君心、豫防逸欲;其七又再次把抱病作为不能身见君王的借口;最后以地域广而人才盛这一观点作结。将整诗脉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不论身体状况如何糟糕,老杜都一直密切关注时事,并依然渴望能在帝王左右,基于现实的残酷,他又以疾病来宽慰自己,导致这份宽慰带有凄凉的意味。但是,杜甫的眼界不止于自身,而是天下,当目睹民生安稳时,他更乐意去赞美为平定战乱付出巨大努力的当世英雄(如李光弼、郭子仪),此时,老杜个人仕隐问题带来的凄凉感被冲淡。杜甫对“再使风俗淳”这一理想的坚守,贯穿于他的整个涉病诗世界。
杜甫的涉病诗构建起一个独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杜甫畅快淋漓地表达着自己的所思所想。身处困境又身染疾病的杜甫,在表达自己对疾病的看法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浓烈的个人情感。首先,由于长年患有多种疾病和四处漂泊,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壮年早衰感,主要体现在生理上和托物言志的物上。其次,在患病的情况下,杜甫面对亲友的分离、友人的升迁与疏远及自己的漂泊不得归时,产生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最后,疾病,一方面使老杜报主从仕之心更切,另一方面又成为老杜在仕途受挫时的慰藉。老杜求仕之热情即使是在患病最严重时也从未消退,但是,求仕的最终目的是“再使风俗淳”,在实现这个造福社稷生民的社会理想的过程中,杜甫个人的仕与隐被消解了。盛年早衰的哀伤、孤立无援的茫然、对理想的坚守,这些情感融合共生,使杜甫的涉病诗闪耀出特殊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