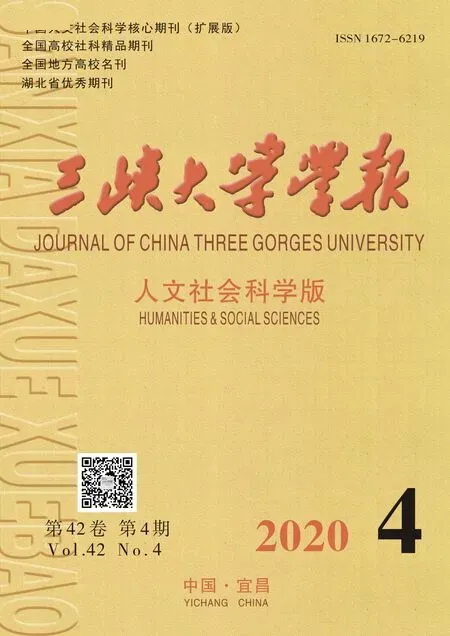批评的在场和文学经典的建构
2020-12-24聂家伟
聂家伟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取得合法性地位并形成一门独特、鲜明的学科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也举步维艰地开始进行。虽然当时已出版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但是,一些学者却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提出了质疑。1985年,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在《文汇报》上发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随后,施蛰存提出“当代事,不成史”以示呼应与认同,之后,文学界对此话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尽管争议不小,不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却从未停步,截至目前,已经有一百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但是,唐弢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工作的推进而成为过眼云烟,反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20世纪90年代,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在北京大学进行系列演讲并结集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出版,在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背景下,佛克马的演讲和著作激发了中国学界探讨、研究“经典”的热情。比如,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出版,既是钱理群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视角的副产品,更受到当时“经典”话题的影响。有关“经典”话题,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而文学史的写作、文学批评正与这场“经典”之争息息相关。
一、经典建构的时间意识
关于“文学经典”,有两类界定:一类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即认为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属于所有时代,并且是常看常新,它因其自身富有魅力而成为经典;一类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即认为经典不是因为作品自身的魅力,而是由于作品之外的刺激因素被建构的。与此相应,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认为文学经典无需被发现、被命名,它们是自动呈现出来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则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需要在阅读的基础上慢慢体现出来,它需要同时代的人或后代的人不断阅读、研究、评论、选择。
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认为文学经典是自身带着“经典”的光环从天而降的,而事实上,无论怎样,这种经典的光环都是作品产生之后被赋予的。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作品可谓灿若星辰,但任何时代的任何一部经典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都是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诗经》如今被奉为经典,无可置疑,但是其地位却与先秦的“称诗言志”、两汉的经学化以及后世说诗、解诗等文化背景分不开,如此才造就《诗经》人类社会学、历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侧面的阐释向度。诗人陶渊明的成就,在他那个时代,尽管有九首诗歌被萧统选入《文选》,但是几乎同时代的刘勰,在其“体大虑周”之作的《文心雕龙》里,却只字未提“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也只是将其放在中品而已。直到唐宋时期,陶渊明的诗歌得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推崇,他才渐渐为更多的人熟知,渐渐产生影响,从而慢慢奠定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计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36作家并非按照“经典”的标准来创作文学作品,而其“经典”之誉也只是后世不断累积所赐。我们今天以为天经地义的文学经典,其经典地位并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确定了的。再以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为例,也可见一斑。
《狂人日记》现在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其发表并不像文学史上所说的,立刻引起思想界、文学界巨大的轰动。这篇小说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直到大半年之后,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上发表傅斯年署名为“记者”的《书报介绍》,在向广大青年推荐《新青年》杂志时,才顺带提到《狂人日记》,不过,他认为该小说以写实的手法寄托志趣,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2]。同年4月,傅斯年又以“孟真”之名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一段疯话》,详尽表述了对“狂”的阅读感想,这算是最早的对《狂人日记》的思想内涵进行解读的文章[3]。同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吴虞提出“吃人”与“礼教”两个对立的概念,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定位在对礼教的批判上[4]。不过,真正比较成熟的从文学艺术角度进行评论的则是1923年10月8日茅盾在《时世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一文。茅盾谈到《狂人日记》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并详细回忆描述当时初读《狂人日记》的新奇感觉,认为“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进而看出这篇小说在用新的形式、新的现代技巧来表现作者的思想的意图[5]。至此,鲁迅的《狂人日记》因他的革命闯将的身份特殊以及评论众多,渐渐为更多的人熟知。它是一篇可以进入文学史经典书写范例的作品,也因为“表现的深刻”以及“形式的特别”而成为一篇文学经典著作。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鲁迅已享誉文坛,受到学界的认可,但是,并非得到一致的推崇。1926年鲁迅已经出版《呐喊》《热风》等集子,而《祝福》《伤逝》等名篇在当年也结集成为《彷徨》集;而自文学革命至此时,也已经发表了诸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重要文章;但当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国语文选》(共6集)时,编纂者选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汪精卫、邵力子、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等新老各个阶层人士的文章,甚至选了周建人、周作人的文章,但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考虑到这套书的读者群乃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力量,可以想见,鲁迅的文章风格和态度并不是时人所喜欢的[6]23。
不过,应予以承认的是,经典的两类界定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两者均有合理之处。即是说,所谓“经典”,既有客观性、恒态、普遍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动态、相对性的一面。有诸如《荷马史诗》、莎翁戏剧等世界公认的普世经典,也有限于某一国度的经典文本。但无论怎样,那些普世经典之作在经过历史化的过程之后,才真正确立其经典地位,而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经典”特性也使得它们与非经典文本截然区别开来。鲁迅及其小说、杂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通过一代一代的批评建立起来的,但是,当其地位确立后,其独特性又作为与其他作家以示区别的标志,成为一个经典的标杆。不过,就“经典”一词的英文“classical”来看,其本身既有“经典的”之意,也有“古典的”“传统的”等含义,而那些被普遍视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大多离我们的时代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经典”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作品,只有那些过去的已被历史化的作品才属于文学经典,似乎当代文学离得我们太近,没有资格列入“经典”之列。
毋庸讳言,文学经典的历史化过程中,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某一时代流行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经典,那些获奖的作品也不例外。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不过百年历史,放置世界文学之林也显得微不足道。但另一方面,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大系”的编写、50年代初在政治呼声中的“现代文学史”的编纂,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90年代的“经典再解读”,我们都看到批评家急于将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迅速将之历史化。不可否认,经典建构需要时间,但经典的建构工作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需要时间慢慢沉淀,不能操之过急。而我们的经典建构工作,往往就像修建希望小学、南水北调这种工程一样被提上日程。正因为如此,有许多学者反对将当代文学经典化,在这批学者看来:既然经典化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我们过早地断言或急于将某部作品经典化,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如果说,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时,我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研究的沉淀,使中国现代文学取得合法性地位,对经典作家确立的认识没有太大的分歧的话,那么,该如何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地位,又怎么面对或处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当代文学批评能否担负起经典建构的重任?
二、批评缺席—时间评判的误区
中国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已经发展七十多年,在高校的学科建设里也似乎成了气候,但是由于当代文学被划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而其学科基础都是由一批治现代文学的学者所建立的,这就导致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以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导。而现代文学的研究总体上已经走过经典化的历程,其当下的研究更侧重于史学研究,因此,受此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研究,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人就要比进行文学批评的人多得多。此外,由于文学史研究在研究难度上要略高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更容易使人产生“高人一等”的光晕,而批评界对于“史”的偏好,使得当下的文学批评被文学史所劫持:文学史在文学研究中几乎被视为最为“客观”也最具权威的知识,被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已经被经典化,而文学史建构的经典秩序以及对经典的阐释话语反过来又制约或规范文学批评,致使在文学批评文字中,“结论性陈述多于分析式描述,概念演绎取代文本解析”[7],“文本的意义,有时可能不完全是以文学为中心,而是成为文学史演变、重要的文学史现象等的一种印证”[8]181,从而使文学批评有成为文学理论(文学史)建构的练靶场的危险。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谈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又说:“文学理论如果不根植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不能‘凭空’产生。”[2]32-33可见,固然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三者关系密切,文学批评要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指导,但是,文学批评毕竟只是文学批评。脱离了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的文学批评,被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劫持,看似在行使文学经典建构的责任,事实却在走向反面:文学批评被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一些空洞的概念、理论、结论式话语架空,而未真正关注当下文学,文学经典的建构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切实际。
(2) 虽然不同生物炭添加比例的土壤样品水分总蒸发量相差不大,但随生物炭添加量的增大,土壤吸水量及连续蒸发12天后的含水量亦增大。
惟其如此,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真正在场的批评处于缺席状态。本文所说的在场的批评出于专业批评家之口,但这类批评家虽多出自体制内的学院,其批评却有别于学院派那种重理论研究或文学史倾向而忽视具体文本分析的批评,也有别于媒体或大众之口的时评或“酷评”,它们从历史现场出发,评述出具体作品的具体特色,真正贴近作品,是能够把握作品脉搏的真正在场的批评。在场批评的缺席,导致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批评意识和深度,多所谓“酷评”、时评或学院派批评:批评文字本身缺少对当前文学的凝视与思考,只盯着跟当下相关的文化现象,置身于均质化的大众之中,使其更趋近和亲近大众文化,但对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和价值判断置之不理,甚至沉浸于一堆与文学相去甚远的术语或空洞的概念之中。凡此种种,均以不同批判形态掩盖自身的缺席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批评氛围之中,批评家一边对着作品指点江山、逢人说项,一边却对文坛的批评牢骚满腹。
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考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与现代文学作品相比,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每年都呈几何式增长(据说当前长篇小说每年以三千多部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当下的批评家将批评、经典化的任务交给时间——亦即后来的研究者(批评家)的话,这是否是一个明智之举:在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面前,后来的研究者是否有能力“披沙拣金”,发现经典?此外,随着当代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如果不区别评述和对待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是否意味着越写越厚?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说法,其实就是放弃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标准,将其经典化的权利和义务推给时间和后人,意欲阻断当代人认识和理解当代文学经典的路径,从而将经典的当代建构悬置起来,但问题是:难道后人真比我们同时代的批评家更可靠、更具有发现经典的眼光吗?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要知道,时间在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历史面貌的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感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窠臼”[9]。正因为亲历了当代文学现场,我们有着切身的感受,更容易把握住历史的现场,那些在场的批评作为文学史料,生动记录了当时文坛的情况,更利于后来者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期,萧红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叶紫小说集《丰收》作为“奴隶丛书”,在鲁迅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并得到鲁迅为之作序的殊荣。鲁迅的序,对三部小说(集)都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指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这些评论文字也成为后来者再研究的基础。而几乎同时期,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版,当时,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还只过去七八年,但《大系》各集的编选者却以各自独到的眼光选出了代表这十年的作品和文章。这套《大系》的出版,为我们展现了第一个十年文学界较为真实的面貌,其各集导言中的批评文字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即使后来的学者从史料中挖掘出其他一些作家作品,也难以改变《大系》对这段文学史总的把握。
将文学经典交由时间去检验的做法,无疑只是“今不如昔”“厚古薄今”的老生常谈,似乎只有时间越久的作品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而当代文学没有资格成为经典。此外,那些“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的刻意贬低也只不过是意气用事,就当代文学本身的活力而言,当代文学的创造力并不逊色于现代文学。将经典交给时间不仅贬低了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推卸了批评家的责任,也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当代批评家的能力。《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王瑶于1951年开始编纂的,其时离现代文学结束仅仅两三年;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8)》,成书时间是1961年,离现代文学结束也不过十年多而已,而离最近的时间也只三年。虽然撰写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凭借着各自的深厚学养,写出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文学史著,从而使其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范式,或影响后来中国大陆“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这两部文学史著都有或大或小的缺点,但是撰写者却履行了他们应该有的责任,并未“以待来者”,这两部文学史著也为这两位学者带来了本专业内的无上殊荣。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界定和修正“传统”体系:“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11]3新的文学作品只有拥有某种独特性,进入之前的文学经典所建构的秩序时,通过不断调整,才能达到新与旧(传统)的适应。但是,在解读某些文学作品时,事实却往往正应和了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在场批评的缺席,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在没有对历史语境有所把握的基础上,用当下的观点解读过去,从而产生“溯及既往”的强制阐释,即“以后生的场外理论为标准,对前生的历史文本作检视式批评。无论这个文本生成于何时,也无论文本自身的核心含意是什么,都要用后生的场外理论予以规整,以强制姿态溯及既往,给旧文本以先锋性阐释,攀及只有后人才可能实现的高度”[12]。但是,文学批评等“社会科学的众多结论具有历史性特征。逾越相对的历史语境,合理的命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13]。如果说沈从文这类作家有着向往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太为过的评判的话,那么,说沈从文是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这个评判则显然是无稽之谈。要知道,沈从文文学创作高峰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业的发达、城市的兴起是一个历史趋势;沈从文的小说中,虽然有一定的反思现代性的色彩在里面,即使我们可以用生态批评理论去批评其小说,但是他对于乡土的热爱和对于都市的隔膜或抵触,更多地是基于对身处其中的两类人人性的比较上,他并没有那种生态意识。正所谓,其“解读无法在既有的历史语境得到足够的支持,既有的史料、理论均不能证实特定的结论,这样的评价就遭到否定”[14]。
三、在场的批评与经典建构的意义
针对建构文学经典的因素,童庆炳先生将其归纳为六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被阐释的空间属于文学内部的“自律”问题,而“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则属于文学外部的“他律”问题;唯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经典的“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其中,缺少读者的期待和发现人,经典的建构也无从谈起[15]。不过,在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体制中,“发现人”并不仅仅限于“最早发现某个文学经典的人”,经典的发现有赖于三方的力量:专业批评家、一般读者和官方。
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三方力量不断博弈。但是,这三方力量中,专业批评家是起决定性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一般读者意见作为参考,而官方会对经典的建构作进一步确认。即使有官方、一般读者力量的介入,没有专业批评家的评论,作品的意义是不会被发现的,作品也很难被纳入经典之列。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在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官方的认可。这部小说中人物人生轨迹具有励志色彩,而其抒情手法使得读者阅读时有强烈的代入感,这部小说不仅发行量之大,当代小说无出其右,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几代读者的精神世界和“三观”。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本世纪初,这部小说并未得到批评界的一致肯定,反而因其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落后而未被写进文学史。最近几年,在民间价值观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之前对这部小说持冷淡态度的批评家(比如雷达)才开始转变评价立场,给予这部小说比较高的评价,而文学史也逐渐增加这部小说的评述字数。
赵毅衡先生在《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一文中,将符号学与文学场概念结合起来,将文学经典重估分为两类:符号纵聚合轴代表的是在“比较、比较、再比较”基础上的批评性经典重估,这种重估是“历史性的”,需要“历史认知”;而符号横聚合轴代表的是在“连接、连接、再连接”基础上的“群选的经典更新”,后者也有比较,但群众(与精英、官方三分天下)不将其与历史经典比较,而是与同时代的同行作比较,从中选取他们接触最多而非真正最优秀的。赵先生认为,当前文学界在经典重估问题上,令人担忧的不是群选经典能否进入经典之列,而是批评家已经采取了群选经典选取经典时“全跟全不跟”的原则,文学场有向横聚合轴(群选经典)倾斜的趋势,从而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那种取悦于普通民众的文学文本大行于世,让文学经典被商业利益追求和物质享乐文化遮蔽或覆盖,剥夺了人们接触经典的机会,也隔断了专业批评家与普通民众在审美和文化价值观上可能达成的“共识”,批评性经典不再符合普通民众的阅读期待、心理需求、价值观和审美理想。如果置之不理,整个文化将在“经典无需深度,潮流缺乏宽度”之后带来文化灾变[16]。
正如“文化”被泛化使用一样,当“经典”一词也被普泛化,群选经典的市场份额自然就比批评性经典大得多,大众文化的选择使得经典随意性越来越强,而人们对于文学经典的价值以及权威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平凡的世界》的遭遇以及“金庸”进入文学史,多少能够证明赵毅衡先生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不过,这尚属正常现象,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未经文学批评的检验,一些所谓“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就因读者的压力而过早地进入文学史的写作。如果任由大众经典来建构我们的文化,主流文化被侵蚀乃至衰颓也将在所难免。而在场的批评,其批评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加强,将会有益于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利于指引文学创作乃至我们的文化健康发展。
杰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想象共同体更多地建基于共同的文化,支撑共同文化的媒介或元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则是语言。按其理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由文学经典文本所构成的体系可被想象为一张历史性的导航图,指引人们对历史认知与理解,从而凝聚人们文化认同感:因其以感性的文字打开人们的心灵,更易于从事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文学之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自不待言。
如果说,在场的批评抵制经典被侵蚀的倾向,其意义显得抽象而空泛的话,那么,在场的批评的另一个意义则是具体的,也更切近学科建设。
在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沿问题时,李怡认为:拓展学术思想,并不仅仅在于继承文论遗产,更重要的是对发生过的文学现象加以准确思考和体会,这种学术思想的拓展正是基于当前一个个批评家对于当下文学及文学现象的独特文学感受,从而“使之上升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与批评方式”[17]。而这一过程,在场的批评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类文学批评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研究相关联,不是一种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具有“感性提炼和审美观照”,从而形成批评史的脉络;而其“将文学现象流变演绎为一种感性审美逻辑”,也构成文学史的理论基础。这类批评是“一种审美感性的理论化形态,是一种兼具感性特质和经验性的理论化表达,或可以说就是一种到达概念、纯粹理论的途径或津梁”[18]。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及研究状况,许多人采取的是一种理想化、乐观化、浪漫化的理解方式,但是当我们翻看同时代的文学史著或批评文章,就会发现,当时的文学及研究虽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特性,但仍然充满意识形态气息,而这种气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彻底散开。正因为在场的批评从各个侧面记录下历史的面影,当下的历史现场才能真正融进文学(史与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将文学置入历史现场,从而有利于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写作。因此在场的批评不仅有利于文学经典的建构,更为文学史和批评史写作提供巨大的思想资源,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经典,而批评家在发现经典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过去时代,经典的建构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要小很多,今天经典建构的环境却越来越复杂,在这样一个文学氛围中,怎么消除经典建构中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一部作品经典的建构能否确立,不是批评家能够说了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既检验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也检验作品的经典建构过程中是否夹带私货。当前的文学批评的质量固然参差不齐,不免“夹带私货”,有过誉之词,而且数量庞杂,但是鲜见真正有分量、能经得起检验的批评文章,而能够建构经典、为文学史和批评史写作提供巨大思想资源的在场批评更是少之又少。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更应该呼吁更多有分量的批评文章的出现。
对于当前盛行学院化批评导致“文学批评已天然失去了对创作应有的指导与传播功能”的担忧,有学者寄希望于驻校作家批评:驻校作家走出了自己的创作天地,在一种无我的公共意识中,拓宽艺术境界,在用通俗化的表述(“批评的大众化运动”)中,从而瓦解了学院派那套批评体系,对于改变批评话语格局与复兴作家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19]。不过,驻校作家的数量毕竟有限,他们这种批评也只在一个小圈子里传播,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抵制极其有限。此外,驻校作家的批评文章大多感兴而发,虽不无才情,但多印象式点评或就事论事,缺乏一定的批评逻辑:驻校作家批评可点缀批评界,以增其彩,但终不可多得。近几年在高校比较流行的“驻校作家”,与其说是短期交流,培养学生的创作灵感与想象力,还不如说这就是一顶作家本人赐予高校也是高校赐予作家而可以彼此互换的高帽子:驻校作家的出现,固然增强文学现场感,但使人怀疑与其相关的文学批评里“夹带的私货”更多。
四、结语
本文呼吁在场的批评,意在使文学批评回归文本分析,摆脱学院派批评的桎梏,以便及时把握住文学发展历史的脉动,展现文学发展历史真实生动的面貌,在此基础上建构文学经典,不仅对于当前的学科建设有益,而且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善莫大焉。文学经典的建构并不排斥在场的批评,而在场批评因为切近历史语境,也将与文学经典文本构成互文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