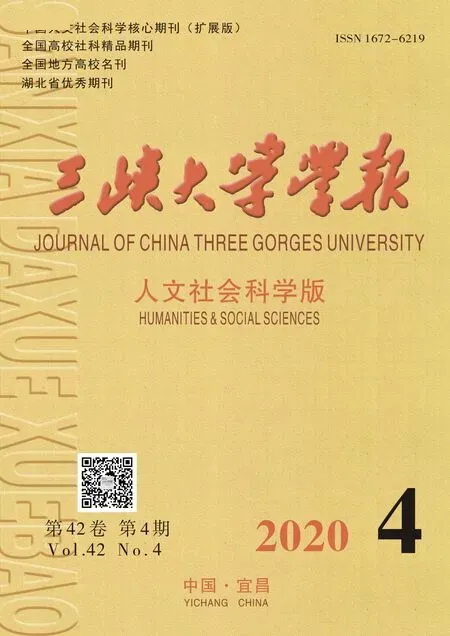理学视域下的宋季诗学“情性”观
2020-12-24邓莹辉赵雨丝
邓莹辉, 赵雨丝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情性”内涵的历史演变
唐宋诗是中国诗国的两座高峰,其创作成就可谓空前绝后。但两个朝代的整体诗歌风貌却迥然不同。早在南宋后期,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明确指出了唐宋诗歌的差异:“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1]696自此,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观念便深植于学者的意识之中,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诗分唐宋……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力取胜。”[2]“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3]当代学者李春青亦认为,“在以‘义理之学’、‘心性之学’为核心的学术话语的影响下,宋代诗学对诗学本体的认识由‘情性’变而为‘意’或‘理’。”“宋代诗学在‘以意为主’的旗帜之下突破了以‘吟咏情性’说为主要倾向的诗学本体论的藩篱,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开出又一重要本体论倾向。”[4]但这种看似意见一致的认识背后,却掩盖了宋诗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仔细翻检宋人、特别是宋季的诗歌批评,“吟咏性情”依然是宋季诗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所不同的是,在宋季批评者视域中的“情性”论,与传统“情性”观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差别。辨析二者的关系,对于厘清文学的本质属性,尤其是了解宋季与其他时代在诗学观念上的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宋前诗歌“情性”观
在古代诗学演进史上,“吟咏情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命题和核心概念。早在先秦时期,“情性”便成为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学者极为关注的学术问题,无论是主张“性本善”的孟子一系,还是提出“性本恶”的荀子、韩非子等人,都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观念,论性而不及情:“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真正将“情性”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纳入学术体系的是荀子:“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6]436“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6]437-438他所谓“情性”,几乎是“人之性恶”的代称。在他看来,人性之“恶”与生俱来,“善”则需要后天学习、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其《乐论》中首次将“情”运用于音乐理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把“情”视为音乐产生的主体心理依据。而从文学角度看,汉代学者首先将“情性”这一学术概念引入诗学领域,成为以后批评者诗学话语系统中的日常用语。《诗大序》是将“情性”运用于诗歌批评的始作俑者:“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7]按照《毛诗序》的理解,“情性”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后天因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密切相关的由“人伦之废”、“刑政之苛”所引起的哀伤愤懑等不满情绪。正是吟咏情性具有理论的开放性,才给后代学者提供了更广泛的阐释空间。
魏晋时期当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人们关于“情性”的讨论也更加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这样系统且专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使得“情性”理论探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刘勰阐述“情性”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8]他所谓“情性”包括文人的才气、性格、气质、心境等。而钟嵘对“情性”的解说也颇有特点:“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9]所言“情性”即指人的情感或情绪,与刘勰的“情性”说涵义一致。
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唐代讨论“情性”问题的重要文献:“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10]在经历六朝感物、缘情理论盛行之后,其观念重新回到汉代的儒家诗教立场。但他特别强调诗的抒情功能,对变风“吟咏情性”的文学价值予以更多的肯定,对有唐一代的诗学产生重大影响,唐人普遍接受其诗歌上可通教化、下可理情性的双重功能。如唐玄宗李隆基在《答李林甫等请颁示太子仁孝诏》中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将以道达性情,宣扬教义。”[11]中唐诗人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称赞张氏乐府“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12]元结《刘侍御月夜会序》在与友人吟诗言怀后感叹道:“於戏!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13]唐人将“吟咏情性”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依据,形成了唐诗以情取胜的整体风貌。从诗歌批评上看也是如此。皎然说:“囊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14]司空图亦云:“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15]都是强调诗歌要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体。唐代关于“情性”的阐释与六朝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主要区别在于,“六朝诗学更强调‘情性’的本体地位,目的是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异;唐代诗学则侧重于探讨诗歌本体与其表现技巧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大约是因为在六朝时士族文人要消解汉代工具主义诗学思想的束缚,所以不得不突出‘情性’的本体地位,而在唐代文人看来,诗歌本体问题早已不成其问题了。”[4]
2.宋代文人的“情性”观
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情性观主要源于儒家的性本善观念,还属于道德的层面;那么宋代则是从本原(或本体)的意义上追溯情与性的关系,属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唐人作诗倡导自然情性,宋人则主张涵养情性。宋代关于“情性”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文人情性观和学者情性观两类,前者多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强调其抒情特质,偏重于“情”的一面;后者则多从哲学的层面探讨性对情的制约作用,即强调“性其情”。苏轼是主情论者:“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16]他从哲学的高度对情性进行辨析,“性”为本,“情”乃性之用,二者没有善恶之分,只有体用之别。苏门弟子黄庭坚作诗也主张“情性”,提倡“不累于物”,反对“强谏”“怨忿”之情肆意表达。其《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有云:“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朝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静,抱道而居,与时乖违,遇物而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失,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17]认为诗歌是人情性的流露,但此情性不同于“缘情绮靡”对情的不加约束,而是诗人通过心性涵养而形成的圣贤人格,体现了以性约情的理性精神和涵养道德的艺术追求。南宋姜夔关于“情性”的阐释与黄庭坚一脉相承,其《白石道人诗说》言:“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18]他所谓“情性”,实际上也是通过涵养心性而获得的一种“中道”境界。
二、理学“性情”论的独特性
理学家是在以理为本的基础上,承认文学的存在价值,所谓“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19]1177他们强调“理”,但并不否定“情”,甚至还非常重视“情”。但与文人多任情而为不同,他们对情是有规范和指向性的,即要求情能得其正。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曾对“情性”做出论述:“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19]77提倡无过无不及符合中道的“性其情”,反对“纵其情而至于邪僻”的“情其性”。用之于文学创作,就要求诗歌表达“情性之正”。从二程弟子杨时的“言者,情之所发也。今观是诗之言,则必先观是诗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则虽精穷文义,谓之不知诗可也”[20]可以看到,理学诗人对诗歌的抒情特质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更强调诗“情”的表现要符合中庸原则,“诗之为言,发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轻,其辞婉,其气平,所谓入人也深。其要归,必止乎礼义……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所谓发言为诗,故可以化天下而师后世。”[21]从情感表现上做到“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从语言风格上追求“辞婉”“气平”,其中所包涵的是作者的人格修养。
“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是一位喜欢作诗且自成一体的理学诗人。他对“情性”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情伤性命”;二是“以物观物”。关于第一点,他说:“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称善蹈者,未始不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则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则败坏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伤性害命一也。”[22]4他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文人作诗的根本准则,那些只关心“一身之休戚”、沉溺于个人一己之私情而不能拔的诗歌,不仅不能垂训后世,而且还会“伤性害命”。关于第二点,诗人要摆脱利害和情感的束缚,从“发乎情”转向“发乎性”,就要采用以物观物的态度对待人之情性。“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22]4强调抛弃杂念、不受音律限制、以随性的审美状态来吟咏情性,“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自然而然。如此便能体验天理流行、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圣人之境。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关于他的“性情”观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讨论。首先从哲学的层面,他注重厘清“理”与“气”、“性”与“情”之间的关系。《答黄道夫》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3]“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24]而“性”又细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因源于太极而纯粹至善;“气质之性”因理气混杂,存在偏倚驳杂之弊,故有善有恶。人可以通过持敬立本、格物致知和反躬践行的修养功夫变化气质,消解气质之性中“恶”的部分,复归天命之性的本然状态——至善境界。“心”是人一身之主宰,它贯通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情,是一个包含理与气总体的范畴,它虽然有心、性、情三个概念,但三者本身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问‘心统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义礼智是性也,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则见得心可以统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动静,静者性也,动者情也。’”[25]心具有虚灵明觉的特性,它兼具性情,既包含万理,又融摄万物。通过此“心”,上可以抵达天理本体,下可以感受万物表里。这种豁然贯通的境界,既是一种道德境界,更是一种审美境界。其次从文学的层面,朱熹将心统性情、性体情用的“情性”观用之于诗歌研究,提出自己独特的抒情理论,即“情性之正”。他在《诗集传序》中说:“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26]他一方面认同“感物道情”的传统理论,承认诗歌的抒情价值;同时也强调心之所感要“正”,吟咏诗歌更要体验其心与物妙合冥契、万物之理皆备于心的境界,也即“得其情性之正”。
三、宋季诗学的“情性之正”与“情性之真”
朱熹从“体用一源”的思想观念出发,提出诗歌要以吟咏情性为主,提倡自然平淡的审美风格,对宋季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南宋后期,随着程朱为代表的理学登上正统独尊地位,朱熹等的“情性”理论也成为这一时期文人所恪守的诗学规范和原则。以道学家为主体的宋季诗人关于“情性”的讨论,大致可以概括为“情性之正”与“情性之真”。正宗理学派诗人接受传统儒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学原则,多强调“情性之正”;受心学影响的诗人则注意到“情性之真”的价值。从“情性之正”到“情性之真”,一定程度反映了宋季文学从“重道轻文”到“文道融合”的嬗变。
1.朱子后学的“情性”观
徐复观在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时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常常于强调性情之后,又接着强调‘得性情之正’。所谓‘得性情之正’,即是没有让自己的私欲熏黑了自己的心,因而保持住性情的正常状态……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则性情的本身自然会与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因而自然会‘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而诗人的心便是‘一国之心’。由‘一国之心’所发出来的好恶,自然是深藏在天下人心深处的好恶,这即是由性情之正而得好恶之正。”[27]2-3这既是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更是两宋理学诗学的根本原则。
真德秀是朱熹学说的正宗传人,也是将理学推向官学正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对文学的态度受朱子影响甚深。其《文章正宗·纲目》云:“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28]176-177在“明义理切世用”思想指导下,他提出自己的诗歌“情性”观:“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后世之作,虽未可同日而语,然其间兴寄高远,读之所以忘宠辱,去鄙吝,悠然有自得之趣,而于君亲臣子大义,亦时有发焉。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盖不必专言性命而后为关于义理也。”[28]176-177将“义理”的内涵从儒家学说和道德伦理扩大到符合中庸无过无不及的“情感”内容,从而实现了理学范围的“义理”与文学范围的“情性”相结合。他在《问兴立成》中进一步论述到:“古之诗出于性情之真。先王盛时,风教兴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间虽喜怒哀乐之发微或有过差,然皆归于正理。故《大序》曰:‘变风发乎情,本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情谓喜怒哀乐,此乃民之性不能无者,然其归皆合于正理,故曰本乎礼义。先王之泽,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虽叔季之世,人犹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诗,惟其皆合正理,故闻者莫不兴起其良心,趋于善而去于恶,故曰‘兴于诗’。”[28]380-381只要抒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感是真实的,哪怕“或有过差”,只要最终“归于正理”,就是符合其“文章正宗”标准的好诗。按照这一标准,他认为“诗三百”篇之后,能得其“情性之正”的诗人,前有陶潜,后有杜甫,因此他将这两位诗人的大量作品选入《文章正宗》,并且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尔。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28]235而杜甫是他眼中能得“情性之正”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也是唐人作品入选《文章正宗》数量最多(92首)的诗人,其篇幅之大,点评之多,其他唐代诗人难望其项背。杜甫忠君爱国,关心民生疾苦,其“三吏”“三别”等并非显言义理的诗歌被真氏视为能够体现教化功能、得“性情之正”的典范作品。
魏了翁与真德秀并称“真魏”。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言志抒情“本诸性情之正”。其《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有云:“诗以吟咏情性为主,不以声韵为工。以声韵为工,此晋、宋以来之陋也……转失诗人之旨……然余犹愿徐君之玩心于六经,如其所以得益于诗史,则沉潜夫义理,奋发乎文章,盖不但如目今所见而已也。”[29]20“情性”乃诗之本,言辞为诗之末,舍本逐末自然会“失诗人之旨”,将“沉潜夫义理”与“奋发乎文章”相结合,是处理“性情”与诗意关系的正确途径。其《钱氏集传序》云:“古之言《诗》以见志者,载于《鲁论》、《左传》及子思、孟子诸书,与今之为《诗》事实、文意、音韵、章句之不合者,盖什六七,而贯融精粗,耦事合变,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诸性情之正,而说者亦以发起性情之实,不拘拘于文辞也。”[29]57主张无论作诗,还是论诗,都应该“本诸性情之正”,不要把精力放在雕章琢句的末事上。
黄震亦强调诗歌创作应该有感而发,本之于创作者内心的“情性”。其《张史院诗跋》以陶、杜等的作品为例,论述了诗歌与情、性之间的关系:“诗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后之为诗者始凿之以人焉。然陶渊明无志于世,其寄于诗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负志不偶于世,其发于诗也慨然以感。虽未知其所学视古人果何如,而诗皆出于情性之正,未可例谓删后无诗也。”[30]206诗歌因“感物而起兴”,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心灵感应而体悟自然天道,从而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他在《书刘拙逸诗后》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一太极之妙,流行发见于万物,而人得其至精以为心;其机一触,森然胥会,发于声音,自然而然,其名曰诗。后世之为诗者,虽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沉潜义理,以养其所自出……盖不求为诗,而不能不为诗,此其所以为诗也。”[30]197无论古今,所有优秀诗歌都是“自然而然”,故能得“情性之正”。
宋末元初,金履祥通过《濂洛风雅》的编选,阐扬朱熹“万殊而理一”的思想,并形成理学“风雅”诗学观:“所言者道德,所行者仁义,安有风雅之名哉。不知人之生也,有性必有情。有体必有用,即圣门教人。依仁则游艺,余力则学文。未尝离情以言性,舍用以言体也,但发而中节与否,则在人而不在天。”[31]此序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有性必有情”,故抒情要得“情性之正”;二是不能“离情以言性”,性体情用,情是性的具体呈现,诗更是通过情的表现来体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总之,宋季理学家的诗学思想几乎都是以理为主,又一定程度关注艺术性,既注重诗歌“发挥义理,有补世教”的功用,同时又强调其抒情性,尤其是要求诗歌创作与批评都要发而中节,得“情性之正”,所谓“以情存性,以性约情”。
2.心学影响下的“真情性”
诗歌抒情要做到“情性之正”,就必须加强个体的道德修养;而“情性之真”就是强调其情感的单纯可信,是很少掺入道德因素的当下情感呈现。“一个伟大的诗人,因其‘得性情之正’,所以常是‘取众之意以为己辞’,因而诗人有个性的作品,同时即是富于社会性的作品。这实际是由道德心的培养,以打通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的。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的,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所以‘性情之真’,必然会近于‘性情之正’。但性情之正系从修养得来,而性情之真,即使在全无修养的人,经过感情自身不知不觉的滤过纯化作用,也有时可以当下呈现。欢娱的感情向上浮荡,悲苦的感情向下沉潜。”[27]3-4从逻辑上说,“情性之正”包含“情性之真”,二者有其共通性;而“情性之真”则未必等同于“情性之正”,它虽然真实,但极可能因为情感表现过分而违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当然,宋季以心学为主体的道学家所提倡的“情性之真”并不是作为“情性之正”的对立观念而出现,而是有节制地回归“缘情”的诗歌传统。
严羽是“性情之真”诗学观的代表,其《沧浪诗话》以“心”为本,以所抒之情的真伪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尺度,对历代诗歌进行评点。他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688他论诗推重汉魏、盛唐,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其以吟咏性情为主,且能够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歌却转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把陶写情性弃之不顾。他评价前人作品也以抒情真实与否作为判断标准,体现出与理学家不同的审美眼光。如对屈原的《离骚》,朱熹重视其能“增夫三纲五常之重”的教化意义;而严羽则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洟涕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否则如戛釜撞瓮耳。”[1]698认为《离骚》的真正价值在于,作者通过千古悲情的“真心”表达,使读者在“洟涕满襟”的情感冲击下去体验诗人忠而被谤、忧而遭贬的愤激之情。这种解读显然不符合理学家的“情性之正”要求,却更准确揭示了文学的抒情本质。
包恢论诗受心学影响很大,他特别强调诗歌的抒情特征,提倡有感而发,因情而作,反对无病呻吟的“作”诗。《答曾子华论诗》云:“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扰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孰发挥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风、雅、颂,作乐殷鉴上帝之盛,其孰能与于此哉!其次则所谓未尝为诗而不能不为诗,亦顾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触,或遇扣击,而后诗出焉。如诗之变风、变雅与后世诗之高者是矣。此盖如草木本无声,因有所触而后鸣;金石本无声,因有所击而后鸣,非自鸣也。”[32]他认为,优秀作品源自两种情况,一是“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它得之于天,是从“道中流出”,非人力所能至,可谓之“神来之笔”;二是诗人“或遇感触,或遇扣击,而后诗出焉”,只有发自“真心”的抒情才有生命力,惟有直击心灵的诗歌才让人产生共鸣。“情真意切”是抒情诗的本质。因此,他在《石屏诗集序》中提出“真诗”理论:“石屏以诗鸣东南半天下……古诗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诗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来;古诗贵乎真,而石屏自真中发……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予谓其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果无古书,则有真诗,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32]303-304。在此,他针对诗坛以议论、文字、古书等为诗和以经传、语录等为诗,提出了“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有靖节之意”“自胸中流出”的“真诗”标准。何谓诗之“真”或“真实”?包恢如此解释:“然真实岂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内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当并与精神意趣而得。境触于目,情动于中,或叹或歌,或兴或赋,一取而寓之于诗,则诗亦如之,是曰真实。”[32]315在包恢看来,所谓“真实”,其前提是“境触于目,情动于中”,也即感物而起兴,然后与人的“精神意趣”相结合,通过“寓之于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精神意趣”所指向的虽然是仁智等儒家道德义理,但以“浑然天成”的“自然”面目呈现出来。包恢论诗特别强调浑然天成、自然而然:“大概以为诗家者流,以汪洋淡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谓造化之未发者,则冲漠有际,冥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者焉。所谓造化之已发者,真景见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32]286不管是“造化之未发”,还是“造化之已发”,其最终都要归于“混然天成”的自然,这是诗应该呈现的“真”的境界。包恢用“真”“无意”来处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实现了理学与文学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刘辰翁也提倡诗歌抒情要做到“情性之真”。其《欧氏甥植诗序》曰:“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也,虽极疏憨朴野,至理碍辞亵,耳识者常有以得其情焉。”[33]他在《古愚铭》中亦言:“《离黍》何求,《怀沙》惑志。自伤为传,以至憔悴……欲知生直,尤贵情真。”[34]强调诗歌抒情要率性而为,真情洋溢,光明坦荡。他继承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思想,在《不平鸣诗序》中说:“亘古今之不平者无如天。人者有所不平则求直于人,则求直于有位者,则求直于造物,能言故业也……人之不平所不至于如天者,其小决者道也。小决之道,其惟诗乎?故凡歌、行、曲、引大篇小章,皆所以自鸣其不平也。”[33]将心中的怨愤情绪通过诗歌发泄出来,强调诗歌泄导人情的功能。其诗学思想和理学家主张“情性之正”的观念有较大差别,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使偏离了历史轨迹的宋季诗坛,一定程度回归了诗的本质。
当然,并非只有理学家关注“情性”问题,作为宋季诗坛生力军的江湖诗人有更多此类问题的探讨,如被视为江湖诗派领袖的刘克庄《跋何谦诗》有言:“以情性礼仪为本,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化;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幽人羁士饥饿而鸣,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宗主斯文,而于诗无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欤。”[35]严羽更是抒写“情性”的倡导者,他的《沧浪诗话》从“吟咏情性”出发,明确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1]688,强调情、理、词三者的浑融。这说明“情性”问题始终是古代诗学界所关注的话题,在理学占据诗坛主流的宋季也没有例外。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将“情性”作为人的先天个性从哲学层面展开讨论,延续到魏晋六朝转化为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刘勰扩大了情性的范围,认为它的形成既有“肇自血气”的先天禀赋,也有“陶染所凝”的后天影响。宋代理学则从本体的意义上探讨情、性关系,关注诗歌“情”的表达方式。宋季对“情性”的关注热情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理学或受理学影响的诗人都强调得“情性之正”,要求抒情要有节制,要“性其情”,不能“情其性”。这是理学体用思想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理学诗学题中应有之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受心学影响的学者提出“真”诗主张,它使得理学“情性”观从过分关注道德教化、人格修养的狭隘领域,部分转向对诗歌审美境界的追求。虽然这种转向的力度还不是很大,是戴着义理的“镣铐”跳舞,但在宋季要么江湖诗歌横行、要么理学诗“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的现实困境中,提倡抒写“真性情”,无疑为宋季沉沦的诗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