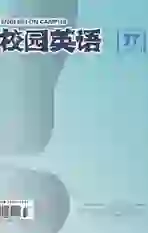“形似”和“神似”:《将进酒》的两个英译本比较
2020-12-23陈明
【摘要】李白是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其作品风格独特、意义深远。《将进酒》作为其代表作之一,被各路翻译名家译成多个英语版本。本文拟就“形似”和“神似”,从措辞、韵律、修辞和意义四个方面,比较分析孙大雨和许渊冲的《将进酒》译本,并揭示两个译本各自的优势所在,各家可博采众长。
【关键词】《将进酒》;译本比较研究;形似;神似
【作者简介】陈明(1987.06.11-),女,汉族,四川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
一、引言
唐朝时期,诗歌鼎盛,尤以李白 (701–762)为代表。作为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享誉中外,其《将进酒》被各路翻译名家译成多个英语版本,包括孙大雨和许渊冲。这两位翻译大师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译文也因此呈现出不同风格,尤其是在“形似”和“神似”方面。关于翻译应追求“形似”还是“神似”,争论从未休止。对于卞之琳等支持“形似”的翻译家而言,“形似”是基础,而后追求“神似”。而以傅雷为代表的一众翻译家认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神似”胜过“形似”。其实,“‘形与‘神,两者从根本上说,是互为依存的” (许钧,2003)。于是钱钟书先生呼吁形神兼备,提出应以“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尤其是诗歌翻译。诗歌本身就是形与神的高度融合,形神合一是翻译孜孜以求的目标。本文拟就“形似”和“神似”,从措辞、韵律、修辞和意义四个方面,比较分析孙大雨和许渊冲的《将进酒》译本,并揭示两个译本各自的优势所在。
二、两个译本之“形似”和“神似”比较
1.措辞。诗歌语言博大精深,字字珠玑,句句精妙,无论是传形还是传神都绝非易事。《将进酒》属于乐府诗,颇具古典之风。作为一名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孙大雨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译文措辞古典优美。诸如“seest”“thou not”“hath”“doth”“ye” 等古体语体现了原诗的乐府风格;“Carouse”“golden beakers”等辞藻文采横溢;“glint”生动地描绘出金樽与月光交相辉映的浪漫意境……相较于孙大雨的用词考究,许渊冲的措辞更为简洁平实,重在传意,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语体风格。例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两位翻译家的措辞大相径庭,“saints and sages” 对比“great men”,“solitary” 对比 “were forgotten” 以及 “renown do retain” 对比“famous”。由此可见,孙大雨的译文措辞更为典雅隐晦,着重体现原诗的古典美;而许渊冲的译文措辞简练,可读性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大雨的译文中,存在一些用词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孙大雨将“黄河” 译为“Luteous River”,颇具误导性,不如许渊冲译为“Yellow River”来得准确,因为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具有很鲜明的文化特征,已有固定英译,任何改动都不利于原文意象的精准呈现。此外,“主人何为言少钱” 被译为“Why doth our taverner say there is any lack of cash”,其中“taverner”一般指酒馆老板,但此处的“主人”应指李白的朋友,包括许渊冲、杨宪益、宇文所安等在内的翻译家都译作“host”,更为恰当。“cash”一词让人联想到纸币,而这与历史不符,因为李白所处的年代并未通用纸币,因此影响了译文的忠实性。
2.韵律。古代诗歌的音乐性极强,韵律感十足,《将进酒》也不例外,慷慨激昂,可谓一气呵成。韵律涉及押韵、音节、节奏等,各种元素之间互相交融互相影响。虽然韵律是“形似”和“神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英文属于不同的语系,语言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诗歌翻译并不要求也很难照搬原文的韵律,比如韵脚或者音节完全一致。這并非提倡用自由诗来进行翻译,因为中国古诗抑扬顿挫、意境悠远、寓意深刻,若完全脱离原诗的框架自由发挥,便无法展现原作的风姿。译者还是应通过技巧性和创造性尽量使译文体现原诗的韵律美,从而助力“形似”和“神似”。
整体上,孙大雨和许渊冲都非常重视译文的韵律,为了韵律均省略了部分字母,例如“ne'er” “o'er”“we'd”等。许渊冲的译文流畅,押韵格式为“abab ccdd ee fgfg hhii jjkk llmmm”,非常规整,且每行诗的音节与原诗有所对应,句子有长有短,读起来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灵动,充分体现了音美和形美。孙大雨的译文押韵虽不如许译对仗,但每行诗的音节都大体一致,且多音节词较多,起伏跌宕的节奏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韵律美。此外,孙译较许译使用了更多头韵,类似“saints and sages”“sadly sober”的表达带来了视觉上和听觉上的美感。由于原诗的韵律比较灵活,三言、五言、七言并用,也没有严格押韵,因此留给译者很大的发挥空间。孙大雨的版本和原诗一样抑扬顿挫,而许渊冲的版本和原诗一样朗朗上口,各具特色。
3.修辞。李白擅用修辞,其诗歌风格恣意潇洒,充满了神韵。原诗中运用了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王佐良先生认为“应该把它直译过来,保持它原有的新鲜和气势”(2015)。但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有些修辞在原语里非常惊艳,到了译文中可能平淡无奇;或者原语的修辞耳熟能详,如何翻译得让译语受众眼前一亮,却是一门艺术。为此,修辞是直译还是意译取决于原诗内容和译入语的文化背景。英译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形式,看视觉上是否保留了原诗的结构;但细品之后,还原神韵才是真正升华译作的地方。而译好修辞内容是传形和传神的关键一步。
夸张是李白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将进酒》中比比皆是。例如,“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等虚指产生了强烈的夸张效果,孙大雨和许渊冲对这些数字都进行了直译以保留原诗的夸张性。但对有些夸张内容的翻译,孙大雨在表达力度上更加到位。例如,首句中的“天上来”,孙大雨译为“rushing down from the sky”,相较于许渊冲的“come from the sky”,动感更强,气势更磅礴,黄河奔腾向海的壮观景象跃然纸上。第二句中的“朝如青丝暮成雪” 强调人生短暂,孙大雨保留了“朝”和“暮”的意象,而许渊冲直接用“once”指代,弱化了原句的夸张对比效果。除了夸张,拟人也是诗中画龙点睛的亮点。“高堂明镜悲白发”中的“悲”用得十分妙,暗示诗人无尽的悲伤和郁闷。孙大雨间接译为“white locks are wailed at”,而许渊冲直译为“grieve o'er”,两者都揭示了隐含的拟人手法。孙大雨和许渊冲的译文在修辞方面侧重不同,各有千秋。
4.意义。诗歌的意义往往是基于创作背景和作者心境蕴含在字里行间,若要追求“神似”便必须贴切地传递原意。在《将进酒》的翻译中,有时为了忠实性需要紧跟原文。如“千金散尽”,孙大雨译为“pieces of gold being scattered”形象生动,一撒千金的豪迈和狂放跃然眼前;而许渊冲译为“gold coins spent”,侧重于点明字面背后的含义,并没有还原“散”字的精髓。具体而言,“scattered”比“spent”的既视感更强强,更传神地体现出李白的直率和洒脱。
此外,翻译有时又需要概括原诗含义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例如,“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官场失意,唯有借酒消愁,但即便是描写悲伤,李白仍然充满激情。因此,许渊冲灵活译为“Dear friend of mine, / Cheer up, cheer up! / I invite you to wine ”,充分体现了李白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许译并未像孙译一样保留“岑夫子”和“丹丘生”,也没有像孙译一样将“杯莫停”直译为“pause not in drinking”,但原句意义却丝毫未减,甚至更直击人心。这种意译手法与许渊冲的“三美论”是一致的,他认为“如果译得‘失真却可以和原诗比美,那倒可以说是以得补失”(2000)。
再者,翻译有时又需要将意象具体化,从而揭露其隐含意义。例如,孙大雨和许渊冲都对“陈王”进行了解释,以便让读者明白作者为何借陈王来抒发抑郁之情。又如“天生我才必有用”,相较于许渊冲所译“made us talents, we are not made in vain”,孙大雨译为“endowed me with talents for good use”,通过“endowe”和“good” 两个词业具体形容,更有张力,将李白的自信和抱负展露无遗。最后一句中的“儿” 和 “尔”较为口语化,体现了李白放任不羁的个性。孙大雨分别使用了“my boy” 和“ye”來指代,在意思和神韵上都与原诗非常贴合。简而言之,在达意方面,孙大雨的译文更注重细节,以求完整准确地传递原意;而许渊冲的译文不拘于细节束缚,重在把握大意和神韵的传递。两种策略都是为了更好地传递出原诗的含义,力求达到“神似”。
三、结语
如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大势所趋,而唐诗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备受世界各国青睐。这便对诗歌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既重“形似”又重“神似”,尽量神形兼备。诚然,每位译者的翻译风格不一,对“形似”和“神似”有着各自的解读和创作方式。正如在《将进酒》的翻译中,孙大雨和许渊冲的两个译本在“形似”和“神似”方面有同有异,但无论是孙译的精雕细琢、忠实贴切还是许译的简洁精练、行云流水,都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略原诗的风采。通过译作比较,读者和翻译工作者可以博采众长。
参考文献:
[1]孙大雨.英译唐诗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王佐良.王佐良全集(第八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3]许钧.“形”与“神”辨[J].外国语,2003(2):57-66.
[4]许渊冲.李白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5]许渊冲.新世纪的新译论[J].中国翻译,20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