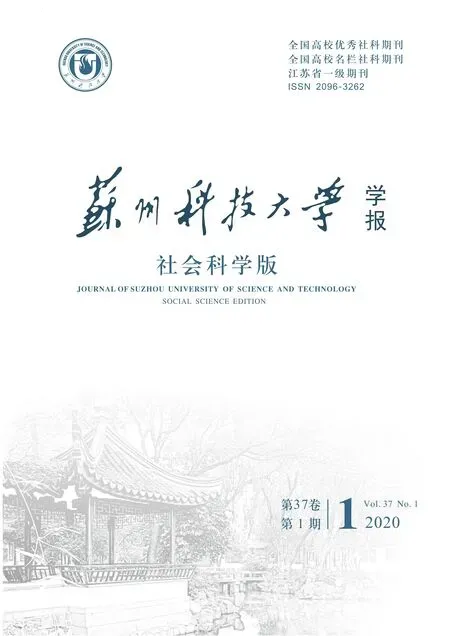论王国维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
2020-12-20刘颖
刘 颖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是我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学术,尤其是《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东壁)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1]12。但他又说1920年在北大任图书馆编目员时阅读丰富的藏书,“得益最多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述……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1]14,并引用自己1923年、1924年的两则日记来证明,“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1]15。针对大家对他和胡适的交往以及胡适对他的影响这个事实,他却明确地指出:“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可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看表面现象的。”[1]15但王国维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他产生影响,顾颉刚并未细说,只有如下表述:
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我很想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能够有新的建设,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做破坏伪史的工具。[1]14
我心仪于王国维,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1]15
关于顾颉刚的学术渊源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是根据顾颉刚自己所提及的学者,考察顾颉刚与他们之间的关联,也有唐宋时期直至近代的未被顾颉刚明确指出的学者,甚至还有将源头追溯到屈原或孟子、韩非子等更早期的人物。对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目前主要有曹书杰、杨栋的《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一文,从顾颉刚对王国维著作的研读借鉴以及对二重证据法的接受等方面来谈,展现史实较多。[2]另外,赵利栋的《〈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主要涉及他们史学思想中信古与疑古的动机、方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3]这两位学者所提及的学术关联方面的成果之稀少与顾颉刚所说的“影响尤为深刻”“得益最多”似乎不太匹配。2017年出版的林庆彰专著《顾颉刚的学术渊源》仍说:“顾颉刚虽然佩服王国维的学问,但是哪方面的学问,顾氏并没有说清楚,这还有待后人进一步探讨。”[4]笔者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些补充与推进,认为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应是王国维的过人之处,以及顾颉刚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能够契合的几个方面。
一、科学性:“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
西学的影响以及传统的民本思想等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激荡焕发,使得先觉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文化立场关注民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否定“礼不下庶人”时说:
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以为民也。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5]302
又说《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故知周之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5]302,处处着眼于“民”。他在《殷周制度论》完成之后对罗振玉所说的“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6](王国维《致罗振玉》),就表明了这种文化自觉意识。这种眼光向下的文化立场之转变,也是追求学术科学性的表现,它是将传统学术中被遮蔽的“民”及与其相关的学问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客观求真的治学态度,亦拉开了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序幕。
要做到求真精神与客观态度,首先取决于正确的历史观念。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说:
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7]90
正确的历史观不仅包括上述了解“事实”及其原因与结果,更重要的还包括历史应反映谁的历史,历史究竟是帝王圣贤史还是应包括人民在内的“人间全体”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历史既为普通学中最要者,学术转型也便首先体现在史学上。当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反传统的循环论史观、反天朝中心史载、反帝王中心史统以及反笔削褒贬法等。
提到新史学的正式开端,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梁启超。因为他在1902年写了著名的《新史学》的文章,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新史学的一些思想。其实在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里就体现了新史学的一些观念,如提到“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而“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并由此提出“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这样在当时还被视为偏激的看法。[7]1然而,1899年王国维在代罗振玉为日本那珂通世《重刻支那通史》写的序中,就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新观点:
故所贵乎史者,非特褒善贬恶、传信后世而已,固将使读其书者,知夫一群之智愚贫富强弱之所由然。所贵于读史者,非特考得失、鉴成败而已,又将博究夫其时之政治、风俗、学术,以知一群之智愚贫富强弱之所由然。[8]679
他认为我国古代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能够起到接近上述的作用,其他虽“卷帙纷纶”,但“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8]679,如“东家产猫”,不关体要。1899年王国维还为范炳清译的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撰序,1900年为徐有成译的《欧罗巴通史》作序,都提倡从科学的视角看待历史,强调历史要有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8]2(《东洋史要序》),认为中国的古史,只不过是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只能称作史料,不能称为历史;“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8]3(《欧罗巴通史序》)。他还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与阅读历史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用以解释目前东方各国的社会情况。王国维在梁启超之前(或者不比他晚)就提出这样的“新史学”观点,这大概是顾颉刚佩服王国维的原因之一。在文学上,王国维也主要致力于传统非主流的文体,如词、戏曲与小说,这种学术实践本身就体现了明显的民间倾向。不仅如此,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期间,还写了《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三种学术札记,断断续续发表于《盛京时报》上。这三种札记内容博杂,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民间文学及通俗文艺方面的,还有不少关于民间风俗的内容,如关于灶神、咒术,瓜皮帽、胡服,刘海、缠足,共饭、茶汤遣客等,涉及信仰、服饰、生活等习俗。
王国维的这种客观求真、关注民间的学术取向对顾颉刚影响很大。如顾颉刚日记记载,1922年10月29重点读《殷周制度论》与《先公先王考》、1923年8月19日读《鬼方昆夷猃狁考》、1924年2月26日看《观堂集林》、1924年看《红楼梦评论》与《静安文集》等。不仅如此,顾颉刚几乎终生都在研读王国维的著述。顾颉刚认为王国维的学问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批评一般人把王国维和别的研究旧学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是大错误。除了与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在于“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王国维是建设真的古史,他还认为学问的新旧绝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思想上,即王国维运用的是西方的学术方法,除了史学,他十几年前在哲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就“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9]284。顾颉刚在自己的学术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如1922年他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中指出,要弄清各时代的大势,不应像传统方法那样只关注政治方面的材料,也应从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去寻找各种社会事实与心理。1928年3月20日他在岭南大学所作的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中也认为,民众在数量上、工作复杂性上、行动的真诚性上比圣贤要大得多,高得多,但是“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所以要打破贵族圣贤为中心的历史,自己下手收集从而“揭发全民众的历史”[10]。这些观点基本是对王国维在《重刻支那通史序》中所表达观点的具体演绎和阐发。相似的说法在1928年《民俗》发刊词等其他的文章中也多次出现。他呼吁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甚至说自己就是民众,从群众艺术、民间信仰及习惯中发掘民众历史,记载中国历史全貌,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些表述反映了顾颉刚受王国维影响的历史观,也是他称许王国维“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之体现。这种学术科学性的追求,还体现在顾颉刚的某些研究方法上。如姚名达1927年3月20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先生从研究故事和神话的方法去研究,总不失为求真的一条路。”[11]《古史辨》第一册结集出版后,胡适评价:“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12]335此外,顾颉刚从疑古到信古态度的转变也能看出他一直走在学术“求真”的道路上。
其次,王国维对学术科学性的追求还体现在其对研究对象以及史料的平等视之的态度上。 王国维在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认为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也有研究的价值,“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8]130-131;强调有用无用的相对性:
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8]132
正由于有这样客观平等的态度,王国维才能将民间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视域,对非主流文体倾注心力,将词、戏曲、小说等统统纳入“诗学”范畴从而体现出一种广义的诗学观。
同史学上反帝王中心相一致,王国维在学术上也不惟圣贤论:
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8]130
所以王国维将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放在一个标准上来评价,“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5]4(罗振玉《观堂集林序》)。这个标准即“真”与“自然”,符合此标准的文学,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民间吟哦,都是好的文学。另一方面,王国维批判游词、鄙词之病以及饣甫饣叕的文学,就在于它们不符合这一标准,甚至因为文人文学的这些毛病,他更倾向于推崇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如他认为民歌“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也真”;认为元曲为一代绝作,“一言以蔽之,自然而已矣”;他所说的“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8]93(王国维《文学小言》),也实在大有奥秘。
由上观之,王国维对学问的新与旧、中与西、真与不真、是与不是、深湛幽眇与迂远繁琐、大与小、远与近、俚辞与雅故等等都平等对待,也不会因为圣贤的原因影响是非判断。可以说,这正是客观求真的典型表现,也反映了王国维的学术眼光与学术心胸。王国维不仅明确表达了平等的科学态度,在实际研究中也非常重视将民间资料作为证据。他的戏曲研究结合民间风习,敦煌学研究关注民间文艺,诗词研究重视民间歌谣,古史研究中纳入民间文化。无论是他对自己研究方法命名的“二重证据法”,抑或是陈寅恪将之归纳为所谓的“三目”——“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外来之观点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1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都包含了他对民间资料的不同程度的重视。
顾颉刚认为,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9]284。受到这种客观平等甚至对民间通俗文艺更推崇的态度的影响,顾颉刚说:
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14]
顾颉刚也认为,“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要比正史官书要紧”,“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于敷衍门面”[15]。他还认为,“一部《道藏》,用实用的眼光看固然十之八九都是荒谬话,但若拿它作研究时,便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信仰与思想,这种书比了儒学正统的《十三经》重要得多”[1]72。以上都和王国维的观点比较一致。顾颉刚在实际研究中也十分注重民俗学的材料。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已入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16]。顾颉刚认为从孟姜女故事的启发中,“就可历历看出传说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定的古史所迷误”[1]70。可以说,顾颉刚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他的古史研究服务的,但从《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开始,上古史事真伪的问题被搁置,其关注的中心转移到了古史/神话如何在流变中层累,无形中为故事学以及民间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同时又走上民俗学的道路,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我所以放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17],跟学术研究的实际有关,也跟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
二、会通性与独创性:“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
顾颉刚1912年进北大学习,在几位很有学问的老师指导下走向专门研究工作。在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与章学诚《文史通义》三部书的启发下,顾颉刚认为对文学、史学都应走批评的路子,循着这种思路发现了郑樵的《通志》。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从天文到生物都放在一部历史书里,而且很有批判精神;但在封建社会里一直被贬斥,只有章学诚替它辩护。章学诚认为它能启发思想,有独创性见解——郑樵觉得各科的学问是必须会通的,因此他打破了各学问不能相通的疆界,综合他一生的学问编出这部《通志》来。受郑樵《通志》以及章学诚对它评价的影响,顾颉刚认识到学术应该具有会通性与独创性。在这两点上,王国维堪称楷模。
首先,在会通性上,顾颉刚认识到王国维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涉及甲骨青铜、金石汉简、唐人写本等等,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为他目力所及,“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做打通的研究”[9]284。确实,在王国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中就可以看出他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故罗振玉《观堂集林序》中赞叹他是“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穿者”[5]4,所谓“贯穿”即会通之意。王国维对学术会通性的追求上,其来有自。据其《国学丛刊序》,他认为今学有三大类——科学、史学与文学,而“三者非斠然有疆界”,“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王国维认为,学问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8]131
所以“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8]131。在学术研究中,对某一问题的分析阐释离不开其他相关学问所涉及的对象、事物和道理,只有在比较、仿拟、借鉴等方法运用中才能更好地认识与理解所要阐释的对象。除此之外,还要具备对研究对象所涉学术背景的尽可能全面掌握的能力,“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8]132,所以,会通既是学术方法也是学术能力。
顾颉刚终生都在向王国维学习如何在学术之海中深涵潜泳的能力,这在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对王国维的某些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研读,并力求从中学习“会通”之法。1963年9月15日他在《致叶国庆》中说:
译《尚书》首须从语言、文字、训诂、文法入手,不但要总结前人,并须超过前人,因此必须按照研究甲骨、金文及其他经典,尽量利用比较资料,方可做出较为妥帖的结论。[18]
确实如此,顾颉刚经过数年几易其稿完成的七十万字的《大诰议证》,在清代学者为主的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考古学与古文字学,调动了几乎所有的相关古文献材料,在会通性上“为后人成功一个‘示范之作’”[19]518。对顾颉刚后期的《尚书》研究,许冠三也认为:“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20]119顾颉刚在学习王国维的会通性上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确实如顾洪所说,他是把《尚书·大诰》篇的整理当作“学术的遗嘱”[19]517来做的。
其次,在追求独创性上,王国维体现出一种执着与崇高的理想。他在《元剧之文章》中说:
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依傍,自创新体。后人诸书,不过庚续之,摩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后人每无人能及之者,可谓豪杰之士矣。[21]120
这五六位作者“一空依傍,自创新体”,后人只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庚续、模拟和注释。此外,他认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因其“一空依傍,自铸伟词”[21]120。关汉卿与司马迁、许慎、郦道元、杜佑、沈括在王国维眼中都是“豪杰之士”。王国维也始终将成为如上述几人那样的“豪杰之士”作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并得以成功实现。他的《〈红楼梦〉评论》被视为“一项别开天地的创举”[22];“二重证据法”开创了史学研究新范式;他的哲学研究标志着现代转型的开端。他对自己的成就也颇为自信与自豪,如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21]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在词的创作上,说自己“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8]122,借樊抗夫之口解释“《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高楼’‘春到临春’等阕”是“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虽谦虚了一下,“自谓才不若人”,但又说“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23]494(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二十六》)。“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即“一空依傍”,追求独创性。用意“力争第一”,明确表达了学术追求的决心。诚如陈寅恪1934年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犹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3]
故王国维的学术贡献,除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更在于其在诸多领域的开山之功。
贯穿王国维学术历程的,始终有一种深厚的独创自觉意识。他在1899年为罗振玉代写的日人那珂通世《重刻支那通史序》里发出的“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8]679的悲叹,这为他成就中国新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开山之功埋下了种子。王国维研究戏曲的原因,除了对戏曲在搜集、研究与传承的资料作用方面的忧心,最重要的还是站在振兴国家民族文学的层面上看到了我国文学存在的弱点:
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8]121(王国维《自序二》)
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8]93(王国维《文学小言》)
王国维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看出,我们的叙事文学与西方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计”,尤其戏曲是最不振的。虽然王国维对自己的词作颇为自信,但也深知戏曲与词的差异,一叙事,一抒情,二者之间难易悬殊,所以对所谓创作戏曲的“文学家”之责,也不敢轻易承揽。但王国维对自己的性格也颇有自知之明,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少故不能做纯粹哲学家,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也不能成为纯粹诗人,作为一个学人可能比较合适,因而他专注戏曲这一少有人关注的研究领域,而恰恰这个某种程度上的学术“空白”能够使他实现“一空依傍”“力争第一”的宏愿。从他对戏曲研究的选择,可以看出他独特的学术眼光、非凡的学术勇气与强烈的责任感。
顾颉刚认为王国维是他“学问上最佩服之人”[1]15,这种力争第一、追求独创性的学术自觉意识,顾颉刚深受感染,或者说暗合了他自己的学术理想,所以他也具有如此“雄心”或者“野心”。顾颉刚认为,“过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写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奇耻大辱”[24]。顾颉刚在进行历史与民俗学研究伊始,对民众的东西是不太注意的,甚至有些轻视,认为很简单。但随着研究与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这一领域竟也有很深厚的复杂情状,他想弄清楚,但所依存的文献材料极其稀有,所以第一步就是要下手搜集材料。他并没有畏难情绪,而是感到“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踏地万里的雄心”[1]39-40。1931年,他在致谭惕吾的信中又说:
我抑制不住的野心,总想把中国历史重新排过,倘使我们能做成一部历史……吾深信国民的思想将顿然为之一变,将激起其勇往直前的精神,走上向上和合理的道路上。[25]
顾颉刚有关历史与民俗学研究成果之一——发表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不仅是顾颉刚本人故事研究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故事研究的开山之作。他的《尚书》研究如许冠三所说是“空前创获”[20]119。就算有争议的《古史辨》,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胡适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中心学说代表中国史学界的新纪元[12]338;郭沫若由讥笑到最终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26];余英时也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27]。尽管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史传说的创造及其演变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在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一点上还有思想的价值,就历史观而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历史意识,对历史观的现代转变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上这些具有独创性的成就体现了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追随,实现了他的不能说全部但至少一定程度的“雄心”和“野心”。
三、纯粹性与独立性:“学术界惟一的重镇”
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中说:“以前读书人……专注目于科第仕宦,不复肯为纯粹的艺术和科学毕生尽瘁。”[9]285不仅是以前的,当时的读书人也几乎“都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王国维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9]283。对给他的影响不亚于王国维的康有为的去世,顾颉刚的态度却是淡然置之,竟然不觉得悲伤,原因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完成后没有继续学术研究而走上了政治之途。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已死了”[9]283。可见在他心目中,王国维是惟一的“肯为纯粹的艺术和科学毕生尽瘁”的人。从这篇悼文中可以看出,顾颉刚对于王国维在学术追求上的纯粹性是深深赞赏的,也绝对是他在当代学者中最敬佩王国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与顾颉刚,亦师亦友,一直联系密切,后来却逐渐疏远了。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梳理了他们关系变化的脉络,从中也能看出他对胡适的态度。最初因为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略去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又不胜其烦的一段,他认为胡有截断众流的勇气,对胡是赞赏的。他们联系密切,胡适常给他通信要他帮寻资料,胡适作的文稿也先送给顾看。顾的《清代著述考》也长期在胡处,供他参考。尽管顾对胡很欣赏这部作品并说顾抓到了“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个同调很高兴,但却埋怨胡“并没有供给我一点帮助我完成这部书的条件,使得这一部可以供应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者查考的参考书早日问世”。1929年,胡适对顾颉刚说自己的思想变了,不“疑古”改“信古”了,顾颉刚表示听此话惊了一身冷汗,不明白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之后,认为胡适的《说儒》是为“信古”而编出的谎话。[1]13此外关于老子的年代、观象制器说、唯物史观以及对待民众的态度,两人都产生分歧,随后交往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在顾颉刚的心目中,胡适应该不算是纯粹的学者,或者至少应该也是“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的其中一人,所以才会有“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1]15的说法。
王国维对学术纯粹性与独立性的追求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研究实践中都有充足的表现。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批判我国哲学、文学等现状是唯视西方思想与学说的枝叶之语为政治教育之手段,却忽视自身的学术价值,提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的观点,表明追求学术的纯粹性与独立性的态度。[23]123王国维在1907年《教育小言十则》中批判我国“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其为学术自己故而尊之者几何?……其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8]83-86而他自己在学术上开拓区宇,补前修之所未逮,以学术托名之人自命,确实是倾注了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追求“绵密”“深邃”与“伟大”。诚如梁启超在《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中所言:
先生之学,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而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窠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颛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28]208
王国维虽然反对学术和政治挂钩,沦为政治的手段,但他也绝非固守书斋不问政治。他的学术取向与他的政治观念密切相关,如甲午战争后弃举业习新学;辛亥国变后,专研国学;俄国十月革命后,转研西北史地。他对国家民族面临的问题非常清楚,对当时的“人间”陋俗都有清醒的认识和剖析,比较集中的如《人间嗜好之研究》《去毒篇》等。他认为,造成这种陋习局面,所谓“政治家”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感慨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虽然王国维对政治家颇有微词,自己也极少写政论文章,但在与罗振玉等人的书信中讨论时局,以过人的史识对政治走向精准预测,都显示了作为一个非保守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眼光与识见。
然而,他始终以建立与振兴民族学术为己任,不与世迁流。他在为己之学中,同时寄托了“为人”“经世”的理想,在保持学术纯粹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又体现出一种深沉的人生关切与民间关怀。甚至终赴一死,也别有文化意义,正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
至于流俗恩怨荣辱、猥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28]203
他的学术贡献以及学术特性,没有比“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8]206(陈寅恪《海宁王先生之碑铭》)更好的评价了。
顾颉刚对于王国维,尽管来往并不是很多,但一直保持谦虚向学的弟子姿态,甚至不惜用“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9]283这种看似夸张的说法来表达对王国维的尊敬。“恋慕”也不只是他在语言上的一种修辞策略,1923年3月6日的日记记载梦见与王静安携手同行;1924年3月31日记载他梦见与王国维一起吃饭,说近年的梦以祖母死及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他保留了与王国维一生中仅有的三次往来的信件,对王国维的评价之高,感情之深,原因只能是“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也”[1]15。虽不做政治家,但将学术与政治形势密切联系,从学术上挽救危亡,是一切有良知的具有深沉爱国之心的学者共同的价值取向。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一是在研究《尚书》的时候发现《禹贡》的很多问题没有厘清,他认为历史地理学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就无从依托。二是此时也恰是日本蓄意侵略我国之时,为对抗日本学者为侵略而做的别有用心的关于中国地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为防止俄国为我西北大患,因此他倡导历史地理、边疆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并出了不少影响较大的成果。而这些史地研究也恰是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目的、领域的相似也印证了顾颉刚与王国维之间的学术联系。虽然王国维因早逝而脱离了顾颉刚此后的各种生存环境,具体境遇不同,但顾颉刚在追求学术的纯粹性上是初心不改的。可以说他自己一生也是不断克服种种实际工作上的困难,力求排除世事纷乱的干扰,渴求学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学习王国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理想,如“去世前一年才发表的《盘庚三篇校释译论》既重视版本校勘,又引用契文与金石文为证,特具王国维风格”[20]94。
尽管顾颉刚在学术成就上难以与王国维展开全面比较,王国维“文化神州”的名号也不是谁能轻易撼动的,但顾颉刚在历史学与民俗学上确实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尚书》的研究上,有学者认为已超过王国维。“顾颉刚最后二十年的功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译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其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20]111总之,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导师确实很多,但终究影响最深久的还是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