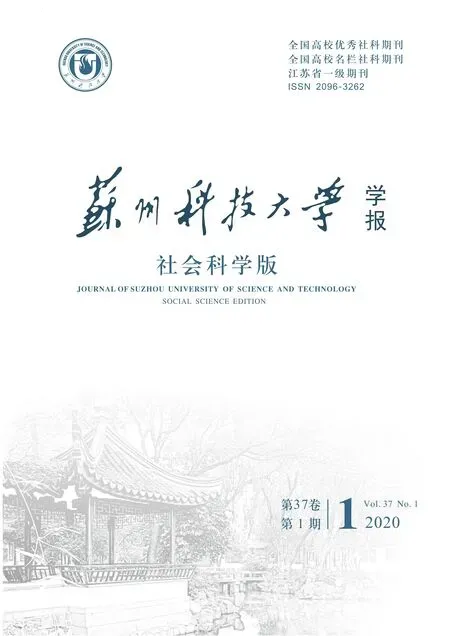后冷战时代澳美同盟强化的动因及挑战*
——基于联盟管理视角
2020-12-20许善品李苗苗
许善品,李苗苗
(湘潭大学 a.东亚研究中心;b.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南锚”,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支点,因此研究澳美同盟的强化对于分析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澳美同盟的强化,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现有的关于澳美同盟强化原因的探讨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战略需求论。战略需求论认为,冷战后的澳美同盟之所以会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是澳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考虑的结果。(1)参见沈予加、喻常森《特朗普时期美澳同盟发展趋势探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第24~29页;崔越《中等强国逻辑: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成因》,《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第4期第36~53页;孙通、刘昌明《“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外交困境与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3期第62~77页;岳小颖《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与澳美同盟构建》,《人民论坛》2013年第18期第252~253页;赵昌、许善品《从租借达尔文港看澳大利亚的中美平衡外交策略》,《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2期第57~73页。运用战略需求论来解释澳美同盟的强化,立论的基础在于澳美双方的战略需求与双方的共同利益相契合。澳美双方战略需求与共同利益契合,澳美同盟就会强化;反之,澳美同盟则不会强化。该观点忽视了澳美双方为了协调诉求及利益分歧所做出的努力。在澳美同盟的发展历程中,澳美两国的利益和诉求并不完全是契合的,澳美对这些分歧进行协调,澳美同盟才能不断强化。第二,同盟性质论。同盟性质论认为,澳美同盟能够存续多年并在冷战结束后只经历短暂的“漂浮”就迅速强化,是因为两国同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有着相似的
认同感和价值观,二者是一个同质性同盟。(2)参见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许少民译,《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56~69页;Hugh White,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No.2;岳小颖《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38~62页;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徐维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政治信念、价值观等因素在利益占主导的同盟关系中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毕竟利益才是决定同盟关系的核心要素,有共同利益,异质性的同盟也可以存续强化;缺乏共同利益,同质性的同盟也可能会走向瓦解。此外,同盟性质是不变因素,而澳美同盟的强化发展是不断变化的,运用不变因素来解释发展变化,缺乏说服力。第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给澳美两国带来的威胁,澳美同盟不断拓展强化。(3)参见威廉·陶《特朗普总统对澳美同盟及澳大利亚在东南亚角色的影响》,《南洋资料译丛》2018年第1期第22~25页;于镭、赵少峰《澳美同盟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蜕变》,《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第130~157页;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70~86页。虽然澳美两国存在着应对“中国威胁”的共同利益,但两国在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方面存在分歧。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其全球霸权的潜在挑战和全球问题中的可能合作伙伴。[1]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澳大利亚视中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澳方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较弱,中澳双方不存在战略主导权的竞争,中澳的冲突面小于中美。由上可以看出,现有的原因探析大多限于外部因素分析,缺乏从联盟管理的角度来解释澳美同盟的强化。
关于联盟管理方面,现有关于联盟管理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联盟管理这个概念本身(4)参见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6~25页;王帆《联盟管理理论与联盟管理困境》,《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放在解释、说明这个概念内涵上,注重理论分析但缺乏实际运用。目前学术界将联盟管理理论运用到联盟发展演变上的成果较少。(5)凌胜利表示:“美日联盟之所以在冷战后得以维系和强化,归根结底还是联盟管理的相对成功,并结合钓鱼岛的具体事例进行解释说明。”参见凌胜利《冷战后美日联盟为何不断强化?——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6期第45~68页;刘丰表示:“美国联盟管理对于美国维持主导地位和推进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并评估了美国的联盟管理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参见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106页。故而,笔者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联盟管理与澳美同盟的强化联系起来,从澳美同盟内部的联盟管理视角入手来分析澳美同盟强化的原因,并对澳美同盟强化过程中遇到的(通过联盟管理也无法解决的)挑战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联盟管理
联盟是建立在有关各方拥有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但在联盟发展过程中,有关各方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因而,在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存续的过程中,联盟管理不可或缺。澳美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故而,对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不可或缺。“从狭义上看,联盟管理是指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对各自承担义务、应对威胁等的分配,主要依据的是所签署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和规定;而在广义上,联盟管理包括联盟成员国为协调各自行为而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2]
联盟国之间通过结成同盟关系获取一定的收益,满足一定的利益诉求,相应的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自身安全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多数盟国都希望在其联盟关系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收益而付出更少的成本,这就涉及联盟成员国间的成本与收益的协调问题。这是联盟管理的重要问题,在联盟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澳美同盟也不例外。在澳美同盟关系中,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希望在不威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以较少的成本换取更大的收益。为了实现这种目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对此进行协调则成了澳美同盟联盟管理的主要内容,双方在联盟内的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成本协调展开的。可以说,协调联盟的成本和收益是澳美同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联盟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联盟困境问题。“联盟管理主要强调联盟内部的协调与谈判以及外在威胁不明时如何重塑或强化原有联盟;在原有威胁弱化后,针对联盟裂变的趋势和可能,如何增强凝聚力,同时如何加强对内控制以避免裂变的示范效应等等。简而言之,联盟管理是与避免联盟管理困境连在一起的。”[3]如何弱化联盟困境是强化联盟关系、增强联盟凝聚力的关键。因而,澳美同盟的强化离不开美国的联盟管理。只有通过联盟管理,弱化联盟困境,才能更好地实现澳美同盟的强化;也只有处理好澳美同盟内的联盟困境问题,澳美同盟才能存续下去。
总的来说,联盟管理可以界定为:联盟成员国为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持联盟关系,对联盟内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协调,在缓解联盟困境的同时实现联盟收益与联盟困境相契合。[4]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是澳美两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联盟管理方式,协调联盟内部成本—收益间的关系,弱化联盟困境,从而维持联盟稳固、强化联盟关系。
二、冷战后澳美同盟强化的表现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澳美同盟呈现出不断强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同盟合作空间的扩大、同盟伙伴关系的拓展以及同盟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等方面。
(一)同盟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太平洋战争期间,澳美同盟仅是一个战时军事同盟,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TheANZUSTreaty)签订的时候,澳美同盟的合作领域也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到了1996年《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签订时,澳美间同盟关系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同盟,澳美双方开始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1世纪以来,出于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理,美国对澳美同盟进行再调整,澳美同盟的同盟关系有所强化,澳美同盟已经成为无特定针对对象的、全球性和全方位同盟。同盟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深化。
美国在2006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声称,“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同盟是面向全球的同盟”[5],这奠定了澳美同盟全球性同盟的基调。澳美同盟的辐射范围覆盖了全球,并不仅仅局限于亚太地区,这一点在澳美同盟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所体现。澳大利亚不仅参与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还追随美国参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还在美国的支持下领导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等。澳美同盟之间的合作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全天候、多领域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备情报、反恐合作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均有合作。政治外交方面,澳美两国多次进行政治交流及外交外事活动,政治协商对话机制不断完善,多次进行高层会晤。军事情报方面,2014 年澳美两国签署《美澳军事力量部署协议》,澳大利亚同意美国提升其在澳的海上安全力量,并同意美国在其领土北部部署空军力量[6],澳美同盟军事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澳美双方还签订情报安全协定,进一步完善双方情报合作机制。反恐合作方面,“9·11”事件发生以后不久,作为美国的坚强盟友之一,澳大利亚立即启动同盟响应机制。2001年9月14日,在堪培拉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澳大利亚决定与北约一样,启动《澳新美同盟条约》,援引该条约的第四款,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7]网络安全方面,2011年澳美举办“2+2”部长级磋商,明确将澳美同盟安全机制的范围由传统的领土完整和政治安全扩展至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攻击行为。由此开始,澳美两国不仅将网络空间的安全纳入军事同盟协定范围,更进一步将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化。[8]此外,澳美同盟在亚太、印太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都有新的进展,实现了亚太、印太地区的互联互动。
(二)同盟伙伴关系日益拓展
澳美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的。而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盟网络化。美国不仅加强自身与其亚太同盟的联系,也致力于加强其亚太盟国间的联系,意图在亚太地区形成自身的同盟网络,从而更好地实现本国的战略诉求,并达到遏制、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故而,美国在原有的亚太同盟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澳美同盟与日本、印度等地区伙伴的联系与互动,深化美日澳印的合作对话机制,由原来的双边关系逐步向多边伙伴关系拓展。
澳美、美日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南北双锚”,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因而,增强澳日双边的联系与互动是美国亚太同盟网络化的关键一环。近年来,美国一直积极推动美日澳安全小三角的建设,不断升级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自2002年起,美日澳三国开始进行三边战略对话(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TSD),该对话最初是在局一级的层面进行,到2006年提升至部长级层面。[9]截至目前,美日澳三方共举行了五次三边战略对话。除此之外,美日澳三国还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加强多边军事安全合作。美日澳三国还签订了情报安全协定,进一步分享彼此的军事情报。澳日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其互联互通,合作的大趋势愈发明显。虽然澳美同盟短期内不会发展成美日澳三边同盟,但三边关系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防范、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仅靠自身难以实现,需要借助澳大利亚的力量。为此,美国不断强化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合作与联系,推进三边关系的互动发展。例如,2007 年9月4日,美、澳、印、日、新在孟加拉湾开展了“马拉巴尔2007”海上联合演习。此次军演,除美、印之外,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也积极参与,五国联动态势明显。澳印两国还就印度核能问题进行多次协商探讨,此举是澳印双边关系强化的显著体现。这些都表明,澳美同盟的伙伴关系持续拓展。
(三)同盟地位持续提升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和日本并称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南北双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倚重的两个国家。然而,作为“南锚”的澳大利亚受到美国重视的程度一直低于“北锚”日本。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逐步调整以及军力的重新配置,澳大利亚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甚至是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澳大利亚在诸多问题上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支点价值被重新发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政治与现有的国防能力以及设施,扩大了美国的战略纵深,为美国其他重要的军事利益提供了帮助,使美国能更为有效合理地分配军事资源,这也提升了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6)David Berteau and Michael Green, et al.,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12, p.13. https: ∥csis-prod. s3. amazonaws. 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转引自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美国防部长哈格尔(Hagel)在2014年声明中强调:“美澳同盟依旧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10]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崛起后的中国会对现有的美国霸权构成严重挑战”[11]的观点日渐流行。基于此,美国希望进一步发挥澳大利亚的地理优势,将其打造成制衡中国的战略支点及前沿阵地。因此,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驻军,建立军事指挥中心;美国还不断升级与澳大利亚军事、情报、技术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越发重视澳大利亚在其亚太战略中的作用。这些都表明,澳美同盟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
三、澳美同盟强化的原因
联盟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联盟的可靠性,缓解联盟困境,实现联盟的存续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联盟管理一般可采取制度约束、权力强制、权威引导、利益协调四种方式。
(一)提升机制化程度以增强联盟约束力
制度约束就是盟国通过在联盟中建立完备的制度(一般是指盟约),增强联盟的机制化程度以此来维持联盟的可靠性、增强盟国的约束力、规范联盟中权责分担的行为。一般而言,联盟的制度越完备、机制化程度越高,主导国对弱势国的战略选择的影响也就越大。[12]联盟将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制度化,并且形成各个成员都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只有遵循相关的行为准则,联盟才能作为一个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增进联盟成员的利益最大化。[2]95
由于澳美同属于西方价值体系,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及历史文化,所以美国对澳大利亚信任度较高,较少对澳方采取制度约束的手段,导致澳美同盟的机制化程度相较于美国亚太地区的其他同盟来说要低。这使得澳美两国的协同行动能力相较于其他联盟来说较弱,澳美同盟的分歧增多,同盟关系弱化。为了强化同盟关系,协调利益分歧,美国加强了澳美同盟的制度建设。
澳新美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探讨同盟内军事合作机制问题时,澳新希望组建一个能接近美国军事决策机构的军事委员会。而美方给出的建议则是缔约方可以派一名军事代表隶属于澳新美同盟理事会;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代表由美国军事代表担任,并对理事会负责。[13]这是澳美双方关于军事合作机制的初步探讨。冷战结束后,双方的条约和机制建设越来越多。在军事合作机制建设方面,2000年澳美两国签订《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声明》,澳大利亚在军舰和潜艇的战斗系统、电子战系统和空对空导弹系统等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与美国协同作战的能力。[14]2004年7月,澳美两国签署导弹防御体系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正式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在外交防务磋商机制建设方面,2006年12月,澳美举行首次年度国防、外交双部长磋商,双方“2+2”战略对话机制正式运作。[14]除了军事、安全及外交方面的机制建设,澳美双方还在1996年签订了《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在2005年签订美澳自贸协定(AUSFTA),将机制建设拓展至经济、贸易领域。
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明确划分了澳美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增强了双方协同作战能力,增加了同盟对双方的约束力以及同盟的可靠性,从而实现了澳美同盟的发展与强化。
(二)运用权力强制迫使澳大利亚服从美国的意愿
权力强制,指联盟关系中实力较强的国家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在联盟的日常决策中强制弱势国服从自己的战略意志。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在非对称性联盟关系中,实力较强的盟国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实力弱小的盟国则没有选择的余地。[15]
唐世平等提出:“一国GDP总量与人均GDP的乘积超过了弱国的两倍时,则该同盟属于非对称性同盟;反之则属于对称性同盟。”[16]美国2018年GDP总量约为20.54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26万美元;澳大利亚2018年GDP总量约为1.43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5.73万美元。(7)世界银行澳大利亚及美国数据(2019-07-02),资料来源:https:∥date.worldbank.org/country/Australia; https:∥date.worldbank.org/country/American。据此标准计算可知,美国的GDP总量与人均GDP的乘积约为澳大利亚的16倍,故而澳美同盟是典型的非对称性同盟,美国是同盟关系中的主导方。美国的实力优势决定了其可以用权力强制的方式来管理澳美同盟。美国以减少安全保护以及弱化联盟关系相威胁,“劝说”澳大利亚服从美国的战略意图;如果“劝说”无效,则会采取权力强制方式。这一点可以在澳大利亚租借达尔文港上看出。2011年11月,澳美达成军事协议,在澳北部重镇达尔文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他军事设施。2014年8月,澳美签署了为期25年的军事合作协议,达尔文港向永久军事基地转变。2015年10月,澳大利亚宣布,将达尔文港的经营权租借给中国岚桥(Land bridge)公司,为期99年。[17]此举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在各种场合多次给澳大利亚政府施压,意图强制叫停。而澳方也迫于美国的压力,在租借问题上有所动摇。
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澳大利亚自主意识增强,澳大利亚要求增强战略自主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美国也开始在澳美同盟的权力配置方面尝试着适度放权,在与澳大利亚进行协商时也会适当地考虑澳大利亚的意见和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澳大利亚的权力强制,在诸多问题上,美国仍不时地采取权力强制的方式管理澳美同盟。虽然美国运用自身实力强制澳大利亚服从它的管理,违背了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但通过权力强制的方式来管理澳美同盟,强化了澳美双方的协同行动能力,加强了澳美同盟的管理。
(三)善用权威加深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认同
权威引导指联盟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弱势国的价值认同而建立起自身的权威,并据此来协调联盟关系的行为。权威关系指的是主导国和从属国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是对一种不平等的社会逻辑的认同。[18]
在当今主权规范被普遍接受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对盟国的影响不是通过强制,也不是完全通过利益交换,而更可能是通过权威关系来实现的。[19]对于澳美同盟来说,因其是同质性同盟,两国拥有相似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两个民族同宗同源,两个国家拥有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正因为有着较高的信任度,美国在对澳美同盟进行管理时更倾向于运用权威管理的方式。例如,2003年,澳大利亚派兵参与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此举引发了中国的担忧。为了缓解中方的担忧,澳大利亚外长唐纳(Donner)随即在北京公开表示,《澳新美安全条约》应该只在澳大利亚或美国遭受直接攻击时才启动,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能启动该条约。澳方做出这一表态后,美国随即向澳大利亚发布6封电邮,要求澳方对其言论进行解释。在美国权威面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John Howard)立即纠正唐纳的表态,唐纳本人也表示撤回此前的“不当言论”。(8)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 Relations”, China Brief, 2005, No.8.转引自刘若楠《美国权威如何塑造亚太盟国的对外战略》,《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55~75页。美国并没有使用权力强制要求澳方解释,而是充分利用自身权威,让澳方改变自身策略。
权威引导在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相较于权力强制,美国更倾向于让同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澳大利亚自觉认同其理念、服从其权威。美国通过在澳美同盟内部建立起自身的权威,形成一定的价值认同,让澳大利亚在诸多行动上自觉“追随”美国,从而减少澳美两国的分歧,弱化澳美同盟的联盟困境,加深了澳美双方的关系,促进了联盟关系的强化。(四)通过利益协调管控双方分歧
联盟成员之间由于受各自外交政策目标、国内政治体制以及领导人等因素影响,必然会出现各自利益冲突甚至对立的情况,也就是说,联盟的形成和运作始终伴随着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2]95利益协调包括利益交换和利益拓展两种方式。利益交换是指联盟之间通过议题联系、利益补偿等方式实现利益的再平衡;利益拓展是指联盟通过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来实现联盟共同利益的扩大。[1]
联盟建立的基础是联盟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但在联盟后续的发展、存续过程中由于联盟双方的诉求、自身的发展情况不同等,双方必然会存在利益分歧,为了化解分歧,就需要利益协调。澳美同盟内部的利益协调从澳美同盟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并且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澳美双方经常使用利益协调的方式来协调双方的分歧。美国签署澳美同盟条约主要是为了争取澳大利亚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TreatyofPeacewithJapan),防范日本法西斯势力东山再起。为了获取澳大利亚的支持,使澳大利亚接受《旧金山对日和约》,接受对日“软和平”,美国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以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换取澳大利亚支持其对日“软和平”的承诺,而澳大利亚则是以放弃对日强硬惩处换取了美国对其安全庇护承诺,双方的利益进行了一定的协调和交换。冷战结束后,澳美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协调双方利益分歧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双方的诸多协调行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方式也是协调分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利益拓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浮”之后开始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澳美同盟经历利益拓展成为全方位、全球性同盟。澳美同盟通过利益交换和利益拓展协商解决双方的利益分歧,调和了联盟内部矛盾,化解了利益分歧的同盟必然更为稳固。
相较于权力强制及制度约束来说,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权威引导及利益协调的方式对澳美同盟进行管理。美国运用权力强制、制度约束、权威引导、利益协调四种方式对澳美同盟进行联盟管理,弱化了澳美同盟面临的联盟困境,加深了联盟内的羁绊与联系,稳定了联盟关系,实现了澳美同盟的强化。澳美同盟的强化与美国的联盟管理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美国联盟管理的成功,澳美同盟才能在冷战后只经历短暂的“漂浮”,就迅速实现再强化。
四、 澳美同盟强化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整体呈现不断强化的态势,但在其强化、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联盟管理无法完全调和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联盟内部的联盟困境问题,以及澳美两国对于如何认知和应对中国崛起而出现的分歧。
(一)澳美同盟的联盟困境始终存在
联盟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联盟困境的变化问题。所有的联盟都存在着联盟困境,主要包含“被抛弃”和“被牵连”两个方面。联盟困境的程度对于联盟的发展存续来说至关重要,决定联盟困境程度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利益、依赖性和承诺(9)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转引自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如果盟国间有高度的共同利益且相互依赖较弱时,联盟的困境较为缓和;反之联盟困境的程度则会比较严重。格伦·斯奈德( Glenn Snyder) 将其总结为利益相对、利益共享以及利益不同。[20]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趋稳定,联盟国的安全威胁有所缓解,这就使得影响联盟困境的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加剧了联盟管理的难度。
在澳美同盟的发展历程中,联盟困境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变化。在澳美同盟内部,澳美双方都存在着联盟困境。对美国来说,一方面,美国担心“被牵连”。美国作为同盟关系中的主导方,常常会因为对弱势盟国的安全承诺而卷入地区冲突当中。在澳美同盟关系中,一旦澳大利亚与别国发生冲突,美国则不得不履行对澳的安全承诺而卷入冲突中,从而“被牵连”。另一方面,美国害怕“被抛弃”。随着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美国担心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战略需求变弱,从而在诸多事务中不再支持美国的政策,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甚至进入中国的战略轨道。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以丧失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为代价获取了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为自身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此同时,因外交自主权的丧失,澳大利亚更易受同盟“牵连”,从而被迫卷入一场“与自身利益无关或相悖的冲突或战争中”[21]。而为了避免被卷入无关冲突,澳大利亚可能会弱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此举又使澳大利亚面临被美国疏远、抛弃的风险。此外,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澳大利亚又面临着“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22]的战略选择新困境。
通过适当的联盟管理,联盟的新老困境虽然能够得到缓解,但无法根本消除。虽然联盟新老困境短期内不会对澳美同盟的稳固性产生根本性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澳美同盟强化的不确定性,成为澳美同盟未来强化过程中一个不小的挑战。
(二)澳美对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崛起存在差异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美国遏制、防范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作为美国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积极追随美国,响应美国的亚太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会无条件地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澳美同盟之所以会不断强化,中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澳美两国无法完全通过联盟内部的联盟管理来进行协调解决,这就给澳美同盟的强化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首先,美澳双方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不同。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则较弱。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由来已久,“在90 年代初,一部分美国政界开始抨击中国的‘无节制’发展导致亚太及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一些白宫官员、智库学者、经济学家、政策制定集团等与之相应和,并一致认定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直至90年代末期,‘中国威胁’话语成为美国政经界、知识界以及国际新闻界等各大领域分析中美关系重要的话语批评逻辑框架”[23]。此后,美国政界、学术界关于中国崛起将对美国霸权带来挑战和“威胁”的认知与言论甚嚣尘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以及特朗普首份国情咨文均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并明确贴上 “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24]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威胁和挑战的认知较弱。虽然近年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感日益明显[25],但其国内各界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也尚未形成(类似于美国战略学界形成的)一致的战略共识。澳大利亚学者任格瑞(Richard Rigby)就曾表示:“就整个世界而言,一个更加富裕、强大的中国不一定是一种挑战。对世界而言,一个失败的中国比一个成功的中国更为危险。”[26]
其次,双方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存在差异。美国更多地强调以武力施压、军事威胁等硬制衡(Hard Balance)方式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则更倾向于运用国际舆论、国际法等对中国进行软制衡(Soft Balance)。美国遏制派强调用“挤压、敲打”中国的强硬政策,以削弱中国的实力,使之不能成为美国的安全隐患和竞争对手。[27]如特朗普政府大幅提升2019 年军费预算,明言欲作遏制中国之用。[24]美国自身强大的实力决定其能够直接采取施压、威胁等硬制衡手段来应对中国的崛起,而澳大利亚不具备硬制衡中国的实力,故而更倾向于运用各种软制衡手段。澳媒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中国干涉论”,试图在世界舆论中塑造中国“咄咄逼人”“以大欺小”的国际形象。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6年5月发布题为《孔子学院课堂的背后:中国政府机构为南威尔士州学生授课》的报道,文章称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文化入侵的工具,是对澳进行政治“渗透”[28]。此外,澳大利亚还倾向于运用国际法来约束中国。例如,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宣判后,澳方声称南海仲裁庭裁决结果具有国际法效力,要求中方遵守。澳方试图借此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达到约束、限制中国和平发展的目的。
五、结 语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对澳美同盟进行有效的联盟管理,实现了澳美同盟的强化,但联盟管理无法解决其内部(“被抛弃”“被牵连”的联盟困境始终存在)与外部(澳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挑战。虽然内外挑战可能会给澳美关系的发展、强化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借助澳美同盟可以达到分摊联盟成本、约束中国,以及降低独自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等目的,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澳美同盟的持续强化态势将延续下去。
虽然澳美同盟是非对称性同盟,但在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中,澳大利亚实际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是美澳双向管理。本文仅将写作的侧重点放在了美国对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上,主要探讨美国如何通过成功的联盟管理促进澳美同盟的强化,而对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着墨不多,但这并不意味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管理不重要,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的联盟管理可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有待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