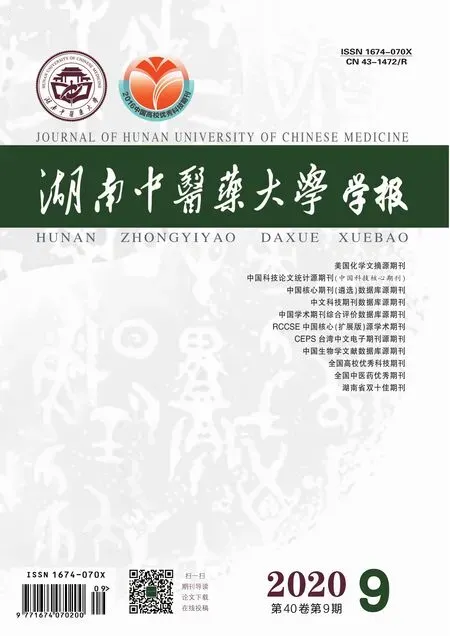伍大华教授运用平眩定晕汤结合SRM-IV前庭诊疗系统治疗耳石症经验
2020-12-20伍大华
彭 舟,伍大华*,谢 乐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410208;2.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6)
耳石症又称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一种因头位运动变化诱发的阵发性外周性眩晕,持续时间常不超过一分钟[1]。其多发于50~60 岁女性,存在22.79%~28.89%的复发率,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2-3]。部分患者可伴严重的恶心呕吐,或存在长时间的漂浮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正常工作,且随年龄增长患者跌仆、摔伤的风险随之上升[4-6]。
伍大华教授为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脑病研究中心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湖南省第二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先后师从国医大师刘祖贻及程丑夫、周慎等名中医,从事临床、科研、教学30 年。伍大华教授善取现代医学及中医学之长,对于耳石症性眩晕病,提出应分阶段治疗,常运用其自拟方平眩定晕汤并结合SRM-IV 前庭诊疗系统(SRM-IV 系统)治疗此病,每有佳效。 笔者有幸跟诊学习,现将其辨治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肝风夹痰上犯为标
在古代医书尚未见耳石症这一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伍大华教授将其归于“眩晕病”范畴。 “眩晕”一病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在《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风致眩之论。 《圣济总录·风头眩》载:“风邪鼓于上,脑转而目系急,使真气不能上达,故虚则眩而心闷”,指出肝风上袭头目,邪扰清窍故致头眩胸闷。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云:“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认为痰饮阻滞清阳导致眩晕,并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创泽泻汤、苓桂术甘汤、肾气丸等温阳化饮之方剂治之[7]。 可见风邪及痰邪是导致眩晕发作的重要病理因素,伍大华教授认为在此病的急性期两者常相兼致病,肝风夹痰上犯,清窍失养,是眩晕发作的重要病机。 正如《医碥·眩晕》中记载:“痰涎随风火上壅,浊阴干于清阳也,故头风眩晕者多痰涎。 ”风性主动,故此病发时病者较多表现为头目眩晕。 痰阻清阳,浊阴不降,故常伴恶心呕吐、胸闷等症状,体位改变病性加重是因风痰之邪易于流动之故。
1.2 肾元虚损为本
耳石症的病位在耳,《丹溪摘玄·卷十八》云:“夫耳者,肾之听候。肾者,精之所藏。肾气实则精气上通,闻五音而志矣”。 肾开窍于耳,肾是耳石症的病根所在。 伍大华教授认为,肾虚为眩晕之本其证有三:一则肾主骨生髓,如《医经精义·中卷》曰:“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 伍大华教授认为耳石为骨之余,由肾精生髓而化生,肾虚则失之充养固护,脱于耳窍发为眩晕;再者《医学衷中参西录》有言:“脑为髓海,实由肾中真阴真阳之气酝酿化合而成,缘督脉上升而灌注于脑”。肾元虚损,不能生髓充脑,清窍失养,可直接导致眩晕发作;三则“肾主水”,庞安常在《医贯·先天要论》中云:“有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原出而不纳则积,积而不散则痰生焉”。 肾虚则水液代谢失司,水聚而为痰。 清代医家林佩琴在《类证治裁·眩晕论治》中言:“肝胆乃风木之脏,相火内寄,其性主动主升。 高年肾液已衰,水不涵木,以至目昏耳鸣,震眩不定。”肝肾同源,肾虚则肝木失水之涵养而内风内动,夹痰上犯,清窍为风痰所扰亦可发为眩晕[8]。
2 辨治思路
2.1 急性期首选复位治疗
耳石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有半规管结石症和嵴帽结石症两种学说,这两种学说认为其发病与耳石的掉落和不正常沉积有关[4]。 复位治疗可通过外力使患者头位定向的变化,让脱落的耳石从半规管回到椭圆囊[9-10]。 但传统的手法复位限于医师的自身经验,且部分患者无法耐受,SRM-IV 系统是最新结诊疗一体的设备,较传统手法复位更易操作,且研究报道SRM-IV 系统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4]。在发病的急性期,病情急变,治宜速驱病邪,眩晕复位治疗较之更为便捷有效。故对于处于耳石症发作期的患者,伍大华教授常推荐SRM-IV 系统的自动复位治疗,而对于复位后的残余症状如头晕昏沉或行走不稳等,则予以中药巩固治疗。
2.2 平眩定晕汤补肾化痰
经复位治疗后的部分患者阵发性的位置性头眩明显减轻,SRM-IV 系统检查眼震阴性,但仍有持续性头昏蒙不清、行走不稳等主观症状,部分则反复发作,需多次复位治疗[11]。 伍大华教授认为其病机以肾元虚损为主,兼有未尽的风痰,属本虚标实之证,治宜补肾培元固骨为主。清代陈念祖在《医学从众录·眩晕》云:“乙癸同源,治肾即所以治肝,治肝即所以熄风,熄风即所以降火,降火即所以治痰。”肾之阴阳和调则精气充盈,能收摄诸水,肝阴得肾精的濡养则虚风得息,风痰自然就祛除了,补肾培元为之关键[12]。 此外,国医大师刘祖贻有“脑髓阳生阴长”理论,认为肾中的阳气鼓荡作用促进清阳充盈脑髓,在肾精生髓的过程中肾阳的蒸腾十分关键[13]。故伍大华教授认为此病用药应以平和为基,酌情使用温肾药物,以防全方过于阴柔,从而使阴阳和调,达到平补肾元的功效。
平眩定晕汤是伍大华教授基于以上病机特点,据多年临床经验在《医学心悟·眩晕》中的半夏白术天麻汤基础上加入补肾培元固骨的药物加减化裁而来,以奏平补肾元、息风化痰之功。 方中骨碎补、补骨脂固骨生髓,微微生火,鼓肾气,取“少火生气”之义,阳气无阴则不化,《本草从新·卷三草部》言熟地有“滋肾水,封填骨髓,利血脉,补益真阴,聪耳明目”之功,故用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固肾精益元神,于阴中求阳,使阴阳生化不竭,上药共用补肾中之阳气以化痰水,滋肾阴以清虚风;法半夏、天麻平肝息风化痰,茯苓、白术淡渗脾湿,使补而不滞,陈皮理气化痰,使气顺痰消;再佐葛根、丹参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神曲、山楂固护胃气,助运药食。 诸药合用消补结合,固本为主,兼之治标。 随症加减:胃脘不适者加海螵蛸、瓦楞子制酸止痛;血压高者加蒺藜、石决明平肝潜阳;口苦者加黄连清心热;夜寐差者加百合、夜交藤、酸枣仁除烦安神。
3 用药特点
3.1 用药注意固护胃气
《景岳全书·饮食门》云:“且凡欲治病,必须先藉胃气以为行药之主,若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而疾常易愈,此以胃气强而药力易行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胃气充实则药食运化正常,药效才能更好的发挥,胃气虚弱则药食壅滞,反可致病情加重。 故治百病皆以固护胃气为要,伍大华教授在治疗时常配伍山楂、神曲或鸡内金等药物以固护胃气,助行药力。
3.2 适当配伍活血化瘀药物
眩晕反复发作,病久生瘀。一方面因肾藏精,精气是滋养脏腑以维持正常功能的重要物质,肾虚则脏腑功能失调,气血生化失源,因虚致瘀;另一方面肾为水脏,虚则不能纳气归元,水液失于固摄,积聚成痰,痰与瘀血同类互生,痰浊阻滞血脉必导致瘀血内生[14]。 故在治疗久病患者时,伍大华教授常配伍丹参、葛根等活血通经活络之药物[15]。
4 验案举例
王某,女,51 岁,2019 年7 月17 日初诊。主诉:眩晕反复发作2 月。 患者近2 月来眩晕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发作时感天旋地转,曾在当地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经眩晕变位试验诊断为耳石症,予眩晕复位治疗后头晕仍反复发作。 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现服降压药治疗。现患者头目眩晕,体位改变时加重,伴恶心呕吐,平素腰膝酸软,纳食一般,大便、小便正常,睡眠尚可。舌质淡红,苔黄腻,脉弦滑。血压138/85 mmHg。 查眩晕变位试验阳性,提示眩晕发作期。中医诊断:眩晕(肾虚风痰上扰证),西医诊断:耳石症。 予以SRM-IV 系统复位治疗。
2019 年7 月23 日二诊:经眩晕复位治疗后患者诉位置性眩晕减轻,偶有胸闷、脚踩棉花、行走不稳感,纳食一般,胃脘不适,二便正常,睡眠尚可。舌质淡红,苔薄黄,脉沉细滑。 血压140/85 mmHg。 治以补肾固骨,息风化痰。予以平眩定晕汤加减:熟地黄10 g,枸杞10 g,骨碎补10 g,补骨脂10 g,法半夏10 g,天麻5 g,白术10 g,陈皮10 g,茯苓10 g,葛根30 g,丹参30 g,蒺藜15 g,海螵蛸15 g,瓦楞子10 g,神曲10 g,鸡内金10 g。7 剂,水煎服,日一剂,分两次温服。
2019 年7 月30 日三诊:服上方后患者诉头晕及行走不稳感基本缓解,时有脑鸣,两目干涩,纳食可,大便正常,夜尿较多,睡眠一般,口苦,舌质暗,苔薄,脉沉细。 血压125/80 mmHg。 续予上方,去蒺藜、海螵蛸、瓦楞子,加密蒙花10 g,益智仁10 g,蔓荆子10 g。7 剂,水煎服,日一剂,分两次温服。后电话随访患者头晕未再发作,余症状基本缓解,日测血压稳定。
按:本案患者女性,年过五十,处于更年期,眩晕变位试验阳性是耳石症的典型案例。其眩晕发作时觉物眩天摇,缘于风痰上扰蒙蔽清阳所致;胸闷恶心、苔腻脉滑是痰饮阻滞的表现。故急治其标,先予以SRM-IV 系统眩晕复位治疗。 经复位治疗后其标虽缓,但其肾虚之本未复,加之有未尽的风痰,故二诊时仍有残余头晕及胸闷等症状。 陈修园在《医学从众录·眩晕》中云:“河间诸公,一于清火驱风豁痰,犹未知风火痰之所由作也。然欲荣其上,必灌其根,如正元散及六味丸、八味丸,皆峻补肾中水火之妙剂。”可见在下肾之精气满盈,才能养肝阴平息内风,运化虚痰,平眩之本重在补肾培元。故二诊予平眩定晕汤为主方,治以补肾培元、固骨生髓为主,兼以息风化痰。如熟地黄、枸杞子补肾之阴,滋水涵木,使肝木得养,内风得息;骨碎补、补骨脂等温肾助阳之药,推动阳气宣发,以化虚痰,肾阳蒸腾还可助脑髓充养。 此以补为通,肾元得补则风痰之证自减。 并加入法半夏、天麻等药使息风化痰之力倍增。 三诊患者头目眩晕已大有好转,胃脘不适好转,血压恢复正常,故去蒺藜、海螵蛸、瓦楞子,脑鸣、腰酸膝软、双目干涩、夜尿多是肾虚的典型表现,故加入密蒙花、蔓荆子滋肾明目,益智仁温肾固精缩尿。
5 小结
耳石症性眩晕病病机复杂,其发作期和缓解期的病机不尽相同。 急性期风痰之邪亢盛,单一的中药治疗尚不能速达病灶,SRM-IV 系统的复位治疗虽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对于残余症状及反复发作的患者作用有限。《素问·至真要大论》载:“病有盛衰,治有缓急。”因此,伍大华教授提出辨治耳石症当先审查病情急缓、证候虚实,治疗时应有先后主次。 急性期耳石症可首选SRM-IV 系统的复位治疗,对于复位后残余症状及反复发作的缓解期则治以补肾固骨为主,兼以息风化痰,以平眩定晕汤为主方。在疾病的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灵活加减,如此才可使临床疗效达到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