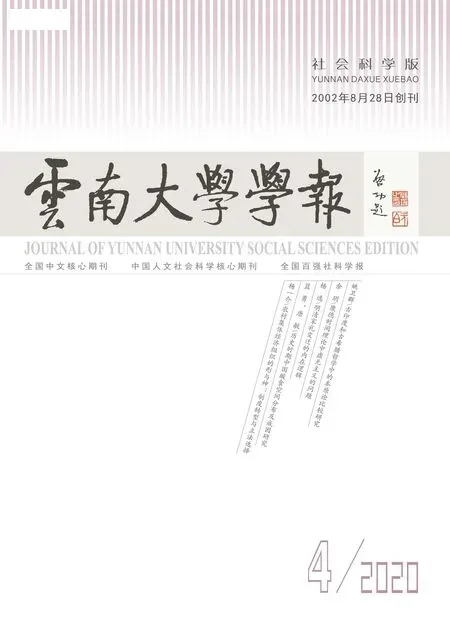希望比知识更重要
——对罗蒂希望理论的一个考察
2020-12-15张艳芬
孙 斌,张艳芬
[1.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2.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对于未来,我们无法形成知识,因为未来不是认知的内容。未来的善或者说美好,是我们出于自身而构想出来的。这种构想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所相信的。对于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我们无法也无须借助知识来对其加以论证以便使其获得一个可靠的基础。我们只是对它满怀希望。所以,罗蒂的想法是用希望代替知识,他说:“说人们应当用希望来代替知识,差不多就是说,人们应当停止担心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是否基础牢靠,而开始担心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想象力为他们当前信念设想出有趣的可供替代的选择。”(1)Richard Rorty,“Truth without 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London: Penguin Books,1999,p.34.知识诉诸的是一种论证的才能,这种才能需要在牢靠的基础或者说根据上运作。而想象力触及到了作为这些基础和根据的前提的东西,它们恰恰是不牢靠的,因此对于它们总是可以有可供替代的选择。这个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即他所说的,“在有充分根据的信念的基础那里存在着没有根据的信念”(2)Ludwig Wittgenstein,On Certainty,Edited by 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Translated by Denis Paul and G.E.M.Anscombe,Oxford: Basil Blackwell,1979,p.33.。当然,罗蒂在进行这样的考虑时,有着自己的目的和用意,这就是他所关心的比哲学更重要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所以,他这里所说的知识以及希望对知识的代替有着明确的指向,他说:“我认为,人们把实用主义和美国联系起来的最好做法就是指出,这个国家以及它的最杰出的哲学家都建议,我们能够在政治上用希望代替哲学家们通常试图获取的那类知识。”(3)Richard Rorty,“Truth without 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24.很显然,知识是就哲学而言的,而代替是就政治而言的。这一切与罗蒂对自由问题的重新思考相呼应。
一、为什么是希望?
到这里为止,希望是什么还没有在任何命题中得到确切的说明,如果不是说定义的话。不过,这也许并不应当受到指责,因为旨在获得知识的说明对于希望来说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说明总是需要一套说明的体系或者说机制;另一方面,说明所达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对象的理解。然而,希望既与那些提供各种各样专业话语的说明体系无关,也不是要通过理解将对象归结到那些已被认知的东西。因此,问题也许不应该是希望是什么,而应该是为什么是希望。对于这个问题,罗蒂的回答恐怕是,因为希望能带来灵感。灵感价值无法在专业领域中被找到,也无法在充当基础的哲学中被找到,它是希望所特有的。罗蒂的以下这番表述透露了这一点,他说:“灵感价值通常不是由方法、科学、学科或者专业的运行所生产出来的。它是由非专业的预言家和造物主的个人笔触所生产出来的。比如,你不能在把一个文本看作是文化生产机制的产品的同时,发现这个文本中的灵感价值。以这种方式看待一个作品所给出的是理解而不是希望,是知识而不是自我转化。因为知识是这样一回事情,即把一个作品放在一个熟悉的语境中——把它同已经被认知的事物联系起来。”(4)Richard Rorty,“The Inspirational Value of Great Works of Literature”,in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3.在这里,预言家和造物主并不进行说明,他们的所言所行出于有着个人色彩的灵感,从而不同于普遍的东西:既不同于普遍同意,也不同于普遍有效。唯其如此,它们无法同已经被认知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起来无非意味着对后者即已经被认作习惯和传统的东西的证明。如果问这样的灵感价值为什么会被他们生产出来,那么回答显然无关乎理由的说明而只可能是:他们希望如此,或者至多再补充一句,如此是令人满意的。无论如何,所希望的这个如此不是确定的。
罗蒂在谈到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时道出了这一点:“存在着两种任务:一种是,参照不变的结构来证明过去的习惯和传统是正当的;另一种是,用更令人满意的未来代替不令人满意的过去,并因而用希望代替确定性。我试图表明,詹姆斯和杜威就真理所说的东西如何成为以后一种任务代替前一种任务的途径。”(5)Richard Rorty,“Truth without 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p.31-32.也就是说,希望是一种与令人满意的未来相提并论的东西。这种相提并论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希望对于那令人满意的未来有所认知并进而给出论证,恰恰相反,乃是因为希望构成了种种这些对于确定性的追求的努力的反面——唯有存在着这样的反面,罗蒂所说的不同于知识的自我转化才得以成为可能。进一步地,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即帮助我们从哲学所提供的这种不变的基础中摆脱出来,不仅使自我转化得以成为可能,而且使新的文明得以成为可能。这其中所传递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希望,而不是理论贡献。而罗蒂也正是指出,詹姆斯和杜威“以一种社会希望的精神来写作。他们要求我们通过放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生活、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宗教信仰‘建基于哲学基础’之上的想法,来解放我们新的文明”(6)Richard Rorty,“Pragmatism,Relativism,and Irrationalism”,in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61.。罗蒂所说的这种社会希望的精神,给予我们以灵感去想象那仅仅从过去的习惯和传统出发想象不到的人生。
如果说以社会希望的精神写作出来的作品能给予我们一种特别的灵感,那么这些作品的写作者也因此而变得特别了,即他们同其他一些写作者区别了开来。作为结果,正如社会希望成为两种任务的区分尺度那样,灵感价值也成为两类学者的区分尺度。罗蒂在一处讨论灵感价值的地方这样说道:“当我把灵感价值归于文学作品时,我的意思是,这些作品使人们想到,对于这一生有着比他们想象的更多的东西。产生这类效果的常常是黑格尔或马克思而非洛克或休谟,是怀特海而非艾耶尔,是华兹华斯而非豪斯曼,是里尔克而非布莱希特,是德里达而非曼,是布鲁姆而非詹姆逊。”(7)Richard Rorty,“The Inspirational Value of Great Works of Literature”,in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p.133.罗蒂的这个区分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对照,这种对照是满怀激情的人和贡献理论的人之间的,当然也是希望与知识之间的。詹姆斯和杜威,作为以社会希望的精神写作的人,一方面对文化、道德、政治、宗教等问题谈了很多,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就它们贡献出可充当基础的理论,以至于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预言家。罗蒂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做了分析:“然而,强调社会希望和解放的这种启示,使得詹姆斯和杜威听起来更像是预言家而不是思想家。这是误导性的。他们对真理、知识和道德说了一些话,尽管在一套套地回答教科书问题的意义上他们没有关于它们的理论。”(8)Richard Rorty,“Pragmatism,Relativism,and Irrationalism”,in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p.161-162.当那些重大的题目以非理论的方式被言说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这些言说轻易地认作是预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希望也以非理论的方式得到言说。因此,把詹姆斯和杜威看作是以希望来进行预言的思想家,也许是避免这种误导性看法的一种方法。不过,由这样的争论所引出的希望与预言的关系可能比这种辩护更加重要,因为它涉及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希望是以何种方式运作的。
在罗蒂看来,希望是以预言的形式来运作的,尽管常常是失败的预言。当希望在预言中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对那些可实证的东西进行预测,而只是给出灵感——灵感(inspiration)从字面上来说还有鼓舞的意思,在这里就是鼓舞人们去过一个值得过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有多少,其基础是社会正义。在罗蒂看来,较之那些贡献理论的人来说,满怀激情的人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后者生产着希望。所以,罗蒂说:“在学院里面,人文学科曾经是满怀激情的人的避难所。……如果他们离开了,那么人文学科的研究将继续生产知识,但却不再生产希望。”(9)Richard Rorty,“The Inspirational Value of Great Works of Literature”,in Achieving Our Country: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rctury America.p.135.
二、作为偶然的自由
在罗蒂那里,希望之所以往往变成错误的或者说失败的预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希望是偶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陈述希望的语言是偶然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已经在前面所援引的“用希望代替确定性”中获得了某种暗示。不过,事情远不止这些,因为对于偶然以及那些可归之于它的东西,罗蒂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入的阐述。他说:“把人们的语言、良知、道德以及最高希望看作偶然的产品,看作那些曾是偶然生产出来的隐喻的本义化(literalization),就是接受一种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使人们适合于这样一个理想自由国家中的公民身份。”(10)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61.一般来说,语言、良知、道德和希望被认为是充当基础的东西,但是它们在罗蒂那里却被明确地认为是偶然的东西。这是因为,罗蒂试图在自由问题上做出重新思考,即坚持一种作为对偶然性的承认的自由。这在这里所提及的隐喻和本义中已经有所道出。并不是说隐喻拥有一个不同于本义的意义,而是说隐喻没有意义,因为只有在某种语言框架中获得自己的位置才能拥有意义,但隐喻不在任何这样的语言框架中。反过来说,一旦隐喻获得了这样的位置,亦即获得了某种习惯的使用,那么它就是一个死了的隐喻,或者说,一个本义化的隐喻。人们通常使用的隐喻往往是本义化了的隐喻,这意味着,它们由之而出的偶然性遭到了遗忘甚至拒绝。
可是,如果隐喻没有以本义化的方式获得习惯上普遍有效的使用,那么它是以何种方式继续保有其在偶然性尺度上的使用的?罗蒂以浪漫主义传统来加以分析,他说:“浪漫者们把隐喻归于一种被称为‘想象力’的神秘能力……”(11)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1997,p.19.这意味着,所问及的那种使用是随着想象力界线的永远延伸而得到呈现的。与此同时,隐喻随着这种永远延伸而永远在语言中得到重新描述,或者说,旧的隐喻不断在死去,而新的隐喻不断在形成。这就如同罗蒂循着戴维森的想法所给出的阐述:“戴维森让我们把语言的历史因而还有文化的历史考虑为达尔文教我们考虑的珊瑚礁的历史。旧的隐喻不断地相继死去而成为本义(literalness),然后充当新的隐喻的平台和衬托。这个类比让我们把‘我们的语言’——即20世纪欧洲的科学语言和文化语言——考虑为某种体现许许多多纯偶然性的结果的东西。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都是一种偶然性,都是成千上万找到定位的微小突变(和数以百万没有找到定位的其他微小突变)的一个结果,就像兰花和类人猿那样。”(12)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16.在这样的偶然性中,罗蒂看到的不仅是语言,而且是自由。这两者在罗蒂那里是融为一体的。
罗蒂这样来考虑语言的偶然性:“我所说的‘语言的偶然性’使之变得难以置信的正是这种普遍有效性的主张,我的自由乌托邦的诗化文化不再有这样的主张。这样一种文化反倒是同意杜威的说法,即‘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艺术比种种道德更有道德。这是因为,后者或者是或者倾向于变成现状的献祭……人类的道德预言家总是诗人,尽管他们是以自由诗体或是用寓言比喻来言说的。’(13)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 Capricorn Books,1958),p.348.——原注。”(14)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69.我们已经知道,“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这句话出自雪莱,而杜威就在这个传统之中。诗人靠想象力说出的东西总是隐喻性的,它们不在任何一种既定的语言框架之中,因此,它们非但不是要论证现状的正当性,反而是要扩展出不同于现状的言说方式。就此而言,它们比那些服务于现状的种种道德更有道德。作为结果,不同地言说成了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它密切关联于语言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乃至人类的变化。而能够不同地言说的就是诗人。
对此,罗蒂继续以浪漫主义的主张来加以阐述:“浪漫者们主张想象力而非理性才是首要的人类能力,他们以这个主张来表达一种认识,即认识到,不同地言说的才能而非良好地论证的才能,才是文化的变化的主要工具。……德国的观念论者们、法国的革命者们、浪漫派诗人们共同隐约地感觉到,如果人类的语言发生变化以至于他们不再说他们向非人的力量负责,那么他们就将因此而变成一种新的人类。”(15)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7.在这里,罗蒂要说的是,变化是偶然的,因而不需要论证的才能,而只需要不同地言说。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非人的力量是偶然的反面,因而它的需要也与变化相反。所有的变化从不同地言说即语言的变化开始。
就自由问题而言,这些变化使得对于自由主义的重新描述成为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当然,这种重新描述与罗蒂所说的自由乌托邦的诗化文化有关。罗蒂说:“我们需要对自由主义做出一种重新描述,亦即,将它描述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被‘诗化’的希望,而不是描述为文化能够被‘合理化’或‘科学化’的启蒙希望。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种希望:一种是特异品质的幻想的实现机会将会成为均等的;另一种是每个人都将用‘理性’来取代‘激情’或者幻想,而我们需要以前一种希望来代替后一种希望。”(16)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53.言下之意,自由主义必须被重新描述为一种与不同地言说相适合的东西,而这种适合的契机就是文化的诗化,即渗透着隐喻、想象力以及偶然性的诗人的言说方式成为一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三、作为反讽的自由
不过,我们还不打算就此结束不同地言说这个话题。这是因为,不同地言说意味着一种词汇与另一种词汇的遭遇,而这就需要我们对遭遇的和被遭遇的词汇做出考察。罗蒂将它们考虑为终极词汇(final vocabulary),他说:“所有人都随身携带着一套语词,他们用这套语词来证明他们的行动、信念和生活是正当的。……我把这些语词称作是一个人的‘终极词汇’。/ 它之为‘终结’乃是就如下意义而言的,即,如果对这些语词的价值产生怀疑,那么它们的使用者没有非循环的论证援助。”(17)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73.换言之,终极词汇无法消除对它本身所产生的怀疑,而只能给予其以一种循环论证。这样一来,终极词汇之间的遭遇就成了一桩至关紧要的事情,因为它使得语词的价值获得了重新描述的契机,即通过另一种终极词汇来描述。不过,这种重新描述要得以成为可能,还必须承认两点:一、不存在一个由以对终极词汇进行选择但其本身超越于终极词汇的元词汇;二、在这些终极词汇之中没有哪一种因为其更接近实在的东西而具有优先性。这是因为,这样的超越性和优先性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可以充当基础的唯一描述,这当然是重新描述的反面。
所以,罗蒂补充说道:“倾向于哲学化的反讽主义者,既不把终极词汇之间的选择看作是在一个中立的、普遍的元词汇中做出的,也不把它看作是由奋力越过现象而抵达实在的东西的企图所做出的,而仅仅把它看作是由以新对旧的游戏做出的。/ 我把这类人称作‘反讽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任何东西都可以由重新描述而显得好或坏,而且他们也放弃了制定终极词汇之间的选择标准的企图……”(18)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73.这意味着,对一个终结词汇的批评只可能来自另一个终极词汇,来自它与它的遭遇。其结果就是重新描述,以及对重新描述的重新描述。
用罗蒂话来说就是:“对我们反讽主义者而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批评一个终极词汇,除非是另一个这样的终极词汇;不存在对于一个重新描述的回答,除非是一个重-重-重新描述。”(19)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80.反讽主义的重新描述是意义重大的,它直接联系着罗蒂所关注的自由问题,因为“寻找基础和试图重新描述之间的差异,象征着自由主义文化和旧的文化生活的形式之间的差异”(20)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45.。如果结合前面的援引,那么这种重新描述所透露的就是,对于反讽主义者来说,自由不在于去了解作为基础的人性,而在于去了解另一个人,正如去遭遇另一个终极词汇。罗蒂由此指出了自由的反讽主义者和自由的形而上学家之间的一个不同,这就是:“对于自由的反讽主义者来说,在想象中进行身份认同的技艺做了自由的形而上学家想要借助特定道德动机——合理性、对上帝的爱、对真理的爱——来做的工作。反讽主义者能够正视并且也渴望防止对于他人——不管在性别、种族、部落以及终极词汇上有什么差异——的实际的和可能的羞辱,但她并不把这种能力和渴望看作比她自己的其他部分更加真实、更加核心、更加‘在本质上合乎人性’。”(21)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93.这里再次提到了想象力的运作,即,唯有以想象的方式设身处地地成为他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并防止对于他人的羞辱。这一点比以理性的方式确立人性的本质更加重要。
但是,如果说想象性地成为他人意味着一种重新描述的话,那么这种重新描述会由于缺乏本质的和普遍的东西而被贴上偶然性的标签。在罗蒂看来,这样的偶然性恰恰是反讽的自由的特征。他在另一处比较形而上学家和反讽主义者的地方说到,反讽主义者“不得不说,我们的自由的机会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而历史的偶然性只是偶尔地被我们的自我重新描述所影响”(22)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90.。归于描述的偶然性正是可以归于词汇。如果我们在终极词汇的意义上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可以说,正如我们前面所援引的,语言的这种偶然性意味着良知、道德以及最高希望都是偶然的。在这里,从反讽的自由与偶然性的这种关联出发,我们可以说,尽管那些东西是偶然的,但人们仍然对它们保持忠诚,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它们是偶然的,所以人们保持忠诚。
关于这一点,罗蒂在转引熊彼特的一段话后给出了自己的评论:“柏林以对于约瑟夫·熊彼特的援引来结束他的文章,熊彼特说:‘认识到人们的确信的相对有效性但却毫不妥协地支持它们,这是把文明人同野蛮人区分出来的东西。’……用我所发展出来的行话来说,熊彼特关于这是文明人的标志的主张转化为另一个主张:我们世纪的自由社会已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能够承认词汇的偶然性的人,他们以这样的词汇来陈述他们的最高希望——他们自己的良知的偶然性——但却仍然对那些良知保持忠诚。像尼采、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普鲁斯特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物,例证了我所说的‘作为对偶然性的承认的自由’。”(23)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46.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即:之所以要对偶然的东西保持忠诚,乃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偶然的东西的产物——对它们的忠诚就是对我们的忠诚。
这样的忠诚使我们得以成为自由乌托邦的公民。对于罗蒂来说,自由乌托邦的公民就是自由反讽者,他说:“总而言之,我的自由乌托邦的公民们将是这样的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审议的语言的偶然性,并因而意识到他们的良知乃至他们的共同体的偶然性。他们将是自由反讽者——这样的人满足熊彼特文明的标准,并把承诺同对于他们自己承诺的偶然性的意识结合起来。”(24)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61.这番话给出了对于作为反讽的自由的一个概括性的写照: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良知以及共同体做出承诺并保持忠诚;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我们所交付的承诺和忠诚乃是偶然的。换言之,我们之所以满足熊彼特的文明标准,不是因为我们成为文明人的本质的载体,而是因为我们成为始终意识到偶然性的自由反讽者。可以说,自由作为偶然与作为反讽无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就是希望。
四、“托洛茨基和野兰花”
罗蒂甚至用了“自由的希望”这个表述。在罗蒂看来,反讽主义者的私人的东西要得到调整以适应自由的希望。就这一点而言,与哈贝马斯立足于公共需要做出的质疑相反,罗蒂坚持认为,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其他与他们相似的人能够在调整反讽主义者的私人认同感以适应她的自由的希望上发挥作用。然而,现在所讨论的乃是调适——而不是综合。我的‘诗化的’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已经放弃了把人们处理其有限性的私人方法和人们对其他人类的义务感合并起来的企图”(25)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68.。如果说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意味着公共的方面的话,那么罗蒂这里是在告诉我们,私人的方面与公共的方面之间的关系乃是调适而非综合。唯其如此,前者才既不会被还原为也不会被提升为后者,或者用罗蒂自己的话来说,不会发生合并——无论是诗人还是反讽主义者都是这样的合并的反面。我们知道,公共和私人这两个方面在罗蒂那里获得了一个比喻性的表达,这就是“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这个表达成为罗蒂的一篇回顾性的或者说自传性的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追溯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经历的思想变迁。
罗蒂说,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从父母书架上的《列昂·托洛茨基案》和《无罪》了解到了公共的方面的存在。与此同时,他又承认自己还有着一些私人、古怪、无法言表的兴趣。这些兴趣构成了他的私人的方面,比如他对野兰花的态度——“我并不十分确定那些兰花是这样重要,但我确信它是如此”。(26)cf.Richard Rorty,“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London: Penguin Books,1999,pp.5-7.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么罗蒂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责任和私人兴趣几乎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可是,一旦我们明白他所说的公共的方面和私人的方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他说:“15岁的时候……就我心中的计划而言,乃是要使托洛茨基和兰花一致起来。我想要找到某种理智的或者审美的框架,这样的框架可以让我——用我在叶芝那里偶遇的一个令人激动的短语来说——‘在一个单一的幻象中把握实在和正义’。我用实在来指……我感到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触动,被某种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的东西所触动。我用正义来指,诺曼·托马斯和托洛茨基两人所代表的东西,弱者从强者之下解放出来。”(27)Richard Rorty,“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p.7-8.尽管这里所说的计划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但是这里对于托洛茨基和野兰花的阐释并没有发生改变,即把它们分别阐释为正义和实在。
对于这个阐释,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托洛茨基所代表的作为公共方面的正义,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是作为私人方面的实在。这是因为,这样的私人方面远远超出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私人兴趣,涉及了形而上学。这种涉及在罗蒂的另一句话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道德的和哲学的绝对听起来有点儿像我所钟爱的兰花——神秘、难找,只为被选中的极少数人所知。”(28)Richard Rorty,“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8.这里所说的绝对就是刚才所说的实在,它们作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正可以被视为罗蒂意义上的野兰花,即属于私人方面的野兰花。因此,在罗蒂那里,计划的改变,亦即使托洛茨基和野兰花一致起来的企图的放弃,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将社会科学的方面和形而上学的方面区分开来,而不是将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公共方面和私人方面区分开来。罗蒂这样来回顾他做出的这个区分:“那本书(《偶然,反讽和团结》)认为,没有必要把某人个人的相当于托洛茨基的东西和他个人的相当于我的野兰花的东西编织在一起。毋宁说,他应该设法放弃把以下两样东西系在一起的诱惑,一样是他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另一样是他与他全心全意所钟爱的无论什么奇特的事或人(或者,如果你愿意,他痴迷于的事或人)之间的关系。”(29)Richard Rorty,“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p.13.在这里,道德责任作为公共的方面,无法以理论的方式来承担,因为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私人兴趣。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人的本质之类的东西考虑为哲学家们的私人兴趣的结果,那么事情也许就更清楚了。事实上,罗蒂之所以提出后哲学文化或者后哲学政治,正是因为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非但无助反而扰乱公共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对于公共领域,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人们如何凭借共同本质团结在一起,而是这些人们如何由于所遭受的相同的痛苦和羞辱而团结成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痛苦和羞辱的蒙受者可以得到不同的指认,但是痛苦和羞辱本身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换言之,要紧的不是那些指认,而是以如前所述的那种想象的方式设身处地地成为蒙受者。只要他们设身处地地成为彼此,那么他们就彼此成为“我们”。这就是罗蒂说的“但是,那种团结并不被考虑为对于所有人类中的核心自我、人的本质的承认。毋宁说,它被考虑为一种能力,即能够明白越来越多的(部落、宗教、种族、习俗等等的)传统差异与痛苦和羞辱方面的相似性比起来是不重要的——这种能力把那些与我们迥异的人们考虑为可以包含在‘我们’的范围之中。……(例如小说或民族志中)对各种各样痛苦和羞辱的详细描述而非哲学或宗教论述,才是现代知识分子对道德进步所做的主要贡献”(30)Richard R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192.。无论在什么时代,弱者从强者之下解放出来都是正义的,这样的正义也是希望,它们为社会科学提供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