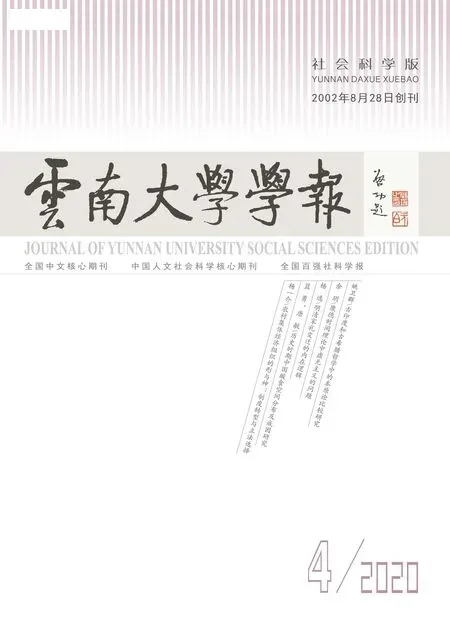历史地理学研究中GIS的认知过程及其人类因素考量
2020-12-15王晗
王 晗
[苏州大学,苏州 215123]
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纷纷开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对未来学术发展的预估和展望。在此情势下,历史地理学也进入到一个需要沉淀积累和蓄势待发的关键时期。由于研究者自身学术经历的不同、所处科研环境的迥异以及学缘关系的差别,因此在对历史地理学所取得成就的认知过程的把握上也存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在新思潮和新技术的影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学术史回顾中的GIS技术
在世纪之交学术史回顾中提及GIS技术的,当首推葛剑雄、华林甫于2002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葛剑雄和华林甫的谋篇布局中,历史地理的信息化的内容被放置在了“第四节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和研究”中。其表述为:“历史地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数字化,进而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用数字化方法重新研制历史地图,包括将有关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果制成相应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葛剑雄和华林甫对GIS技术的应用提出了值得期待的预估:“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坚持标准年代与标准年代之外内容无法同时记录、能够选择的标准年代有限、局部的修订因牵涉全图而不能及时进行等),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1)葛剑雄、华林甫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3期。这篇论文表达了老一辈学者对本学科未来发展的深切希望,同时将敏锐的视角锁定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上。(2)葛剑雄在稍后发表于《东南学术》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一文中,指出了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其认为,“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因此,该文的发表,颇受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共同关注。
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等出身地理学或在地理学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先后在《地理研究》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两篇论文,以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语言表述方式对历史地理学已有的成就和发展的前景做出判读。其一是《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其二是《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干进展》。第一篇论文是在简要回顾20世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共有中华文明演进的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高分辨率环境要素序列建立与时空特征分析,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适应研究与不同地域适应模型建立,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华夏故土嬗变集成研究及其图谱编制,以及文化的区域差异问题研究等方面。(3)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 :《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3期。第二篇论文则是对20世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细化的回顾,并在结论部分继续支持第一篇论文的观点:“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4)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 :《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干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
葛全胜等学者相关论文的发表和观点的持续发酵,曾引发历史地理学界的强烈反应,其后续影响也颇为深远。其深远影响在于,让更多的历史地理学者,尤其是当时成长中的中青年学者,对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三位大师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相关表述和思想进行重新研读和再理解。同时,葛文中多次提及“传统方法和现代技术的结合”,并将这种结合上升到可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贡献的高度。这样的研究高度和“有用于世”的研究理念,对众多初窥历史地理学门径的青年学者起到激励作用,促使其更加密切地关注地理学界的学术前沿领域,尤其是希冀能够通过熟识的前辈们做出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迅速掌握更易理解的研究路径。
2005年初,葛剑雄应《江汉论坛》之请,邀侯甬坚、满志敏、王振忠、张伟然、华林甫共六位学者进行了一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新趋势笔谈》。(5)葛剑雄等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新趋势笔谈》,《江汉论坛》,2005年1期。此次笔谈包括葛剑雄 :《尊重科学还是迎合需要》;侯甬坚 :《关照现实:历史环境研究的出发点》;满志敏 :《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王振忠 :《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张伟然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华林甫 :《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在“编者按”中,葛剑雄提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中规范自身、旁摄他学,在新的世纪达到新的发展境界”,并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讨论,“以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诸如学风净化、学科建设等方面有所助益”。其中,满志敏在《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从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包括河湖、海岸线、沙漠等)、历史植被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学在数字化和信息化过程中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研究数据方式和数据系统建设等方面。满文提出,新技术和方法的掌握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内容之一:“时至今日,以GIS为核心的3S(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卫星定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有关可以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应用的3S 数据和工具也很多,掌握和利用这些新技术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思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从满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前辈学者已经将GIS技术提升到新方法和理论的高度,并将掌握该项技术视为“影响到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从该组笔谈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可知,GIS技术在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情况则略显滞后。
二、近年来GIS的运用 及其职能转变
自2005年以来,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传播、使用和普及过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不乐观。(6)参阅满志敏 :《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满志敏 :《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林珊珊、郑景云、何凡能 :《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方法》,《地理学报》2008年1期;潘威 :《1861—1953年长江口南支冲淤状况重建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辑;潘威、满志敏 :《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1918—1978年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潘威 :《基于分形理论的1915—2000年渭河泾河口—潼关段河道变迁研究》,《沉积学报》2011年5期。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研究者因学科储备、治学经历、科研理念以及学识积累等主客观原因,而对该技术的理论升华尚存不足。实际上,GIS技术自引入历史地理学界以来,研究者在对GIS技术的认识上存有较大差异,其主要可以分为几种声音。
第一种声音是“GIS技术最显而易见的是展示功能”,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由于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这一功能得以较为普遍应用,而GIS技术更多的功能也得以进一步发掘,即其强大的分析功能。然而,前者在研究人员缺乏GIS技术背景的情况下可以广泛的认可和使用,而其分析功能却也因此受限。由此,引发第二种声音。
第二种声音是“GIS技术确实是个好工具,但是不太会用”。这一问题虽然随着掌握GIS技术的青年学者日益增多而有所改观,但相关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仍有待加强。2011年,由华林甫、王社教邀请冯勰、丁超、杨煜达、潘晟和侯甬坚等学者开展了《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7)华林甫、王社教等 :《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3期。此次回顾和评论包括王社教、冯勰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丁超 :《十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评论》;杨煜达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十年:总结与展望》;华林甫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潘晟 :《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研究》;侯甬坚 :《十年来学界学术组织与学术力量评价》。在上述学者的回顾和评论中,不难看出,历史地理学者对于GIS技术的认知过程呈现出接纳、运用和理论升华的发展趋势。王社教、冯勰认为,GIS技术的应用对于近10年来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GIS等新技术、新方法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总结,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精度进一步加强,开阔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丁超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引述了唐晓峰的观点,即:“在哲学思潮及GIS和空间分析技术手段的介入下,人文地理学‘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今天仍在继续’。”(8)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人文地理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0页。杨煜达从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入手,认为:“在进一步挖掘传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也将进一步开拓新的资料来源。不仅要开拓利用现代的GIS、RS数据,对过去古地图、老地图资源的发掘利用也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过去这些资料主要使用于河流地貌的复原,下一步将会发掘这些资料中包含的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的信息。”潘晟则从历史地图研究角度提出很多亟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数字化历史地图编绘理论与方法的完善,数字化历史地图与纸质历史地图的转换编绘,古今图层分色处理方法的完善,古代政区界线尤其是县级政区界线的复原技术与方法,图例与图幅的统一,图幅与比例尺的关系,以及如何超越地理复原,等等。尤其是,至今还没有一种可供参考的历史地图集编绘手册!这些有待今后的工作解决。”应该看到,上述学者都从自身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对GIS技术的运用和理论升华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所起到的方法论功能尚未出现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
实际上,即便是已经熟练掌握GIS技术的学者们,在数据处理方法和数据采集过程中仍会出现某些困惑。这就是第三种声音,即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标准化问题。如侯甬坚在《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一文中提出:“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它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9)侯甬坚 :《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史学月刊》2009年4期。标准问题如何整合,如何有良好的研究未来,实际上是如何将标准化问题统一化、同一化的问题。这也是该研究方向未来生命力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否则便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出现。这方面的危机更容易导致GIS技术的魅力随着其科学性的丧失而消退。
这三种声音,是GIS技术在当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过程中所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也导致21世纪最初十余年来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虽有新颖之处,但理论层面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也就不难理解潘威、孙涛、满志敏在《GIS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10年回顾》的开篇和结论部分所格外强调的那样,“最近10年来,历史地理学已经开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信息化、数字化之路,相信对过去10年此方向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能够促进本学科的信息化建设”。同时“GIS等一系列信息化手段为历史地理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其作为研究手段的思考则更需被强调”。(10)潘威、孙涛、满志敏 :《GIS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10年回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1期。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历史地理学领域许多大型基础课题需要借助GIS技术的支持,这也为GIS技术由“手段”向研究方法的过渡提供了动力。科研人员的年轻化,势必带来GIS应用的大发展,换言之,在历史地理学界,掌握GIS技术的从业人员越多,所谓的三种声音也会随之而有所消减。同时,继之而起的,是相关科研人员在具体研究上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其争鸣的核心,当回归到数据库建设的本真,即历史文献数据化的标准问题大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GIS技术的引入和应用过程,是GIS技术由单纯的研究手段向研究方法过渡的过程,更是研究者对于GIS技术本身的认知过程。其关键在于,研究者用GIS技术来做什么。这就需要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科研背景、科研理路和科研志趣而定。
三、历史文献数据化中的 人类因素考量
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从加强地理学学科属性认知、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有关历史文献里人类因素的考量与界定、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的编码方案标准,以及GIS技术的普及化问题(学生来源、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相关单位)等方面加以关注。其中,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历史文献的人类因素考量应该是目前学界至为关键的环节之一。
历史文献中的人类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其一,历史文献的原始文本内容;其二,历史文献记录者在文献选取和记录过程中的撰述意图;其三,具备现代学术素养的研究者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取舍。这三个层面是解读历史文献时,史学工作者应当/必须具备的史学素养。这也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掌握GIS技术的研究者在数据采集、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加以关注的地方。
以清至民国时期蒙陕交界地带移民社会农牧活动与沙化土地扩展过程为例,这一研究区域地处毛乌素沙地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位于中国北方农牧过渡带的中段,是半干旱气候带向干旱气候带过渡的边缘地区,同时也是历史时期沙漠变化较明显的地区。区域内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理想区域。(11)在半干旱地带,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土地,由于其所处的自然条件较干旱荒漠及极端干旱荒漠地带稍微优越,具有脆弱生态容易破坏,也较易于自我逆转的双重特性。同时,历史时期内的人为活动也非常频繁,所以沙漠化过程较为复杂,而且都以原非沙漠景观的草原地区出现风沙活动与沙丘起伏为显著的标志。参见朱震达等著 :《中国的沙漠化及其治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由于这一生物气候带的特点是生物有机体与它周围无生命环境处于较脆弱的相对平衡状态,气候干燥、多风,地表组成物质多为疏松沙质沉积物,自然因素本身即潜伏着引起沙漠化发生的物质条件。因此,任何人为的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往往会引起环境的改变。此外,该研究区域在历史上长期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的对峙之地。从匈奴到鞑靼,游牧民族不断地侵扰南方农耕区,而历代汉族王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这样一来,毛乌素沙地南缘农耕地的开发遂成为历史时期对我国总体环境具有较大影响的大规模的土地利用事件之一。(12)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土地利用潮对我国总体环境影响最大。一是北部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农耕地的开发;二是宋代以后,南方大兴围湖造田,修造梯田;三是明清时期随着人口骤增,耐旱作物传入,无地农民转向西部开发山区,以及清代雍正年间云贵高原的移民、矿冶业的开发和改土归流,长江上游地区的耕作方式发生改变,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水土流失。参见邹逸麟 :《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18页。其中,自清初已降,蒙古族游牧民在清政府的控制下“分旗划界”,逐步开始驻牧生产,迁往该地的汉族移民也日益增多,从而引发该区域移民垦殖的存在、发展乃至壮大。对于民间来说,无论是商人、汉族移民,还是蒙古牧民,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来自经济因素的驱动力。在经济因素的促使下,来自民间的力量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或通商蒙古,或佃租蒙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于政府而言,除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之外,该地区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始终是政府当局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正是通过对上述不同阶层的分析,我们可以借助对毛乌素沙地南缘人(人群)的社会经济行为研究,得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研究过程中需要关注和着力的考察环节。
1.地理环境复原。毛乌素沙地南缘从战国秦汉开始,直至明代(元代九十年不计)的一千多年里,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长期对峙之地,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等干旱不适合农耕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成为历代汉族王朝的定制。而清王朝在确立对中原的统治之初,鉴于晋陕蒙一带抗清力量此起彼伏,时而威胁北部边塞,遂沿陕北长城北侧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划定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延伸两千多里的禁留地,“蒙旗、汉人皆不能占据”。(13)民国《河套图志》卷五《水陆交通》之《鄂尔多斯七旗地》。在此期间,虽有一些无地、少地农民违反禁令,进入毛乌素沙地南缘进行私垦,但数量有限。加之此时期的地方政府多是遵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实行封禁政策,因此,这一地区“多年不耕,穑草腐朽,地面色黑”,(14)民国《府谷县志》卷一《地理志》之《黑界考略》。生态环境得以逐步恢复。
2.土地权属。土地权属问题的变更是蒙边垦殖出现、深化的契机,亦是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变化的深层原因。清至民国时期,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土地权属经过几次变更,逐步从“汉租蒙地,蒙得汉租”向“汉得蒙地,蒙失汉租”过渡。当土地权属明确时,无论是招租的蒙古贵族,还是承租耕垦的汉族移民,都不会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开发。相反,农牧民会利用各自的生产方式来提高地力,农民会注意施肥、深耕秋翻,在耕种前进行耙耱保墒等一系列的生产举措,牧民则会注意牧场的承载能力。而在土地权属尚未明确或发生变更时,尤其是在土地的转接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剧烈的权属突变,其途径主要包括蒙古牧民驱赶汉族农民、汉族农民焚烧牧场、汉族农民的掠夺式经营(如沙漠田)等。虽然这个这程相对短暂,但能够带来急转直下的环境突变,这种突变并不包括因汉族移民的农业垦殖方式影响下的土地缓慢退化或沙化,它更直接表现为一种人为故意的环境破坏。由于土地权属的变更发生了彻底的、根本性的转变,如光绪末年贻谷放垦时期,许多以前的土地拥有者有可能在这次变更中对即将失去的土地进行破坏,这种破坏实际上掺杂了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情感,因此对环境的破坏力度远远超过蒙汉双方生产者对土地的牧放或耕垦。(15)王晗 :《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伙盘地土地权属问题研究》,《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27-37页。
3.移民社会发展程度。蒙边垦殖的过程实质上是晋陕移民社会构建的过程。晋陕边民由原来的雁行式流动人口向定居型人口转化,移民规模逐步扩大、移民村庄化进程随之加快,这在客观上促使移民垦殖的范围从清初的“边墙以北,牌界以南”(16)道光《神木县志》卷三《建置上·附牌界》。逐渐向北推移,以致发展到民国初年“伙盘界石日扩日远,计府、神、榆、横、定、靖六县边外伙盘地界,东至府谷礼字地,与山西河曲县义字地接壤,西至定边县五虎洞,与甘肃盐池县边外接壤,北至准噶尔、郡王、扎萨克、五胜、鄂套等旗牧地暨东胜县粮地,南至榆、横等县边墙,东西广一千三百余里,南北袤五十里或百余里、二百余里不等”。(17)民国《河套图志》卷四《屯垦第四》。晋陕移民向草原腹地不断延伸,伙盘界石的不断北扩,农牧界线逐渐北移、错位。至民国初年已有1806处移民村庄,可与陕北沿边六县边内村庄数等量齐观。(18)王晗 :《“界”的动与静:清至民国时期蒙陕边界的形成过程研究》,《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9-163页。此外,汉族移民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状态随着边外定居生活的开始、稳定而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心理现象,它不像自然环境那样存在着地带性规律或非地带性规律,它在改变原有土著居民的同时,也在因人因地而变,而且这种变化带来了区域社会的变迁。
4.农牧民生产环节。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农牧交错带环境演变的关系研究逐步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在干旱多风和疏松地表的自然背景下,历史时期人类的强度土地利用—环境发生退化—沙漠化过程的发展和加剧—可资利用的土地减少、生产力下降—进一步强度土地利用。这一研究模式实际上压缩了农牧民的生产环节,片面夸大农牧民在生产过程中对土地的破坏程度和力度,忽视了当地民众出于经济收益的需要而对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诉求,以及保护牧场以有利于牧业生产的想法。因此,通过分析,不能简单地将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环境变化问题和农牧民的生产直接挂钩,而是应该更加细致地着眼于生产环节的细部。
5.制度、政策因素。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政府当局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这是清政府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一个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令往往混淆不明,行政能力也相对低下,从而使得地方官员在这种本来就很难定量、定性的地区,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虚报或是瞒报的手段来藏匿真实的土地数字。而汉族移民则充分利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过程中的漏洞从事农牧业生产。因此,深入到这些民众的农牧生产行为背后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中,细致考察当地社会内部各种政策的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形成可作用于人的利益驱动规定及其调节手段,也就可以完整而准确地揭示移民社会农牧活动如何作用于沙化环境。
6.蒙汉关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蒙汉双方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也存有极大差异,这有可能促成民族间的隔阂,而这种差异又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存有密切关系。
7.商贸活动与农牧业生产的选择。毛乌素沙地南缘拥有为数不少的交通线,塘路、草路的形成,当地市场与商品的流通,有力地促成较为发达的商贸区域带的形成。商贸活动的日益繁盛,也促使许多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汉族移民,开始注意保护牧场用以放牧,尽量将种植农作物经营在原耕地上,很少随便开垦牧场种粮,从而得出“以牧促农、以农养畜”的生产经验。
8.环境效应分析。由于气候等诸因素的变化,自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农牧过渡带有过一定的变化。大约康熙末期至乾隆中叶的18世纪,我国北方气候有一段转暖时期,因此农牧过渡带的北界有可能到达了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19)邹逸麟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期,第25-33页。恰于此时,晋陕沿边民众越出边墙,进入毛乌素沙地南缘从事农牧活动,从而出现“春出冬归(先议秋归,后议冬归),暂时伙聚盘居”形式的伙盘地。(20)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卷四《边外》。伙盘地随后的发展、变化、壮大也在随着气候等自然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动。同时,随着当地民众农牧活动强度的加大、农耕面积的不断扩展,至清代中后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主、放牧为次的局面,土地承载量下降现象日益突出,遂成为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地区。
上述八项考察环节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在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变化与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变化问题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的大背景下,突破传统的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演变的研究模式,构建生境地带地理过程综合研究的平台,以寻求宜于优化和改善当地生态的有效途径。那么,在探究过程中,人类因素(社会经济行为)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时的标准问题该如何把握?或换言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南缘人(人群)的社会属性在事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四、结 论
21世纪以来,学科交叉的时代需求令多数历史地理学及其相近学科的研究者在加强跨学科学习的同时,在所从事工作的研究时段、研究范畴、研究区域上日趋呈现精益求精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引发相关研究者拥有了虽无区域研究之名但行区域研究之实的研究特色的同时,也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方面迅速展开。这样的做法使得历史地理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样的研究具有高度的普适作用,却也带来至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为研究区域的碎片化,即文献材料可以支撑的研究区域逐渐缩小,由一个县逐渐延伸到一个社区、一块土地,其研究的精度逐步加强,但研究的适用度却在日益减弱;其二为研究中的人的“自然化”倾向依旧明显,对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人群)的研究有待加强,即尚需对人(人群)个体性质进行深度关怀。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也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为一部分研究者从辩证法的角度,希望在完成小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小区域和大区域之间的关系,更希冀小区域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大区域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特点,(21)许多有所成就的历史地理学专家已经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开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世纪良方”。但在笔者看来,其更为严重的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青年学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怀着崇敬的心理去模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这势必导致青年学人在自身的研究中将前辈学者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更好地发挥。其结果是青年学人在完成大量的个案分析后,会在试图构建小区域和大区域的内在关联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有的青年学人通过苦思冥想揭开其中的奥秘,有的青年学人生硬地照搬前人的思考模式,呈现在自身研究上则犹如郑人买履。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对“碎片化”进行反思,思考问题的根结在于小区域应该小到什么尺度,才不会丧失它在整体区域研究中的代表性;(22)周尚意 :《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小区域研究的意义》,《世界地理研究》2007年4期,第41-46页。其二为研究者容易在研究中出现对人(人群)的自然属性扩大化和对社会属性深度关怀的遗漏、缺失,机械化地固定社会人群在地理环境中的行为意义,也使得社会人群在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应对和调适中显得更加的机械化而丧失了自身的灵活和情趣。(23)这一问题虽然在早期研究者的论著中多有强调,但真正意义上的改进是在一批世界史研究背景的学者推介西方环境史学的过程中逐步清晰化的。正在诸如此类的研究方兴未艾之时,由世界史学者广泛推介的西方环境史学开始风靡国内学术界,其中,学界对于西方环境史学中人本思想的大力推介促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导致更多的历史地理学者重新反思人地关系中人的要素如何具像化、个性化,并开始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人(人群)本来就有的社会属性。
GIS技术的应用和理论化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注重历史文献中的片段数据、海量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清洗与分析,通过碎片化重组,能够令研究者们在完成小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小区域的研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区域的整体发展趋势和特点,继而深度揭示难以处理或无法预知的科学问题。(24)孙建军 :《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光明日报》2014年7月7日,第11版。而对于研究中人(人群)的社会属性标准化问题,则应该在了解和掌握研究区域内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在不断演进中的关系表达的基础上,对于生存在地理环境中的人(人群)的行为,尤其是对于环境认知和环境调适的过程进行相关研究,以图捕捉到具有人性化的人(人群)在地理环境中所做出的关键性行为表达,以及在不断调试自身和周边地理环境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智慧,以此作为拓展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及研究范畴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