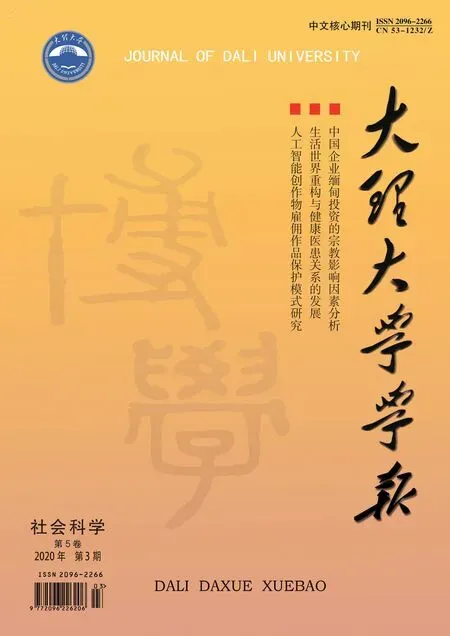译者行为视域下的美国华裔文学文化翻译研究
2020-12-13张林熹
张林熹
(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65)
一、研究背景
美国华裔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创作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这里,美国华裔文学主要指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作家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中国经验的文学作品。由于作品含有大量中国元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涉及汉英翻译行为。这种翻译并不指简单的语言层面转换,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经验的跨时空转述与挪用,是一种隐性的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的概念最早由后殖民理论三巨头之一的霍米·巴巴提出。他认为,“文化翻译”并非指涉两种语言、文化的具体文本之间的翻译,而是融翻译于写作的一种独特的后殖民文学现象。可以说,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理解、翻译中国文化的过程。他们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无疑使其担当起文化译者的职责。美国华裔用主流话语英语进行创作,并成功地将中国文化习俗转化成西方人既能读懂又能接受的文学形式,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这些作品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特色,凝聚了作者同时也是译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双重身份赋予的独特视角使这一逐渐壮大的群体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使者的角色。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准确洞悉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翻译行为模式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从美国华裔作家群体的译者身份出发,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语境下该群体译者行为的共性与个性及其对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译者行为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基于实践的行动理论,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则囊括了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整个翻译过程。译者行为是翻译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本文所指的译者行为是广义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即译内+译外行为。译内行为是译者的语言性行为,处于翻译的基本层;译外行为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处于翻译的高级层。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翻译的普遍性反映了译者对特定社会环境、特殊双重身份以及现行翻译规范作出的共性应对。换言之,文化翻译的普遍存在体现了该群体的共性行为。然而,不同译者受文化翻译的影响程度以及对文化翻译的不同处理态度则反映了译者行为的个性。因此,本文讨论的译者行为从翻译的社会学视阈出发,是对译者译内与译外行为、共性与个性行为的综合评价。
美国华裔作者群体的译者行为共性与个性可以用布迪厄的经典公式来解释,即:[(惯习)(资本)]+场域=实践。惯习、资本和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的三个核心概念。投射到翻译研究中即可解释为译者依靠惯习和资本在翻译场域中作斗争,进而形成译者行为实践。
布迪厄把人类的社会实践场所抽象为“场域(Field)”这一空间概念,认为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1〕。译者作为翻译场域的重要参与者,其行为广泛存在于翻译场域之中。翻译场域的运作法则是译者群体价值观与思想观的集中反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译者行为。译者若想在翻译场域中获得奖赏或赢得地位,则会使其行为在不同程度上遵循其所处翻译场域的规范。因此,翻译场域主要反映了译者共性行为背后的原因。美国华裔作家所处的翻译场域即是远离故土的西方社会,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社会呈现的是变化中的翻译场域。
译者惯习是一个涉及翻译内和翻译外一系列行为的认知系统,它可能持续很久,甚至成为译者的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2〕,但也可能由于场域的演变不断发生变化。它的最终表现形式则是译者从翻译思想(素养),到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等一系列译内和译外行为。译者惯习反映了其社会轨迹,包括其社会阶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因此,来自相同社会阶层,具有相似社会经历或职业背景的译者往往具有相似的惯习。译者的惯习不仅是个体秉性也是社会轨迹的表征,反映了华裔作家群体个性、主观的一面。
个体之所以在场域中有高低之分,究其根本,是因为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有多寡之别。在翻译场域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译者的资本主要包括优秀的双语功底、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作品相关的成长环境、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及写作经验。对于美国华裔作家群体来说,双重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们文化翻译的能力,是他们最与众不同的翻译资本。
在惯习、资本和场域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产生译者行为,构建译者实践。译者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需要我们将翻译内和翻译外研究相结合。美国华裔作家具有特殊的双重文化背景,其翻译行为背后蕴含着民族文化层面的博弈,更需要我们从不同视角,多维度进行考察。
三、译者行为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无论是从初期的边缘化阶段,到20世纪60年代的起步阶段,到今天开始在美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都与美国华裔作者群体的译者行为有着紧密联系。接下来,本文将从译内和译外两个层面分析翻译场域流变中美国华裔作者译者行为的共性与个性。
(一)译外行为
译外行为关涉超出翻译活动本身的因素,对于美国华裔作者来说则包括创作、翻译的文本选择、主题选择、接受环境、翻译目的、个人风格等。虽然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得以进入美国文学界及国际学术界的视野。近代史上的中国满目疮痍,使华人移民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地位卑微的失语状态。他们为美国的发展贡献了血与汗,却处处遭遇冷眼与嘲讽。特别是20世纪初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法案,使华人移民的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在歧视与排挤的逆境中,他们团结在一起并逐渐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地——唐人街。但同时他们也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早期美国华裔文学鲜有作品出版,且创作主题以抗议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为主,但长期被美国主流文学排除在外,处于失语状态。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同盟,美国华裔文学开始逐渐融入主流文学,主题也反映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创作普遍流露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向往。如刘裔昌的《父与子》(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的《华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1950)等。作品中对中国异域风情的描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刻板印象,满足了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凸显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
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华裔文学“无声”的抗议则变成了对美国文化霸权、东方主义、刻板形象的公开质疑与颠覆。第一代移民的子女不甘被永远当作文化“他者”,他们开始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1974年赵健秀等人编写的《啊咦!——美国亚裔作家选读》(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4)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的成熟与发展。赵健秀明确指出,他的创作主旨即“写作即是斗争”。“啊……咦!”是亚裔族群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发出的哭诉和呐喊。这一时期的华裔创作大多采用“小历史”叙事、“反英雄”形象等反西方传统小说的异化策略来解构西方主流话语,颠覆西方话语霸权。如美国华裔作家朱路易的小说《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和徐忠雄的《家园》(Homebase,1979)。两位华裔作家都通过描写某一个体或华裔家庭生活变化来展现整个华裔群体的真实生活境况。这种不同于西方主流话语书写的“小历史”从小叙事揭示出华裔群体被边缘化的血泪史。
民权运动背景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则强调对种族主义与封建父权制的双重抵抗。一方面,她们要冲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枷锁,打破西方种族优越论对东方封建、落后等刻板形象的期待;另一方面,华裔女性作家又必须挣脱中国封建男权文化和美国大男子主义的枷锁,颠覆传统温柔、顺从、娇弱的东方女性形象。鉴于这一双重目的,以汤婷婷、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创作主题不仅指向中国封建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也指向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及性别歧视。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7)通过塑造母亲们的高大形象,刻画女儿们的正面形象以及中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书写美国主流社会的负面形象等途径解构美国俯瞰中国的东方主义视角。《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则以一个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孩视角,展现了新一代华裔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夹缝中艰难成长的过程。小说中,汤婷婷借用并改写了许多中国神话、文学经典和民间传说,这一改写过程则是文化翻译的典型体现。她认为“作为美籍华人,写作是一种新的权利资源,一种扮演社会勇士的新方法。权利源于了解你自己(民族)的历史;权利源于接受古老的故事和歌曲”〔3〕。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通过解构西方主流话语,重构东方女性形象让世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8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倾向。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不再单纯局限于母国或居住国,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虽然各民族间的文化壁垒逐渐消融,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的“凝视”仍在继续。90年代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大量的“中国叙事”正是随着美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应运而生。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交通便利与信息互通使新一代的“中国叙事”更加真实。它们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而非祖辈口口相传的故事与传说。这时,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的翻译资本变得更为丰富,除了优秀的双语功底及与创作相关的成长环境,他们对故国文化有了更深切的体验与了解。与此同时,仍有许多美国华裔作家坚持反击西方霸权话语,为自身族裔群体作斗争。而许多新生代美国华裔作家如任碧莲(Gish Jen)、李健孙(Gus Lee)、伍慧明(Fae Myenne Ng)等则不再将创作局限于华裔群体,他们关注的视角更加广泛,代表了一种由族裔性向普适性的转变。而华裔文学前辈们的新作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汤婷婷的《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2004)和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正如汤婷婷所言:“美国华裔作家这样的名称概念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也许过于狭窄,因为每个作家都想成为全球化的作家。”〔4〕因此,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主题是多元化的,既包含了为华裔族群权益的持续斗争,符合西方期待的“中国叙事”,又反映了对超越族裔身份羁绊的美好愿望以及对人类普适性价值的关注与追求。
综上所述,美国华裔作家群体存在大量共性的译者行为,但随着翻译场域的不断变化、译者资本的不断丰富以及译者生活经验的差异,译者行为的个性化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二)译内行为
译内行为主要包括具体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字的转换和意义再现等因素。由于美国华裔文学文化翻译的特殊性,其群体的译内行为不涉及单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以及中国元素的运用相关。下文将从译内行为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翻译现象。
《喜福会》是华裔美国女性作家代表作之一,其中有大量关于中国食物、中国成语的文化翻译,如:
例[1]To this day,I believe my mother has the mysterious ability to see things before they happen.Shehasa Chinesesayingfor what sheknows.Chunwang chihan:If the lips are gone,the teeth will be cold.〔5〕93
例[2]“What use for?”asks my mother,jiggling the table with her hand.“You put something else on top,everything fall down.Chunwang chihan.”〔5〕103
Chunwang chihan(唇亡齿寒)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而这两次都是直接以音译的方法呈现。例[1]中,作者在音译后辅以成语的直译,这种异化处理方式能让西方读者产生恰到好处的疏离感,让他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国成语产生兴趣。虽然总体来说,《喜福会》中运用的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但偶尔出现的中国元素却能适当扰乱读者绝对流畅的阅读体验,让中国文化慢慢走进西方主流话语,为争夺华裔族群的话语权打开了缺口。例[2]中,母亲以放不稳的茶几比喻女儿的婚姻,“唇亡齿寒”原指两者息息相关,在这里看似用词不当,却传达了女儿婚姻不稳定的寓意。
中国饮食文化颇具特色,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喜福会》中就出现了许多中国特色食物如syaumei(烧麦),chaswei(叉烧),chow mein(炒面)等。同样的音译法不但可以保留汉语本身的特色,还是一种身份标识,可以让读者直接感知中国文化的在场,是文化输出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
美国华裔作家还善于挪用中国历史人物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一点在汤婷婷与赵健秀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中国历史人物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使他们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因而在文化翻译中往往出现“误译”。他们不约而同地杂糅、改写了似曾相识的历史故事,重塑、再现了历史人物。如此,他们书写的中国文化虽异于真实但也成功颠覆了中国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刻板印象。在《女勇士》中,汤婷婷将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与中国历史人物岳飞合二为一,塑造了花木兰(Fa Mu Lan)这样一个女性英雄人物。这样杂合的人物形象一改西方人眼中娇柔、懦弱的中国女性刻板印象,迫使西方读者重新审视这一异域文化,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赵健秀在《甘加丁之路》中则借用了关羽、刘备、张飞三位三国人物。其中他对关羽的描述如下:
例[3]Kuan Yu is the most popular character in Three Kingdoms,…Popular culture quickly made the popular character,…the god of war,plunder,and Literature…〔6〕
这段描述中,关羽摇身一变成为三国中最受欢迎的角色,是战争、文学之神,这显然与历史相悖。其实,历史人物文化翻译的背后是作者的文化诉求,通过塑造关羽这般集英勇与魅力于一身的男性形象瓦解西方主流社会视角下传统中国男性的负面形象。
新锐美国华裔作家更关注对历史与现实创伤的超越。如伍慧明在小说《骨》(Bone,2011)中,通过描述主人公莱拉的生活境遇揭示了美国华人的现实困境与历史创伤。她的小说《望岩》(Steer Toward Rock,2012)也反映了相似的主题。同时,《望岩》也是一部中国气息浓郁的小说,包含了许多中国元素,如“双龙牌香烟(Double Dragong cigarette)”“人参口香糖(gingsen gum)”等。小说共分为五个部分,有意思的是,每一部分的标题都是英汉对照:“Report(报告)”“Respond(报答)”“Requite(报应)”“Release(报晓)”“Return(回报)”,直接保留了汉字形态。此外,作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还采用了更加杂合的方式。如:
例[4]Zhen Que!He said.
Truly Que.I was truly surprised.Zhen used the expression Ihad only heard my father use…〔7〕
很明显,“正确”一词的拼音并不准确。而“我”在翻译这个词时更是将英语与汉语相结合,通过语言杂合解构权威的权力话语,打破单一的文化交流模式,彰显华裔族群的文化间性(in-betweenness),为构建美国华裔群体的民族身份起到推动作用。
综上,任何文学创作都是对一定时期社会语境的反映。因此,美国华裔作者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华裔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政治文化诉求。文化翻译在他们的书写中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环节,集中体现了美国华裔作者面对强势西方主流话语的不同应对策略与态度。通过对该群体译者行为共性与个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断演变,不断发现自我、超越自我,寻求自我身份,重构自我身份的过程。美国华裔群体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属性赋予了我们更加宽广的研究视角,对当下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