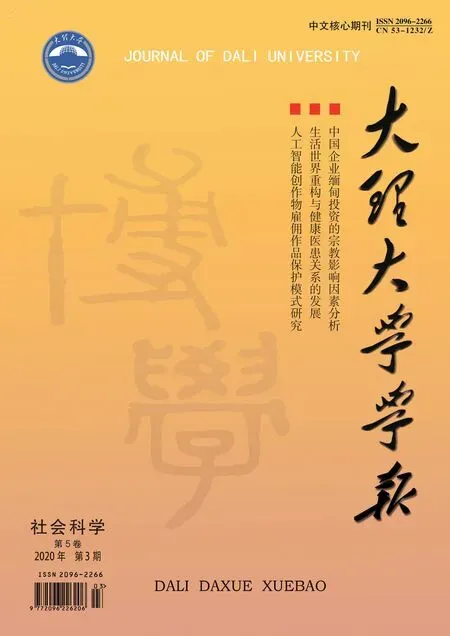彝族俐侎人家庭社会性别关系异化及其重构策略
2020-12-13石林红郑妍鲁云
石林红,郑妍,鲁云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云南临沧677099)
毛泽东的《矛盾论》开篇之句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本研究在彝族俐侎人聚居的5个乡镇中选择15个自然村为调查对象,走访75户家庭,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彝族俐侎人家庭的社会性别关系,发现彝族俐侎人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研究和承认差异并不等于漠视平等,重构彝族俐侎人家庭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有效促进性别公平的尝试之举。
一、彝族俐侎人传统的家庭社会性别关系
(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男女两性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女性主要完成生育和抚养幼童的工作,而男性主要完成重体力活,这种劳动分工基于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本不应有亲疏之分,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看似简单的劳动分工已然为两性的角色发展和角色地位做足铺垫。男孩和女孩从小就朝着社会的既定期待发展,以便最终能成为社会所认可的男人和女人,久而久之,劳动分工上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并以约定俗成的传统代代相传。
通过调查可知,彝族俐侎人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与经济获得能力无关,却与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关。彝族俐侎人生活所在地的经济模式以小农经济为主,俐侎男子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劳作的工作,以重体力活为主,例如种植水稻、打猎、砍柴等,所获取资源主要满足家庭生存需求,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俐侎女子主要从事轻体力工作,如家务整理、饭食准备、儿童照抚、纺线织布等,其中纺出的线和织出的布是集市上的主要交易物品,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能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而比男性高,相反,男性因为“主外”而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在家庭中是更具话语权的一方。在现代化信息社会,多元文化与原有的俐侎文化交融,由于“男主外”的分工模式,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年人走出山寨,进入第三产业务工,务工比务农有更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男性家长的家庭地位更加不可撼动。
“社会分工的一个核心就是把自然分工形成的两性角色用文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根本目的是既保障人类的代际更替,同时又改善生存的质量”〔1〕。彝族俐侎人现代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长期存在,固有观念中男子总被认为是要走出家庭,继而成为家庭主要经济和精神支柱的人,而女子总被认为将来是要照顾家庭的人,因此在劳动分工上女孩往往比男孩承担更多和更为琐碎的家务劳动。
(二)“父子相继”的继承制度
继承制度是父权制度的核心之一,是家庭财富和权利交接的主要方式。女子对于她的原生家庭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一旦出嫁,便会与娘家的关系逐渐疏远,一切起居习惯遵从夫家,包括在意识层面也一切以夫家为重,最终归属于丈夫的家族中。俐侎人实行家族外婚,同一父系家族内不得通婚,但同姓而不同支的青年男女可以通婚。在父权的控制之下,新婚夫妇的后代也必须从夫姓,彝族俐侎人以血缘为纽带,同姓同支则被归为一个家族,例如同样是张姓,就有“百花张”与“河上张”之说,“百花张”指的是崇拜百花树的人,而“河上张”指的是住在河边的人,他们虽然同姓,却属于两个家支,因此在权利和财富的继承上不具有交集。
家族内,祖业是由男子继承的,若是一个俐侎人家只有一个男孩,那么父业理所当然地由儿子来继承;若是家中有子,且有多子,祖业则是平分,平分的过程中老人也有一份,日后哪个儿子赡养老人,老人的财产则给这个儿子;若是家中只有女儿的人家,女儿就不外嫁而是改成上门招婿,按照当地习俗,上门后的女婿相当于给女方家长做了儿子,将来有了后代的话孩子和母亲同姓,这样的话,祖业由女儿和女婿继承;若是家中没有子女的人家,他们会在家族内收养一个孩子作为自己的子嗣,日后财产由他继承。
(三)“阴阳相济”的宗教意识
胡塞尔认为:“人不仅生活,而且得为生活寻求力量。在人自己的力量与另一力量遭遇之处,宗教遂生。”〔2〕人类社会有了宗教,就会有宗教传承,有了宗教传承便会有宗教教育。俐侎人属彝族的一支,继承了彝族先民对万物的认知。彝学典籍中记载,彝族先民把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分公母、雌雄或阴阳。《宇宙人文论·八方》曰:“哎为父,主南方;哺为母,主北方;且为子,主东方;舍为女,主西方。”天地分阴阳,时间分阴阳,男女两性也分阴阳。天为阳、地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为阴,万事万物有阴必有阳,阴阳相济才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原始的阴阳观是彝族俐侎人宗教教育过程中遵循的内在主线。
彝族俐侎人宗教教育中体现出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敬奉,一种是趋避。他们认为生活中存在超自然的力量,例如山神、龙王、灶王等,同时也认为祖先的精神和意志一直与家支同在,这些超自然的力量能满足自己或是家庭的愿望,因此对神灵和祖先应当敬奉。在神灵的对立面则是鬼魅,鬼魅的存在会给人带来疾病和灾祸,因此当厄运降临时应驱赶鬼魅。需要敬奉的神灵和祖先灵魂是阳,是能给人们带来吉祥的力量,需要增强,而需要趋避的鬼灵则是阴,需要减弱。用彝族俐侎人原始的阴阳观解释:男为阳,男性刚好是能增强正能量和压制邪恶力量的人。女为阴,加之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生理期的女性被认为是不洁的,会冲撞神灵,因而彝族俐侎人的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诸多对女性参与的限制,如女子不得进入宗教圣地色林,生理期的妇女是不能参与耕地活动的,也不能跨越家庭农作的工具,不然神灵便会怪罪使粮食不得丰收等。
(四)“各司其职”的家庭角色定位
彝族俐侎人在生育观念上讲究“儿女双全”,一个家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才是完满的。在俐侎人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家庭功能,因此家庭教育中对男孩和女孩的角色教育也各有不同,为的是将来他们能顺利“各司其职”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彝族俐侎人的社会制度以父为大,因此,男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既是一个家庭物质财富的继承人,也是家族精神延续的传承人。在调查访问中发现,必须生育男孩的观念已经植根于每个俐侎人的意识中,因此便有了传统的“求子习俗”和男女有别的“养育习俗”。“求子习俗”中人们总是将希望寄托于能满足他们愿望的神灵身上,只有平时循规蹈矩、虔诚而忠实才能得到神灵的青睐,若是真能如愿得子便会以仪式感谢神灵恩赐,若是不能如愿,便会以虔信的心态反思自身。屡次生育不得子的人家便会采取其他方式得子,例如过继,从亲戚或同支族人中选取一个男孩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以便将来有人行孝和继承家业。
当然,彝族俐侎人家庭中只有男孩也是不完整的,顺利得子的家庭也会祈求神灵至少赐予一个女孩。彝族俐侎人注重仪式,如办理老人丧事时必须有儿女行孝,家人的孝服必须由所逝之人的女儿亲手缝制,而且需要女儿跪哭于灵堂前,这样的话去世的人才算得了体面。因此,没有女孩的家庭,也会采用过继的方式得女。
彝族俐侎人在家庭中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遵循他们各自将来的社会职责,男孩主要接受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劳动教育,女孩主要接受家务训练。
二、文化传承中彝族俐侎人家庭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异化
据调查分析可知:彝族俐侎人目前仍然遵守着传统的父权制度,经济模式上虽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也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小农经济。彝族俐侎人先民在确定家庭各项习俗之初,本意应在于用习俗的力量维系家庭关系和谐,而不在于区分出男女两性的优劣,但文化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因此彝族俐侎人家庭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异化。
(一)“男外女内”异化为“男主女从”
人类的劳动分工有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两种类型,按照人的生理性别、年龄进行的分工叫做自然分工,以劳动特点为基础进行的分工叫做社会分工。俐侎人女性在生理性别上相较于男性而言气力更弱,但具备孕育新生命的能力,因此适于从事轻体力劳动及生育和抚育未成年子女,但看似简单的劳动分工却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两性角色的发展。
彝族俐侎人集中生活在云南半山区和山区,生产生活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劳动形式主要为山地耕作、畜牧和狩猎,因此,肢体力量更强大的男性更具备生存的优势。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彝族俐侎人的社会分工被定格下来:男性主要从事农耕、砍柴、狩猎等重体力活以及负责家庭与社会的对外沟通;女性主要从事生育、养育后代、纺织、操持家务等劳动。“社会分工的一个核心就是把自然分工形成的两性角色用文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根本目的是既保障人类的代际更替,同时又改善生存的质量”〔3〕。
人类男女两性的生理特点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使彝族俐侎人形成了强弱搭配、内外分工的社会分工模式,这本应该是两性和谐发展的标志,但事实上,女性在社会中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因为身体的力量优势,长期接触并控制着家庭必须的经济性生产资源,而女性的生理特征也使得男性这样的控制得以维持,正因如此,男性成为家庭生活中更具有控制力的一方,而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其演化为社会地位弱势的一方。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彝族俐侎人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以改善,女性的家庭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是“夫唱妇随”的观念依旧对家庭社会性别关系有强大的影响力,男性在家庭中主要负责对家庭重大事情做出决策,女性则对男主人的决定无条件支持,这种思维定势使女性在很多场合及机会面前,自愿出让应有的权利,进而使“男主女从”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阴阳相济”异化为“男尊女卑”
“彝族原始阴阳观念最初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尤其是对自身两性天然区别的观察以及对两性功能的实践、体验、推演、概括的结果”〔4〕。也就是说彝族原始的阴阳观是基于男女两性天然区别的思考,以及结合自然界观察的结果,是生活经验的总结,这种经验基本符合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传承的过程中后人不断丰富其内涵,也不断修改其中的细节。彝族人认为万事均分公母、雌雄和阴阳,而阴阳的形式可以被形容成兄妹、恋人或者是夫妻,这在彝族俐侎人的民间故事与传说中能找到佐证,例如彝族俐侎人的创世神话《兄妹成婚》、民间故事《太阳和月亮》(把太阳比作小伙子,月亮比作小姑娘)等,阴阳调和是万物之源,这也是彝族最原始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于每一项社会制度的定立,不可能满足族群中每一个人的需要,宗教在与人的生活结合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更新、调整,当然也可能会走向异化。彝族俐侎人的阴阳观念起源于对两性差异的观察和认识,反过来,从性别的角度审视他们的阴阳观就会发现:男为阳,女为阴,阳代表具有正能量的一方,而阴代表具有负能量的一方,因此彝族俐侎人在宗教活动中对女性有诸多限制,甚至对女性本身带有歧视的眼光,认为生理期的女性是不洁的,是会冲撞神灵从而带来灾难的。为了避免阴盛阳衰,为了使彝族俐侎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保持正能量,因此需要对女性的行为采取禁令。
“阴阳相济”异化后的方向清晰地指向“男尊女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彝族俐侎人生活条件艰苦,文化发展落后,在遇到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情时只能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人们应对风险的无力状态。在生产力落后的自然社会,身体柔弱的女性比起男性来说更容易遇到风险,这些风险有的会影响当事人本身,有的会因个人而影响到集体,当人们无力应对风险时便对女性采用一系列的禁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教中对女性的种种限制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要区分出男女的尊卑之别,只是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异化成了“男尊女卑”。
(三)“各司其职”及“父子相继”异化为“男权至上”
彝族俐侎人家庭生活中,女性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要比男性更早学会克制与忍耐,要尽快接受并适应社区及家庭中对女性的各种禁令,可以说女性的整个成长过程是不具备中心话语权的,她们成长的目的就是尽快使自己成为未来家庭的辅助者。在这样家庭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具备很多共性,如性格中都含有害羞、谨慎、谦卑的特点。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父母对两性的社会认知直接作用于子女,是子女社会性别建构的主要影响力,与此同时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教育的方式反映的是社会对培养人的需求,因此女性的成长不仅仅受到家长传统观念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劳动结构、社会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彝族俐侎人生活在云南高寒山区,平均海拔2 500米,由于海拔高、气温低、地势限制、土壤贫瘠等多重原因,彝族俐侎人农作物产量不高,生产劳动的结构也相对简单,主要以旱地、山地耕作为主。农作物主要发展经济性林木,如核桃、茶叶,部分村寨也尝试种植苦荞、草果,但是由于产量低,近些年来种植苦荞和草果的人家越来越少。由此可知,彝族俐侎人农业劳作的样态单一、结构简单,日常农业管理不需要全员参与,一般掌握核桃嫁接技术、懂得茶园管理技巧的均是男性,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作用只有在丰收农忙的时候得到体现,其他时间都被局限于家务劳作之中。由此看来,彝族俐侎人中的男性处于劳动结构的上层,而女性处于劳动结构的下层,生产劳动的结构性特征是导致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彝族俐侎人尊崇的是父权制度,家庭生活中以父为大,家族精神以及家庭物质财富的继承人默认为家庭中的男性,这在彝族俐侎人“男留女嫁”的婚姻制度中也得以体现。可以说男性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未来,在一个家庭中男性的地位仅次于父辈,因此也拥有资源优先的权利,例如在经济困难的家庭中男孩优先享有受教育权、在多子女家庭男性优先享有继承权、在婚姻关系的维系上男性优先享有决定权,女性始终处于被安排和被迫接受的角色地位,失去很多人生的重要节点上的话语权。
三、彝族俐侎人家庭社会性别关系重构的发展策略
传统父权制和小农经济模式是影响彝族俐侎人家庭社会性别关系异化的重要因素,要改变现状重构彝族俐侎家庭社会性别关系,个人、家庭、社会都应做出努力。
(一)强化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建构
由于受到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的影响,各种禁忌不仅禁锢了女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心灵,“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传统思想仍然占主导,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沦为父权制度的执行人和守护人,俐侎女子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后代的生育者和社会生活的辅助者,这种意识成为当地女性发展的内在阻力,在倡导两性平等的今天,改善女性地位除了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应体现为观念上的扶持。在批判文化对女性发展限制的同时,更应加强女性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在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压制的同时,更应注重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
首先,女性应当接纳自己的性别,合理审视两性差异。女性首先是人,具有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类两性中的一个性别,虽然说男女两性在生理和社会角色上是有差异的,但只能证明男女两性对社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在性别上并不具有优劣之分。女性应当看到自己性别上的优势,冲破思想禁锢,树立信心,接纳自己的性别,但同时也应接纳自身不完善之处,找到自身价值,做好自己。
其次,女性应当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条件。尊重不应是别人给予的,而应是自己争取的,作为意识觉醒的一部分,女性应当积极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条件,主动进行自我教育,既认识到自己社会性别角色,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积极要求参与群体活动,又能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促进。
(二)家庭承认社会性别差异,摒弃刻板印象
承认和正视差异是转变观念的前提,彝族俐侎人教育习俗中社会性别差异客观存在,如彝族俐侎人认为生理期的女性是不洁的,从身体和心理层面给予女性多方面的暗示和限制;女性不能进入色林,不能参加村寨及家庭的祭祀活动。这些习俗本是彝族俐侎人先民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他们将自己的言行与祸福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并小心翼翼地将经验收集、总结、流传,本应是造福后人的事,但人的认识能力因人而异,因此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部分习俗已经严重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习俗和观念的结合使得人们的性别刻板印象更加难以根除,“性别观念一旦与习俗相结合,便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人们往往将这些性别规范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很少问为什么?”〔5〕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观念与习俗比物质和制度更难改变,性别观念一旦形成,便会被内化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符号,社会成员从儿童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就能了解和掌握这种符号,并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认同这种文化符号,当他长大成人后也会不自觉地用同样的观念和行为来要求和教育后代。成人在抚养和教育儿童时候必然对子女采取与心目中性别特征相适应的行为,或鼓励或禁止,从而让子女趋向和认同于社会的社会性别观,让子女更加努力地去靠近社会所认可的性别角色,例如让男孩更加勇敢坚强、女孩更加贤惠善良。
性别刻板印象不仅不利于女性发展,而且也限制了男性发展的诸多可能性,但是改变陈旧观念在实践中并不像书写文字那样轻而易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也会出现反复,需要人们给予这个过程充足的时间和耐心,也许需要数代人思想的层层过滤才能让彝族俐侎人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真正明白性别刻板印象的弊端。
(三)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
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将性别主流化纳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起,我国各级政府在着力促进两性社会性别平等上做了很多积极尝试,如从政策方面干预与调节男女两性拥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但是彝族俐侎人生活所在地属于云南边远山区,国家“男女平等”的国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的挤压,从而导致“大部分情况下,乡土社会、甚至是城市中,人们所倡导的性别平等的概念仅能在意识层面上进入主流,而在实际行动中男女不平等的行为模式却是常态”〔6〕。
国家公共政策的落实应与彝族俐侎人的风俗相结合,切实解决性别盲视问题。传统的父权制度是导致彝族俐侎家庭社会性别关系发生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习俗中代际关系以男性长者为尊,夫妻之间以夫权为大,习俗中潜在的社会性别观念对彝族俐侎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公共政策虽然为女性争取了一定发展空间,但是根本上还不能完全破除当地人的性别成见,在许多家庭决策上仍然以男性家长的意志为主,不自觉间形成性别盲视。国家推进性别公平的公共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固有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当行动起来,加强对俐侎人的社会性别意识宣传和教育,让彝族俐侎人从根本上认识到性别偏见的客观存在,再谈及转变观念。
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实重视妇女、女性的生活境遇,帮助她们认识自己和树立自信,鼓励她们走出大山,做自己的主人;重视女性的政治参与,优先考虑女性干部的晋升,赋予女性话语权;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女童的入学问题和对女性的心理辅导,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积极竞选班干部,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关注女性在学校的学业问题和安全问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
(四)着力解决彝族俐侎人家庭留守女性的就业问题
小农经济是影响彝族俐侎人家庭社会性别关系发生异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使男性始终处于劳动分工结构的上层,而女性始终被困于家庭,处于劳动结构的下层,劳动分工的低结构性是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欲变更两性劳动分工的结构性,推进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无疑是一条出路。首先,市场化能改变农民传统的种植内容,使得单一的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其次,市场化解放出的劳动力能加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进城务工的方式增加家庭收入。但是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的影响,相比于男性,留守妇女的问题更加凸显。家庭社会性别关系重构,需要让留守女性掌握劳动技能,找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树立生活信心。
彝族俐侎人对女性的定位以贤惠、勤劳、能干为主,女性从儿时起就开始接受有关于女性气质的训练,她们比起男性虽然承担更多琐碎的家务,但是任劳任怨;虽然被迫接受来自家庭和群体的各种禁令,但是谨慎隐忍,这是文化现象中的不平等,但也是女性的优势所在,她们比起男性来说更有耐心,更擅长于精细劳作。产业扶持应有的放矢,针对留守女性和留守妇女开发出适合于她们劳作和发展的产业链。据调查可知,彝族俐侎人生活的地理位置为云南高寒山区,农业产量较低,政府产业扶持可从手工业、畜牧业和旅游业着手。
首先,彝族俐侎女子善织,女性从孩提时便耳濡目染女性长辈纺织的全过程,从纺线、织布到靛染、剪裁、缝制是一个漫长而又需要富有耐心的工作,几乎每家每户的女性都具有这项劳动技能,以往手工布匹及手工缝制的衣物仅满足家庭所需,政府如果对这项传统的手工业进行产业扶持,既能进行民族文化传承又能给女性带来学习动力。其次,彝族俐侎人居住地以山地为主,适合发展畜牧业,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对彝族俐侎人留守人员进行养殖技术培训,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态肉类不失为一项脱贫举措。最后,彝族俐侎人生活居住地较为封闭,交通不便,改善彝族俐侎人生存条件的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兴修公路,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将彝族俐侎人传统的手工业及畜牧业与旅游业结合,实现产销一体,是拉动就业、脱贫创收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