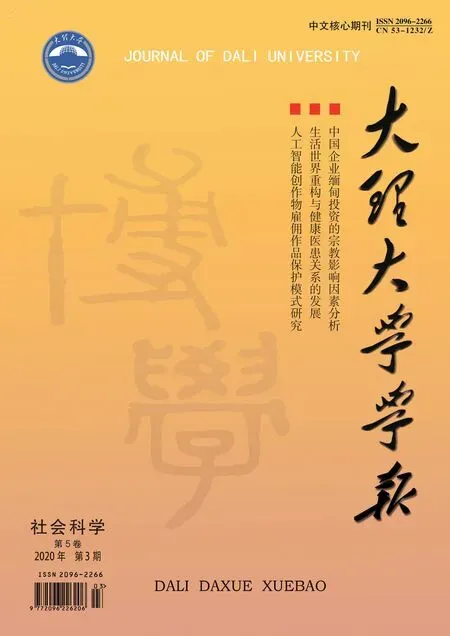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探究
2020-12-13沈朝华王紫霞
沈朝华,王紫霞
(1.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671003;2.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大理671000)
关于女性主体性,有的学者将其视为女性肯定自身能力、自身力量,在谋求自身地位、自我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1〕。我们认为能思、自主、具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只是女性主体性的一方面。女性能否以主体身份出场,还受到不可知的、不可控的力量的限制。有关女性主体意识,通行的解释是指妇女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地位,并自觉地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拒绝父权制文化对自我的塑造和命名,在物质和精神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走向独立的自我意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如果用于诠释少数民族女性的主体意识,有一定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少数民族妇女,作为女性,她们受到男性的歧视和压迫;作为少数民族,她们还受到主体民族的歧视、压迫。所以,少数民族女性的主体意识不仅只存在于男女的“二元关系”之中,还存在于民族与国家的“结构性的共生纽带”之中。在这个“共生纽带”中的跨境民族妇女,她们的主体意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2017年和2018年课题组曾多次在德宏州三台山德昂族乡调研①三台山乡的德昂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多数村寨位于山区,与景颇、汉、傈僳等民族交错分寨而居。据统计,三台山德昂族乡辖勐丹、出冬瓜、允欠、邦外4个村民委员会36个村民小组(德昂族村民小组21个1 038户4 228人,景颇族村民小组7个322户1 228人,汉族村民小组8个380户1 579人),耕地面积38 705亩,其中水田2 854亩,旱地35 851亩。2015年三台山乡总人口1 748户7 161人,其中农业人口7 035人,占全乡总人口的98.2%。农业人口中,德昂族村民小组21个1 038户4 228人,景颇族村民小组7个322户1 228人,汉族村民小组8个380户1 579人。参见《芒市年鉴2016》,内部资料,2016年,第129页。另,文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均为课题组的调研所得。,本文就以三台山乡德昂族妇女为例来剖析这一问题。何以选择德昂族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德昂族②德昂族先民在古文献中称之为“闽濮”“扑子蛮”“蒲人””蒲蛮”“崩龙”。新中国成立后沿用元明清时期的族称“崩龙族”。德昂族系1985年之后更名的族称,现中国境内德昂族有2万多人。在境外的人口没有确切统计数据,有50万,70多万,100多万之说。系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国家一直很重视对德昂族的帮扶和援助。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其二,德昂族属跨境民族,在缅甸被称为崩龙族①关于缅甸崩龙族的支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研究者认为缅甸崩龙族有19支族系(参见李茂琳,王素勤:《缅甸的勃欧族与中国境内的阿昌族非同一民族》,《德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而《芒市年鉴2016》一书则认为德昂族有20多个支系,有绕买、绕昂、绕科、绕旺、绕果、绕波、绕进、绕峨、绕本、绕别牙、绕腊、绕王、绕别列、干得别列、绕孟丁、绕布冬、绕不峨、绕孟得丁、绕格若等,其中绕迈、绕科、绕买、绕静等7个支系在中国有分布,其余皆居于缅甸。。德昂族妇女经常到缅甸探亲访友。在发掘和利用中缅民间交往资源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关注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引导德昂族女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三,新中国成立前,德昂族妇女长期处在父系制大家庭的社会结构之中,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低。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的政策使德昂族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德昂族女性的主体意识,有助于我们认识跨境民族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表现
德昂族女性的主体意识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巨变当中是如何表现的?我们通过对三台山乡德昂族妇女的考察,将其表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别平等意识增强
越来越多的德昂族妇女开始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部分德昂族妇女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依附性人格的影响,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劳动交换之中有了建构“主体性人格”的愿望。对于女孩子来说,表现为不愿意按照家长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自我决定的意识在未婚和已婚年轻德昂族妇女身上尤为突出,表现为不愿意再像自己母亲、奶奶那样牺牲自我的发展去为家庭做奉献,终其一生将男人作为轴心,按照男人的价值观和期望来塑造自己,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衣、做饭、挑水、织布、插秧、采茶、制茶、下地来向家人乃至家族证明自己的勤劳和贤惠。在行为上表现为,部分已婚妇女自觉地摒弃民族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现在德昂族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和家庭压迫的形式就是外出打工。村里干部说:“一旦女人说要去打工,男人通常情况下会很快妥协。”男人想要确立家庭秩序的权力常常因女人的抗争而削弱。而男人想要保住在家庭中发号施令的权威,也因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已经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尤其是德昂族妇女在家庭经济活动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后,德昂族女性有了家务劳动男人也应共同分担的意识。家庭重大事项的决定,也由“男主女从”变为平等协商。在调研中,50岁以上的德昂族妇女对中青年德昂族男性的评价是能干家务,能带孩子,比他们的父辈强。德昂族妇女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还表现在道德遵循上有了男女均有责任与义务的意识。我们在调研中曾询问中年和老年的德昂族男性,他们眼中好女人的标准。中年男性的标准是“贤”“礼”“孝”“勤”,老年男性则是“孝”“礼”“义”“勤”,而德昂族妇女对这些要求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这些道德品质不应仅是用来要求女人,男人也应当遵循。德昂族妇女已经不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意识到家庭道德是双方的义务。对于德昂族妇女来说,有了国家法律和政策撑腰,自己在家庭中希望配偶将自己“当作独立自主的个体来对待”〔2〕的底气也就更足。与老一辈的德昂族妇女更关注家庭相比,年轻的德昂族妇女既关注家庭,也关注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且能在家庭与自我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上述这些变化,固然与改革开放后德昂族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德昂族妇女已经自觉地将人格平等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二)自我发展意识被激发
德昂族女性的自我发展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中不断得到激发。其一,德昂族妇女就业创业意识不断增强。2018年暑期,课题组在出冬瓜村调研时,注意到在奘房从事佛事活动的多是50岁以上的妇女,很少有年轻妇女的身影。反映了新一代中青年德昂族妇女不再将美好生活寄托于神佛,而是更注重个人努力,甚至留守家中的年轻德昂族妇女也希望能够独立创业。三台山出冬瓜村德昂族惠民食馆的主厨HL,德昂族,31岁,初小文化,曾经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打工,现留守家中照顾两个儿子。但HL并未只仅限于料理农活,依靠丈夫薪资养家,而是就地创业。除了餐馆的工作,她还利用微信给本村及邻村妇女推销护肤品。YR,25岁,中专毕业,一个嫁在本村的德昂族妇女,出嫁时父母给了5亩地。丈夫小学毕业,在外打工,家里孩子一个4岁,一个9个月,小夫妻俩花了7万多块钱,在娘家附近买了房子。YR的梦想就是能够在家里发展养殖业。这样既能照顾好孩子,又能贴补家用。这两位年轻德昂妇女没有给人留下可怜的农村留守妇女这样刻板的印象。她们并不想在经济上依靠男人,而是想着如何既能扮演好媳妇、母亲、妻子的角色,又能够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劳动者。其二,德昂族妇女对生产技能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欲望。德昂族妇女对经济作物及林果种植管理技术、家禽规模养殖管理技术、生猪肉牛的养殖管理技术及疾病的防控、“畜—沼—肥—果”的循环农业、农产品的电子商务营销都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意愿。出冬瓜村的妇代会主任说:“只要是有益于提高生产生活技能的培训学习,她们都会踊跃地参加,包括家居环境、礼仪培训以及家长学校举办的法律知识培训、子女教育等。”
(三)自我表现欲望趋于增强
德昂族妇女多数能歌善舞,但过去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占了大量的时间,妇女的文化娱乐需求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在日复一日重复性劳作中被压抑。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实施的“兴边富民行动”以及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德昂族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妇女的劳动负担减轻,德昂族妇女自我表现的欲望逐渐趋于增强。首先,妇女们踊跃地参与村里文体活动。过去,德昂族妇女因为生产生活重负,很少参加村里的文艺活动。现在的三台山乡德昂族妇女尤为喜欢“三八”节的活动,上至五六十岁的妇女,下至二十几岁的媳妇,都会很积极地参加村委会组织的文艺表演。一位56岁的德昂族妇女曾对我们说:“他们不来,我们不表演。”这种渴望被承认的社会心理已经成为德昂族妇女较为普遍的一种自我意识。其次,德昂族青年妇女还会将自己的审美追求通过民族服饰彰显出来。女人天生爱美,最能体现德昂族妇女自我表现欲望莫过于妇女的着装打扮。在调研中发现50岁以上的德昂族妇女在着装打扮上会严格遵循传统。但新时代年轻的德昂族女性的着装不会像中老年妇女那样固守传统,也不会像她们的祖辈那样通过嚼草烟、芦子、沙基寻求文化认同。“花德昂”“红德昂”的年轻妇女也不再像老年妇女那样剃掉头发。过去,德昂族妇女在织布制衣中不敢过于大胆地去表露自己的审美情趣,但现在年轻的德昂族妇女则会无所顾忌地将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通过改造传统的织布手艺、缝制挂包展示出来。她们会根据现代人审美观对本民族服装进行改造,添加现代元素,使之看起来更加大方美丽时尚。腰箍、挂包、服饰成了德昂族妇女构建和彰显主体意识,定位自己的新角色,塑造德昂族妇女新形象,展现德昂族女性精神气质的重要活动。
(四)“文化自信”意识彰显
对德昂族妇女来说,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文化自信”,也包括德昂人对自己的文化要自信。当许多年轻的德昂族人已经遗忘了德昂酸茶的制作工艺,遗忘了德昂人与茶相关的民俗礼仪,甚至遗忘了这个古老民族洗手洗脚礼,三台山乡一部分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德昂族妇女和男人一起承担起了拯救民族文化的重任。而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有关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成为了德昂族妇女坚定文化自信的制度支撑。德昂族妇女开始自信地把德昂传统民宿、德昂“农家乐”、德昂织锦、德昂酸茶、德昂菜作为品牌亮出来。在如何利用好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项目扶持上,德昂族妇女表现出决断力和行动力。我们在三台山出冬瓜村见到民宿“德昂人家”女主人、德宏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织锦传承人ZY。这位50岁的德昂族妇女,从无意识地传承民族文化到逐渐转化为有意识的文化坚守,将保护德昂族文化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从决定保留自家用木头搭建的干栏式建筑的老屋到将其作为德昂餐馆兼客栈,并销售自家发酵的德昂酸茶,走民族特色的经营路线。这其中固然有党委政府、妇联的支持,更多的则是ZY作决定。在如何保护本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这位普通的德昂族妇女始终坚持要完整地保留德昂人传统的民居样式,而不是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对民居作现代化的改造。作为德宏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昂织锦传承人,ZY曾多次接待中央电视台和省电视台摄制组到家里拍摄德昂族妇女织布的情景。和她一起织布的德昂族妇女们每次都会自然大方地面对镜头,毫无忸怩之态。德昂族妇女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将民族服饰制作变成塑造民族形象的活动。2017年暑期在出冬瓜村,一位德昂族妇女曾告诉我们:“一套纯手工制作的德昂妇女衣服,价格是1 500元到1 600元。人家觉得太贵,不好卖,只能租。比赛、表演都是拿我这里的衣服,有时候拿七八套,或者拿去昆明,或者拿去北京。”德昂族妇女通过将手工制作的服装出租给相关单位、社会团体,将女性自我表现的欲望变成民族意识的自我表达,一方面,表明德昂族妇女在民族形象塑造上将自己置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达德昂族妇女对本民族文化的满满自信。身为德昂女人,不仅是在织布机上编织岁月,在稻田里挥洒汗水,在奘房虔诚礼佛,而是也可以将中国德昂文化播撒到中国辽阔疆域,播撒到“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沿线国家,向世界展示中国德昂族人的文化自信。
二、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动因
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在新时代何以能够蓬勃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不断推进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保障妇女人权等制度化的实践,才能深刻洞悉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为妇女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前,德昂族妇女作为女性,除了受到民族压迫,还面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所带来的性别压迫,不得不顺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强制性的规定”〔3〕,而身为少数民族妇女,相比汉族妇女,受压迫的程度更深。她们的“族裔身份”,常常使其遭受性别和民族等双重歧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一,压制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以其所蕴含的平等、公正、正义的价值理念将历史上被统治者完全边缘化的德昂族纳入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架构中,使德昂族妇女享有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提升了民族间基于团结而产生的相互尊重感,也给德昂族妇女维护自己的尊严提供了政治保护。其二,社会主义致力于追求妇女解放,使德昂族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渐摆脱性别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体现男女平等原则的政权组织形式嵌入到了三台山的基层社会之中,德昂族父系氏族公社逐渐解体。边境地区的党委政府也将发动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妇女党员作为工作重点。中国共产党通过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制度化,从制度上瓦解德昂族原生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打破三台山乡德昂族父系氏族社会结构使男女平等变得不可能的僵局。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使德昂族妇女摆脱性别压迫具有了可能性。
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新中国妇女人权事业的不断进步。首先,在培育少数民族妇女主体意识的过程中,新中国特别重视清除少数民族价值信仰系统中严重侵害妇女人权的文化陋习。德昂族在其文化价值系统中有“歹”“琵琶鬼”①在德宏,很多少数民族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不能解释疾病、死亡等现象,经常将人畜死亡视为鬼怪作祟。被称之为“歹”“琵琶鬼”的人,被视为被魔鬼或某种邪恶的魂魄附身,能够四处传播恶疾,祸害人畜,而且还会传给后代。的观念。德宏州法院高度重视处理少数民族信仰系统中打“歹”、诬陷他人为“琵琶鬼”等此类严重侵犯妇女人权,残酷迫害虐待妇女的案件〔4〕23。各县结合地方实际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1984年7月16日潞西县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潞西县社会治安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不准诬陷他人为‘琵琶鬼’”〔5〕的规定。在国家力量的威慑之下,边境地区打“歹”、驱逐“琵琶鬼”等事件基本绝迹。其次,新中国构建起了相对完备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保护妇女权益,消除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各行各业各个家庭的行为规范。德昂族妇女进入到了一个公开承认女性拥有婚姻自主权、财产权、自由权的新社会,第一次在国家的法律保护中感受到人的尊严。德宏州法院干部为宣传《婚姻法》,背着铺盖,走村串寨,边办案,边讲解〔4〕166,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觉醒。改革开放后,妇女权益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明确妇女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198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使在民族习惯法中失去财产继承权的德昂族妇女有了保护自己权益的武器。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宪法中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具体化为“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这些法律法规在三台山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德昂族女青年打破“同姓不婚”“不与异族通婚”族规的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达到了高峰。199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0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1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保障妇女生命健康变成了国家行为。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唤起德昂族妇女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现在的三台山乡,育龄妇女要进行孕前检查,及时增补叶酸,按照医嘱进行孕检,生孩子要到县妇幼保健院,在德昂山寨已经逐渐成为了常识。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不能“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依法依规保护农村外嫁女的合法权益,为德昂族妇女摆脱父权制的宰制,增强独立自主意识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巨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三台山,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使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德昂族妇女提供了经济自立的机会。列宁曾指出“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6〕。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边疆少数民族女性带来了进城务工的机会。男女平等的价值观也使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对德昂族女性的诸多限制和约束逐渐消解。这群“腰箍套不住的女人”快速融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潮。德昂族女性开始到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务工,实现了从“家庭中人”到“社会中人”的转变,追求性别平等,人格独立的意识,也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视野的不断开阔而趋于增强。
其次,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德昂族传统的性别分工趋于模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台山乡部分德昂族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例如邦外村逐渐不再种水稻、玉米、茶叶,而是开始大规模地种甘蔗。妇女成为自家甘蔗种植的重要劳动力。在其他村寨,德昂族村民开始种植祖辈从未弄过的咖啡、香蕉、杨梅、板栗、柑桔、澳洲坚果等经济林果。德昂族传统文化中塑造女性角色的织布、插秧、采茶等活动对德昂族女孩来说变得无足轻重。生计方式的改变使传统社会性别支配的物质基础逐渐瓦解。在广泛地参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劳动交换中,德昂族妇女独立自强的意识不断地被激发。
最后,“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为德昂族妇女的发展提供了自由时间。恩格斯曾说只有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去谈妇女解放〔7〕。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三台山,生活的重负和艰苦的环境曾使德昂族妇女把大量时间用于劳作。1999年,国家启动了“兴边富民”工程。德宏州编制完成了《潞西市人口较少特有民族脱贫发展规划(2003-2004年)》《潞西市兴边富民行动五年规划三纲要(2004-2008年)》等。2006年到2010年,云南省为德昂族聚居村制定了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四通五有三达到”,“即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有学校、有卫生室、有安全的人畜饮用水、有安居房、有稳定解决温饱的基本农田地或牧场;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纯收入、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国家扶贫开发纲要的目标,现有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以上水平”〔8〕。上海市在全国率先签署了帮扶云南德昂族发展的协议,《上海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项目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援助2 500万元资金,帮扶德昂族发展〔9〕。随着“兴边富民”持续推进,三台山乡的水电、村内道路、住房、人畜饮水等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沼气灶、自来水、洗衣机、电冰箱相继进家,德昂族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极大缩减。有了空闲时间的部分中青年德昂族妇女和丈夫一起参加了“上海市对口帮扶德昂族农村人才培训学校”和“上海市对口帮扶德昂族青年就业培训基地”的技能培训,然后双双奔赴上海务工。
(三)十八大以来妇联工作方法的不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省妇联的工作在贯彻“五位一体”的布局,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广大妇女发展上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云南省、市、县、乡、镇、村等各级妇联组织围绕着国家的工作重点,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形成了上下联动,合力推动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新局面。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的彰显,从内因上,与德昂族妇女外出闯荡获得的城市经验及参与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有关。从外因上,与妇联在妇女的“关爱行动”上采取的新举措有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妇女在云南各地大力推进“妇女发展循环金”“云南省农村单亲贫困母亲安居住房援建”“受艾滋病影响社区儿童关怀救助项目”、实施救助女童的“春蕾计划”等项目。芒市各级妇联连续几年开展“妇女创业就业促进行动”,以服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妇女增收致富”为工作重点,大力培育科技致富领头人、培育农村女能人、“致富女能手”。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典型培树,开展创业分享。在项目扶持上,实施了贷免扶补、少数民族妇女乡村道路养护项目、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科技致富示范等项目。
三、新时代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进一步提升还有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德昂族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张扬,但离现代妇女的发展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认为,奋进新时代,提升德昂族女性的主体意识还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各部门要增强性别意识
在调研中发现无论是中央,还是实施对口帮扶内地城市,省、州等各级政府在制定帮扶人口较少民族的规划和政策、脱贫攻坚政策时,并没有将少数民族妇女纳入到其中加以考虑,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是当前政策上的盲点。很多职能部门将妇女的发展问题归于计划生育部门、卫生部门、妇联。而有时妇联在工作上强化了对女性家庭角色塑造。课题组在三台山乡调研时,发现与家庭环境卫生清洁、烹饪等相关技能培训,村妇女主任也多动员妇女参与。而对生产技能型培训,很多德昂族妇女则知之甚少。大多数职能部门没有意识到每个规划都会涉及占人口总数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妇女,她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制定政策和项目规划时,如果为少数民族妇女专门设置项目,将少数民族妇女纳入到项目扶持之中。这些少数民族妇女可能会做得更好。我们认为,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并不是要强化传统的性别分工,而是要将少数民族妇女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进行发掘。
(二)教育部门需重视德昂族妇女的社会教育
教育有助于唤起妇女的主体意识,尤其是结合生产生活需要开展的社会教育,能够让妇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三台山乡的社会教育,覆盖面较为广泛的主要是扫盲,而且扫盲又主要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在短期内以运动式集中整治的形式展开。关于德昂族妇女的扫盲情况,有研究者提到大多数德昂族妇女文化程度较低,而且在扫盲教育中复盲的现象较为普遍〔10〕。扫盲教育成效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脱离妇女的实际需要。扫盲教育在三台山乡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教育形式,但只有结合妇女生产生活的实际,以满足妇女的需要为培训内容的扫盲教育对妇女发展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在三台山乡调研时也感受到了部分德昂族妇女学习技能、技术的欲求,德昂族妇女已经意识到德昂族正在经历着生计方式的转型,而新的生计方式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是自己所不具备的,也验证了朱真莉的观点即少数德昂族妇女“希望村里继续办夜校,教大家识字和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10〕。我们也深切地感到政府援助的项目必须要重视相应的技术扶持,尤其是不能忽视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有的村妇代会主任说,“男人培训了不动,但女人培训了立马就会动起来”,现在各村寨的少数民族妇女真正成为了农民致富、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三)培育德昂族妇女参与意识需持续发力
妇女的参与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妇女的社会参与可以理解为妇女能够“自发性投入许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争取自我权益及发言机会”〔8,11〕。虽然德昂族妇女的社会参与意识相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大多数妇女参与较多的公共事务是村内垃圾清理,环境卫生清洁,浇花节等重大节日的义务劳动,而这些社会参与大多与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关。在政治参与上,虽然,村“三委”班子的换届选举工作,妇女们都会到场。对德宏州“一乡一品牌、一路一风景、一村一特色”,实现环境、产业、乡风文明协同发展理念,妇女们也会做出响应。但农村的德昂族妇女对自己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缺乏足够的重视。大部分村寨的德昂族妇女对妇女小组长的工作,竞选村委会干部包括妇代会主任,均表示出不情愿,表明大部分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并不高。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三十至四十岁年龄段德昂族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家庭生产生活、养育子女,对于政治事务参与的热情不高。
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是个体突破“小我”的限制,从自立走向立人,从“小我”走向“大我”并确立“主体性人格”的重要环节。
我们认为就提高德昂族女性的参与意识而言,妇联及相关部门的引导不能局限于文体活动、妇幼健康讲座、打扫公共环境卫生等,还应在参与维护边疆稳定、边境地区的安全上发挥主体作用。可以由妇联及村委会牵头组建妇女护村队、巡逻队,民族工作妇女小分队、调解矛盾纠纷的妇女工作组,在妇女之中发展情报信息员、调解员,使妇女成为民族团结、乡村治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力量。在中缅跨境文化交流中,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都可以引导德昂族妇女参与到其中,利用德昂族妇女语言优势,熟悉缅甸民情的优势,充分发挥其在中缅合作中的桥梁作用,为中缅的人文交流、经济交往奠定民意基础。在三台山乡不同支系的德昂族妇女中培养民间公共外交人才,让她们成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支持德昂族妇女逢重大节日跨境交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为促进中缅民间互信贡献力量。总而言之,要引导德昂族妇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追求自我价值,而不是仅仅将自我价值定位于家庭、丈夫、儿女。
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曾说:“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12〕十八大以来,德昂族妇女作为德昂族跨越式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历史见证者,以昂扬的精神风貌,投入到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剧中人”和“剧作者”的身份谱写中国跨境民族奋斗新时代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