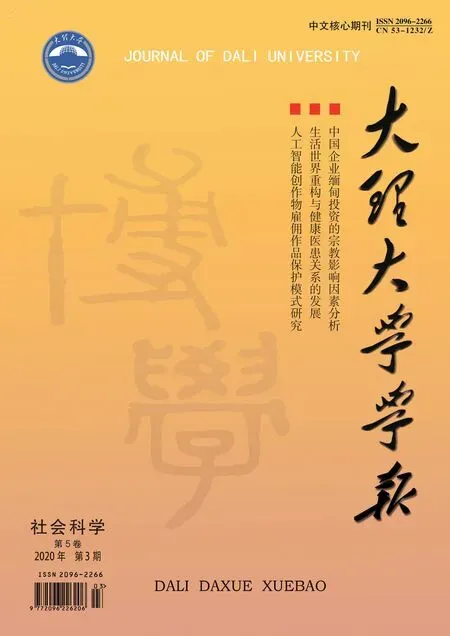中国企业缅甸投资的宗教影响因素分析
——以莱比塘铜矿为例
2020-12-13李丰春
李丰春
(大理大学法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缅甸与中国一水相连,法乳相通,素有“胞波情谊”。缅甸作为澜湄合作机制的主要合作方,在构建澜湄流域命运共同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参与者。但自从2011年米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单方面叫停以来,我国在缅甸的多个投资项目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特别是莱比塘铜矿项目,更是命运多舛。中资企业在缅甸投资受阻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于不懂缅甸的宗教信仰、宗教习俗和宗教礼仪而引起缅甸民众的不满或抗议,是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归纳分析法,以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尝试探讨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遇阻的宗教因素以及应对方法,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借鉴和建议。
一、莱比塘铜矿开发遇阻的基本情况
缅甸莱比塘铜矿是中缅合作开发经营的一项标志性示范项目,但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宗教、环保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原因,自2012年3月20日莱比塘项目正式启动以后,该项目便一波三折,经历坎坷。从2012年6月开始,当地佛教僧侣就带领村民不断抗议和阻止项目的进展。6月2日,僧侣和附近村民围堵矿区营地的主大门,要求项目停工。6月4日,项目的主体工程被迫停工。6月8日,莱比塘项目全面停工。直到8月21日,抗议局势稍微稳定之后,项目主体建设实现部分复工。但到了11月18日,局势再次恶化,佛教僧侣和附近村民等维权人士在铜矿营地设立多个据点,封堵万宝公司营地的出入口,而且提出一些与项目无关的政治诉求,诸如要求缅甸政府“解散军方背景的经控公司”,并高呼“中国人滚出去”〔1〕等口号,使整个莱比塘事件滑向政治化的发展方向,铜矿项目工程建设不得不被迫再次停止。11月29日,当地一些村民及僧侣再次到莱比塘铜矿示威,并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结果酿成著名的“11·29”事件〔2〕,这成为后来被国际舆论指责的“莱比塘项目侵犯人权”的口实。这次事件直接导致12月2日莱比塘项目被迫全面停工。
随后,缅甸政府设立以缅甸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领导的莱比塘铜矿调查委员会,就莱比塘铜矿的开发进行全方位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莱比塘铜矿不存在破坏环境等环保问题,特别是针对宗教僧侣提出的有关佛教寺庙搬迁等问题,也在委员会的协调之下得到妥善的解决,并根据僧侣和村民的要求,莱比塘铜矿施工方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3〕。直到2014年12月24日莱比塘铜矿项目完成围挡扩建,2015年1月初全面复工。2016年3月,莱比塘铜矿实现顺利投产。
二、莱比塘铜矿项目遭遇的宗教影响因素分析
莱比塘铜矿项目一波三折,虽说有环保、补偿不透明、缅甸民众与前军政府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但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没有重视或忽视了缅甸全民信教的宗教因素,以及由此带来的宗教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缅甸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的因素
1988年,缅甸政治开启民主化运动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缅甸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军人政权允许多党制的存在,并于1990年举行了多党制大选。这次大选,标志着缅甸政治从权威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2007年9月,以油价大幅度上涨为导火线,爆发了由民众和僧侣组成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由于有僧侣的参与,这场示威活动被称为“袈裟革命”或“番红花运动”(Saffron Revolution),数万名僧侣走出寺庙,走向街头,积极参与到反政府的政治运动中。有关佛教人士对这次“袈裟革命”进行这样的评价:“佛教积极的入世,与当权者或主流价值对抗,介入众生权益的争取,也可以消除人们认为佛教是消极遁世宗教的观念。”〔4〕这种凭着以利益众生为由,行佛教政治化之实的游行活动,在缅甸常常发生,如1988年的“8888运动”①缅甸8888民主运动,亦称“8888事件”,是1988年在缅甸发生的一场争取民主的大规模民众运动,“8888”的名称来自1988年8月8日的大示威。这场反对军政府的运动,其主要参与者就是僧侣和学生。。
在缅甸,佛教积极入世,是与缅甸自古以来的政教关系分不开的。从11世纪佛教成为缅甸的国教开始,政府和僧团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的佛教政治思想中,国王的一项神圣使命就是积极宣扬佛教和保护佛法。在殖民时期,僧侣为了民族的独立,领导民众掀起反英浪潮,僧侣成为政治活动的领头人。1948年缅甸独立后,吴努政府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和缅甸人自古以来信奉佛教的传统,通过宪法规定佛教为缅甸的“国教”。吴努视自己为佛教信仰的保护者及净化者,发动了大规模的计划来宣扬并强化佛教。从此,缅甸在佛教政治化和政治佛教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如1954年,迫于宗教的压力,政府不得不把佛教教义列为各级学校学生的必学科目〔5〕。
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僧侣又参与反对军政府的活动,如“僧侣民主联盟”拒绝为军政府举行宗教仪式等。僧侣认为,“社会运动一方面是监督政府,减低政策错误的机率,甚至是为了改变恶法,另一方面要面对群众,帮助群众抛弃成见,更正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袈裟革命正是为了维护众生的权益,希望缅甸军政府改变恶法的一种无畏施”〔6〕。与此同时,缅甸的佛教组织积极参与反对“德祐”②缅甸语中的“德祐”指华人。活动。在莱比塘事件中,僧侣的身影更是频频出现在抗议活动之中,企图用宗教的政治影响抵制莱比塘铜矿项目的开发。正如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说:“政治转型过程中宗教意识形态填补了世俗意识形态的空虚,利用和强化宗教情绪被政治家视为实现政治目标、获取政治利益的有效手段。”〔7〕因此,在缅甸,“无论何处,任何一场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中,僧侣总是会出现在领导者之中,没有哪一场运动是没有僧侣作为精神领袖的”〔8〕。
总之,在缅甸,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选政府,领导人都在弘扬佛教和保护佛教方面不遗余力。他们崇佛、礼佛,跪拜高僧,给予“僧侣大主席团”极高的待遇。特别是在大选期间,竞选的双方为了拉到更多的选票,佛教徒都是他们极力拉拢争取的对象。对于佛教极端主义事件,他们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为缅甸佛教的政治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忽视了缅甸佛教极端势力的影响
缅甸极端势力的出现,也与宗教政治化紧密相连,僧团意图通过民族宗教冲突,影响外国对缅甸的投资进程。最早注意到缅甸佛教极端势力的是美国著名的上座部佛教学者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他2014年在缅甸考察时发觉缅甸佛教极端势力在极速扩张和蔓延,于是,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佛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下,……宗教因缺乏容忍,种族主义泛滥所引起的冲突正迅速地蔓延。”〔9〕他对这个国家佛教当时的变化深感担忧。杰克·康菲尔德认为,缅甸佛教中的极端势力在民主的掩护下,出现不良势头,特别是佛教的极端团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形成一股极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其带来的后果是缅甸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迅速扩张〔5〕。更有甚者,缅甸激进主义高僧所宣扬的“我们和他者”的理念,被军政府利用,作为政治修辞来证明军政府政治的合法性〔10〕。因此,当“僧权”与“政权”相结合,“政治精英往往倾向于沿着社会裂痕进行动员,因为这种动员无需提前构建制度,只需被动员对象具有关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在不确定性面前本能的归属感,宗教和族群记忆成为其最好的动员工具”〔11〕。在此基础之上,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缅甸本拉登”〔12〕的缅甸极端主义僧人维拉督(Ashin Wirathu)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我们要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体系,保护我们民族和宗教不受外人侵害,这类似于甘地呼吁人们抵制外国产品”〔13〕。维拉督提到的“外人”,显然不仅仅是指非缅族、非佛教团体。在莱比塘事件中,维拉督领导的“969佛教极端组织”从2012年就开始动员佛教徒,抗议和干涉莱比塘铜矿的正常开采。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传媒手段和宣传工具,在缅甸的民众中强化中国投资企业和在缅的华人“经济掠夺者”的形象。利用“沉默螺旋”效应,把“抗议”描绘成“优势意见”,是“民意”的体现,加之民众对搬迁寺庙的顾忌心理,在舆论上绑架人民的意志,别有用心地抵制莱比塘铜矿项目的开发。
(三)忽视了缅甸人民的宗教感情
缅甸是一个佛塔之国,素有“千塔之国”的美称,国内到处佛塔林立,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建有佛塔和寺庙,根据《中国与缅甸宗教交流分析报告(2010-2015)》统计显示,缅甸有80%以上的国民信仰佛教,和尚在世俗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由此,和尚也具备了常人所不及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凝聚力。一般情况下,寺庙是不轻易搬迁的,因为在缅甸人的信仰中,有“寺庙佛塔不拆迁”这一传统。而莱比塘铜矿项目采区中央正好有一座佛塔,当地人认为是18世纪的高僧莱迪曾经修行打坐做法事的地方,应当当作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来保存。但这座寺庙正好位于采区的正中心,若不搬迁,势必影响项目的进展,若搬迁,就触动了缅甸人宗教信仰这一敏感神经。
中国的施工方人员大多为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许多员工根本没有南传佛教信仰常识,进寺庙不脱鞋,见和尚不跪拜。腾讯财经《棱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方管理者往往沿用国内的管理办法,只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不会主动研究缅甸人的宗教信仰和实际需求”〔14〕。有的管理者认为钱是万能的,“有钱就任性”,奢望给些钱(补偿款)就可搬迁寺庙。同时,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沿用国内的办事逻辑,“跟政府谈好了,剩下的就是政府的责任,不主动去面对民众”。曼德勒孔子课堂中方主任何林对莱比塘事件调查后认为“村民(寺庙)未必与政府作对,但在外来NGO(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等组织的支持下,可以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15〕。
缅甸民众和僧侣的表现可归结为一种宗教情感,即对所信仰宗教的虔诚、敬畏和尊重。本文所指的宗教情感还包括对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宗教物品等的依恋和崇拜,以及对宗教仪式、习俗的沿用。在莱比塘事件中,一些人利用缅甸的“寺庙不拆迁”的传统,煽动宗教感情。缅甸的一位高僧在采访中所说,寺庙佛塔搬迁的问题,是莱比塘事件的最大导火线之一,闹事者就是利用这样一个理由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反对搬迁〔16〕。这是别有用心者利用民众对佛塔和寺庙的情感,阻扰莱比塘铜矿的开发。
缅甸一位商业组织负责人认为,有时给缅甸村民发放补助款,还不如请几个和尚念经更能赢得民心。因为和尚在缅甸人的心目中,是佛陀的化身,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而要搬迁寺庙,也要首先与和尚沟通好,尊重他们的意愿与抉择。直到2013年3月11日,莱比塘铜矿调查委员会出台调查报告,报告结论认为,“很难认为这些佛塔(指建在莱比塘矿区中央的佛塔)是文化古迹”,其中的佛塔和禅房“找不到是由村民传说的莱迪高僧修建的宗教古迹的证据”。后来在整改中,对寺庙进行了妥善的搬迁和重建工作,莱比塘铜矿项目才得以顺利施工。
三、莱比塘事件的启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企业投资缅甸由于忽略宗教方面的影响,并把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带到缅甸“生搬硬套”,致使民众抗议,工程一再停工。这种忽略表明中国企业缺乏对被投资国宗教信仰的理解与尊重,在投资的过程中缺乏对被投资国宗教风险的评估与防范。只有真正地重视海外投资的宗教影响因素,积极评估宗教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风险意识,并及时防范,中国企业才能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走得更稳、更顺利。莱比塘事件给予我们如下的启示。
(一)宗教风险评估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前提条件
进行海外投资,无论是企业的决策者还是专家学者,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常常把重点关注在投资国的政策变化、经济环境以及突发事件等方面,对于宗教因素的影响或宗教风险的评估重视不够,或处于一种忽略或不重视状态。但对于全民信教或有种族冲突和宗教矛盾的国家,由于宗教因素引起的风险亟待给予特别的重视。“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可能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17〕。相对于缅甸这样一个80%以上的人信仰佛教的国家,宗教风险几乎无处不在。
缅甸的僧权集团是个既得利益团体,其明显的表现就是“佛教的世俗化”〔18〕,他们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在国外投资者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时,部分僧侣利用民众信仰的心理,发挥其“参政”的优势,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肆意破坏项目的进程。与此同时,缅甸的许多官员信奉佛教,他们在审批项目时,往往先到寺庙礼佛,询问高僧有关项目是否吉利,项目是否破坏了当地的风水,以及项目的开工时间是否与佛教节庆时间冲突等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到佛塔佛寺的搬迁问题时,更是触动了缅甸人“寺庙不搬迁”这一敏感神经。再加上若被询问的高僧有宗教沙文主义倾向,他便会从佛教伦理中找出各种理由,阻止项目的审批。即使在审批之后,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僧团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动员能力,阻挠工程的顺利开展,莱比塘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个案。他们打着莱比塘矿区是“风水宝地”和“名胜古迹”的名义,煽动民众围堵矿区,直接导致项目停工。这种“僧权”与“政权”相结合的风险,在进行投资之前,不得不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考量。
(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保障
对待缅甸国内的僧侣团体,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分类方法,确定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才能在与僧团的周旋中,做到“有理、有力、有节”。缅甸的僧团根据反华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顽固派,有西方势力的插入。如维拉督领导的“969佛教极端组织”,在我国投资中缅油气管道、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项目中,他们都是反华抗议活动中的组织者和煽动者。第二类是为反对军政府而反华的僧团。他们反华的目的当然有政治倾向,更多的是通过反对有军政府支持的在缅华人项目,制造不利的舆论,或打出反华的口号,激发当地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和强化其排斥心理,以达到反对军政府的目的。第三类是温和派,他们持观望的态度。对于这三类不同的僧团,中国企业要采用不同的统一战线策略,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特别是那些佛教精英,利用他们的影响做好缅甸的民意沟通,尽可能建立中缅友好统一战线,为中国企业保驾护航。利用高僧既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及时引导民众,宣扬中国企业的正面形象。如此,中国到海外投资的杂音会少一些,道路会畅通一些。
(三)做好民心相通工作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民意基础
中国企业在缅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心相通”出现了问题。要实现项目顺利的进展,就要像昂山素季所说,“中国投资在缅甸要更加成功,最重要的不是民盟的政策,而是民众的接受程度,民众希望投资对国家有利,对经济有帮助”〔19〕。和项目所在地的信教民众沟通,是中国企业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一项措施。
2013年莱比塘铜矿停工后,万宝公司针对发生的问题进行整改,特别是针对宗教问题,作出如下的整改:第一,利用佛教节庆日,举行公益活动。例如每年缅历的“月圆节”,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就组织员工参与矿区周边佛寺的捐赠、布施、法事活动,给寺庙僧侣捐赠袈裟、大米、食用油、储物柜等生活起居必需品。第二,加强与宗教领袖之间的沟通。项目负责人主动联系宗教领袖人物,向他们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或援建部分寺庙年久失修的禅房等建筑。通过宗教领袖的动员,让矿区周边的村民相信矿区的开发有利于民众的福祉,而不是在破坏当地的风水和他们的神灵。第三,密切联系矿区周边的信教民众。投资莱比塘项目的中国企业注重企业形象宣传,特地招聘一批了解缅甸民情的当地记者,做好宣传工作,争取舆论的主动权,特别是积极宣传企业参与僧团组织的大型法事活动的情况;同时,还积极招收移民和矿区周边的民众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不仅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兼顾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需要。如公司员工在佛教节庆期间,可以带薪请假回家参加佛教的法事活动。并且对于不能回家参加法事的员工,在矿区设有临时的佛塔跪拜和修行场所,方便缅籍员工的跪拜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夯实了民心相通的民意基础。
总之,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关注了解投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及时把握其动向,处理好跨文化管理中存在的宗教风险。特别是对于缅甸这样具有较强宗教属性的国家,决策者应该在对其宗教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充分把握当地“民意”,才能制定出来既“接地气”,又“惠民生”的优质项目,使企业得以落地生根,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