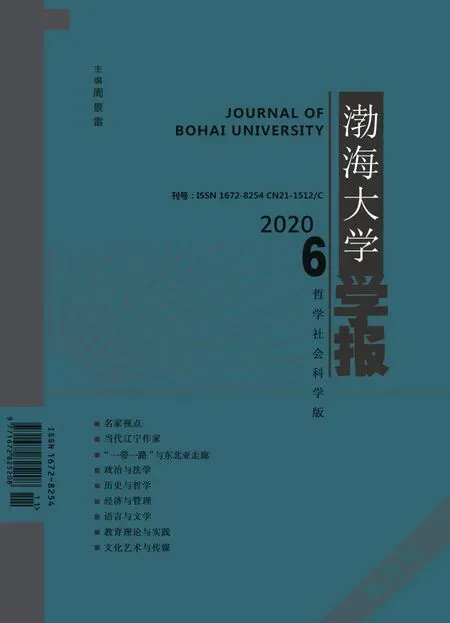孔子编辑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
2020-12-11温艳华渤海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锦州121013
温艳华(渤海大学学报编辑部,辽宁锦州121013)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关于孔子是否从事编辑活动,能否称其为编辑家,学术界至今依然存在一定的分歧。持肯定意见的认为,孔子是我国编辑活动的开先河者,是对中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编辑家;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孔子做了大量的编纂活动,并不是现在所定义的编辑活动,孔子虽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能将其称为编辑家。笔者认为,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第一次有意识地把编篆活动与创作活动分离开来,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等编辑思想,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一、孔子编辑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国昌平乡陬邑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人类文明成果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古代文明奇迹般地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中包括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及古希腊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7年)、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年)、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4—前484年)。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年)、季札(公元前576—前484年)、晏婴(?—公元前500年)、子产(?—公元前522年)、左丘明(公元前502—前422年)、伍子胥(公元前559—前484年)、孙武(公元前545—前470年)等也是这一时期灿烂文化的代表[1]。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年)末期,这一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成熟,铁制生产工具得到了广泛使用,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学派思想空前活跃、交相辉映,文学艺术极大繁荣。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面临着重大的变革,“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替代,诸侯分封制变为郡县制。随着政权的不断下移,旧的社会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周王朝奴隶制社会不断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整个社会形态处于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的社会转型期。
(一)孔子编辑思想源于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
周礼是周王朝的典章、制度、仪节、礼乐、习俗的总称。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保存了比较完备的周朝礼乐文化和典籍。孔子自幼接受周朝文化的熏陶,在耳濡目染中对周礼极其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孔子毕生都在学习、研究、传播周礼,把复兴周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恢复周礼,主张“以国为礼”“克己复礼”,力图通过恢复周礼,实行“德治”“礼治”,重新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
孔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得到各国诸侯的采纳。回到鲁国后,他把编辑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作为恢复周礼、重构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把精力投注到教育和编修《春秋》、修订《诗》《书》《礼》《乐》《周易》,开创了个人对古典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读、修订和编纂的先河。
(二)孔子编辑思想源于经邦济世的教育旨归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开办私学的第一人,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教育上,“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旨归是为恢复周礼、重塑社会秩序培养能够经邦济世的从政人才。因此,他编辑“六经”也是在编选教材,在编辑过程中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兼具道德修养和艺术精神的君子。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教育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是主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通过学习懂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显然寄托了孔子个人的政治理想。
钱穆说:“窃谓孔子思想之重点和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来。此原则繄何。用现在的话来说,只‘道德’二字便是。”[2]孔子讲的道德,是君子的修为。在孔子之前,君子是上层社会贵族的通称,与之对应的是小人,即底层民众。“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孔子则把君子从社会阶层的概念中剥离开来,把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视为君子,无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培养君子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编辑思想源于“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
“和而不同”见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而不同”是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不同而不违背规律、彼此冲突,是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是“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解释“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即君子内心所想相同,但外在表现不尽相同,但其“不同”却能致“和”;小人虽嗜好相同,但因私利之争而生内讧,其“同”反致“不和”[3]。“和而不同”体现了孔子的文化主张,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真正的和谐是包含互补与差异的统一,是融合对立与冲突的平衡。“和而不同”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文化策略,承认文化的差异和个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和而不同”是一种对不同文化理解和尊重的宽容精神,也是对自身文化发展需要的基本态度[3](206)。
二、孔子编辑思想的内涵
孔子编纂古籍、兴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推动了当时学术中心的下移。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纷纷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经典之作,也使编纂活动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从而“与著作活动一起成为文化发展与传承的两条主脉”[4]。
(一)“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
孔子编写的“六经”都是依据前代的史料,而他对待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就体现在他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上。“述而不作”是孔子编辑“六经”时所遵循的原则,“述”指传述,“作”指创作。朱熹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论语集注》)孔子“述而不作”编辑思想在中国文化史和编辑史上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将散存的古代文献汇编成册,且注重保留其原貌;2.在文献选取过程中坚持“择善而从”,注重“垂世立教”的社会功能;3.把“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与“作”区分开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把编辑活动与创作活动有所区分,开创了编辑活动自觉性的先河。
孔子“述而不作”的前提是“信而好古”。他编辑整理“六经”源于他对上古文化的热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是殷商的后裔,自幼喜爱古代礼乐文化,“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矣;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他热爱古之礼乐文化,如饥似渴地汲取其中的营养,“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他对传统文化不仅热爱,而且有深刻的领悟,他认为《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对古代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孔子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对古代文化由学习到热爱直至以传承发展为乐事。孔子以“述而不作”编辑原则整理、编纂传统文化,既体现了“信而好古”的历史观,也体现了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是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孔子在编辑“六经”过程中遵循“述而不作”编辑原则,但并不是泥古不化、一成不变,而是寓作于述。在孔子编定的文献中蕴含了其编辑原则、政治理想和审美取向,在搜集大量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校勘、增删,“笔则笔,削则削”,“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述而》)在孔子修的《春秋》中有这样的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天王狩于河阳”。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简单、客观的叙述,实际上体现了孔子的“作”。真实的事件是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周襄王召到晋国的河阳,史称“践土之会”。孔子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尊严,没有按照事件原貌叙述,而是用“天王狩于河阳”的简单叙述将这一历史事件一笔带过。另外,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已不再奉周朝的正朔,而孔子仍用周朝纪年“元年,春王正月”记录史实,也体现了自身的思想倾向。
(二)“不语怪,力,乱,神”的编辑导向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怪,怪异;力,暴力;乱,叛乱;神,鬼神。就是说,孔子从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他的这种思想在编辑“六经”和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述而不作”体现了孔子编辑思想的客观性,“子不语怪,力,乱,神”则体现了孔子编辑思想的主观性。孔子在编辑《春秋》时对原《鲁春秋》中一段记载: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夏四月夜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认为,陨星下落,离地一尺又返回天上是荒诞离奇的怪事,因此他在编辑《春秋》时只记述“星陨如雨”,余则不记。学生季路问孔子怎样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如何看待死亡,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认为聪明的人应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古人将认识对象分为可知世界与不可知世界,可知世界即为人间世界,主要体现在人伦纲常;人间以外的世界为不可知世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人文学科,它关注的命题是仁德礼制、教化天下。在这一命题中,必须舍弃与之无关的领域与方向。因此对于鬼神与死亡这些不可知的对象,孔子主张敬而远之,不去研究和讨论。
孔子在整理文献典籍时,面对纷繁杂芜的史料,在选材上坚持“不语怪,力,乱,神”,竭力排斥鬼神并删去荒杂妄诞的篇章。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就是以“思无邪”的标准,对收集到的3000 多首诗进行编选,最后删定305 首。《易》在当时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孔子绕开迷信巫术,汲取书中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来教育弟子,成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指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三”是概数,表示多次;“绝”是断的意思。这是说,孔子为读《易》而经常翻断编连书简的皮绳。孔子的学生对于老师下这么大功夫研究卜筮之书不能理解,孔子说:“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意思是说,我不是在研究占卜术,而是在探究《易》的德义内涵①。朱子说:“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5]。《左传·哀公六年》载:“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周大史说“这应在楚昭王身上”,需要昭王祭天才可以转移灾祸,昭王不祭。孔子得知后,称赞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他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大道”办事[6]。
作为殷人的后裔,孔子虽然不像殷人那样重鬼神祭祀,但也不会是无神论者,在那个时代他能提出“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正如鲁迅所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7]。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因有三:其一,孔子编辑“六经”用于教学,而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够经邦济世、匡扶天下的君子。孔子教育弟子做君子之儒,学道以修身,道明而身修,言谈举止无不合于正道,而“怪,力,乱,神”则不属于正道。其二,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秩序,而“怪,力,乱,神”的传播不利于君王统治和社会稳定。其三,孔子对于自己不曾见过的、怪诞离奇的超自然现象不能确定其有无,因此采取回避的态度。
(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编辑风格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注释有不同版本②,但是不同版本对于“异端”的解释是相似的,那就是与中庸相对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们可以理解为排斥异端,遵从中庸才不会有危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拈出这两个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就是折中的、平常的东西[8]。“中庸”是和谐、平衡,是恰到好处;异端则是偏执、冲突,是过犹不及。孔子在编辑诗经时强调“思无邪”,他在谈论诗经《关雎》这首诗时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明因为这首诗的情感表达恰到好处而被选编在诗经中第一篇。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9],在编辑“六经”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孔子提出的君子“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这是孔子中庸思想实践性的具体体现。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又未免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这才是君子[8](61)。孔子这段话体现了中庸的审美观,在编辑活动中则是要求内容和形式并重,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孔子对待“异端”采取的态度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8](87-88)。“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也是孔子对待“异端”的态度,观念不同就不要一起讨论问题,也不勉强达成一致。
三、孔子编辑思想的新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摆在当前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0]孔子作为我国编辑的鼻祖,第一次将“述”与“作”两种文化活动作出了明确区分,并对“述”的原则、导向和风格作出了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孔子的编辑思想及其编辑实践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孔子的编辑思想是新时代编辑工作者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对新时代文化活动和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告往知来”: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编辑活动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是人类的创造。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是源于中华文化的代代相传。在中华文化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编辑活动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21世纪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历史时期,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海量信息的不断涌入,市场经济的日新月异,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不断变化,把编辑活动推入新的历史阶段,编辑工作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就出版工作而言,“告诸往而知来者”,传承、发展和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是新时代编辑活动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新时代的编辑要通过自身的工作使受众正确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要激发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他们充分感受到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的魅力,并深深爱上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华优秀文化。
(二)“垂世立教”: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编辑工作者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也与孔子“垂世立教”的编辑思想一脉相承。不管是过去和将来,编辑工作都承担着国家、社会所赋予的文化服务社会的责任。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1]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者要善于提炼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使“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发展,产出更多内容、形式俱佳的时代精品,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资政的功能,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挥出版领域的传播和服务功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择善而从”:文化选择与审美判断
文化选择与审美判断是编辑的基本功,贯穿于整个编辑活动的全过程。孔子“择善而从”的编辑思想在新时代的运用,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时代的“善”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编辑者个人的道德坚守,也是作为时代编辑工作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选择和审美判断。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者只有多出版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化产品,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社会舆论,引导和教育广大受众在新时代“择善而从”,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辉煌业绩。
①故事记载在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帛书《易传·要》中。
②朱熹等解释为“如果钻研异端邪说,那么危害就大了”;杨伯峻等解释为“批判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