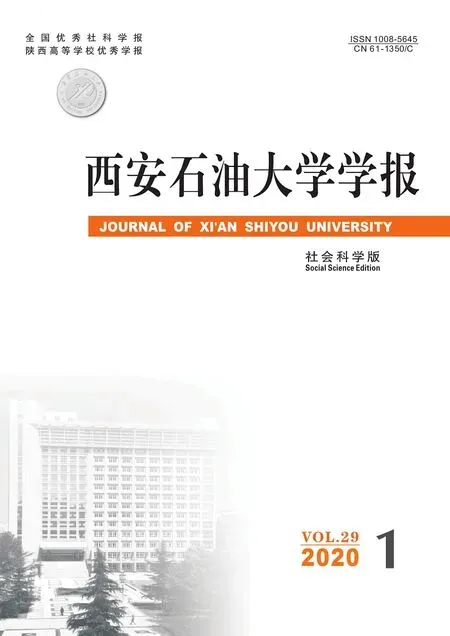“风骚”还是“艳情”
——论李商隐无题诗多维解读成因
2020-12-09雷晶晶
雷晶晶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0 引 言
“风骚”与“艳情”是古代文论中常用的两个术语,代表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诗歌传统、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然而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风骚”还是“艳情”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1]22,元好问一语道破了玉溪生诗的朦胧特质,同时隐含了读者必然会为其作出多种“郑笺”的反应。在一千余载的接受史中,读者对无题诗大略有两种读法。“一种基本上是就诗论诗,一种是将这些无题诗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诗联系起来,加上自己的想象,然后对它们作出小说化的阐发。”[2]71前者虽能够紧扣题面,避免穿凿附会,却难免沦于窠臼,或失于肤浅;后者启用联想、考据本事,虽能够独备一说,却总会陷入索隐猜谜。当两种解释方式聚焦于同一首无题诗时,便见仁见智,怅叹“一篇《锦瑟》解人难”[1]24。实际上,这两种阐释方式分歧的核心在于李商隐的无题诗究竟有没有比兴寄托。显而易见,后者否定了无题诗中比兴寄托的运用,并将其缀合成为李商隐个人的艳情史。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李商隐无题诗文本本身的特点,尤其是在绮艳题材的无题诗中,“风骚”还是“艳情”的争议愈演愈烈。其实,这恰是李商隐无题诗不同于传统准无题诗之所在。本文拟就李商隐无题诗的美学特质进行探究,分析李商隐绮艳题材无题诗的新变,剖析其多维解读成因。
1 李商隐无题诗理论划分概况
探讨李商隐绮艳题材的无题诗,首先需要确定在其诗作中哪些诗属于无题诗。杨柳在《李商隐评传》中根据题目形式将其分为以下四种情况:题目标明《无题》者共二十首[3]391;以开始二字(或三四字)为题者共四十五首[3]392;取诗篇中间或结尾数字(多半为二字,间有一、三、四字)为题者共二十六首[3]393;其他如《漫成五首》、《偶题二首》以及《鸾凤》(“旧镜鸾何处,衰桐凤不栖”)等凡八首,共计九十九首,约占总量的六分之一。从题目形式上确认无题诗的范围,是在综合考量诗的内容与题目的关系中做出的更为通达的结论。在这九十九首无题诗中,要进一步确定绮艳题材的范围。根据余恕诚提出的绮艳题材的内涵,“除男女之爱、闺情、宫怨者外,还包括带有爱情脂粉气息的咏物、写景与描绘绮楼锦槛、歌舞房闱的题材。”[4]21这就进一步明确和聚焦到李商隐最具争议的无题诗。
然而,在这些绮艳题材的无题诗中,从思想内容上看,确有世所公认的、没有寄托的、实属狎邪的诗篇。刘学楷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明确标有《无题》的诗篇中,从寄托的有无显隐这一视角,将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无题》诗分为三类:寄托痕迹比较明显的,譬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八岁偷照镜”“照梁初有情”等篇,此其一;寄托痕迹不明显,处于疑似之间的,或虽有一些寄托痕迹,但寄意颇难捉摸的,譬如“凤尾香萝”“来是空言”“飒飒东风”,此其二;没有任何寄托的,譬如“长眉画了绣帘开”“寿阳公主嫁时妆”,这一类或戏为艳体,或实属狎邪,此其三。[5]40-44这一视角使思想内容驳杂的《无题》诗有了初步的整理,对进一步探讨无题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上有开拓之功。但在具体探析过程中,仍尚存争议。譬如《四库全书》“提要”便指出“《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6]634,而《李商隐的无题诗》将“来是空言去绝踪”一篇归于其所划分的第二类。即此说明李商隐绮艳题材无题诗的性质特征和美学特质实有探讨空间及探讨之必要。戏为艳体、实属狎邪而没有寄托的无题诗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 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
李商隐绮艳题材的无题诗往往汇具体与普遍为一体,融形象与抽象为一炉,集叙事与抒情为一身,这是造成李商隐无题诗“风骚”还是“艳情”争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构成李商隐无题诗美学特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7]81
表面上来看,这首诗似乎叙述了一次艳遇而始终不能结合的故事。既有明确的时间(昨夜)、地点(画楼西、桂堂东),又有具体的场景(隔座)、活动(送钩、射覆),鲜明的生活质感使得这首无题诗充满了叙事的意味。不过“诗的叙事与一般日常叙事不同,虽曰叙事,抒情也就在其中了。”[8]37且看春风淡荡,月影斑驳,于画阁桂苑之间,人生初逢恰彼此倾慕。接下来娱乐场面的欢畅、暗寄情思的美酒,“暖”的生理感受与“红”的视觉色彩,既促成了两人的情感温度陡增,又是这种微妙心理的外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催促一方奔赴兰台的鼓声中,两人幽微脉脉的情思倏忽被斩断。流逝的一切又复归热闹本身,只是酒暖烛红的场景已不在,绵邈的情思却汩汩涌来。时间线索的步步推移,空间变化的循序渐进,线性的叙述结构使得事件完整自足,情感的起伏变化亦随之层转层深。
描叙语言的详细与抒情语言的细腻进一步加深了叙事的成分,深化了抒情的意味。譬如“画楼西畔”“桂堂东”“隔座送钩”“分曹射覆”,这些详细的描叙语言,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形象画面,从而避免了概念性情感的空洞铺陈;抒情语言的细腻,在叙事的逻辑推进中,情感的抒发按诗人创作意图进行联想、引申和探索。“昨夜星辰”中初见的陌生、知遇的激动、语言缺失的阻隔、眼神交汇的共情、隔座的疏离感、送钩的共通感、鼓声的突发性、离开的失落感在诗人的叙事安排下渐次生成。描叙语言为抒情语言提供了感发的基础和载体,使情感具体化;抒情语言在描叙的敷衍中有了附着与张力。叙事因素在抒情中成长,抒情成分在叙事载体上扩张,“叙”“抒”紧密无间,无分主次,既能梳理出匀畅分明的脉络,又能铺排出徜恍绵邈的情境,虽深邃却绵密,虽朦胧却空灵,从而将流荡与蕴藉结为一体,把跌宕与隽永融为一炉。叙事与抒情交融互渗,相互成全而臻于化境,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此达到高度的和谐。
诚然,李商隐是一位抒情诗人。叙事在诗中的功能表现为辅助情感的感发。诗歌的创作意图和表现内容密不可分,同时二者的特殊性又促成了李商隐无题诗朦胧多义的审美特质。就表现内容的特殊性而言,叙事的模糊与细节的典型为诗歌提供了多义的可能性, 情感的层进与警语的恰切镶嵌进一步加深了该诗多义解读的基础。在《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 李商隐从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视角出发, 通过几个典型细节的描叙, 譬如时间(昨夜)、空间(画楼、桂堂)、主要事件(隔座送钩、分曹射覆、听鼓应官), 构成了诗歌的叙事主体, 典型情节的叙述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始末。然而叙事的核心与事件的行动元——人物, 即“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对对方的模糊性描叙, 譬如首联点染相约地点的风雅, 然未及对方之状态;颔联强调二人心灵之契合, 而未言伊人之身份;颈联雕绘气氛之协谐, 却搁置美人之形态;尾联勾勒离席之黯然, 但不及佳人之行动。对核心人物的省略留白使叙事内容有了多方填补可能, 然清晰无疑的情感脉络在典型的叙事细节中被生动传递,从而能够让读者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需要进行再创作。这种“不注重容貌、体态、服饰、举止等方面的描绘和刻画”,“而着力发掘和烘染情爱相思的内在心理,展现人物的各种心态”[9]361,“深入地体验心灵的美丽和意境的澄鲜”,“侧重于神思的悠远和意态的秀逸”[10]3,强化了风教与风情的分歧,进而影响着读者可能解读到的诗中情感抒发的走向。这种模糊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同样杰出的无题《锦瑟》中。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7]220
考据本事亦或觅求兴寄的接受思路影响着诗歌的“风骚”还是“艳情”的解读结果。然而在《锦瑟》中,叙事的充分模糊似乎打破了传统的接受路径,以致读者从多个角度找到的所能解开“锦瑟”的“密码”似乎都是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锦瑟》中的隐喻手法是模糊叙事的重要手段。隐喻性处理在《锦瑟》中将具体的叙事化解成为庄生梦蝶、望帝春心、沧海珠月、蓝田玉烟般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叙事)是无法坐实到具体的哪一件事上的;同时,“因为隐喻式的表达,‘华年’不再是一个被抽象认知的时间判断,而是一个个‘事件’及此事件经历的心理或意识活动本身。”[11]124在这里,事件的特殊性被强调,而事件激起的反应却具有某种普遍性,故读者能深切感知到《锦瑟》中表达的情感的真切细腻,即由庄生梦蝶等事件引发的情感及其意义,能够激发起读者对自我类似既往的观照,并具有了结合李商隐的人生经历对此诗作出多方面合理解读的可能。
《锦瑟》中作为目标域的“华年”是庄生与蝴蝶的迷梦,是化作啼血杜鹃的望帝的春心,是明月下沧海边鲛人的珠泪,是玉田上日光下不可把捉的云烟。迷梦、春心、珠泪、云烟这四种现象就是独属李商隐的人生阅历,而读者在阅读中既经历着李商隐独特的人生阅历,也体验着这些独特人生阅历中的情感。“至于它们可能暗示的李商隐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知晓也无知晓的必要,迷梦、春心、珠泪、云烟的经历已经足以让我们感知到诗人华年里的复杂、迷茫的心思。”[11]127在《锦瑟》中,诗人自己充当叙事者,对所涉事件或人物进行经过心灵折射的“平铺直叙”,且多用典故隐喻等间接手法来叙事传情,刻画人物缺乏动作,推进事件隐匿冲突,故此形成《锦瑟》叙事的内视化与主观化倾向。诗人说得典雅委婉,予现实本事“不着一字”,而读者尽可领略其中大意,得其情意之“风流”。这一张古老而美丽的锦瑟,咏物、咏事皆咏怀,随着心灵的起伏,响起凄婉沉郁的节奏,表现出李商隐晚年坚贞自葆的高洁风标和意蕴深微的晶莹肌理。叙事的模糊与情感的真切最终使得具体的事件及其情感上升为一种对某一类普遍世态的描绘及其引发的感悟。
明确的生活场景使得无题诗充满叙事的意味,叙事的明晰使情感的抒发具有了层次性和内容性;叙事中隐喻手法的运用模糊了对具体事件的指证,叙事的模糊性消解了对个别事件的纪实可能,情感在叙事的模糊中具有了类的普遍性和虚阔性。叙事乃文学叙事,是基于现实而不拘泥于现实的艺术的真实;抒情是缘事而发、为情造文的人生遥慨,是人性的真实。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使得对绮艳事件进行记录的艳情说与以其托喻而抒发君子慨叹的风骚说在此进一步模糊。
3 “异质同构”下的心灵世界——“士不遇”与“女失时”的心灵书写
叙事与抒情的完美融合是李商隐无题诗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这种艺术手法及读者解读的现实基础则是李商隐复杂的社会人生背景与其幽微深邃的心灵世界,以及“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文学传统、中正平和的审美追求。正是在现实基础的作用下,李商隐无题诗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再次强化了“风骚”与“艳情”多维解读的可能。较为典型的譬如《无题》(凤尾香萝薄几重):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7]228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有感》)是“士不遇”主题的生动注解,在绮艳题材的无题诗中,“才命两妨”的兴叹也可以经由“碧文圆顶夜深缝”的情爱不畅表现出来。其机枢就在于,“士(忧虑)不遇”与“女(忧虑)失时”的心理共通性是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根由。这种心理共通性具体体现在空间的阻隔、时间的流逝、此际的孤寂、前路的未知四个方面。“凤尾香萝”中,女子深夜缝制罗帐的情景说明其与所欢分隔两地,同时暗示了佳人此际的孤独寂寥。“羞掩面”、“语未通”以及颔联的“断无消息”再次说明了因某些原因错失机会而始终不能相见的空间阻隔。“金烬暗”一方面说明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也成为佳人从深情期待到失望感伤的心理外化。然而对未来的热情期盼又冲淡了此际的孤独寂寞,“斑骓”指欲归而尚未归之人,佳人设想所欢并不遥远,只等西南风送他回归身边。“这样,痴情的佳人在经历了一番失望之后,心里又转生一念,再次天真地开始期待了。结尾仿佛回到了起点,甚至比原来更有信心。”[12]249-250类似的结构同样体现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上。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7]201
“蓬山”意味着天上与人间的空间阻隔,“云鬓改”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夜吟”“月光寒”是此际孤独心灵的表征,而“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又是对未来的无比坚定,“青鸟”正是希望之所在,前路之如何,良人正满怀期待。
艳情诗的四个要素也可以同样存在于干谒诗中,故对《无题》(凤尾香萝薄几重)和《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理解也可以是“士不遇”主旨。当李商隐陷入党争屡遭打击,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干谒而无门时,这种由于地位差异而带来的阻隔感便加深了与所托之人心灵上的空间距离;长年累月的辛苦奔波却仍旧为生计而寄人篱下,当下的逆挫感与寂寞感,以及对老大无成、仕途无望的哀颓感,造成士人对时间白白流失的深深忧虑,这与佳人对青春不再,虚度年华的迟暮感是一致的。士人一次次努力想要抓住机会,希望的明灭闪烁给他带来坚定追求的信心,只待好风、勤为探看的动作成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当种种挣扎最终都陷入绝望的深渊时,“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感发便自然发生了。至于这坚定与颓败、积极与消极交织的背后究竟包蕴着怎样的事实,无题诗是不屑于再现这些琐事的。因为“一首抒情诗中根本不存在真正叙事意义的情节,它只呈现某种情境,某种情绪或意向,过多地把它与诗人的事迹拉扯到一起,只会降低诗的素质,乃至扼杀它的感发功能。”[12]250
除上述诸要素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李商隐无题诗中共有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是李商隐“不遇”与艳情诗中“女失时”的共同底色。然而,不同于战国时期屈原不遇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离骚》)的深沉真挚;不像西晋时期左思不遇时“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的愤世嫉俗;也不似盛唐时期李白不遇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放浪不羁;在“沧海月明珠有泪”“一寸相思一寸灰”“走马兰台类转蓬”中,无奈和无力的感伤笼罩、浸淫着李商隐的笔端心头。以“感伤”的风格表达“不遇”的心境自然与晚唐的末世情绪有关,而更加直接、具体的影响当然还是在于李商隐的生平遭际,以及诗人的一种自我选择。如吴调公言,同处中唐和晚唐文学交替的时代,“杜牧把作赋论兵和听歌纵酒集于一身,怀着跌宕坦率的豪情,唱出十载扬州的绮梦;而李商隐却是那么执着而惆怅地留恋着乐游原上的夕阳,绵邈而深沉地弹奏着那象征华年如水的锦瑟。”[10]1不同诗人的个性气质从多个侧面折射出同一时代不同群体的多元风貌,同时具体的诗歌中也缩印着个体诗人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思想,因而哀艳感伤的无题诗就是忧戚哀怨的李商隐。这种感伤情绪一则或与其早年于玉阳学道相关。道家强调对个性的泯灭,从而达到消除矛盾痛苦的目的,因而无题诗中能够表现出诗人将内心矛盾淡化后,外化而成为淡淡的忧伤。二则或是由于李商隐仕途坎坷近乎无望,于是也便在其诗中显示出了安于岑寂、追求安稳的另一人格。这种哀伤的心绪和人生的无力感就成了无题诗的主题,也成就了无题诗中正平和的审美趋向。落拓无着的李商隐,“面对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敏锐有余而分析不足,只将大体的意绪泛泛地表述出来,形成了朦胧的审美世界。”[13]210于是,诗人在人际疏离或情爱不畅的情境中就有了共同的感伤色彩。情感取向的一致性,加剧了表现情爱与仕途的相似性。
4 “风骚”与“艳情”的完美融合
“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14]18形式上沉博艳丽,内容上深情绵邈是李商隐无题诗的显著特征。艳丽的外衣与深情的内核勾连出的是中晚唐时期文学的三大走向:“一、爱情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二、追求细美幽约,补救韩、白的发露直致;三、重主观、重心灵世界的表现。”[4]21李商隐不会不受时代文学风气之影响,因而无题诗中绮艳题材的选择确有其时代背景。但是,李商隐并非热衷于绮艳题材的书写,绮艳作为契机、作为触媒,作为一种流行的元素,在无题诗中呈现出了另一种新的境界。
4.1 风骚精神中纤柔圆融的特质
贺裳有云:“义山之诗妙于纤细。”[15]356“纤细”不仅体现在李商隐诗的情感深微绵长上,同时也体现在表现这种情感的意象选择上。除了上述提到的之外,再以《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为例进一步说明。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7]233
刘学楷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评价“飒飒东风”是“一身而兼二任”,既有艳情闺思,又有身世之慨。总体上讲“飒飒东风”是与爱情相关的诗,而在末句又融入了诗人的身世之叹。故解读时既不能附会于幽隐的情事,也不必穿凿具体的身世,而应灵活把握,要“允许艺术鉴赏与评论按照客观存在的复杂情况去感受、分析。”[4]46“细雨”之温润,“轻雷”之柔婉,香雾之袅袅,轳绳之悠悠,透过诗人心下这些意象细小圆融的美质,能够捕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纤柔和婉。即使在绝望处,也依然没有晦涩或直露的表现,“一寸相思一寸灰”下隐匿着的伤痛,宛若平静海面上,远处的一角冰山,似有还无。“情深于言,义山所独。”[16]23这是李商隐学杜甫而不同于杜甫的最突出所在。试以“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与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17]252比较:一轻盈纤长,情感深挚、幽微;一场面宏阔,情感博大、坦露。个中原因一则因盛、晚唐的时代气质已然不同;再则李、杜二人的身世遭际不一,这两点深刻影响着二人的个性气质与人生选择;“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杜甫一心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7]33,开放向上的时代环境是杜甫修、齐、治、平思想的有力支撑;而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7]271的哀颓时世,身陷党争囹圄而一生穷愁落拓的李商隐,虽“正直而不免软弱,关心国运却又常沉溺于个人命运”[18]52,多愁善感、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其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般的和谐匀调,清丽圆融是李诗在感时伤世时的特质。
4.2 艳情趣味里真切遥深的品格
爱情与绮艳题材在诗中的增长,齐梁声色在晚唐的回归表现在李商隐诗中,并不是对前代艳情文学的单调重复。在艳情趣味的镶嵌下,情感的真切遥深超脱了对脂粉艳情的勾勒,表现出人生普遍的情境。试以温庭筠代表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与李商隐的“来是空言”比较: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峨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9]3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的闺情主要通过女主人公的居住环境、神态动作、服饰外貌来表现。“男子而为闺音”的词作是把女性按照士人美的理想放置在一个封闭幽禁的环境中,以其境之清绝、其态之娇娆达成文人好色心理的满足。从女性主义批评出发,可以看出“他将女人看作诗,极尽赞美之能事,但他仍将女人作为另一性,在他眼中,女人是真,美,诗——她就是一切,在那另一个形式下的一切,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20]189艳情趣味在此成为文学全部的表现对象。而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中,已然有大不同。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7]232
《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已经脱去俗脂腻粉,转而进入人物内心深处。在动作的推进中,现时的抱怨与寂寞,梦中的伤悲与疼痛,手书的焦急与不安汇成情感的洪流。烛影绰绰,纱帐盈盈,时间仿佛在此际凝滞,无边的春愁弥漫了整个空间,于是一切的描摹都成为心境的再现,情感的表露。“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的呼唤与叹息成为人生困境中人的共同心声。“蓬山”之境已非人间,“蓬山”之憾却永存心间。在“来是空言”中,人间天上互通有无,“刘郎”之恨贯穿始终;“蓬山”婉丽迷离的色彩开拓了情感的表现空间;空际转身后扑朔无望的境况呈现了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情爱的忠诚与志意的不渝和谐共通,为情造文的无题诗渗透着诗人敏锐的心灵感知力与高超的艺术把握力。
以上,风骚精神中纤柔圆融的特质,艳情趣味中真切遥深的品格,二者两面一体,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诗人能够“把体验自己情感和外在事物的精切,同‘韵外之致’结合起来,把刻镂深细的形貌和意在言外的韵味结合起来”[10]12,从而使其无题诗既有别于香奁诗庸俗琐碎的描头绘足,又使忧愤激切的个人感兴增加了缠绵摇曳的风姿。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风骚的精神与艳情的趣味臻于融合,从而开辟了诗学中的新境界。其一方面构筑了李商隐诗美学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无题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地位。
要之,“风骚”还是“艳情”争议的解决最终在对无题文本的观照下得以实现。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促成了无题诗美学风格的形式艺术;“士不遇”与“女失时”的心理共通性是形成无题诗美学特质的内在动因;风骚精神与艳情趣味的融合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开辟的新的诗境,至此,古典诗学发展至最后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