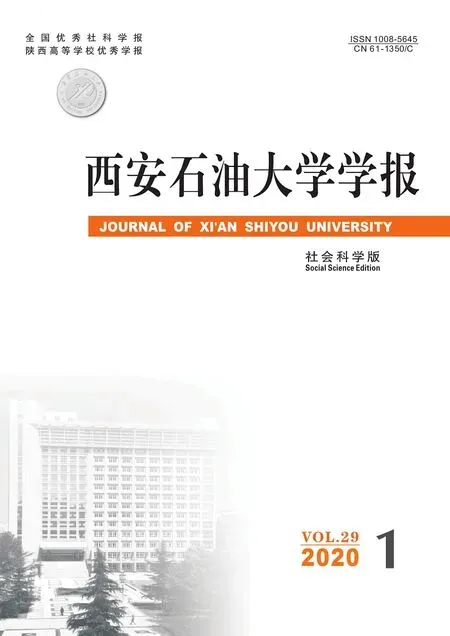承接与嬗变:《文心雕龙·隐秀》与《周易》爻辞研究
2020-12-09陈沁云
陈沁云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0 引 言
《文心雕龙·隐秀》存在补文真伪问题,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一。万奇等认为:“很多龙学学者,如黄侃、范文澜、杨明照、刘永济、王利器、王达津以及周振甫、牟世金、祖保泉等人,皆从纪昀之说,认为补文为后人伪造。当代学者詹锳,经过深入考察研究,力排众议,在1979年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真伪问题》一文,指出补文是宋版原文,不容置疑。”“关于补文真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由于《隐秀》篇脱落文字太多,还需要深入细密研究,或者有新的史料发现,才能明其真伪。”[1]233-234也就是说就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对此有统一的结论,所以本文对补文真伪不加以讨论,只对《隐秀》的文学艺术性进行研究。
1 承接:《文心雕龙·隐秀》与《周易》爻辞的“隐”以载道
毫无疑问,《周易》是《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著作的思想本源。戚良德教授亦指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易传》的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2]47《文心雕龙》全书一共有21篇直接论述到《周易》,该书既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哲学,又将其中的典故作为例子来证明其理论观点,可见《周易》对《文心雕龙》具有指导性作用。戚良德教授之论无疑是切实的。《隐秀》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篇章就承接了《周易》爻辞含蓄蕴藉的创作理论。
1.1 《周易》爻辞之含蓄蕴藉
《周易》爻辞乃是帮助理解的工具,用来解释卦象,但其具有局限性,即无法穷尽卦象之意,故象与辞需要配合帮助理解,也正因如此,让读者产生无穷想象。《周易·系辞上》第十二章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3]326《周易》的爻辞用来解释卦象,卦象即是图像,阴阳关系、世间规律变化皆在其中,为《周易》这部经书的核心内容,但因其变化复杂,意蕴无穷,所以语言难以穷尽卦象之意。故《周易》爻辞用带有意象的文辞来解释卦象,并且以比喻、寓言和想象等多种艺术方法来帮助阐释。这些文辞大多简洁、精准且生动形象,可以将读者带入其中,引发无限想象。
《周易》爻辞利用意象对卦象进行解释,其意象清晰,寓意深藏于意象之中,虽字数不多,但所用之字皆精准,充分涵盖所要表述的内容,虽简单隐晦却蕴含着无穷的意义。
1.2 《文心雕龙·隐秀》对含蓄蕴藉的理论承接
《文心雕龙·隐秀》承接了《周易》爻辞含蓄蕴藉的创作方法,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故《隐秀》开篇就强调文章创作不能将创作意图浮于表面,提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4]373其认为文章创作应有文外之意,需含曲折重复的思想,且对“隐”的意义和特点进行诠释:“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 ”[4]373《隐秀》用卦象“互体变爻”为喻来阐释此类文辞变化之特点,认为含蓄蕴藉的创作方法可以将无穷无尽的变化藏于文辞之中,此处即是受《周易》卦象和爻辞的启发,意欲说明看似普通的文辞其实内含乾坤,可窥探到文外之意。若想要表达深远的立意就一定要做到“隐”,大道隐于文辞,好比内藏明珠,外现光润,反复阅读,文章意味深远,令人玩味无穷。此处即在肯定隐晦的创作方法,认为含蓄蕴藉之法即可将文外之意创造出来,而文外之意可让文章充满意蕴。下文又阐述含蓄蕴藉文章创作的艰难性:“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煅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4]375将新奇的立意藏于文辞之中,实乃大师之作。在文辞之上,仍有含义,并且意味深远,耐人寻味。这种优秀的文章对写作者有较高的要求,创作者需冥思苦想,经历世间沧桑,深知天地万物周而复始之变化,真正悟得自然之道,经年累月,对立意进行反复推敲,才能创作出来。如果文章直言不讳,一语就说破所有的立意,则过于肤浅,不值得深追。含蓄蕴藉,立意深邃的文章必然有其自身的变化,且此等变化无穷无尽。所以《隐秀》最后总结道:“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辞生互体,有似变爻。”[4]378这样的文章方可承载变化,且韵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
《周易》的爻辞简短而含蓄,深邃立意藏于文辞之中,在有限的内容下隐藏着天地之间的规律,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其爻辞可多方位进行理解,且阐释的规律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周易》爻辞是含蓄蕴藉创作方法的源头文本,《文心雕龙·隐秀》作为文学理论篇章,承接了此类创作方法,认为隐晦的文章可载无穷之道。刘勰将含蓄蕴藉的创作方法划为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嬗变:文章艺术价值的革新
《文心雕龙·隐秀》充分肯定了《周易》爻辞含蓄蕴藉的创作方式,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文学理论观点。《文心雕龙》对《周易》爻辞的艺术性略有微词,故《隐秀》在其含蓄蕴藉的基础上,要求文章需“秀”,同时对写作者和读者提出了要求,认为作者需要创作出具有吸引力的文章,读者也需要有高深的学识和理解能力,才能达到两者的共鸣,从而真正实现文章的艺术价值。
2.1 《文心雕龙》对《周易》爻辞文学艺术性的认可度述略
正如上文所言,《周易》是《文心雕龙》的思想本源,而在文学艺术层面它亦给了《文心雕龙》较多启发。事实上仔细观察可发现,刘勰对《周易》的选择有侧重,在《隐秀》篇中亦可发现这样的特点,所以在此篇中他更加强调“文辞秀彩”,重视文学艺术性。《文心雕龙》对周易的《经》和《传》两部分都进行了吸收,但各有侧重,在文学艺术层面,其更加倾向于《传》的理论思想,而对《经》的爻辞略有微词,运用相对而言较少。
《文心雕龙》全书一共有21篇引用了《周易》中内容,其中《经》一共6篇,《传》一共11篇,另有《原道》、《征圣》、《附会》和《诏策》4篇是两者皆有。重点阐述文学艺术的篇章多以《传》中的内容为例证来证明观点,《通变》、《熔裁》、《丽辞》、《比兴》和《夸饰》皆是如此。如在《丽辞》中讲述对偶时曰:“《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4]335此处用《文言》和《系辞》中的文辞对偶为例来说明文章创作时采用对偶创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可以使得文章变得更加精密,更加富有韵味。文章对偶即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艺术方式,刘勰在讲述这个理论的时候,极其推崇《传》的文辞对偶,故以此为范本。反观以《经》爻辞为例的文学理论文章,如在《声律》中曰:“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4]322“往蹇来连”出自《周易·蹇卦》六四爻。该篇讲的是如何运用声律以及声律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上述这句话意在说明不会声律而要作好文章极其困难,犹如文人患了口吃。此处用爻辞举例并不是用来说明文学理论观点,只是借用“蹇”这个字来形容困难的意思,无文学层面的解释意义。
刘勰更有直接讨论《周易》爻辞晦涩难懂之处,其在《宗经》中指出:“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4]42他在充分肯定《周易》哲学思想的同时,用《系辞》中的原文来称赞《周易》文辞精美,含意深远,只不过部分说理明事的文辞晦涩难懂,较难理解。从中可以看出刘勰既引了《系辞》中称赞的话,也用了其中批评的话,并未因推崇《周易》而删减批评的内容,其对《周易》爻辞的态度还是较为中正的。
《文心雕龙·隐秀》亦是如此,在讲述“隐”的时候引用了《经》的爻辞,但在重点阐述“秀”的时候却未将爻辞作为例据,而是大量引用了两汉魏晋的作品,如嵇康的《赠秀才入军》、阮籍的《咏怀》以及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等。《文心雕龙》对《周易》如此推崇,《隐秀》的文论思想又与《周易》如此紧密,既承接了含蓄蕴藉的创作理论,为何在言及文辞时不以爻辞为例?若是言爻辞中没有可以用来作为例子的文辞,那是有失偏颇的,但部分爻辞不达“秀”之标准应该是确实的。也就是说刘勰认为《经》的爻辞虽然整体精美,但部分文辞过于艰涩,这也可能是导致刘勰多选《传》而少择《经》的一个原因。
此外,从中还可以看出刘勰更欣赏《传》文辞的艺术性,他在《传》中找到了优美的文辞,并发现了其中的文学规律,故以此来作为理论证据再合适不过。刘勰虽然对《经》的爻辞使用没有《传》这么多,但并未对其完全否定,只不过相对《传》来说,《经》在文辞艺术方面确实略有不及。刘勰从根本上接受的还是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周易》,儒家解《周易》之后的思想,也是儒家对文章艺术的要求。《文心雕龙·隐秀》大谈“文辞秀彩”即是对《周易》爻辞文学艺术性的补充,“道”之大不用再言说了,但粗枝大叶的“文”也承载不起大“道”,故对文辞提倡艺术是必须执行的。
2.2 文章秀彩亦为文章之根本
《文心雕龙·隐秀》第二部分谈到“秀”,文章创作需秀彩,即在文学艺术层面对文章提出了要求,将“文”与“道”上升到同一个层面,以平衡两者的关系,强调文学艺术的重要性。
2.2.1 “秀”乃文辞自然天工之美
《周易》爻辞虽含蓄蕴藉,立意深远,但部分简短晦涩。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文章的创作需文道并重,新奇立意固然是文章安身立命之根本,但如果没有秀采的辞藻仔细雕琢来阐释表达的话,其文章艺术价值难以到达较高的水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风雄起,风骨盎然,文章创作者对于文辞的要求越来越高,骈文也盛行于这个时代。《文心雕龙》虽为文学理论作品,但其本身就是骈文,骈文以四六句为主,讲究对仗,工整,对声律和文辞音韵等有着严格的要求,且行文思路清晰,对偶得当,多处用典来说明问题。《文心雕龙·隐秀》在肯定《周易》爻辞含蓄蕴藉的基础上,对文辞表达提出了要求,文辞秀采挺拔是文章创作必须具备的,其应与内容处于同样地位。
在《文心雕龙·隐秀》中亦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对于文辞秀采的重视,其在《隐秀》中指出:“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4]373即文章创作既要有大道之“隐”也要有辞采之“秀”,两者结合方可构成完整的文章。刘勰将文辞华美视为文章创作的重要环节,将文辞秀采提到与含蓄蕴藉的创作之法同样的高度,体现出文辞创作的重要性。关于《隐秀》的“秀”,在文章第一段中其指出:“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4]373“秀”乃文章之中突出挺拔的辞句,可以作为全文最精彩的文辞,将创作者才华显露无疑的文辞,此类文辞不可华而不实,而是应自然巧夺天工,以体现出文章自然之美。后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彼彼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女农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4]374这段话亦是在着重强调文辞之美必须是自然的,不可妄加人工修饰,亦不可华而不实。只有通过悟“道”而形成真实的感悟从而产生发自内心的文辞,才称得上是秀采英华。对于好文章的定义,其在下文指出:“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4]378以自然界的花朵和染色的丝绸作对比,意欲表明花朵美得自然,而丝绸美的世俗,故好的文章就是花朵,自然而芬芳,无人工修饰的俗气。《文心雕龙·隐秀》对文与道同时进行论述,并没有忽视文辞的作用和文学的艺术价值,指出文辞的精妙也是衡量一篇好文章的关键。
《周易》的爻辞意象众多,立意深远,但部分文辞仍过于隐晦,从而影响了其文学艺术性。《文心雕龙·隐秀》在肯定《周易》爻辞含蓄蕴藉的基础之上,做出了嬗变,即对文辞提出了要求,认为无论是何种文章,都不可忽略文学艺术性。优秀的文辞可以提升文章深度和表达力度,从根本上提升文章的文学艺术性。含蓄蕴藉之文必然具有较高的哲学义理在其中,但只求“隐”而忽略文辞,势必会让文章呈现出空有骨架的枯涩之状。文辞秀采无疑是《文心雕龙·隐秀》在先驱作品《周易》爻辞上的艺术提升。
2.2.2 “秀”乃文辞警策之美
对“秀”的训诂除文辞秀彩、自然天工之外,另有警策。吴林伯在《文心雕龙义疏·隐秀》篇中指出:“曹魏张揖《广雅》:‘秀,异也。'异者,特出而不凡,本篇称文辞之警策。”[5]762吴林伯先生认为“秀”除文辞秀彩外,还有文辞警策之意,并认为刘勰提出文辞警策实因现实而致,故“秀”含警策之意不容置疑,他指出:“魏晋以降,王室倾轧日剧,家家思乱,人人自危。明智之士,莫不悼国伤时,不能自静,因兹发咏……且作者‘偶俗',摛文不免‘淫丽',‘虽美非秀',彦和为此而论隐、秀。”[5]762吴林伯先生的看法是极其中肯的,刘勰论“秀”一方面是在阐发文学创作理论,另一方面是以论“秀”来纠正魏晋文坛之靡风,以警策中正之文辞来纠正绮靡文风是刘勰的文学理念。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隐秀》篇虽未直陈“秀”乃警策之意,但亦认为刘勰提出的“秀”意在纠正魏晋文风,并指出:“秀者,理有所致, 而辞效其功……若故作才语, 弄其笔端, 以纤巧为能, 以刻饰为务, 非所云秀也。”[6]185此处明确指出用字造句故作奇态, 语句纤巧绮丽不是“秀”, 所言“秀”者文辞需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不作无病呻吟。《文心雕龙》徐正英、罗家湘译注版亦将警策解释为“秀”的一个意思, 虽未在注释中直接阐明, 但其译文却阐发了警策之意。如译“句间鲜秀, 如巨室之少珍, 若百诘而色沮”[4]375这句话, 其译为“句子中间缺乏警句, 好像大户缺少珍宝, 倘使多问就神色沮丧”[4]376, 直接将“秀”译成“警句”。
从《隐秀》篇中可以发现,后来学者将“秀”解释为警策是符合刘勰本意的。且看《隐秀》篇中讲述“秀”时摘取的诗文,如《怨歌行》、《与苏武诗》、《伤歌行》以及王赞的《杂诗》等。这些作品文辞隽秀,语言自然平实,刘勰从中所选的词句皆为全诗的点睛之句,如“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4]377,表达了对战争的厌倦,以及希望结束边疆羁旅之行,同战马共同回归的愿望,从文辞之中可以体会出作者百感交集,非常无奈,全诗的感情皆集中在此句。文章在评论作品时指出:“公幹之《青松》,格刚才劲,而长于讽谕。”[4]376此处称赞刘桢擅长作讽喻诗,并且认为他的文辞风格刚健,才力坚劲,也就是说文辞之“秀”应该要包含刚健中正并且可以用来讽喻的警策辞句。刘勰举的例子皆是警策语句的代表,诗文因为有警策句子的存在而提高了艺术水平,使诗文充满了能量,振聋发聩,无绮靡柔弱之风。他将这样的感受进行了总结:“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4]379警策的语句是各种思虑交织的结果,其可以达到让人震撼心灵的效果,不同凡响。
《文心雕龙·隐秀》虽未在文中直接将“秀”作警策之解释,但事实上刘勰在文章中阐发的文意已经指明了作文含警策辞句亦是“秀”之要求。在魏晋文坛,绮靡之风盛行,而刘勰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所以其提出作文需用中正警策之句乃合情合理,意在纠正时代文风。
《文心雕龙·隐秀》在承接《周易》爻辞含蓄蕴藉创作方法的同时,提出作文亦需“秀”的观点。由于时代的原因,文章的文学艺术功能越来越被重视。《周易》爻辞历时已久,其部分爻辞的文学艺术性有一定的局限是无法否认的,刘勰在承接儒家传统易学思想的同时积极提倡文学审美艺术。文章之“秀”意在强调文辞艺术不可被“道”淹没或者忽略,同时刘勰将文学艺术发展引上一个正确的道路,积极纠正其在发展道路上的畸态,提出“秀”应该是天然形成,拥有巧夺天工之美,并且必须言之有物、中正警策,不作无病之呻吟,反对故作奇字和纤巧靡丽之风。
2.3 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共鸣
读者即接受者是文学的四要素之一,一部完整的作品由作者创作出来,但如果没有读者正确对其欣赏,那作品的价值也无法彰显出来。《周易》已历三千多年,只有当读者体悟到其中奥秘,才能实现这本著作的价值。刘勰意识到类似《周易》的古文本深奥艰涩,其中博大的世界非所有读者皆可悟到,因此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新的文学理论,即创作者需要作得好,接受者也要悟得好,读者需要一定的学识涵养,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故文章指出:“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4]374即含蓄的好文章内藏珍珠,慢慢阅读便会发现其中内有乾坤,并且变化无穷,自然而然就吸引了接受者的注意力。这是对创作者的要求,需要作吸引眼球的文章。对接受者而言,优秀的读者和庸劣的读者对优秀文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故言:“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煅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4]375创作者辛苦创作出来优秀文章,若接受者昏庸不识其中之奥妙,则只会迷迷糊糊,不知所云;相反慧眼识珠、学识渊博的接受者则会悟得其中之真谛,与创作者产生共鸣,就如同“高山流水”一般觅得知音。无论是含蓄蕴藉的文章之道还是秀采英华的辞藻,宽博深沉的接受者都可以悟得。最后又指出接受者识得优秀文章之后应有的反应:“动心惊耳,逸响笙匏”[4]379,即接受者在读完文章以后应该拍案叫绝,感叹文章对自身心灵的震撼。
《周易》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不识其妙者不进其门,初入其门者嗅得其味,深入其门者方知其妙在何处。其爻辞简约晦涩复杂,对于这类文本的接受,《文心雕龙·隐秀》认为接受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学识和一定的生活阅历积累,并且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能够仔细地研究分析,方可在字里行间发现创作者隐含的深意。文章指出优秀文本的最终归宿就是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产生跨时空的共鸣。《周易》爻辞虽然言不尽意,但是言不尽意的背后给予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其运用各种的艺术手法进行阐释,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将读者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将爻辞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规律,通过思考研究,进行探索挖掘,寻求真理。《文心雕龙·隐秀》不仅对创作者提出了文学理论创作的要求,同时力求将接受者和创作者放在同一个视角之下讨论研究,创作和欣赏同样重要。刘勰此论的提出不再只是文本创作这么简单,更是在将其系统化,文学四要素被全部纳入《文心雕龙·隐秀》篇中。在千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就意识到文学发展需要系统化、完整化,文学创作不应只局限于文本,作者、读者、作品、世界四要素的统一才能真正彰显文学的价值。
3 结 语
将《文心雕龙·隐秀》和《周易》爻辞放在一起研究,即是在窥探刘勰文学思想在继承儒家道统的同时作出了何种革新。《文心雕龙·隐秀》作为一篇系统的文学理论指导文章,吸收承接了《周易》爻辞隐晦的创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文辞秀彩的观点,即文辞之自然天工和警策中正,增强了文学艺术性。文章意在平衡“道”与“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皆是文章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文心雕龙·隐秀》对创作者与接受者皆提出了要求,认为创作者需作出具有吸引力的文章,读者也需要有一定学识积累,只有学识渊博、耐心研究的人方能在文本中洞察玄机,得到与创作者的共鸣,形成交流。《隐秀》既是在承接《周易》爻辞的文论思想,亦在从文学本源思考文章创作,力求发展提升。“秀”不仅是文学理论发展潮流中的必经之路,也是刘勰着力调整纠正魏晋绮靡文风的重要方法。《周易》爻辞经文学潮流的不断嬗变,其中的文论思想在《文心雕龙·隐秀》中得到了系统化的总结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