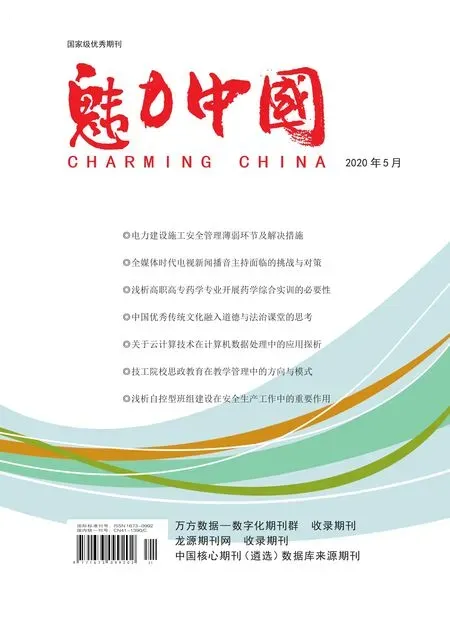关于《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身份认同的讨论
2020-12-08王铎振
王铎振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奥尔罕·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这种来自故乡的“呼愁”在一方面给予了他无与伦比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借助其笔触表现了一代人的迷茫与徘徊。莫言所说的“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如何作好定位的问题。
“身份认同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国籍或者文化)的表现。身份认同会因历史、文化和政治而改变。”而五海三洲之地,向来就是东西历史、文化、政治的交错地。可为何帕慕克对奥斯曼的情谊远远深厚于罗马帝国?他对于东西方的“征服”与“陷落”是否有一种潜在的看法……这其实都囊括在“身份认同”探讨中。因为对身份的界定间接地决定了归属感的去处。
一、助推西化的传统者:身份探寻
那些描绘伊斯坦布尔贫民区的艺术家,恰恰是站在贫民区之外的西化环境里去审视和喜爱它的。这点与帕慕克的无奈之语“西化,让我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得以把我们的过去当作‘异国’来欣赏”如出一辙。而书中每时每刻都体现出这种“矛盾”色彩,即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书中的故事大致可分为:对文化的讨论,如《四位忧郁的作家》;对废墟的思索,如《废墟的“呼愁”》;对自我的追忆,如《奥尔罕的分身》。其中对“矛盾”的直观反映体现在对不同身份的探寻之中,如:科丘究竟是一位东方传统文化的收藏家还是一位迫于生计的西化作家?
“这个民族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他们的虔诚把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一起拖垮。”她更像一个多文化混合体。在这种基础上,东方文化的内涵,自然不够稳固,她就像那位戴白头巾的老妇人;虽具神力,但虚无缥缈。这种文化特质间接暗示了东方传统的全面败退和消亡,但为何东方传统者竟是在为西化推波助澜呢?
首先,“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的事物,而我们当中的西化者却把相同的每件事物看作障碍,应当尽快从城市表面铲除。”这同时也是双向过程,本土人民对西化的观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纵容,而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因此产生了“呼愁”。其次,东方传统者的话语权是不足的,在这种博弈中,陷入迷惘的抗争者往往会滑向原来反对的那一端,或者陷入深深的怀疑。再次,即最直观的身份认同问题。那些在西化中暴富的人民,借助“我”母亲之口说出来的“这可不是巴黎,这是伊斯坦布尔……就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画家,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便反映了在这种畸形社会形态中个人发展受限的情况。“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他们必须去迎合那个西化的身份,才能获得一种合乎潮流的名正言顺。
二、逆潮流的“呼愁”:身份溯源
原文中作者对“呼愁”作了详细的词源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但无论如何,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呼愁”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一种溯源情感,并带有三个特点——集体性: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文化性:充塞于风光、街道与盛景的“呼愁”已渗入主人公心中;贫困性:“呼愁”源自他们对失去的一切感受的痛苦,但也迫使他们创造新的不幸和新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贫困。
讨论“呼愁”是不是逆潮流的旧时代哀叹,就要回到叙述本身。《光影伊斯坦布尔》讨论了拍摄的“无意”与“有意”。类似“呼愁”是一种旧时代“无意”的产物,但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家“有意”的指向。它象征着奥斯曼伊斯坦布尔对西化共和国发出的宣言,可比东方传统者的抵制更没有力量,但却更生生不息。作为一种集体上的文化感受,“呼愁”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宣示着城市记忆。每一栋旧式建筑的推倒,都带来一份新的“呼愁”,而每一份新的“呼愁”,都“是为一个衰落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哀悼的方式”。“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贫穷悲惨”,但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
三、另一个奥尔罕:身份凝固
奥尔罕是孤独的,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作为一个没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我”虽没有物质之虞,精神上却极度空虚。首先,受困于一个即将解体的旧式大家庭里,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西方的,这就与“我”眼里看到的贫穷与废墟是不符的;其次,父母不和,信仰缺失,最令“我”怀念的反而是那位从小打到大的哥哥;最要命的是“我”的志向与当时的社会风向严重不合,终致错失初恋。“我”最爱的本领不在于观察和画画,而在于能够自由地徜徉于自己构建的“第二世界”里。因此可以说另一个奥尔罕,就是那个孤独的“我”渴望成为的样子。
“对回忆录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叙述得准确与否,而是前后是否呼应。”同样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究竟能否得到身份认同感,而是在这种找寻中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因为伊斯坦布尔直接地与作者的创作生活连接在一起,所以这种主题反映了他作品里浓厚的文化寻根意识。然而帕慕克不是在文化寻根,因为他早就明确了“根”只能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在寻找一种能概括和反映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即身份。
地理和历史等维度上的身份,伊斯坦布尔业已拥有,但却仍旧没有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这就有了根,结果便是“呼愁”。那是伊斯坦布尔淡淡的忧郁色彩,也是她的身份:一个矛盾、忧伤的即将逝去的黄昏。然而作者却开始偏离既定的寻根路而走出了一条新路。西化要求他学建筑,他深爱的东方传统希望他画下这一切,最后他却选择了写作。尽管写作也确实是他书写的另一种形式,但他始终不忘绘画。书中大量的配图说明他希望展现的不是一个单薄的故乡,而是一个定格和凝固了的厚重黄昏。可奥尔罕未尝不是如此呢?他以儿童视角写下了传记,但此时已是土耳其的文学大使,这又是一种矛盾。
帕慕克不像日前刚恢复了国籍的米兰·昆德拉一样“只是说了句谢谢”,他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认识不到自己的身份,而在于在这种不断认识中深陷于种种矛盾和忧伤而渐趋凝固。伊斯坦布尔造就了“我”,“我”也回馈了最真挚的情感。只是最后的回忆并不能阻止这个帝国余晖的必然消逝,而深陷其中的作家总免不了带上这种深刻印记。
“但是在土耳其只会发疯”而伊斯坦布尔应该值得你我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