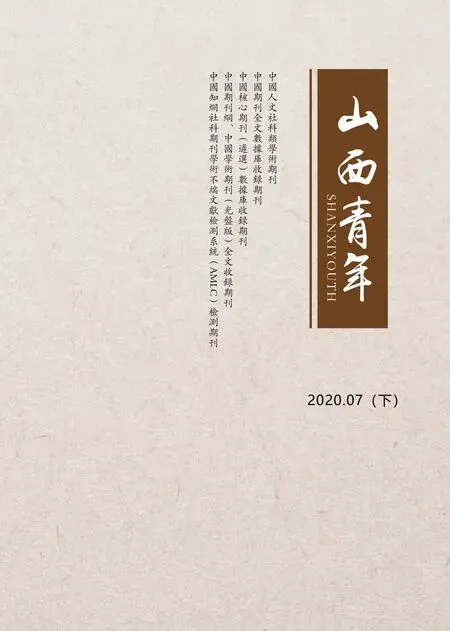浅析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
2020-12-08姚宗楠
姚宗楠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我国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指1949年建国至1956年三大改造全面完成这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社会阶级的问题上采取“边缘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开展,有其内在和外在的成因,也有其实施的特殊途径,这一政策,是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制的重要体现。实质上,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的政策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使民族资产阶级从思想层面上逐步温和的接受和平改造,而随着“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的逐步实施,直至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更加充分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在和平赎买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一、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的成因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身“发育不良”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界普遍认为始于明朝中叶的手工作坊,正式产生于两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60、70年代,它成长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在一战中得到了短暂的繁荣发展,而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被严重压迫,发展缓慢。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产生以来就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自幼便“发育不良”。尽管中国资本主义是受国外资本的外在刺激而产生的,但毛泽东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而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员内在构成上,也大多与地主阶级或与官僚脱不了干系,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地主阶级。尽管如此,民族资产阶级依旧实实在在的受到了这两重大山的压迫,在夹缝中生存,它在有些时期曾得到了短暂的繁荣发展,但始终没能像国外的资本主义一样“蓬勃”地成长。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自身“发育不良”使国家在过渡时期始终无法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历史证明,自身“发育不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只能依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逐步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历史进程中消失。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以及与资产阶级“完全”对立的理论。但是,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渐渐了解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充分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点,尤其是其在经济建设上的优势。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依旧有着消灭资产阶级的使命,这一内在使命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向民族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就如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正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下提法:“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冒进的直接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展开“进攻”而是更温和的消灭它——即采取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
(三)“五反”运动的影响
经历了建国后的1951年短暂的“黄金时代”后,个别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本家趋利的本性搞起了“五毒”,更甚者趁着抗美援朝的战争大发国难财,大批偷工减料的军需物品被运往前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整治这一现象,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民族资本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毛泽东更是表示,一定要“借此机会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一定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2]。
这一运动后,不仅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声望大大降低,更深层次的影响是,长期占据党内“左”的思想又一次被点燃,对于消灭资本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影响极其深远,乃至于在之后的二十年来一直左右着党内党外的政治生活。
(四)苏联模式的影响
建国初期,我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化和优先大力发展重工业等模式下,极速的整合了国家资源,迅速的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至于可以在冷战时期和美国“掰手腕”,这些都深深吸引和影响着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而冷战的局势和中苏的友好时期,都从客观上引导我们向苏联模式学习。在苏联模式体制下,民族资本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被逐渐边缘化。
(五)国际局势的迫切需要
我国在建国初期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全面封锁,不可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当中,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都以世界贸易和垄断的形式发展,失去了进入世界贸易市场的机会,我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更需要仰仗国内的资源有效整合和利用,这样才能在国外资本势力的封锁下,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在短时间内让国家重工业快速发展,增强国力。而在国际局势上,美国在台湾的包围和封锁、朝鲜半岛的抗美援朝战争,都增加了国家对重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需求,而在这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上,是不能任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国家集合资源发展,这就从国际局势上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
二、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的途径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通过多种途径来实施对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的政策,总结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资金来源上的控制
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脉,实施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要控制企业的血脉来源,从资金源头上,让私营企业对国家产生依赖。
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先行对金融行业公私合营的政策,来实现对私营企业资金的来源的控制。到1952年底,党和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一来,私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民银行的贷款。
首先实现金融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国有化,再进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党和政府对于企业生存发展之道的有力把握,当私营企业在资金上逐步依赖国家后,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会逐步边缘化。
(二)生产销售上的依赖
1949至1953年,党和政府对私营企业实行了扩展性的加工订货政策,这一政策在短期上看,是为了帮助长期受战争摧残和国民党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保证了私营工商业在建国初期的困难环境下维持生产和利润。而在长期作用上看,这使得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私营企业逐步依赖于国家。
1949年,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在私营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占12%,到1953年就达到了62%。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国家初期控制物资都有着重要作用。而随着加工订单的逐步增多,私营企业也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市场下的盲目生产逐步转向计划经济。国家掌握着主要物资,使得私营工商业在原料上大大依赖于国家,而国家的加工订单增多使得企业在销售层面也依赖于国家的支持,逐渐失去了自由竞争性,融入到计划经济当中,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铺平了适应性道路。
(三)工人监督生产制度
在私营企业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上,“五反”运动前后有很大的差别。“五反”运动前,民族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而“三反五反”运动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3]运动过后,企业内部逐渐建立起来了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随着制度的加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逐渐取代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私营企业决策组织,实际上控制了企业,资本家逐渐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在企业内部的阶级中被边缘化。
(四)利润分配上的削弱
建国初,在私营企业分配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规定:资本家应得的利润份额不少于60%。这一分配制度对于建国初恢复国民经济、鼓励资本家投资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五反”运动以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在分配制度上打压资本家,实行“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所谓“四马分肥”,是指1956年以前,国家规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全年盈余按以下四方面分配:国家税收占30%,企业公积金约占10%到30%,职工福利奖金约占5%到15%,资本家红利约占25%。
因这种分配制度的确立,使得资本家的利润从不得低于60%降到了不得高于25%,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归了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无法追求到高额利润,不能对其资产做扩大再生产,减缓了其财富积累的速度,从而在企业的末端利润分配上实现对资本家的控制,使其失去独立发展的空间。
(五)阶级政治觉悟提升
尽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一些情绪是抵触的,但在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有所提升。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清醒的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终究会退出新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不可逆的趋势,很多中小私营企业的资本家经营困难,在国家的帮助和扶持下继续维持企业生存,逐渐依赖国家,对接受改造是欢迎的。很多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资本家,也在几次运动中体会到“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只有接受改造,拥护党和政府,才能求得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行业内的领头人政治觉悟逐渐提升,像“猪鬃大王”古耕虞、被周总理称为“全国第一号资本家”的荣毅仁,他们开始在资产阶级内部宣传鼓励接受改造,由于他们的带头作用和在资本家中的显赫地位,他们的行为对和平赎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在自我认知上,也意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被逐渐“边缘化”,要想融入进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接受改造,脱下“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身份。
三、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的反思和再认识
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在我国历史上自诞生到走向“消亡”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但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建国以后,我国并没有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直接“消灭”的极“左”方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部分资本家不满足于正当获利渠道,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谋取暴利,削弱国营经济,甚至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大发战争财、国难财,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为彻底铲除这“五毒”行为,国家开展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开展后,党和政府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限制”大于“利用”,逐渐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的政策。从根本上看,这是资产阶级在自身趋利性的驱动下内部缺乏有效监督管制使他们违背了党和政府的发展愿景,从而使党和政府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发生了较快的转变。
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就如同《共产党宣言》上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党和政府实行的是“温和”的发展中削弱,一步步让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自身地位在各个层面的边缘化,从而接受和平改造。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的不足所在,从生产层面上看,过分压制民族资产阶级打消了其生产积极性,一些企业生产效率大不如前,甚至一些资本家破坏即将被国有化的企业;从思想层面上看,边缘化政策使党、国家和人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刻板的印象,乃至于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资本家的评价都是消极的,给日后形成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思想埋下了种子。从领导集团层面上看,在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这使得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的“左”的情绪,为日后埋下隐患。1955年底,周恩来总理也婉转地提出:“我们可以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性急”。[5]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边缘化,是过渡时期必然要实行的一种特殊政策,从根本上是为了从思想层面上让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平稳的接受和平改造,这对于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思想缓冲作用,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家的实际职权已变成了“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6]至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