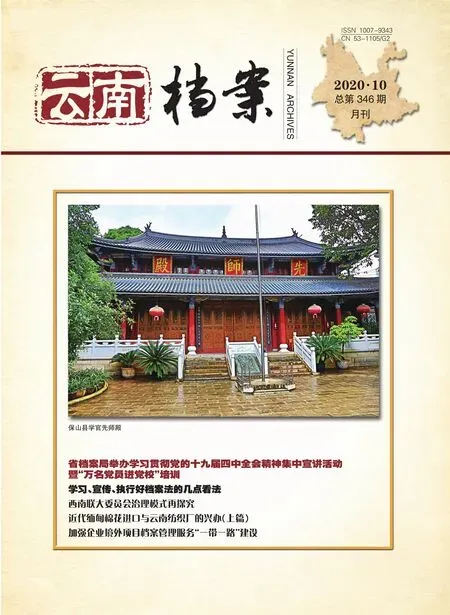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再探究
2020-12-05史晓宇
■ 史晓宇
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是西南联大根据“衡”的治理理念,[1]为保持治理的有效性而在内部形成的以委员会为组织形态的治理活动结构和型范。其治理模式的基本类型构成是: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分校校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项委员会;它们在西南联大内部形成了委员会形态的整体治理系统,是西南联大彰显的制度性的架构。
一、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的背景
1、追溯联大之前的联合
1929年夏,南开大学发生了教授出走导致大学一定程度的危机:在南开工作多年的关键教授,如萧遽、蒋廷黻、萧公权、李继侗等离开南开而赴清华任教,其中由于生活压力的增加与薪金的水平比例悬殊是重要原因。为此,张伯苓重新考虑南开教授出走背后的资金匮乏问题,“他承认南开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2]相比张伯苓早期与北大、清华联合合作的心向而言,北大和清华由于地域上的关系,其联合则来得更为直接和实在。
史料显示,1934年6月,因各省市学生会考,数学理化成绩较劣,教育部令各大学利用暑假期间,创办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北平师范大学拟定计划自办,而北大、清华则是联合设办。1935年,北大、清华仍旧按照上年的方式,再次进行联办,并由时任北大课业长的樊际昌前往清华大学磋商合办事宜。
2、大学信念的共同坚守
三校都有自己的大学章程,以及笃信和践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使之在大学内部深入人心,形成了制度认同。兹以教授治校原则为例进行说明。
清华教授治校的原则,体现在教授居于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关于清华大学以师资为第一要务,我们在梅贻琦对清华的总结中可以知晓,“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所最应致力者也”[3];清华大学在校级层面设立了教授会,即使是在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其中未有教授会的组织之设)之后,也依然坚守这一传统,不改初衷,这在三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努力整饬校务,聘请教授,更费煞苦心”。[4]蒋梦麟发展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各级的细致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把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学院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高深学问。此外,北大的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吸纳大量教授的加入,使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政方针上发表意见,发挥积极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
南开的教授治校也是蔚然成风。评议会、教务会议、各种委员会、事务会议各学院教授会议、各系教授会议中都是教授绝对力量的存在。南开特别注意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授延聘,开始委托专人负责。南开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大猷教授认为,“以学校的历史、规模、师资阵容、在社会上的声望言,南开实不能与北大、清华比拟,政府之重视南开,是由于什么考虑呢?无疑的,我以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平”。[5]
3、通家之好的情感纽带
通家之好是西南联大人际关系的整合力量,是一条贯穿西南联大的非组织形式的纽带。西南联大的“通家之好”由“四缘”关系——地缘、姻缘、学缘、校缘关系构成,最突出、最重要的是校缘关系。
通家之好可能是西南联大教员之间最多的共同符号表达。三校之中,梅贻琦、胡适、张伯苓、冯友兰、朱自清、周炳琳、吴泽霖、汤用彤、饶毓泰、江泽涵、罗常培、黄钰生都有许多通家之好的故事。
1946年,在三校共同纪念联大九周年校庆大会上,清华校长梅贻琦讲道,“前几年,教育当局谈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这不是偶然的,原因是由于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半是熟人,譬如:胡适先生即为清华校友,冯友兰先生是清华文学院长,但[也]是北大校友,再如南开之黄子坚先生,亦为清华校友,张伯苓曾为清华教务长,我本人亦为南开校友,已为“通家”。间或有远有近,但是很好”[6]。北大校长胡适接着表达“说到三校是‘通家’,在美时,渠曾为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现在还是南开的董事。战前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现任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长饶毓泰都是南开之教授。江泽涵也是南开校友。清华教授朱自清,是北大校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7]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三校的通家之好,是三校的学术联合的基础、共同信念的基础、人脉关系基础、利益的基础、价值观念统一的基础,是西南联大团结、友爱、稳定的基础,通家之好是亲密的、有凝聚的融合剂,是西南联大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联合成功的基础。
4、院校地位与学科优势互补
高校之间有效的合作离不开院校地位的接近,巨大的落差会造成彼此悬置的状态,本身就直接影响彼此合作的心理和平台的靠拢和对接。抗战之前,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这三所一流的大学已然分别执中国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牛耳,三校地位层次接近,办学的任务层次都有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社会地位、办学声誉显赫。在此不再赘述。
学科优势的互补也是三校合作关系的融合剂。“早在抗战以前,这三所大学在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已是名声在外了”。[8]清华在理科和工科方面的成就卓越,工科的直接服务社会能力在战时显得特别珍贵和闪亮,而北大的自然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北大在社会科学领域是潮流的引领者,而清华和南开是紧随其后的追赶者;南开的现代经济问题研究特别强调当前经济问题解决,而清华则是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独占先机。南开的经济学和商学研究享誉中国大学,而且独有的化学工程系,为联大的工学院填补了系科的空白。接近的院校地位与学科的优势互补,为三校之间合作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走向学术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二、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的条件
1、教育条件: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教学上和人才培养中的最大特色就是坚持通才教育,这是西南联大能够保持联合的一种教育力量。通才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高尚情操、高深学问、高级思维,能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人才,主张知识的基础性与经典性,知识内容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它不主张过早的、细微的专业化。
通才教育不仅在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也必然通过内部治理结构——联合的结构反映出来。专业教育强调知识的分化细化,即知识专业的碎片化表现。通才教育思想上是强调综合,较宽的口径基础,而不是分化和分裂。通识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综合和稳定力量的教育模式。
西南联大的三常委及教授们都提倡或默认通才教育。战前北大和清华都是实行通才教育的典范。领导人和教授的信念限制或解放着大学的结构,梅贻琦在集中体现了他的大学办学理念的名文《大学一解》中,明确提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9]。蒋梦麟早在创办《新教育》月刊时,就主张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为宗旨,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思想。[10]虽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本人,“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11]但是他也并不反对通识教育,在战时环境设备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体现的更丰富和广泛的学科领域,对职业的、技术的和实际的学习何尝不是一种有益补充。所以,西南联大的教学核心制度——《教务通则》——清华大学的教学制度摹本,这一体现通识教育思想的具体实施方案,在北大和南开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施行起来基本没有障碍和阻力。
假如我们从组织系统的角度来认识通才教育与委员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通才教育是委员会治理模式支撑性力量,委员会治理模式又是通才教育的具体体现。委员会治理模式的组织构成体现出机构的联合,在运行过程中强调三校人员的联合,强调学科综合,特别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联合,这无疑与联大的风格与精神相一致。而各项委员会体现出来的广泛、灵活、适应性好,与通识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是一脉相通和延续相承的。
2、哲学依据:絜矩之道
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委员会制的运行思想,是以《大学》中的“絜矩之道”为引领。所谓“絜矩之道”,即《礼记》所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絜矩之道强调以互相信任为前提,顾及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上下之间的关系以层层节制,左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合作,前后一致步伐整齐,使之关系分明,最终努力能上下沟通,活动灵敏,形成协同治理,以期达到整体连贯一气,取得所谓“自治丝毫不苟,治事有条不紊”的效果。[12]
我们从联大教授的行事风格和在委员会治理中协调关系的方式来看,絜矩之道对西南联大内部治理影响颇深,亦成为西南联大委员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的哲学遵循。
3、制度要求:合议制
西南联大内部治理的统领和核心是合议制度,即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制度。同时,合议制度也是西南联大内部治理结构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1937年8月底,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就推举临大常委负责人事致电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和杨振声,“组织规程第五条规定: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在使常委会议之决议对内对外随时有人执行,不必遇事临时推人。此为合议制度应有之办法,否则将缺乏灵活与统一。兹拟请诸兄互推一人,以便照章指定。如虞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亦可。倘尚有其它意见,亦请见示为荷”[13],“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14]可见,西南联大的核心制度是共同负责的合议制度。互推一人的做法,在当时也较为常见,如1939年3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出席人员开始是规定凡是常委制的院校由常委互推一人出席,后又改为全体常委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合议制度在会议机制上、在行政工作运行中、在教学工作中已经成为西南联大中行政人员甚至教学人员所明晰和共同遵守的根本制度,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1940年8月,郑天挺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如以为各长不称职,可以更换三长,如以为常委不负责,则凡事皆合议行之。”[15]如此可知,合议制的议事规则已深入人心。合议制还体现在审查研究生的考试成绩上,令人称道,“开委员会导师阅卷委员联席会议,审查昨今两日研究生考试成绩,纯采合议制,试卷公开评阅”。[16]及至1945年2月,西南联大的常委会上,适逢主席梅贻琦出差,但临行匆匆,未指定代行常委职责之人,于是根据合议制度精神,出现了如下一幕,“五时至南开办事处开常务委员会,……月涵先生行时未指代理之人,今日石先推余,余推石先,最后决定由石先、勉仲及余三人共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