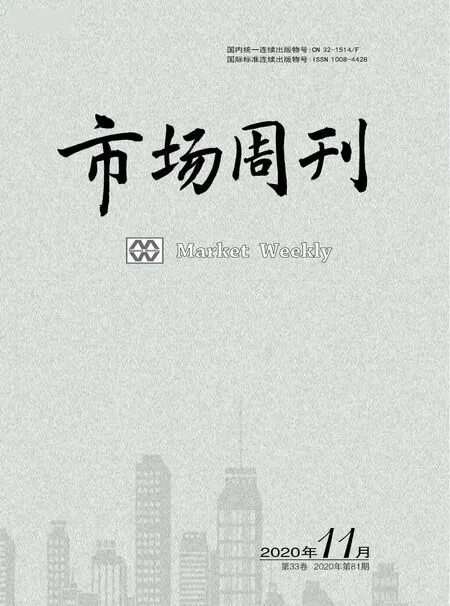澜湄流域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研究综述及展望
2020-12-03鲍立刚
鲍立刚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崇左532200)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由中国发起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是指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围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实施可持续开发和开展互惠务实合作的机制。从世界各种机制或组织的实际发展来看,其正常运作和持续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人力资源的协同开发与管理,澜湄合作机制也不例外。澜湄流域的地理范围跟大湄公河次区域地理范围相同,自从1992年以来在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的协调支持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下的澜湄流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有所发展,历经了尝试摸索阶段和调整发展阶段。2014年11月由中国倡导的澜湄合作机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升级版(卢光盛和金珍,2016),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把澜湄流域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带进了第三个平等、包容、务实、真诚和亲情的安定繁荣阶段。面对域外国际组织和国家在次区域多机制竞争甚至排他性地介入,面对澜湄流域贫穷、动荡、敏感和复杂的现实,如何推进中国“一带一路”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引领澜湄流域走向平等、包容、务实、真诚和亲情的安定繁荣阶段,将变得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史梳理
(一)1992~2001年GMS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尝试摸索阶段
1992年,亚行发起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GMS)是一个通过加强与各成员间的经济联系,消除贫困,促进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制。合作机制推动了成员国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促成实体经济多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1995年GMS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WGHRD)(杨阳,2011)。在亚行的协调下,利用国际组织或外国资金援助成立了专门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机构。例如1996年新西兰资助泰国孔敬大学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学院(湄公学院)(周传方,2000)。亚行在其秘书处下设了人力资源开发和环境处负责相关协调工作(段学品,2010),其中就包括GMS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协调工作。
本阶段GMS与澜湄流域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主要集中在人员交流和高层论坛方面,特点是层次高、参加人数少,普通民众对GMS还比较陌生,人力资源开发重点在培训、防拐、减贫、防控疾病等基础项目上,私营部门开始参与GMS。
(二)2002~2013年GMS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调整发展阶段
2002年11月在金边首次举行的六国领导人会议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未来10年战略框架》,内容就包括“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应用能力”。本次会议还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金边规划》,这就是GMS人力资源领域骨干项目“金边培训计划”(段学品,2010)。2002年在GMS首次举行的六国领导人会议期间,我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份《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中国政府表示将在包括人力资源合作领域在内的经济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王勤,2003)。在调整发展阶段,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人力资源开发与规划方面,GMS第二次和第三次六国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报告》都提出包括实体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面的设想。2007年北京首届GMS农业部长会议对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做了战略重点部署。②在合作机制建设与发展方面,包括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小组,亚行是领导协调机制(吴世韶,2011)。早在1992年云南就参与了GMS合作,1994年我国政府就成立了“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小组”,广西2005年加入GMS合作。③在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方面,包括亚行举办的高官战略能力培训,湄公学院的培训和研究课题来加强GMS合作以及提升人才能力,积极打造GMS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网络,加快教育合作,积极推进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合作,进行国内培训(段学品,2010)。
本阶段GMS把解决基本健康和教育服务的援助项目,调整转变为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源国际培养等方面。各国已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是各国实体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其主要方式是人员的专项培训。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对于GMS的影响力也在增大。澜湄流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以教育、培训和健康项目为主。但是,面对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政治互信等问题,以经济合作为主的GMS几乎无法有效处理。
(三)2014年11月以后澜湄合作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安定繁荣阶段
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的倡议。2016年3月,在海南三亚召开了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会议认可作为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成果的澜湄合作初期五个优先领域,即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等实体经济合作。会议一致同意提升澜湄合作国家间科技合作和经验分享,深化人力资源开发、教育政策、职业培训合作和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间交流。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2018年1月10日在柬埔寨举行,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提出做好包括提升人力资源合作在内的五点建议。此次会议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其中谈到加强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开展该领域的交流培训与考察学习。
中国倡议成立的澜湄机制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合作领域,通过澜湄合作能有效地协调好“澜沧江—湄公河”上下游关系,除了主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能着手解决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政治互信等问题。澜湄合作机制并不排他,而是与本地区其他机制互为补充。
三、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研究动态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流域经济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澜沧江—湄公河这一跨界河流的管理。例如,佩奇·索科姆(Pech Sokhem)的《跨界河流管理:以湄公河为例》,万纳瑞斯·常(Vannarith Chheang)的《湄公河地区的环境和经济合作》等。二是大国在该次区域的政治博弈、经济合作问题,例如,小笠原孝(Takayuki Ogasawara)的《日本将湄公河流域的发展作为其东亚政策的一部分》、斯科特·皮尔斯-史密斯(Scott W.D.Pearse-Smith)的《湄公河流域的“水之战”》。三是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动机、措施及影响,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如,提莫·门尼肯的《中国在国际资源政治中的表现:湄公河的教训》,吉姆·格拉斯曼的《角逐湄公河——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与泰国》等。在国内学者研究的成果中,涉及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分布在如下三个阶段。
(一)尝试摸索阶段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机制探析、基础培训项目开发和国际人才培养。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而尚未充分开发的地区之一,使这一地区呈现出多种合作机制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孔晓莎,1999)。我国宜将重点放在“黄金四角”的小区域合作的具体项目上(史育龙,1998)。应加强发掘人力、水能和矿产等资源(刘诗嵩,1996),培养流域地区国际经济合作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贺圣达,1997),加强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培养,在昆明建立次区域人才培训中心(郭宽,2000)。
(二)调整发展阶段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技能培训、创新人才培养、经济与人力结合和GMS机制反思。
为了促进次区域经济发展,应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技能开发(杨宇白和史爱平,2002),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加快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刘烈武,2009),把次区域内经济技术合作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结合起来(范爱军和于增成,2005;郭祥焰和郭永文,2006),应改变项目导向的合作机制,进一步增设常规性管理机构(杨阳,2011;赵亮,2014)。
(三)安定繁荣阶段
未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培训机构地域分布探讨、放宽培养条件和教育培训交流。
争取澜湄合作中心(办公室、办事处)落户昆明或南宁,也可以考虑讨论在昆明建立湄公学院分院或第二学院(卢光盛和金珍,2016)。建议放宽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语言门槛,在帮助湄公河国家培养经济社会所需的各领域人才的同时培养更多的知华友华人士(李晨阳和杨祥章,2017)。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加强教育政策、职业培训等领域交流合作(卢光盛和别梦婕,201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二十多年来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实体经济合作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在经济发展、区域霸权和对中国参与澜湄合作的焦虑上。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在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并且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教育培训及人员交流上;没有对次区域人力资源一体化进行研究,没有对澜湄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源协同管理进行研究,也没有对澜湄流域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进行研究。尝试摸索阶段GMS跟人力资源开发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机制探析、基础培训项目开发和国际人才培养研究上,成果数量很少而且没有对区域间协同进行澜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研究。调整发展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技能培训、创新人才培养、经济与人力结合和GMS机制反思。有关学者开始思考把区域内实体经济合作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结合起来研究,但是并没有正式开展协同研究;没有对区域内经济建设中人力资源的不平衡问题进行研究,也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合作抱有戒备心理提出解决方案。值得肯定的是,学者们开始反思GMS机制的存在的弊端和呼唤新机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现实需要下,澜湄合作机制出现了。安定繁荣阶段才刚刚开始,目前仍然还是主要研究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和培养,人们的思维中仍然还处在对员工的占有和对培训机构地域分布的争夺,没有去认真研究人力资源如何共享、人力资源如何互联互通,也没有认真研究如何让人才能够安心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为员工解除后顾之忧而使其能够安心工作,更没有对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进行研究。
四、澜湄合作机制下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展望
虽然GMS二十多年来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经验积累和成果,无疑是澜湄合作机制下的澜湄流域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研究的必要借鉴;但是澜湄合作机制下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还处于研究初期,并没有形成系统研究成果,还出现了上述各种不足,对此论文提出澜湄合作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展望,试图抛砖引玉以利于后续研究。
(一)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一体化顶层设计,建立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院
由于澜湄流域贫穷、动荡、敏感和复杂的现实情况,域内各国共同体意识不强;为了次区域的长远发展,澜湄合作机制国家应不忘同饮一江水、共为命运共同体的澜湄精神;可尝试在主权色彩不是很浓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领域进行一体化顶层设计,建立“澜湄合作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院(简称研究院)”,用来推动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研究和实践。研究院除了下设各国研究所处理日常事务,还可以下设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智库、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杂志社、澜湄人力资源开发高峰论坛组委会等直属机构处理专业事务。详见图1《澜湄合作机制下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展望》框架图。
(二)适应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需要,采用广西和云南协同管理模式
广西和云南两省区有着相同的区域优势和经济水平,在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研究和应用上分工协作,打造广西和云南协同进行澜湄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云南在GMS经济合作及其教育培训上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加上教育培训人文交流在澜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工作量最大,云南主要进行次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和实践;因此,云南只负责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智库、云南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的组建和管理,并负责教育培训人文民心相通交流工作。考虑到广西在东盟各类论坛有较丰富的经验,在澜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研究有先发优势和基础,因此,广西负责澜湄合作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院、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杂志社、澜湄人力资源开发高峰论坛组委会、广西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的组建和管理,以及各机构所负责的业务。澜湄流域其他五国分别设立各国的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协助研究院开展工作并接受研究院的业务指导。

(三)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互联互通建设,打造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网站大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其中就包括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打造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网站大平台,为澜湄合作招募所需各类人才,解决区域内人力资源的不平衡问题、人力资源共享问题和跨国合作的地域障碍问题。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网站大平台,由澜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院负责管理。网站大平台除了进行常规的宣传,还可以分设如下互联互通子平台:澜湄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澜湄网络招聘共享平台、澜湄网络培训共享平台、澜湄人力资源市场等,这些子平台由研究院和各国研究所负责管理。
(四)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人文民心相通交流,构筑澜湄人力资源交流桥梁
次区域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有效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并且对中国的合作心存戒备,限制了澜湄经济合作的深化和拓展,也影响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高阶”发展,在教育培训方面自然要有更高的要求和更深层次的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加强区域内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文基础和民心保障。人力资源交流桥梁的构筑包括教师项目交流、学生项目交流、专业技术项目交流和其他交流项目,这些项目主要由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智库负责管理,研究院和各国研究所协助。
(五)适应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需要,探索矩阵制员工关系管理模式
澜湄机制在不同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过程,所在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会对实体经济机构和劳动力产生影响,必须要研究当地劳动法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加快了人才的流动,因此我们势必要对实体经济机构的用工方式进行研究。澜湄各国不仅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语言文化相差较大,国家内部还存在多民族现象,对中国的次区域合作抱有较强戒备心理,有必要进行跨文化管理研究。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员工对工作信息的接触更加容易,管理者对员工的直接控制难度越来越大,新生代员工个性张扬、特立独行,加之澜湄机制下的实体经济合作的人员来自不同国家;作为实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必须从传统的指挥和命令的角色转化为授权和协调的角色,员工从直线职能制下的被管理者,也要转变为实体经济矩阵制组织下的协同合作者。如何让员工能够安心为企业服务?如何为员工解除后顾之忧而能够安心工作?员工关系管理的模式必然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员工关系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应用,由研究院、各国研究所和澜湄人力资源开发杂志社负责管理。
五、结论
人力资本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源泉,运用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生产率,促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管理的出现,带来实体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区域实体经济合作深化,会产生“外溢”效应,最终能够促进其他领域的合作,逐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人力资源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如果把澜湄合作机制多领域合作的人力资源执行主体与合作的实体经济项目进行协同发展研究,这种“外溢”效应会更加强烈和有效。澜湄合作机制的多议题合作不仅能满足澜湄流域国家发展经济并获得收益的迫切愿望,还能稀释澜湄流域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加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十分有利于解决澜湄流域贫穷、动荡、敏感和复杂的现实问题。因为这种“澜湄合作机制下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多议题合作的制度框架可以为调解冲突提供更多选项,并且有人力资源这条深耕民心交流和厚植澜湄文化的纽带。通过经济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两个学科协同交融、中国与澜湄不同国别协同推进、广西与云南两个省区协同合作等“三对”协同方式进行研究和实践,实现人力资源互联互通、澜湄国家民心相通和员工关系和谐沟通等“三通”目标,最终期望实现澜湄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