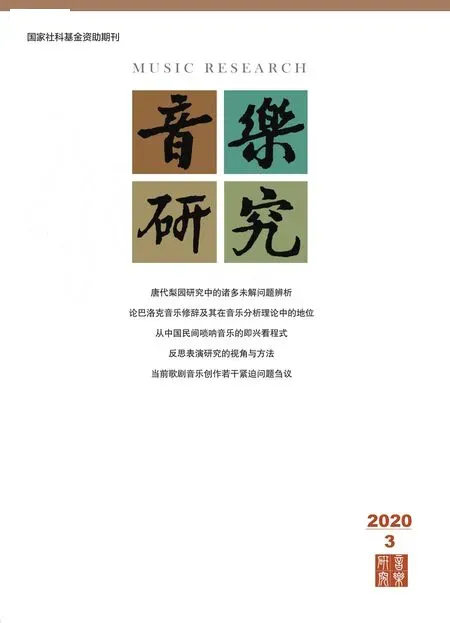当前歌剧音乐创作若干紧迫问题刍议
2020-12-02居其宏
文 居其宏
近年来,我国歌剧创演领域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年,在全国各地首演的新创剧目数量,由过去的个位数激增至两位数。创制单位除了中央、省级及地市级专业歌剧院团之外,一些高等艺术院校也纷纷加入创排歌剧的行列。与此同时,歌剧理论批评领域也一改以往的寂寥状态——不仅报刊上歌剧评论文献日见其多,作者队伍日益壮大,且在近两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歌剧重大问题研究”(中央音乐学院)这两个歌剧选题被列为重大项目。
然而,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前歌剧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下,也暴露出一系列紧迫问题,隐伏着诸多深刻危机;而对歌剧音乐创作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知及其在当下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则是其中最紧迫和最严重者;若得不到及时回答和有效化解,势必对我国当代歌剧艺术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其实,笔者在此前发表的诸多文论中,对上述诸问题多有论述,可惜未能引起某些同行的足够注意,致使若干错误观点和实践依然盛行于世。本文就这些紧迫问题,或重申、或进一步阐发,以引起大家重视和研讨。
音乐在歌剧中的主导地位
鉴于歌剧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在参与歌剧的诸多艺术元素中,音乐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在歌剧、舞剧、话剧、电影这些综合艺术中,戏剧因素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除戏剧之外,构成其形式“诸元”中的“另一元”若在其综合体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一元”便成为判断某一综合艺术与其他综合艺术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对话剧来说,是语言;对舞剧来说,是舞蹈;对电影来说,是蒙太奇组接;对歌剧来说,则是音乐。
音乐因素在歌剧中的主导地位,是由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和歌剧本性共同决定的。歌剧作为综合性的音乐戏剧样式,它的生命形式即是由“音乐”与“戏剧”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所构成。戏剧向歌剧提供的人物、情节、动作和冲突等,仅仅是一种略图,一种具有明确语义性的佳思巧构,一种空间性的框格和视觉性的实体展开;而因为音乐艺术的时间特性和听觉特性,它独有的抒情性和表现性的巨大魅力,却可以在戏剧所提供的空间框格和视觉实体基础上,给以歌剧充分的展开、充实、丰富、扩展、深掘、发挥、引申和升华,从而使略图变为立体的、血肉充盈的艺术建筑,使佳思巧构成为活泼泼的生气灌注的生命形式。用一个也许不很贴切但却能说明歌剧中音乐与戏剧相互关系的比喻来说,如果歌剧是一个生气灌注的生命形式,那么,“戏剧因素”则是它的骨架,而“音乐因素”则是它的血肉。很显然,骨架和血肉都不是独立的生命形式,只有当它们在歌剧综合体中相互依存、有机结合达于浑然天成状态时,歌剧的生命形式才是鲜活的和完满的。
对于音乐因素在歌剧中主导地位和作用的考察,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
首先,音乐作为主情的艺术,它是直接诉诸心灵的——心灵的歌唱来自歌唱的心灵,并且以最直接的形式“袭击”欣赏者的心灵。因此,无论是音乐的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是心灵对心灵的对话,情感对情感的倾诉。音乐音响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音乐的品格是非语义性的,较之其他的艺术形式,音乐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模糊性。音乐艺术的这些基本特性是任何其他艺术——语言艺术、形体艺术及蒙太奇艺术——所不可能具备的。在歌剧中,凡是戏剧、语言和其他构成元素无能为力的地方,常常也是音乐因素得以大显神通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歌剧能够区别于其他综合艺术的独特优势。
其次,由于音乐因素在歌剧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导地位,那么,它就不能不对构成歌剧综合体的其他艺术因素(尤其是戏剧)的存在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从总体上规定着歌剧艺术的美学品格和宏观面貌。于是,戏剧的音乐性乃至整个歌剧的音乐性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命题,就被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一命题的提出,逻辑地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歌剧是音乐的戏剧。歌剧综合体及构成它的其他艺术因素,毫无例外地应当充分尊重音乐因素的独特规律和表现优势,应当把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并为之创造一切可能的契机,作为自身艺术构思的前提;而关键问题是,若要完满达成这一任务,势必要向歌剧的情节构成、主题选择、人物关系、场面设置、戏剧冲突的组织与展开等提出音乐化的要求,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戏剧因素和其他艺术因素存在方式的变化。歌剧历史上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创作实践都表明,无视音乐艺术在歌剧中的主导地位,纯粹的戏剧构思,以及追求戏剧本真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创作实践对于歌剧来说是致命的。
当然,音乐艺术一旦进入歌剧综合体中,成为歌剧的综合元素之一,那么,它自身的独立性和非语义性的特点也就必然随之丧失,而与其他的综合元素构成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歌剧中,音乐因素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关系才能获得创造和存在的意义;它的每一句抒情状物写意的表达,必须同特定的人物性格、情感状态、戏剧情境有机契合才具有戏剧性;它的歌唱部分,由于同特定人物的剧诗唇齿相依,因此便获得了语义的明确性和性格的规定性;而它的乐队部分,由于始终在歌剧的规定情景中鸣响,于是也失去了绝对音乐的纯粹性,而具有依稀可辨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清晰的戏剧意向。
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尽人皆知的命题,即音乐的戏剧性。不具戏剧性的音乐,游离于歌剧戏剧冲突、人物性格和特定情境的音乐,对于歌剧来说,毫无价值和生命力。即使作曲家把它写得十分华丽动听,至多可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欣赏,对于整部歌剧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赘疣而已。
由此可见,在歌剧中,音乐因素不但可以决定歌剧综合体及构成它的其他艺术因素的整体面貌和存在方式,而音乐自身的整体面貌和存在方式,也为歌剧综合体和其他艺术因素所决定。因此,歌剧艺术的整体音乐性,戏剧因素和其他艺术因素的音乐性,音乐因素的戏剧性,它们的有机协同,才是关于音乐在歌剧中主导地位的完整表达。
作曲家在歌剧一度创作中的定位
如今,有一种观点在我国歌剧界非常流行,即歌剧必须以作曲家为中心,作曲家主宰歌剧一度创作,这大概是从“音乐在歌剧中的主导地位”这一命题推演出来的。在最理想的意义上,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不仅符合从莫扎特、罗西尼、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到贝尔格和肖斯塔科维奇等西方歌剧大师的创作实际,也基本符合郭文景等我国当代优秀歌剧作曲家的创作实际。但请不要忘了,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歌剧创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作曲家,不仅是才华横溢、修养全面的作曲家,同时,也必须是深谙戏剧创作规律的戏剧家。
试看瓦格纳和威尔第二人的创作实际——众所周知,瓦格纳许多剧目的剧本都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这种一人身兼编剧和作曲,而且皆能达到顶级大师境界的歌剧家,在世界歌剧史上,除瓦格纳外迄无二人。而威尔第创作歌剧,几乎都是由他自己寻找并决定题材,写出提纲,勾画出情节发展、人物关系和场面组接的基本轮廓,对歌剧主人公的性格甚至外貌特征做出具体描述,然后交由剧本作家按照他的要求写出台本。进入作曲过程后,威尔第不厌其烦地向剧作家发出各种修改要求和指示,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剧作家必需一一照办,绝无商量余地;如有必要,威尔第甚至自己动手写作剧诗乃至某些关键场面。有时,当威尔第感到某个剧作家已经没有能力和可能实现他的艺术构思时,他便毅然决然地临时更换剧作者,甚至不惜开罪于老友。
威尔第歌剧题材选择的首要前提,是戏剧情节的独特性及其展开的丰富性。一般化的情节铺陈和毫无新意的老套故事,是为威尔第所不屑的。他钟情于这样的剧本——故事新颖独特,情节充实曲折,戏剧冲突具有强烈动力性,情节展开中那不同凡响的舞台色彩和令人窒息的戏剧效果,①威尔第对《弄臣》的剧本这样评论:“这部歌剧的情节最富于戏剧性,它很多样化,既灿烂辉煌,又富于生活气息,而且动人肺腑。”(1853 年4 月22 日致友人的信)。参见〔俄〕柳波芙·索洛甫磋娃《威尔第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年版,第155 页。从不回避因此而给音乐创作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威尔第正是在勇敢面对这些挑战,战胜这些困难中,才成就了他的大师业绩,奠定了他在浪漫主义歌剧中与瓦格纳“双峰对峙”的崇高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威尔第对莎士比亚戏剧情有独钟,于是才有他《麦克白》《奥赛罗》《法斯塔夫》等不朽剧作。《弄臣》《阿伊达》两剧之所以能够一下子激起威尔第的创作灵感,也是因为它们的剧本有着不同寻常的复杂情节与色彩,与威尔第的戏剧美学理想十分投契。
威尔第在歌剧一度创作中这种主导地位的建立,恰与大师对歌剧之戏剧品格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密切相关。事实上,威尔第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将这种强烈兴趣一直保持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舞台经验的积累,威尔第对莎翁戏剧中深刻的人文精神、情节的丰富性和性格的鲜明性,有着越来越真切的感受。后来,威尔第又认真研究了席勒、雨果等大作家的戏剧作品,从中悟出组织曲折情节、在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营造令人惊异的剧场效果等方面的戏剧真谛——这也是威尔第的许多歌剧题材,何以都是取自上述这些伟大戏剧家之经典作品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精深而细致地分析了前辈歌剧大师莫扎特、罗西尼、贝里尼和多尼采蒂等人的经典作品,以及瓦格纳的乐剧理论与实践,从而学得了用音乐展开戏剧的成功经验,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加以探索、运用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其创作生涯中许多成功与失败的鲜活例证,成了他最直接的老师和最生动的教科书,使威尔第在大量舞台实践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获得了比同时代许多作曲家和剧作家更为切实的戏剧感悟。
由此可知,即便在西方歌剧史上,“作曲家主导歌剧一度创作”,也不像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是一种必须如此的艺术规律和常规的制度性安排,而是由作曲家在长期歌剧创作实践中修炼而成的深厚音乐戏剧综合素养所决定的。
具体到当下的中国歌剧创作,鉴于作曲家队伍的构成、背景和具体情况非常复杂,对“作曲家主导歌剧一度创作”这个命题,切切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作曲家郭文景,虽然他本人并不直接写剧本,但他的戏剧修养、艺术目光,以及对歌剧文学剧本的理解,却明显高于同时代的多数作曲家,当然也必然施巨大影响于同他合作的剧作家们。因此,他的歌剧,无论是早期的《狂人日记》,还是几年前的《诗人李白》,抑或是近年的《骆驼祥子》,在音乐与戏剧的有机结合和综合平衡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再如作曲家莫凡,也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修养全面的歌剧家,他的一些歌剧作品如《雷雨》《赵氏孤儿》,不仅自己作曲、配器,而且亲自编剧,其音乐和戏剧的品相都不低。
还有一些作曲家,虽有若干歌剧作品问世,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作曲家对戏剧的本质领悟不够深刻,常按自己的主观愿望修改剧本,致使一些原本好的剧本品质大打折扣。
另一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某些从事歌曲或器乐创作的作曲家,此前从未涉足过歌剧创作,对何为歌剧音乐和歌剧文学的戏剧性、音乐性,尚处于懵懂甚或全然无知的状态,你就让他主宰歌剧的一度创作,不出乱子才怪。
事实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我国当代歌剧创作的某些乱象,恰与某些既不懂戏剧也不懂歌剧的作曲者在歌剧一度创作中自以为是有很大关系。
事实已经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至少在目前阶段,处理中国歌剧创作中剧本和音乐、剧作家和作曲家的关系,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提倡在共同遵守歌剧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彼此尊重,和谐合作;而不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主张作曲家主导,更不宜把这种模式提高到歌剧规律的层次上加以尊奉;否则,必将对歌剧创作造成极大戕害。
待到若干年之后,中国歌剧作曲家的绝大多数都成了真正的戏剧内行,而中国绝大多数歌剧剧作家依然不懂歌剧剧本的戏剧性、音乐性、文学性为何物,唯在这个情况下,再来伸张作曲家的主导地位,也不为迟。
总之,我国歌剧作曲队伍林林总总,每个作曲家的个人素养、技术装备、歌剧创作经验积累、艺术悟性和创作态度各不相同,因此,在“作曲家主导歌剧创作”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结论,首先要基于个人经验,但又必须高于个人经验,如此方能切合全国同行的实际,切不可将个人经验(哪怕是非常成功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在全国同行中推行。
旋律在歌剧音乐中的地位
最近在一份歌剧重大课题的开题报告中看到这样一种观点:长期以来在歌剧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即认为歌剧中优美的旋律就是全部。事实上,歌剧音乐中是各种要素在起作用,歌剧的戏剧性的塑造,其音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合唱、重唱、乐队,即使是独唱,旋律性不强的宣叙性、咏叙性歌唱对于人物的塑造和戏剧性的推动也非常重要。
对这个说法,我有不同意见。首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从未见到有人公然提出“歌剧中优美的旋律就是全部”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偏激甚或无知,显而易见。其次,由咏叹调、咏叙调、谣唱曲、宣叙调、重唱、合唱等声乐形式,与乐队音乐构成的高度复杂而又高度综合的立体化歌剧音乐戏剧性表现体系,同样也没有人公然提出异议。说“旋律只是歌剧音乐的局部”,当然并不错;但这个局部,并非普通的局部,对西方歌剧音乐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局部;对中国歌剧而言,甚至是带有主导意义的局部。
我们先来看旋律在欧美歌剧中的地位。在后期浪漫主义之前,从莫扎特、罗西尼到威尔第、瓦格纳和普契尼为代表的西方歌剧主流,历来重视优美旋律和动人咏叹调在歌剧音乐表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即便后来瓦格纳的乐剧作品风靡整个欧洲,但威尔第在停笔沉静思考了多年,部分吸纳瓦格纳乐剧观念和手法之后,仍决定坚持意大利歌剧“以声乐为主,以优美旋律见长”的传统,于是才有后期的《阿依达》《奥赛罗》和《法斯塔夫》。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普契尼,同样继承了以罗西尼和威尔第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传统,把旋律(特别是具有优美歌唱性和鲜明个性的旋律)创作置于歌剧音乐创作的首位。此外,还有法国比才的《卡门》,几乎每一首歌剧分曲(包括器乐曲在内)都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歌唱性。捷克歌剧、波兰歌剧、俄罗斯歌剧、挪威歌剧和芬兰歌剧,也都非常倚重旋律在歌剧音乐表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今天依然在国内外音乐会上被历代著名歌唱家咏唱不绝、被广大歌剧观众津津乐道的那些经典性的歌剧咏叹调,其艺术魅力生生不息的源泉,正是来自那些抒发人物情感、刻画角色形象的优美动人、过耳难忘的歌唱性旋律。我想,几乎没有人能敢于公开否认这些大师、这些剧目、这些咏叹调、这些优美旋律在西方歌剧史上的经典地位。当然,在瓦格纳乐剧时代的声乐部分,以及后来的西方现代歌剧,基本上都废弃了歌唱性旋律,同样也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经典作品;但若考察全世界广大普通歌剧观众对其受欢迎和被追捧的程度而言,则远逊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剧杰作。也正因为如此,到了20 世纪50 年代之后,随着调性在欧美乐坛的回归,旋律在歌剧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又得到了不少作曲家的重视。
我国作曲家创作现当代歌剧,当然可以废弃优美旋律,因为它另有艺术追求,而不在意普通观众是否喜欢、是否爱听爱看。然而,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对以雅俗共赏为旨归的中国正歌剧、民族歌剧和歌舞剧而言,若否认旋律在歌剧音乐中的灵魂地位,若不讲旋律的优美动听,若不讲旋律的人物个性化和戏剧性,那就是主动自绝于普通歌剧观众,无疑是死路一条。我们再来看旋律在中国歌剧中的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在中国,歌剧艺术是舶来品,中国歌剧是中西合璧的产儿。近百年来,中国歌剧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歌剧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则必须令这种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民歌、说唱和戏曲艺术)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人民审美习惯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强烈华夏风格的中国歌剧。重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审美习惯”?什么是“鲜明中国特色和强烈华夏风格”?
就音乐思维的特性而言,与西方人立体化多声部思维不同,除某些少数民族的多声民歌之外,中国人在长期音乐审美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单旋律的线性思维,即特别注重旋律的丰富表现力,对旋律特别敏感,要求也高,音乐审美多以旋律在横向展开中所蕴含的独特美感为标准,而且其风格、韵味与方言的字音、语调有着最直接、最天然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民间音乐之歌种、曲种、剧种划分的主要依据。
正因为如此,也就决定了中国歌剧何以特别重视旋律的表现功能。因为,既然中国歌剧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写中国人的,写给中国人看的,就必须向莫扎特、威尔第、普契尼的歌剧学习,向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把写好声乐声部的旋律(尤其是符合特定戏剧情境下典型人物性格的、真正动人优美的旋律),写好主要人物的核心咏叹调和抒情唱段置于歌剧音乐表现体系的首位,而不能全然照搬瓦格纳乐剧和西方现代歌剧的模式。
事实上,从最早的儿童歌舞剧、延安秧歌剧;到稍后的正歌剧《秋子》和民族歌剧《白毛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正歌剧《草原之歌》《望夫云》;到新时期乃至新时代的正歌剧《原野》《苍原》《骆驼祥子》,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无一不是坚持“以声乐为主,以如歌旋律见长”的,所以才会有万口传唱的抒情短歌《北风吹》《洪湖水》《红梅赞》《绣红旗》《紫藤花》等,以及百听不厌的大型咏叹调《恨是高山仇是海》《飞出这苦难的牢笼》《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情歌》等等。这一点正是中国歌剧的特点和优点,是它之所以长期赢得普通观众的喜爱,得以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生存、发展的成功奥秘之一。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认同我国现当代歌剧按照作曲家的艺术观念摒弃调性和旋律,也完全可以批评以上提到的多数正歌剧,几乎所有民族歌剧在重唱、合唱和乐队创作中的某些严重弱点,但这些痼疾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治,乃另有原因在,绝非优美旋律之过也。
针对我国歌剧音乐创作的历史与现状,我的主张是,最好是“增强补弱”,即在发扬注重优美旋律这一传统优势基础上,增强宣叙调、重唱、合唱和乐队的戏剧性表现力;而不是“削强就弱”,即宣叙调、重唱、合唱和乐队戏剧性表现力很弱的弊端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又把优美旋律的固有优势丢掉了。
中国当代歌剧的旋律创作是个重大问题
同样在这份歌剧课题开题报告中,有这样的观点,“目前中国歌剧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优美’旋律的堆砌太多,这不符合歌剧的艺术规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只说到了问题的一面。真正成为中国歌剧音乐创作之重大问题者,还有如下三个。
第一,某些歌曲作家用歌曲思维为歌剧作曲,要么,只会写优美的旋律,却全然不知音乐的戏剧性为何物;要么,旋律倒也通顺流畅,但多是大路货、口水歌,毫无特点和人物个性。这些歌曲作家中的某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配器功力太差,写不好歌剧器乐。
第二,一些被作曲四大件武装到牙齿的作曲家,乐队写作的功力很雄厚,唯独就是写不出一段优美的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也写不好宣叙调,只会用飙高音、拼难度手法来获取所谓的剧场效果,然其实际效果是:台上演员的反应是既难唱,台下观众的感觉是又难听!
第三,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则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因此更值得重视——根本否认旋律对于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又根本不顾汉语的四声规律和特殊美感,导致腔词关系别扭,洋腔洋调横行,让同音反复式的宣叙调充斥全剧,令演员和观众都极为反感。
时至今日,除了《狂人日记》《夜宴》《白蛇传》等优秀的现当代歌剧外,中国歌剧的其他类型,如正歌剧、歌舞剧、民族歌剧,仍必须将清新优美、别具一格的旋律写作,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重唱、合唱的旋律写作,列为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重视和研究,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找到切实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在歌剧旋律创作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其一,以中国正歌剧、民族歌剧、歌舞剧注重优美旋律的传统来要求、衡量、批评乃至否定中国的现当代歌剧。其二,以中国现当代歌剧之泛调性、多调性、无调性、十二音等特点,来要求、衡量、批评乃至否定优美旋律在中国正歌剧、民族歌剧、歌舞剧中的重要地位。这两种倾向之所以要注意防止,乃是因为,在当代观念多元、风格多元的健康歌剧生态下,他们却试图将自己的艺术观念和风格强加于不同于己的歌剧观念和风格。
总而言之,在“如何认识音乐元素在歌剧综合体中的主导地位”“如何认识作曲家在歌剧一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如何认识旋律在歌剧音乐中的主导地位”这三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由于中外歌剧之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作曲家及其歌剧观念、艺术素养、技术装备和代表剧目各不相同,故对此人言人殊实属正常。当代中国歌剧家,理应视其中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对待,切不可一概而论。风格与规律不是一码事,风格可以多样,规律必须遵循,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将某些个人经验、某些风格手法、某些歌剧观念、某些偏狭见解甚或某些错误认知下的某些错误实践,打扮成歌剧规律强求人们遵奉。若听凭这些偏狭见解乃至错误认知、错误实践恣意发展,我敢预言,对中国当代歌剧创作而言,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