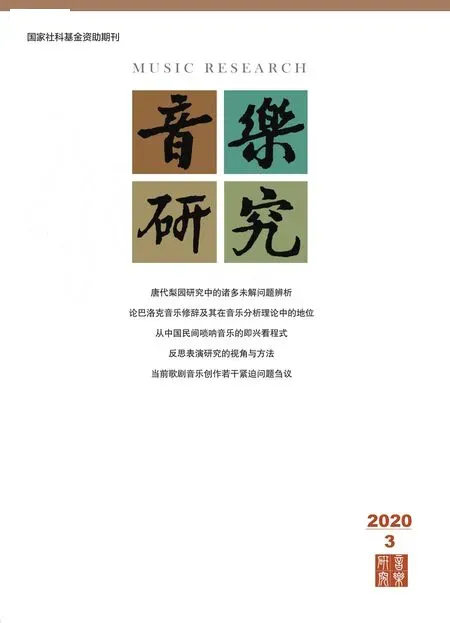“传统的发明”: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元素的融合
2020-12-02欧阳平方
文 欧阳平方
“传统”与“现代”,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是一个“不老的”论题。在西方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即“现代”既是对“传统”的否定,又是从“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而在中国历史上,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是一种“被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以拒斥中国传统为代价。故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与“现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①参见姚新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第51 页。这种狭隘的理解也反映在我国音乐文化研究领域。
当下,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笔者以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绝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现代”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重塑,也不是对“传统”的完全拒斥,二者应是互为存在的关系,即只有“现代”的出现才有所谓的“传统”,而“传统”的意义是相对于“现代”而显现的,“传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②参见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学术研究》2007 年第11 期,第9 页。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率先提出了“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认为“传统”实质上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被发明的”,而“被发明的传统”必然暗合着与过去的连续 性。③〔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 《传统的发明》第一章“导论:发明传统”,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2 页。因而,在全球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叉语境下,我们既要以“传统”为基础,也要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本土化”建构,进而纵深地理解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既是地方的,亦是全球的。④同注①,第56 页。
本文以“原生态民歌”话题作为切入点,在梳理、界定“民歌”和“原生态民歌”概念的基础上,以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的表演实践为例,对其与现代元素融合之范式予以分析,进而展开“非遗”保护视域下“原生态民歌”当代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讨。
一、再议“民歌”和“原生态民歌”
“何为民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已过时,但在现实音乐生活中,大家对传统民歌、创作歌曲、改编民歌、新民歌、“原生态民歌”等类型的理解一直存有混淆。“民歌”基本概念模糊,会在音乐实践中产生诸多问题,如民歌的归属权问题、“非遗”保护对象的审定工作问题,以及其他民间音乐体裁划分问题等。因而,对民歌的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是极其必要的。
(一)“民歌”概念的界定
民歌(folk song),即“民间歌曲”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诸多称谓,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载有:“歌、辞、诗、风、谣(谣吟或民谣)、声、曲(曲子)、山歌、小曲(小令、俗曲或俚曲)、调(小调或时调)”⑤《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36 页。等称谓。“民歌”这一概念术语是在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音乐百科词典》将其解释为:“由人民群众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而集体创作的歌曲”⑥缪天瑞主编《音乐百科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年版,第422 页。。吕骥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总序中指出:“民歌是人民自己的创作,它记录了各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IBSN 中心出版1993年版,第3 页。此外,《民族音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民间音乐概 论》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年版,第8 页;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版,第3 页;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 页。等著述都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劳动中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以口头创作、流传的方式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受人民群众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至此,我们大致可归纳出:民歌是指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口头传唱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歌唱形式,其中“人民性”“集体性”“口头性”是民歌的基本特征。
当前,人们之所以对民歌概念产生混淆,是因为人们对民歌“集体性”中含“个体”因素,“口头性”中含“笔头”因素的模糊,并直接指向对“传统民歌”“改编民歌”“创作歌曲”之间的区分。关于这一问题,我国音乐学界于20 世纪80 年代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歌概念的基本特征已生发异变,“口头性”中有“笔头”因素,“集体性”中有“个体”因素,因而优秀的个体创作歌曲亦可称为“民歌”;⑨宋大能《振兴民歌之路——评1982 年四川省民歌调演兼谈民歌消亡问题》,《人民音乐》1983 年第1 期,第41——44 页;曾遂今《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转化》,《音乐探索》1985 年第1 期,第62——69 页。而不同的观点认为,“民歌”的概念不容转化。⑩苗晶《民歌的概念改变了吗?——读〈振兴民歌之路〉有感》,《人民音乐》1983 年第3 期,第34——35、16 页;晓明《也谈民歌——与宋大能同志商榷》,《人民音乐》1983 年第2 期,第32——33 页;彭国华《民歌概念不容转化》,《音乐探索》1985 年第4 期,第83——84 页。关于民歌“集体性”中的“个体”因素问题,黎英海先生早在1956 年就有过论述:“民歌是人民的集体创作,或者也有少数是一人创作后又在流传中经过世世代代人民的修改而形成的。”⑪黎英海《试谈民歌改编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56 年第10 期,第19 页。
笔者以为,民歌终归是姓“民”的,它必须经过人民的集体检验,即便其存在“个体”创作因素,但亦要经过人民群众长期的生活口头提炼方能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性。民歌之所以为民歌,是因为其“人民性”、“实用性”(言情志事)、“集体性”、“口头性”之概念内涵(还有“地域性”特征)。这是当下我们区分“传统民歌”与“创作歌曲”“新民歌”“改编民歌”的“根”之所在,也是民歌与现代元素融合过程中需要维系的“本真性”所在,不可把民歌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
(二)“原生态民歌”及其当代传承、传播、发展与创新
进入21 世纪以来,在民歌研究领域涌现出一股新文化时尚潮流,即“原生态民歌”。“原生态”一词,源于自然生物科学领域,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⑫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人民音乐》2006 年第1 期,第26 页。,泛指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用“原生态”来指称民歌(即“原生态民歌”),最早见于1996 年古宗智《贵州民歌的文化特征》⑬该文首次在音乐文化领域提及“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和“新生态”的概念。参见古宗智《贵州民歌的文化特征》,《音乐研究》1996 年第1 期,第61——65 页。一文。2004 年在山西左权举行的“中国第二届南北(原生态)民歌擂台赛”,坚持“原生态民歌”单独比赛规则。在音乐领域,对“原生态”一词用得最为明确、产生影响最为广泛的是2006 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十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该赛事把“原生态唱法”单独列为一个门类,引发了音乐界与媒体界对“原生态民歌”的广泛论争与质疑。⑭参见樊祖荫《由“原生态民歌”引发的思考》,《黄钟》2007 年第1 期,第94 页。论争与质疑主要聚焦于“原生态民歌”的提法及其对音乐类“非遗”保护的价值。⑮关于“原生态民歌”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已是“约定俗成”而无须易改,如樊祖荫指出,从歌唱主体、民歌词曲、歌唱语言的方式方法、表现形式及伴奏形式来看,舞台上的“原生态民歌”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并考虑到现实媒体大众对这一称谓似已约定俗成,不一定非改名称不可;田青认为,“原生态”唱法与“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的命名一样,虽不甚准确,不可评比,但对其取名实属一种约定俗成;等等。另一方面,从表演实践层面来说,“原生态民歌”在演唱的场域、形态、心态等方面发生转变后,还能否称之为“原生态”的问题,成了论争之焦点,冯光钰、杨民康、桑德诺瓦、刘晓真和赵晓楠等人认为,只要离开民歌的原生环境,则不能称之为“原生态民歌”;另一种观点是,虽说舞台上的“原生态民歌”离开其原生环境,但它的提出却“充分表达了大家对‘原生态民歌’的热烈追求和理想”。
在中国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过程中,“原生态民歌”已成为一种时代热点现象,并辐射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可以说,类似于“原生态”“本真性”“活化石”“原汁原味”等词汇,在一定时期内代表了国内音乐类“非遗”保护的重 要方向。⑯参见姚慧《何以“原生态”?——对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文艺研究》2019 年第5期,第143 页。当前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讨论已逐渐减少,但它自2006 年兴起至今这十多年来,诸多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仍未解决,如“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遗产与资源”等关系,仍需要做进一步讨论。
“原生态民歌”是作为现代性的概念而出现的,它是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为适应人们现代生活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文化重构现象,表达了传统民歌在与现代元素融合过程中,一种走向现代性但又有别于现代文化的相对规定,⑰参见马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变迁中的地方社会》,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8——180 页。它是在现代社会中被发明与再生产的文化“传统”。⑱同注③,第1——17 页。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关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传播、发展与创新等问题。
当前,许多人出于对“原生态民歌”进行传承、传播、发展与创新之目的,对民歌进行加工、改编或据其音调进行创作,涌现出诸多的音乐样式。那么,经过改编或创作的民歌还能否称为“原生态民歌”?这涉及前文所述民歌概念及其外延的问题。为此,首先需要区分“原生态民歌”与作曲家“创作歌曲”⑲本文所述的“创作歌曲”均是指借鉴原生民歌元素进行创作的歌曲。之不同;此外,经改编的“原生态民歌”虽然离开了原生环境,但如果仍留有原生民歌的本质风格特征,则仍可看作“原生态民歌”之外延。⑳参见樊祖荫《集中展现中国民歌文化多样性的歌唱盛会——从传承与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原生民歌的展演活动》,《中国音乐学》2010 年第4 期,第101 页。这里还涉及“改编民歌”与“创作歌曲”的区分,对其区分则须把握当中存在的“阈限”问题,即保留“原生态民歌”本质风格特征 的“量”。[21]笔者曾就“改编民歌”与“创作歌曲”(根据原生民歌元素创作)的区分问题,多次求教于樊祖荫教授并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从传承、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角度来说,“原生态民歌”“改编民歌”“创作歌曲”均存在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从传承的角度来说,传承当前存在于民间“相对自然”的“原生态民歌”,是我们极力追寻的。这类民歌的歌唱主体、演绎场合、曲调形式、语言声调及其用乐观念等方面,均具有本土的生活习性特征,是当前“非遗”保护的文化基因所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各种外来强势文化的挤压,当前这一类“原生态民歌”,在现实民间音乐生活中的生存空间正日渐式微。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改编民歌”对“原生态民歌”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在现代媒介中演绎的“原生态民歌”,多是经过改编而成的,这种改编虽脱离了民歌的原生环境,但其歌唱主体、曲调形式、语言声调及用乐观念等方面,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而是较为本原地再现了本土的生活习性特征。现代媒介的传播功效及其更吻合现代人审美眼光的优势,又促进了“原生态民歌”的传播。这也说明,民歌在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过程中,“原生态民歌”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不仅存在于“具象化”层面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存在于歌唱主体“抽象化”的思维观念层面,这也是对民歌生活习性的情境再现。
此外,“改编民歌”与“创作歌曲”都是经过专业作曲家对“原生态民歌”的吸收和提炼,融合现代元素并保持其文化“本真性”特征,进而实现了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变,是有效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现象,因而从发展与创新的角度来说,它们是有益的。虽说这些歌曲作品是从“他者”视角,将“原生态民歌”的音乐形态、行为方式作为一种彰显本土生活习性的符号标志进行再改编与创作,但从中也可显现“原生态民歌”的文化记忆,这亦可促发人们进一步去认识和体悟“原生态民歌”的文化特征。
综上,厘清“民歌”的内涵与外延,有助于我们对民歌的当代传承与传播;辩证、客观地认识“原生态民歌”现象,则有助于我们对民歌与现代元素融合的分析与思考。在全球化语境中,传统音乐文化不仅是作为过去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传承是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传播与发展,发展与创新是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利用,这是一个动态、互惠的过程。但不论是传播与发展,还是创新与利用,都要以传承的“本真性”(尽管是相对的“本真”)与“整体性”为基础,否则将会使“传统的发明”沦为无“根”之本。下文以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的表演实践展开具体论述。
二、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元素融合之范式
苗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除中国以外,还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及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22]参见张晓《跨国苗族认同的依据和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10 期,第15 页。贵州是国内苗族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23]参见石茂明《跨国界苗族(Hmong)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2 页。世居贵州的苗族同胞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民间还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不会唱歌难做人”之说法。不同类型的苗族“原生态民歌”,描绘了贵州苗家人的生活画面,主要包括古歌、飞歌、游方歌、酒礼歌、婚嫁歌、丧葬歌和儿歌等类型。
当下,全球化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其采取何种态度,它都不容否认地存在着并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24]参见薛晓源《前沿问题前沿思考: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追踪与探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 页。在这种社会情境中,贵州苗族社区被“裹挟”进入了全球化进程,苗族“原生态民歌”遭遇了全球化的文化冲击,这是一种被动且无法回避的境况。既然无法回避全球化,那么,能否变被动“裹挟”为主动参与,能否在坚守苗族“原生态民歌”本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即传统与现代的“视界融合”[25]党圣元《回到原点:再论传统文论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1 期,第47——58 页。呢?下面,笔者将从“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现代旅游开发”“现代舞台文艺展演”三个层面,对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进行分析。
(一)与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融合
当前,人们对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地方性音乐知识”日渐关注,这也充分反映在现代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即作曲家结合具有“原生态”意味的民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以彰显音乐作品的地方性特征。创作此类作品,往往是为了吻合现代文艺舞台展演与现代大众审美趣味。词曲作者往往会按“本我”的知识结构,去挖掘所认为的“原生态”民间音乐素材,再按现代作曲技术理论进行再创作。
以苗族“原生态民歌”元素创作的现代音乐作品,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醉苗乡》《家乡的味道》《苗乡侗寨》《苗岭飞 歌》等。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是因为作曲家在创作中突出了歌曲的苗族文化风格特征,以及运用了丰富的苗族民间曲调。
例如由李再勇作词,浮克作曲,阿幼朵演唱的《醉苗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原生态民歌”的看法。“让民歌通俗起来了”便是对其最好的诠释,歌曲中的传统苗族音乐元素在现代专业音乐创作中变得个性、时尚、动人。[26]《让民歌通俗起来》,《贵州都市报》2007 年7 月18 日。笔者认为,《醉苗乡》成功的原因在于,词曲作者的“二度”创作和演唱者的“三度”演绎,均建立在对苗族音乐文化的深层理解之上。
该曲的苗族音乐文化特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苗族原生音乐文化场景的再现。苗家人素来热情好客,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曲名《醉苗乡》与歌词“敬酒的飞歌飘山梁”,诠释了苗家人的酒俗和歌唱文化。苗家人能歌善舞,且崇拜鼓,歌词“苗山人的木鼓敲得山岗响”,表达了苗家人对鼓的自然崇拜。芦笙是苗家人的“圣器”,歌词“苗乡人的芦笙吹得东方亮”,表现了苗家人的乐俗文化。歌曲高潮部分“苗乡人,爱苗乡,苗乡人,情豪放”,充分表达了苗家人对苗族文化的深层认同。此外,歌曲中穿插的流水声、苗族日常说话语调等听觉元素,为我们营造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是对苗族民间音乐元素的挖掘。歌曲的引子与尾声是用民间木叶吹奏的,引出传统苗族飞歌旋律,整首作品始终穿插着木鼓的击奏。歌曲的音列为Do——Re——微降Mi——Mi——Fa——Sol——La,调性以五声性为主,其中微降Mi 与Fa 的运用,反映出苗族民间音乐的调式调性特征。此外,歌曲创作还考虑到苗话的使用。
可以说,《醉苗乡》这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元素的融合,它吻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反映出人们对“地方性音乐知识”的倾心,表达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性,而对话的张力亦将促发人们对苗族音乐文化的体验与感悟,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二)与现代旅游开发的融合
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相结合,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贵州苗族地区,“原生态民歌”是当地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西江千户苗寨”是当地旅游开发的重要场域之一,苗族“原生态民歌”成为旅游开发商的重要宣传“名片”。当地青年芦笙乐手杨昌杰认为:“以前我们这里还没有搞旅游的时候,唱苗歌、吹芦笙的人比现在少多了呢!现在好多家里都让孩子学(唱苗歌),因为可以得钱啊,同时我们唱自己的歌、吹自己的芦笙也开心呢!”[27]笔者于2014 年8 月23 日对杨昌杰进行采访。由于苗家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演唱“原生态民歌”可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进而增强了他们对苗族“原生态民歌”的传承动力与文化自觉;此外,旅游者在苗族“原生态民歌”展示过程(这种展示既是地方性的亦是全球化的)中,进一步了解苗族民间音乐文化,客观上也推动苗族音乐文化的对外 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代旅游开发为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的当代传承与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这个重新发明与建构“传统”的过程中,如果不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逻辑(即文化持有者的主动参与及文化的“本真性”与“整体性”)而进行新的文化符号建构的话,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也是难以实现的。也就是说,若要使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旅游开发进行有效融合,则需要倾听当地苗族音乐文化持有者的声音,尊重苗家人的文化生存选择,以及苗族文化的主体性历史文明。
(三)与现代舞台文艺展演的融合
上述关于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专业音乐创作、旅游开发的融合过程,均涉及与现代舞台文艺展演的碰撞与融合,此类舞台的存在是由不同文化主体参与整合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而共同建构的。在融合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对苗族“原生态民歌”进行提炼、加工与改编,使其有别于传统而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有关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要不要变的问题,学界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传统音乐要生存与发展,定然要融入现代社会,必须对其进行提炼、加工与改编,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提炼、加工与改编什么?如何进行?谁来进行?其音乐本质是什么?其音调、律制、节奏、音色、行为方式、观念体系是如何表现音乐本质的?这不仅是音乐理论研究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的实践创作问题。[28]参见张应华《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年版,第129 页。对此,笔者认为需要政府部门、音乐创作者、改编者、旅游开发商等深入了解苗族文化,加强对话与交流,进而在深入体验苗族民间音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苗族民间音乐元素,并对其音乐形式进行 内化。
当前,在现代电视媒介主流文化的影响下,通过传唱中国“原生态民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音乐类竞演节目层出不穷,它们为来自不同区域族群文化身份的传唱者,提供了一个向世人展示自己族群“原生态民歌”的现代文艺舞台。歌曲《对歌对到日落坡》,是苗族歌手蝶当久[29]蝶当久,原名为潘兴周,在当地被誉为“苗族歌王”,2017 年2 月于《耳畔中国》亮相并成功晋级;同年10 月,参加《中国民歌大会》;次年,他与被誉为“苗族歌后”的阿幼朵,一同参与2018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贵州黔东南分会场的演出;代表专辑为《对歌对到日落坡》。的代表性作品,他曾将其带上《耳畔中国》《中国民歌大会》等现代文艺舞台。歌曲在保持苗族“原生态民歌”原有风格韵味的同时,又融合了现代多元的、符合当下大众审美情趣的流行音乐元素。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具体表现为:歌曲的前奏与尾声部分,蝶当久采用了当地苗语方言演唱;在主歌部分较好地再现了苗族“对歌”的生活场景,如歌词“隔山隔水唱飞歌”“吹起芦笙去游方”;在歌曲伴奏方面,由音乐人捞仔担任乐队指挥并对现场电声乐队进行配乐;整首歌曲的演唱,始终穿插着蝶当久的原生苗语演绎。
虽说现代文艺舞台上的《对歌对到日落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苗族“原生态民歌”,但它说明了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文艺舞台进行有效融合的可能性,让人们间接体验到了苗族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在与现代元素融合过程中的原生张力。这对于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传承与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进行“本土化”重建的一次尝试。
余 论
不论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理论到现实,还是从西方到东方,人类文化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不断发展并获得新 生。[30]参见张再林《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5 期,第66——68 页。诚如黄翔鹏先生所云,“传统是一条河流”[3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年版,第1 页。,故而绝对意义上纯粹的传统音乐文化是不存在的。因此,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与创新的探讨,我们要立足其自身的社会语境,还需要辩证地认识到不同文化选择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不必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性变迁持一味的批判态度,但我们要找准传统音乐文化的“根”,即文化的“本真性”与“整体性”,这也是当前我们对“民歌”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特征,进行界定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近年来,民俗学与人类学界,对于“本真性”与“原生态”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如刘晓春提出了“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32]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 年第2 期,第153——158 页。的问题;刘正爱提出了如何界定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之系列问题;[33]刘正爱《谁的文化,谁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认知困境与理性回归》,《民俗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10——18 页。等等。在国际性“非遗”保护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 年通过的“非遗”保护决议中,提出了要禁谈或慎谈“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主张,[34]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s://ich.unesco.org/en/。2015 年审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第八条指出,“本真性”不应构成“非遗”保护的问题,主张“非遗”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35]参见巴莫曲布嫫、张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民族文学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6 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提出对“原生态”“本真性”等概念的禁用或慎用,是因为这些概念与“非遗”的动态性、活态性特征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非遗”文化事象的“原生态”与“本真性”,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一种文化一旦从原有的生存语境进入新的语境,它便不再是原有的“本真”,新的语境定然会使它与周边文化发生融合与互动,进而获得新生。当然,文化的新生,绝不是“无本之源”式的任意发展,而应是在其文化主体性历史文明的积淀中进行的。故而,我们在关注国际性“非遗”保护动态之同时,更需要根据中国自身的文化现状去处理问题。笔者以为,“本真性”仍可作为我们当前“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方向路标,因为这种“本真性”并不是指向传统文化的“固态化”表征,而是指向其历史文化主体积淀下的“动态化”过程。因而,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须在继承其“本真性”的基础之上,以发展的眼光将其与现代元素进行融合,进行新时代意义的“传统的发明”。
民歌作为人类社会音乐艺术的基础,[36]参见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版,第3 页。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其概念内涵的梳理与界定,有助于解决当前一些不易解决的音乐现象。对于“原生态民歌”现象所引起的诸多论争与质疑,直接关涉到民歌的当代传承、传播、发展与创新问题。本文所分析的贵州苗族“原生态民歌”与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现代旅游开发、现代舞台展演的成功融合案例,初步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互生式”对话,及其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与发展之路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