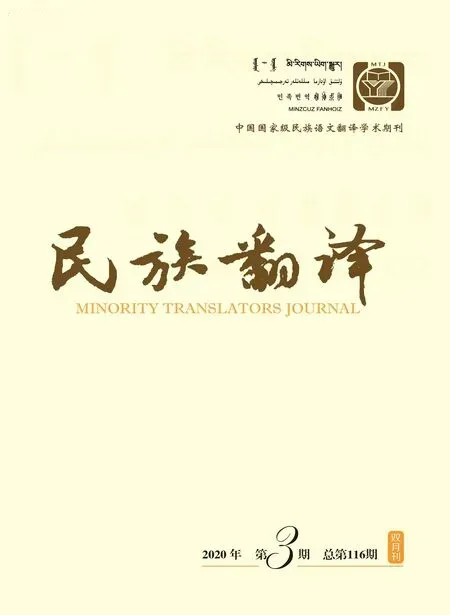民族志撰写模式的嬗变与西方翻译研究发展的相互观照*
2020-12-02李寐竹
李寐竹
(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一、引言
随着译学疆域的不断拓展,跨学科特性在翻译研究中体现得愈发明显。近年来,文化人类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在国内外译学发展中兴起,并且逐渐成为人类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话题,这无不与翻译研究的“文化属性”息息相关。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跨学科研究的版图上,作为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展示形式——民族志,其与翻译研究的相互观照理应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个案研究为主,极其缺乏从历时角度对民族志撰写方式及其与西方翻译研究不同时期理论观点、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的相互阐发展开动态观察,相关成果尚付阙如,这造成了民族志与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相互征引利用方面的严重失衡和对于其整体脉络与动态发展认识上的偏颇。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族志撰写方式的嬗变出发,探讨“何为翻译”“如何翻译”“为何翻译”在不同阶段的历时形态变化,以期从整体历史脉络中把握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互鉴,并尝试提炼出翻译学在文化人类学中所体现的重大实践价值和理论参考价值,以及文化人类学为翻译学领域拓展注入的新生学术生长点。
作为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展示形式,民族志文本是一种关于“他者文化的描述”。民族志中“文化的描述”关注的对象并不是印刷出来的文本,而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是对“他者”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整体“再现”。在文化“再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化“翻译”的影子。事实上,“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本身就来源于人类学民族志实践当中。为了对人类学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阐释给予学理性指导,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社会人类学大师、牛津大学教授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chard)的倡导下,文化翻译逐步成为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者认同的使命。[1]这就引出了民族志文化翻译的核心——“文化作为文本”(culture as text)[2],其为人类学与翻译学都注入了新的概念。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57)中文本概念的不断扩大,无不为这一术语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论基础。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在《翻译理论探索》(ExploringTranslationTheories,2014)一书中为民族志视角下的文化翻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英国社会民族志的传统之下,文化翻译指对外国文化的描述,也就是说,民族志学者将他国文化“翻译”成了(以英语写就的)民族志描述。[3]由此可见,民族志视角下的“文化翻译”与传统意义上有着源文本的“翻译”概念并不一样,此处以“他者文化”为“源文本”,是通过语言转换和文化意义的传达和阐释,将他族文化向本族读者转述和引介的过程。可见,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和阐释,不仅单纯指代语言技术层面上的转换,更多的是解读与建构“他者文化”的意义之网,而这也构成了二者相互阐发的基础。
二、民族志发展的四个阶段与西方翻译研究的相互观照
(一)“探索性”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人类学前学科时代的民族志具有“探索性”(exploration)特征。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中,以东方旅行见闻游记、探险家著述及传教士或者殖民政府官员写就的民族志报告为代表。初来乍到,欧洲的探险家和旅行者经常会遇到了解“他者”文化的困境。最初使用的手势与符号很快就被通用语和洋泾浜用语所替代,而这一批最初学会通用语和洋泾浜的人就成为了最初的译者。[4]2这些先锋者不仅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了语言转换的功能角色,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由此扮演了“传送带”的角色。他们向西方社会专业学者们传递了“他者文化”,诸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在图书馆或办公室里做研究的人类学家们都是这条“传送带”的受益者。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易洛魁联盟》(TheLeagueoftheHo-de-no-sau-neeorIroquois,1851)是第一部详述易洛魁人亲属制度、物质文化及宗教信仰的经典民族志作品,所有的素材来源于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易洛魁人,此人名叫帕克(Ely S.Parker)。虽然摩尔根在19世纪60年代曾亲自到北美印第安部落收集过有关亲属关系的数据,但他所采用的大部分素材都是源自于印度或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及业余爱好者。[5]
遗憾的是,翻译在人类学前学科时代完全处于附属地位,没有人关注翻译在数据采集中的关键作用,更遑论对翻译本体的探索。对当时的人类学家而言,这些数据资料在收集过程中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是否用到了译者?翻译策略是什么?翻译后的数据资料是否产生变动?这些都不在当时人类学家的考察范围内,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信息本身,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去支撑他们对理论图示的假定。[4]2翻译在这一时期“传送带”式的概念,导致这些完全未经考证的民族志资料被贴上“臆想的民族志”的标签,而基于其建立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文化演变构建也难免引发了后世的诟病。
即使是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自己走进“田野”采集数据,翻译在数据采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仍然没有被给予重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博厄斯(Franz Boas)在加拿大因纽特人社区中生活和考察了一年多,并开始建立起文化相对性的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续著作《夸扣特尔人民族学》(EthnologyoftheKwakiult,1921)一书中呈现了夸扣特尔文和英文版的对照,并著文以强调文化中语言的中心角色,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是对濒临消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事实上,博厄斯意识到这种来自新世界的语言组织确实与印欧语系不同,而这种分属于不同语法范畴的差异性也正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4]2
(二)“科学性”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一书中,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准则。科学的民族志指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合二为一,并能够保证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验和对当地土著语言的熟练掌握和运用。[6]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诸如: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弗思(Raymond Firth)等人深受英国社会人类学和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认为与洋泾浜语、通用语或殖民地政府官方用语相比,学习和使用当地语更为重要,因为由此可以避免“剥夺了文本的所有重要特征——抹去了所有要点”。[7]但是,民族志的最终流向是西方读者群体,即使参与观察的过程中使用当地土著语言,最终文本的呈现仍然是以西方语言规范来书写,翻译仍然是人类学者们无法绕过的屏障,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学者认真思考翻译对他们理论建构的影响。
这一阶段,人类学家自己的身份从过去“书斋”中的资料接收者转变成了“田野”中的资料制造者。如果把“他者文化”看作是“异文化文本”,那么人类学家则是这一域外文本的译者,民族志则是向西方目标语境流通的译本,是用西方社会科学语言来翻译非西方文化的产物。此外,科学民族志也被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强调以“整体”“客观”“描写”的方式将遥远的土著部落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客观性”与“描述性”决定了这一时期民族志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属性”,其本质为基于模仿论的语言转换技艺。尤其是后来的结构主义盛行时期,翻译研究本质被定义为是“科学”的,对翻译的态度偏重于“客观”,即重点是“基于语言学”的研究。[8]两个学科同时强调“科学性”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种争夺各自学术地位独立化与合法化的必然结果。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社会科学界要求自己成为一种“科学”的呼声很高,力图使自己能够独立而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9]
此外,人类学家身份的转变让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实质上是对“他者文化”的“翻译”工作。牛津大学是英国最早开始关注“文化翻译”的人类学中心。林哈德(Godfrey Lienhardt)在1954年发表的《思维模式》(ModesofThought)一文中明确指出:“向他人描述遥远部落中的成员如何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翻译问题被提了出来并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原本就存在于异邦语言中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始思维可以用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思维的一致性清楚地再现出来”。[10]此外,同样出身于牛津大学的贝亚蒂耶(John Beattie)也强调“翻译问题”在社会人类学中的核心地位,并且指出这也成为了人类学家向目标语境受众引介他族文化所面临的主要困境。[11]另外,剑桥大学教授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认为社会人类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确立为翻译文化语言所用的方法论。[12]至此,“文化翻译”正式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广泛运用于民族志研究、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当中。
该阶段的后期,一部分人类学者对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作为一个欧洲白人如何保证不受西方价值序列体系的介入而对原文本(“他者文化”)做到绝对的“忠实”?就如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笔下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波斯诗人俄默·伽亚姆(Omar Khayyam)的例子,认为自己应在其译文中“展现自由”,同时也使之更符合当时西方文学的规范。[13]此外,也有人对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的“纯洁性”提出了疑议,即其研究是否为殖民政策服务抑或其功能主义理论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事实上,这也正是记录当地语言文法的人类学家被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视为直接“参加支撑殖民主义权力基础的庞大的收集与编纂工程”的历史缘由所在。[14]
(三)“阐释性”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20世纪后半叶,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特纳(Victor Turner)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也被成为解释人类学)登上历史舞台。象征人类学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符号,尤指公共符号(public symbols);二是理解,且为“在解释之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三是观点,特指“土著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在格尔兹看来,民族志作者的任务是从当地“土著的观点”出发,去阐释当地人对社会公共符号的解释(只有当地人能够做到第一层解释),是阐释之上的阐释。而这些公共符号背后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从而建构出“社会性话语”(social discourse)。要将这张“意义之网”予以解码,就必须对被放置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的“话语”予以“再现”。英国社会学家霍尔(Stuart Hall)指出,文化的再现是形成文化的核心行为之一,再现是一个意义通过符号被建构的过程。[15]在此处,再现后符号群集合体的文本形式,就是这一时期带有浓厚“深描”色彩的民族志文本。格尔兹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1973)一书中开始倡言关注“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深入当地土著浓厚的人文背景当中,从他们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文化体系剖析其中的公共符号及意义。由此,过去传统翻译学所讨论的“不可译性”也得以重新解释。翻译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对等”与“忠实”,而是读者对译作做出不同的阐释,译作又是译者对原作的阐释。而在民族志翻译中还多加了一层当地人对当地文化的阐释,翻译最后成为了阐释之上的阐释之阐释。这一观点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延异”观不谋而合,每一个文本与先前的文本都略有不同:它们都是翻译的翻译。[16]12
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对照格尔兹的深度描写,著文《深度翻译》(ThickTranslation)(2000)并加以阐释。所谓“深度翻译”,指通过为译文添加注释、评注等手段,将其置于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当中。[17]据这篇论著所述,加纳中南部城市库马西的阿坎人口头文学被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阿皮亚发现在翻译中最让他感兴趣的绝非字面意义,而是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指导下语境中的语用意义。然而,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似乎并不适用,因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并不是表达作者的语用意图,而是源语中的核心文学属性得以共享,这是字面翻译远不能及的。那么,理想的文学翻译就应该是译本和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关系,就如同源文本和源语文化的关系一样,以获得相同的语用理解和读者期待,但这种理想状况通常是不可实现的。在阿皮亚看来,文学翻译应该被看作一种“学术翻译”(academic translation),并在文学教学当中体现其重要性,借助注释与评注等手段重构源语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并促使读者了解源语言话语中的隐喻意义,这有助于克服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自卑情结。
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也著文《作为深度翻译的跨文化翻译研究》(Cross-culturalTranslationStudiesasThickTranslation,2003)探讨了深度翻译的概念。与阿皮亚不同的是,在他看来,“深译”至少一部分是作为对当前翻译的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个广义形式的描述或翻译手段。他认为,“深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工具,具备对抗翻译研究中公式化术语还原的潜在功能,相反还会引入更多元的词汇系统,不失为一种可以减少变形误读和翻译难度的有效方式。如此一来,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两大“错位”(dislocation)便不会发生:一是源文本不需要被外来方法论和词汇系统探查以致扭曲,二是目标语译者也不需要为了适应相似性或差异性而改变自身原本的话语惯例。[18]387此外,“深译”还具备对同期其他翻译文本的批判功能。该论著中伊拉斯谟(Erasmus)就认为他的译本(充满大量的脚注、注释、阐释)是一种对哲罗姆(Jerome)译本的修正,且大量的注解甚至将原文缩小化了。赫曼斯还在文章的结尾列举了“深译”的优势,其中的两个观点值得思考:一是“深译”试图通过引入翻译的其他概念和隐喻来质疑西方翻译理论的权威;二是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抵消了翻译中“透明的幻觉”以及中立的描述,并将一种叙事性语言带进描述中,从而使描述具有了明确的视角。[18]388
至此,我们了解到“深度翻译”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在译文中尽可能地“厚语境化”,以接近所研究的文化用语和思维。其实在此之前,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概念——“释译”(gloss translation),即最贴近源语结构和内容,通过附以注释阐明文化差异,使得目标语境中的读者得以最大限度地了解原语文化中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表达路径。[19]159但是,奈达也同时关注读者的需求,指出翻译应以“表达得自然”为特征,源语文本场景的“异域性”亦应减至最低。[19]167-168正如韦努蒂谈到的“透明的幻觉”,这意味着翻译必须具有易读性,让译者和外界条件影响下的翻译至于无形。但是,在人类学家看来,这样流畅的翻译是对“目标语境”的妥协。他们认为应在“翻译”尽可能忠实的情况下,通过“抵抗”或“异化”翻译来强调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除了考虑可理解性外,不应做出任何让步以使描述更能被目标受众接受。[4]9显然,人类学家需要处理翻译的这些互不兼容的方方面面,同时还要关注他们所做的工作应该达到何种平衡。
(四)“实验性”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思潮下,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对以往“科学性”和“阐释性”民族志文本和理论加以质疑的人类学潮流——后现代人类学,也被称为反思人类学。反思人类学提出新的“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ies),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组织并讲究艺术性;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现象进行阐释。[20]
“实验民族志”摒弃了传统科学性民族志与阐释性民族志中对人类学家主观能动性的忽视,彰显了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地位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实验民族志反对科学民族志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与事实描述的“客观性”相分离而得出的结论,不仅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予以展现,同时也把这一时期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说”纷纷予以呈现,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即将人类学家自己也作为被观察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以往的阐释性民族志从“土著观点”出发,而实验民族志则主张对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体系予以彰显。这让这一阶段的民族志体现了更多的“人情味”,让民族志文本翻译中的译者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研究对象,这与翻译研究文化范式下的译者转向不谋而合。
同时,“实验民族志”强调文本的“艺术性”特征,认为民族志向来就是文化的“创作”(cultural invention)。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Routes:TravelandTransl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1997)一文中,终于正面探讨了翻译的问题。他支持在关键术语“traduttore, traditore”中隐含的观点,即“译者是一个叛徒”。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应该知悉在理解、欣赏和描述“他者”文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被遗漏,被歪曲的情况。[21]在此之前,盖尔纳(Ernest Geller)也在其文章《概念与社会》(ConceptsandSociety,1970)中指出并不存在调解当地语言和自己语言的第三种语言,各自的语言有各自处理世界的方式,因而容易歪曲那些被翻译的东西。[22]这两者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志作者在将“他者文化”翻译成文本之前,势必要对“土著语言”看待世界、信息传达及意义获取等方式进行“重写”,然而所有的重写(改写),不管它们的意图是什么,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文学的社会功能。[16]ix
“实验民族志”的第三个特点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关于“文化翻译”的术语建构,并开始探索权力如何进入“文化翻译”话语实践场域。英国人类学家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于1986年在文章《论英国社会人类学中文化翻译的概念》(TheConceptofCulturalTranslationinBritishSocialAnthropology)中指出,盖尔纳虽然开始关注人类学家解释和翻译异域社会(alien societies)的话语问题,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文化翻译”当中“不平等的语言”问题,以及在不可避免地陷入权力的条件下对话语隐含意义的判定。这种“不平等性”体现在“‘文化翻译’必须使自己融入一种不同的语言,已经确立的强大的生活结构(有它自己的话语游戏和它自己‘强大的’语言)的僵化,和其他的因素一道,最终决定了翻译的有效性”。[23]在这样的状况下,以西方语言写就的民族志与被研究的非西方民族之间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而这也不是任何民族志或翻译中的个别手段所能克服的。在翻译学领域,学者们通过倡导异化以打破目标语的文化符码,强调文化和语言形式的不连续性和多样性。这种方法旨在抑制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是一种文化干预的策略,反对英语霸权国家和他们与全球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24]这种方法似乎与人类学的目标相一致,这一时期无论是民族志文本还是作为进入目标语文化的译本,都抵达了文本实践之外的权力和抵抗。
三、结语
在民族志撰写模式演变的“探索性”“科学性”“阐释性”以及“实验性”这四个阶段中,民族志研究和翻译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转向都极为相似。以“探索性”为特征的人类学前学科时代民族志阶段,翻译扮演着向西方社会专业学者们传递他者文化的“传送带”角色,“何为翻译”“如何翻译”在数据采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没有被引起重视;进入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科学性”民族志阶段以来,“照相机式”的现实主义观察决定了这一时期民族志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属性”,该阶段的后期由于人类学家身份的转变,让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实质上是对他者文化的翻译工作,“文化翻译”正式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广泛运用于民族志研究、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当中;在格尔兹倡导的“阐释性”民族志时期,对照深入当地土著浓厚人文背景中的“深度描写”“深度翻译”概念应运而生,翻译研究从前一阶段的“语言学属性”朝向“文化属性”发展,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当中的话语隐喻意义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核心;最后,在反思人类学旗帜引领下的“实验性”民族志阶段,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中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之阐释探讨了“改写”的必然性,并从“文化翻译”中“不平等的语言”开始探索权力如何进入“文化翻译”话语实践场域。
由此,翻译研究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众声喧哗,这无不与两者之间相同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研究的关注范围从过去固有的“语际翻译”发展出新兴的“文化翻译”概念,这不仅为人类学学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阐释给予了学理性指导,也为新出现的翻译现象与翻译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依据;同时,翻译学科也受诸如“深度描写”这种民族志方法论的启发,发展出了“深度翻译”的手段方法,在此基础上继续衍生出“副文本”研究、文本内深度翻译和文本外深度翻译等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对翻译研究的认识经历了从“早期自由式翻译的热情”[25]到诉诸于科学性的“语言学转向”,再到后现代思潮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演变。由此翻译研究的发展路径从单一的文本对照、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发展成为原作者、译者、读者都参与到文本再现的多元文化环程当中,且参与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性以及意识形态、诗学及权力因素等都促进了文化的循环和互通。
从上述简略的历时性回顾当中,我们似已初步了解到文化人类学中民族志与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阶段特征、动态发展趋势和相互交织的理论观照与借鉴,其所引发的学术问题跨越了学科、历史和地理的界限,也将成为跨学科交叉型研究当中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笔者希望本文不仅能够为此提供概貌性的历时发展路径,同时还能通过不断的交叉比较研究促进翻译学研究内容的创新、翻译实践方法的拓展以及对翻译理论研究认识的深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学科在我国的长足发展添砖加瓦。
注 释:
①虽然当代出现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人类学”,即以“本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大部分民族志作品仍以对“他族文化”的研究为主,因本文主要考察对异文化的研究,故以“本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并不在该文的考察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