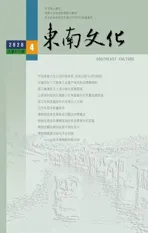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可视化设计
2020-12-01范陆薇李富强隋吉祥
范陆薇 胡 波 李富强 隋吉祥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物馆 湖北武汉 430074;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发展规划处 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可视化作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主流输出途径,是近年来博物馆解说牌中常见的表达方式。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是以科学性为前提的美学表达。然而,我国博物馆解说牌存在可视化信息的个元选取求泛而不求精、忽略可视化加工技术与加工对象的相互匹配、缺乏对展览信息的逐级解码、互动性和参与感不强等现象。根据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加工的“简单、相似、连续、一致、关系”的原则,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设计可按照信息采集—信息架构—视觉转化—符号传达的建构流程,以使博物馆解说牌的设计更加个性化、人性化。
一、导言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迅猛。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博物馆数量由1996年的1219家,发展至2019年的5535家,年接待观众总人次12.27亿[1]。随着博物馆数量的激增和运营理念的革新,展览作为沟通博物馆与观众的桥梁,不仅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开展非正规教育的核心平台。新形势下,博物馆的展品不再是展览的唯一焦点,它变身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博物馆从“展品首位”走向“观众中心”,强调传授物件相关知识,重视物件之于观众的意义构建。展品信息的选择、分类、安排、拓展和表达在展览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博物馆解说牌是博物馆向公众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在《阐释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书中提出“解说通过直接的体验和媒介的介绍来揭示事物内涵和相互关系”[2]。博物馆解说牌正是通过媒介加工,结合空间变化和情绪因素,将关联信息系统性地传递给观众,引导观众的意识、行为和思维。然而,并非所有的解说牌都能吸引观众的注意,达到预期的展示教育效果。研究显示,解说牌的知识类型、内容元素、设计排版等直接影响观众对于解说牌信息的接收和反馈[3]。一些博物馆的解说牌堆砌大量文字,忽视挖掘展品内涵,疏于梳理展品信息之间的联系,很少运用视觉科学的研究成果“升华”解说牌的信息表达,限制了博物馆展览的展示效用和教育效果。本文以博物馆解说牌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可视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博物馆解说牌可视化加工的原则和建构流程,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
二、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表达相关概念
(一)信息可视化:信息传播活动的主流输出途径
20世纪40年代,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给出了“信息”的定义——“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4]。之后,“信息”被定义为经过加工后的数据,它蕴含着事物的特征、现象和规律。信息实质上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为符号,二为意义。符号是信息的形式和载体,意义是信息的内涵和精神。在传播活动中,符号和意义合而为一,意义通过符号的形式与对象交流。信息以物理刺激的形式作用于感觉器官,之后这些信息又被传送到大脑,从而产生各种心理活动。
信息的可塑性很强,它可以被加工成多种形式传播,如高度抽象简化的文字加工、自然多变的声音加工、直观具象的视觉加工等。其中,信息可视化(visualization)是对信息的视觉化加工。视觉是所有感知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获得形状、距离、亮度、颜色等丰富的信息。视觉信息处理是人类大脑的核心功能,与其他感知觉相比较,视觉在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中占据统治性地位。美国公共关系学家道格·纽瑟姆(Doug Newsom)认为可视化表达是人类不断挑战交流方式的产物,它主要包括基于信息数据的图表、图解、图形、表格、地图和名单[5]。对信息进行合理的可视化,不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更能具象化揭示信息之间的规律、关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信息可视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地铁站的交通线路图、天气预报的气象图表、公司的财务报表、博物馆的解说牌等都可见信息可视化的应用。
(二)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以科学性为前提的美学表达
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可视化加工有别于以引人注意为目的的平面广告、以数据分析为主旨的科研图表和以信息集成为着眼点的新闻插图。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的表达方式建立在受众需求的基础上,将展览信息的有效传达作为“主业”,对展品所承载的庞大信息群进行搜索、过滤、整理和表达,构建起展览信息体系。其信息的准确、科学、简洁和有效传达是第一要义,其美学表达是第二要义,不仅要引起观众的参观兴趣,更要综合考虑观众需求、信息类型、展览基调等多种因素。
本文所讨论的博物馆解说牌中的信息可视化,是采用图形图像技术方法,将展览中的非结构化文本等抽象数据、信息、知识进行可视化加工,从庞大的信息中整理、抽提有效个元,挖掘个元逻辑关联,以直观、有趣甚至可互动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视觉传达,凸显展览信息的准确性、关联性、简洁性、创新性和直观性,旨在帮助观众目睹、探索并在短时间内理解展览蕴含的海量信息,激发观众的思考。
三、我国博物馆解说牌中信息可视化加工的误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迎来了博物馆建设的新高潮。博物馆展览有明显进步,但总体而言,展览质量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6]。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基于传播学和教育学,集学术文化、思想知识和审美于一体的,面向大众的知识信息和文化艺术的传播媒介。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知识传播和公众教育。与其他行业一样,博物馆也经受着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的冲击。如何将藏品信息、科学知识以富有逻辑性、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方式传递给观众,使观众从中得到态度与经验、知识与信息、情感和价值上的收获,并引发思考,这是博物馆展览策划者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目前,博物馆解决上述问题的常见方法是将展览信息进行梳理、归类、组合和可视化加工,架起观众与藏品对话的桥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内博物馆解说牌开始有意识地减少文字描述,增加图表展示,但仍存在以下误区。
(一)可视化信息个元选取求泛而不求精
玛塔·洛伦索(Marta Lourenço)等学者于2014年提出了藏品坐标系理论[7],该理论以展品为对象,建立“个性特征”“共性特征”“共时观”和“历时观”的坐标系,分解剖析博物馆展品的信息个元。依照该理论,博物馆的每件展品均承载着多维信息。例如,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国立自然历史与科学博物馆(Universidade de Lisboa,Museu Nacional de História Natural e Ciência)收藏的一件铜制圆等高仪,可以从数学、物理学、材料学、测量仪器学、历史学、社会学、档案学的角度,剖解出二十余条展品信息[8]。如果用作新闻素材,该铜制圆等高仪的信息图应凸显其丰富性、全面性。因为新闻读者有充分的时间阅读信息图,并有兴趣理解完整的信息体系,拓宽思路。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提取则截然不同,观众在解说牌前停留的时间十分有限。设计者应综合考虑展览主题、展品特性、观众兴趣点等因素,抽样提取信息个元,以吸引观众关注,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易于理解且有意义的信息。目前,国内一些博物馆注意到了展品信息的多元性,却忽略了信息选取的基本原则,在对解说牌可视化加工的过程中泛化设计元素、罗列展品信息,不仅降低了解说牌的可读性,加重观众参观的疲劳感,更间接造成了展览的同质化现象。
(二)忽略可视化加工技术与加工对象的相互匹配
格式塔原理(Gestalt)探讨了视知觉的特点:在有限的视觉范围内,人眼能接受的碎片化的视觉信息单位有限。如果视域内包含了过多碎片信息,眼睛和大脑就会把这些信息简化、拼凑,使之成为易于理解记忆的整体;如果碎片信息无法通过此种方式“还原”,大脑中的视觉信息将呈现无序或者混乱的状态,被大脑储存在“易于遗忘”的区域[9]。除此之外,由于大脑对于色彩、亮度、形状等的认知易产生错觉,导致观察者对信息产生误解。为使观众获取准确信息,博物馆解说牌的设计应遵从人类大脑视觉认知的规律。一些博物馆的解说牌设计忽视了这些规律,例如有的解说牌采用气泡图标识数据信息的大小值。然而,人类的视觉对于实际面积大小的认知并不敏感,如果用气泡图中泡泡的面积比较来代替数值比较,会使观众对信息的理解产生偏差。又如有的解说牌在使用颜色上杂乱无章,忽视色彩对视觉认知的影响,使展览中的有用信息由于加工失误而变成无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
(三)缺乏对展览信息的逐级解码
约翰·桑切克(John Sancek)在《教育心理学》一书中探讨了人类复杂的认知过程。他通过研究证实,将教学内容通过知识点关系和等级结构进行解析,并绘制成图,有助于受教育者理解并记忆知识[10]。毫无疑问,对博物馆解说牌中信息个元的联系和层级结构进行可视化加工,更能凸显展品的重要信息,展览的逻辑脉络更清晰,信息之间的连接路径更清楚。对展览信息的逐级解码是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加工的两个步骤。一方面,设计者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展品服务于展览主题,每一个独立展品都应在展览整体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另一方面,设计者还应注意到展览展示的脉络和走向。展览中各节点的展品信息是具有层级次序和优先级的。一些博物馆解说牌设计为了可视化而可视化,虽用图示表述展品的基本信息,但没有深入思考各展品信息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导致解说牌内容割裂;还有一些博物馆解说牌的可视化加工忽视了信息呈现的次序,将一些观众并未理解和接受的概念突兀地展示在解说牌中,导致展览逻辑结构混乱;另有一些解说牌照搬深奥的学术论文,把本应“解码”的信息铸成“密码”,使展览晦涩难懂。
(四)博物馆解说牌的互动性和参与感不强
提升博物馆展览的参与性、提高展览与观众的互动性是现代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方向。研究者斯蒂芬·比特伍德(Stephen Bitgood)表示,人们在参观前和参观中都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人们在参观过程中觉得展览的内容质量较高,他们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11]。但是,牢牢抓住观众参观博物馆的注意力并非易事。1916年,本杰明·伊夫斯·吉尔曼(Benjamin Ives Gilman)提出了“博物馆疲劳”(museum fatigue)的概念。提升展览的参与感是缓解观众“博物馆疲劳”的重要方式之一。苏格兰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动物展区的一个交互解说牌就给出了成功的示范[12]。该展区大型动物骨架前的电子解说牌清晰列出了多种动物的重量数据及其比例关系。当观众站在解说牌前的“脚印”上,解说牌上的电子指示灯会直观显示观众的体重与哪种动物类似。这种交互信息图(装置)以变化的信息解决博物馆对动态信息展示的需求,同时也给观众带来参与感和体验感。然而在我国博物馆中,类似的互动可视化解说牌设计尚不完善,未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近年来,信息可视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博物馆解说牌设计,但在设计和使用上还存在种种误区,主要原因可归结为:第一,信息可视化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属于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其话语体系和概念受复杂的应用领域影响,而显得相对混乱、缺乏规范;第二,虽然博物馆领域的信息可视化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跟不上发展节奏,学界的相关探讨不够深入和全面,行业通用标准尚未建立;第三,不少设计者不具备信息可视化、图形图像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背景,对解说牌的可视化加工还处于摸索阶段,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较为欠缺;第四,受传统观念的限制,不少设计者将解说牌的设计思维局限于解说牌本身,未将解说牌的设计与展览主题、观众需求、教育活动、科研成果结合起来,造成解说牌设计策划相对孤立的局面。
四、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可视化表达:原则与建构
(一)可视化加工:从信息到智慧
信息可视化发展迅猛主要受两个因素驱使。一是大数据时代信息爆炸,信息接收者需要专业人士通过专业手段对信息进行多次“编码”,完成“信息—知识—智慧”的升华,从而帮助信息接受者从纷杂繁复的信息中提取可用的信息。信息爆炸使人们感受到已知信息与应知信息之间的巨大缺口,易产生信息焦虑。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梳理、分类、重组和加工,过滤无用信息,建构可视化信息体系,成为大数据时代最为现实的公众心理需求,它将缓解信息风暴给人们带来的信息焦虑。二是人类的视知觉工作机制影响大脑的理解和认知。人类对外部信息的感知中80%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大脑一半以上的组织结构都与视觉信息的加工处理有关。人类视觉中枢具有层次结构,呈阶梯级。低级视觉中枢向高级视觉中枢提供信息,高级中枢也向低级中枢发出反馈信息[13],从而决定低级中枢的“注意力”和“焦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曾比较单纯的文本文件和以视觉语言为主的文件对受众的说服效果,发现67%的受众认为包含视觉语言的文本更有说服力[14]。罗伯特·E.斯莱文(Robert E.Slavin)指出,信息可视化揭示了信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多元信息相互关联的知识网络,降低了学习者的认识负荷,促进新旧知识的关联与整合,变机械学习为有意义学习,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15]。教育是当今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信息可视化表达的有效运用将大大提高博物馆的教育成效。
美国国家阐释协会(Na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 Association)将“阐释”定义为“一种既能激发观众兴趣又能解释资源意义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过程”[16]。就博物馆解说牌的设计而言,其阐释过程就是根据展览的传播目的,对展览(品)的学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将其转化为大众传播文化产品,旨在与观众进行观点和思想、知识和信息、感觉和价值的沟通,满足观众的欣赏和求知需求。这是一个将学术信息通俗化、知识问题趣味化的过程。
与文字等传统表达方式相比,博物馆解说牌的可视化设计有诸多优点。首先,用图示表达信息,在受众脑中建立起形象,区别于语言文字的告知过程,它显示与展品有关的多元信息内容,有助于表达展览信息的完整性。其次,经过可视化处理的博物馆解说牌,不仅是对可见或可读信息的简单呈现,还包含建立信息之间联系的过程。合适的信息可视化表达可传达藏品信息之间的关系、藏品与藏品的关系,从而达到扩展藏品信息背景、支撑学科内容交叉融合、梳理展览或展品信息逻辑关系的效果。信息图表设计中的设计元素也可以通过分类、对比、联系等方式凸显藏品的特性、层级等。
(二)解说牌信息可视化类型
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依据加工内容和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统计信息图、示意信息图、地图信息图、逻辑结构信息、历法信息图和交互信息图(装置)。
统计信息图主要用于科学的数据统计,以统计图的方式呈现数据,因此数据显示是统计图表的显著特征。根据数据显示方式的不同,统计图通常又可以分为表格类、坐标类、条块类、圆形图、图示类等。在许多博物馆都可以见到基于统计信息图设计的解说牌。例如,英国斯旺西水岸国家博物馆(Swansea National Waterfront Museum)在描述该市工业发展历史与全球经济关系时,就大量使用了这类统计信息图作为解说牌的表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馆解说牌中使用统计信息图必须全方位考虑受众的认知水平、数据的图像化程度、解说牌信息容量。这主要是由于统计信息图包含图标、图例等细节元素,观众需要长时间驻足阅读,方能掌握其具体信息。因此,从观众的认知水平、人流缓冲等角度考虑,统计信息图对博物馆解说牌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示意信息图是以图画语言和象征符号为基本特征的图表表示方法,以抽象图形或具象事物示意某个原理、事件、关系的图表。示意图表又可细分为概念图表、流程图表或系统图表。解说牌对展品的构造、用途、空间位置以及其他相关的科学知识进行可视化信息加工。通过突出展品的某一种或几种特征,与同类对象进行对比,“放大”展品所“携带”的信息。例如,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鳄鱼骨架展区,其解说牌按比例设计了不同生物学种属的鳄鱼体型对比、鳄鱼与人类身高的对比,并设计背景网格(每一格代表1米),给观众以准确的数据信息。背景网格的设置在此处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类大脑虽不善于计算面积,却特别善于计算一维事物,例如长度或高度。如果没有背景网格线,观众则无法获知这类信息的准确比例。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此类解说牌很科学地遵从了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结论,在许多示意信息图中都注意图例颜色、比例等方面的统一性,并简化藏品信息,加入网格等参考坐标系,对展品进行科学、简洁、醒目的可视化加工。
地图信息图是用图示描述地域性信息的图表。地图主要分为通用地图和专用地图。地图模式应是博物馆解说牌中最常见的模式,一般用于传递与展品有关的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信息。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人文展区用不同的色块在世界地图上标注不同大洲,将带有民族文化传统的照片附在地图的相应位置,增加了展品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逻辑结构示意图是展示逻辑结构的图表形式,常采用简化的图标、结合其他图形侧重展示逻辑关系、结构等。例如,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采用布里斯托恐龙家族树图,用简化的线条勾勒不同生物学种属的恐龙,通过线条连接,展示各种属恐龙的亲缘关系。由于形状、重量等因素不是馆方重点输出的信息,因此,图标简化了这些信息。这也是信息可视化表达的一个特点,即侧重表达重要信息的科学性,而对次要信息进行“过滤”处理,简化甚至丢弃无用信息。
历法信息图是依据时间顺序,把一方面或多方面的事件串联起来,形成时间上相对完整的记录体系,再运用图文的形式呈现给用户;时间轴可以运用于不同领域,最大的作用就是以时间为坐标把展示信息系统化、完整化、精确化。历法信息图理顺整件事情的脉络,用逻辑的架构来理清已知、推理未知。时间信息呈现的方式既有单向的、线性的关系,也有非线性的关系。线性的关系是指在一个时间维度内,事情的发展是单向的、一直往前的、不可逆转的。例如英国布里斯托社区博物馆(M Shed)的解说牌用时间轴串联了布里斯托的移民历史和地理迁移区域。简单的一幅图勾勒出布里斯托居民的来源和去向的脉络,表达简洁明了,也容易引起观众共鸣。非线性关系的历法信息图则适于串联不同空间的信息。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以时间作为联系,讲述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交流故事,揭示多元文化交融共生所创造人类文明,形成跨越式的碰撞与讨论。
交互信息图是近年来在博物馆解说牌中较为流行的一类信息图。一方面,动态的信息需要动态的展示;另一方面,观众也迫切需要与博物馆展示的互动来获得代入感和体验感。
(三)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加工的基本原则
从前文论述可知,视觉系统只是脑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大脑对视觉信息的处理过程中也掺杂其他工作,因此,我们最终形成的视觉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情绪状态、经验偏好、关注目标等。例如,人们注视并关注某一事物,往往会对周边景物视而不见;人们看见自己熟悉的形象,也会轻易将其从复杂背景中识别出来。事实上人类眼球的构造包含了相当于镜头、感光芯片和图形处理器的数码相机功能,而大脑则对这些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编码、解析、分类、整合、变换乃至赋予意义。
基于这些理论和研究成果,可视化加工类型应视加工内容和受众特点而定,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美学表达为途径,以信息传达为目的,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在设计视野上追求跨学科融合。
总结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加工的原则,即“简单”“相似”“连续”“一致”“关系”。可视化加工的“简单”原则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从展示内容上理解,信息个元应呈现为简化、有序的图形,如基本几何形状,因为人类大脑对于简单事物的理解和记忆较为擅长。二是解说牌画面应简洁明了。解说牌的构图上应减少背景干扰,突出主题。“相似”原则要求设计者在抽象信息形象时,以多数人认可的约定俗成的形象为模板进行加工。“连续”原则指对解说牌进行可视化加工时,应注意同一主题展示区域的内容、设计风格的连续性,让观众明白展示信息的群落属性。“一致”原则指完整展示区域的解说牌要保持设计思路的一致性。如果在同一展区,设计思路的突然跳跃会破坏观众观展思维的形成,影响信息表达效果。“关系”原则指解说牌的设计应遵守基本的大众认知规律,在表达展览信息的层级关系、平行关系、从属关系等时,应考虑观众的观展习惯,控制合理的逻辑关系拓展,并强调信息指向性。
(四)可视化博物馆解说牌建构与加工
信息可视化表达的目标为简洁、准确、美观。要实现目标,设计者需要理解并掌握大量相关信息,搭建信息框架,然后进行一系列加工。博物馆解说牌信息可视化的设计流程主要如下。
首先是信息采集。信息采集指信息中的功能要素及相关数据的采集,它包含理解和提取两个步骤,是极为重要的信息积累工作。它需要超越单纯的时间和空间,对展品进行多维思考和处理,获取丰富可用的展览信息。
其次是信息架构。信息架构工作基于信息采集和信息分析工作。设计者需要从海量信息中提取与展览主题密切相关的元素,并搭建信息框架。这一过程使信息与数据实现高效性的整合,也基本明确展览的思路、脉络和风格。在这一过程中应重点思考如何满足公众理解信息的需求。比如针对儿童的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构建信息逻辑时就不应采用成人理解信息的模式;对于不同学习风格类型的群体,也要区分视觉型、听觉/言语型,还是动觉/触觉型来加以区别[17]。
再次是视觉转化。该环节通过符号编码的方式将抽象的信息转化为可以读取的视觉化语言符号。视觉转化不仅需要依靠灵感支配创意,更是具有逻辑性的创意过程。因此,在实现数据信息采集和信息架构的基础上,需要对信息内容进行视觉转化,方便观众了解庞杂的、多维的数据信息,以及数据信息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18]。
最后是符号传达。符号传达是对视觉转化成果的修改。它基于对符号理解、认知和掌控,涉及对于复杂且具有变量性的信息,设计者如何编码和公众如何解码的问题。完成符号传达的关键是建立以符号为元素的传递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共识性的意义空间。
与其他领域的信息可视化表达不同,博物馆的参观环境、人流缓冲、参观动线等都为信息可视化的自由度设限。博物馆解说牌对于信息可视化的运用应遵从相应的原则,从而保证解说牌版面的简洁性、信息主次分明等。
五、展望
美国博物馆与网络协会(Museum and the Web)在探讨博物馆发展趋势时,提到未来的博物馆将更具有可及性,更注重观众体验,更多策划讲故事的展览[19]。显而易见,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可视化将在提升观众体验和助力阐释性展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博物馆未来的可及性贡献力量。
当前,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的场所,展览不同于以往的“展什么”,而开始重视“怎么展”,展示叙事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展示过程首先是有叙事性的。无独有偶,信息可视化的发展趋势也在向“叙事式”方向发展。故事叙述转换到可视领域,可直观展示大量信息,更容易被观众吸收[20]。计算机技术提供的新媒体和模式使得信息传递也可以采用类似故事的风格[21]。
与此同时,叙事表达往往隐含故事情节的动态发展线,因此,它还会为博物馆的展览带来一项“副产品”,即提升观众参观展览体验,解决观众与解说牌(装置)互动性不强的问题。众多可视化领域的专家已经针对交互故事可视化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迈克尔·沃尔法特(Michael Wohlfart)提出交互式的可视化方法,在故事叙述中将一部分故事通过交互让观众控制,剩余部分从预先设置的故事脚本执行,并提出了基于故事节点的故事录制方法[22];爱德华·塞格尔(Edward Segel)等整理了叙事式可视化在新闻叙事、教育媒体等领域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叙事式可视化的设计策略[23]。可视化在叙事场合的应用极具感染力,使观众更能沉浸于可视化故事中,有效地提升观众对于数据信息的理解性和记忆性[24]。
本文讨论了信息可视化在博物馆解说牌设计领域的应用。对博物馆解说牌的内容进行可视化加工将使专业知识或复杂的信息更容易被认知,更具故事性、美观性、实用性。未来,随着博物馆展览向叙事化风格发展,叙事式可视化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也将会应用于博物馆解说牌的设计中。因此,提升博物馆解说牌的信息可视化加工质量和水平,增强展览对观众的吸引力和持续作用力迫在眉睫。随着可视化解说牌在博物馆的运用,对其概念、特征、建构流程进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1]刘玉珠:《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开幕 博物馆进入最好发展时期》,搜狐网,[EB/OL][2019-01-09][2019-10-20]https:// www.sohu.com/a/396015810_114731?_f=index_pagerecom_17&spm=smpc.content.fd-d.17.1589800475861Ya-CyKsA.
[2]F.Tilden,R.B.Craig.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
[3]吕玥仙:《基于眼动分析的环境解说展示效用评价研究——以黄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4]转引自李帮义、王玉燕:《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5]Jacques Bertin.Semiology of graphics:diagrams,networks,maps.Redland ESRI PRESS,2010.
[6]严建强、许捷:《博物馆展览传播质量观察维度的思考》,《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7]Marta C.Lourenço,Samuel Gessner.Documenting collec-tions:cornerstones for core history of science in museums.Science and Education,2014,23(4):727-745.
[8]Marta C.Lourenço.Royal cabinets of physics in Portugal and Brazil:An exploratory study.Opuscula Musealia,2012,19:71-88.
[9]阎安:《报纸版面的视觉优化》,《当代传播》2003年第1期。
[10]〔美〕约翰·桑切克著,周冠英、王学成译:《教育心理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11]Stephen Bitgood.An Analysis of Visitor Circulation:Movement Patterns and the General Value Principle.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2010,49(4):463-475.
[12]范陆薇:《“超级链接”——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多元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协会《艺术专业管理人才国际交流项目成果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
[13]Kaiming He,Xiangyu Zhang&Shaoqing Ren.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CVPR),2016.
[14]〔美〕保罗·M.莱斯特著,霍文利、史雪云、王海茹译:《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15]〔美〕罗伯特·斯莱文著,吕红梅、姚梅林等译:《教育心理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16]Lisa Brochu.Interpretative planning:the 5-M Model for successful planning projects.Singapore:Interpress,2003.
[17]胡小妹:《信息可视化设计与公共行为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8]同[17]。
[19]《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搜狐网,[EB/OL][2018-01-21][2019-10-20]https:// www.sohu.com/a/218029214_488371.
[20]N.Gershon ,W.Page.What storytelling can do for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01,44(8):31-37.
[21]W.Wojtkowski,W.G.Wojtkowski.Storytelling:its role i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DB/OL][2019-07-14]https:// wenku.baidu.com/view/c4041e1da76e58fafab003fa.html.
[22]Michael Wohlfart.Story telling aspects in medical applications.[DB/OL][2019-07-14]http:// pdfs.semanticscholar.org/b5d0/bef946ef184800a8bd6eb62ed3565a523a50.pdf.
[23]Edward Segel,Jeffrey Heer.Narrative visualization:telling stories with data.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2010,16(6):1139-1148.
[24]E.M.Kadembo.Anchored in the story:the core of human understanding,branding,education,socialization and the shaping of values.The Marketing Review,2012,12(3):2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