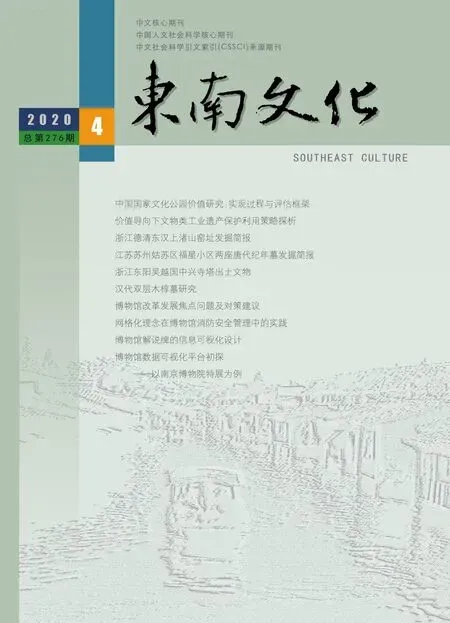新技术影像与博物馆集体记忆的多重建构
2020-12-01于莉莉
于莉莉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互动影像、全息投影、AR影像、VR影像等新技术影像成为博物馆中集体记忆新的内容载体和传播媒介。新技术影像以其交互、增强、沉浸的视觉特征,对集体记忆表现出的历史时空以及集体记忆的传播方式带来了诸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记忆的客体通过多维的视觉重构与原真性再现被进一步“活化”,记忆的主体由对物的记忆转变为对生活方式的记忆。博物馆的新技术实践使集体记忆在“延续”的表象之下也有着隐蔽的“断裂”,并且还存在被逐步异化的危机。集体记忆变得复杂而多元,为多重建构提供诸多可能。
集体记忆是集体经验在时间长河冲刷下的留存与积淀,它承载着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们的情感,对于国家或地方文化的延续和身份认同的生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25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他将记忆视作一种社会行为,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哈布瓦赫在探讨“建构集体记忆”的同时,也指出记忆往往需要与某个场所建立联系,强调记忆场所化的重要性[2]。在哈布瓦赫之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记忆的场所”进行系统性研究。诺拉认为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档案、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纪念仪式、节日等都是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是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诺拉将“记忆之场”划分为物质性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在他的这种研究框架中,博物馆是一种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性记忆之场[3]。
博物馆作为集体记忆的场所,一方面表现在其文物藏品和景观建筑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是承载集体记忆的典型物质现实,是记忆的载体,为书写集体记忆提供了大量的记忆资源;另一方面,博物馆对文物与建筑的说明、阐释和展陈布置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既是对历史的再现也是对意义的重新建构。因此,博物馆被当作话语建构争夺的空间,通过对零散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和系统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依照特定逻辑进行叙事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和“再现”的是博物馆设计者和管理者力图构建的一套价值论述[4]。在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其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与功能已从以审美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形塑国家或地方的文化认同为主。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博物馆中进行参观和鉴赏,这种文化实践活动使其参与国家或地方集体记忆的共享、交流与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不断得到强化,进而使国家或地方的文化认同得以生成。
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和机制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变革,利用新的摄影技术、图形处理技术和投射显示技术等制作的影像,成为博物馆中记忆载体的新样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对集体记忆的保存、呈现与传播,由传统的实物、文字、图片、二维影像等形式向动态、多维、立体的多媒体形式发展,互动影像、全息投影、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影像、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影像等新技术影像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工具。新技术影像由于其交互、增强、沉浸的视觉特征,对集体记忆表现出的历史时空以及集体记忆的传播方式带来了诸多改变。本文选取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故宫”)、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江苏苏州博物馆(以下简称“苏博”)等作为典型个案,力图通过对新技术影像视觉特征的考察,阐述集体记忆的活化过程,并揭示其中集体记忆延续、断裂和异化的问题。
一、跨越时空:作为记忆载体的新技术影像
数字技术的介入使新技术影像成为博物馆新的记忆载体。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建构力量,新技术影像深入文物、建筑的实物内部,寻找更多尘封其中的记忆内容,打开更广阔的记忆时空;并且,在以信息传播为导向的展示方式中,厘清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叙事线索,呈现出更具关联性的记忆时间。参观者在新技术影像创造的具有交互性、增强性、沉浸性的实践体验中,记忆的空间范围被极大拓展,记忆的时间期限被无限拉长,集体记忆的时空屏障被突破,时空观得以重构。
新技术影像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交互性。首先,它被应用于博物馆中时,最直观的表现是其各种交互界面使参观者可以自主控制观看的方式。新数字建模技术通过对展品进行360°全方位激光扫描和多图像摄影,可生成高精度的三维模型,使以前较难看到的文物珍品或诸如榫卯等只能远观的建筑构件等,都能在交互界面中清晰呈现。参观者在交互屏幕上控制、改变观看的角度和距离,就可轻松获得多种观视体验,从过去的“观看文物”转变为“把玩文物”。
其次,参观者可以在交互式导览中自主选择想要观看的内容。交互式导览中的数字化文物影像往往呈现结构化,包含很多局部信息点,参观者可以获取制作工艺、纹饰特点、使用方式、背景信息等诸多方面的介绍。故宫、南博等推出了平板电脑导览设备,通过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服务)技术还会根据参观者的移动路径自动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展品信息。
最后,博物馆的新技术影像往往被嵌入微信小程序、应用程序(App)等具有社交功能的数字交互平台中。由于网络技术的加入,线上线下被联通起来,展品被放置在一个多元交织的、流动的展览环境中,其承载的相关城市记忆也从原有静止的、有限的状态变为不停生长、不断丰富的状态。目前,不少博物馆的数字平台支持对展品进行点赞、分享、评论甚至打赏。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模式中既有参观者观点的表达、相关意见的交流,也有个人对藏品相关信息的细致补充。这些个性化内容能够将记忆信息发散开来,有效勾连起更为丰富宏大的记忆内容。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在历史记忆里,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别人讲述,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5]。数字化平台正是这样一个供群体聚集并进行共同回忆的网络公共空间,人们在其中进行的数字化交往能强化自身记忆。博物馆通过“物”来记录、保存和展示地方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展陈布置通常表现为一种单向的、线性的“凝视—接受”型传播模式。这种记忆的唤起方式是被动的,作为记忆主体的参观者所获取的记忆内容比较有限且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新技术的介入使博物馆对集体记忆的书写与塑造表现出非线性的特点,其交互的特性将历史信息与参观者的现实行动联系在一起,激发了记忆主体主动探索与分享的热情,增强了其能动性,对主体记忆的唤起形成了新的“参与—实践”模式。
心理学研究中,记忆被唤起的过程常常需要寻找特定的线索。线索是记忆主体回忆的支点,通过线索达到对过去的人、物、事件的再认识。博物馆的文物和建筑为参观者提供了可作为线索的丰富的记忆资源,但这些留存下来的记忆资源往往是残缺、孤立和零散的。很多情况下,参观者在头脑中无法从有限的线索中再现出具体的记忆空间,从而也难以获得一段相对完整的城市记忆。模糊不清的回忆与生动真切的历史情境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记忆鸿沟。新技术增强性的视觉特征在各个记忆线索之间能够起到连接和填补的作用,更加有效地将记忆资源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勾画出更为宽阔的记忆场景。南博数字馆的“热血青年”主题主要讲述了西汉时期刘非协助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历史故事。旌旗装饰、模型陈列、集合分列式多屏幕、裸眼3D屏幕、透明LED液晶屏幕共同营造了一个立体、丰富的展示场景。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铜虎、错金银铜俳优俑、错金银铜嵌宝石鸟柄汲酒器等文物是这一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记忆线索。动画影像发挥填充作用,通过描绘具体情节进一步扩展这些记忆线索。尤其是关于弩机的陈列,弩机模型被放置在“冰屏”(透明LED液晶屏)展柜中,透明显示屏上弩机的活动影像与屏幕后静态实物相呼应,通过虚实叠加共同解释说明古代弩机的机械结构和工作原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具有联合模式,“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6]。在这一段历史记忆的呈现中,各种文物是记忆的线索,新技术影像利用自身增强性的特征补充了这些线索背后难以留存、几近消逝的记忆内容,从而使塑造出的记忆空间扩展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场景。
记忆是过去到现在不断积淀的结果,具有历时性的特征。博物馆对集体记忆的呈现是将纵向的历史时间轴线进行切割,使其成为一个个瞬时的横剖面,每一个横剖面都是对特定历史空间的描绘。由于时间单向性的限制,参观者对每个横剖面呈现的历史空间只能旁观却无法进入,但沉浸式的新技术影像却能够将参观者带入历史中。上博在2018年推出了“乐游陶瓷国”VR体验,通过使用头戴式显示设备和六自由度模拟器座舱,参观者可以从博物馆展厅“穿越”到古代制瓷窑址的场景中去,完成“瓷土开采”“水碓粉碎”“瓷泥陈腐”“拉胚画彩”“采集松木”“烧制瓷器”等一系列陶瓷制作流程。参观者在进行VR体验时视线范围被影像完整覆盖,可获得深度的视觉感知。同时,模拟器座舱又为参观者增加了听觉感知和运动感知,形成4D的模拟环境。参观主体沉浸在模拟环境中而产生的脱离现实时空的知觉感受,可以视为一种“阈限体验”。“阈限”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转折时刻或空间维度上的边界地带,具有“之间”和不确定或流动的特征。经由阈限,人们获取共融的体验,是一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7]。由VR影像创造出的模拟环境是一种在微观层面上的情境性的“阈限空间”,人们在这一空间中的实践活动能够使其自身暂时从现实的结构性角色中脱离出来,也即从参观者的角色临时转换为模拟环境中的人物角色,获取与历史情景共融的体验。虽然这种阈限体验是临时的、转瞬即逝的,但现实与过去的时间区隔因此被打破,作为记忆主体的参观者走进历史似乎变成了可能。
二、记忆的活化与转型:从“物质性”到“生活方式”
集体记忆的客体也就是记忆的对象,既包括历史中的物质现实,也包括在过去生活的人与发生的事。新技术影像以其交互、增强、沉浸的视觉特性,改变了博物馆中集体记忆的表现时空和传播方式,从而记忆的客体在文物、建筑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更多人物、事件、风俗文化等元素,并且突破了传统的静止状态被进一步“活化”。
一方面,记忆客体的“活化”表现在新技术影像将记忆客体中固定不动的物质现实进行多维的视觉重构,赋予其一定的“活动性”。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就展出3D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通过三维可视化技术和12台电影级投影仪的共同作用,原画卷中的人、车、船、河等各种元素都动起来,展现出北宋东京汴梁漕运繁忙、街市喧哗的都市场景。与此类似,南博数字馆的墙壁上投射有动态版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南都繁会图》影像,画作比例的放大、亮度的提升以及观看距离的拉近,都使参观者能够更为细致地了解、感受五代南唐时期贵族的生活和明代晚期南京的市井风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媒体形式应用于历史物品的活化,例如苏博利用AR技术为展品“白玉镂雕山水人物香薰”添加烟雾缠绕的效果,通过实物与AR影像的叠加,共同还原西汉时期香薰在祭祀等活动中的使用场景。由于新技术影像的活化,记忆客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本体所代表的绘画、雕刻、纺织、机械等传统的制作工艺,更在于它体现了物品在使用状态中蕴含的独特生活方式。当记忆的客体把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特征传递给当代时,这个地方的文化面貌便清晰起来,使人如临历史之境。
另一方面,新技术影像对记忆客体中难以保存的人、事、风俗文化进行原真性的视觉再现,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活态性”。2017年故宫推出了“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参观者能够近距离地体验、探索养心殿:在数字馆的“召见大臣”项目中,参观者可以通过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术与文武大臣、宗亲王公自由对话,了解清代皇帝与臣子之间的问话内容和语言风格;在“亲制御膳”项目中,参观者可以学习素馅饺子、六宝豆腐等多道宫廷御膳的制作方法和盛放摆盘方式,并能够将生成的菜谱带回家亲自实践;在“穿搭服饰”项目中,参观者可以通过搭配衣服、饰品来体会清代宫廷繁复、严格的冠服制度,还能够利用Kinect体感技术进行试穿。动态的人物形象复原、直观细致的情境再现使记忆客体在当下的环境中有了延续性,养心殿不再是一座静止的古代建筑,而变成一种呈现清代宫廷日常工作、起居的舞台和背景,纯粹的物理空间转变成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文化、生活场所。
记忆客体在“活化”过程中还原了缺席的人和故事,重塑了消失的他者和历史,唤醒了参观者对过去生活的理解,进而传递出更多的地方文化内涵与场所精神,促使记忆主体从对物的记忆转变为对人与事件相关的生活方式的记忆。集体记忆以场景化的形式出现,使记忆主体形成对地方的综合感知和体验,记忆与个体的身份归属产生关联,从而建立起特定的“家园感”和“地方感”。记忆主体通过博物馆中的物质性客体认识国家或地方的历史、环境等固有特性,同时又通过新技术影像表现出的非物质性客体生成对国家或地方文化的情感,最终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与国家或地方之间的深切连结。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这种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被称为“恋地情结”或“地方之爱”(Topophilia),是探讨特征性场所中“依附”和“归属”问题时的核心概念[8]。博物馆中生成的这种恋地情结是参观者与国家或地方深度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经由这种感知和经验,记忆主体在社会层面将自我认同和国家或地方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具身体验:记忆的延续、断裂与异化
对集体记忆而言,其形成与演化的过程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记忆主体能动性、认知差异等一些内部因素的影响。从记忆建构的内部因素来看,博物馆新技术影像的加入使作为参观者的记忆主体在交互、增强、沉浸的视觉刺激下产生一种“记忆快感”,这种快感体验激发了内部作用力的活跃性和创造性。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研究社会记忆的产生与传递时,提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忆实践——刻写实践(inscribing practices)和体化实践(incorporating practices)。刻写实践通过各种符号系统的记录和保存来传递信息,可以独立于人的身体来完成;而体化实践则通过亲身在场参与活动来传递信息,完全依赖于人的身体,例如各种仪式活动[9]。一般来讲,博物馆对集体记忆的保存、呈现与传播方式属于一种刻写实践,记忆的内容被特殊的符号系统固定下来,具有独立性。但新技术影像的加入使记忆的传递过程增添了体化实践中“身体在场”的部分,形成一种包含多种身体经验的新型刻写实践。作为记忆载体的直接使用者,记忆主体与记忆载体之间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记忆主体在参观过程中通过身体直接的、即时的操演生成自己的集体记忆,使集体记忆在个体的再生产中获得新生命力。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群体的回忆往往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实现。群体塑造出的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简单相加的产物,而是属于群体成员每个人的,存在个体化和具体化的方面。由于个体在公共认知层面的区别,即使涉及同一记忆对象,每个记忆主体的描述和体验都不尽相同,都会生成自己的集体记忆。这个记忆在保持相对稳定基本特征的同时,也蕴含着记忆主体个人丰富的思维细节。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博物馆中刻写实践发挥铺垫作用,记忆主体的体化实践起到助记的作用,主体切身的记忆和体悟得到深化,从而获得为个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博物馆中集体记忆的唤起一次次地被个体再生产,获取记忆不是终点,记忆的建构成为一个正在进行、不断延续的过程。
从记忆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记忆实践中的快感体验为各种外部作用力提供了新的庇护所,在某种程度上又遮蔽了城市记忆中的断裂与丧失。集体记忆建构的外部作用力主要来自政治权力者、专业工作者以及社会精英等。保罗·康纳顿在分析权力在社会记忆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时,谈到“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10]。也就是说,控制记忆的权力等级越高,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力就越大。法国学者刘易斯·科瑟(Lewis Coser)也在《论集体记忆》的序言中说道,“我们对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11]。外部作用力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是以现在为中心的,它把当下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发展作为所依据的立场,力图确立一种范式秩序,以此来统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外部作用力充当着集体记忆“把关人”的角色,对集体记忆的内容进行过滤,对过去的再现总是在强调某部分的同时弱化其他部分。博物馆既见证了地方的历史,也体现着一个地方的未来发展,它们筛选记忆的基本机制是突显地方特色、彰显地方实力、创造地方认同,其他关于现存的困境、矛盾、冲突等记忆往往在这种叙事模式中被舍弃和遗忘。在如今的数字时代,外部作用力对记忆载体的技术性因素进行逐步渗透,使技术成为其施行的工具,通过对技术的支配和利用,引导个体展开回忆。作为记忆载体的设计者、呈现者,外部作用力在新技术影像中绕开了人的理性意识,利用参观者的快感体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变得更具感性和弥散性,虽无处不在却又凭借技术将自身更好地隐藏起来。
此外,从记忆建构的路径来看,记忆实践中的快感体验还可能造成集体记忆的异化。以扬·阿斯曼(Jan Assmann)夫妇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曾声称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记忆危机”的来临。当今社会,历史意识的隐退和消费文化的渗透使我们不得不担忧这样一种情况——当参观者利用博物馆的新技术影像建构集体记忆时,很大程度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记忆内容,而是想要寻求一种感官上的满足。首先,作为记忆载体的新技术影像使记忆内容与具体文物逐渐发生分离,弱化了其与现实之间的物质性关联,使其只是成为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虚幻想象。其次,数字化的信息往往过于丰富、详细,超量的记忆内容可能会造成参观者的整体无意识和不自觉的遗忘。最后,当“娱乐”变为博物馆展陈中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时,新技术影像对于记忆主体的吸附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具有现场感的、可观看的视觉空间,而不是内容的记忆场。也就是说,记忆主体不在乎新技术影像的功能性意义,而将它视为一个随时可以进入并有各种新奇景观的体验空间。当记忆内容变成视觉性商品,记忆实践异化为一种视觉消费实践,记忆文化就可能被视觉消费文化替代。
在博物馆中,新技术影像为作为参观者的记忆主体提供了一种快感体验。在这种体验下,集体记忆在建构过程中内部作用力的“写入”与外部作用力的“忘却”并存,集体记忆在“延续”的表象之下也同样发生了“断裂”,并有着被逐步异化的危机。因此,博物馆的新技术实践使集体记忆变得复杂而多元,产生多重建构的诸多可能性。
四、结语
新技术影像以其丰富的视觉特征和交互方式在博物馆展陈中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它既创造了各种奇幻的视觉景观与具身体验,也传递出更为多样的文化内涵与场所精神。无论是博物馆自身的数字化建设,还是地方集体记忆的新型建构,都需要积极有效地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但在复杂的视觉文化时代,如何把控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模式,关注其功能与效用,将其更好地与博物馆的文化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与讨论。
[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2]〔法〕杰罗姆·特鲁克著、曲云英译:《对场所的记忆和记忆的场所: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式社会——民族志学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4期。
[3]〔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
[4]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3期。
[5]同[1],第43页。
[6]同[1],第93页。
[7]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8]〔美〕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35页。
[9]〔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93页。
[10]同[9],第1页。
[11]同[1],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