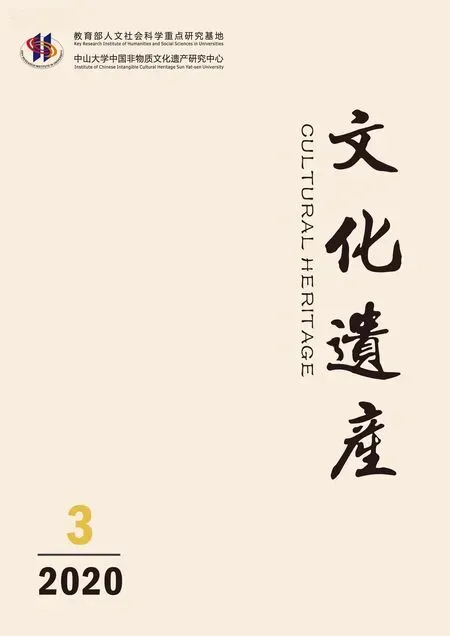湘潭槟榔的传说与际遇*
2020-12-01周大鸣
周大鸣
一、导言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这首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很多人误以为是海南民歌,其实是湖南湘潭人黎锦光创作的民国流行歌曲。黎先生在湖南花鼓戏双川调和湘潭食槟榔习俗的基础上,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采槟榔》,间接反映了食槟榔习俗在湘潭的传播历史与流行程度。
截至2018年,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槟榔”为篇名的研究文章约有2500余篇,其中医学类的文章约2200余篇,人文社科类的文章约300余篇,且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说明学界目前仍集中关注槟榔的医药属性,而关于食槟榔习俗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逻辑仍缺乏关注。
在湘潭的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槟榔商铺、摊点和广告,还有嘴中时时嚼食槟榔的湘潭人。据湘潭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的抽样调查显示,湘潭城区居民的槟榔咀嚼率为58.81%,其中男性咀嚼率为62.45%,女性为54.82%。(1)萧福元等 :《湘潭市城区居民咀嚼槟榔情况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实用预防医学》2010年第10期。可见,湘潭虽不产槟榔,但普遍流行着食槟榔的传统。我从小便养成了食槟榔的习惯,这也促使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槟榔。
二、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食品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烟草、白糖、食盐、辣椒等研究上,如班凯乐(Carol Benedict)通过美洲烟草到中国的传播史与大众消费,透视了全球经济发展史。(2)班凯乐 :《中国烟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季羡林探讨了糖在中国的制作、传播、消费以及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3)季羡林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年。西敏思(Sidney Mintz)以糖为切入点,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4)西敏司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还有关于食盐、辣椒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较常见,如舒瑜通过盐的流动探讨了西南地区不同族群、地方与中央、地方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5)舒瑜 :《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0年。曹雨探讨了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史、文化隐喻和阶级地位变迁。(6)曹雨 :《中国食辣史——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总的来看,学界关于不同种类食品的历史、传播与消费的关注较多。石汉生还曾形象地用“胡、番、海、洋”四字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外来食品的中外交流与互动,如“胡”指从丝绸之路传进的,“番”指宋代开了番司后引进的,“海”指从明清海交之路传入的,“洋”指从清中叶至今传入的。
槟榔与其他食品相比,学界对其关注相对较少。其研究多见于槟榔盛行的岭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如19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在中山大学办《民俗》周刊时就有一个容媛主编的《槟榔专号》。容媛结合地方志、中药典籍等历史资料,分别从槟榔的产地、种类、嚼食缘由、嚼食方法、槟榔礼仪、食品功用等方面,详细叙述了广东等地的槟榔历史。(7)容媛 :《槟榔的历史》,《民俗》1929年第43期。还有陆恒生曾提到“满清时,北京旗人不论穷富,饭后都要啖几颗槟榔。来客多拿它敬客,年节多拿它送礼……常见种类有枣儿槟榔、盐水槟榔、白槟榔和五味槟榔。”(8)陆恒生 :《北京人也啖槟榔》,《东方杂志》1927年第1期。说明在清民时期,槟榔在中国多地已十分盛行。
纵观近年中国的槟榔研究,大致可分四类:一是槟榔习俗研究,如刘莉探讨了海南疍家食槟榔的习俗与族群互动,(9)刘莉 :《海南疍家的陆地印记:从食槟榔习俗谈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吴盛枝比较了中、越两国食槟榔习俗的异同;(10)吴盛枝 :《中越槟榔食俗文化的产生与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二是槟榔历史研究,如郭声波等人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中国槟榔种植格局、习俗文化空间分布、制作与嚼食方法及销售方向、槟榔礼俗衰减等作了探讨;(11)郭声波,刘兴亮 :《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三是槟榔产业研究,如王丹等人对海南省槟榔种植业的发展现状及其主要动力作了分析,(12)王丹等 :《海南省槟榔种植业发展现状及其动力分析》,《广东农业科学》2013年第15期。陈君等人对海南槟榔种植、加工和消费市场概况进行了介绍;(13)陈君等 :《海南槟榔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2期。四是槟榔医药研究,这类研究最多,如对槟榔的中医药属性(14)孙露等 :《中药槟榔及其制剂的安全性系统评价》,《中国中药杂志》2017年第21期。以及与口腔、肠胃等疾病的关系论述等。
综上,湘潭食槟榔的习俗盛行且历史悠久。我也曾对湘潭槟榔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槟榔习俗进行过考察,(15)周大鸣、李静玮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周大鸣、李静玮 :《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但关于湘潭槟榔的来源与流通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本文将作出补充。
三、中国食槟榔的习俗
中国历朝历代对槟榔多有记载,但称呼可能有所差异,如大腹子、马金囊、紫槟榔等。历史上吃槟榔的区域主要有台湾、湖南、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槟榔的发展历史可追溯到汉武帝的扶荔宫中槟榔移植,再到中国民间社会将韩愈奉为槟榔业的始祖。民国时期,容媛编《槟榔专号》时,整个广东还在吃槟榔,但是后来吃槟榔习俗慢慢消失了。因为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将吃槟榔视作陋习而全面禁止,广东、福建受运动影响较大,因此人们便不再吃槟榔。“槟榔”这一词则被另一种食品代替,如潮州那边的槟榔被橄榄代替。
(一)槟榔的简介
槟榔为棕榈科槟榔属常绿乔木,原生于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中,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植物,主要分布在亚洲与美洲的热带地区,主要生产国有印度、泰国、斯里兰卡、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印度槟榔产量占世界一半。中国槟榔主要种植在海南和台湾。亚洲地区咀嚼槟榔是一种传统习俗,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槟榔主要消费地也在亚洲地区,主要进口国有巴基斯坦、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世界槟榔食用消费市场已初具规模,全球约有7亿人消费槟榔,吃槟榔的习俗也逐渐流行到了英国和北美地区。(16)黄慧德 :《2015年槟榔产业发展报告及形势预测》,《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17年第1期。
槟榔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是它是一种成瘾性食品,与烟、酒类似,一旦开始吃就可能上瘾;二是它是较常见的中药,具有健胃、御寒、提神等药理功效,是历代医家治病的药果。槟榔虽然是一味常用中药,但是其大部分原料产品却并非流向药材市场,而是用于简单加工成商品槟榔供咀嚼。正是由于槟榔的医药功能,在中亚、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及周边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南、湖南等省,咀嚼槟榔十分盛行,甚至成为一种传统习俗,印度、台湾是槟榔鲜果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槟榔的习俗。槟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婚姻里象征着多子多福。在台湾,文学作品或采风一类的文章中常见关于槟榔西施的描述。台湾槟榔以前都是鲜制,现在也开始有类似湘潭包装的干制槟榔。台湾槟榔的符号演变早已超越食品本身的功能,如槟榔的象征意义从早期的社会阶层问题演变为族群关系的问题,甚至涉及到政党身份的问题。举例而言,台湾社会最初认为底层阶级才吃槟榔,只有没文化的卡车司机和农民才吃;后来变成台北人经常说自己不吃,都是台南人在吃;然后变成本省人在吃,外省人不吃;现在又变成民进党人在吃,国民党人不吃,形象地反映了台湾槟榔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二)槟榔的历史
历史上关于槟榔的记载很早,因为过去番邦、诸侯常把自己本土稀奇的物品朝贡,槟榔大概也是作为一类稀奇的物品朝贡到朝廷中。一般认为对槟榔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中的“仁频” 便指槟榔,《文选》唐人李善在《仙药录》注引“槟榔,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17)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9页。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远征南越国,四海一统,南国的珍奇植物也移植到了长安的扶荔宫。据《三辅黄图》卷三载,“所得奇草异木……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本。”(18)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8页。
孙吴到西晋时期(公元3世纪中后期前后)对槟榔的文献记载开始增多,如吴时期的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曹魏的李当之《药录》、周成《杂字》、西晋初吴人张勃的《吴录》、西晋时期嵇含的《南方草木状》、郭义恭的《广志》、左思的《吴都赋》等。(19)郭硕 :《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从“异物”到“吴俗”》,《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说明从孙吴到西晋这一个时期,中原政权与南方的联系增加了,因为槟榔是热带植物,只有靠近热带地区才能生长,连广州的槟榔树也不结槟榔,反映当时政权的联系比广州更南。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载,孙吴时期就有派船到台湾的记录,也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在《文选》卷五《吴都赋》的《荆扬已南异物志》中对槟榔树有详细的记载:“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这个描述一定是看过槟榔树的,当时的人已经到了生长槟榔的区域。交趾、日南、九真就是现在越南一带。(20)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第209页。
南朝有刘穆之吃槟榔的故事,如《金楼子》卷九《杂记篇》记载:“刘穆之居京下,家贫,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为妻兄所辱,穆之不以为耻。一日往妻家,食毕,求槟榔。汪氏弟戏之曰‘槟榔本以消食,君常饥,何忽须此物?’后穆之为宋武佐命,及为丹阳尹,乃召妻兄弟,设盛馔,劝酒令醉,言语致饮。座席将毕,令府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曰‘此日以为口实’。客因此而退。”(21)萧绎撰,许逸民校笺 :《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30页。所以槟榔的消食功能其实在南朝就有记载了,刘穆之穷困时便被人取笑吃不饱还消食。湘潭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吃完酒席后吃槟榔来帮助消食。
南朝士人社会嚼食槟榔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屡见六朝史籍记载和诗文之中,如《南史》载任昉之父任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22)李延寿 :《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3页。所谓“常饵”,则似槟榔已是日常生活中常备品。还有《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载其遗嘱,其死后“三日施灵,唯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且“朔望时节,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23)萧子显 :《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17页。豫章王嶷死后的祭祀用品很简单,槟榔却是不可或缺的,可见在王室显贵中食用槟榔之普遍。槟榔成为祭祀的用品,它的功用就不仅是日常食用,还有仪式的神圣功能。
唐代,食槟榔习俗进一步发展。李白、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篇中不乏槟榔的记载,如李白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提到“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提到“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台湾与湘潭民间还将韩愈敬为槟榔业始祖与行业神,始于这一时期韩愈与槟榔的渊源。据传,韩愈贬至潮州期间,有感于粤东地区的山岚瘴气,写下“知汝远来应有意,收好吾骨瘴江边”的诗句,韩愈为驱避瘴气便开始嚼食槟榔,后来官至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等职,食槟榔习惯依旧不改。朝中官员见其嗜好槟榔,纷纷效法,在短期内为嚼食槟榔在长安城乃至北方都市内的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
宋代,食槟榔习俗更为普及。苏轼被贬儋州时,就曾写下《食槟榔》《咏槟榔》《题姜秀朗几间》等多首槟榔诗,在《题姜秀郎几间》一诗中写道“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他的《咏槟榔》全面介绍了槟榔的产地、枝干、花、果实、吃法和功效等。(24)苏轼 :《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8页。苏轼在《食槟榔》曰:“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25)(宋)苏轼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十一,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479页。在这首诗中,苏轼便形象地描述了自身吃槟榔的体会。
有学者还曾做过大致统计,宋代有百余首诗与槟榔有关。嚼食槟榔的习俗迅速传播当在宋代。比如宋代的广州城,“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口敢,夜则置盘旁,觉即嚼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26)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8页。说明那时饭都可以不吃,但是槟榔要吃,已经开始成瘾了。在福建的泉州、广南西路和云南等地,嚼食槟榔的习气也相当兴盛,如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中提到:“闽广人食槟榔,每切作片,蘸蛎灰以蒌叶裹嚼之。”
明代,槟榔习俗从广东逐步向外扩展,东至福建省的泉州府、漳州府,西达广西的桂林府、浔州府(贵港市)、柳州府,甚至是云南元江地区也有槟榔习俗。(27)杨秋 :《东莞槟榔歌的缘起、功能及其民俗意义》,《岭南文史》2003年第2期。如明代雷州人“人事往来以传递槟榔为礼”,(28)阮元 :《广东通志》卷九十三“舆地略十一·风俗二”,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4年,第1802页。明代广西各地民众用槟榔作为宴会的请柬。此外,岭南民众还习惯用槟榔来化解矛盾纠纷,如“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29)屈大均 :《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页。槟榔作为一种商品的流通,与流域也有很大关系,从广州沿着珠江、西江一直上溯至桂林、贵阳、柳州。在明代,贵港也是主要的粮食集散地。当时珠三角开始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主要从广西输入,从贵港溯江而下就到了珠三角。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里有关于槟榔的记载:“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 如果仅仅从文字去读,而不是去看槟榔的内涵,就看不懂这一段话真正的意思。这其实是一种性隐喻,因为槟榔与婚姻是联系在一起的。再比如,第八十二回,宝玉上学后袭人得闲,“倒可做些活计,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荷包儿”,说明那时贵族会随身绣个槟榔荷包来装槟榔。
另外,从各地竹枝词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槟榔的分布,如《电白竹枝词》“篓叶青青香正好,送郎灰蘸裹槟榔”、《南台竹枝词》里“十五盈盈羞择婿,翠槃无语饷槟榔”,这些都跟婚姻有关系。《福州竹枝词》“君爱城居我住乡,闲时过我吃槟榔”、《珠江竹枝词》“依去西江郎北江,江水未如侬意长。相约思贤滘前泊,共擎藤盒吃槟榔”,描述了用藤盒来装槟榔的情景。《韩江棹歌》“聘妇寻常礼数能,槟榔蒟叶代金缯”、《粤西竹枝词》“一盒槟榔代聘银,倩媒说合娶新人”,说明槟榔可成为聘礼。《桂林竹枝词》“送得槟榔红颗颗,小姑已许嫁彭郎”、《台湾杂咏》“相逢岐路无他赠,手捧槟榔劝客尝”,槟榔还是待客之物。总之,早期吃槟榔的区域比较密集地分布在台湾、海南、广东和广西一带,主要分布区域是槟榔产地或与产地相近的地方。但湘潭是个例外。
四、湘潭槟榔食俗始末
湘潭食槟榔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食俗之始;二是清朝时期(1636-1911):食俗的成型;三是民国时期(1912-1949):变迁中发展;四是建国后(1949-1978):饥饿与稀缺中持续的食俗;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至今):槟榔业之春。
(一)槟榔城——湘潭掠影
湘潭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湘江中下游。现辖湘乡市、韶山市、湘潭县和雨湖区、岳塘区两个城区。全市总面积5015平方公里,2008年末总人口293万(全省人口最少的省辖市),其中市区(两区)面积281平方公里,人口104.3万,城市人口94.6万。湘潭虽不产槟榔,但却是槟榔的主要加工基地。2017年,湘潭从事食用槟榔加工的规模企业30余家,年产量20余万吨,就业人员近30万人,年产值超过200亿元。(30)“槟榔产业:不断壮大的湘潭地方特色产业”,湘潭在线,http://news.xtol.cn/2018/1010/5221335.s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湘潭市中心建设路口竖立着高31.5米的橄榄型城市雕塑,很多人解释中间竖着的是槟榔,还有四个高3.5米的仙女雕塑递槟榔给客人尝(其实是莲子),在湘潭举办省运会开幕式也有人化妆成槟榔的形象,可见槟榔在湘潭的象征意义。湘潭槟榔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采购鲜果、鲜果制作到制成产品再销售出去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湘潭槟榔的传播早已不局限于湖南。2014年我在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山前镇、2015年我在西双版纳、老挝等地做田野调查时,都发现众多销售湘潭槟榔的商铺。现在全国各地基本都能买到湘潭加工生产的槟榔。
湘潭吃槟榔的习俗应始于明末清初。到清朝,吃槟榔的习俗可能才开始成型,民国时期得以发展。解放后出现一些波折,有一段时期湘潭人饭都没得吃,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难吃到槟榔,因为那时湘潭与海南的贸易联系断了,缺乏生产槟榔的原料。我记得当时吃槟榔还要去找副食品公司领导批条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每户才分一点点。改革开放后,海南岛农民开始自己种槟榔树,过去很多地方把槟榔树砍掉种橡胶树,现在又重新种回槟榔树。海南岛五指山市通什镇属于五指山的腹地,是槟榔树最多的地方。那里就有很多经营槟榔的湖南人,通什周边的一圈餐馆全是湘菜馆。我曾做过调查,大量的湖南人在五指山市承包鲜果生意,甚至承包一片片的槟榔林。
(二)湘潭食槟榔的来源
湘潭吃的槟榔来自海南,嘉庆时期《湘潭县志》载:“领表滇黔必道湘沅,则西北滋货往者,亦就湘沅舟运以往。”(31)转引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就是说过去在航运时代,岭南进入贵州、云南的货物都必须经过湘江、沅水。如贵州苗疆走廊的起点就是沅江,沿着沅水而下的舞阳河、清水江等大的支流往贵州腹地走,将贵州、云南与长江水系连通。在元代以前,进入云南的主要通道是从汉中到成都平原再到云南。诸葛亮七出岐山,都是先占汉中,然后再打出去。实际上,元代以后西南通道长江水系就打通了。沅江很宽阔,进入清水江、舞阳河都要换小船。洪江古城就是换船的地方,所以很发达。当时的物资,就是沿着湘江到湘潭。
湘潭在明清两代坐享“小南京”的盛名。乾隆《湘谭县志·风俗》载:“凡粮食、绸缎、 布匹、棉花、鱼、盐、药材、纸张、京广货物,竹木排筏皆集于此,以为湖南一大码头。”城中沿岸商业街区按总划分是湘潭一大特色,各总区域内分布有码头,“城总市铺相连,几二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十九总以下。”(32)转引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页。湘潭码头繁华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因素。湘江从株洲绕过来,绕着湘潭一圈然后到长沙,这样湘潭就像伸出来的半岛。在航运时代特别是木船时代,湘潭一方面沿河适合做港口的地方很大,另一方面特别适合木船的停靠,因此湘潭港口全盛时期就出现了从一总一直延伸至十八总。“总”便是码头的管理方式。湘潭也是当时湖南最大的粮食转运基地,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各类商品、粮食、药材均在此集散。历史上清军和太平军都把湘潭作为争夺的战略要地。
长沙未开埠前,湘潭曾是湖南区域贸易体系中的重镇。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中曾提到“湘潭和广州两地之间的陆路运输量极大,至少有十万脚夫跨越南风岭在这条路上掮运货物。”(33)容闳 :《西学东渐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这实际上就为广东食槟榔的习俗传播至湘潭创造了条件。再加上明清时期湘潭是各类商品、粮食、药材的主要集散地,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人口伤亡带来的饥荒或瘟疫,便很容易在湘潭民间社会将既能入药抵御瘟疫又方便食用的槟榔直接联系在一起,为槟榔在湘潭民间社会的传播奠定基础。因此,在湘潭槟榔起源的民间传说中,瘟疫说和市场说是目前学界引用最多的两类观点。
(三)湘潭槟榔起源传说
第一种说法是战乱瘟疫说。这是流传最盛、记载最多的一种传说,此说的起源时间分别有顺治元年、顺治六年与乾隆四十四年三个版本。相传顺治元年清兵于湘潭大肆屠杀,持续十余日,尸横遍城,不下十万,后“有老僧收白骨,以嚼槟榔避秽”;(34)湘潭文史资料委员会 :《湘潭文史》第十二辑,湘潭:东坪印刷厂1995年,第148页。顺治六年反清复明,一位将军在湘潭起兵,发生战争又死了很多人,一老和尚将口嚼槟榔避疫之法教给一位来自安徽的程姓商人,商人依此法在城中收尸,而后他于湘潭安家,也将嚼槟榔习俗延续下来;乾隆四十四年则“居民患臌胀病,县令白璟将药用槟榔劝患者嚼之,臌胀消失。尔后嚼之者众,旧而成习。”(35)《湘潭市志》第一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第二种说法是药材市场说。我认为市场的因素更重要。明末清初,湘潭作为湖湘地区最大的药材和商品集散中心,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供货商,有“药不到湘潭不齐,药不到湘潭不灵”的说法。药商带来的药材槟榔开始在湘潭流行,因为不断地有商人从海南、广东、广西通过南岭走廊进入湘江并在湘潭转运商品,因此商贸移民带来了食槟榔这一习俗。如光绪版《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记载:“批发行店林立,零售五步一桌,合面相向,岁交易额在200万以上。”其时,槟榔业务由广、西、本三帮控制,经营最早的为广东人,称为广帮,多主营字号,资金较大,直接在海口来货。后江西人继起,称为西帮,多营店铺。人数最多的为本地人,称本帮,多数为摊贩。在《湘潭槟榔行情况》一文也提到湘潭槟榔行经营的先后顺序。由于湘潭邻近湘江湿气很重,广东槟榔又有除瘴气、解油腻、祛湿寒等功效,因此在湘潭做槟榔行的最初是广东人经营的“怡和祥”,陆续又开了“怡安祥”“怡顺祥”,后来江西人开了“刘洪兴”,湘潭人也开了“曾兴和”“潘时茂”“李同义”。(36)原载于《大公报》,长沙 :《省城槟榔业调查记》,1919年11月9日。
第三种说法是风水说。据传一个风水先生来湖南看风水,到了湘潭他说湘潭是牛地,而湘乡是马地。话传到皇帝那边,皇帝说湘潭既然是牛,而牛又爱嚼槟榔,便传赐槟榔给湘潭人。而居住在“牛地”的人们果然十分喜爱这种食物。(37)《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湘潭县资料本》,1989年,第254-255页。这种说法认为槟榔食俗是湘潭一带的风水导致。作为对年代和人物语焉不详的风俗传说,其具体时间难以考证。另外,皇帝是如何知道风水先生的话,那位风水先生的话又为何对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牛什么时候吃过槟榔?同样经不起推敲。
第四种说法富有浓厚的想象成分,在槟榔的种植地海南也广为流传。故事中,一位来自湖南的官员被贬至海南万宁,由于情绪低落,他常在槟榔林中徘徊,借酒消愁。一日,他在林中遇到槟榔仙化作的美貌女子,遂结为夫妻。后来,这位官员调任湘潭,时逢瘟疫,槟榔仙发挥法力,将具神力的槟榔果赠予当地民众,食槟榔者无一患病者。因此,湘潭人得以借槟榔仙的神力度过劫难。数年后,官员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而其妻槟榔仙诞下的儿子也学有所成,一举高中状元,在湘潭当地传为佳话。
(四)食俗的形成:从外来槟榔到本地槟榔
湘潭槟榔食俗的形成总体而言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食槟榔能成为一种需求与习俗,且被当地群众广泛接受,战争说和市场说都有一定的道理。槟榔习俗在湘潭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人们食用的主要是药用槟榔,之后嚼槟榔逐渐成了当地人的日常习惯,湘潭地区对作为食品的槟榔有了持续性的需求,槟榔业也由此诞生。比如我长期在广州读书和工作,由于过去商品运输和储存都没有现在方便,曾经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槟榔,后来有了真空包装的槟榔后又慢慢地吃起来,只要不断维持吃槟榔的来源即可。因此,清民时期湘潭槟榔习俗的盛行,侧面反映作为当时湖南主要商品集散地,湘潭与广东等地密切的商贸联系。
湘潭成体系的槟榔业务大体形成于乾隆末年,并在之后不断发展。在这一时期,湘潭槟榔业务的经营形式发展为字号、店铺、胪陈、商贩四种。其中,字号专营大额批发,店铺从字号进货,为胪陈和摊贩提供小额批发,胪陈店与摊贩主要经营零售,摊贩有的自制槟榔,有的也从胪陈店中批发。大宗槟榔生意主要由来自广东的商人经营,后来江西商人实力壮大,也占据了一部分槟榔市场。
乾隆末年槟榔业务的初步成型,至嘉庆年间槟榔习俗出现在嘉庆版湘潭县志中,“士大夫燕客,米取精细,酒重酵娘,珍错交罗,竞为丰腆。一食费至数金,而婚丧为尤甚,至槟榔蔫叶,所口酷嗜。”(38)转引丁世良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92页。光绪年间,湘潭城外沿着湘江的十余里街道上,均是摩肩接踵的行人,热闹的街头随处可见槟榔摊子,“日剖数十口,店行倍蓰焉。”槟榔的零售生意十分红火,“每桌日得百钱之利,日当糜钱五六百万。”(39)(清)陈嘉榆、王闿运 :《湘潭县志》,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438页。槟榔摊子的生意自然要归功于当地人对于槟榔之喜爱。“槟榔之费,拟埒稻粮”。湘潭人买槟榔所用钱竟与购粮所费相近,对槟榔之好可见一斑。
历史上,很多名人都与湘潭槟榔密切相关。如左宗棠与槟榔的故事就在光绪版《湘潭县志·山水》提到:“近岁左文襄赘居妇家,有槟榔之恨,及后富贵,更为美谈。”(40)(清)陈嘉榆、王闿运 :《湘潭县志》,第78页。光绪版《湘潭县志·烈女》提到:“长(女)诒端归湘阴左宗棠,初婚时宗棠贫甚,赉于周,周以其轻脱,未甚礼之。”(41)(清)陈嘉榆、王闿运 :《湘潭县志》,第390页。左宗棠当初屡试不中,于道光十一年应周诒端堂兄周诒煜邀请共读,次年入赘周家为婿。左在读书期间,周母王慈云常许诺诗作最佳者奖以槟榔,周氏姐妹均擅长作诗,左宗棠每居其次不得槟榔,这就是“槟榔之恨”的来历。后左得贤妻相助,奋发读书,终成大业。还有王闿运在北京时,同乡张百熙曾在新年馈赠槟榔给王闿运,王闿运作诗《张野秋馈槟榔》谢之:“蒟叶微辛桂气和,并刀亲剖赤丝窠。为思远物殷勤觅,莫笑长饥乞请多。酒半早看红上颊,海南曾见碧无柯。新年茶罢留乡味,略似含香佩紫荷。”(42)王闿运 :《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702页。槟榔既可作为读书的奖品,也可作为湘人年节互赠表达乡情的佳礼,可见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五)湘潭的槟榔文化
当下的湘潭街头,嚼槟榔的人和贩卖槟榔的摊点随处可见。人们探亲访友必送槟榔,逢年过节在家中备有槟榔待客。新人结婚时,为进门的客人递一根烟、一枚槟榔。老友见面,先敬上一口槟榔。宴席上,“槟榔佩烟,法力无边”“槟榔就酒,越喝越有”的民间俗语层出不穷……关于槟榔的种种习俗显示出其食用的普遍性,在此背景下,进了杂货店却找不到槟榔的踪迹,反成不合常理之事。湘潭已经形成一种槟榔文化,在各类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日常娱乐、社会交往、家庭生活中处处都有槟榔的身影,槟榔已融入到湘潭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更为重要的是,与槟榔产地的食槟榔习俗相比,湘潭早已衍生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槟榔文化体系。
首先,特有的食用标准。湘潭与海南、台湾等槟榔产地普遍食用鲜果槟榔不同,湘潭人多食用干果槟榔壳(很多产地流行吃槟榔核),这种吃法可能是在药物槟榔(方便运输和储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新鲜槟榔摘下后需要在海南等地用火烟熏着色后再运至湖南,用石灰、红糖、桂子等配料制作的卤水进行煮制。早在清民时期,湘潭已在干果槟榔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白槟榔、桂子槟榔、玫瑰槟榔、芝麻槟榔等多个品种,并对碱性过重的石灰槟榔进行了改良(初食者嚼在口里会满嘴起泡),并借助红糖、桂子油、玫瑰油、芝麻、葡萄干、枸杞等辅料,将其改造成了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另外,湘潭人一般将槟榔级别从次到好分为统子、中子、上子和究脑壳。“究脑壳”是极具湘潭语言特色的称谓,也是湘潭槟榔等级划分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代表着质量最好、形状最佳、价格最贵的槟榔类型。
其次,特有的加工技艺。由于湘潭地区特有的干果槟榔食用传统,便衍生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槟榔加工技艺。湘潭槟榔的大致流程为:秋末摘下青果槟榔后需要先用水煮出酸汁,晾干去水后并置于烘灶上用烟熏制,使青果变成乌黑皱皮的干果。湘潭槟榔商户拿到干果后,各家各户会自己制作特有的槟榔卤水,卤水制作涉及生石灰水的熟化、熟石灰水的过滤、石灰水的熬制、饴糖及配料(薄荷、桂子、食用盐、香料等)等基本过程。槟榔商户会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口味以及不同消费层级,有针对性地制作出不同类型的槟榔品种,因此在湘潭大街小巷中随处能看到各类打着自家名号的槟榔摊点,如“牛哥槟榔”“张新发槟榔”“龙少爷槟榔”等。20世纪90年代湘潭槟榔业发明了真空包装和机器加工后,当地槟榔口味才逐渐趋于统一。但目前湘潭仍有上千家自主制造槟榔的家庭商铺,因此湘潭槟榔产业早期雏形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手工作坊逐步发展而来的。
再次,特有的历史记忆。2000年以前,湘潭民众对于槟榔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普通消费品和日常零食的层面上。2000年以后,随着槟榔企业和品牌化的快速发展,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关于湘潭槟榔的文化与历史才开始在民间社会快速传播,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湘潭槟榔产业的发展。例如,湖南皇爷食品公司旗下的槟榔品牌“张新发”,近年来便挖掘出了以张新发为主线的各类历史故事、人物传说和生产技艺等。其门店外观被统一设计为红砖绿瓦式的、极具老字号特色的装饰风格,店内背景墙上显著的“百年张新发”字样也时刻提醒消费者其悠久历史。“张新发槟榔制作技艺”在2014年、2016年还先后入选湘潭市第三批非遗名录和湖南省第四批非遗名录,甚至在宣传中打上湘潭槟榔文化象征的旗号。事实上,近年来湘潭槟榔产业在全国乃至境外的快速传播和品牌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湘潭民众对于本地槟榔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但我们也应正视,湘潭的槟榔文化早已融入了跌宕起伏的城市历史、各具特色的摊铺技艺、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某一类槟榔企业或品牌能轻易代表的。
最后,特有的地域符号。在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商铺中,以“湘潭铺子”“湘潭老字号”为广告的包装槟榔随处可见。历史上长沙、株洲以及湖南各地食槟榔的习俗多以湘潭为中心传播开去,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发现湘潭槟榔产业经历了从最初的外地引入→后期的本地改良→现在的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湘潭槟榔的快速传播,无形中也成为了一种象征湘籍人口地域身份和族群认同的商品符号,比如广东的湖南人数量众多,大家看到嚼食槟榔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她肯定是湖南人或湘潭人。湖南人在全国各地见面时相互递食槟榔的行为,已经变得与熟人递烟一样普遍。2018年,湘潭县政府成立“槟榔办”,对外宣称要“打造中国槟榔文化名城,大力弘扬槟榔文化,扩大湘潭槟榔品牌价值和影响力,确保槟榔产业销售收入三年实现300亿元,五年实现500亿元的目标。”(43)“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槟榔产业发展的意见”,http://xttydz.xiangtan.gov.cn/govxxgk/001001/2018-11-06/d87d9e0c-8e0a-4dd9-9902-d13b968f10d9.html,访问日期:2018年11月6日。可见,湘潭地方政府将地域经济与槟榔产业相互绑定的发展规划,一定程度已预示了湘潭槟榔的商品符号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展演将会愈演愈烈。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槟榔在湘潭从外来食品转变为本地食品的演化过程。研究表明:槟榔文化已经嵌入到了湘潭人的日常生活中,嚼食槟榔作为湘潭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到地域文化之中。这种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食俗已经使槟榔超脱了它本身“物”的属性,使其具有了与人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首先,从实用到象征的转变。湘潭槟榔的起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传说?如瘟疫说、市场说、风水说、仙子说等,其实反映了槟榔功能正在不断变化和丰富的动态过程,人们开始把各种想象融入到了槟榔之中,从实用的物品慢慢变成象征性的符号。湘潭槟榔的演化实际上就经历了这样一种过程。最初的瘟疫说更多的是体现槟榔的实用功能,然后人们才慢慢地把更多美好的思想融入其中,比如高中状元、美好爱情、多子多福等,槟榔起源便有了多个版本的民间传说。人们也逐渐忽略了槟榔本身的实用功能,而在各类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社会交往中将槟榔作为必备用品,其本质是在不同的场域中不断赋予了槟榔新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其次,外来食品的传播逻辑。为什么外地槟榔能够顺利地成为湘潭本地食品?说明了中国自古便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食品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食品都是外来的物种,如玉米、红薯、土豆、辣椒、槟榔等,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对外来的物种、食品,包括文化要素并非一昧地持排斥的态度。当然,外来食品成为本地食品会产生一些变化,槟榔传入湘潭后就变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然后将这一非必需的外来食品发展成了最重要的地方支柱产业。湘潭也借助槟榔将其背后的食俗和湖湘文化传播到了全国乃至国外。槟榔只是我们探索文化传播逻辑的一条线索,如槟榔能在湘潭扎根与传播就离不开早期广东、江西等地移民的融入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移民文化。因此,中国地域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理念以及移民文化在地化融入与创造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要点。
最后,食俗传习的基本脉络。一是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湘潭槟榔在过去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街边零食,但近年来的价格差异变得日益明显,各商家纷纷推出数百元一斤甚至上千元一斤的产品,其价格差异反映了不同阶层的结构差异以及消费分层化的趋势;二是槟榔的文化内涵与成瘾特质。槟榔与香烟一样具有成瘾特质,人们一旦有了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嚼食槟榔后就会很难戒断。尽管医学研究对槟榔有众多负面评价,但是槟榔产业仍然越做越大,槟榔消费人群也在不断增长,因此从槟榔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到成瘾性食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过程;三是饮食和环境的关系。前文提到槟榔具有防瘟疫、提神、促消化、去湿毒等多重功效,因此槟榔是与南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食物;四是外来人口与资本的推力。槟榔在商业资本推动下,能够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食品,无论是清民时期广东、江西等地商业资本的推动,还是目前湘潭规模最大的数家槟榔企业多由外地资本掌控,可以发现资本力量对食品传播的介入与推动;五是从文化接触与文化涵化来看地方社会对异地习俗的选择与接纳。每种地域文化对于食品都有相对固化的选择,如湖南人普遍吃辣的习惯。但辣椒也是外来食品,过去湖南高级宴席是极少有辣菜的,而且普遍是乡下人比城里人吃得辣,收入低的人比收入高的人吃得辣。还有土豆在进入欧洲时各国皇室一直排斥,他们认为土中挖出的植物难以成为餐盘中的食品。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地方社会对外来习俗为什么会进行有选择的接受?因为并非所有外来食品我们都全盘接受,如起司、巧克力等。因此,通过对湘潭槟榔的历史过程分析,很多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深入研究。